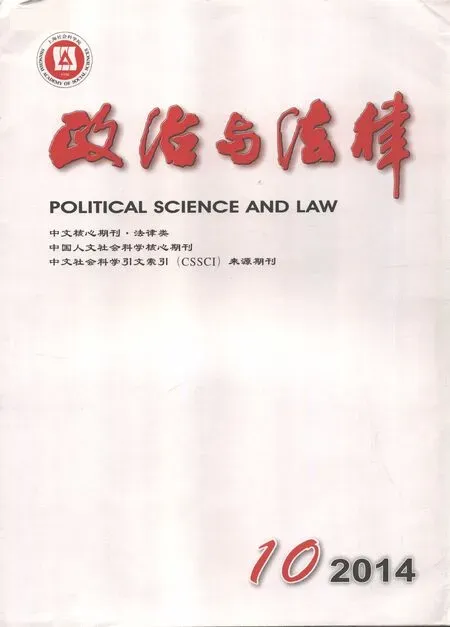“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特殊性辩驳*——从“教育机构侵权责任”展开
韩 强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200042)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的颁行,意味着在我国无论将来是否编纂民法典,侵权责任单独立法的理论已经实现。这一立法例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六章。《民法通则》以专章的形式对包括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在内的各种民事责任作出专门的规定,这一体例被认为是中国民法的重大创新。①参见魏振瀛:《论债与责任的融合与分离——兼论民法典体系之革新》,《中国法学》1998年第1 期;另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的中国特色》,《法学家》2010年第2 期。《侵权责任法》不仅延续了这一体例上的创新,而且在内容上也对传统侵权责任大加扩充,形成了一部包含92 个条文的独立法律。就其整体而论,《侵权责任法》分为两大部分,第一章至第四章为一般侵权责任之规定。所谓一般侵权责任通常认为是以过错责任作为归责原则的侵权责任。第五章至第十一章是所谓特殊侵权责任的规定。决定特殊侵权责任的标志往往是推定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或者所谓的危险责任。②若衡量德国危险责任的范围和我国侵权责任法特殊侵权的范围,我国对特殊侵权责任的界定并非全以危险为标准,比如物件损害责任、医疗事故责任则难以符合危险责任的一般特征。事实上,这一区分标准并未彻底贯彻,在特殊侵权责任的章节中,过错责任的身影也经常出现。如物件损害责任、医疗事故侵权责任中的某些条文都采取推定过错责任,甚至是一般过错责任。
在《侵权责任法》关于一般侵权责任的规定中,第四章“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又是一般规定中的特殊问题,是一般侵权责任与特殊侵权责任的交融地带。比如第32 条的监护人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监护人独立承担“替代责任”,在归责原则上也采取了无过错责任。而同样的问题,在《德国民法典》第832 条第1 款则被规定为过错责任,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7 条第1 款更要求监护人和被监护人负连带责任。除监护人责任之外,《侵权责任法》第四章还规定了另一种比较典型的替代责任“用人者责任”(或称为雇主责任)。监护人责任和用人者责任作为典型的替代责任,其核心是为他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区别于传统的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情形,因此也被称为准侵权行为。③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 页。侵权责任关于责任主体特殊规定中真正具有创新性的,是有关行为失控责任(第33 条)、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第36 条)、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第37 条)和教育机构责任(第38 至第40 条)。这些条文在责任主体上是否有特殊之处,应否有特殊之处,将其归并在一章之中道理何在?对此,民法学界似乎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也缺乏细致的论述。然而,笔者认为,其对于《侵权责任法》第四章的研究十分重要。对第四章的研究不仅仅是个别条文的解释和适用的问题,而是事关整个侵权责任法体系乃至民法体系的问题——特殊规定往往能够说明一般性的问题。本文拟对第四章第38 至第40 条教育机构侵权责任做法律解释上的研究,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反思整个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技术和结构体系问题,尝试为我国民法体系的争论提供一个从微观切入的视角。
一、教育机构侵权责任的调整对象:不法行为的类型界定
《侵权责任法》第四章用三个条文来规范教育机构侵权责任,无论在我国民法历史上,还是从比较法上来看,均属首创。④各国民法未见此类专门性规范,《民法通则》亦未见此类规范。这三个条文系脱胎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0 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 条的有关规定。既为创新性规定,则其作为研究样本的意义无论在立法论上还是在解释论上都非常突出。
教育机构侵权责任所涉及的责任主体有两大类:第一类是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下简称为教育机构);第二类是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以下简称为校外人员)。如果从调整对象来看,我们又会发现三个条文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第38 条和第39 条的调整对象均为在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第40 条则解决在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情况。为叙述方便,姑且将这两种情况分别概括为“受到校内人员损害”和“受到校外人员损害”。
(一)关于受到校内人员损害
《侵权责任法》第38 条和第39 条在调整对象的界定上采取的是一种时空概念,即“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这里的时间概念是在学习、生活期间,而空间概念则是在教育机构之内。从时、空两个维度加以判断,这就决定了致损情形的多样性。结合实践经验,我们可以认定受到校内人员损害的情形应有如下三种。
其一,是单纯由教育机构原因造成的损害。这里的致害原因主要包括教育机构本身的行为、教育机构工作人员的行为,以及教育机构的物件设施造成在校未成年人损害的情形。比如,学校对学生实施纪律处分但未及时通知其监护人,结果学生因羞愧而自杀;⑤参见“李建青、宋宝宁诉青海湟川中学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第4 期。学校教师体罚学生,造成学生人身伤害;⑥陆士桢主编:《未成年人保护手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2 页。教室突然坍塌造成学生受伤。⑦李克、宋才发主编:《未成年人保护案例》,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 页。表面上,这三种情形都应包括在第38 条和第39 条的调整范围之内。然而,关于教师行为致害的情形,在《侵权责任法》第34 条的用人单位责任中已经得到调整;而关于物件损害的问题,可以适用《侵权责任法》第85 条关于物件保有人责任的规定。如此一来,关于单纯由教育机构原因造成损害的情形中,真正具有独立规范价值的仅为教育机构行为致害一种。当然,此种行为是否就真的具有独立规范价值,下文仍将继续讨论。
其二,是由校内其他学生造成的损害。在第38 条和第39 条所划定的时空界限内,由校内其他学生造成的损害似乎也应包含在其中。对此,有学者指出,第40 条所谓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应指在教育机构学习、生活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外的人。⑧程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59 页。这就意味着在教育机构内学习、生活的未成年人之间互相加害的情形,适用第38 和第39 条。但这样一来,会产生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因为上述两个条文是按照受害人的行为能力来设定不同的归责原则的(这一做法本身也值得讨论,下文将做展开),如果11 岁的学生加害9 岁的学生就适用第38 条,而如果9 岁的学生加害11 岁的学生则适用第39 条。显然,这两条的区别不仅在于责任主体的范围上,更在于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根据权威意见,第38 条适用推定过错责任,而第39 条适用过错责任。⑨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11 页。于是,从教育机构应更加有力地保护受害人的角度,学校对于9 岁的受害人应比对于11 岁的受害人负担更重的证明责任,而从教育机构应更加周密地监管加害人的角度,学校对于9 岁加害人的管理义务反倒比对11岁加害人的管理义务更轻。尽管本文所讨论的仅为一假设之情形,但由此发现了第38 条和第39 条之中蕴含着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逻辑矛盾。这一逻辑矛盾的成因不仅仅是两个条文采取不同的归责原则,更是与其调整对象有关。关键的问题在于:教育机构是否应对未成年学生致人损害的行为负责?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很少有国家法律明确规定要求教育机构对未成年学生的致害行为负责。⑩[德]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卷),张新宝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 页。《德国民法典》第832 条第2 款规定,根据合同承担前款监督义务的人也负同样的责任。有疑问的是,通过合同承担监督义务具体指何种情形?在德国司法实践中,幼儿园、私立学校、寄宿制学校等都被认为属于通过合同承担监督义务的责任人。Erman/Bearbeiter, BGB, 12. Auf., §832 Rz5. 相应地,《日本民法典》第714 条第2 款应作同样解释。参见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90 页。更有学者明确指出,教育机构侵权责任是对在校学生等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责任,而不包括在校学生等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⑪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0 页。
由此引起讨论的问题是:第38 条和第39 条所规定的是所谓“替代责任”还是“自己责任”,抑或两者兼有?据上文所述,教育机构对自己行为所引起的损害负责,固然是典型的自己责任,而对在校、在园未成年人相互间造成损害的情形,上述两个条文也没有明确排除教育机构负责的可能。教育机构承担责任的基础在于学校、教师管理不当引发学生人身伤害。⑫刘士国等:《侵权责任法重大疑难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 页。又由于教育机构对未成年人不负有监护义务,也就不存在承担替代责任的可能。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 条规定的替代责任,在侵权责任法中被排除了。⑬参见马特:《照猫画虎还是画蛇添足:“草案”中的校园事故责任》,《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8 日第007 版。如果这种理解是正确的,那么第38 条和第39 条就仅仅是关于教育机构自己责任的规定,其特殊性无非是第38 条采推定过错而已。然而,这两条作为“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有何特殊性,令人疑惑。如果参照法国的立法例,认为教育机构为其管理下的学生的加害行为负责也属于替代责任,倒符合关于责任主体特殊规定之本义。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教育机构被归责的根据何在?在法国法上,显然是因教师自身的过错。⑭《法国民法典》第1384 条第6 款规定:“小学教师与家庭教师及手艺人,对学生与学徒在受其监视的时间内造成的损害,负赔偿之责任。”第8 款规定:“涉及小学教师与家庭教师时,其受到指控的造成损害事实的过错、轻率不慎或疏忽大意,应由原告按照普通法于诉讼中证明之。”关于此点,下文也将做进一步的研究。
其三,是由于受害人自身行为或者自然事件引起的损害。受害人自身从事危险行为并导致其遭受损害的情形,如未成年学生攀爬到窗外消防平台捡试卷不慎摔伤;⑮(2013)浙丽民终字第158 号民事判决书。除人为原因加害造成未成年人损害的情形外,自然事件导致的人身损害情形也较为多见,如学生在体育运动中突发心脏病导致死亡。此种损害在时空观念下亦可落入“在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损害”的范畴,教育机构是否对此负责,则取决于教育机构是否违反由教育、管理职责所产生的注意义务。
(二)关于受到校外人员损害
《侵权责任法》第40 条的调整对象是未成年人受到校外人员损害的情形。界定此类损害首先应确定校外人员的范围。有学者认为,所谓“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是指排除以下两类人员后的人员:其一,教育机构的工作人员,如教师、职工等;其二,在教育机构学习、生活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⑯同前注⑧,程啸书,第359 页。做出这一范围划分的关键就是要将校内未成年人之间相互伤害的案件,排除在第40 条的适用范围之外。
仔细研究《侵权责任法》第38 条、第39 条和第40 条的文义,可以发现其对教育机构注意义务的规定有显著区别。第38 条和第39 条将其规定为“教育、管理职责”,第40 条仅规定为“管理职责”。显然,所谓教育职责所指向的对象应是在教育机构内生活、学习的未成年人,而管理职责的对象可以包括对校外人员的管理。从这一表述上的差异可见,第40 条不调整教育机构内未成年人相互伤害的案件。这也符合立法者的原意。⑰同前注⑨,王胜明主编书,第216 页。此外,从第40 条和第38 条、第39 条相互参照研究来看,当教育机构因未尽到对未成年人的教育职责从而导致学生伤害他人的,教育机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时,加害行为人是未成年人,责任主体却是学校,很难说这不是一种替代责任。否则,这三个条文就不应被规定在“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之中。
需要附带指出的是,当在教育机构内生活、学习的未成年人伤害校外人员时,则不能适用第38条至第40 条的规定,此时只能适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 条的规定。根据这一规定,教育机构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替代责任的意味更加明显。
(三)关于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的法律适用
第38 条至第40 条调整的损害仅限于人身损害,而不包括财产损害。与我国相似,日本的学校事故一般也是指学校教育活动中发生的学生人身伤害事故。⑱牛志奎:《从诉讼案例看日本学校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外国教育研究》2012年第5 期。在法律适用上,在教育机构内生活、学习的未成年人如果遭受财产损害,或者造成他人财产损害的,似乎只能适用《侵权责任法》第6 条以下关于一般侵权责任的规定,或者第32 条关于监护人责任的规定。为何教育机构侵权责任只调整人身损害,而不调整财产损害呢?这一疑问从侵权责任法本身很难找到答案。据笔者推测,《侵权责任法》的三个条文显然系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 条脱胎而来,是对司法解释规定的进一步细化、明确化。但《侵权责任法》的制定者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顾名思义只解决人身损害赔偿问题,不可能调整财产损害赔偿,而侵权责任法上的损害当然应包括财产损害。《侵权责任法》在对不同损害的法律适用上厚此薄彼,缺乏有说服力的解释。对此,有学者认为,《侵权责任法》将教育机构的侵权责任限制在人身损害的情形,是法律漏洞,应通过类推适用的方法将这些规定适用于财产损害。⑲王利明、周友军、高圣平:《中国侵权责任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447 页。从强化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立场出发,《侵权责任法》没有必要对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采取不同的法律政策,从而造成法律适用上的复杂性。因此,笔者也倾向于认为《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存在法律漏洞,通过类推适用的方法解决比较合理。
二、关于归责原则和过错认定——违反管理义务还是保护义务
教育机构侵权责任诸条文的最大特色在于,根据受害人的行为能力,为教育机构设置了不同的归责原则。受害人为无行为能力人的,教育机构适用推定过错责任(第38 条——“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受害人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教育机构适用过错责任(第39 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尽管《侵权责任法》第38 条就推定过错的表述与第6 条第2 款等所采用的推定过错责任的经典表述有所不同,即没有使用“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字样,而是使用了一种恰好相反的语式。立法者如此安排文字表述的原由何在,缺乏可查考的文献与其他依据。也许第38 条的表述旨在突出教育机构对未成年人负有法定的教育、管理职责,并以是否尽到该职责作为判断过错的根据。总之,无论第38 条采取何种文字表述,其采取推定过错责任作为归责原则应是确定无疑的。至于区别受害人的行为能力采取不同的归责原则,赞同意见认为无行为能力人无法清晰地描述事发过程,如果要求无行为能力人或其监护人来证明教育机构的过错,显然是有困难的。无行为能力人的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非常低,应要求教育机构尽到更高度的注意义务。⑳同前注⑨,王胜明主编书,第209 页。反对意见则认为,单纯以行为能力分配证明责任,难免畸轻畸重,殊无必要。㉑同前注⑬,马特文。若以立法论的立场言之,《侵权责任法》区分受害人行为能力设置不同的归责原则,似乎意在强化未成年人保护与教育机构举证责任负担上谋求平衡。然而,这一平衡却可能面临两头不讨好的尴尬。而且,以受害人行为能力决定不同的归责原则,给人一种法律政策不清晰、不一贯的印象。
总体而言,教育机构侵权责任采取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包括推定过错责任),因此,《侵权责任法》也未将其列入特殊侵权责任范畴。既然采过错责任原则,如何认定教育机构的过错便至关重要。《侵权责任法》第38 条和第39 条明确规定了教育机构所负担的注意义务是“教育、管理职责”,这一注意义务是对未成年人在教育机构内受到损害而言的;如果未成年人受到校外人员伤害,则此时法律要求教育机构尽到管理职责。如前文所述,所谓教育职责显然只能以学生为对象,而且在《侵权责任法》意义上,这一教育职责更多地应该指向加害学生,即学校没有很好地教育、约束加害学生,以至于该学生对他人实施了加害行为。㉒所谓教育职责,主要包括对未成年人的各种安全教育,如增强危险意识、加强自我保护、注意卫生安全、掌握救助逃生技能等。参见奚晓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277 页。因此,认为教育机构侵权责任具有替代责任属性的观点,其根据正在于此。而所谓管理责任则宽泛得多,举凡教育机构对其教职员工的管理、对校舍设备的管理、对治安保卫的管理、对食品安全的管理等等,都可纳入教育机构管理职责的范围。教育机构侵权责任是过错认定标准客观化的典型例证,即法律不再简单地规定加害人应具有过错,而是直接将认定过错的标准即违反相应注意义务明确规定出来。这样的规定既为法官裁判提供了明确依据,也为教育机构提供了清楚的行为模式指引。
当然,《侵权责任法》的这三个条文较之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 条,在认定过错的标准上进行了更为精细的、区别化的处理,但这一处理是否有意义,仍然值得讨论。立法者在第38 条和第39 条中将教育机构的注意义务设定为“教育、管理职责”,而在第40 条中仅表述为“管理职责”,显然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抛开教育机构对加害学生的教育职责可能会引起替代责任的争论不谈,单就管理职责而言,其与过错一样地抽象,并无特别明晰之处。如此一来,《侵权责任法》就教育机构侵权责任设置了三个条文,在归责原则上进行了区分,在过错认定标准上进行了细化,在责任性质和调整范围上也试图重新作出界定。然而,其结果却是:归责原则的区分并无法律政策上的坚强理由;管理职责的提出没有起到明确过错认定标准的作用;教育职责的存在又引起了教育机构侵权责任是自己责任还是替代责任的争论。在没有立法理由书明确阐释立法原意的背景下,对法律条文的任何一种解释似乎都难以取得压倒性的优势;而《侵权责任法》在立法技术上的种种弊病,又进一步加剧了法律解释上的混乱。从《侵权责任法》将教育机构侵权责任放置在“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一章中的做法看,我们推测教育机构应为加害学生承担替代责任,否则责任主体毫无特殊性可言。㉓最高人民法院的研究观点似乎也认为,教育机构侵权责任中包括自己无不当行为的情形。参见前引奚晓明主编书,第291 页。但众多学者又强烈主张教育机构侵权责任仅为自己责任,是对受害学生承担责任,不是替加害学生承担责任。其实,杜绝此争论仅需在立法技术上稍作调整即可。如果立法者确无设置替代责任之意,那么,首先,应将教育机构侵权责任移出《侵权责任法》第四章;其次,明确教育机构对未成年人所负注意义务并非什么教育、管理职责,而是保护义务。㉔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 条第1 款就列举了保护义务,值得注意。如果将保护义务作为衡量过错的核心标准,则一切争论将化于无形。㉕中学生在上体育课期间因练习跳箱运动而摔伤。法院审理认为体育教师无论在示范指导上,还是在运动中的保护上,以及在事发后的救助处置上均无不当之处,判定学校对受害人之损害无过错。见(2013)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200 号民事判决书。本案中,法院衡量学校有无过错的核心其实就是看学校是否尽到保护义务。在德国法上,监督人责任也是交往安全保障义务具体化的一种表现形式。㉖Larenz/Canaris II 2 § 76 III 3c.显然,保护义务仅能针对受害人发生,无论加害行为来自校内还是校外,教育机构仅因其违反保护义务而对受害人负责,其自己责任的属性至为明显,无复争论之余地。㉗参见前注1○,张新宝书,第192-193 页。而且,从比较法最新的研究成果来看,为他人承担责任正逐步摆脱间接责任的论证路径,在归责价值判断层面体现为针对受害人的直接责任。㉘朱岩:《侵权责任法通论·总论》(上册·责任成立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33 页。
三、教育机构侵权责任与其他侵权责任的竞合关系
法典乃法律规范的逻辑体系,而非法律规范的简单组合,这是所谓法典编纂和法律汇编的区别,也是大陆法系侵权法典与美国侵权法重述之间的区别。毫无疑问,《侵权责任法》是符合大陆法系传统的法典,而非英美法系的法律重述或者示范法。既为法典,则法律条文之间必因分工而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各法条均应有其特定的调整范围,法条之间在调整范围上一般也不应交叉重叠。虽然在法典化之下法条竞合现象难以避免,但多为偶然现象,并非常态。纯粹由于立法技术的原因所造成的法条竞合,在立法之时就应竭力避免,否则法典化的价值必将大打折扣。但是,教育机构侵权责任作为《侵权责任法》独创的全新条文,却与众多传统侵权责任条文发生了竞合关系。此时,必须以立法论的立场思考这一现象:既然一组新条文与众多旧规范发生竞合,那么制定新规范的意义何在?而且,本文所研究的法律规范竞合基本上都发生在同一部法典之中,这一现象更加引人深思。
(一)教育机构侵权责任与物件损害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85 条和第86 条分别规定了物件保有人责任和物件设置人责任,其中保有人责任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搁置物、悬挂物脱落、坠落致人损害为主要形态,设置人责任则以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致人损害为主要形态。在教育机构侵权案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案件与物件致人损害有关。在此类案件中,教育机构基本上也都构成第85 条、第90 条和第91 条上的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或者第86 条上的建设单位。当教育机构的校舍发生脱落、坠落,甚至倒塌致使未成年人受到人身损害的,《侵权责任法》第38 条、第39 条与第85 条、第86 条等条文将发生竞合关系;而教育机构管理下的树木、地下窨井等设施致人损害的,也会与第90 条和第91 条发生竞合。㉙学校移植的柳树突然倾倒将学生砸伤,见(2013)沪民初字第00550 号民事判决书。此时与教育机构侵权责任存在竞合关系的是《侵权责任法》第90 条“林木折断损害责任”。关于在《侵权责任法》内部发生条文竞合应如何处理,该法并未作出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122 条关于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的规定能否适用于此,仍有疑问。
比较两类责任,不难发现物件损害责任比教育机构侵权责任在法律政策上更为优越。物件保有人责任(第85 条)的归责原则是推定过错责任,物件设置人责任(第86 条)则采无过错责任,而教育机构侵权责任针对无行为能力人不过是推定过错责任而已,针对限制行为能力人则仅为过错责任。可见,同一侵害事件因选择适用的法律条文不同,其法律效果可能会有重大区别。而号称强化未成年人保护的教育机构侵权责任,却未比一般物件损害责任来得有力,这不得不让我们对最初的立法设计产生质疑。
既然《侵权责任法》未对请求权竞合作出任何规定,我们也只能再次将目光投向合同法第122条,这毕竟是我国制定法上关于责任竞合的唯一规定。依通说,合同法第122 条采请求权自由竞合说,㉚参见崔建远主编:《合同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12 页。但也有观点认为该法第122 条采请求权规范竞合说,参见朱广新:《合同法总则》(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42 页。即权利人在请求权出现竞合时可以自由选择一项请求权行使,另一项请求权随之归于消灭。如果在《侵权责任法》内部类推适用合同法第122 条的规定,受害人也可以自由选择请求权基础:教育机构侵权责任或者物件损害责任。由于两类责任在归责原则上的显著差异,受害人的选择将直接影响证明责任分配,这对于当事人而言具有重大的诉讼利益,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诉讼风险。如果法官放任受害人自由选择,无异于将诉讼风险分配给未必精通法律的受害人,此点在法律伦理上也大有可议之处。于是,为纠正请求权自由竞合说之弊,在德国法上便发展出所谓“请求权相互影响说”来加以匡正。请求权相互影响说以请求权自由竞合说为基础,强调产生于不同基础的请求权独立存在,但可相互影响。原告选择某一请求权的同时,仍可主张其他请求权上对其有利的规定。㉛参见王泽鉴:《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之竞合》,载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5 页。如果我们在教育机构侵权责任和物件损害侵权责任的竞合上也引入请求权相互影响说的观点,则无论受害人选择哪一个请求权,都能享受到法律赋予他的最大优惠,避免因当事人选择不当而造成的不适当结果。
如果我们在教育机构侵权责任和物件损害责任竞合的问题上采取所谓“法条竞合说”,㉜前引王泽鉴文,第353 页。即认为物件损害责任系特殊侵权责任规范,而教育机构侵权责任系一般侵权责任规范,两者在竞合的情况下,特殊规范优先适用,则上述疑惑便也不致发生。但如此一来,教育机构侵权责任被独立规定的价值又有所降低。
(二)教育机构侵权责任与一般过错责任
学校自身行为导致未成年人人身损害的情况也不少见,如学校食堂未能确保食品安全致使学生食物中毒,㉝(2003)惠中法行初字第3 号行政判决书。学校运动设施不符合安全标准导致学生受伤等。㉞(2012)安白民初字第219 号民事判决书。上述情形均可涵盖在第38 条和第39条之内。通常情况下,这些加害行为也完全符合《侵权责任法》第6 条以下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唯一不同的是第38 条针对无行为能力受害人采取了推定过错责任。另外,第40 条前段关于未成年人受到校外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也属于一般侵权责任的范畴,在构成要件上应以第6 条为依据,而不能因其未强调过错字样就被断然认定为无过错责任。当教育机构的行为或者校外人员的行为造成未成年人人身损害的时候,多数情况下都符合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要件。虽然按照法律适用的规则,特殊规范具有优先适用的地位,但《侵权责任法》第39 条和第40 条前段与作为一般规范的第6 条实质相同,其仅为形式上的特殊规范而已,并无真正的特殊性可言。其只不过将教育机构侵权责任单独凸显出来,除了具有某种宣示意义外,并无法律作用上的实益。
(三)教育机构侵权责任与其他替代责任
如前文所述,对第38 条和第39 条的一个重要争论是教育机构侵权责任是否也构成一种替代责任,即教育机构为未成年人的加害行为负责。尽管笔者在应然的角度也不赞成替代责任说,但法条却为替代责任说保留了存在空间,而且替代责任说也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 条一脉相承。姑且承认教育机构侵权责任作为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也是替代责任,那么,《侵权责任法》第四章中还规定了监护人的替代责任(第32 条)和用人者的替代责任(第34 条、第35 条)。如果说教育机构对未成年人的替代责任尚有争议的话,那么教育机构对其教职员工的替代责任则毫无争议。在同一章节中,条文之间的竞合关系再次出现,如何协调法律适用的问题不能回避。
《侵权责任法》的监护人责任基本上延续了《民法通则》第133 条第1 款的规定。我国民法对于监护人责任的规定与传统民法也有所不同。《德国民法典》第832 条第1 款后段规定监护人尽到监督义务的,则不负赔偿责任;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7 条还规定以被监护人有识别能力为限,与监护人负连带责任。相较于传统民法,我国监护人责任既无连带责任之规定,也无免责条件之规定,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仅能减轻责任。由此看来,我国监护人承担的是一种近乎绝对责任的替代责任。㉟王利明、周友军、高圣平:《侵权责任法疑难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278 页。其责任之严格,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侵权责任法中非常罕见。㊱监护人责任在绝大多数国家都体现为过失责任,只有法国法将监护人责任规定为无过错责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国的监护人保险制度极为普遍。同前注㉘,朱岩书,第442 页。当未成年人在教育机构控制之下侵害其他未成年人的时候,受害人可以根据第32 条追究监护人的责任,也可以根据第38 条、第39 条追究教育机构的责任。显然,监护人责任比教育机构责任更为严格,对受害人有利。问题是:此时请求权之间能否相互影响呢?笔者认为不能。请求权相互影响应以在同一对主体之间发生多个请求权的情况下方可适用,意在纠正因法律选择不同而造成法律效果的差异。当请求权针对不同主体发生时,法律因对不同主体区别对待而往往有不同规定:毕竟教育机构不承担监护义务,㊲监护人将未成年人送入教育机构并非委托监护,除非另有约定。《侵权责任法》也仅仅将教育机构的注意义务定位于教育、管理职责,而并非监护职责。因此要求其承担过错责任是合适的,受害人不得援引监护人责任的规定影响其对教育机构的请求权。
此外,仍有疑问的是:受害人能否将监护人和教育机构列为共同被告,在实体法上两者是否构成共同侵权?㊳(2013)沪二中少民终字第16 号民事判决书。有观点认为,在无行为能力人相互造成损害的情况下,监护人与教育机构应向被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请求权基础在于《侵权责任法》第11 条。㊴同前注⑧,程啸书,第360 页。在《侵权责任法》上,一般侵权责任的规定中可能产生共同被告的规范有如下几类:共同侵权行为(第8 条和第9 条)、共同危险行为(第10 条)、原因竞合侵权行为(第11 条)、原因聚合侵权行为(第12 条)。第8 条共同侵权行为要求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关于共同实施的认定以主观说为通说,即要求多数行为人具有意思联络,或曰共同过错。㊵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28 页。必须根据第38 条和第39 条认定过错后教育机构始可承担责任,而监护人根据第32条无论有无过错都须负责且不能免责,如此,两者之间难以认定共同过错。究其根本,教育机构侵权责任仍是过错责任,其归责根据在于对责任人主观状态的否定性评价,而监护人责任是出于身份关系,甚至有观点认为被监护人具有不可避免的人身危险性,此种责任已经接近于危险责任。㊶参见前注,朱岩书,第442 页。当然,此结论系立足于《侵权责任法》之规定,在传统民法上监护人责任仍为过错责任的情况下,结论或有不同。同样,教育机构和监护人也不可能构成共同危险行为,此点至明,毋庸赘言。《侵权责任法》第11条和第12条均调整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的情形,所异者在于第11条要求每个侵权行为足以独立致害,而第12条下的每个侵权行为不能独立致害,必须结合之后方能导致全部损害。严格言之,教育机构的过错行为无论表现为作为或者不作为,仍属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监护人基于其身份关系替被监护人的行为负责。从导致损害发生的原因力关系来看,被监护人的加害行为是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也不是唯一原因;如果教育机构善尽教育、管理职责,则有可能阻却损害结果的发生。因此,教育机构的不作为与加害人的作为便构成所谓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㊷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比如,在未成年学生某甲因相互斗殴而用刀将某乙刺伤的案子中,某甲的加害行为与教育机构未尽教育、管理职责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某乙的损害,两者的行为均对损害结果贡献了一定比例的原因力。此时,《侵权责任法》第12条的规定恰好可以发挥作用。事实上,实践中法院也正是根据案件各方当事人的过错比例判决承担按份责任。㊸(2013)焦民二终字第00041 号民事判决书。
《侵权责任法》第34条规定了用人单位责任,其与传统民法的雇主责任都属于典型的替代责任,但也存在很大的不同。我国用人单位责任在归责原则上采无过错责任,而传统民法关于雇主责任多采推定过错责任,㊹如《德国民法典》第831 条第1 款、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8 条第1 款。但晚近以来,关于雇主责任也有严格化之趋势。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8条第1款还要求雇主与雇员负连带责任。如前所述,教育机构侵权责任中有相当一部分比例是为教职员工的行为负责。此时,教育机构与其教职员工之间无论是否构成劳动合同关系,其“用人单位”和“工作人员”的关系是必然成立的。㊺况且,《侵权责任法》第34 条也并不以成立劳动合同关系为构成要件,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都能适用,构成国家赔偿责任的除外。参见前注⑨,王胜明主编书,第170-171 页。于是,当教育机构的教职员工在执行工作任务期间实施侵权行为造成未成年人人身损害的时候,受害人也面临两项竞合的请求权。而且,教育机构侵权责任以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而用人单位责任以无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立法者所宣称的通过教育机构侵权责任强化未成年人保护的目的,再次轻而易举地被其他法条所超越,创设此等新条款的价值未免再受质疑。
(四)教育机构的相应补充责任与全部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40条对教育机构侵权责任规定也属异类。其第一句规定未成年人受到校外人员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这一规定本系一般侵权责任,即使不做规定也并无不妥;第二句规定教育机构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一般认为,相应的责任系指与加害人过错相适应的按份责任,补充责任则意味着在校外人员不能承担责任的范围内由教育机构承担第二顺位的按份责任。㊻同前注㉒,奚晓明主编书,第297 页。但相反意见认为,所谓相应的补充责任仅指教育机构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按份责任,此“补充”
一词实为赘文,不具有规范意义。㊼曾大鹏:《第三人侵害学生事故中的学校责任》,《法学》2012年第7 期。
该条规定与第37条第2款(场所管理人责任)的规定在法条结构和立法思想上完全一致,其作为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在于创造了所谓的“按份补充责任”。如果说,在第38条和第39条之中,教育机构出于对未成年人和教职员工的特殊关系还可以承担替代责任的话,那么教育机构对于校外人员则无任何承担替代责任的理由。校外人员与教育机构一开始就只能立于共同侵权的层面来讨论其责任关系,即要么构成共同侵权,要么不构成。立法者之所以在第40条中连续使用“相应的”、“补充”两个定语限制教育机构的责任,本意在于减轻教育机构的负责压力。㊽同前注㉒,奚晓明主编书,第297 页。但问题是:教育机构所可能承担的相应的责任是按份责任还是全部责任?比如,学校门卫放任陌生人员进入学校,后该人员在校内伤害未成年人,且保卫人员未对受害人给予必要的保护,事后施救也多有瑕疵。㊾日本的池田小学事件即属于此种情形。2001年6月8 日上午10 时左右,被告宅间守携带装有两把菜刀的塑料手提包,来到大阪教育大学附属小学,企图从学校正门进入学校作案,但正门关闭,于是被告从学校机动车辆出入专用口进入学校,并进入一楼的教室砍杀,造成23 名师生伤亡。参见前注⑱,牛志奎文。在此种案件中,学校的过错对于损害结果而言究竟具有部分原因力还是全部原因力至关重要。并且,不论学校过错的原因力如何,只要认定学校存在过错,则此种情形与第38条和第39条所调整的学校独立负责情形又有何不同呢?前已述及,第38条和第39条的主旨思想在于确立教育机构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义务。只要未成年人在教育机构控制下受到伤害,就要检讨教育机构保护义务的履行状况。如确定教育机构未履行保护义务,则认定其有过错。至此教育机构责任成立的构成要件已经满足。接下来便是审查责任范围问题。而任何过错行为对于损害之发生都存在特定的原因力比例,此种比例便是责任范围因果关系问题。㊿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184 页。也就是说,即使在第38条和第39条中,教育机构也未必一律承担全部责任,而有可能根据原因力比例承担部分赔偿责任。比如,学生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学校知情但未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后学生在体育课上猝死。此类案件,根据第38条或者第39条也只能要求教育机构承担部分责任,而不是全部责任。[51](2011)綦法民初字第1866 号民事判决书。因此,教育机构最终是承担全部责任还是部分责任,端视其过错行为的原因力而定。第40条将教育机构责任一律限定为相应的责任,给人以教育机构只能承担部分责任的错觉,殊为不当。在日本发生的池田小学案件中,由于侵害人被判处死刑,受害学生家长与日本文部科学省达成《和解意见书》。因池田小学系公立学校,故由文部科学省赔偿受害人家属共计4亿日元。[52]参见前注⑱,牛志奎文。此时,文部科学省承担的已然是全部责任了。至于补充责任在赔偿顺位上对教育机构是一种优惠,也是中国侵权责任法的独创,但其在逻辑上与按份责任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53]参见前注㊼,曾大鹏文。在实践中效果如何也不得而知。因此,第40条除补充责任是一项有争议的创新之外,其他内容并未超出第38条和第39条固有的法律效果。
(五)教育机构责任独立性根据不足
通过法律解释学的分析可知道,将教育机构侵权责任放置在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中名不副实。尽管《侵权责任法》第38条和第39条没有排除教育机构承担替代责任的可能,而且只有承担替代责任似乎才符合特殊责任主体的本意,但教育机构侵权责任根本上仍应是自己责任、过错责任,而不应具有替代责任的性质。教育机构无论系公立还是私立,也不论其规模和层次,都不承担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义务。关于监护义务的安排,《民法通则》已有明确规定,[54]《民法通则》第二章第二节“监护”和第133 条“监护人责任”共同构成我国监护制度的基本框架。《侵权责任法》无权加以改变。那么《侵权责任法》能否创造出一种针对教育机构的替代责任呢?在笔者看来,产生替代责任的理论根据无非是风险—收益理论、报偿理论或者深口袋理论等。这些脱胎于雇主责任的理论,无法套用于教育机构之上。而《侵权责任法》也并未就教育机构承担替代责任提出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因此,应摒弃教育机构侵权责任是替代责任的观点。如此一来,教育机构侵权责任在《侵权责任法》第四章之中便再难以立足。
四、结语:不得不回到立法论的立场
与教育机构侵权责任相类似的还有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第37条)。此种侵权责任在责任主体方面并无特殊之处,在归责原则上也是一般的过错责任,[55]陈现杰:《中国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精义与案例解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30 页。而且《侵权责任法》也规定了所谓的相应的补充责任。鉴于两类侵权责任的相似性,似乎可以考虑将第38条、第39条与第37条合并为场所管理人责任。而教育机构作为一种特殊的场所管理人,可强调其对学生(不限于未成年人)的保护义务,在针对未成年人时如需适用推定过错责任,可以考虑单独设立一款;第40条则可以与第37条第2款合并。鉴于此种责任是针对各类公共场所管理人自身过错的责任,应将此项规定整体移出《侵权责任法》第四章,放置在第6条以下,明确其一般侵权责任条款的地位。另外,将其明确为一般责任条款还可以解决与其他特殊责任条款之间的适用关系问题,以消除请求权竞合带来的困扰。当教育机构侵权责任与用人单位责任、物件损害责任出现竞合时,特殊条款优先适用。
由教育机构侵权责任出发,推及《侵权责任法》第四章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笔者发现其特殊之处甚少,独立设置一章缺乏根据。尽管有学者指出,第四章的条文都是关于责任主体与行为人分离、责任主体承担转承责任的情形。[56]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的中国特色》,《法学家》2010年第2 期。但严格来说,该章中只有监护人责任(第32条)、用人者责任(第34条)属于特殊规定,即传统民法上所谓准侵权行为(同时包括物件损害责任)。其他各条在责任主体问题上并无特殊之处。如行为失控侵权责任(第33条)本为一般侵权责任之常见免责情形,完全可以归入第6条以下,至于无过错的补偿责任则可以归入第24条。个人劳务关系侵权责任(第35条)完全可以归入或准用用人单位责任,并无独立规定的必要。网络侵权责任(第36条第1款)尽管颇具时代气息,但仍属于一般侵权责任的范畴(第6条),其在归责原则、过错认定标准上并未提出特殊规则,没有独立规定之必要。[57]当然,对此也有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之间一般不具有侵权的意思联络,且网络一般采取技术中立的态度,因而在判断侵权责任时,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主观要件判断也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立法者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有专门对待之必要。参见杨明:《〈侵权责任法〉第36 条的释义及其展开》,《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3 期。第36条第2款和第3款则属于共同侵权范畴(第8条),[58]参见上注,杨明文。其意义仅在于宣示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依法所应承担的注意义务。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通过立法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并非没有意义,但这一规定与特殊责任主体没有关系,仍然是一般侵权责任、自己责任范围内的问题。[59]张新宝、任鸿雁:《互联网上的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6 条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4 期。至于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第37条)已如前述,也属于一般侵权责任和自己责任,并非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其意义仅在于宣示管理人承担法定安全保障义务而已。就整个第四章而言,只有两个条文(第32条、第34条)属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而且,这些规定也只是责任构成要件中有关责任人的特殊规定,其他构成要件诸如过错等未必当然具有特殊性。如果第四章除该两个条文之外均“文不对题”,则第四章的设置便难以成立。《侵权责任法》第四章的问题显然已经超出解释论所能化解的范畴,惟有将来法律修正之时再做整体性的考虑。
当然,《侵权责任法》第四章的意义也不能被完全抹杀。法律主体对其应承担的注意义务也有一个逐步认知的过程,通过基本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和责任,以及学校等公共场所管理人对于各类场所进入者负担安全保障义务,具有法律宣传和教育的作用,同时也构成对法官裁判案件的明确指引。法典化的价值本身也就在于,不必寻求先例支持或者动辄“向基本原则逃逸”,在法典内就权利义务的安排已经比较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