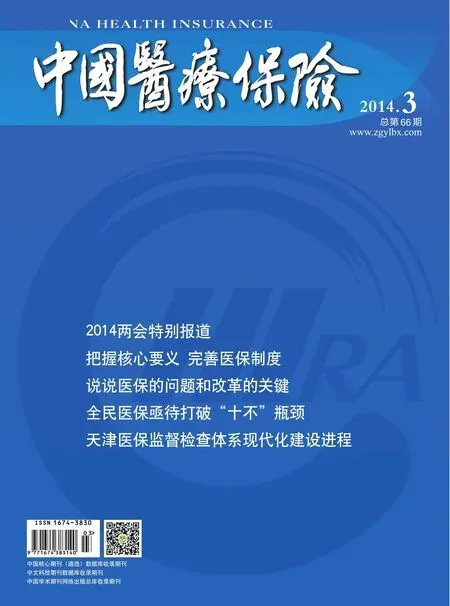说说医保的问题和改革的关键
文/陈金甫
说说医保的问题和改革的关键
文/陈金甫
我以为现阶段推进各项改革,必须紧紧扣住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基本精神。就医保改革而言,关键是四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问题导向和总揽改革全局。
一、医保问题的基本判断
以问题导向推进改革,可以避免没事找事瞎折腾,遇到问题绕着走。问题导向,首先要搞清哪些是需要通过改革解决的问题。这就不是一般性的话题、某个概括性命题,而是社会发展之必须又自身存在着功能性、制度性或外部匹配性缺陷等的难题。
自“两江试点”以来的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尤其是全民医保体系建立,是最为成功的改革之一,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极少案例的成功典范。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医保就没有问题,不仅有问题,而且很多,也很麻烦。但这些问题有一些属于内部体制机制性问题,但主要还是外部支撑与匹配问题。这个判断决定着医保改革重点和方向。统筹谋划医保改革重点和实施方案,必须先梳理问题,进而客观评估,明确哪些必须改,哪些不能改;改革的重点在哪里,改革的难点是什么。
二、医保功能和保障责任问题
医保当然是管参保病人看病医药费报销的。如果问题这么简单,那肯定天上掉馅饼了。报销不是问题,问题是报多少。这就涉及到医保功能和保障责任。而恰恰是这个问题关系到医保改革的目的和健全全民医保体系的任务。
谈到医保功能,必须回到国家治理和政府责任的命题上来。老百姓要吃饭,政府就给钱,这不是国家治理。现代社会国家治理的最基本任务之一,是社会风险管理。医保功能不是纯粹为了解决看病报销问题的,而是解决老百姓看不起病的医药费补偿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随着功能增强和待遇增长,医保越来越呈现出福利化的惯性,越来越成了政府单一责任,其风险防范的制度属性和互助共济的社会机制却被忽略了。
与医保功能相应的是基本保障责任。既然社会医保是通过互助共济机制形成的疾病费用风险防范制度,只能是基本保障而不能承担全部费用的支付责任。在这里社会保险是不是属于纯粹的公共产品还有待讨论,但将之归结于纯粹的政府责任则是有害的。政府管不了那么多事,政府没有那么多公共资源,所以政府要尽可能集中较少资源解决社会问题。
医保必须解决什么问题和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是谋划医保改革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关系到制度属性和政府责任,影响着舆论导向和公共决策,尤其不能误导性地忽悠民众,不能假借民意倒逼制度。因此,医保改革,既要重点解决一定阶段保障功能不足的问题,又要从制度机制上解决影响长远的福利扩张问题。
三、医保成本与均衡社会负担问题
任何不计成本的投入都是不可持续的。最可怕的是,在当下的舆论环境甚至学术探讨中,几乎对一切公共福利性投入成本都出现了集体性地失语。这就是一个大问题,是国家治理环境的恶化。而社会保障成本问题,又是当今中国与经济增长、民生建设、收入分配和财政平衡等同等重要又内在关联的重大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作出适时降低社会保险费率,体现了高度的政治担当和勇气。为什么不做好人,多筹点钱,多发点福利?因为社会保障一头关系到民生福利,一头影响着经济发展动力。
医保成本,就是社会负担率。涉及到总的社会承受能力和均衡负担两个问题。从总成本看,1万亿的医保基金支出就是1万亿的社会负担。从结构看,用人单位和财政承担了80%左右的筹资。这个结构一方面导致企业和财政负担沉重,侵蚀了经济发展动力;一方面导致受益群体成本意识淡薄,福利诉求强劲。如果再考虑经济减速和医疗消费增长趋势,基金运行的风险将会在医保成本问题上集中爆发:是增收还是减支?西方福利政治的荒诞剧就会在中国上演。
鉴于西方教训和中国现实,任何时候搞改革,都不能没有成本观念,都不能放弃发展这个硬道理。特别在医保改革中,牢固树立医保成本观念,是正确处理医疗保险与医药服务关系并由此健全完善相关体制机制的理论基础。
四、大病负担与托底保障问题
“刻章救妻”“抢钱救儿”“锯腿保命”“剖腹自救”,近年连续报导的几起困难群众大病难医的极端案例,冲击了社会道德的底线,也催生了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试点。试点取得了成效,因为多报销必然会降低参保人员医疗费用负担。
但单靠费用补偿机制能消除上述极端案例吗?1.看看京沪各大医院挤满等候就医的大病患者,本身就不单纯是医药费报销问题,转诊、重复、异地就医等的就医成本如何解决?从案例反映的群体看,几乎都是农村困难居民。当地看不好的病,对他们来说,不敢到大城市大医院看病才是真正的问题。2.普惠式的公平保障机制会让困难群众更受益吗?正如投资与竞选,在公平规则下必然受到自身能力的限制。暂且称之为“公平漏斗”。无差别化的支付政策是普惠式公平保障制度要求,但只要有自付费用(而这同样也是必须坚持的制度功能要求),富人就会得益更多,而穷人的承受能力则会止步于一定自付费用段。如果大病保险仍然沿用无差别化的支付机制,上述结果就会放大,同时带来刺激医疗消费的结果。3.有新的制度安排就要有相应的支持条件,仅靠阶段性的医保基金结余能支撑长期制度的运行吗?没有结余的地区如何实施?
不是说大病保险制度不能做。必须做,而且要抓紧实施。但这是一项有别于基本医疗保险一般功能和原理、针对困难群众大病医疗的托底保障措施,既要解决一般性的医疗资源配置失衡问题,又要采取有针对性的特殊保障政策,同时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应同步建立稳定的筹资机制。
对穷人大病保障机制的研究,还会引申出全民保险时代的特殊性诉求的公共政策问题。自医保制度建立之始,就面临着持续不断的特殊利益诉求:各种奖励性、照顾性、困难性等的医保待遇需求要求在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政策中给予解决。果真如此,这个制度早已支离破碎,无丝毫统一性、公平性可言。但从穷人大病这个话题看,一方面,医保确实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主要就医费用,但另一方面,对少数患大病的穷人,包括工薪阶层,总有个人自付所不能承受的极限。全靠基本保险包打天下不行,对正当特殊诉求置之不理亦非长策。这就需要通过建立制度衔接、功能协同的多层次保障体系,处理好社会保险的一般性原则和多元需求的特殊性问题。在改革的总体思路和顶层制度上,一定要坚持“一根支柱、两头辅助”的制度体系:坚持基本保障战略,筑牢全民医保基础;整合基本医保与医疗救助,切实解决穷人的重病负担;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满足富人更高医疗服务和保障需求。
五、异地就医费用结算问题
这是近几年来社会反映强烈的医保问题。政府部门通过提升统筹层次、推进省内结算平台、探索区域协作和改进医保信息系统等举措,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跑腿垫支问题。现在突出的问题集中在“跨省”“住院”“老人(异地安置退休老人)”三大问题上。但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真实现了全国异地就医费用实时结算,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吗?
事实上这绝不仅仅是一个费用结算问题。1.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异地就医?这与前面说到的大病问题一样,是资源配置和分级诊疗体系问题。2.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属于异地就医吗?只是由于区域差距和福利负担能力,对社会转型中集中出现的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难以转移保险关系。这就不单是医保问题了。3.与流动就业一样,公共政策应保障必要的转诊就医需要,但充分放开的异地就医加高效便捷的费用结算,对个别必需的转诊就医是好的,但在总体上会加剧医疗资源失衡、增加患者就医成本、加大基金支出风险。
因此,真正解决异地费用结算问题,要三管齐下,综合治理。一要下决心从根子上、战略上解决异地就医问题,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分级诊疗体系;二要从制度和管理上进一步强化异地就医管理和完善费用结算,该转的转,不该转的不让患者跑冤枉路花冤枉钱;三要通过创新管理和建立基金与财政支持机制,逐步实现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医保管理本地化、医保权益同城化。
六、医保统筹问题
当前,城乡医保管理体制分割和区域医保统筹层次过低,是医保统筹急需解决的两大问题。管理分割阻碍了制度整合和功能效应。体制服从于机制,体制是维护良性机制有效运行的组织保证。中国医保改革并有效运行二十多年,原本可以基于理性判断和实践总结作出结论,本不复杂。统筹层次过低的实质是政策管理权限过于分散,导致区域政策差异和管理壁垒。这也是制度碎片和接续不畅的症结所在。
上述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医保统筹的全部要求和关键所有。统筹,意在效能。医保统筹是基于客观存在的资源短缺、利益冲突和系统割裂,通过整合公共政策,集聚资源能量,平衡利益诉求,以实现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发展总要求。
这就涉及到两个层面的改革:一是提升决策系统问题,涉及到统一管理和统筹协调各类医疗保障决策的横向集中和纵向提升问题。提高决策的集中度和层级,目的是消除制度冲突和政策分散,但同时要充分考虑部门职能和地方责任,避免权力集中,责任上交。二是解决跨制度、跨区域的基金集中和财务平衡问题。制度整合、转移接续、共济范围扩大、老龄化及医疗成本平台提高等,一方面需要提高基金集中度,一方面也需要建立区域间的基金平衡调剂机制。
七、医保支付方式问题
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成功,既有制度合理因素,也有管理有效因素。这其中逐步完善的医保支付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建立了第三方付费的制约机制,二是有效遏制了医药费用的过快增长。否则医保基金结余无从谈起,连原公费、劳保医疗制度普遍存在的医药费拖欠都难以根本解决。这并不意味着医保支付方式无须改革,任何管理机制都有逐步完善的必要。随着医改的深入,在医保制度中与医改最紧密关系的支付方式确有系统升级的必要,也有机制创新的可能。
改革医保支付方式,首先,要区分医保待遇支付政策和医疗服务付费方式,通常讲的支付方式是指后者,因而也是改革的重点;其次,必须准确定位医保支付方式的功能作用,既然是医保的支付方式,控制费用是其本质要求;第三,医保支付的核心机制是利益机制,其作用结果就是能否获得集团购买的合理价格。正是这三条,都出现了认识偏差和决策背离。一是将待遇支付政策与服务付费方式这两个不同机制的问题搅在一起,将问题复杂化了;二是将对医疗服务付费机制单纯理解为医院补偿机制,将机制作用方向搞反了;三是强调支付方式作用却架空利益机制,抽取了机制的灵魂。
当下,医保支付方式改革问题被看得很重,它也确实是医保管理的最核心机制,是世界难题之所在。医保支付机制是医保对医药卫生运行机制发挥基础作用的核心机制,因而医改既有对支付方式改革的内在需要,更在系统层面提供了完善医保支付方式的最好机遇。改革的关键:一是将医保支付方式由单纯的控费手段提升为医保购买服务的询价机制,实现由结算管理向成本管理的转变;二是重构医保支付机制真正发挥作用的利益机制和谈判机制,这就涉及到医疗服务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命题,如果医生利益不能由市场决定,就走不出政府定价的老路,也就谈不上医保谈判询价;三是建立就医管理、预算管理与询价谈判三位一体的医保支付系统作用机制,形成医保支付对利益调节、成本控制和资源配置的综合功能。唯如此,医保支付机制才能对内实施有效成本控制,对外优化资源配置。否则,医保支付机制也就一奶嘴而已。
八、医药卫生体制问题
医保支付的核心机制是利益机制,但不断进行的医保支付方式的探索,都是“与风摔跤”:你深陷利益漩涡,却抓不住利益主体。因为医院是公益性的,医生工资并不由医保付费决定。因此,谈医保改革绕不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近年报道的“天价医疗费”“天价芦笋片”“医闹”“医倒”“伤医”和“假评”等案件,引发了阵营分明的对立情绪。这就侧面印证了医药卫生领域确实存在着的体制性问题。目前讲医改进入深水区,也应是指前面的改革已经触及体制问题的壁垒。那么,阻碍深化医改的体制性问题到底是什么呢?这就要回到重新学习和领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基本精神和对医药卫生运行规律的再认识。
破解一个难题,首先要对这个难题有起码的敬畏。既然是体制性问题,就要承认它有着方向性、根本性、系统性的影响力,不是一般性的认识和改革措施能解决的,或者看似综合配套却是七零八碎的改革拼盘。或许,问题是最好的法官。如果我们走出政府大院,到各大医院排队就医取药,问题会引导我们去发现医药卫生体制的症结所在:你让政府去配置如此庞大复杂的医药服务资源,能做得好吗?你让上千万医务人员在繁重的服务且流水般的收入中没有利益冲动能做得到吗?
医药卫生领域的体制性问题,关键是两个:一是面对如此庞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如何处理市场在卫生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作用;二是关乎亿万人群健康保障和经济利益的医疗服务,如何建立合理且有作用的利益机制。到目前为止,影响医药卫生改革的主导思想是:由于其行业的特殊性而必须加强政府管理,由于其趋利行为必须坚持卫生事业公益性方向。这两个思路都在强化政府的责任,排斥市场作用。行政化管理并没有解决好卫生资源配置问题;公益性保护也没有遏制不良利益冲动。
由国家管理向国家治理转变的一字之变,意味着行政方式的深刻变革。一个重要的命题,是如何充分运用社会的力量、市场的力量来做以前政府包揽或没人做的事。政府能力的提升不在于做事的多少,而是减少政府事务,多做谋划和制定有效的规则。不可否认,中国的医药服务,已经形成了巨大的买卖关系和利益关系。改革医药卫生体制,决不能因为我们无力驾驭市场而排斥市场和利益机制的作用。政府管的卫生事业必须坚持公益性,但并不是所有的医疗服务都需要政府管,都定位于公益性。与之关联,面对公益性的机构定位和收入分配机制,医疗保险的购买服务与付费机制是难以发挥作用的。
全民医保,已犹如一条滋润土地、调节气候的大河,改与不改,都在发挥着保障亿万民众基本医疗权益的作用。但她也存在水源枯竭、堤坝溃漏的风险。健全医保,也如大河治理。谋当登高望远,行需跋山涉水。推进医保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需要站在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基本精神的制高点,以改革的勇气和担当破除部门利益和思想束缚,以抓铁留痕的韧劲破解难题。唯有如此,才能让全民医保更健全、更有力、更稳固地造福全体国民。
(作者单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