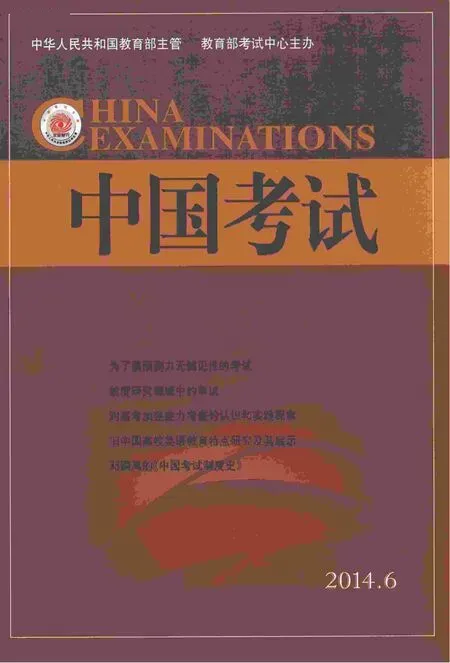旧中国高校英语教育特点研究及其启示
田强 乔辉
旧中国高校英语教育特点研究及其启示
田强 乔辉
由于历史的原因,对于旧中国高校英语教育的研究过去几十年一直受到忽视。本文在简要介绍了旧中国高校英语教育发展的几个时期后,从社会教育系统中的“定位”和英语学习的目的、教育内容的知识构成、课堂教学、教师和教材的系统功能、教育教学的方法、师资的构成与水平、校园环境的建设及对于学习的影响、学习成果评估的形式、母语在英语学习中的作用八个方面探讨了旧中国高校英语教育系统定位清晰,语言知识与专业知识有机结合,系统中各部分功能明确,注意培养学习者自主学习的能力,师资水平高,汉语基本功扎实等成功经验。
旧中国;高校;英语教育;教学;评价
旧中国的高校英语教育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原因也不算很复杂:过去近半个世纪里,人们先是不能提出这样的问题;等外部环境的变化允许人们提出这一问题时,绝大多数亲历者都已经离我们而去,留下的记录不仅有限,而且大多带有外部环境的烙印。
但我们必须回答这一问题。首先,中国高校英语教育需要发展,而任何现实中的发展和进步都需要历史提供的智慧。同时,我们一直相信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循着前人的足迹走路,而且我们认为自己不需要为行为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承担责任,因此错误的根源在于并不太遥远但我们却所知甚少的那段历史。可我们今天走的真是大半个世纪之前那些高校英语教育的大师们走过的路吗?如果是,那为什么他们在英语方面会有那样高深的造诣,能够在学习和教学中取得那样令人羡慕的成绩或成就,而我们却不能呢?如果不是,他们走的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我们能否从中学到些什么呢?
1 旧中国高校英语教育发展概述
1.1 中国英语教育的发端
提到中国英语教育的发端,人们就必须提到一个名字:同文馆。成立于1862年的同文馆被公认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教育机构,也是中国最早的官办高校英语教育机构。
由于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外交活动中因语言不通而遭受巨大损失,清政府建立同文馆的首要目的就是培养外交领域的专业人才[1]。无论从招生对象还是教育模式看,最初的同文馆都属于一所中等教育机构:入学者都是十三四岁的满裔贵族少年;所学习的都是英语语言、通识类及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后来又增设了法文馆和俄文馆。
1898年12月,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正式开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由官方建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高等学府,是中国人自己大学教育的发端,而且也将成为作为社会教育组成部分的中国高校英语教育的第一个“母体”。
从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新派官僚相继开办了一系列军事和科技类学校,其中非常著名的有福建船政学堂(1866)、上海江南制造局机械学堂(1867)、天津水师学堂(1881)等。这些学校中大部分专业类课程都是用英语讲授的。虽然这些也都是中等教育水平的机构,但为后来高校英语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895年和1896年,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盛宣怀先后在天津和上海创办了中西学堂(后于1913年和1951年先后更名为北洋大学和天津大学)和南洋公学(1921年更名为交通大学,1957年分设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从教学内容上看,这两所学校将英语学习和知识学习更为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即通过英语来实施教育和学习知识,语言水平在知识水平提高的同时得到提高。这两所学校的整体办学模式(学制)更对后来中国社会教育的体制产生了巨大影响。中西学堂的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虽然在学习内容上更分别接近于后来的中学阶段和小学阶段,但受教育者的年龄结构和教学模式更接近于大学本科和预科。南洋公学则是创造性地建立了外院、中院、上院三级制(每级四年,相互衔接)的范例,并成为后来中国现代社会教育初、中、高等教育晋级制度的雏形。
1872年,在曾国藩、李鸿章和中国近代留学史上著名人物容闳的推动下[2],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30学生赴美留学。虽然此后一段时间留学项目时断时续,但1908年“庚款”留学项目的启动不仅催生了中国现当代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机构——清华大学,先后培养和帮助培养了梅贻琦、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一大批在中国后来的历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物,也为中国高校英语教育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早在1882年和1890年,上海的中西书院(美国基督教纽约监理公会于1881创建,东吴大学前身)和约翰书院(美国圣公会圣于1879年创建,圣约翰大学前身)就已经开始招收本科学生,从时间上看,它们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大学。但由于这些学校均为私立教育机构——办学资源、办学模式、课程设置、学校管理等均不受清政府管理——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与国家统管的社会教育系统几乎无关,而且由于本科教育初期阶段规模非常小,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政府(朝廷)、地方大吏、民间人士、教会组织等“多元”的资源和组织机构,培养外交官、培养技术人才、为出国留学、达到某种宗教方面的目的等“多元”的培养目标,成为中国英语教育早期历史的一个主要特点。
1.2 中国高校英语教育系统的建立
1900年至1902年,因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刚刚开办一年多的京师大学堂和同文馆被迫停办。恢复运行后不久,京师同文馆更名为“译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1903年7月京师大学堂译文馆正式招生。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6月,象征着近现代中国新教育体制的《奏定学制方案》(史称“癸卯学制”)颁布,并从1904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这一学制具有明显的“仿日”倾向,大概与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的惨败有关。
该“学制”规定:高等教育十一至十二年,由高等学堂或预科(三年)、大学堂(相当于今天的专科或本科,三至四年)、通儒院(相当于今天的研究生,五年)三级组成。该“学制”根据学科性质将预科阶段分为三类:第一类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文科和商科;第二类相当于今天的理科、工科、农林科;第三类相当于今天的医科。该“学制”对三类科目中英语在培养目标上作出具体规定:学习第一类科目者“英语必通习……”;学习第二类科目者“外国语除英语外,听其选德语或法语习之”;学习第三类科目者“外国语于德语外,选英语或法语习之”。也就是说,对于文、理、工、商、农林等科的学生来说,英语是“一外”;对于医科学生来说,英语虽是“二外”,但也是必修课。这是最早关于高校公共课英语教育的“国家级”规定。
大学堂阶段共分经学、政法、文学等八个“科”(学科),共四十六个“门”(专业)。在“文学科”的九个“门”当中有一个“英国文学门”。这是首次在我国社会教育系统中正式设立“英语专业”[3]。
京师大学堂译文馆的招生和“癸卯学制”有着重要的象征和实际意义:英语教育正式作为国家兴办的中国高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出现,也就是说,这意味着作为社会教育系统组成部分的中国高校英语教育开始登上了现代社会教育发展的历史舞台。
1922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法令,以仿欧美的“壬戌学制”取代仿日的“癸卯学制”。从1912年到1937年的二十五年是中国高校英语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各种英语教育的基本形式均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办学模式日臻成熟。
在早期的高校英语教育基础之上共衍生出了四种基本办学形式:国立或省立大学——如北京大学和南京的中央大学;教会学校——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和北平的燕京大学;由专门的赴美留学机构衍生出的大学,即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大学——如天津的南开大学。
这四种形式大致分属两种不同的模式,即国家管理的社会教育“主流”大学(如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的英语教育和“非主流”的教会大学(如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的英语教育。每一类办学模式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办学特色,但每一种模式都为中国高校英语教育的发展贡献了成功的经验。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1904年清朝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将通儒院规定为大学教育的最高阶段。这可以被视为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发端[4]。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其颁布的《大学令》中对大学院——由通儒院演化更名而来——的学生入学资格和学制等作出了系统、具体的规定[5]。此后1922年的“壬戌学制”和1929年的《大学规程》在培养的整体方向和方法等方面均未有大的变化。但旧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整体规模非常小,即便是到了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1935年到1949年的十五年间,全国总共仅有200多名研究生被授予硕士学位。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生英语教育无法形成独立的教育教学系统和鲜明的特色。
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于绝大多数高校都处在东部,特别是沿海地区,所有的国立大学和大部分私立学校均迁往大西南的“国统区”,教会大学则选择留在日寇占领的沦陷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包括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在内的教会大学也完全沦入日寇之手,正常的教学活动根本无法进行,日本侵略者强行命令沦陷区各大学改用日语教学,英语教育难以为继。
迁到“大西南”的各高校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办学,以一种教育工作者独有的形式宣示着中国民族的坚强和不屈。由于中央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教学设备和资料得以运往大后方,因此在重庆和昆明两地,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合并而成)都能够保证开展英语教学活动。
1945年到1946年上半年,随着抗战的胜利,迁往大后方的各大学都迁回原办学地点(城市),各教会大学也都得到恢复。但由于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同时爱国师生对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日益不满,到1948年上半年,“国统区”各大学的教学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无法正常进行。这一阶段外部比较稳定的时间实际上只有两年左右,且师生们已不再有当年那种由爱国热情转化出的动力,这一阶段高校英语教育并没有大的建树。
2 旧中国高校英语教育的特点
如上文所述,旧中国高校英语教育发展的黄金期是1912年到1937年。本文对于旧中国高校英语教育特点的总结主要也是围绕这一时间段。
旧中国的高等教育从社会教育的发展阶段来讲属于典型的“精英教育”。首先,高等教育受教育者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非常低。即便是在高校在校生数量最多的1947年,人数也不过十三万左右,而当年的毕业生(包括本专科)只有25 000人,仅仅是我国当时人口总数(4.575万)的约两万分之一。即便是按同龄人口计算,这一比例也只能是数百分之一。其次,受社会发展整体水平、教育所需费用、人们关于教育的观念等因素的影响,高等教育的受教育者主要是来自上层社会和具有稳定的且很高或较高收入的家庭,包括高层官员、富商(绅)、社会贤达、高校教师和个别中学教师等。由于出身条件较好,受教育者原来的基础教育水平和整体修养大多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最后,由于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极低和绝大多数人较好的家庭背景,受教育者的就业更多取决于其受过的高等教育和家庭关系,而与专业学习之间并不一定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些典型的“精英教育”特征对旧中国高校英语教育产生了多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在这样一种大的社会背景下和教育体制内,旧中国的高校英语教育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出一些独有而且显著的特点:
2.1 社会教育系统中的“定位”和英语学习的目的
对于任何一个行为者来说,目的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它从根本上决定着行为的其他要素,诸如行为的内容、行为的方式等,因此也从源头上决定着行为的质量。而对于一个社会行为来说,决定着行为目的的前提是该行为在更高一级系统中的定位。这种定位通常体现为行为在系统中的功能,而这种功能的实现一般就是行为者要达到的目标。
那么,旧中国的高校英语教育在社会教育系统中的“定位”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从前面的介绍和讨论中我们知道旧中国的高校英语教育大致分成两种不同的模式,即国家管理的社会教育“主流”大学(如北大和中央大学)的英语教育和非主流的教会大学(如圣约翰和燕京大学)的英语教育。社会教育“主流”大学的英语教育在初始阶段(1912年之前)只有一种定位和功能:培养翻译人才。但后来(自1912年起)逐渐分为两种不同的定位和功能: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受到当时国际(主要是美国)社会教育理论关于高等教育社会功能思潮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与中国社会教育传统中关于教育社会功能的观念相吻合——英语专业被定位为培养“通才型”人才。
高校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教育分为两个阶段(部分):“通识英语教育”和“专业英语教育”。“通识英语教育”是与英语专业学生一起进行的,目的是通过英语教育培养受教育者的高素质。这与后来的“公共英语教学”在方向和功能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为受到另一种国际思潮的影响,“专业英语教育”则是为了提高受教育者的专业水平以便使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更具有针对性和使其更容易就业。这是今天整体上处于雏形的“专业英语”未来发展应取的大方向。由于“通识教育”阶段的英语教育是与英语专业同步进行,而“专业教育”阶段的英语教育是以针对个专业科目进行的,因此,旧中国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公共英语”教育体系及其分支。此外,由于当时的课堂是“开放式”的,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可以自由选听英语专业的课程。
按照办学者的初衷,非主流的教会大学的英语教育最初是要融入宗教教育系统中的。布道是根本目的,教育是布道的知识基础。但由于教育属于“善举”,有利于从感情上赢得受教育者和周边人群,当然也就有利于达到布道的目的,可谓“一举两得”。
但在现实中,实际效果却越来越偏离办学者的初衷:在中国过分“宗教化”的教育难以为民众所接受;而即便是教会当局所在的国家,教育的“世俗化”也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抵御的时代潮流。现代社会教育的非宗教目的逐渐成为教育的主要目的。通过英语教育培养受教育者的生活能力——教会大学基本上都有医学院,并尽可能地达到宗教教育的目标——各教会大学基本上都保留了神学院,这应该就是教会学校对于教会大学英语教育的基本定位。
2.2 “物化”体现:教育内容的知识构成
旧中国高校英语教育中语言知识和专业知识实现了较好的有机结合。但社会教育“主流”大学和非主流的教会大学对于高校英语教育的不同定位决定着其在作为教育内容的知识构成上是各不相同的。
在社会教育“主流”大学的“通识英语教育”阶段,作为英语专业前身的英国文学和非英语专业在学习内容上是没有区分的,即从英语国家(主要是英国)的文化知识和语言知识两个方面主要在阅读和写作上提高受教育者的水平。
但在专业阶段,英国文学专业和非英语专业在学习内容上有着明确的系统分界:
英国文学专业是以“文学性”为其“专业性”的,此知识构成是以文学为核心或框架的,而且非常注重课程的系统性。学习内容和课程设置都是“以内容为基础和以体裁为系统”(Content-Based and Genre-Systemized)的:以文学形式为“横向坐标”设定为“诗歌”、“戏剧”、“散文”、“小说”等课程类型;同时,每门课程又是以文学历史(如按照作家的生平时间顺序)为“纵向坐标”展开。这样就够成了清晰的知识“经络”系统[6]。后来英国文学专业课程体系又向外“延伸”,收入了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基础等学科或领域的内容。但并非所有的“延伸”都是合情合理的。如西南联大把“生物学”作为唯一的自然科学课程“植入”英国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做法就令人感到费解。
各非英语专业在自己的专业学习阶段所实施的大多是“双语教育”:涉及中国文化的部分基本上都用汉语教学;涉及专业知识——当时的专业教材很少用汉语编撰——和外国文化的部分基本上都用英语教学。尽管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但彼此互补,在受教育者身上“汇总”,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
教会大学最初是完全以英语实施教育的,而且大部分课程都是从国外直接引进。但后来也开始增加用汉语开设的课程:或(如圣约翰大学那样)增设以汉语开设的有关中国文化知识内容的课程,或更进一步(如燕京大学那样)建立起“双语教育”的知识和课程系统。两个不同语言构成的系统同样彼此互补,也在受教育者身上整合成了完整的知识体系。教会大学的英语教育模式与社会主流大学非英语专业的模式有相似之处,只是没有“通识英语教育”阶段的那种综合性知识内容。
2.3 课堂教学、教师和教材的系统功能
旧中国高校英语教育的课堂教学、教师和教材在整个教学系统中的功能应该说是比较明确的。在大部分学校里(除了圣约翰大学等少数学校外),课堂教学在时间和规模上只是整个学习过程或学习活动中的一小部分,其主要功能是帮助学生解决“新知”和典型性疑难问题。教师通过课堂教学所体现的作用在于通过讲解来“示范”,教材是为这种“示范”提供合适的材料。
如果把学习内容比作一张网络,而学习过程或学习活动是编制网络的话,那么课堂教学就出现在一些关键的新、难、重“结点”上;教师就是在这些“结点”上通过示范告诉学生该如何“结网”;教材则是汇集了以往“结网”过程中人们认为最典型的新、难、重“结点”素材。学生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参照教材的范例和教师的示范,通过课下大量的实践学会读书和学会学习,即“学会结网”;最终建立相关领域——如文学或其所在专业的各个分支——的合理知识系统,即“结成网络”。过多的课堂教学不仅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且从根本上违背了教育的一般规律。在这一点上,旧中国高校英语教育的经验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
2.4 教育教学的方法
旧中国高校英语教育在方法论的层面上有许多经验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更多的学习活动是由学习者自己通过课下或课外读书来完成的。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完成作业”式读书活动,更包括了学习者对读书内容系统的选择和安排。也就是说,学习者在读书过程中学会了学习,特别是自主学习。而从教育的整体目标上看,这比“完成作业”式的读书活动更有多重的重要意义:(1)满足基于理性和动态化的个人生活需要是现代社会教育的一个核心目标和标志;(2)而自主学习不仅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合理和最有效方式,同时也是现代社会教育的又一个标志;(3)只有学会学习,终身教育才能真正得到实现,而终身教育是解决“动态”知识状态下社会教育问题的唯一方法。可以说,通过自主学习来满足个性化需要是最能反映现代社会教育特点的学习行为的。
如果再结合前面提到的系统定位、教育内容、课程设置等方面的因素,我们就会发现,旧中国高校英语教育在系统完整性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还应专门提到的是,旧中国的高校英语教育基本上不需要受到各种形式的考试,因此没有被干扰和“切割”成为若干支离破碎的部分,其整体和微观上的完整性和系统性都得到了保证。
2.5 师资的构成与水平
旧中国高校英语教育的师资是由两部分人构成的:中国籍教师和外籍教师。由于教会大学等因素的存在,外籍教师所占的比例要高于今天。
中国籍教师大部分人都有较好的留学背景。与今天的情况不同的是,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在中学和大学阶段出国留学的。由于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出身教会中学或其他英语教学水平很高的学校,如杨宪益、俞大缜和俞大絪姐妹等多人都曾谈到他们教会学校的英语教育对他们英语学习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在出国前他们的英语水平就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而且与今天英语教师为了所谓的“学术”考虑而出国进修不同,他们留学的目标就是提高英语水平。因此,中国籍高校英语教师的英语水平整体上是很高的。但由于没有独立的“公共英语”分支,因此也就没有一支专门从事公共英语教育的教师队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材都是英语的,授课语言也是英语的,讲授这类课程的教师也应被视为高校英语教育师资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时在“主流”大学工作的外籍教师也不少。这些人在其本国大多也都是专业教师——这与今天中国各高校外籍教师的出身多有不同——不仅水平高,有经验,而且相当敬业。
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师基本上都是外籍教师。这些人大多都是由教会在其所在国的上级组织来安排,而且所聘请的也都是其教会组织的成员——这与今天中国各高校聘请外籍教师有很大的差别——因此更有可能保证教师的水平和在教学上的投入,从而保证教学的质量。
旧中国各大学之间的教师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吴宓、梁实秋、钱钟书等都在多所学校任过教。这种时常变换的组合不仅有利于英语教育人才资源的整合和更为有效的利用,更可让学习者接触和感受不同的英语教育大师在教育教学上的不同风格和特点。
2.6 校园环境的建设及对于学习的影响
中国社会教育各个阶段的英语教育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外部环境贫瘠,生活中几乎找不到与英语教育有关的资源。这种情况很像生活在陆地上的人为了赶海而学习游泳。旧中国各种模式的高校英语教育都试图通过校园环境建设从微观上解决这一问题。许多学校规定:校园生活的各种活动除不得已而使用汉语外一律使用英语。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开展各种形式的文艺、社交等活动为学生提供使用英语的机会。这种努力又很像生活在陆地上的人们为了学习游泳而建设的游泳池。这些努力不仅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也获得了诸多有益的经验。
2.7 学习成果评估的形式
旧中国高校英语教育的学习过程中基本上没有我们今天盛行的各种考试形式,更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化”考试来评定学习者的成绩。课堂表现和读书报告是评估学习者学习成果的主要依据,如林语堂先生就常常根据每个学生的表现在课堂上当场决定并告诉他们在该科目的成绩。这种做法的有益之处在于可以保证学生长时间(周期)地专注于学习,很少受到各种“干扰”。这对于英语学习可谓裨益甚大,而这也可以看作一种形成性评价的雏形。
2.8 母语在英语学习中的作用
由于旧中国的初、中等教育阶段依然强调“典籍”的学习,能够进入大学学习的人都有着很好的汉语和民族文化知识基础,大学教育也延续了这一传统。(圣约翰大学等学校在早期阶段曾忽视对于学生汉语和中国文化基础的要求,但后来纠正了这种“偏向”。)对于“学习”而非“习得”英语来说,母语是知识的基础、系统、框架,是发展和进步的方向和途径,是成绩评估的坐标和尺度;母语的知识水平从根本上影响乃至决定着英语的知识获取质量。母语的水平——包括涉猎的范围与总量、涉猎内容的构成、涉猎的方式、涉猎后掌握的程度等——从根本上决定着英语学习的质量和整体水平。
3 对于今天教育与评价的启示
尽管当时办学的外部条件有限,不仅设施和设备简陋,而且还要受到战乱的袭扰,但是这一阶段中国高校英语教育在学科的归属和定位、英语教育自身的学科系统性、英语教育与素质(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等大的方面和教学系统内部的师资水平、环境建设、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等方面都是可圈可点的,其中的一些方面更是达到了后人(迄今为止)难以企及的高度。
今天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远远超过“精英教育”的发展阶段,同时早已建立并完善了母语的专业和公共课程教材系统,既不可能也完全没有必要复制或效仿旧中国高校英语教育的整体模式。但是这种模式或体制的许多方面都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
3.1 我国高校英语教育功能方面的定位不仅要明确,更要合理。
旧中国高校英语教育虽然属于“多元化”,无法有统一的表述,但无论是社会教育“主流”大学和非主流的教会大学,英语教育的“整体目标”不仅明确,而且合理和具有可操作性。
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高校英语教育的功能一直被定位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从语言系统和功能的角度看,这一定位似乎无可厚非。但从教育的系统和功能看,这一定位恐怕值得商榷:教育的主要功能应该是知识的传承。另外,这一定位也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在中国高校英语教育的受教育者中,绝大部分人生活中并没有经常性和功能性的跨文化交际活动。
3.2 我国高校英语教育应与专业教育和素质教育有机地结合为一体
由于特定历史发展背景和条件的限制,旧中国高校的专业教育几乎都是通过英语教育实施的,英语教育对于受教育者的素质培养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历史在向前发展,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头去建立一个以英语为载体的专业和素质教育系统。但只有将英语教育与专业教育、素质教育有机地结合为一体,中国高校的英语教育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3 我国高校英语教育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母语和民族文化教育基础之上
旧中国高校英语教育培养出了一批如范存忠、王佐良、李赋宁、许国璋、徐燕谋这样的英语教育大师。这些大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汉语和民族文化基础好。我国的外部社会生活环境中不具备自然形成的英语教育认知系统,英语教育必须以母语和民族文化为认知基础、知识框架、认知途径和成果评估尺度。大师们的经验也证明,英语并不是母语的天敌。
3.4 我国高校英语教育必须有效、充分但又适度地利用考试这一“指挥棒”
旧中国的高校英语教育是多元的,规模也要小得多。即便如此,作为主流的“国立”大学也有各种考试。同样是由于我国的外部社会生活环境中不具备自然形成的英语教育认知系统,大规模的英语教育活动极容易产生盲目性,进而导致混乱和费时低效,必须有合理和有效的导向和调节手段。无论从民族文化传统还是教育系统管理的角度看,考试都是最佳的选择。在未来相当的一段时间里,我国英语教育尚离不开“应试”。我国高校英语教育目前存在的“应试模式”问题并不在于我们采用了应试模式,而在于所“应”之“试”自身存在问题。正确的解决之道是提高对于认识和操作水平,最终找到应“应”之“试”,而不是降低考试应该发挥的作用甚至取消考试。
4 结语
由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和六七十年代的“文革”,中国高校英语教育的历史出现过两次“断裂”。同时,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对旧中国英语教育发展历史的研究受到了不应有的冷遇。这导致我们对于历史的了解和认知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偏差,对于旧中国高校英语教育缺少必要的正确认识,未能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高校英语教育必须回过头去客观、系统、全面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站在历史的高度和前人智慧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真正的长足发展和进步。
[1]金林祥.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六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7.
[2]陈青之.中国教育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1.
[3]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4.
[4][5]董宝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12.
[6]付克.中国外语教育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11.
(责任编辑 吴四伍)
A Study on the Features of English Education in Old China’s Universit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TIAN Qiang and QIAO Hui
Studies on English education in Old China’s universities(EEOCU)has been neglected,as a result of historical causes.On the basis of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periods of its progress,the paper treats EEOCU in such eight aspects as its“orientation”in the system of social education and its general goals,its epistemological features,classroom teaching,functions of teachers and textbooks,teaching methods,teaching staff,its features in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assessment faculty,and the roles of mother tongue.The paper highlights the success of EEOCU in the distinct orientation in social education,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verbal knowledge with specialty knowledge,the distinctive functions of different parts in the system,the emphasis on self-directed learning,the high competence of teaching staff,and the solid and well-knit foundation of the mother tongue.
Old China;Universities;English Education;Teaching;Assessment
G405
A
1005-8427(2014)06-0036-9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研究生英语入学考试的本体研究”(课题批准号:GFA111021)阶段性成果。
田强,男,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哈尔滨 150001)
乔辉,男,教育部考试中心外语处,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