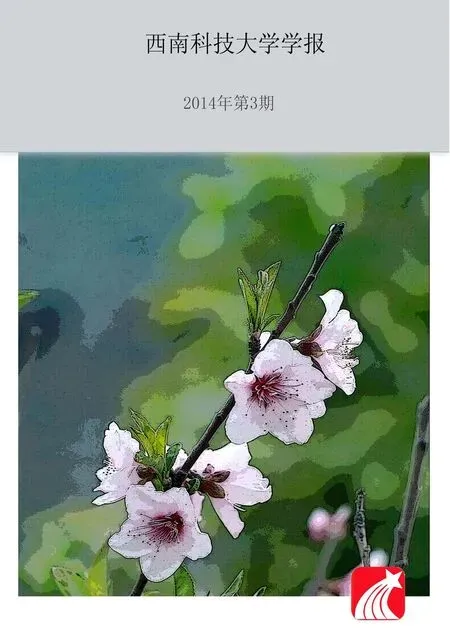论“信息-想象”
——舆论恐慌心理的形成
刘海明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绵阳 621010)
论“信息-想象”
——舆论恐慌心理的形成
刘海明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绵阳 621010)
对安全感的渴望是人的基本需求。在现实社会中,危及群体安全的讯息一旦在社会上传播,成为舆论议题后,容易造成舆论恐慌事件,扰乱人们的正常生活。研究舆论恐慌,需要探求舆论恐慌心理的发生。影子事实是舆论恐慌的前奏,合理想象是舆论恐慌的始作俑者。从“信息”到“想象”的连环反应,成为酿成舆论恐慌的发生轨迹。舆论恐慌心理的“信息-想象”机制表明舆论恐慌主要是群体性心理反应,和政府信息不透明没有太大关联。
舆论恐慌心理;影子事实(信息);合理想象
舆论是群体社会的产物,舆论的发生对世界产生影响。人们不管是在现实世界还是在虚拟空间里聚集,交流必须有可资讨论的话题。话题产生观点,有分歧的观点必然有论争,论争导致观点的汇流,最终形成两三种相左的观点,舆论自此形成。社交媒体(如微博)出现后,信息和观点的传播呈现出空前的活跃之势,一个微不足道的信息,一句不经意的个人诳语,都可能被无限放大,成为舆论事件,影响公众的情绪。2013年3月7日,新浪微博用户“少林寺的猪1986”爆料称,黄浦江上游横潦泾段一级水源保护地中出现大量动物尸体,微博还附有相关图片,一时间该消息引起网民关注热议。随后,媒体虽对黄浦江漂死猪的原因和饮用水安全等问题进行了报道,但是官方的回应未能让民众释疑,反倒激化网民不满情绪,舆情热度急剧攀升。该舆论事件的影响超出了公众口头议论的层面,演变成具有普遍性的群体行为。这种自发性的群体行为有一个显著特征:群体性恐慌。我们将其称作舆论恐慌。舆论恐慌造成的群体性反应,包含在舆论规律内,同时也有自己的独立性。舆论恐慌事件搅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威胁着社会稳定。
本文以近几年的几次重大舆论恐慌事件为例,具体考察舆论恐慌心理的发生机制。
一、恐慌心理的刺激反应
恐慌属于人和动物特有的一种刺激性反应。这种刺激性反应首先表现为内心的严重不安,进而体现在其行为上。恐慌心理并非人的天然属性,而是社会属性。实验表明,一个新生的婴儿并不具有畏惧心理,更谈不上恐慌。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加,他们与外部环境接触的频率加快,获取的教训也越来越多。婴儿的切肤之痛,会存储在其大脑皮层中,以后遇到类似情形时,这种教训型记忆复活,迫使其选择是否重复类似的行为。这种犹豫、畏惧心理,即恐慌的初级阶段。可见,恐慌更多属于人类的经验性反应①。
既然恐慌是人类后天形成的,恐慌就不是无中生有的东西,而是至少有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刺激源,向大脑中枢发出预警。这个刺激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原型。原型被纳入人的记忆库,一旦遇到相似的环境,这种记忆则随即复活。恐惧型的“原型”被唤醒,使人产生恐惧感。恐惧心理加剧,首先表现为意识反应,进而形成恐慌,最终反映到行为上。恐慌是个体心理活动在行为上的反映。舆论恐慌则是群体性心理恐惧的骤然加剧,最终导致某些非理性行为。
关于“原型”与人的记忆之间的关系,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最有代表性。其实,荣格并未严格界定过“集体无意识”这个概念,他对集体无意识的阐释散见于其相关论著中。1917年,荣格第一次对“集体无意识”进行分析,认为“集体无意识作为人类经验的贮存所,同时又是这一经验的先天条件,乃是万古世象的一个意象”,它由“本能及其相关物、原型的总和”组成,“包含了从祖先遗传下来的生命和行为的全部模式”[1]。在荣格看来,原型是构成集体无意识的基本内容,以至于“人生中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这些经验由于不断重复而被深深地镂刻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之中”[2]。
引起恐慌心理的事实可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也可能是我们暂时还没有意识到的事实。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事实,需要在特定的环境下被唤醒。原型即事实,事实又是什么?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事实即存在。作为客观存在的,只有能够被人意识到,并且已经意识到,才成为事实。这是我们所谈论的“纯粹事实”。在现实世界中,“事实”包括了目睹型事实、传言型事实、想象型事实。
二、影子事实:舆论恐慌心理的信息刺激
世界无时无刻不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因果关系是其中一种联系。按照辩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原因和结果是揭示事物先后相继、彼此制约的一对关系。舆论恐慌是一种结果,导致恐慌心理的原因是某种信息引起多数人产生共同的恐惧性反应。引起舆论恐慌心理信息要么是多个人亲眼目睹了某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要么是少数人经历了类似的状况,通过人际传播扩散了相关信息,越来越多的人接收并认可这个信息。假如只是收受到这个信息,并不能认同这样的信息,也就无法产生共鸣。没有舆论共鸣,也就没有舆论恐慌。
先有事实,并且是目睹了的事实,然后才有本能的反应。人类对眼睛的信赖程度相当高,很少怀疑自己所见到的事实。必须承认,眼睛只是视觉器官,它在捕捉客观世界的影像时,也会受到形形色色的干扰。这些干扰,也就是所谓的假象。有幅摄影照片,将事实和假象同时固定在一个时空内: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阳光照射在街上的一面围墙上。街道上,一位小伙子和一个姑娘相向而行。一个摄影师捕捉到这个瞬间。在拍摄到的照片上,墙体上的男女对面凝视,即便当时在场的人,如果没有留意这一男一女擦肩而过的真实场面,他在墙体上看到的只能是一对情深意切的男女[3]。墙体上的影像是典型的“影子事实”,影像的存在,我们无法否认它,但对于那些只看到影子的人而言,因为他们首先相信了自己的眼睛,进而相信进入自己视野的影响,最终使得影像构建的事实成为“真相”。假如这对男女刚好在一个小镇子上生活,大家都认识他们,“影子事实”可能经过一个目击者传播给其他人,进而演变成一个罗曼蒂克的传说。应该承认,现实生活中不乏这样的巧合。
上面的例子富有喜剧色彩,能给人带来乐趣;有的影子事实本身蕴含了令人恐惧的元素,对相信眼见为实的公众来说,悲剧色彩无疑多于喜剧色彩。进入21世纪,造成全国性的舆论恐慌事件愈发增多。2003年的SARS流行就是典型,当时全国出现了抢购板蓝根、84消毒液、口罩的风潮。2011年的日本核辐射危机造成的抢盐风潮,再一次掀起全国范围内的舆论恐慌波澜。2011年3月11日,日本宫城县以东太平洋海域发生9.0级大地震。地震引发约10米高海啸。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机组出现故障。面对可能出现的核泄露,3月12日,日本首相菅直人要求福岛核电站周围10公里以内的居民进行疏散[4]。日本核电站泄漏,核辐射弥漫在中国陆地的上空,核辐射危及中国公众的生活,尽管谁都无法看到,却也不敢掉以轻心。这些信息是通过媒体源源不断传播给中国公众的。地震是事实,核泄漏事故是可能的事实,中国公众从新闻报道的信息中接收到了有关核辐射在中国各省份的检测数据,以及核辐射可能污染到中国的蔬菜和水源的信息。于是新闻报道让公众不得不信以为真,恐惧情绪开始滋生。2011年3月中下旬全国多个省份上演的抢盐风波,就是“地震”、“核泄漏”、“核辐射”、“碘盐能预防核辐射”事实或影子事实的混合体急遽发酵的结果。
影子事实不是事实,它只是事实的映射。影子事实能对社会舆论产生巨大影响,在于它可以让人们以偏概全为纯粹的事实。目睹型事实是构成“影子事实”基础,这种事实一旦具备形成的条件,其影响超越了地域的界限,可能变成席卷全国的重大舆论恐慌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影子事实是舆论恐慌的天然温床,也是其逻辑起点。
三、传言信息:舆论恐慌情绪的放大镜
传言以某个事实为基础,经过广泛传播后,事实部分被严重扭曲,形成了亦真亦假的信息混合体。言语世界中的有关事实的信息每一次传播,总会有所损益。不同的传播者,对事实的记忆、理解难免存在差异,加之每个传播者的目的不尽相同,同一个事实传播后,本质虽然没有改变,但细节已经和传播前有所变化。变形了的事实中,与公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实片段被曲解放大,经过广泛传播后,所引发的舆论恐慌情绪在相互感染中也不断地放大。
为了适应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找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途径,适应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型为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发展动能,实现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十九大提出了“现代化经济体系”,为了实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标,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在乡镇实施产业扶持政策,建立产业园区,由点及面、由小及大,为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应该加强对乡镇产业园区的研究,为乡镇地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科学理论支持。
传言信息容易引发舆论恐慌。传言借助新闻媒体造成的舆论恐慌事件并不罕见。2010年3月13日晚8时,格鲁吉亚“伊梅季”电视台在“特别报道”节目中声称:“俄罗斯军队毫无征兆地入侵格鲁吉亚,猛烈地轰炸了机场和港口,格方有3个营向俄罗斯投诚,格总统萨卡什维利遭暗杀身亡”。节目中还出现了模拟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发表的“关于入侵格鲁吉亚的演讲”,以及“俄军入侵”的画面。这条编造的“新闻”让许多格鲁吉亚人想起了2008年俄格爆发的一场短暂战争,此举最终引发格鲁吉亚全国性恐慌并招致多方批评[5]。2011年出现的罗马大地震预言,在意大利民众中间造成不同程度的恐慌。一些意大利媒体提前公布了“地震逃生路线图”,一些报纸甚至以图表形式画出罗马地区“可能在地震中倒塌的建筑物”。媒体的跟风,加剧了民众的恐慌心理,有的学生家长请求学校在2011年5月11日“大地震”那天给孩子放假[6]。传言是未经证实的信息。传言的生命力,在于它常常以某些现象为原型。这种现象未必每个人都经历过,却符合集体无意识假说中的原型理论:我们无法意识到其存在,它们确实蛰伏在我们的记忆中。和公众安危相关联的传言,传播速度极快,产生的冲击波也非常强烈。
传言将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乔装打扮,以新闻信息的形式出现,借助有效的传播媒介,经过人际传播,危害结果被放大,终将酿成社会性的群体非理性行为。2009年发生在河南杞县的钴60卡源故障,因为地方政府封锁消息,当地居民借助电话和手机短信传递信息,对核放射恐慌导致大规模的逃离行为。2011年2月江苏的“响水事件”,也很典型。2月10日两点多钟,有人称江苏大和氯碱化工有限公司将发生爆炸,多个村庄村民连夜冒着大雪大规模逃亡。响水事件造成四人遇难,多起车祸的悲剧。响水事件造成的舆论恐慌,首先是当地居民夜间闻到刺激性气味,使人喉咙难受,加上2010年7月28日,南京栖霞区迈皋桥街道辖区原南京塑料四厂发生爆炸,造成22人死亡,方圆数里变废墟[7]。这些前车之鉴让饱受化工污染的居民对爆炸新闻比较关注。闻到怪异气味,恐慌之中电话通知亲朋好友连夜采取逃离行动。
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兴起和使用,使得传言的流传更加迅速和广泛。例如微博的流行,知名度高的用户凭借其可观的粉丝数量,发布一则讯息可以很快让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受众知晓。2011年3月16日17点52分,南京盐业公司官方网站推出一则《每月3元钱,硒盐防辐射》的新闻,文中有“与大家分享一下通过食用硒强化营养盐的方式来防御辐射的做法”的内容。这条新闻发布的时间与“抢盐潮”开始的时间相近[8]。当时,对于那些正置身于日本核辐射危机阴影下的中国民众而言,渴望找到防治核辐射的办法,成为其最迫切的愿望。食盐可以预防核辐射的传言已经出现,地方盐业公司的“网络新闻”,刚好印证了传言,传言由此被转化成“事实”。随后,大江南北上演的抢盐浪潮,商场的货架上和盐沾边的商品,统统成为抢购的对象。这表明,传言信息只要得到 “印证”,通过微博、论坛和手机短信等新媒体迅速传播,可以在数小时内演变成全国性的舆论恐慌事情。
四、合理想象:舆论恐慌心理的“科学逻辑”
不论是客观事实还是影子事实,它们只是造成舆论恐慌心理的外部条件,但不是舆论恐慌心理的充要条件。群体性舆论恐慌的最终形成,离不开人的大脑对他们所接收到的信息进行特殊地加工。想象是恐慌心理产生的必要程序。
(一)想象的心理活动机制
想象既是思维的高级方式,也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武器。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在范围上逐渐由近到远,人类已观测到的离我们最远的星系为130-200亿光年之间。超出这个范围的宇宙对我们来说,属于未知世界(宇宙)。对未知世界的了解,天文学家只能靠推测描摹其形状。这里所说的认知,仅是指粗线条的认识。迄今为止,即便人类能观察到的世界,未知的远远多于已知的。比如,地壳的内部情况、人体的灵与肉的结合、不少疾病产生的原因,这些看似简单的东西,科学家还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一个人皓首穷经,也无法掌握人类已有的全部知识。即便掌握了这些知识,仍然无法解释我们已经观察到的世界(宇宙)。人类征服世界的欲望如此强烈,征服世界的前提是全面认识世界。人类要合力实现这个目标,就只能通过想象的方式来认识世界。
正常的想象应该是愉悦的,给人以思维的快乐。然而,想象也并非总是愉悦的,有些想象给人带来的则是不安甚至是某种惶恐。恐慌是想象的产物,恐慌不是别的什么,是人对自己孤立无援的担忧。这种担忧的结果,通过想象往往变得更加糟糕,而不是相反。可能是外部环境的刺激,比如说,一个人在黑夜里看到恐怖电影,听到诡异的故事,不由自主地产生恐惧感;也可能因为周边环境的骤变,因为缺乏安全感强迫想象令人不寒而栗的结局。
按照普通心理学的解释,想象属于人类特殊的思维形式,是人在头脑里对已储存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形成新形象的心理过程。想象的主体是人脑,想象的客体是外部信息,想象的结果是产生新的形象或者图景。从目的论的角度看,想象可以分为无意想象和有意想象两种。无意想象是无目的的想象,人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随意流动,想象的结果可能有令人意外的收获,也可能一无所获。这类想象,结果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想象的过程给人以某种精神的愉悦。
当人们带着目的去想象时,人的思绪在意识的控制下,可以自觉地完成思维,这种形式属于有意想象。有意想象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主动式和被动式两种。有一定程度自觉性和计划性的想象,属于主动式有意想象。并非所有的人、所有的问题都能促使人主动去运用想象来寻求答案。有时候,麻烦从天而降,并且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做出抉择。在这种情形下,抉择的过程也就是被动式有意想象的过程,人们被迫在脑海里权衡利弊,把麻烦可能带来的多种结果进行分析。这表明,想象以现实为原材料,对未来的现实图景进行某种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想象的客体有某种现实的依据,但想象的结果却是虚拟的,是对未来世界的假设。这种虚拟的现实,我们称之为想象型事实。想象型事实建立在人的价值判断之上,包含着对结果趋利避害的特殊期待。正如萨特所说:“想象的意识活动是一种假定活动(position);这种假定是从一种非现存的不在场向一种现存的在现场的状态的过渡;在这一过渡之中,现实性是不存在的:作为意象的对象,虽然被假定是现存的,但却是不存在的。”[9]
(二)想象在舆论恐慌事件中的作用
对于成年人来说,多年的知识积累和社会阅历,可以基本满足他们对世界的认知需要,遇到问题时可以通过自己的想象预测未来,不至于产生恐慌感。这是就个人来说的。人是社会动物,社会中的人必须和外界保持接触,这种接触以能满足个人生存为前提。个人所遇到的问题,既是纯粹个人的问题,诸如个人情感的纠葛,也有社会性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物价上涨。对于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必然成为某个时期社会大众议论的对象,舆论的议题随之产生。
1、形成共同的想象客体
想象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集体。集体想象的进行,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想象客体,在同一时间段内进行,想象的结果具有高度的默契。集体想象的适用范围受诸多条件的限制,从历时的角度看,它多适用于对灾难威胁的应对。以清末京城的彗星与政局的关系传闻为例:“京师政界喧传咸丰年间曾见彗星,发现未几致有发逆之变,今当萑苻遍地,人心动摇之时,而彗星呈现,恐本年内将有不测之险。”[10]人心思安,但自然天象总会被某些人赋予神秘的色彩。当时,民智已开者毕竟为数尚少,不足以成为主流声音。即便当时的报纸也有辟谣的声音,民间主流声音还是担心灾祸的降临。毕竟,人们无法预知未来,对灾祸可能不期而至充满忧虑并不奇怪。正如李普曼所说:“现实世界太大,我们面对的情况太复杂,我们得到的信息又太少,舆论的绝大部分就必定会产生于想象。”[11]
舆论恐慌的形成,是公众集体想象的结果。社会处于变动之中,人们对社会现象的看法存在着差异,共识总是暂时的、相对的,且某种共识多形成于特殊或者巧合的时间段内。2013年3月,黄浦江漂浮死猪事件发生之初,民众急需了解事实真相,但是当时主渠道信息不透明,以致猪瘟爆发、转基因污染、水源安全被破坏等耸人听闻的信息开始不胫而走,部分市民开始产生恐慌心理。随后,任由政府宣布调查结果,也不能取信于公众。前面提及的江苏响水事件亦是如此,当地居民担心爆炸灾难的发生,连夜冒雪逃离家园。这些都是民众共同想象形成的舆论共识的结果。
集体想象所形成的舆论恐慌,源于他们对事件真实情况的确切需要。如前所述,恐慌不是天生的,恐慌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产物,需要后天特定原型的再现唤醒这部分记忆。对死亡的恐惧,是集体无意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型”。自然死亡发生在特殊的年龄阶段。对于年轻人来说,无意想象可能涉及死亡这个主题,但通常会转瞬即逝,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具备这个现实性;有意想象,必须具备特定的环境,如传闻将有特大地震,或者附近的化工厂可能发生大爆炸。地震和爆炸传闻属于非现实的信息,可以是真,也可以是假。在传闻阶段,人们无法预见危险是否真的发生。这时,他们只能采取非现实的方式进行预测和判断。自己和家人下一步的命运如何,既然没有现成的答案,就必须通过想象来完成。想象“注定要造就出人的思想对象的要素,是要造就出人所渴求的东西的;正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人才可能得到这种东西。”[12]
2、由想象虚拟非现实恐怖事实
想象活动虚拟出一个非现实的世界景观——想象型事实。虽然这种虚拟具有某种随意性,但在其虚拟的过程中,却是以主观的严肃方式制造出自己中意的世界图景,以慰藉自己的心理恐慌。在恐怖气氛笼罩下的想象,以强迫的方式施加给想象主体。2011年7月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网络版上介绍了日本横滨市立大学教授高桥琢哉研究小组对恐怖记忆形成机制的研究成果:大脑中神经细胞的联系会在体验恐怖的感觉后加强,从而形成对恐怖的记忆[13]。恐怖的记忆一旦被假设为真,必然会刺激人们的行为,从心理恐惧变成行为恐慌。舆论恐慌造成的是集体的非理性行为。这方面最经典的传播学案例是“外星人入侵地球”事件。1938年2月30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持人奥森·威尔斯在圣诞节特别节目中,将威尔斯的《世界大战》科幻小说改编成了广播剧。一连串的假新闻让许多民众信以为真,误以为真有外星人攻击地球事件发生,引发一场全美社会骚动,其紧张程度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600万人收听了广播,近170万人相信广播中的新闻是真的,而120万人吓得惊慌失措[14]。
同样的舆论恐慌在2011年2月的“响水事件”中反映得也很典型。舆论恐慌造成当地居民的慌乱景象,媒体有比较形象的记述。
“到5点半,路上警车和警察越来越多,可人们或者继续往前走,或者停下来看着,没有人愿意回头。”蔡中友对独家深读记者说。事后,响水县政府新闻发言人周厚良表示,当日加入逃亡大军的人涉及陈家港、双港、南河、老舍4个乡镇的30多个行政村,超过1万人。凌晨6点左右,孙晓健的手机上收到了官方辟谣的短信,折腾了大半夜,他再也没有心情看这条短信,随手删掉了。“[15]
舆论恐慌是非理性的,并不意味着集体想象是非理性的。产生于舆论恐慌前的集体想象,想象的结果非理性,想象的形式具有某种理性的色彩,因而,舆论恐慌的集体想象可以被称作“合理想象”,正是因为其包含有“合理”成分,想象成为舆论恐慌的基本逻辑。
3、“经验”和“科学依据”成为“合理想象”的素材
除了想象的客体之外,在想象和恐惧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中介物:经验。经验是自主的知识,它源于人生阅历点点滴滴的积累和总结。经验的地位,随着经验的被验证逐步得以强化,最终凌驾于外部知识之上。以“响水事件”为例,江苏响水县陈港镇的当地居民将空气中弥漫异味与爆炸相联系,显然,这个判断以经验为主。这样的经验来自于对以往经历的记忆,响水事件中的江苏响水县陈家港化工园区有40余家各类化工企业。2007年11月27日,园区内的原华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爆炸,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2010年11月23日,园区内的氯碱化工有限公司发生氯气泄漏,30多名员工中毒[16]。曾经发生的事故并不是陈家港每个居民都经历过的,但这两起事故的过程和危害,则通过当地居民的口口传播,已经家喻户晓,被纳入他们的“经验”体系,在遇到类似前兆时,这些“经验”快速成为“合理想象”的素材。
然而,经验能给人们提供的“合理想象”素材毕竟有限。在民智已经大开,科学素养整体大幅度提升的今天,舆论恐慌并不像媒体普遍批评的那样,主要是政府信息不透明和政府公信力低所致。突发性事件,政府掌握的信息同样匮乏,否则就可以避免许多灾难事件的发生。在经验判断的基础上,集体想象需要借助科学的威望,才可以变成舆论的共同意见,进而引发舆论恐慌心理。1915年,意大利气象学家拉菲尔·班单迪预测2011年5月11日意大利罗马会发生大地震。随着预言时间的迫近,罗马市当地居民同样变得恐慌起来。“地震”前夕,数千名罗马市民逃离家园避难。意大利当地媒体对民众进行的调查显示,每5名罗马人中就有1人选择在5月11日那天请假,带着孩子去海滩或者乡下避难。大地震的预言使得罗马市充满了恐慌的气氛,许多商店在11日前夕宣布临时停业,罗马市长不得不开通一条热线来安抚市民[17]。
在“科学外衣”的包装下,灾难性质的预言者运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推理,为其描摹的灾难场景提供合理性。“科学依据”一旦被利用,恐慌就会引起社会性的骚乱。从这个意义上说,想象,尤其是那些有着一定科学依据作基础的想象扮演了科学逻辑的角色,最终制造了舆论恐慌。这种夹杂了“科学逻辑”的合理想象,在台湾的14级大地震预言事件中,得到了验证。自称“王老师”的民众王超弘,预言2011年5月11日早台湾将发生14级大地震,届时会引发170米大海啸,造成百万人死亡[18]。在预言破灭前,王超弘的这个预言在岛内引起不小的恐慌。同样,抢盐风波也是有人将碘盐赋予能够预防核辐射的特殊功效,这种借助“科学道理”编造的事实,通过“科学”的形式让公众进行合理想象,最终多数人冲进大小商场和商店,目标直奔搁放食盐的货架。
经验加上“科学”依据,形成合理想象,经过传言散布,造成了一起又一起舆论恐慌事件。审视历史上历次著名的舆论恐慌事件,总能看到恐惧阴影下的人们,由于受到自己构想的虚拟环境刺激而慌乱不堪的特殊景观。
结语
安全感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只有这种需求得到了满足,人才可以向更高层级的需求迈进。人对安全感的追求源自于内心需求,由于这种需求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得不到满足,人处于缺乏安全感的状态,就会产生恐惧心理。当涉及公共安全的谣言和传言出现之时,个人安危受到威胁又无法及时得到安全保障,想象的惨重后果引发个人内心的恐惧,个人的恐惧相互传染,最后演变成社会性的恐慌。美国著名的舆论学家李普曼承认:“即使对训练有素的法学专家来说,把反应推迟到真相大白之后是多么困难。反应是突如其来的。虚构被信以为真,因为人们迫切需要这种虚构。”[19]
多年来,人们倾向于将舆论恐慌的酿成归咎于信息不透明,最终将矛头指向政府部门的实质,就因为其公信力欠佳②。通过前面对舆论恐慌心理形成过程的研究发现,舆论恐慌心理与信息供给不足相关,但这类信息并非政府所能掌握的信息。事实上,无论是美国的外星人入侵事件,还是俄罗斯军队入侵格鲁吉亚,以及意大利和我国台湾地区的511大地震预言,以及响水事件和抢盐风波,在短暂的恐慌时期抱怨政府信息不透明可以理解,但这种抱怨并不客观。事实证明,政府不是先知先觉的上帝,无法未卜先知某年某月某时某地将有灾祸发生。如果是政府事先掌握某种具有破坏力量的信息,政府肯定会采取措施,避免破坏性灾祸的发生。就我们能看到的舆论恐慌事件来看,并没有发现因为政府隐瞒信息造成舆论恐慌的案例。
舆论恐慌事件具有可重复性,必须从深层寻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舆论恐慌事件虽然有前兆,但其爆发却不以某个人、某个机构的意志为转移,其在本质上属于群体性心理活动产生的连锁反应。而舆论恐慌心理有自己专属的形成过程。影子事实,作为舆论恐慌心理的“逻辑起点”;合理想象,作为舆论恐慌心理产生的“科学逻辑”,这些都是导致舆论恐慌心理反复集中出现,舆论恐慌事件不断重复的重要因素。
舆论恐慌是社会心理的集中反映,无法完全避免。然而公众科学素养的提高,媒体报道的规范,将有助于减少舆论恐慌事件的发生。
注释
① 动物遇到险情,也有恐慌反应。这种恐慌通常被看作条件反射,即属于生理性反应。应该说,动物的恐慌反应源自经验。外部事件给其群体造成的伤害,形成某种原始记忆。以后遇到类似情形,出现某些惊恐症状。
② 2011年的响水事件和抢盐风波,媒体和研究者毫无例外将责任推给政府部门。根据媒体报道,这两起舆论恐慌发生后,相关部门都曾利用手机短信和新闻媒体发布信息,但这种澄清没有实质性效果。研究者因此将政府公信力欠佳作为造成舆论恐慌的重要因素。
[1] (瑞士)荣格.荣格性格哲学[M].李德荣,编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15-16.
[2] (美)C.S.霍尔,V.J.诺德贝.荣格心理学入门[M].冯川,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5.
[3] 草根牛博.一个非常罕见的“巧合”……[EB/OL].(2011-7-15).http://weibo.com/2077944001/l4EWLdaQt.
[4] 中国新闻网.福岛核电站或已泄露 反应堆辐射强度异常千倍[EB/OL].(2011-03-12).http://www.chinanews.com/gj/2011/03-12/2901252.shtml
[5] 靖鸣,童莉.格鲁吉亚“伊梅季”电视台假新闻事件的教训与启示[J].新闻记者,2010(5):3.
[6] 凌朔.“5·11”地震?罗马击碎百年传言[N].新民晚报,2011-05-12(A18).
[7] 新华纵横.“响水大逃亡”为何发生[EB/OL].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1-02/15/c_121081724.htm.
[8] 吴志刚.刊文称“硒盐防辐射”被指误导民众[N].东方早报,2011-03-24(A24).
[9] (法)让-保罗·萨特.想象心理学[M].褚朔维,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译者前言:3.
[10] 大公报.官场之迷信[N].1907-08-22(3).
[11] (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51.
[12] (法)让-保罗·萨特.想象心理学[M].褚朔维,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192.
[13] 蓝建中.日本发现人类大脑形成恐怖记忆部分机制[EB/OL].新华网(2011-07-16).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7/15/c_121674208.htm.
[14] 杨柳.史上十大假新闻:格鲁吉亚遭侵略 外星人入侵地球[EB/OL].(2010-03-18).国际在线,http://news.163.com/10/0318/10/6226Q8SF000146BD_6.html.
[15] 刘超群.响水“万人大逃亡” 那一夜[M].每日新报,2011-02-16(26).
[16] 新华纵横,“响水大逃亡”为何发生[EB/OL].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1-02/15/c_121081724.htm.
[17] 城市快报.百年前地震预言 引发罗马大恐慌[N].2011-05-12(6).
[18] 吴斌.台湾今日14级地震预言引发民众避难潮[EB/OL].中国台湾网(2011-05-11).http://news.cntv.cn/map/20110511/103547.shtml.
PsychologicalMechanismof“Information-Imagination”inthePanicofPublicOpinion
LIU Hai-ming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ianyang 621010,Sichuan,China)
The sense of security is a basic need of people. In real life,when the information which threatens the public security spreads and becomes the topic of the public,it will cause the event of the panic of public opinion and then disturb people’s normal life. It is important to explore how the panic of public opinion happens when the panic of public opinion is studied. Shadow facts are the prelude of the panic of public opinion and reasonable imagination is the initiator of the panic. The chain reaction from “Information” and “imagination” caus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nic of public opinion. The mechanism of “Information-imagination” in the panic of public opinion shows that the panic of public opinion is a group psychological reaction and that there is no close relation with information non-transparent of government.
Public panic; Shadow facts(Information); Reasonable imagination
2014-01-03
刘海明(1967-),男,河南新乡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新闻伦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微博语境下媒体应急管理研究》(13BXW041)和西南科技大学媒体应急管理科研团队的阶段性成果。
B842
A
1672-4860(2014)03-003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