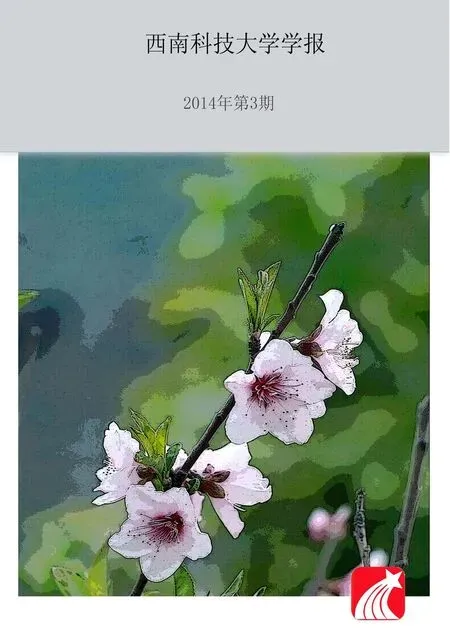基督教的生育观与西方女性作家的生育想象
李莹莹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贵州兴义 562400)
基督教的生育观与西方女性作家的生育想象
李莹莹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贵州兴义 562400)
从性别层面来看,以《圣经》为主的基督教的生育观植入了十分浓厚的父权制思想,其中的女性生育遭到了深重地压制。这种压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上帝造人神话对女性生育能力的篡夺;以上帝的名义压制女性生育能力的再现;管控女性的生育活动。而西方的女性作家基于自己的身体体验,其创作与基督教中的生育观念形成一种互补,从而给读者展现了一系列具有女性特色的生育想象。
基督教生育观;父权制;西方女性作家;生育想象
基督教的生育观主要源于《圣经》。女性主义的相关研究发现,《圣经》是经过父权制的方式编辑而成的[1],其中蕴含了很多父权制的思想。基督教的生育观与性别问题密切相关,其中也植入了十分浓厚的父权制思想。从性别层面来看,《圣经》中女性的生育遭到了十分深重地压制。心理分析学家霍妮(Karen Horney)在研究中发现,生理上并不具备怀孕生子能力的男性存在“子宫嫉妒”的心理。她认为男性对于女性能够怀孕、分娩,对于女性的母亲的身份以及乳房、哺育等功能怀有强烈的嫉妒心,这种嫉妒心使得男性在无意识中贬低母性[2]。在基督教的生育观中,这种“子宫嫉妒”表现为男性对于女性生育能力的篡夺和控制。
一、单性的造人神话
很多文化中都存在男性生育的想象。古希腊神话中,雅典娜诞生自宙斯的头颅,普罗米修斯用泥土捏出了人形;中国神话中也有鲧生禹的传说。这种生育想象有助于确定男性在生育中的地位。在《圣经·创世纪》中,我们同样能看到这种男性生育的想象——上帝造人。创世纪的上帝造人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用言说的方式创造人类;一个则是利用尘土造人。不论是哪种造人的版本,都遮蔽了女性的生育力。
加拿大的文学评论家诺索普·弗莱指出,基督教信仰中的上帝是一个男性神,跟一般民间故事中大地母亲繁衍万物的神话有很大的不同,其创生的方式就是“说”[3]。创世纪的开篇就是上帝造物的过程:“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创世纪1:3),上帝用6天的时间创造世间万物,继而造出了人类;“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爬的一切昆虫’”(创世纪1:26)。这里描述的上帝创世及造人是以命令的口气实现的,使用的工具是语言。这种创造丝毫不涉及女性的生育力。叶舒宪曾指出,创世神话有两种最常见的母题:“造”和“生”。“前一母题讲述某一至高的创世主神——常为男性神——用其特有的超自然力量与智慧创造出世界万物,并规定其存在秩序。后一母题则将宇宙的由来描述为生物性的生育过程。”[4]而创世纪所述的创世神话就关乎于“造”的母题。
上帝造人的另一个版本则更偏向于造人的具体过程:“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创世纪2:7)。这一创生过程与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造人过程十分相似。普罗米修斯的造人同样以泥土作为原料,但不同的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给予人灵性的神并不是造人的普罗米修斯,而是雅典娜,“她惊叹这提坦神之子的创造物,于是便朝具有一般灵魂的泥人吹起了神气,使它获得了灵性。”[5]雅典娜作为一个女性神,在造人的活动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赋予人类灵魂。而在创世纪中上帝造人的过程没有别人的参与,上帝既创造了人的肉体,也创造了人的灵魂,这种全能的创造正说明上帝造人对于女性生育能力的排斥。
在这一版本的造人故事中,上帝并非如前一版本中将男女一同造出,而是首先造出了男人亚当,然后再抽出亚当的肋骨造出了女性夏娃。这一造人的次序再次强调了男性的诞生在女性之先,而女性孕育生命的能力则被视为上帝这一男性神的赐予,从而将女性的生育能力纳入到男性的管辖范围之下。
费尔巴哈指出:“上帝的生殖,当然不同于凡俗的、属自然的生殖,是超自然的生殖……是缺乏使生殖得以成为生殖的那种规定性的生殖,因为,这里面缺乏性的差异。”[6]基督教中上帝的创世完全是一种男性神单性的创造工作,与女性无关。这种创世观确立了上帝的唯一性和权威性,压制了女性的创造力,体现出这一神话产生时男权家长统治的社会现实。
二、被遮蔽的女性生育
除了上帝造人之外,《圣经》中还多次出现了对女性生育的描述,但不论旧约还是新约,都一致地将这种生育置于上帝的庇佑之下,强调上帝对于女性生育的控制。当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后,夏娃怀孕生下了该隐,她认为是“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创世纪》4:1)。这样的例子在旧约中十分常见,参孙的降生便是耶和华的赐予(《士师记》13:2);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生育能力也视乎于上帝,在上帝开恩之后她才诞下撒母耳(撒母耳记上1:5-19)。《诗篇》中更是多次称颂耶和华,认为“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诗篇》113:9)。“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诗篇》127:3),而一旦上帝发怒,他就会收回这种赐予:“至于以法莲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何西阿书》9:11)。这些言辞都体现出了上帝作为创生者的大能。依据信徒的表现,上帝决定什么时候赐予或者收回女性的生育力。也就是说,女性的生育力成为了体现上帝赏罚分明的工具。
新约中体现上帝控制女性生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耶稣的降生,对于这一事件记叙最为详尽的就是路加福音。为了对耶稣的降生进行铺垫,同时也为了显现上帝的大能,在叙述耶稣降生之前,路加福音还记叙了年迈的伊丽莎白在上帝的启示下怀孕生下施洗约翰的故事(路加福音1:8-25)。而童女马利亚的孕育也是上帝的命令:“天使对她说:‘马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取名叫耶稣’”(《路加福音》1:30-31)。从表面上看,马利亚的怀孕是上帝的赐予,说明了其虔信的品质得到了上帝的认可。但如果从性别层面来看,作为一名女性的马利亚却无法自主自己的身体,她是否怀孕则取决于上帝这一男性神的意愿。而马利亚的应许则可以视为女性对于被支配的地位的接受:“马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路加福音》1:38)。
新约强调了马利亚处女的身份,也就是说,马利亚的生育与两性的性爱没有任何关系,她的生育是上帝向世人展现的奇迹。更重要的是,马利亚作为圣母是上帝赐予的,耶稣仍然被称为上帝的儿子。可见,此处的生育仍是上帝的单性创造,女性的生育能力仅仅是上帝创生的工具而已。基督教通过这种方式去除了圣母身上性的特质,只保留了其生殖力,并且将这种生殖力置于上帝的管控之下。这种手段以牺牲其性的特质的方式,提升了马利亚的地位,并且为信徒们塑造了一个圣洁的母亲的典范。
《圣经》中的女性常常以两种面貌出现:一种是淫妇的形象,这类形象突出其性的特征,往往作为负面形象,成为罪恶的源头(如《箴言》7:1-27;《何西阿书》2:2-5;《启示录》17:1-18);另一类就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贤妻良母,这类形象因其崇高的道德品质而得到神的祝福,因而也往往是多子多福的形象,如路得。由于《圣经》中,尤其是旧约时代评判女性的标准很大程度上与生育能力有关,这也使得很多女性自觉自愿地成为了生育的工具。
上帝在与挪亚订约的时候就指出“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荣”(《创世纪》9:7)。因此,能否传宗接代就成为了古代希伯来女性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甚至有无子的寡妇下嫁丈夫兄弟的法令(《申命记》25:5-6)。为了符合这一标准,他玛才会在丈夫死后设计与公公犹大同房,为犹大家传下后裔(《创世纪》38:1-29);雅各的两个妻子利亚和拉结为生育而互相竞争,发展到让使女代为怀孕的程度(《创世纪》29:31-35;30:1-24)。这样的评判标准使得女性沦为了生育的工具,母亲的其他性格品质被抛开,基本上仅剩下生育孩子的形象。甚至连后世基督教中代表慈爱、善良的圣母玛利亚在《圣经》中也只是模糊不清的信徒和生育者的形象。
《圣经》最大限度地遮蔽了女性的生育能力及其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从而凸显出了上帝与其子民的父子关系。上帝在《圣经》中常常以天父自居,如诗篇《神对大卫的应许》一诗所言:“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诗篇》89:26-28)。新约中刻意淡化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以此保证信徒对于天父上帝独一无二的爱。耶稣曾训诫他的门徒“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10:37),而当有人告诉他,他的母亲和兄弟想要与他见面说话时,“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马太福音》12:48-50)。可见,耶稣所宣扬的教义否定了人间的亲情,而用人与天父之间的关系取而代之,从而进一步强调了上帝的父性威严。《圣经》中天父的形象时而威严,时而仁爱,比之于其中面容模糊的母亲形象要生动得多。
三、管控女性生育
除了将男性凌驾于女性生育之上而外,《圣经》中还对女性生育进行了十分严格的管控,这种管控或隐含在神话故事中,或以法律条文的方式出现,对女性的生育加以束缚和控制。在创世纪中,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之后招致了上帝的惩罚,而生育之痛就是上帝对夏娃施加的惩罚:“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创世纪》3:16)。这一惩罚强调了女性生育与原罪之间的关系,“原罪之秘密,就是性欲之秘密。所有的人都在罪恶之中受胎,因为他们的受胎是伴同感性的,也即属自然的喜悦和乐趣的。生殖作用,作为一种富有乐趣的感性作用,是一种有罪的作用。罪恶从亚当开始一直繁殖到我们,这只是因为繁殖是属自然的生殖作用。”[7]
而后世的基督教则将这种惩罚变本加厉,认为生育的痛苦是上帝对于人类的惩罚,因此反对在女性分娩的过程中减轻女性的痛苦。1591年,一个助产士辛普森·艾格尼丝因为给分娩的女性服食鸦片减轻分娩的痛苦,而被处以火刑[8]。
对于女性生育的管控还以法律条文的方式出现,除了上文提到的寡嫂嫁叔的条例之外,《利未记》还有这样的条例:“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她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妇人在产血不洁之中,要家居三十三天。她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她若生女孩,就不洁净两个七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产血不洁之中,家居六十六天”(《利未记》 12:2-5)。生育的女性被视为不洁,必须要经过献祭才能恢复洁净,这种不洁甚至因生育女婴而加倍。这样的规定强调了女性生育中不洁的一面,而回避了其中崇高和牺牲的一面。
在《圣经》的基础上,后世的基督教教会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定,规范信徒的生活。其中涉及女性生育的一些条款,虽然基于不同的目的,但实际上却成为了控制女性身体及生育的工具。旧约时代的希伯来人认为多子乃是有福,无后是咒诅(如《创世纪》30:2; 48:4;《申命记》7:13-14)。《新约》中则没有强调这一神谕,而是认为只要虔信上帝,有无子女都是大福。但由于受到“生养众多”这一观念的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基督教教会都反对避孕。直到1968年,梵蒂冈的通谕仍然认为:“男人,在使用避孕工具的环境中长大,也许将最终丧失对女人的尊敬,并且不再关心她们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平等,也许会仅仅把她们当作一个满足私欲的工具,并且不再把她们看作是自己心爱的、尊敬的伴侣。”[9]虽然基督教反对避孕的目的是希望人们不只关注性爱的欢愉,而要注意精神的沟通。但由于无法采用避孕手段,很多女性丧失了对于自己身体的掌控权,沦为了生育的工具。社会活动家桑吉尔之所以会涉足于避孕药的发明,就是因为她曾目睹自己的母亲因为无法避孕,在多次生育后体虚死去[10]。
同样的例子也表现在基督教禁止女性堕胎行为的规定上。早期基督教法规《十二使徒遗训》中就明确规定“不可堕胎杀孩童”,公元4世纪左右,从西方教会到东方教会都一致谴责堕胎的行为。“西方教会不仅谴责堕胎,而且把堕胎的妇女赶出教会,在她离世前绝不接受她对自己行为的忏悔。”[11]“马丁·路德声称‘那些不关注怀孕的妇女,对胎儿冷漠的人,都是杀人犯,都犯了杀亲罪’。约翰·加尔文说:‘未出生的孩子……虽然还在母腹当中,却已经是一个人,不应当剥夺他尚未开始享受的生命。’”[11]虽然这些规定的初衷在于讨论胎儿的人权问题,这一问题直到今天都还很有争议。但如果抛开胎儿的人权这一极富争议性的话题,单从性别层面来看,这样的规定则意味着女性无法选择是否需要生育,这同样意味着女性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
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强调了女性生育与原罪的关系,甚至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管控女性的生育,体现了父权制思想的影响。而后世的基督教教会虽然抛弃了《圣经》中一些带有父权制影响的条文,制定的与女性生育有关的规定基于宽容和仁爱的思想,但这些规定在很大程度上仍损害了女性对于身体的主导权,让女性在面临生育问题的时候常常遭遇两难的选择:如果不避孕,也不能堕胎,那么就陷入无限的生育循环中,沦为生育机器;而如果避孕或堕胎,则会受到违背教义的谴责,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
四、西方女性作家的生育想象
西方女性在基督教的背景下成长,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由于其生理特征,女性十分关注生育的问题。西方女性主义者对上帝作为一个父亲神却拥有创生能力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进行了深入地思考。以罗斯玛丽·鲁瑟(Rosemary Ruether)为代表的西方女性主义神学家认为,上帝就是一个威严的父权制家长的形象,把信徒当成“妻子”和“孩子”,要求他们绝对服从[12]。她们认为基督教中的上帝创造了人类的说法,是把男人看成是女人的源头,因而女人必须听命、服从于男人[13]。这些思考质疑了上帝的权威,也挖掘了掩藏在基督教神话中的父权社会实质。而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y)在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中不仅质疑了上帝造物的权威性,而且也进一步探讨了男性单性生育的危害[14]。
除了反思基督教中的父权制影响之外,一些女性主义者开始尝试重新解读《圣经》,试图从中发掘出被压抑的母性特征。德国女性主义神学家温德尔(Elisabeth Moltmann-Wendel)提出“上帝并非男人的梦,并非英雄史诗,并非以胜利者姿态出现的救世主。上帝就在没有教会去寻找他的地方。上帝就在女人们生活着并确立其价值之处。在那里,上帝也被当作女性,当作母亲,当作智慧来崇敬。”[15],她还指出“在希伯来文里,上帝的慈爱意味着子宫。”[16]这种对于上帝的重新解读带有很强的女性特征,体现了女性从自我特征出发,对于母性上帝的期许。被认为最早用英语写作的英国女作家朱丽安(Julian of Norich)也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来思考上帝和耶稣,在其代表作《上帝之爱的启示》(TheShowingsofJulianofNorich)中,她把上帝的代言人耶稣当成了养育信徒的母亲,并认为耶稣体现着母亲一般的仁爱[17]。这种想象,把上帝的创生能力与母亲的生育能力结合在一起,通过赋予上帝母性的特质而淡化了基督教上帝父权神灵的特征。父权的上帝也因而变成了女性的上帝。
美国最早的女诗人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AnneBradstreet)作为一个虔诚的清教徒,不仅歌颂清教徒的家庭生活及对孩子的热爱,还在《作家致她的书》(TheAuthortoHerBook)一诗中将其诗歌创作比作自己的孩子,把母性与创作结合,将当时清教徒社会中“女人是多产的”的生育观念引申为女性的创作能力,从而获得女性创作的合法性①。
还有一些西方的女性作家在创作中描写了女性生育的体验。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的诗歌《三个女人》(Three Women)对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地开掘。诗歌表现了3个怀孕的女人的声音,她们分别是年轻的女人、秘书、妻子。虽然3人的身份不同,孕育的结果也不一样(秘书流产了),但她们对于生育的态度却十分相似——充满了焦虑和恐惧。生育的痛苦以及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异己感被作者放大,这种生育经验不同于基督教中宣扬的圣母马利亚的崇高和牺牲,而是一种从女性自身的身体体验出发发掘出来的生育的另一面——充满了恐惧和痛苦的一面。
比之于基督教中因原罪而产生的生育痛苦,一些女作家认为生育的痛苦更多的来源于女性无法掌控自己生育的痛苦。在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宠儿》(Beloved)这部作品中,黑人女奴塞丝因为不愿意幼女宠儿成为奴隶而杀死了她,却陷入了以母爱的名义的正当性以及杀婴带来的强烈罪恶感的矛盾情绪中。莫里森将压在黑人女性身上的种族和信仰的重负很好地反映了出来。类似的作品还有沃克(Alice Walker)的《紫颜色》(TheColorPurple)。其中以西丽为代表的黑人女性在传统的男性社会中无法掌管自己的身体,她在未成年的时候就被继父强暴,生下的孩子还被送走,下落不明。最终西丽在对上帝救赎的质疑之后,找回了自我和自己的孩子,成为了自己身体的主人。
基督教对于女性的生育有一套系统的严格的规定:一方面,基督教以人类的原罪将生育视为上帝的惩罚,否定了两性性爱的快感;一方面,用上帝的威严否定了女性处理自己身体的权力。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通过其创作质疑了这种操控的正当性。她在《使女的故事》(TheHandmaid’sTale)中虚构了一个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国家——基列国,在这里,女性的身体,尤其是女性的生育被严格地管控起来,性爱的快感被禁止,生育变成纯粹的传宗接代的仪式。这种反乌托邦的书写以极端的方式探讨了生育被管控之后可怕的景象,对基督教的生育观进行了反思。可以说,在基督教的影响下,西方女性文学对于生育的描写带上了强烈的宗教色彩。西方的女性作家基于自己的身体体验,其创作与基督教中的生育观念形成一种互补,从而给读者展现了一系列具有女性特色的生育想象。
结语
正如E·M.温德尔在《女性主义神学景观》中所认为的,基督教的宗教经典《圣经》中充满了父权制的思想。从基督教的生育观来看,这种父权制思想更加明显:《旧约》中上帝造人的神话故事反映了一种男性单性生育的想象,这种想象排斥了女性在生育中的位置;《新约》中圣母马利亚接纳了上帝恩典而以处女之身生育了耶稣基督,这一事件的叙述非但没有改变这种男性单性生育的想象,反而让女性沦为了上帝创生的工具。除了这两个典型的例子而外,《圣经》中的很多条文都体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生育的严格管控。后世的基督教教会在制定与女性生育相关的规定时,尽管抛弃了《圣经》中充满男权意味的条文,但其中的一些规定仍然损害了女性对于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因而可以说,基督教的生育观体现了父权制思想对于女性生育的控制。
尽管西方女作家生活在基督教背景之中,她们的思想和创造力并没有被基督教充满父权制思想的生育观局限。通过多样化的思考和创作,西方女作家给读者呈现的是丰富多彩的生育想象,其中既有顺应基督教生育观而尝试在其中加入女性特质的努力,也有针锋相对地对基督教生育观中的父权制思想的批判,还有女作家试图发掘出与基督教生育观不一样的女性生育体验……这些具有女性特色的写作让读者看到了与基督教生育观不一样的,能够与之互相补充的生育想象。
注释
① 在《上帝之爱的启示》在第60章,她写道:“母亲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喂养乳汁,但是我们的母亲基督用圣餐喂养我们,这是生命中最珍贵的食物。……母亲可以轻轻地把孩子揽在怀中,但是我们可爱的母亲可以让我们从她体侧的伤口中进去,并在那里享受天堂的欢乐。”参见张亚婷.与基督对话:英国中世纪女性的写作政治[J].泰山学院学报. 2007,3.
[1] (德)E·M. 温德尔. 女性主义神学景观[M]. 刁文俊,译. 北京: 三联书店,1995,8.
[2] Horney,Karen. Feminine Psychology[M]. W.W. Norton & Company,Inc. 1973: 60.
[3] 刘意青. 《圣经》的文学阐释——理论与实践[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15.
[4] 叶舒宪. 老子哲学与母神原型[J]. 民间文学论坛,1997,1.
[5] (德)施瓦布. 希腊神话故事 [M] . 刘超之,艾英,译.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1:1.
[6] (德)费尔巴哈. 基督教的本质[M]. 荣震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4:291.
[7] (德)费尔巴哈. 基督教的本质[M]. 荣震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4:398.
[8] (美)彼得林娜·布朗.夏娃:母亲走过的历史[M].刘乃菁,刘剑,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12:46.
[9] (美)阿斯贝尔.避孕药片——一个改变世界的药物传奇[M].何雪,晓明,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6:304.
[10] (美)阿斯贝尔.避孕药片——一个改变世界的药物传奇[M].何雪,晓明,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6.
[11] (美)施密特. 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M]. 王晓丹,赵巍,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3.
[12] 高师宁. 一个女性眼中的女性神学[C]. 基督宗教思想与21世纪. 罗秉祥,江丕盛,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0:219.
[13] 黄怀秋. 永远的女神:从女性神学到女神学[C]. 基督宗教思想与21世纪. 罗秉祥,江丕盛,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0:247.
[14] 李莹莹. 生育的另类想象——《弗兰肯斯坦》中的生育再现[J].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2,4.
[15] (德)E·M. 温德尔. 女性主义神学景观[M]. 刁文俊,译. 北京: 三联书店,1995,8: 6.
[16] (德)E·M. 温德尔. 女性主义神学景观[M]. 刁文俊,译. 北京: 三联书店,1995,8:93.
[17] 苏忱. 中西方女性文学身份建构的比较研究[J]. 江淮论坛. 2007,1.
BirthConceptofChristianityandBirthImaginationofWesternFemaleWriters
LI Ying-ying
(Xingyi Normal College for Nationalities,Xingyi 562400,Guizhou,China)
From a gender viewpoint,the idea of patriarchy was deeply rooted in the birth concept of Christianity,especially inTheBible,which suppresses women’s birth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 myth that God created man deprived women of their birth ability; the reoccurrence of suppressing women’s birth in the name of God; the control of women’s birth activities. Based on their body experience,the works of western female writers showed a complementation with the birth concept of Christianity,thus displaying a series of birth imagination with female characteristics.
Birth Concept of Christian; Patriarchy; Western Female Writer; Birth Imagination
2014-01-03
李莹莹(1979-)女,贵州省兴义人,副教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该文是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基督教与西方女性文学研究》(批准号:GD10CWW07)阶段性成果。
I04
A
1672-4860(2014)03-004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