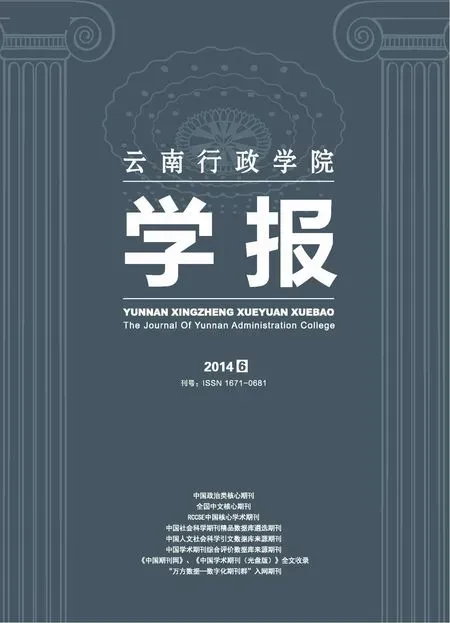“各得其所”与实现的正义
张剑源
“各得其所”与实现的正义
张剑源
(云南大学法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从“建构的正义”到“实现的正义”,正义理论发生了重要转向。与过往正义理论相比,“实现的正义”观特别强调正义不只是物质的分配,其更是“可行能力”的赋予;强调正义不是先验的,而是实现的;强调正义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建构,而是要在社会民主基础方能实现的现实制度安排。“实现的正义”观认为,正义难以实现的症结并不在于正义理论建构的困难,而恰恰在于社会生活中僭越行为和不正义现象的广泛存在。因此,欲真正实现正义,需要在消除僭越的基础上实现一种每个人“各得其所、各尽所能”的社会和谐适配状态。
正义;实现的正义;各得其所;阿玛蒂亚·森;僭越
一、正义如何可能?——过往理论及其问题
关于正义如何可能的问题,曾产生出很多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一种理论以自由为主要主张,意在限制国家的干涉,以人的自由为制度设计的第一位考虑;另一种种理论以平等为主要主张,意在通过绝对平等的制度设计来保障正义的实现;还有一种理论被称为是一种“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是一种以自由优先,同时注重公平的正义观。
在哈耶克和诺齐克看来,正义的首要价值(甚至是唯一价值)是自由,制度设计应该首先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不受损害。哈耶克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努力运用我们所掌握的政治组织,为贫弱者或为不可预见之灾难的受害者提供福利救济。事实可能的确如此,为防阻一国公民所可能共同面临的某种危险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给予他们每个人以保护以使其免受这些危险的侵扰。诺齐克则说,富人志愿地以其资源帮助穷人符合正义原则,但由国家实行再分配则是侵犯权利的严重事情。他甚至认为,对劳动者所得征税等于强制劳动(on a par with forced labor),因为被征税者的部分劳动被无偿地拿走了,尽管是拿去用于公益事业或支援贫困者。
诺齐克在对洛克有关私有财产占有理论的修正的基础上提出:如果一个人对原始公有之物的占有未导致其他人境况的恶化,那么他的占有就是合法的。比如,设想有一个两人世界,甲把公有土地占为己有,乙就只能给甲当雇工,如果甲非常能干并善于安排,使土地的总产量大大高于以前,他可以使乙的所得高于以前,如果不谈乙在生产过程中受支配这一点,仅从分配结果考虑,那么甲的占有是合法的。
公平主义论的倡导者科恩将辩论的焦点指向了诺齐克。科恩说,为什么是甲而不是乙?即使乙的境况可能在甲的带领下有了一定的改善。他认为,按贡献所得的原则尊崇自我所有,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原则。他的解决办法是不承认自己创造和生产的东西属于自己,不承认能力强的人应该多得。他寄希望于国家干预,他理想的制度是通过税收系统对收入进行再分配,使人人完全平等。
罗尔斯所做的努力则是试图去平衡自由和公平之间的紧张。他提出了正义的两项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2)依系于地位和职务(的机会)向所有人开放。根据这两项原则,罗尔斯认为,自由优先于平等,自由的平等原则又优先于差别原则。在罗尔斯看来,鉴于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特征和条件,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比一个效率优先但却无法实现普遍的公平正义的社会更值得欲求,也更能够保持理性多元化民主社会的长治久安。无论以何种理由,都不能将哪怕是极少数社会成员的权利要求排除在社会的组织安排之外,更不能出于某种或者某些社会功利或效率的考虑牺牲哪怕是极少数社会成员或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否则,该社会或社会状态就是非正义的。
总的来看,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社群主义者,不管他们所持的是自由的主张还是平等地主张,抑或如罗尔斯一样,提出一种更具操作性的、具有一定层次的正义主张——实际上都从不同的侧面回答了正义如何可能的问题。然而,一旦将视角从理论诉诸于实践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以上的理论在实践上依然面临着一系列不可克服的难题。
首先,若将这些理论看作是一种有关实现正义的制度设计,我们不难看出这些理论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都在于通过物质的更好分配和权利的保障来实现正义。然而,这些理论或许都忽视了人本身所具有的无限潜能。或者可以说,很多时候人们所希冀的并不只是物质或权利的赋予,人们所希冀的恰恰是能够在自由和平等(让渡)中作出自由选择的可能。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所提供的是一种正义的结果,而它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提供出实现这种结果的可行手段;其次,人类社会生活是及其复杂的,自由主义、公平主义和“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为人们安排了可能的法权秩序,但就如上边所说,这些理论与制度安排从根本上来说乃是建构的、指向的是结果。在其各自的制度设计中,我们无法看到它们对现实生活复杂面向有效回应的可能。甚至可以假定,正义虽然可以被建构,然而,一旦不正义产生,人类将如何适从?这是这些理论所无法回答的;再次,不管是自由主义、公平主义还是“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的产出都是在西方社会语境中阐发出来的。西方社会所推崇的民主、法治、市场化原则乃是实现这些正义主张的先决条件。然而,世界发展不平衡和人类社会空间上的巨大差异恰恰可以表明:这些正义主张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生态中是否会遇到极大的挑战?而恰恰,这种挑战在殖民地国家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困扰着后罗尔斯时代的政治哲学思考,同时也在理论层面上困扰着人们对贫困、战争和底层民众的艰难生活等问题的哲学思考。在这样的困境中,来自第三世界的学者作出了十分积极的回应。
二、实现的正义:一种新的论说
印度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阿玛蒂亚·森(以下简称:森)通过长期的对饥荒、贫困的研究指出,贫困的根源并不总是物质的匮乏,而在于可行能力的剥夺。
森首先对功利主义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功利主义漠视分配,忽略权利、自由以及其他非效用因素。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它很容易被心理调节和适应性态度所改变。在森看来,当那些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人在长久遭受剥夺和不公正对待的情况下,极有可能会在逆境之中变得易于忍受和缺失对不公正的反抗。他说:“受剥夺的人们出于单纯的生存需要,通常会适应剥夺性环境,其结果是,他们会缺乏勇气来要求任何激烈的变化,而且甚至会把他们的愿望和期望调整到按他们谦卑地看来是可行的程度。”也正因为这样,“快乐或愿望的心理测度具有太大的弹性,因此不能成为被剥夺和受损害状态的可靠反映。”森同时对自由至上主义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诺齐克的“灾难式道义性恐慌状态”(人们通过行使这些权利而享有的“权益”,一般来说,不能由于后果而被否定,不管那后果是多么糟糕)“会导致损害人们用以实现他们有理由认为很重要的事物,包括逃脱可以避免的死亡、享有充足的营养和保持健康、有能力阅读、写字、计算等实质自由。这些自由的重要性不能因为‘自由权优先’的理由而被忽视”。自由权优先的信息基础是很有局限性的。
森认为,不管是功利主义的心理测度还是自由优先的基本物品(social primary goods)和实际收入,这些东西所呈现出来的“效用”均不能实际反映出福利评价的结果。正因为人与人之间在个人异质性、环境多样性、社会氛围差异、人际关系差别以及家庭内部分配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对人的评价单从物质角度来进行的话势必会存在很大的问题。森指出,“重点必须是商品所能产生的自由,而不是商品自身”。在此基础上,森提出了他的“可行能力”方案。
合适的“空间”既不是效用(如福利主义者所声称的),也不是基本物品(如罗尔斯所要求的),而应该是一个人选择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实质自由——即可行能力。…一个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或者用日常语言说,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自由)。
“可行能力”理论的提出从根本上扭转了政治哲学对正义的关注从物到人的转变。可行能力方法具有的广度和敏感度使它有空阔的适用范围,能够对一系列重要因素给予评价性关注,其中某些因素在别的方法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忽略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森对我上文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作出了有力的回应。
对于第二个问题:作为一系列的制度设计,过往正义理论是否一劳永逸的解决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面向?森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过往的正义理论都是一种建构意义上的正义理论,所提出的是一种先验的(transcendental institutionalism)、安排的正义(“arrangement-focused”approaches to justice)理论。这种理论始于霍布斯于17世纪创立的社会契约论,经卢梭、康德、罗尔斯等而得以发扬光大。但是,这种先验的正义观在后来遭到了极大的批判,正义不再认为是先验的,安排的,而应该是实现的(“realization-focused”approaches to justice)。
关于这一问题,18到19世纪,大批思想家都对实现的正义理论的发展作出的极大的贡献,包括亚当·斯密(Adam Smith)、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沃尔斯顿克拉芙特(Mary Wollstonecraft)、卡尔·马克思、约翰·密尔等。他们不是先验地去寻找正义的设计,而是通过自己所观察到的社会发现不正义的存在。从对正义的建构(安排)到对不正义的发现,政治哲学对正义的理解正在悄悄发生着改变。1995年所罗门在《对正义的热情》(Robert C.Solomon)中写道,正义是“一套需要苦心经营的复杂热情,而不是凭空设想出来的抽象原则……正义始于同情和关心,而不是原则和观点。但是一开始,它也涉及一些负面的情感,像嫉妒、愤怒、怨恨、被欺骗、被忽视的感觉,以及想要报复的欲望。”最后,所罗门暗示,“正义感的出现就像这一切的归纳,最终使私人受到的不公正得到合理化解决”。而早在1987年,沃尔加斯特(Elizabeth H. Wolgast)在《正义的文法》一书中也注意到了,对因果性解释的欲望——也就是要认真地思考“不公正的感觉”促使知识分子努力与建立一种正义理论,她强调,“非正义”一词在文法上实际上早于“正义”一词出现。而阿玛蒂亚·森的哈佛同事迈克尔?桑德尔(M ichael·J.Sandel)也在新书《正义:做什么事才是对的?》中指出,“摆脱暴行的关键就是对非正义有所察觉”。虽然阿玛蒂亚·森既没有提及所罗门或是沃尔加斯特的研究,但是森继承了这种对正义的理解的进路。
森通过三个来自印度梵文中的单词给我们呈现了这样的一种对正义理解的深化过程。第一个单词niti,是指组织、规则和制度,用英语可以表示为rule或者regulation,是一种文本意义上的规则,是社会制度建构的必要的条件,但不是充分的条件。第二个单词nyaya,是指实现的正义,是超越文本的,有足够的措施予以保障的正义的制度设计。森指出,nyaya不仅仅是一个对制度、规则进行评价的制度,其同时也是对社会自身的评价。不管这个社会的制度设计多么完美,只要“大鱼吃小鱼”的事例仍在发生,就是对人类正义在nyaya层面上的违背。因此,还需要考察第三个单词matsyanyaya,这个单词意指“鱼类的正义”,也就是可以允许大鱼吃小鱼的存在。它告诉我们,弱肉强食违背了人类的正义,应该在人类中避免“大鱼吃小鱼”的诅咒乃是正义的基本原则。可以说,从正义/非正义理论发展的视角可以看出,有关公平和自由的讨论如果只凭一套建构的、安排的理论和制度设计是无法回应社会发展的复杂面向的,也并无可能对社会问题提出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对非正义的发现和克服日益成为了政治哲学的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任务。
对于第三个问题:自由和平等的正义以及对不正义的克服之于复杂的世界秩序和复杂的地理空间又是何种状况?不难看出,在自由至上主义者(诺齐克、哈耶克等)、自由优先主义者(罗尔斯等)、功利主义者(密尔等)、平等至上主义者(德沃金等),甚至对自由主义提出深刻批判的社群主义者(如麦金泰尔、桑德尔、沃尔泽等)看来,正义都必须是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才有其实现的可能的。也就是说,任何的理念和设计都必须有合意的基础。森指出:“在判断经济发展时,仅仅看到国民生产总值或者某些其他反映总体经济扩展的指标的增长,是不恰当的。我们必须还要看到民主和政治自由对公民的生活及其可行能力的影响……在普通民众几乎没有政治机会来表达看法、更无法与掌权的当局争论的情况下,完全不清楚如何能检验这个命题。对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轻视,当然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政府领袖的价值标准系统的一部分,但是把它当做是人民的观点却是大成问题的”。因此,既要看到民主自身的重要性,也要看到它的工具作用和建设性价值。从这里看来,森的民主主张同他消除不正义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在罗尔斯等西方政治哲学家的视域中,民主并非一个十分困难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正义的实践是可以顺利的在一个民主和开放的框架下进行的。然而,森所要面对的是第三世界并非充分民主和开放的社会体制下的贫穷和能力剥夺的问题(森同时对李光耀等并非落后国家领导人的非民主理论进行了批判)。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国家扶助”和“市场开放”之上,森认为实现民主更是实现人自由发展的重要保障。
总的来看,从罗尔斯到森,政治哲学对正义的解释有了较大的发展。首先,正义理论从一种建构的正义向一种实现的正义的转换。与其说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复古,倒不如说这是一种对人类现实苦难的大爱和大智慧的发展;其次,正义理论从专注物质的正义到专注人本身的正义的发展,而基本能力的提出则成了这一发展的标志性产物;再次,森注意到了正义实现的社会民主基础,若非这一点,我们只会继续忽视掉正义实现可能会遭遇的巨大挑战。
三、僭越与不正义——对“实现的正义”观的挑战
从建构的正义到实现的正义,政治哲学的转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正义的新的视角。然而,“实现的正义”若不能充分注意到实践面相上阻碍正义实现的诸多障碍,“实现的正义”反而有可能会复归到一种单纯的理论建构,而不能称其为是一种可行的策略。因此,在考察“实现的正义”过程中,我们首先必须看到是什么在阻碍着正义的真正实现。关于这一问题,在罗尔斯和森以前的政治哲学研究中已经有了很好的讨论。
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正义的时候首先就对公正和不公正的辨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看到,所有的人在说公正时都是指一种品质,这种品质使一个人倾向于做正确的事情,使他做事公正,并愿意做公正的事。同样,人们在说不公正时也是指一种品质,这种品质使一个人做事不公正,并愿意做不公正的事。”亚里士多德正义理念的核心是分配的公正,但是他也看到了在分配过程中不公正产生的可能,于是他又提出了矫正的公正。他说,“尽管平等是较多与较少之间的适度,得与失则在同时既是较多又是较少:得是在善上过多,在恶上过少;失是在恶上过多,在善上过少。又由于平等——我们说过它就是公正——是过多与过少之间的适度,所以矫正的公正也就是得与失之间的适度。”这种对分配中出现的问题的矫正是一种预防性的措施,但同时也是一种建构性的努力,其最终将会对政治产生影响。“政治的公正是自足地共同生活,通过比例达到平等或在数量上平等的人们之间的公正。在不自足的以及在比例上、数量上都不平等的人们之间,不存在政治的公正,而只存在着某种类比意义上的公正。”在政治的公正中,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治理者的公正,指出依法治理的重要性,“政治的公正或不公正如我们看到的是依据法律而说的,是存在于其相互关系可以由法律来调节的,即有平等的机会去治理或受治理的人们之间的。”
关于这一问题,霍布斯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正义与不义这两个名称用于人的方面时所表示的是一回事,用于行为方面时所表示的是另一回事。用于人时,所表示的是他的品行是否合乎理性,而用于行为时,所表示的则不是品行或生活方式,而是某些具体行为是否合乎理性。因此,义士便是尽最大可能注意,使他的行为完全合乎正义的人;不义之徒则是不顾正义的人。在我们的语言中,把这两种人成为有正义感与无正义感,比之称为正义与不义更为常见,只是意义并没有两样。”那么,在霍布斯这里,怎样才算是合乎理性呢?他说,“自然律是理性所发现的戒条或一般法则。这种戒条或一般法则禁止人们去做损毁自己的生命或剥夺保全自己生命的手段的事情,并禁止人们不去做自己认为最有利于生命保全的事情。”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想的城邦政治生活是一种“自足地共同生活,通过比例达到平等或在数量上平等的人们之间的公正”的状态。而在霍布斯那里,则是一种“合乎理性”的生活状态,一种尽最大力量寻求自保的正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则看以看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各得其所”的生活之所以会遭到破坏完全是基于“配得”没有得到公正的分配,可能源于治理者对公正之品行的僭越,也有可能源自交易者之间违反意愿的交易。而在霍布斯那里,“各得其所”的生活之所以会被打破,可能源于权利侵害、违反契约、不懂回报、不合群,也可能源于侮辱别人、自傲以及裁判时偏袒一方等情况。
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到:建构一种正义的理念是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清晰看到不正义的普遍存在。而不正义的产生,从根本上乃是因为僭越正义的存在及其对正义实现的消解。也因此,“实现的正义”理念更多的具有了某种消极的意义——它不再是旨在通过单纯的建构来欲求正义——恰恰相反,乃是需要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人类的“品质”以及霍布斯意义上人类的“理性”。而两者从本质上来说也就是森意义上的“可行能力”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体现。这种“可行能力”要求人们一方面能够各自做好分内之事,另一方面又是能够获得充分展现自己的机会。
四、迈向实践:“各得其所”与“实现的正义”
对于个人来说,做好自己分内之事乃是与个人“品质”和“理性”密切相关的重要变量。但个人“品质”和“理性”同样需要在必要的社会生态中得以展现,或者可以说,个人的展现需要有具体的“场域”存在。在这个“场域”中个人自由得以保障,而社会的整体价值和公平进而得以维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各得其所”恰恰为我们新的要求提供了充分的注解。且需要指出的是,“各得其所”的正义观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实现的正义”观的理论和现实关怀,但其却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观念和论说——对当下“实现的正义”观的实践运作同样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
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对格劳孔说:“我们在建立我们这个国家的时候,曾经规定下一条总的原则。我想这条原则或者这一类的某条原则就是正义。你还记得吧,我们规定下来并且时常说到的这条原则就是: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
苏格拉底:现在请你考虑一下,你是不是同意我的下述看法:假定一个木匠做鞋匠的事,或者一个鞋匠做木匠的事,假定他们相互交换工具或地位,甚至假定同一个人企图兼做这两种事,你想这种互相交换职业对国家不会有很大的危害,是吧?
格劳孔:我想不会有太大的危害。
苏格拉底:但是我想,如果一个人天生是一个手艺人或者一个生意人,但是由于有财富、或者能够控制选举、或者身强力壮、或者有其他这类的有利条件而又受到蛊惑怂恿,企图爬上军人等级,或者一个军人企图爬上他们不配的立法者和护国者等级,或者这几种人相互交换工具和地位,或者同一个人同时执行所有这些职务,我看你也会觉得这种交换和干涉会意味着国家的毁灭吧。
格劳孔:绝对是的。
苏格拉底:可见,现有的这三种人互相干涉互相代替对于国家是有最大害处的。因此可以正确地把这称为最坏的事情。
格劳孔:确乎是这样。
苏格拉底:对自己国家的最大危害,你不主张这就是不正义吗?
格劳孔:怎么会不呢?
苏格拉底:那么这就是不正义。相反,我们说: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国家称为正义的国家了。
在苏格拉底看来,“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而正义的实现要求城邦中的人必须至少具备三种品质,分别是智慧、勇敢和节制,而一个人所应具有的理智、激情和欲望又是与他们的品质相对应的。
苏格拉底:那么,这两者(理智和激情)联合一起最好地保卫着整个灵魂和身体不让它们受到外敌的侵犯,一个出谋划策,一个在它的领导下为完成它的意图而奋勇作战,不是这样吗?
格劳孔:是这样。
苏格拉底:因此我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激情无论在快乐还是苦恼中都保持不忘理智所教给的关于什么应当惧怕什么不应当惧怕的信条,那么我们就因他的激情部分而称每个这样的人为勇敢的人。
格劳孔:对。
苏格拉底:我们也因每个人身上的这个起领导作用的和教授信条的小部分——它被假定为是这个人身上的懂得这三个部分各自利益也懂得这三个部分共同利益的——而称他为智慧的。
格劳孔:完全对。
苏格拉底:当人的这三个部分彼此友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不是有节制的人吗?
格劳孔:的确,无论国家的还是个人的节制美德正是这样的。
从城邦到个人,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的与格劳孔的对话为我们呈现了由节制、勇敢、智慧三种品质所建构的“各得其所”的正义图景。
虽然很多的批评者指出,柏拉图对正义的界定:“使得权力和特权的不平等但不是不正义,成为可能”。然而,柏拉图的哲学家治理和人民大众各尽职能的安排并不是与现时所称的“特权”完全吻合的,柏拉图提供的仅仅是一个样板,他说:“那么,我们当初研究正义本身是什么,不正义本身是什么,以及一个绝对正义的人和一个绝对不正义的人是什么样的(假定这种人存在的话),那是为了我们可以有一个样板。我们看着这些样板,是为了我们可以按照它们所体现的标准,判断我们的幸福或不幸,以及我们的幸福或不幸的程度。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表明这些样板能成为在现实上存在的东西。”
再来看中国的孔子和儒家。
孔子和儒家以“礼”和“仁”为核心的生存之道是与柏拉图意义上的“各得其所”的生存之道有着很大的相似性。柏拉图强调个人的理智、激情和欲望统摄于智慧、勇敢和节制之下,进而创造出治国者、辅助者和生意人“各得其所”的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孔子亦然,他说: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礼记·曲礼上)
通过“礼”,孔子欲实现一种“仁者爱人”的和谐社会局面。这种和谐的社会局面是由“慈”(父母爱子女)、“孝”(子女爱父母)、“悌”(弟弟爱哥哥)、“友”(哥哥爱弟弟)、“义”(丈夫爱妻子)、“顺”(妻子爱丈夫)、“仁”(君主爱臣下)、“忠”(臣下爱君主)、“信”(朋友之间相爱)等个人品质所型塑的。通过这种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间的多层次的礼仪建构,使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记·礼运)
孔子建立了一种“各得其所”的政治主张,与柏拉图的正义主张相类似,这种主张并不是要以特定的法权安排来固化身份和阶层。他特别强调“尊贤而容众”(《论语·子张》)。“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论语·微子》)。他还主张以“仁”为交往之准则,避免对人的压抑,他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除此之外,孔子还重视对礼之“序”、礼之“异”的调和,“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礼记·乐记》)。
这样一种法权安排从总体上乃是一种对理想秩序僭越的基本防范。其指向从根本上来说乃是与自由和公平相适恰的。更为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自由和机会展现的空间。在以“仁”为基本交往准则指引下,人们“各得其所”、“各尽所能”的展现着自己的“品质”和“理性”,社会则呈现出一种“仁者爱人”的和谐局面。
结语
正义是一种理想的诉求,但它更是一种可检验的社会实践标准。若将“各得其所”作为一种衡量正义的标准,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社会生活中很多不正义的发生恰恰源于对“各得其所”的社会生活安排的僭越,比如职业伦理的丧失、越轨行为的发生,贪得无厌、侵权、滥用职权、渎职、消极怠慢、投机、乱伦……如此等等,实际上都在毁坏着消解着我们应有的社会正义。
同时,“各得其所”的正义并不只是一种建构的正义,它从本质上来说乃是一种实现的正义——强调通过多层次的制度设计以保证每一个人在公平秩序中实现自身价值。
首先,正义的实现并不只是对有限资源的分配。中国古人所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与森意义上的“可行能力”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实际上都强调人们对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掌控能力。而这种掌控能力的实现,除了与自己身体意义上的力量、智慧有关外,也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每一个人身处的社会空间中具体的法权安排。这就需要建构一个基本的公共空间,每一个人有基本的权利能够进入这个公共空间实现自身的价值。而且这个公共空间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向所有人开放的,而不只是对少数人开放。这就如康德所说:“人民和各民族,由于他们彼此间的相互影响,需要有一个法律的社会组织,把他们联合起来服从一个意志,他们可以分享什么是权利”。
其次,在开放的公共空间中,不可否认僭越发生的可能。僭越的普遍存在可能会打破有效分配的制度设计,可能会消解公共空间的开放性,也有可能会割裂官方行动与法律之间的一致性。因此,在开放的空间设计基础上我们切不可忽视对消除僭越行为的重视——消除腐败、特权、欺凌以及不公正的差别待遇对于保证每个人正常地进入公共空间乃是必要的,否则公共空间的设计只会成为摆设,而不能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宪政原则。同时,消除僭越行为对于每一个人“各得其所”的展现自己的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保障。
再次,不管是公共空间的设计还是对僭越行为的消除,最终都必须是在一种基本的民主原则框架内展开。也就是说,“各得其所”与实现的正义的形成需要依据事物自身的要求,而不能凭主观意志和权力;需要依据一种长效稳定的法律和制度设计,而不仅依赖于权力的运作。在很多情况下,虽然国家权力还是引导和有计划变革社会制度的主要工具。但是,除非法律秩序已然明确规定了社会变革的根本制度,制度才会发生改变,但这种改变绝非社会刻意选择的结果。长效稳定的法律和制度设计从根本上保证着公共空间的稳定、开放以及对僭越行为的法治化规制,保证着每一个人能够“各得其所”的使自身能力得到展现,进而在更大范围内保证社会整体正义的实现。
[1][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2]Nozick,Anarchy,State and Utopia,Basil Blackwell,1974,p29.周保松.资本主义最能促进自由吗?[J].开放时代,2007,(4).
[3]徐友渔.中国当代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哲学[M].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徐友渔.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当代思考[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徐友渔.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若干理论[J].国外社会科学,2001,(5).
[4]罗尔斯.正义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5]万俊人.罗尔斯的政治哲学遗产(上)[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1).
[6][美]威廉·伊斯特利.白人的负担[M].崔新钰译.中信出版社,2008.[英]阿布杜勒·帕力瓦拉,萨米·阿德尔曼,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法律与危机[M].邓宏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
[7][印]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颐,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8][印]阿玛蒂亚·森.正义的理念[M].王磊,李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9]卡琳·罗马诺.阿玛蒂亚·森:改变思考“正义”的方向[M].王雪译.社会科学报,2009.
[10][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9.
[11][英]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
[12][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9.
[13][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商务印书馆,2005.
[14][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M].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
[15]富勒.法律的道德性[M].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
[16]钱逊.“和”——万物各得其所[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5).
[17][美]安·赛德曼,罗伯特·赛德曼.发展进程中的国家与法律:第三世界问题的解决和制度变革[M].法律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刘强)
D089
A
1671-0681(2014)06-0044-06
张剑源,云南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2014-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