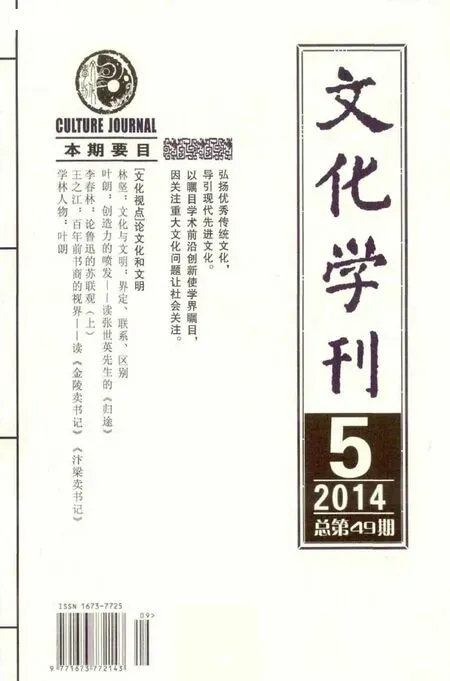从“威斯康星理念”到《拜杜法案》
——美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思想的法律化进程
邵慧峰
(大连理工大学,辽宁 大连 116023)
美国科技发达世所共睹,这与其科技创新体系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个体系的核心则是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制度。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保障了大学的科研成果能无障碍地实现商业化与产业化,进而促进科学发现,推进技术创新,培养科研队伍,培育经济繁荣。然而,西方大学承载科技成果转化使命的历史并不悠久,似美国今天这等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昌隆局面的出现,一个世纪前大学管理者们对大学职能的开创性探索功不可没。自那而后,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思想在美国驶入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快车道。以“威斯康星理念”为发端,经过一系列联邦和州立法的推动,美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思想在大学角色转变的历史大潮中与时俱进,并与法律制度密切衔接,有效互动,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促成了对美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拜杜法案》的出台。从这样一个美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思想的法律化进程中可以看出,大学为适应社会系统的要求而变革资源分配方式或者激励模式的一系列作为,成为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力。推而言之,对于一国创新体系的发展,仅由国家自上而下地铺陈,没有大学等科研主体发自本愿的配合,是很难有所建树的;大学必须于其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大学不仅要做科技成果转化的承担者,还应成为科技成果转化思想的缔造者和科技成果转化法制建设的助推者。因此,考察美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思想从“威斯康星理念”到《拜杜法案》的法律化进程,可以为完善我国的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法律制度提供一定启示。
一
美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最早的思想火花是“威斯康星理念 (Wisconsin Idea)”,其发源地为创立于1848年的威斯康星大学。“威斯康星理念”的核心内涵是合作,即大学与其外部盟友的多边合作,一种足以使大学得到公众、政府以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合作,但“威斯康星理念”的产生,绝非偶然,它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美国大学教育发展之初,在新英格兰清教主义的影响下,高等学府对科学的兴趣往往带有强烈的宗教情结,“既是作为感知上帝的威力和融入到上帝造物体系中的唯一途径,也是作为一种方法去认知理性支配下的世界,去履行自身赞颂上帝的责任”,[1]直接的物质利益、世俗的功利效益则全然不予考虑。即便在独立之后,美国的大学那种浓厚的宗教和古典色彩仍保留了很长时间,它们看重的是大学的教育职能,以讲授深奥、抽象、难懂的课业为荣,对研究则抱轻视态度,更遑论产学合作了,很多大学甚至与产业界老死不相往来。
到了南北战争期间,在参议员加斯汀·莫雷尔的推动下,国会于1862年通过了《赠予土地设立学院以促进农业和机械制造工艺在各州和准州发展的法案》,即《莫雷尔法案》。该法案允许国家无偿赠与联邦所有的土地给各州,藉此资助它们设立以应用教育为核心的农工学院,发展农业与机械制造工艺。随着该法案的实施,大批赠地学院比肩并起,并成为日后诸多州立大学的鼻祖。之后,美国国会又陆续通过了《哈其法案》《莫雷尔第二法案》和《施密斯—赖沃法案》等系列法案,同早先的《莫雷尔法案》一起,开拓了美国大学教育实用化、平民化的改革之路。
《莫雷尔法案》问世之前,美国的大学因受制于教学资源和自身规模,人才培养质量常常成为欧洲学者的取笑对象。但这一局面终于在19世纪中叶以后得以扭转,在联邦政府赠地颁款的财力支持下,美国各州的高等学府普遍增设实用性的课程,大量设立专门研究机构,踊跃开展技术推广服务,以教学、科研和技术推广紧密结合为特点的新的大学体制逐渐形成。我们很难想象,今日闻名世界的一些美国名校如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它们的前身都是赠地农工学院。
“威斯康星理念”就诞生于这样的大时代环境下。1904年,有着威斯康星大学教育背景的威斯康星州州长拉福赖特提名范海斯出任州立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拉福赖特一向主张州立大学应与州政府紧密合作,协力发展本州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项事业,而范海斯与他不谋而合。范海斯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威斯康星大学设立了大学延展中心,开展函授教育和职业教育,并为州政府提供信息咨询;同时,威斯康星大学结合本州实际,以当地乳业为科研对象,对当地农场进行调研走访,还开办了多种主要由当地农民参加的短期培训班;此外,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们还参与了州的立法工作,主持制定了《公共事业法案》《工业委员会法案》和《铁路费率委员会法案》等重要州法。
1912年,威斯康星大学教授麦卡锡对范海斯的改革举措进行概括、总结,最终在《威斯康星理念》一书中将其定义为“威斯康星理念”。“威斯康星理念”认为,既然大学所拥有的资源取之于民,就该用之于民。“大学之责任,除了促进学生个体的发展,还在于增进全社会的福利。”[2]大学应在官、产、学的合作中,将服务社会的效能最大化。“威斯康星理念”整合了大学的教学、科研与公共服务资源,打破了古典大学的封闭状态,建立了大学与社会的立体联系,这便是该理念的实质。
可以说,《莫雷尔法案》等联邦立法所蕴育出的历史机遇,为“威斯康星理念”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若无法律秩序所开辟出的社会经济文化土壤,任何改革都可能成为无本之木,任何理念皆可能胎死腹中。“威斯康星理念”因《莫雷尔法案》而相生,它的出现,是为美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思想的发端。随着美国经济步入20世纪,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呈现必然趋势,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思想日趋成熟,并对联邦及各州的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尽管有《莫雷尔法案》等法案的推动和“威斯康星理念”航标灯式的引导,但从19世纪中叶到二战期间,美国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远未达到社会所期望的效果。追本溯源,主要在于美国大学普遍存在着对纯科学研究重视不足的现象。一种影响颇广的观点认为,在象牙塔内,真理的传授比真理的发现更至关重要。这个时期的美国大学,重技术轻科学,重实用轻理论。如前所述,南北战争之后,众多专注于农业和机械等专业的赠地学院大量涌现并呈快速发展之势,人们开始转而折服于技术的奇妙力量,技术主义和实用主义在大学里一举取得主流观念的地位。另一方面,当时美国的技术创新主要由独立发明家或者企业技术专家在大学之外的实验场所完成,而社会生产部门提供给大学的科研经费杯水车薪,难以支撑大学科技成果的商业化应用。这一时期,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思想再未有如“威斯康星理念”那般革命性地发展,其法律化进程也陷入停滞的状态。
不过,新的契机很快出现。随着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踵而至,美国人认识到了大学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其对国家安全的维护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原子武器的成功研制更是验证了这一点。1949年,时任美国联邦科研与发展部门负责人的范内瓦尔?布什教授,在给杜鲁门总统的报告中指出:科技创新活动需要持续地将知识与人才扩散到生产部门,并由市场判断其价值意义。这个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报告后来成为二战后美国确立科技政策导向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范内瓦尔·布什的报告是继“威斯康星理念”之后美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思想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
随着范内瓦尔·布什的建议被采纳,战后的美国的大学出现了三大趋势:其一,科学研究地位飞升。美国通过一系列法案的实施,对大学科学研究的扶持堪称登峰造极,使美国大学成为了全球科学研究的领军者。其二,美国大学轻学重术的局面得以改观。在南北战争之后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美国大学较之欧洲传统大学理念,矫枉过正,鄙弃基础学科和理论知识,热衷教授应用学科和实践技能,导致人才培养上的短板,难以适应科技发展的需求。但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大学开始意识到过往的做法有本末颠倒之嫌,对待教育应着眼于长远,须重视高新科学的研究与发展。其三,联邦政府大幅增加大学的研究的经费。二战之后,美国执行反垄断法更加坚决,其严厉的反垄断法规使得大学科研与产业研发分道扬镳,其科研经费缺口主要由联邦政府的财政扶持加以填补。
任何事物的演进都难免伴随着反复与曲折,大学以及大学科研也不例外,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人们所见到的美国产学研合作井喷式的发展,是诸多有利于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历史因素积聚到一个临界点之后必然出现的结果,但在此之前,美国大学的发展也曾经迷失航向。就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普遍认为大学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这一时期出版的一些相关书籍,仅看书名,就不难发现他们这种焦灼的心态——诸如1970年的《无政府状态的高等教育界》《高等学府内的混乱状况》,1971年的《退却中的大学师生》《混乱中的专科院校》《彻底垮台》《高速公路上的盲人》,1972年的《高教政策的破产》《一位大学校长的毁灭》《垮掉的高等教育界》《美国大学的衰落》,1973年的《美国大学的灭亡》[3]等等。
这种焦虑与美国政府对大学科研的巨额投入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比。此前,由于受到苏联在短短四年内实现发射人造卫星和载人航天的刺激,美国对基础科学的研究资助每年均呈快速增长态势:1952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财政拨款为300余万美元,1959年飞升到1.34亿美元,10年之后达到5亿美元,到了1980年代,年均20亿美元;1960年,联邦政府的科技投入为75.22亿美元,1980年则跃升到297.39亿美元[4]。巨额的资金投入奠定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人却发现,灿如繁星的科研成果并没有带来高科技产业的日新月异,拥有着号称世界第一的科研优势,反倒眼睁睁地看着美国经济在世界市场的份额被逐步蚕食,产业竞争力不升反降。
事态至此,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存在着科研及成果应用上的体制缺陷。由于法律规定联邦政府拥有由其资助的科研成果所有权,因此大学难以产生科研成果转化的动力,而复杂的技术转让相关法律,又使企业难以获得上述科研成果并施加以应用。1980年,联邦政府拥有的2.8万个此类专利,仅有5%通过专利使用许可而投入生产部门;而为数众多的美国大学,在1980年之前每年获得的专利数竟从未超过250项,[5]能开展科技成果转化者更属凤毛麟角。如此之低的转化率必然造成大量科研成果的浪费而且加剧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显然,到了这个时期,美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思想需要新的转变,并通过法律形式加以制度化,从而突破科技成果转化发展的瓶颈。
三
为改变这一局面,美国政府转而向大学提供新的制度激励。这其中,在美国针对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制度设计中,《拜杜法案》最有代表性。1980年年底,美国国会通过了后来影响深远的《拜杜法案》,即《专利与商标法修正案》,因其提案人为参议员博奇·拜耶和洛波特·杜尔,故有此名。该法案允许大学、微小企业和公益性研究机构享有联邦政府资助发明创造的相关专利权,鼓励大学开展应用研究和技术转移。《拜杜法案》是美国专利法律体系的一次革命性变革,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资助科研成果的归属原则。
概而言之,《拜杜法案》采取了如下措施激励大学的技术转移:其一,除约定在先外,给予大学对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知识产权保留与否的选择权;其二,如大学选择保留上述权利,应在法定的期限内提出专利申请;其三,大学有权向第三方转让上述知识产权,大学可以将独占性许可授予给企业尤其是本土的微小企业;其四,联邦政府对因资助而创造的大学科研成果享有非独占的无偿使用权;其五,如果大学放弃科研成果的所有权,经各方协商,相关主创人员有权取得该所有权。《拜杜法案》提供了科研成果由联邦政府所有转向大学所有的制度路径,使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大规模实现具备了现实条件,也令科学工作者因而更关注研究成果的经济价值。
在此之外,美国国会还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法案如《史迪文森—怀特技术创新法案》《联邦技术转让法案》和《小企业创新开发法案》等,美国联邦政府也颁行了对应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在它们的激励作用下,美国大学参与技术转移工作的积极性日益高涨,科研成果的转化效率显著提升,转化数量逐年增长。迄今为止,美国基于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产生的年度GDP超过500亿美元,每年缔造就业岗位30万个,税收收入逾60亿美元。[6]
需要注意的是,在美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思想的法律化进程中,类似《拜杜法案》这样的制度化产物并不总是赢得一片赞誉。美国企业界认为,由于大学受到《拜杜法案》的鼓舞,即便在与企业的研发合作中,也往往期待获得研究成果的全部所有权,哪怕此项研究是受到企业资助的。企业界无法接受这样的科技成果转化文化,为此,它们更倾向于与不受《拜杜法案》影响的国外大学合作,从而规避在美国本土大学那里可能引发的知识产权纠纷。非美国大学更乐于分享科研成果,并不在意企业资助方获取合作成果的所有权,结果使得美国企业纷纷将科研资金转移到国外,投入到与国外大学的科研合作中。
正基于此,《拜杜法案》对大学发展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视。这样一个带有阶段性功利目的的激励机制,使美国本引以为豪的研究型大学陷入到对短期应用性研究的迷恋之中,终日寻觅于对尖端技术的独占性许可,反而制约了新技术、新知识在更大范围的推广与流传,反而在实质上损害了大学的公共服务职能。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大学的意义不在于单纯维护教育者自身或者大学的一己之利,而在于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如果一项制度只能使大学获取单向的物质利益而不能激励大学更好地回馈社会,那这项制度以及支撑它的思想基础就该迎来反思了。
当美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思想的法律化进程发展到《拜杜法案》这一阶段时,我们固然不能随意抹杀它的正面效应,但其无时不存在的负面效应也在提醒人们在评判《拜杜法案》时必须采取一个冷静客观的态度,在借鉴该法时也断然不能只看表面文章。“威斯康星理念”为美国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开启了通向现代科技创新体系的大门,范内瓦尔?布什为美国点燃了战后科技复兴的火种,然而任何一项尚处在探索与不断自我完善中的制度都是双刃剑,《拜杜法案》的作用虽为世人瞩目,但毫无疑问它不是美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思想法律化发展的最高峰,这是我们借鉴美国的他山之石,寻求其对完善我国的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法律制度之启示时,应该保留的一份清醒和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