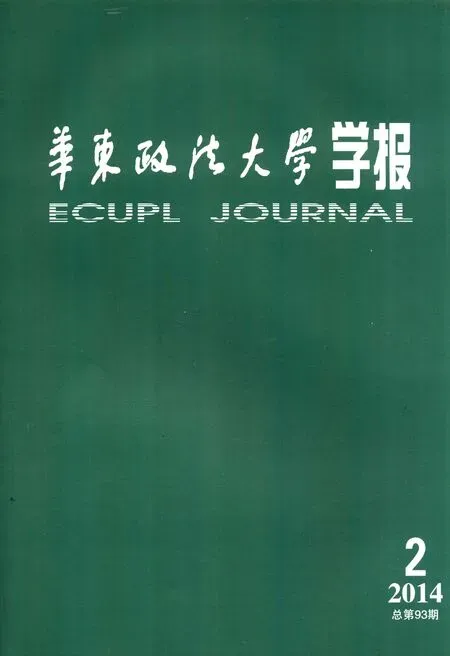《岳麓简(三)》“癸、琐相移谋购案”中的法律适用
邬 勖
《岳麓书院藏秦简(三)》(以下简称“《岳麓简(三)》”)收录的十多则秦代案例,多编写于自秦王政时期至统一六国的这一段时期内,其中保存有许多当时各级地方机构所作的定罪量刑意见,若将其与以往已见的秦汉法律文献相对照,往往可明某一具体法制的沿革,或可补充已知法制体系的缺失,对于我们探究那段“五年之间,号令三嬗”的剧变期前后的法制变迁轨迹,有着十分宝贵的价值。本文即尝试对《岳麓简(三)》中的一则案例“癸、琐相移谋购案”作一解析,并重点关注其中的定罪量刑意见所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
本案现存30支简,由格式和内容可知首尾简俱在,整理者又标出3支脱简,〔1〕其中简6、简7之间的脱简或即残453简,今存“四万三百廿钱癸”七字,“四”字上似可补“死罪购”三字,与简6连读为“尽鼠(予)琐等四万三百廿钱。”即原本应共有33支简。全案由以下两组案卷组成:(1)州陵县的谳狱书(简1-23)及其所附的州陵县吏的“议”(简24),(2)南郡对谳狱书的报书(简25-30)。其中简12、简24末尾均留白不书,与下一简不相连,将全卷区隔成3部分。本案所经的程序总体上与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的疑狱上谳案例(案例1-13)相合,包括从案件启动、审理、上谳直至上级回报的全部环节。其不同之处在于,本案最初不是疑狱案件,县廷曾作出过判决,因被监御史劾“不当”,在尝试重新判决时产生分歧,然后才作为疑狱案件上谳,这一程序是以往所见的材料中所从未出现过的。与《奏谳书》中的大多数案例一样,本案也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色,史载秦始皇时“赤衣塞路,群盗满山”(《新序·善谋》、《汉书·贾山传》等),本案即正与捕捉群盗有关。
一、案情概要
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的一天,治等十人在南郡州陵县辖境内群盗盗杀人,事情被发觉后,州陵守绾下令校长癸和令佐行率领求盗柳、士五轿、沃进行追捕,五名吏徒追踪治等人进入了邻近的沙羡县。〔2〕《二年》简140-141:“群盗杀伤人、贼杀伤人、强盗即发县道,县道亟为发吏徒足以追捕之,尉分将,令兼将,亟诣盗贼发及之所,以穷追捕之,毋敢□界而环。”癸等人追踪群盗进入邻县辖境,或即依据此类规定行事。正在沙羡山上伐取木材的六名戍卒得、潘、沛、琐、渠和乐将治等捕获,包括治在内的四人供称自己是秦国人邦亡,其他人则都不说出自己的罪行,戍卒们无法诣告(大概只能以亡人来诣告)。〔3〕从睡虎地秦简《封诊式》和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的告发案例来看,诣告时必须控以明确的行为,有时可以给出二种可能的行为,但也必须明确,如《法律答问》简43:“甲告乙盗牛若贼伤人”。若其行为不明而贸然诣告,则要冒着“告不审”的风险。简文说“弗能告”,是指戍卒们无法以明确的罪行来告,但若只以亡人来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得、潘和沛三人留在亭中,让琐、渠和乐三人把治等诣送到沙羡县廷,约定得到购赏后共分购赏钱。琐等在诣送途中遇见了追踪而来的州陵吏徒癸等。癸等发现琐等并不知晓治等的罪行是群盗盗杀人,于是意图得到捕群盗盗杀人的购赏八万六百四十钱,他们欺瞒琐等,请求把治等交给自己向州陵县诣告,领出捕死罪的购赏四万三百二十钱,然后把这些钱全部还给琐等。琐等听从了请求,双方立下支付捕死罪购赏钱的契券,癸等并用私钱向琐等先行支付了二千钱。癸等得到治等后,即向州陵县诣送,其中令佐行不知何故未参与诣送,但所有人均参与了得手后分配购赏钱的谋约。
四月辛酉日,癸、柳、轿、沃四人将治等十人诣送到州陵县廷,告他们群盗盗杀人。三天后的甲子日,在该案尚未了结、购赏钱尚未发放时,沙羡县方面告知州陵县:治等人是由戍卒琐等捕获,而移予癸等的。州陵县据此立即启动了对琐等、癸等涉嫌捕盗相移谋购一案的调查。
五月甲辰日,琐、癸等人的案件审理完毕,州陵守绾、丞越、史获三人作出判决:论吏徒癸、行、柳、轿、沃五人和戍卒琐、渠、乐三人各赎黥;论癸、行罚戍衡山郡各三岁,并在戍前先偿清赎钱;论戍卒沛等三人无罪。
案件论定后,为南郡监御史康所劾。康认为该案论狱不合法,癸等支付给琐等的二千钱未作区处,应重新论狱,重新论狱时要一并论及论狱有失的责任人,将全案断决后上报。州陵县据此启动了对绾、越、获涉嫌论狱有失一案的调查。
案件审理完毕,事实清楚,但州陵县吏在定罪量刑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一说绾等的判决正确,一说绾等的判决不正确,癸、琐等应论耐罪。于是六月癸未日,州陵县将整个案件一并上谳到南郡。
十余天后的七月乙未日,南郡假守贾对上谳案件作出回报:案件事实清楚,癸、琐等人应按“受人货财以枉律令,其所枉当赀以上,受者、货者皆坐臧为盗”的律条论处,初次判决的负责人绾、越、获则应各赀一盾,其他事项均按律令办理。整个案件至此全部完结。
二、法律适用问题
(一)五月甲辰州陵县的判决
1.“癸、琐等各赎黥”、“(癸、行)先备赎”。五月甲辰州陵县的判决中,吏徒校长癸、令佐行、求盗柳、轿、沃和戍卒琐、渠、乐共8人被论以赎黥之罪(“令癸、琐等各赎黥”),其中癸、行还要“先备赎”。
判决负责人守绾、丞越、史获是这样解释自己的判决理由的:
整理者将“盗未有取吏赀灋戍律令”连读,又读“灋”如字。劳武利先生将“盗未有取”断读,〔4〕[德]劳武利:《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与岳麓书院秦简〈为狱等状四种〉的初步比较》,李婧嵘译,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陈伟先生的意见与之相同,并对“盗未有取”作了非常好的解释。他举出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几条材料:
《答问》4:甲谋遣乙盗,一日,乙且往盗,未到,得,皆赎黥。
《答问》30-31:“抉籥(钥),赎黥。”可(何)谓“抉籥(钥)”?抉籥(钥)者已抉启之乃为抉,且未启亦为抉?抉之弗能启即去,一日而得,论皆可(何)殹(也)?抉之且欲有盗,弗能启即去,若未启而得,当赎黥。抉之非欲盗殹(也),已启乃为抉,未启当赀二甲。
《二年》182:越邑、里、官、市院垣,若故坏决道出入,及盗启门户,皆赎黥。其垣坏高不盈五尺者,除。
陈伟先生指出:“这些律文及解释,大概即与‘盗未有取’有关。癸、琐等‘购未致,得’,所以绾等援引‘盗未有取’律判处‘赎黥’。”〔5〕陈伟:《“盗未有取吏赀灋戍律令”试解》,来源: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92,2013年10月22日访问。这无疑是正确的。上面二条《法律答问》分别列举了二种具体的“盗未有取”的情形,处罚均为“赎黥”,现在据本案的这则论罪可以推知,当时应有明确的规定将一般的“盗未有取”都处以赎黥之罪,而不止限于“未到,得”和“抉钥”这二种特殊情形。
将癸、琐等人谋取购赏的行为视作“盗”的法律依据,整理者注释已指出与下面这条《二年律令》的律文有关:
《二年》155:捕罪人,弗当以得购赏而移予它人,及诈伪,皆以取购赏者坐臧为盗。
以往对此律的理解存在一些分歧,〔6〕参见彭浩等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153页。黄杰先生认为,此律应断作“捕罪人,弗当以得购赏,而移予它人,及诈伪、皆(偕)以取购赏者,坐赃为盗”,它规定了二种情形,一是“按照法律规定本身不能得到赏钱,便让给别人”,二是“用欺骗的手段共同谋求购赏”,分别可与本案中琐等、癸等的情况相对应。〔7〕黄杰:《〈岳麓书院藏秦简(三)〉释文注释商补》,来源: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900,2013年10月22日访问。此说近是,但仍未得确解。其实,“弗当”就是一般的“不当”的意思,秦汉律中多用“不当”表示禁止性规范,与“勿”、“勿敢”等相近,该条意为:“捕捉罪人,不当以得购赏为目的而将所捕罪人移交给他人,以及诈伪,(这两种情形)均以领取购赏的人坐臧为盗”。本案整理者断为“捕罪人弗当以得购赏,而移予它人及诈伪”,〔8〕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三)》,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页。大体是不错的。
回到本案,琐等捕得群盗,并以得购赏为目的将之移交给癸等,癸等四人前去诣告领赏,这四人是“取购赏者”,按律应坐臧为盗,自然毫无问题。但令佐行和琐等三名戍卒均未参加诣告,为何也要坐臧为盗呢?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有一条类似的情形:
《答问》139:有秩吏捕阑亡者,以畀乙,令诣,约分购,问吏及乙论可(何)殹?当赀各二甲,勿购。
捕得阑亡者的“有秩吏”并未实际去领赏,但因为已经和乙“约分购”,故而也被视作“取购赏者”,与实际领赏的乙同等论罪,这应是当时司法实践的固定做法。本案中“皆谋分购”的行和立下契券约死罪购的琐等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绾等即按“盗未有取律令”将癸、琐等八人全部论为赎黥之罪。
癸和行被论戍衡山郡三岁后,还加上了“先备赎”一项,整理者注释疑其前脱“琐等”二字,认为其“表示在未派戍边当法之前琐等全已赎清”。〔9〕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三)》,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页。陈伟先生则认为“先备赎”是指在判癸、行戍衡山郡时,要求他们在出戍之前提交赎金。〔10〕陈伟:《“盗未有取吏赀灋戍律令”试解》,来源: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92,2013年10月22日访问。后一种理解不仅文意较为顺畅,也更加合乎事理。睡虎地秦简《金布律》云:
金布律《十八种》76:有责(债)于公及赀、赎者,居它县,辄移居县责之。公有责(债)百姓未赏(偿),亦移其县,县赏(偿)。
“移”指移书,该律规定,应清偿债务或应缴赀、赎钱而居于它县的,县应移文书到所居县追缴。里耶秦简中有许多这样的文书实例,〔11〕其一例如下:廿六年十二月癸丑朔庚申,迁陵守禄敢言之:沮守瘳言:课廿四年畜息子得钱,殿沮守周,主为新地吏,令县论,言史(事)。●问之:周不在迁陵。敢言之。●以荆山道丞印行。(正)丙寅水下三刻,启陵乘城卒秭归□里士五顺行旁。壬手。(背)里耶8·1516(释文据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3页。本文对标点有所调整。)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载“牛羊课”文云:“牛大牝十,其六毋子,赀啬夫、佐各一盾。●羊牝十,其四毋子,赀啬夫、佐各一盾。”沮守周在廿四年的畜息子课中殿底,当有赀罪,其后周调往新地为吏,至廿六年十二月,沮县方面才移书南郡查询周的下落,显然是其赀钱尚未偿清的缘故。像这样异地追索陈年官方债务的文书,在里耶秦简中还可见许多(8·63、9·1-9·12等)。它们清楚地表明异地追索给众多地方机构带来了额外工作负担。因此,本案在判決时特别要求在戍前缴清赎钱,这样就完全避免了在戍后通过文书追索造成的麻烦和浪费,作出这一判决的官吏应有十分丰富的公务经验。
2.“癸、行戍衡山郡各三岁,以当灋。”癸、行二人被论“戍衡山郡各三岁,以当灋。”整理者注释解“当灋”为“充当法定刑”,认为戍衡山郡三岁的作用是充当前面所判黥罪的执行方式,即以兵役抵消罪过。对此,陈伟先生有不同的解释:“回过头来看绾等对嫌犯的初步裁决,是根据‘盗未有取’律令判处‘癸、琐等各赎黥’;根据‘吏赀废戍’律令判处‘癸、行戍衡山郡各三岁’。”〔12〕陈伟:《“盗未有取吏赀灋戍律令”试解》,来源: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92,2013年10月22日访问。视戍和赎黥为互不相干的二项刑罚,又读“赀灋戍”之灋为废,以“吏赀废戍律令”为判决癸、行戍三岁的依据,其说甚确。又,秦汉律中的赎罪有明确的法定金额可供执行(《二年》简119:“赎劓、黥,金一斤”),即便财产不足以清偿,法律还设置有“居赎”的抵偿措施,而以戍边来充当赎罪的执行方式的,迄今尚未见有明确的例证。因此,“当灋”还是照字面理解为“将行为对应于法律规范”为好,《庄子·寓言》云:“鸣而当律,言而当法”,史汉有“致法”,秦简有“当律”、“当令”、“当律令”、“应律”、“应令”、“应律令”,汉简有“应法度”(EPF22·39)等等,这些词的涵义均应相近。
然而,作为罪罚的三岁戍期在文献中并不常见,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中只有戍一岁、二岁和四岁,其中适用于吏的主要是戍一岁和二岁,如《秦律杂抄》的“徒食、敦(屯)长、仆射弗告,赀戍一岁”〔13〕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译文以“赀戍”为“罚戍”,张伯元师则认为“‘赀戍’的惩处用的是钱,而不是直接去守边。”参见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页。张伯元:《爵戍考》,载张伯元:《出土法律文献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94页。案《杂抄》简35-36载“敦(屯)表律”文云:“冗募归,辞曰:‘日已备,致未来’,不如辞,赀日四月居边。”说日有不备的,一日当赀居边四月,而不说一日赀若干财物,又《答问》简7有“赀繇(徭)三旬”,也难以认为是将赀徭折抵为赀财物,似仍以整理小组的意见为是。和“同车食、敦(屯)长、仆射弗告,戍一岁”(简11-15),《二年律令》的“盗出黄金边关徼,吏、卒、徒部主者……弗智(知)、索弗得,戍边二岁”(简76)等,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下两条:
(1)《二年》140-143:群盗杀伤人、贼杀伤人、强盗即发县道,县道亟为发吏徒足以追捕之,尉分将,令兼将,亟诣盗贼发及之所以穷追捕之,毋敢□界而环。吏将徒追求盗贼,必伍之,盗贼以短兵杀伤其将及伍人,而弗能捕得,皆戍边二岁。卅日中能得其半以上,尽除其罪;得不能半,得者独除。●死事者置后如律。大痍臂臑股胻,或诛斩,除。与盗贼遇而去北,及力足以追逮捕之□□□□□逗留畏耎弗敢就,夺其将爵一络〈级〉,免之,毋爵者戍边二岁。兴吏徒追盗贼,已受令而逋,以畏耎论之。
(2)《二年》144:盗贼发,士吏、求盗部者及令、丞、尉弗觉智,士吏、求盗皆以卒戍边二岁,令、丞、尉罚金各四两。
本案正好属于这两条所适用的县吏徒追捕盗贼的场合,但是一来其中并无三岁的戍期,二来“吏、徒”或“士吏、求盗”均被同等论戍,与本案中只有二名“吏”(校长癸、令佐行)论戍,而三名“徒”(求盗柳、轿、沃)只论赎黥明显不合,由此可知其并非绾等的判决所援引的条文。
秦汉时的“戍”有许多名目,如“徭戍”(多见于睡虎地秦简、岳麓秦简、张家山汉简和《汉书》,不知为一词否)和“更戍”(里耶秦简),应属于正规的徭役,又有“冗戍”(里耶秦简),可能是自愿的应募者,〔14〕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简151载“司空”文云:“百姓有母及同牲(生)为隶妾,非适(谪)、罪殹(也)而欲为冗边五岁,毋赏(偿)兴日,以免一人为庶人,许之。”“冗”,《说文》解为“散也”,《周礼·夏官·稾人》“宂食者”注:“谓外内朝上直诸吏,谓之宂吏,亦曰散吏。”秦汉简中的“冗”当与“员”相对。此“冗边”或与“冗戍”为一事,即以“冗”而非常员(即践更徭役的戍卒)的身份戍边。该条以非谪、罪为冗边免隶妾的前提,可见谪与冗边有一定的相对性。一般的戍卒当即来源于此。此外则有“赀戍”(睡虎地秦简)、“罚戍”(里耶秦简、岳麓秦简、张家山汉简)和“谪戍”(典籍和里耶秦简中多见),仅由字面即可知,三者都是惩罚措施,且相互间应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5〕赀、罚、谪三字词义本近,《说文》:“赀,小罚,以财自赎也”,“谪,罚也。”陈伟先生已指出,把癸、行所戍的地点定为“衡山郡”,在岳麓简律令中可以找到其依据:〔16〕陈伟:《“盗未有取吏赀灋戍律令”试解》,来源: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92,2013年10月22日访问。
绾请许而令郡有罪罚戍者,泰原署四川郡;东郡、叁川、潁川署江胡郡;南阳、河内署九江郡,南郡、上党□邦道〔17〕所脱一字似为“臣”或“属”,或可断读为“南郡、上党、臣/属邦道”。当戍东故徼者,署衡山郡。〔18〕此文系于薇先生根据岳麓简0194、0383、0706三支简文复原而成。参见于薇:《试论岳麓秦简中“江胡郡”即“淮阳郡”》,来源: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090,2013年10月22日访问。释文见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比照之下,本案所判的“戍衡山郡三岁”无疑便是上面所谓的“有罪罚戍”了。
《汉书·晁错传》载晁错奏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而《武帝纪》载天汉四年春“发天下七科谪”,颜注引张宴说与之略同,唯以“亡人”代替“闾左”,以“吏有谪”作“吏有罪”。又《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也以有罪(“治狱不直”)之吏为谪戍。〔19〕《淮南子·人间训》记南越败秦军,“杀尉屠睢”,秦“乃发谪戍以备之”,《六国年表》三十三年“遣诸逋亡及贾人赘婿略取陆梁,为桂林、南海、象郡,以适戍”及《本纪》三十四年“谪治狱吏不直者”当即其所谓“乃发谪戍以备之”。曹旅宁先生据荆州博物馆藏汉简文“秦始皇三十年苍梧尉徒唯攻陆梁地”考定秦攻南越在三十年。据此,可由《人间训》载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推出秦军败在三十三年左右,与《六国年表》相合。参见曹旅宁:《从出土简牍考证秦始攻南越之年代》,来源: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535,2013年10月22日访问。本案中只对校长癸和令佐行判决的罚戍,当即《晁错传》所谓的“吏有谪”,属于谪戍和罚戍的交叉概念,而以柳、轿、沃的“徒”的身份自然是无须适用这种“吏赀、灋(废)、戍律令”的。
3.“不论沛等。”即不论戍卒沛、潘、得三人的罪。沛等三人与琐等三人一同捕得群盗治等,属于案件的知情人,故也遭州陵县讯问。沛等因故留处亭中,与琐等约定好分配购赏后,由琐等诣告沙羡县,自己则并未成行,其后才发生了琐等遇见癸等并相移所捕群盗之事。沛等对琐等未将群盗诣告沙羡(“弗诣”)、将群盗移交给他人(“相移”)、接受私钱二千(“受钱”)诸情节毫不知情,琐等和沛等的供述均证实了这一点,癸等的供述也与之符合(癸等始终未提及沛等),可谓证验明白。至于沛等与琐等之间相移约分购的行为,《二年律令》中有正条规定其无罪:
《二年》150-151:数人共捕罪人而当购赏,欲相移者,许之。
本案中州陵绾等论沛等无罪,南郡的报也未提及沛等,说明沛等无罪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在绾等的判决被劾后的州陵县吏议中,其前一议云“沛、绾等不当论”,后一议不巧正遇脱简(第3枚脱简),只保留下对癸、琐等的当罪,但从前一议专门提到了沛来看,其很可能就涉及了对沛等的当罪。若此推测不误,则上引《二年》的这条规则在秦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时也许尚未明确化。
(二)监御史康的劾
州陵县在五月甲辰作出论罪后,简文记述道:“监御史康劾,以为不当,钱不处,当更论,更论及论失者,言决。”
秦的监御史见于史籍的有《史记·萧何世家》的“秦御史监郡者”,又多见郡中的“监”,《曹参世家》集解引《汉书音义》说即御史监郡者,其职责从记载来看十分宽泛。〔20〕参见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下)》,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5-18页。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0年版,第273页。今由本案监御史康劾州陵县“论失”,可知司法也是秦的监御史的重要职责之一,〔21〕《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侍御史四人,从六品下”条载汉惠帝三年,“相国奏遣御史监三辅不法事,有词讼者、盗贼者、铸伪钱者、狱不直者、繇赋不平者、吏不廉者、吏苛刻者、踰侈及弩力十石以上者作非所当服者,凡九条。”是为汉代的御史监郡之制,其所监有“狱不直者”一条,与本案中监御史所劾的“论失”有相近之处。里耶秦简8·632有“御史覆狱”之文,不知即此监御史否。
本案是监御史监察县廷判决的第一例,也是迄今所见的唯一一例,这应当不是案件所必经的一般程序,它可能与《奏谳书》案例16的淮阳郡守“掾新郪狱”、案例19的攸县守“视事掾狱”一样,含有抽查的意味在内。
劾,整理者注释云:“官员以职权告发或检举犯罪行为,与普通告发形式的‘告’相对。”〔22〕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三)》,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页。此说甚确。《二年律令》云:“治狱者,各以其告劾治之。敢放讯杜雅,求其他罪,及人毋告劾而擅覆治之,皆以鞫狱故不直论。”(简113)规定治狱、覆狱必须以告、劾为依据,无告、劾不得擅自治狱、覆狱,可见告、劾在律中是作为案件启动的必要程序而存在的。〔23〕同时,司法实践也允许其他的案件启动方式,如《岳麓简(三)》“猩、敞知盗分赃案”中,嫌疑人猩并没有被人“告”过,他是被嫌疑人去疾、号的供述牵引出来的,江陵县据去疾、号的供词启动了对猩的调查,这应该就是张斐“上律注表”所说的“囚辞所连似告劾”(《晋书·刑法志》),《急就篇》谓之“朋党谋败相引牵”,传世文献中其例甚多,如《汉书·景十三王传·江都王建》:“及淮南事发,治党与,颇连及建”,又《淮南王传》:“河南治建,辞引淮南太子及党与”等。另外,《奏谳书》案例15“江陵忠言:醴阳令恢盗县官米二百六十三石八斗”,《岳麓简(三)》中本案的“沙羡守驩曰:士五琐等捕治等移予癸等”,“猩、敞知盗分赃案”的“醴阳丞悝曰:冗募上造敞……”等例,分别导致恢、癸等琐等、敞被立案调查,这些以官文书为依据启动案件的做法应也不属于“各以其告劾治之”中的任何一种。二者的区别当包括:(1)劾的主体一定是吏,告可以是民,也可以是低级的吏;(2)劾须以文书进行,告则多以口头的形式;(3)告必须对明确的对象控以明确的行为,劾则可以针对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如《奏谳书》案例16的淮阳守劾新郪狱“疑有奸诈”即是。
监御史劾州陵县论狱“不当”,所谓“不当”应即“不当法”之意,〔24〕里耶秦简中有一篇讯狱文书(8·754+8·1007):卅年□月丙申,迁陵丞昌、狱史堪讯。昌辞曰:上造,居平□,侍廷,为迁陵丞。□当诣贰春乡,乡渠、史获误诣他乡,□失道百六十七里。即与史义论赀渠、获各三甲,不智(知)劾云赀三甲不应律令。故皆毋它坐。它如官书。堪手。与本案性质相同,该案也是官吏因论狱遭劾而被立案调查的案件。其中引“劾”云:“赀三甲不应律令”,所谓“不应律令”应即本案的“不当”。该文书的释文、缀联从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6页。其理由是“钱不处”,“钱”指癸等给予琐等的“私钱二千”。在随后的调查中,论狱负责人绾等供述道:“令琐等环癸等钱”(简16),“令”前一字作“”,虽然难释,但无论如何也不大可能是“不”、“未”等表否定意义的字,因此不能把绾等的供述理解为“没有让琐等还钱”。
由此可知“钱不处”实际上是指没有对癸、琐等人私相授受“私钱二千”的行为进行定罪,而不是指真的没有进行任何处罚。审查案件的监御史康仅凭“钱不处”这一点,就能断定州陵的判决有不当法之处,而无须再作更多更深入的分析,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当更论,更论及论失者”,是要求州陵更改原判并重新判决,重新判决时应一并论处“论失者”。“失”,整理者注释引《二年律令》简107“论而失之”等材料解为“误判”,得之;但以“失者”为一词,解“论失者”为“论处误判的官员”,〔25〕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三)》,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页。则不确。睡虎地秦简《语书》云:“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论及令、丞”,“及”字的用法与此处相同。“更论及”即《语书》的“论及”,“论失”即《二年》的“论而失之”。
监御史康的这条劾下达后,立刻在州陵县产生了二个法律后果,其一是根据其“更论”的要求,癸、琐等捕盗相移谋购案开始进行重新判决,其二是根据其“更论及论失者”的要求,绾等涉嫌论狱有失一案也同时启动了。
(三)重新判决时州陵县吏的分歧
州陵县根据监御史康劾的要求重新进行判决,因此而产生了二种分歧意见即“议”。其前一议云:“癸、琐等论当殹,沛、绾等不当论”,说绾等判决正确,沛等(沛、潘、得)、绾等(绾、越、获)不须论罪。后一议云:“癸、琐等当耐为侯(候),令琐等环癸等钱,绾等……”,主张癸、琐等当耐为候,琐等应还癸等“私钱二千”,因值脱简,绾等被当何罪不得而知,笔者在上文并推测,脱去的简文中很可能还涉及对沛等的当罪。
“耐为候”在睡虎地秦简中共3简,《秦律杂抄》简4云:“为(伪)听命书,灋(废)弗行,耐为侯(候)。”又简6-7载《除弟子律》云:“当除弟子籍不得,置任不审,皆耐为侯(候)。”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答问》中的这条:
《答问》117:当耐司寇而以耐隶臣诬人,可(何)论?当耐为隶臣。▕当耐为侯(候)罪诬人,可(何)论?当耐为司寇。
整理小组以为“侯”下有脱字,〔26〕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页。或是。案《二年律令》规定有诬告反罪原则(简126:“诬告人以死罪,黥为城旦舂,它各反其罪”),若其同样适用于睡虎地秦简,则据有关简文,劳役或者说身份刑的反罪并罚可能一般是取吸收原则,〔27〕《答问》简119:“完城旦,以黥城旦诬人,可(何)论?当黥。”此“当黥”即当黥为城旦,又简120云:“当黥城旦而以完城旦诬人,可(何)论?当黥?(劓)。”此“当黥劓”即当黥劓为城旦。此二条都是劳役刑的反罪并罚取吸收原则之证。对于此二条的理解,可参见栗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1页。该条后半部分原应作:“当耐为候罪而以耐为司寇罪诬人,何论?当耐为司寇。”若此理解不误,则候作为一种处罚应等于或略轻于司寇。〔28〕栗劲先生认为候是“轻于司寇的徒刑”。参见栗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6页。
《秦律十八种》载《内史杂》文云:“侯(候)、司寇及群下吏毋敢为官府佐、史及禁苑宪盗”(简193),把候与司寇、群下吏相提并论。但到了《二年律令》中,候已全然不见踪影,《户律》授田宅的条文将“司寇、隐官”排在“公卒、士五、庶人”之下(简312、316),《傅律》云:“公士、公卒及士五、司寇、隐官子皆为士五”(简364-365),《赐律》规定赐衣的等级,“公乘以下”就是“司寇以下”(简283),司寇似已成为庶人之下等级最高者,完全没有给候留下存在的空间,候这种身份或者说劳役在《二年律令》的时代可能已被废除了。
睡虎地秦简《杂抄》中有一条《捕盗律》文:
《杂抄》38●捕盗律曰:捕人相移以受爵者,耐。
所处的刑罚就是一个“耐”字,但是耐罪并不会被单独判决,而是一定要同时处以某种身份或者说劳役刑,《二年律令》的《具律》有明文规定:
《二年》90:有罪当耐,其法不名耐者,庶人以上耐为司寇,司寇耐为隶臣妾。
三国时代出土文字资料研究班云:“本律条是在与耐相伴的主刑名不明确时,庶人以上均处耐司寇,司寇处耐隶臣妾。”〔29〕彭浩等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页。是为正解。在睡虎地秦简中,与司寇相近的候很可能也是“其法不名耐者”所当同时论处的身份或者说劳役刑,以此解释秦简《捕盗律》,则捕人相移以受爵者应论耐为司寇或候。回到本案州陵县吏议的后一议,其主张癸、琐等当耐为候的法律依据,不能排除就是这条《捕盗律》或与之类似的某一律文,这也许是依据现有资料所能作出的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
(四)七月乙未南郡的最终判决
州陵县的上谳作于六月丙辰朔癸未(28日),十余天之后的七月丙戌朔乙未(10日),南郡假守贾即作出了报谳。其报云:“谳固有审矣,癸等其审请琐等所,出购,以死辠购备予琐等,有券。受人货财以枉律令,其所枉当赀以上,受者、货者皆坐臧为盗,有律,不当谳。获手。其赀绾、越、获各一盾。它有律令。”
1.癸、琐等“皆坐臧为盗”。南郡的报谳指明要适用“受人货财以枉律令,其所枉当赀以上,受者、货者皆坐臧为盗”之律,以解决监御史康所劾的未将癸、琐等相移的“私钱二千”入罪的问题。至于州陵吏议的后一议,如前文推测不误,依据的是《捕盗律》“捕人相移以受爵者,耐”之类的律文,其明文规定只适用于“相移以受爵”的情形,据该律定癸、琐等的罪是一种脱离正条的比附,而且也没有解决“私钱二千”入罪的问题,故南郡也未加采用。
所谓“枉律令”,整理者注释已指出即汉律中的“枉法”,与之有关的律文,《二年律令》有:
《二年》60:受赇以枉法,及行赇者,皆坐其臧为盗。罪重于盗者,以重者论之。
规定受赇者、行赇者均应坐臧为盗。西汉中期以后,法规似乎有所增益,斯坦因所获汉简有云:
《敦煌》1875:行言者若许,及受赇以枉法,皆坐臧为盗,没入□□。〔30〕所脱或“县官”二字。行言者本行职者也,□〔31〕释文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92页。本文据文意对标点有所调整。
该简前似有脱去的简文,但可看出应坐臧为盗者中又增加了“行言者若许”一项。秦汉文献中的“受赇”多以官吏为主体,故常常被解释为相当于今天的受贿,但明确的反例也是存在的,《汉书·酷吏传·尹赏》载汉成帝永始、元延间,“长安中奸滑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报仇。”颜注云:“或有自怨于吏,或受人赇赂报仇雠也。”又《奏谳书》案例7云:
《奏谳书》51-52:●北地守(谳):女子甑奴顺等亡,自处彭阳。甑告丞相,自行书顺等自赎甑所,臧过六百六十。不发告书,顺等以其故不论。疑罪。●廷报:甑、顺等受、行赇狂(枉)法也。〔32〕释文据彭浩等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45页。“甑所”二字属上读,见张建国:《汉简〈奏谳书〉和秦汉诉讼程序初探》,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2期。
女子甑让逃亡的奴顺等向自己交钱自赎,但奴婢逃亡是犯罪行为,应受国家法律制裁,〔33〕《二年》简160:“奴婢亡,自归主、主亲所智,及主、主父母、子若同居求自得之,其当论畀主,而欲勿诣吏论者,皆许之。”明确规定了奴婢逃亡“勿诣吏论”的前提条件是“自归”或“自求得之”,且其罪须“当论畀主”,奴顺等的情况显然不合于此。不可主奴双方私自了结,故甑、顺等也被认定为“受、行赇枉法”。《说文》解“赇”为“以财物枉法相谢也”,徐铉注:“非理而求之也”,《玉篇》云:“质也,请也”,都没有限定为吏的意思在内。〔34〕“枉法”一般也多理解为官吏在审判中故意出入人罪,现代刑法里的“徇私枉法”、“枉法裁判”等就是这样使用“枉法”一词的。现在由本案中癸、琐等被认定为“枉律令”,可知当时的“枉法”、“枉律令”的涵义远较出入罪为宽。
本案中,琐等三人接受私钱而将所捕群盗移交给癸等,其行为有悖于“弗当以得购赏而移予它人”之条,应认定为“枉律令”,其所枉之罪即癸等应处之罪(坐盗未有取赎黥),超出了“所枉当赀以上”的要求,故得以“受者”的身份坐臧“私钱二千”〔35〕《答问》简12:“甲乙雅不相智(知),甲往盗丙,毚(纔)到,乙亦往盗丙,与甲言,即各盗,其臧(赃)直(值)各四百,已去而偕得。其前谋,当并臧(赃)以论;不谋,各坐臧(赃)。”《二年》简58:“谋偕盗而各有取也,并直其臧以论之。”据此,癸等5人、琐等3人以私钱二千相受,已谋分购,当并臧以论。为盗,癸等五人则要以“货者”的身份坐臧为盗。借着这种方式,南郡妥善地处理了将“私钱二千”入罪的问题。据《二年律令》的处罚标准(简56),琐等、癸等均应论黥城旦之罪,这一点劳武利先生已经指出。〔36〕劳武利先生已指出南郡是根据“私钱二千”作出了“黥为城旦舂”罪的最终判决。参见[德]劳武利:《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与岳麓书院秦简〈为狱等状四种〉的初步比较》,李婧嵘译,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南郡所判的黥城旦明显重于州陵县所判的赎黥和罚戍,据“罪重于盗者,以重者论之”之条(《二年》简60),前者应吸收后者,实际只执行黥城旦之罪。〔37〕本文初稿在第三届“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时,认为南郡判决是对州陵县判决的补充,二个判决均应执行。会后彭浩先生向笔者指出,南郡判决应是对州陵县判决的替代。按之律文,彭先生的意见显然是正确的。
值得注意的是,据南郡所引律文的规定,只要达到“所枉当赀以上”条件的就应统统按坐臧为盗来处理。但由于秦律中盗的最低处罚标准是“一钱”,当“受人货财”不足一钱时,依该律就无法论罪,而《二年律令》规定“罪重于盗者,以重者论之”,可在所枉之罪和盗罪中取其重者论罪。〔38〕如《答问》简7云:“或盗采人桑叶,臧不盈一钱,可(何)论?赀繇(徭)三旬。”以此为例,如果甲给乙不盈一钱的财物,让乙去盗采人桑叶,其所枉当赀徭三旬,甲当坐臧为盗,但臧直不盈一钱,无法论罪,据《二年》则可按所枉之罪论为赀徭三旬。相比之下,《二年律令》的规则设计显然更加完善,法网也更为严密。
2.“获手,其赀绾、越、获各一盾”。由于南郡对癸、琐等作出的最终判決与州陵的初判有出入,州陵初判的负责人就要因为“论失”而受到处罚。南郡在报谳中专门记下“获手”一项,就是为了明确史获作为判决负责人的地位。“某手”常见于里耶秦简的公文书中,其涵义尚存争议,有撰写者、抄手、校对者、经手人、各官府负责者、官府中的低级办事员等说。〔39〕参见黎明钊、马增荣:《试论里耶秦牍与秦代文书学的几个问题》,载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帛(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5-76页;张乐:《里耶简牍“某手”考——从告地策入手考察》,来源: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61,2013年10月22日访问;陈伟主编:《里耶秦简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注12;单育辰:《谈谈里耶秦公文书的流转》,来源: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03,2013年10月22日访问。本案中的“州陵守绾、丞越、史获论令癸、琐等各赎黥”,是令长、丞、史在判決文书上联合署名之例,汉简《奏谳书》的“南郡守强、守丞吉、卒史建舍治”(简67、74)、“新郪甲、丞乙、狱史丙治”(简97)、“(雍县)丞昭、史敢、铫、赐论黥讲为城旦”(简106)也是如此。可见史虽非如令长、丞那样拥有“独断治论”的资格(《二年》简105),甚至依法不具有断狱的权限(断狱权限最低到县丞为止〔40〕《二年》简102:“县道官守丞毋得断狱及谳。相国、御史及二千石官所置守、叚(假)吏,若丞缺,令一尉为守丞,皆得断狱、谳狱。”此或即令、丞、史联合署名论狱的依据。),但也是论狱的参与者之一。这样看来,“某手”还是理解为某一事务的经手人、承办者为好,“获手”指史获参与了癸、琐一案的判决工作,因此他也须对该判决负责。
由于南郡的最终判决是以坐臧为盗的黥城旦罪代替了州陵所判的赎黥和罚戍,量刑大为提高。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把官吏在耐和黥之间过失地出入罪的行为称为“失刑罪”(简33-36),绾等的“论失”正与之相符,不过可惜的是该条并未记载对“失刑罪”的处罚。又有一条如下云:
《答问》94:赎罪不直,史不与啬夫和,问史可(何)论?当赀一盾。
不直即“端重若轻之”(《答问》简36、93),赎罪不直即论赎罪端重若端轻,整理小组译为“判处赎罪不公正”。〔41〕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15页。啬夫是基层官署的令、长。〔42〕参见裘锡圭:《啬夫初探》,载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论赎罪不直,史不与令、长和而被赀一盾,不直的令长所受的处罚应当更重。本案中绾、越、获在判决文书上联合署名,自然并非“不和”,故三人应负同等的责任,又因论失的罪责轻于不直,故他们被判处与“不和”的史相同的处罚“赀一盾”,这与罪、刑适应原则是相符合的。〔43〕《岳麓简(三)》“学为伪书案”中,胡阳县的治狱官吏也被郡论赀一盾(简0816:“赀某、某各一盾”),这个处罚是针对胡阳县未能辨清冯毋择的爵位而作出的,其所适用的应是与《二年》简17“□□□而误多少其实,及误脱字,罚金一两”同类的条文,与本案所适用的关于治狱不当的处罚规定无关。
里耶秦简第8层中有这样一篇残缺的案卷:
(1)8·1132正、背:卂(讯)敬:令曰:诸有吏治已决而更治者,其罪节(即)重若8·1832+8·1418益轻,吏前治者皆当以纵、不直论。今甾等当赎8·1133耐,是即敬等纵弗论殹,何故不以纵论赎?〔44〕释文及其缀合、编联据陈伟主编:《里耶秦简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1页。本文据文意对标点有所调整。
(2)8·1107:甾等,非故纵弗论殹。它如劾。〔45〕释文据陈伟主编:《里耶秦简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8页。
其中文书(1)是对治狱官吏敬的讯问辞,文书(2)应即敬或其同僚相应的答辩辞。其中引“令”曰:“诸有吏治已决而更治者,其罪即重若益轻,吏前治者皆当以纵、不直论。”据此,敬等没有论应赎耐的甾等的罪,即使并非出于故意(“非故纵弗论殹”),也要被认定为“纵”,论以赎耐之罪。〔46〕《二年》简93:“鞠(鞫)狱故纵、不直,及诊、报、辟故弗穷、审者,死罪斩左止为城旦,它各以其罪论之。”因为甾等当赎耐,所以故纵的敬等也当以赎耐论,可知简1132正面的“论”当与背面的“赎”字连读。本案中绾等的判决被南郡更改,与此令所谓“诸有吏治已决而更治者,其罪即重若益轻”的情形正相符合,但实际上绾等最后只论赀一盾,这是廿五年时此令尚未实施的缘故。岳麓简《三十四年质日》“二月”条下记云:“甲辰,失以纵、不直论令到”(简J18)、“乙丑,失纵、不直论令到”(简621),所谓“失以纵、不直论令”当即此令,《质日》恰好记载了此令颁布抵达的时间,〔47〕由于文书的下达可能同时经不同路径进行,故相同内容的文书分两次送达并无抵牛吾。且正巧就是“适治狱不直者筑长城,取南方越地”的三十四年。可以想见,此令的生效对在南越的军事灾难所导致的劳力和兵力短缺定将有所帮助。这种对官吏治狱有失的处罚的严格化趋势也许一直延续到了汉初。《二年》简95-98云:其非故也,而失不审,各以其赎论之。爵戍四岁及毄城旦舂六岁以上罪,罚金四两。赎死、赎城旦舂、鬼薪白粲、赎斩宫、赎劓黥、戍不盈四岁,毄不盈六岁,及罚金一斤以上罪,罚金二两。毄不盈三岁,赎耐、赎?(迁)及不盈一斤以下罪,购、没入、负偿、偿日作县官罪,罚金一两。该条规定了官吏治狱“失不审”时的处罚,总的原则是“各以其赎论之”,但失不审的罪没有对应的赎罪时,则以罚金来执行。其中最低一等的罚金一两,对应的是赎耐、赎迁等罪的失不审,而本案中州陵的论失是在黥城旦与赎黥之间出入,其所判的罪是赀一盾,即赀甲盾中的最轻者,与罚金一两相当。两相比照,《二年》中虽然已没有了“失以纵、不直论令”的痕迹,但对治狱失不审的处罚仍明显要高于廿五年的秦律。到了汉景帝后元年下诏云:“狱疑者谳有司,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有令谳而后不当(《刑法志》作“有令谳者已报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汉书·景帝纪》)规定谳疑狱而后不当的,不再认定为“失”,所适用的情形虽与本案不同,但也可看出这一趋势的缓和。
三、结语
围绕着戍卒、吏徒捕盗相移和县吏论狱有失两个事实,本案产生了由郡、县二级机构作出的数量丰富的定罪量刑意见,其中有些已经在文中载明了法律依据,比如南郡重新判决时所适用的“受人货财以枉律令”之律;有些可以在迄今已见的秦汉律令中找到明确的依据,比如州陵县判决癸等、琐等赎黥所适用的“盗未有取律令”、判决沛等无罪所适用的“共捕罪人相移,许之”之律;有些虽然尚未找到明确的依据,但是其量刑轻重是可以和已知的同类规定相适应的,比如州陵尝试重判时后一“议”所主张的癸等、琐等“当耐为候”、南郡判决论失的绾等“赀一盾”等。总体上看,其法律依据大多与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中的律令条文相符,变化不明显,延续性很强,只有对官吏治狱有失的处罚经历了较明显的波动,秦始皇三十四年的“失以纵、不直论令”和“谪治狱吏不直者”达到了处罚的顶峰,到了《二年律令》时则又缓和了下来。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本案中既没有出现如《法律答问》中那样引“廷行事”破律的情况,也没有见到如《奏谳书》案例三那样参考已决判例的痕迹,尽管郡、县官吏在法律适用能力上仍存在一些差距,但可以说各级官吏都在试图直接援引律令条文进行裁断,这正是秦国要求“人臣谨奉法以治”(《奏谳书》简149)的一个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