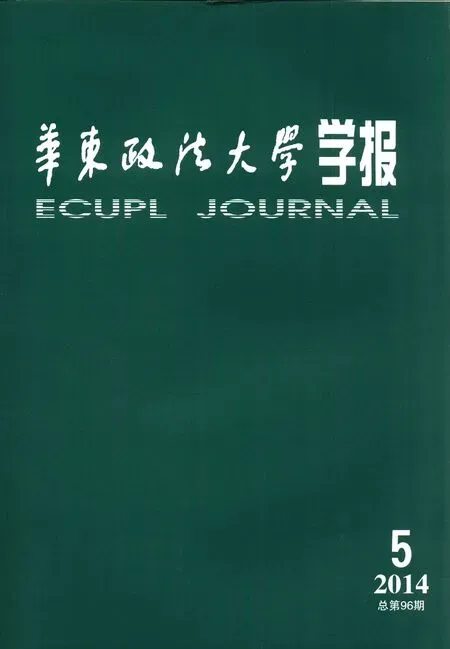论外交保护中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限制
——以联合国《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第15条为线索
张 磊
一、问题的提出:如何限制用尽当地救济原则
外交保护指当本国国民(自然人与法人)在国外的合法权益受到所在国国际不法行为的侵害,且用尽当地救济办法仍得不到解决时,国家对该外国采取外交行动以保护本国国民的国家行为。〔1〕参见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页。这是国家保护海外国民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也是国家属人管辖权的体现。
在新的历史阶段,随着海外利益的与日俱增,中国公民和企业在他国遭遇不法侵害的事件也迅速增多,例如2004年西班牙发生“烧鞋事件”,2009年俄罗斯发生“大市场风波”,2010年菲律宾发生香港游客劫持事件,2011年泰国湄公河流域发生中国船员遇害惨案等。可见,中国在外交保护领域面临严峻的挑战。
用尽当地救济是国家实施外交保护的法律条件之一。所谓用尽当地救济,是指受害人已经充分利用了东道国的所有救济手段(如司法、行政等)。〔2〕参见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页。这是东道国属地管辖权的体现。但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这个原则并不是绝对的,否则将造成对外交保护的过分拖延,甚至导致无法实施外交保护。因此,如何将它限制在一个合理限度内成为重要命题。
在现阶段,这一命题的重要性对中国显得尤为突出。例如,就自然人而言,主要的受害群体是我国规模庞大的海外劳工。由于技术水平不高,他们在国外大多只能从事一些初级、高危险、高强度的工作。当遭到侵害后,劳工们的维权能力又普遍低下。东道国政府对于他们的控诉往往肆意拖延或敷衍应付,甚至东道国政府本身就是加害者。就法人而言,主要的受害群体是我国的国有企业。它们是现阶段中国海外投资的“主力军”。然而,近年来,欧美国家以各种理由制裁我国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中国企业在当地起诉东道国政府后,诉讼往往冗长繁复,还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难以保证公平客观。
近年来,无论对于自然人,还是对于法人,用尽当地救济似乎成为东道国阻挠或抗辩中国外交保护的“万能借口”。当中国有勇气和实力问责他国时,我们应当积极主张在合理的范围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进行必要的限制,从而避免东道国对国际法规则的滥用。
二、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进行限制的基本原理
总体而言,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进行限制的基本原理是属地管辖权的优越性具有相对性,即属人管辖权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优越于属地管辖权。国家对本国国民实施外交保护就是属人管辖权的体现;而东道国有权利要求他国在实施外交保护之前用尽当地救济,则是属地管辖权的体现。
(一)属地管辖权的优越性
相较属人管辖权而言,属地管辖权一般具有优越性。这是因为东道国对当地自然人与法人的控制能力往往强于他们的国籍国。
根据这个基本原理,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外交保护在诞生伊始就将用尽当地救济作为国家实施外交保护的前提条件之一。这种安排是对东道国属地管辖权的尊重。当然,这种尊重是以互惠为基础的。由于各国都希望他国尊重本国的属地管辖权,因此,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获得国际习惯的法律地位由来已久,并在国际法判例和国家实践中被频繁适用和反复重申。同时,也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外交保护之所以能够在现代国际法中被世界各国接受为法律规范,是因为“所有国家都分享了一种重要利益,这种利益来自作为互惠的用尽当地救济原则”。〔3〕Rosica(Rose)Popova,Sarei V.Rio Tinto and the 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 Rule in the Context of the Alien Tort Claims Act:Short-Term Justice,But at What Cost,Hamline Journal of Public Law and Policy,Vol.28,No.2.p.529.
(二)属地管辖权优越性的相对性
属地管辖权的优越性也存在例外情况,即国际法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允许属人管辖权优越于属地管辖权。这是因为现代国际法一方面肯定国家享有领土主权,但另一方面也对国家的领土主权做出一定的限制。常设国际法院审理的突尼斯和摩洛哥国籍法令案就是著名的案例。突尼斯和摩洛哥都曾是法国的殖民地。1921年,法国颁布法令规定:凡是满足条件且出生在突尼斯和摩洛哥的孩子都是法国国民。但是按照英国当时的国籍法,英国男子在国外所生的子女是英国国民。两国就此产生冲突。在协商无果后,英法将争端提交常设国际法院,请求获得咨询意见。在常设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的指导下,法国承诺在未给予出生于突尼斯和摩洛哥的孩子以选择国籍的机会之前,法国将不把其国籍强加给他们。〔4〕参见[德]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及国际法研究所主编:《国际公法百科全书(第二辑):国际法院、国际法庭和国际仲裁的案例》,陈致中、李斐南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64、465页。
根据这个原理,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会受到一定限制。著名的罗伯特·布朗案(Robert Brown Case)就是典型的例子。1895年,南非宣布黄金开采业对外开放。美国公民罗伯特·布朗按当地法律向南非政府申请开采执照。然而,南非政府却宣布之前开放采矿业的公告作废。布朗随即诉至南非高等法庭并胜诉。南非总督竟然因此罢黜首席法官,强令重审此案。于是,美国向英国(当时南非的宗主国)提出外交保护要求。该案中,国际仲裁庭驳回了英国所谓当地救济尚未用尽的抗辩理由。〔5〕See United Nations Report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Vol.VI,pp.120-131.很显然,在司法极不独立的情况下,绝对奉行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可能导致不公正。属地管辖权的优越性就不能得到支持了。
(三)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例外
限制用尽当地救济一直备受争议。这个问题在国际法上尚未得到充分规范,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这是由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之间的博弈造成的,一方面,东道国希望受害者用尽当地救济,防止他国滥用外交保护;另一方面,受害者的国籍国对部分国家的当地救济缺乏信任,希望构成用尽当地救济的例外情况,防止东道国恶意拖延。
我们应当首先肯定用尽当地救济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如果当地救济能够解决争端,那么就可以避免外交保护的发生,即国家之间的激烈对抗,这是因为“指责一个国家破坏国际法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6〕参见[英]M.阿库斯特:《现代国际法概论》,汪瑄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页。第二,相比费用昂贵的外交保护,当地救济不但经济,而且在取证和执行方面都比较便利;第三,用尽当地救济可以给予东道国弥补过失的机会。然而,当上述合理性不复存在时,用尽当地救济就失去了意义,即可以构成例外情况。按照这个思路,例外情况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由于特殊原因而没有必要用尽当地救济;第二,东道国放弃要求用尽当地救济的权利。
以上就是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进行限制的基本原理。不过,这个基本原理在具体适用中会有更多、更细致的问题有待辨析。
三、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进行限制的具体适用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2006年二读通过了《外交保护条款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由于在长达十多年的编纂过程中,各国政府和学者积极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与主张,因此这是目前该领域最权威的国际法文件,是相关研究的集大成者。
关于用尽当地救济的例外情况,《草案》第15条规定:“(a)不存在合理的、可得到的、能提供有效补救的当地救济,或当地救济不具有提供此种补救的合理的可能性;(b)救济过程受到不当拖延,且这种不当拖延是由被指称应负责的国家造成的;(c)受损害的个人与被指称应负责的国家之间在发生损害之日没有相关联系;(d)受损害的个人明显地被排除了寻求当地救济的可能性;(e)被指称应负责的国家放弃了用尽当地救济的要求。”〔7〕U.N.Doc.A/61/10,p.20.
笔者认为,上述意见既有可取之处,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还有应当细化的部分。
(一)对例外情况的表述值得肯定
国际社会对《草案》第15条(a)项的表述存在较大争议。早在2002年,国际法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约翰·杜加尔德在研究报告中将各方意见归纳为三种表述方案——方案一是显属徒劳(obviously futile),方案二是没有合理的成功机会(no reasonable prospect of success),方案三是没有提供获得有效补救办法的合理可能性(no reasonable possibility of effective redress)。
“显属徒劳”的表述方式出现在国际联盟行政院审理的芬兰船舶案中。一战期间,英国征用了部分芬兰船舶。1920年,芬兰船主们根据英国《赔偿法》向英国海事交通运输仲裁委员会起诉英国政府。1926年,诉讼请求被驳回后,船主们没有提出上诉,而是由芬兰直接实施外交保护。两国于1931年提请国际联盟行政院仲裁。英国以未用尽当地救济为由进行抗辩。1934年仲裁裁决认为:依照英国《赔偿法》,芬兰船主们的损失不能得到赔偿,而且该法规定上诉只能就法律问题而不能就事实问题提出。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上诉不可能获胜。因此,芬兰已用尽当地救济。〔8〕See United Nations Report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Vol.III,pp.1479-1550.“显属徒劳”的表述方式不仅要求证明当地救济是徒劳的,而且还要证明这种徒劳已经达到显而易见的程度。这个门槛不但过高,而且模糊。于是,“我们看到这一标准对法官思考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几乎没有任何帮助”。〔9〕David R.Mummery,The Content of the Duty to Exhaust Local Remedies,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58,No.2,1964,p.401.有鉴于此,在著名的1989年西西里电子公司案(Case Concerning Elettronica Sicula S.P.A.)中,国际法院并没有采用这个表述方式。
“没有合理的成功机会”的表述方式来自欧洲人权委员会的判例,例如1997年XZY诉英国政府案就是如此。尽管欧洲人权委员会的判例明确地支持这一表述,但它的适用条件对求偿人过于有利。这是因为它将“是否有效”(whether effective or nor)的概念偷换成了“是否成功”(whether successful or not)。
然而,就规则的初衷而言,考察当地救济是否应被用尽并非依据当地救济能否给予令受害者满意的结果(是否成功),而是看它是否存在给予受害者救济的可能性(是否有效)。如果受害者有可能获得救济,但仅因为预期结果可能无法令受害者满意就构成用尽当地救济的例外情况,那么受害人就获得了过大的自由。换一个角度看,考察“是否成功”会使得国际法庭将过多的因素牵扯进来。正如新西兰学者大卫·马默里(David Mummery)所担心的那样:“假如照此办理,国际法庭不应仅审查法律规定的救济办法,而且应审查救济办法所处的环境。某一具体案件的结果将取决于各种因素间的平衡。”〔10〕David R.Mummery,The Content of the Duty to Exhaust Local Remedies,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58,No.2,1964,pp.400,401.这就使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被过分地扩大化与复杂化了。
“没有提供获得有效补救办法的合理可能性”的表述方式克服了之前两个方案的不足。一方面,“合理可能性”的措辞避免了类似“显属徒劳”那样过于极端的考察导向;另一方面,“没有提供获得有效补救办法”的措辞避免了类似“没有合理的成功机会”那样过分扩大的考察范围。在此基础上,国际法委员会将它作为《草案》第15条(a)项。
(二)条文有重叠、多余之处
首先,《草案》第15条(b)项与(a)项是重叠的。《草案》第15条(b)项所列的“不当拖延”在很多权威的国际法文件中都能够找到,例如1930年《海牙国际法编纂会议第三委员会通过的条约草案》第9条、1933年《第七次美洲国家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国家国际责任的决议》第3条以及1961年《关于国家对外侨造成损害所负国际责任的哈佛公约草案》第19条等。在判例方面,比较著名的案例是1931年埃尔奥罗矿业铁路公司案(El Oro Mining&Railway Company Case)。该案中,当地救济被拖延了9年仍然没有做出判决,因此国际仲裁庭认为构成用尽当地救济的例外情况。1957年国际工商业投资公司案(Interhandel Case)也比较著名。在这个案件中,当地救济被拖延了10年之久。
实际上,《草案》第15条(a)项已经包含了“不当拖延”的情况。然而,为什么《草案》还要将“不当拖延”单独规定为(b)项呢?英国著名学者阿墨拉辛格(Amerasinghe)提出的辩解得到了较多学者的认同。尽管承认(a)项与(b)项是重叠的,但他认为:更好的做法是对“不当拖延”进行独立考察,因为拖延可能不总是意味着求偿人不会在一段时间后获得成功。〔11〕See Chittharanjan Félix Amerasinghe,Local Remedies in International Law,2nd 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210,211.简言之,阿墨拉辛格主张拖延本身并不一定属于(a)项。
笔者认为,阿墨拉辛格可能混淆了两个概念——“拖延”(delay)与“不当拖延”(unreasonable delay)。笼统的拖延行为固然不一定属于(a)项,即“没有提供获得有效补救办法的合理可能性”,但能够上升为用尽当地救济例外情况的拖延必须达到这一程度。这时的“拖延”才是(b)项所要讨论的“不当拖延”。因此,严格地讲,“不当拖延”已经被“没有提供获得有效补救办法的合理可能性”所涵盖。事实上,国际法委员会两位特别报告员阿马多尔(Amador)和阿戈(Ago)在各自的研究报告中都没有将“不当拖延”列为单独的例外情况。
其次,《草案》第15条(d)项与(a)项是重叠的。根据《草案评注》,《草案》第15条(d)项具体包括以下情形:“被告国以法律手段或威胁人身安全的手段阻止受损害的人进入该国领土,从而使之没有机会到当地法庭提起诉讼,或者被告国的犯罪集团阻碍受损害的人在当地法院提出诉讼;虽然受损害的人本应承担在被告国法庭提起诉讼的费用,但有些情况下这种费用过高,明显排除了遵守用尽当地救济的可能。”〔12〕U.N.Doc.A/61/10,p.83.在国际法委员会之前的研究报告中,这项例外情况被归纳为“拒绝接触”(denial of access)。
很显然,《草案》第15条(a)项也已经包含了“拒绝接触”。约翰·杜加尔德尽管承认这一点,但仍主张将其单独规定。他认为:有关的当地救济尽管理论上是可能获得的和有效的,但实际上却没有接触的机会,而且这种事例屡见不鲜。〔13〕See U.N.Doc.A/CN.4/523,p.38.
杜加尔德的理由令人匪夷所思。一项“没有机会接触”(inaccessible)的当地救济怎么能够被称为“可以获得的和有效的”(available and effective)呢?实际上,这种情形明显属于第15条(a)项。至于《草案评注》进一步的辩解理由,即所谓“费用过高明显排除了遵守用尽当地救济的可能”也无法使这种例外情况具有特殊性。更何况《草案评注》自身在有关(a)项的论述中也提到:“要达到(a)项的要求,受损害的人仅仅表明成功的可能性很低或进一步上诉有困难或费用昂贵还不够。”〔14〕U.N.Doc.A/61/10,p.77.这说明《草案评注》在(a)项和(d)项中都考虑了费用过高的问题。
最后,《草案》第15条(c)项过于前瞻而显得多余。在一些情况下,受害者可能与东道国领土没有任何联系,例如在跨界污染事件中,受害者可能在东道国领土之外的地区。要求所有受害者都千里迢迢地到东道国用尽当地救济的确存在困难。于是,国际法委员会将这种情况列为《草案》第15条(c)项。这项例外情况在学界也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
然而,尽管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以此剥夺东道国要求用尽当地救济的权利可能并不是现实情况的反映。诚然,在受害者与东道国缺乏联系的大多数情况下,国际条约或国际法判例没有提及用尽当地救济。不过,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东道国没有权利要求用尽当地救济,而是因为东道国明示或默示地放弃了要求用尽当地救济的权利。例如《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第11条第1款规定:“根据本公约向发射国提出赔偿损害要求,无须等到要求赔偿国或其代表的自然人或法人用尽当地救济后才提出。”〔15〕《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来源 http://www.chinesemission-vienna.at/chn/hplywk/5treatiesCH/t768117.htm,2014年5月2日访问。又如在著名的1941年特雷尔冶炼厂案(Trail Smelter Case)中,加拿大在审理中没有提出用尽当地救济的抗辩。
世界很多国家在上述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笔者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在之前的研究报告中原本是这样表述该例外情况的:“受害人与被指称责任国之间没有相关联系,或依据案情,用尽当地救济实为不合理。”〔16〕U.N.Doc.A/CN.4/567,p.30.奥地利建议,删除该项的前半部分,使其局限于“实为不合理”(otherwise unreasonable)的情况。美国则建议删除“实为不合理”的部分。中国政府也认为“依据案情,用尽当地救济实为不合理”一句提供了任意扩大适用例外情况的可能性,应予删除。英国呼吁有必要对“相关联系”做出说明。意大利则抱怨“没有相关联系”与“实为不合理”之间没有多大的联系,并要求附加例证清单。《草案》最终选择了更为含糊的“相关联系”(relevant connection)。
由此可见,在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与国家实践的基础上,仓促地将《草案》第15条(c)项作为用尽当地救济的例外情况是不可取的。
(三)对东道国弃权的规定应当细化
《草案》第15条(e)项是对东道国弃权的规定。放弃权利看似天经地义,但实际上隐含着比较复杂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东道国是否可以放弃要求用尽当地救济的权利?如果用尽当地救济是一项程序规则,那么放弃这项权利是可能的。然而,如果用尽当地救济是一项实体规则呢?
众所周知,国际不法行为导致国家责任,而外交保护追究的就是东道国的国家责任。如果用尽当地救济是构成国际不法行为的要件之一,那么如果没有用尽当地救济就不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没有国际不法行为就不存在国家责任,不存在国家责任就使外交保护无的放矢。于是,如果用尽当地救济是一项实体规则,那么东道国就没有放弃这项权利的机会。不过,《草案》似乎并没有考虑到这个复杂的问题。
用尽当地救济是程序规则还是实体规则,学界对此是存在激烈争论的,但始终没有权威结论。权威的国际法文件之间说法不一,甚至前后矛盾。例如1929年《关于国家对在其领土内外国人的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所负责任的哈佛公约草案》(Harvard Draft Convention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Damage Done in Their Territory to the Person or Property of Foreigners)第6条至第9条支持实体法说,但是到了1961年《关于国家对外侨造成损害所负国际责任的哈佛公约草案》(Harvard Draft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juries to Aliens)第1条第2款却转而支持程序法说。国际法判例大都含糊其辞。各国在不同的案例中大都出于实用的考虑,而不是根据法理来选择自己的立场,例如意大利在1938年摩洛哥磷酸盐案(Case concerning Phosphates in Morocco)中主张实体规则,但在50年后的西西里电子公司案中却转而主张程序规则。
笔者认为,用尽当地救济的规则性质取决于所指控的行为是否违反国际法义务。国际不法行为的构成包含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前者是指行为应当可归因于国家,后者是指行为应当违反国际法义务。在满足主观要件的情况下,当所指控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义务,那么国际不法行为已经产生,东道国国家责任也随即产生,所以用尽当地救济显然是程序规则,因为此时它已与国家责任无关;当所指控的行为没有违反国际法义务,或只违反东道国当地法律,此时国际不法行为尚未出现。那么,只有用尽当地救济仍然无法获得赔偿的情况下,东道国才会产生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于是,用尽当地救济就是实体规则。
第二,是否可以默示地放弃要求用尽当地救济的权利?《草案评注》对默示放弃采取支持的立场,并予以解释:“放弃当地救济不能是随便默示的。国际法院在西西里电子公司案中认定了国际习惯的一项重要原则,即在没有任何明确表示愿意放弃的言词的情况下,被认定为默示放弃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如果当事方放弃当地救济的意愿是明确的,则必须落实这个意愿。司法裁决与法学家的著作都支持此结论。对于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默示放弃当地救济的愿意,不可能为此制定一项通则。每个案例必须根据有关文书的措辞和制定的背景做出判断。在被告国同意把将来可能与索赔国发生的争端交付仲裁的情况下,国际法院在西西里电子公司案中确认,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不推定默示放弃;被告国与索赔国在争端所涉及的国民受到损害后才缔结仲裁协定的情况下,如果协定没有就保留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做出规定,则可以认为默示放弃了该原则。”〔17〕U.N.Doc.A/61/10,p.84.
对在争端发生之前国家之间达成的仲裁协议没有明确规定用尽当地救济的情况,国际法委员会认为不构成默示放弃。这一点笔者是同意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损害发生后国家才达成的仲裁协议如果没有明确规定用尽当地救济,是否可以构成默示放弃?国际法委员会认为可以,但是笔者认为结论并非如此简单。国家之间在损害发生后达成仲裁协议最多只能被看做放弃用尽当地救济的一个步骤而已,但不能认为放弃行为已经全部完成。这一点用国际法委员会自己的理论也能解释,即“放弃当地救济不能是随便默示的……但是如果当事方放弃当地救济的意愿是明确的,则必须落实这个意愿”。〔18〕U.N.Doc.A/61/10,p.84.也就是说,单凭一个意思表示并不能当然地构成默示放弃,还必须要有落实这个意愿的行动。正因为如此,国际法委员会才认为在损害发生之前达成的仲裁协议没有明确规定用尽当地救济的情况不构成默示放弃,因为它最多只是表达了这个意愿而已。同理,如果在损害发生之后国家之间达成的仲裁协议没有明确规定用尽当地救济,那么该协议也仅仅只是一个意愿。它要构成默示放弃,则必须要有落实这个意愿的行动,例如国内法庭主动停止受害者的诉讼案件等。
四、我国对限制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应当采取的立场
我国对限制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立场应当首先考虑到海外利益增加的现状。在此背景下,国家角色的定位应从维护属地管辖权转向兼顾属人管辖权,同时在具体规则的设计上应对规范导向型与结果导向型予以区别对待。
(一)从维护属地管辖权向兼顾属人管辖权的转变
在《草案》长达十多年的编纂过程中,中国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向国际法委员会递交政府意见,而是在联合国大会上前后6次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简短的发言。具体到用尽当地救济的例外情况,我国的出发点是站在东道国的立场上表示了对限制属地管辖权的不安。简言之,我国对限制用尽当地救济采取了近乎于抵触的态度,希望尽可能减少此种限制。
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官方立场,是因为我国已经习惯于将自己定位为东道国。这源自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旧中国长期沦为半殖民地,对列强的外交保护心存芥蒂。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西方国家常常滥用外交保护,甚至通过武力手段实施所谓的“外交保护”。例如,英国在1840年曾经派遣一支舰队远赴重洋对中国动武,理由是中国政府没有满足英国鸦片贩子的索赔请求。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处于主要的资本输入国地位。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表现为商品、资金、技术和人才等全方位短缺的,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不足,其中“资金短缺”是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因此,我国政府推行了“吸引外资”的政策,并延续至今。因此,我国习惯了从维护东道国属地管辖权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和确定自身的立场。
步入新世纪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变为供给过剩,有效需求不足,其显著标志就是彻底告别了“资本短缺”,步入“资本过剩”的时代。我国如今已经到了资本输出的发展阶段。因此,我国应当从专注属地管辖权转向兼顾属人管辖权,以便更好地对中国的海外利益实施外交保护。近年来,一些国家试图利用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来延迟或阻碍中国的外交保护,给中国企业造成了进一步的损害。因此,我国应当转变在用尽当地救济问题上的立场,对滥用属地管辖权的行为提出合理的限制意见。
(二)区别对待规范导向型与结果导向型情形
如上所述,除了东道国弃权的情况外,《草案》限制用尽当地救济的核心在于第15条(a)项。国际法委员会将《草案》第15条(a)项细分为六种具体的适用情形:“(1)当地法院对所涉争端没有管辖权,(2)当地法院不会审查外国人申诉的行为所依据的国家法律;(3)当地法院极不独立;(4)存在一贯对外国人不利的明确判例;(5)当地法院无权给予外国人适当、充分的救济;(6)被告国没有适当的司法保护制度。”〔19〕U.N.Doc.A/61/10,p.79.笔者认为,应当对这六种具体适用情形做进一步的分类,使其更加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简言之,即将其区分为规范导向型与结果导向型。
所谓规范导向型,采取的是演绎逻辑,它是指根据东道国的法律规范推导受害人是否能够在当地救济中获得公正对待。上述六种适用情形中,属于规范导向型的有第1、2、5这三种。在这三种例外情况中,判定没有必要用尽当地救济的根据是东道国的法律规范。前文所述的芬兰船舶案就是典型的例子。
所谓结果导向型,采取的是归纳逻辑,它是指根据东道国的行为结果推导受害人是否能够在当地救济中获得公正对待。上述六种适用情形中,属于结果导向型的有第3、4、6这三种。在这三种例外情况中,判定没有必要用尽当地救济的根据是东道国之前的行为结果,而非该国的法律规范。前文所述的罗伯特·布朗案就是典型的例子。
由于规范导向型依据的是法律规范,所以它采取的是相对客观的标准;而结果导向型依据的是行为结果,所以它采取的是比较主观的标准。
根据这个基本判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规范导向型的例外情况,中国应当主张国际法采取相对宽松的适用条件;对于结果导向型的例外情况,中国应当主张国际法采取相对严格的适用条件。这是因为降低前者的“门槛”一般不会造成滥用外交保护的情况,同时也能够较为合理地限制东道国的属地管辖权;而抬高后者的“门槛”可以有效防止滥用外交保护,同时不至于对东道国的救济体系做出有偏见的预判。这样宽严相济的立场既考虑到别国对我国实施外交保护的情况,也考虑到我国对其他国家实施外交保护的情况,兼顾了属地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
那么如何具体实现宽严相济呢?笔者认为,对于规范导向型的例外情况,只要推导结论符合法理逻辑即可成立;对于结果导向型的例外情况,只有当东道国的行为结果与推导结论之间的因果关系达到显而易见的程度才能构成例外。国际法院2007年对迪亚洛案(Diallo Case)的初步判决就体现了这一点。迪亚洛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经商的几内亚公民。1996年,刚果对他实施了非法拘禁和没收财产,并驱逐出境。1998年,几内亚为此向国际法院起诉刚果。刚果以没有用尽当地救济为由进行抗辩。国际法院认为,由于迪亚洛被驱逐出境,因此不再有可适用的当地救济,所以不存在所谓尚未用尽当地救济。〔20〕See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1 August 2009-31 July 2010),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2010,pp.22,23.很显然,这属于结果导向型的例外情况。国际法院在分析这种例外情况时,采取了比较高的标准,即刚果“拒绝迪亚洛入境”(deny Diallo’s entry)的行为结果与“要求用尽当地救济已无意义”(meaningless for exhausting local remedies)的推导结论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因果关系。
(三)需要完善的三项内容
第一,我国对“存在一贯对外侨不利的明确判例”应当有所变通。在《草案》第15条(a)项所属6种具体适用情形中,我国明确反对因为“存在一贯对外侨不利的明确判例”而免于用尽当地救济。〔21〕参见《中国代表刘振民先生在58届联大六委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第55届会议的报告”议题(外交保护)的发言》,来源 http://www.china-un.org/chn/lhghywj/fyywj/wn/fy03/t530817.htm,2014年2月18日访问。不过,这种主张在实践中对中国实施外交保护可能造成不必要的障碍。我国对日民间索赔就是典型的例子。
二战期间,日本根据《关于向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强迫大量中国公民赴日从事苦役。1943年到1945年间,有4万多中国平民和战俘被强掳到日本为奴。〔22〕参见管建强:《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对日索偿的法律基础》,华东政法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74页。二战后,中国受害者开始向日本国内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予以赔偿,但都被日本法院驳回。由此可以认定,日本的确存在一贯对外侨不利的明确判例。然而,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坚持成为中国政府实施外交保护的障碍,我国在政府表态中明确反对因为“存在一贯对外侨不利的明确判例”而免于用尽当地救济。由此可见,我国在该问题上的立场似乎应当有所变通。
第二,“受害者与东道国缺乏联系”并不当然地排除外交保护。对于《草案》第15条(c)项,我国政府认为它是多余的,但主张可以通过国际条约来免除用尽当地救济。〔23〕参见《中国代表刘振民先生在58届联大六委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第55届会议的报告”议题(外交保护)的发言》,来源 http://www.china-un.org/chn/lhghywj/fyywj/wn/fy03/t530817.htm,2014年2月18日访问。问题是,如果不存在相关的国际条约怎么办?中国对此并没有做出回答。事实上,“受害者与东道国缺乏联系”并不当然地排除外交保护。就国际惯例而言,此时的用尽当地救济问题往往通过国家弃权的方式得以解决。
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实践中就是这样做的。例如1954年,中国将1架英国国泰航空公司(Cathay Pacific Airways Ltd.)的客机误判为国民党军用飞机,将其击落。该事件震惊了全世界。中国随即主动向有关方面予以赔偿,没有要求用尽当地救济。
第三,默示的意思表示可以适用于国家放弃用尽当地救济的要求。对于《草案》第15条所列(e)项,中国政府在三次政府声明中都建议国际法委员会将东道国的弃权行为限定为明示放弃。然而,笔者注意到,我国的立场似乎并不坚决。刘振民大使表示:“责任国放弃用尽当地救济可作为例外,但‘放弃’应以明示行为做出为好。”〔24〕《中国代表刘振民先生在58届联大六委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第55届会议的报告”议题(外交保护)的发言》,来源 http://www.china-un.org/chn/lhghywj/fyywj/wn/fy03/t530817.htm,2014年2月18日访问。高风大使认为:“我们认为有必要强调,放弃应主要以明示方式做出方为有效。”〔25〕《中国代表高风在第59届联大六委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第56届会议工作报告”议题的发言》,来源http://www.china-un.org/chn/lhghywj/fyywj/wn/fy04/t530633.htm,2014年2月18日访问。段洁龙大使指出:“考虑到有关放弃行为是国家行为,为避免日后产生纠纷,我们建议将上述放弃改为‘国家明示放弃’。”〔26〕《中国代表段洁龙在第61届联大六委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第58届会议工作报告”议题中“外交保护”和“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两项专题的发言》,来源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wjbxw/t283191.htm,2014年2月18日访问。由此可见,我国的措辞中存在“为好”、“主要”和“避免日后产生纠纷”这样商量的语气。这说明我国的观点尽管有合理成分,但法理依据较为单薄。
事实上,存在明示的意思表示是最优的情况,但是在次优的情况下,国际法庭采信默示的意思表示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默示的意思表示在法律认定方面存在比较复杂的规则。不过,我国不能因噎废食,而是应当对默示的意思表示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