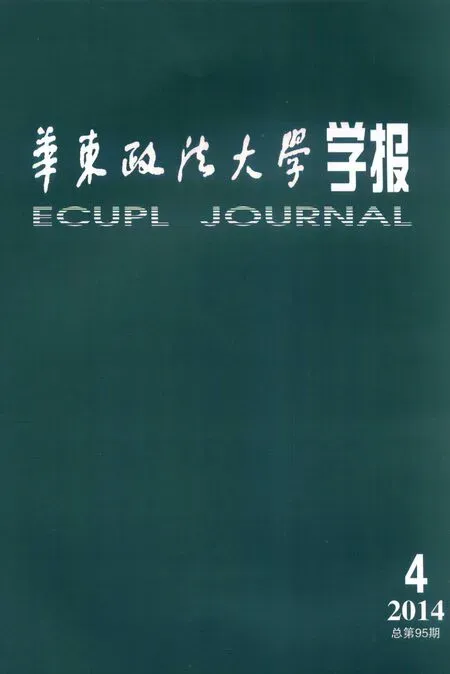见义勇为行为中受益人补偿义务的体系效应
王 雷
笔者在此前的研究中曾经提出:见义勇为属于民法上的紧急无因管理行为;见义勇为行为的救助人对被救助人不存在危难救助义务,这是构成见义勇为行为的前提条件,也是构成要件的核心;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是危难救助义务存在的法理基础;通过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等均不能得出将危难救助义务加诸社会一般成员的结论;对救助人在见义勇为行为中所受损害,应该根据矫正正义和分配正义的要求,建立多元化的救济机制。〔1〕参见王雷:《见义勇为行为中的民法学问题研究》,载《法学家》2012年第5期。
笔者在下文中将继续研究如下问题:见义勇为行为中救助人损害赔偿请求权规范基础的彼此关联和解释适用,见义勇为行为中受益人的补偿义务与无因管理中管理人对被管理人的损害赔偿等请求权、被管理人(本人)必要费用偿付义务等之间的关系,受益人补偿义务与社会救助制度的衔接。这些都属于见义勇为行为中受益人补偿义务对其他相关制度产生的体系效应,这些问题的讨论又都离不开对见义勇为行为作为特殊无因管理的“特殊性”之认识。
一、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定性
(一)见义勇为行为属于紧急无因管理
要厘清见义勇为行为中受益人补偿义务的体系效应,仍然离不开对见义勇为行为本身的性质界定,这也是研究该问题的前提。
从法律实用主义的角度看,见义勇为如果不涉及任何损害事实或者费用支出,法律对此不必干涉,可以将其归于“法外空间”。现实生活中,进入法律调整视野的见义勇为行为往往涉及损害承担、费用支出乃至行政确认、行政奖励、社会保障等问题,属于法律事实。我国大陆民法学通说认为,见义勇为行为完全符合无因管理的最基本要件要求。但见义勇为行为作为无因管理又具有特殊性。一方面,鉴于见义勇为行为所处情势常有一定程度危险性,故而属于高层次的紧急无因管理行为,其体现了更高程度的道德觉悟。另一方面,见义勇为行为所管理的“他人事务”具有特殊性,即具有“多重主观归属性”,〔2〕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请求权基础》,陈卫佐等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页。从管理事务的归属性上看,事务归属之人都可以被视为无因管理中的被管理人。〔3〕See Christian von Bar﹠ Eric Cliveeds,Principles,Definitions and Model Rules of European Private Law,Oxford,U-niversity press,2010,p.3072.据该书介绍,此为意大利法上的做法。实际上,在存在侵权人的侵害制止型见义勇为中,救助者在防止、制止被救助者民事权益受侵害过程中遭受侵权人的侵害,这就在救助者和被救助者之间的无因管理法律关系之外产生救助者和侵权人之间的侵权法律关系。
(二)见义勇为行为属于行政协助行为
如上所述,见义勇为中救助者所涉及“他人事务”的“多重主观归属性”中有一个面向就是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公权力机关。
我国《人民警察法》第6条、第19条规定人民警察有危难救助义务,可见危难救助本属公权力机关为社会成员提供的公共服务范畴,并非其他公民的法律义务,然而社会生活千变万化,警察不能时时站在每个公民的背后保护其权益,危难情势下其他公民的见义勇为行为就是对公权力救济不足的必要补充,此时救助者即代行了公权机关的法定救助职责。从行政法角度来看,见义勇为可以被定性为公民主动协助国家进行行政管理的行政协助行为。〔4〕参见傅昌强、甘琴友:《见义勇为行为的行政法思考》,载《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2期;胡建淼:《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将见义勇为行为界定为行政协助也就提供了国家对见义勇为行为承担补偿法律义务的最重要理论基础,也是构建对见义勇为救助者多元化救济制度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综上所述,见义勇为属于民法上的紧急无因管理,属于行政法上公民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协助行为。见义勇为中救助者所涉及“他人事务”的“多重主观归属性”是见义勇为行为法律性质多元性和对救助者所受损害弥补多元化的根本原因。
二、见义勇为行为中救助者所受损害的请求权规范基础
(一)《侵权责任法》第23条第2句作为请求权规范基础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3条规定:“因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权益被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被侵权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该条规定是见义勇为行为中救助者所受损害的请求权规范基础,也对应着受益人的适当补偿义务。对受益人适当补偿义务的构成要件应该特别明确。
首先,通过对《侵权责任法》第23条第1句和第2句的文义解释可知,受益人对救助者所受损害承担补充的(subsidiary way)适当补偿义务,该义务只发生在“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被侵权人请求补偿”时。当出现“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的情形时,救助者对其所受损害陷入风险自担之境地,此时要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符合民法公平原则。因此,第23条第1句可以成为救助者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时,受益人所得主张的请求权反对性规范(抗辩性规范),〔5〕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请求权基础》,陈卫佐等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当然受益人对救助者应当先行向侵权人主张责任的抗辩事由须承担证明责任。
其次,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的法定义务并不取决于被管理人是否实际获益或者管理事务最终是否成功,〔6〕类似观点参见Christian von Bar﹠Eric Cliveeds,Principles,Definitions and Model Rules of European Private Law,Oxford,University press,2010,p.3034。从对该条文义解释的角度看,其并未像《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5条那样规定受益人“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由此,受益人实际受益范围并非其承担适当补偿义务的法定裁量情节,救助者的受损情况、救助者和被救者的经济状况等因素皆须全面考量,以期在适当补偿范围上进行更加公正的利益衡量,以避免在受益人所获利益较少、其经济能力较强而救助者遭受损害较大时补偿上的显失公平。
再次,受益人适当补偿义务也不取决于受益人是否存在过错,若受益人适当补偿义务以其存在过错为构成要件,则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侵权责任法》第23条就成为多余,因为此时只需要适用该法第6条第1款过错责任的一般条款即可解决。可见,受益人的适当补偿义务不同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但其在义务的严格性上又与其相似。
最后,受益人适当补偿义务可救济的损害范围限于在见义勇为行为中救助者所直接遭受的人身或者财产损害,救助者因时间付出所遭受的纯粹经济损失则不在此救济范围,救助者从事见义勇为行为过程中支付的必要费用或者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负担的必要债务等也都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第23条第2句所支持的救济范围。可见,受益人法定补偿义务对应的请求权规范基础并不解决见义勇为行为作为无因管理的全部法律后果,其无法完全取代传统无因管理之债的内容。救助者所遭受的无法通过受益人法定补偿义务予以救济的不利益仍可通过无因管理制度予以解决。受益人在承担适当补偿义务后,可以就此补偿取得向侵权人追偿的权利,〔7〕在《侵权责任法》立法过程中,“有的地方和单位建议,规定受益人承担补偿义务后,可以向侵权人追偿”。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侵权责任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3、295页。以实现救助者、受益人和侵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二)《侵权责任法》第23条第2句与其他相关规定之间的体系协调
《侵权责任法》第23条还存在与我国现行其他相关民事法律、司法解释之间的体系协调问题,需要通过法律解释对这些法律规范进行体系整理。
第一,《侵权责任法》第23条在适用范围上存在法律漏洞,其未区分存在侵权人的侵害制止型见义勇为和不存在侵权人的抢险救灾型见义勇为,更没有分别讨论其救济机制。特别是从对该法第23条第2句前段所规定的“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的文义解释的角度可见,其未能涵盖抢险救灾型见义勇为。〔8〕此种解释结论与立法部门组织编写的相关释义著作中的历史解释结论(本条不包括自然灾害引起的他人民事权益被侵害的情形)吻合。参见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主张扩张解释该条所规定的“制止侵害行为”并不能单纯从字面来理解,这种行为,不仅针对侵权行为,还针对危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自然灾害、意外事件和其他危险状况。〔9〕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页。而《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5条在适用范围问题上作了广义界定,包括“没有侵权人、不能确定侵权人或者侵权人没有赔偿能力”〔10〕《民法通则意见》(试行)第142条前段做了类似规定:“……在侵害人无力赔偿或者没有侵害人的情况下……”的情形,这就将不存在侵权人的抢险救灾型见义勇为中救助者的损害救济一并纳入,符合类似情况类似处理的法治统一和平等原则。《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5条在适用范围上的缺陷则是其对救助者损害的规定只及于“人身损害”,而《侵权责任法》第23条第1句则未对救助者损害的具体类型做限缩,因而更为妥当。
第二,《侵权责任法》第23条所规定的法律后果(受益人适当补偿)在利益衡量上更符合公平性。作为紧急无因管理的两种类型,侵害制止型和抢险救灾型见义勇为行为中救助者向被救助者主张的损害偿付责任的请求权基础都是无因管理中的必要费用偿还请求权,对此,《民法通则意见》(试行)第132条对《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的“必要费用”做了文义上的扩张解释,包括了管理人(救助者)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11〕从解释论的角度看,《侵权责任法》第23条第2句所规定的受益人适当补偿义务,较之《民法通则》第93条和《民法通则意见》(试行)第132条而言,的确不利于对见义勇为救助者利益的全面保护。参见高圣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立法争点、立法例及经典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9、300页。但如下文所述,笔者认为,此种狭义法律解释的结论反倒更符合见义勇为行为中多方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而根据《民法通则》第109条、《民法通则意见》(试行)第142条乃至《侵权责任法》第23条第2句的规定,同样情形下,见义勇为行为的救助者只能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12〕“朱木杨因其子制止他人财产遭受侵害被刺身亡致家庭生活困难诉受益人吴春秀等补偿案”,载《人民法院案例选》1996年第3辑,第90-95页。笔者认为依赖无因管理制度将救助者所受损害交由受益人(被救助者)进行全部补偿,〔13〕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76条即采此种做法:“管理事务,利于本人,并不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者,管理人为本人指出必要或有益之费用,或负担债务,或受损害时,得请求本人偿还其费用及自支出时起之利息,或清偿其所负担之债务,或赔偿其损害”;“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项规定之情形,管理人管理事务,虽违反本人之意思,仍有前项之请求权。”没有顾及损害引发者是侵权人,受益人无过错情形下要求其对救助者损害进行全部的补偿,也与侵权过错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不相吻合,在利益衡量上有缺失,在问题的终局解决上有局限。单就侵害制止型见义勇为来看,有学者主张救助者对侵害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和救助者对被救助者的无因管理必要费用偿还请求权存在规范竞合(independent concurrent right),应该择一行使。〔14〕See Christian von Bar﹠ Eric Cliveeds,Principles,Definitions and Model Rules of European Private Law,Oxford,U-niversity press,2010,p.3052.笔者认为,存在侵害人的情况下,救助者所受损害由侵害人引起,虽为被救助人的利益而行为,但这两者不属于并列的原因,不能由救助者任意选择求偿对象,宜先由引发损害的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承担的只能是如上文所述“补充的适当补偿义务”。
第三,受益人不能直接主张《侵权责任法》第28条所规定的“第三人侵权”作为免除自己适当补偿义务的抗辩事由,该条不属于受益人对抗救助者的反对性规范。《侵权责任法》第28条规定:“损害是因第三人造成的,第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条也存在法律漏洞,即使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是遭受救助者受损害的唯一原因,也不能当然免除被救助者(受益人)的法定补偿义务,《侵权责任法》第23条第2句构成第28条的例外情形。
总之,见义勇为行为救助者所受损害的请求权基础经历了从无因管理被救助者全面补偿到根据侵权责任法侵权人损害赔偿责任之外由被救助者进行适当补偿的规范变迁,被救助者所承担的是补充的适当补偿义务,利益衡量上兼顾救助者、被救助者和侵权人三方。
三、见义勇为行为中受益人补偿义务对传统无因管理制度的发展
(一)受益人补偿义务的体系定位
就《侵权责任法》第23条所规定的受益人法定补偿义务,在民法学理论上存在体系定性(立法根据)上的争议,相关争议主要体现如下。
第一,公平责任说。该说主张受益人之所以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是公平责任原则的要求。其更远的立法根据为我国《民法通则意见》(试行)第157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见义勇为行为中,救助者是为了受益人的利益进行活动并遭受了损害,受益人和救助者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受益人应当依公平原则予以适当补偿。〔15〕参见黄松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14-227页。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0页。
第二,特殊的无因管理之债说。有学者主张无论何种见义勇为行为,都可以归类于无因管理行为,前者属于后者的特殊情形,侵权责任法关于受益人补偿义务与民法通则中无因管理之债的规定发生竞合时,应该依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优先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16〕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6页。
第三,特定条件下的损失分担说。有学者主张受益人补偿义务并非公平责任或者无因管理,而是特定条件下的损失分担制度。〔17〕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7-289页。
第四,民法中独立类型之债说。有学者主张法定补偿义务作为民法上独立类型之债,与合同之债、侵权之债、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等并身而立。〔18〕参见王轶:《作为债之独立类型的法定补偿义务》,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2期。也有学者分析与《侵权责任法》第23条第2句类似的《民法通则》第109条和《民法通则意见》(试行)第142条,认为后者继受了苏联民法的规定,属于作为债的独立发生原因的抢救社会主义财产的立法模式。〔19〕参见徐同远:《见义勇为受益人与行为之间法律关系的调整》,载《法治研究》2012年第12期。这样一来,《民法通则》第93条和第109条就成为立法多元继受的产物。笔者认为,经由历史分析方法得出的该结论最后却落实到规定于《民法通则》第六章“民事责任”第一节“一般规定”之下的第109条,而非第五章“民事权利”第二节“债权”具体种类的规定之下,可见,此种立法继受结论的准确性尚值进一步论证。
笔者认为,上述争议仅属于对同一法律规范在民法学理论体系上究竟用哪个民法术语进行概括的体系化问题,“是纯粹民法学问题中的解释选择问题”,〔20〕参见王轶:《作为债之独立类型的法定补偿义务》,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2期。而非法律适用中的解释论争议。鉴于如前所述通说理论主张见义勇为行为属于紧急无因管理,见义勇为行为中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的义务也适宜被相应概括为特殊的无因管理之债。传统无因管理之债之所以不足以解释见义勇为中受益人的适当补偿义务,是因为前者主要调整管理人和被管理人之间的内部利益冲突,对侵权人和无因管理当事人之间的外部利益冲突这一属于传统侵权损害赔偿之债的问题未本着法律实用主义的目的一并解决。本着对救助者损害予以最大可能救济的实用主义目的,见义勇为行为中多方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和重新协调无因管理和侵权行为制度的契机。面对见义勇为,无因管理制度应该相应微调完善。
(二)见义勇为对传统无因管理制度的发展
传统无因管理制度不足以充分解决见义勇为行为中的相关民法问题,相反,见义勇为行为推动了传统无因管理制度产生一系列新发展。
第一,传统无因管理制度在适用范围的类型化上存在不足,并不区分紧急无因管理和一般的无因管理;〔21〕See Christian von Bar﹠ Eric Cliveeds,Principles,Definitions and Model Rules of European Private Law,Oxford,U-niversity press,2010,p.3034.对紧急无因管理也未根据引发紧急情势原因之不同,区分抢险救灾型紧急无因管理与侵害制止型紧急无因管理。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主要根据管理事务的标的,将其分为管理他人事务的行为和为他人提供服务的行为。笔者认为,结合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上的相关规定,根据管理事务或者提供服务所处情势的轻重缓急,可以将无因管理分为普通情况下的帮工行为和紧急管理情况下的见义勇为行为。我国未来民法典中,应该在无因管理一章一并设定解决帮工行为和见义勇为行为中利益冲突的法律规则,回归帮工行为和见义勇为行为作为无因管理的本来面目,〔22〕参见王雷:《民法学视野中的情谊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页。赋予无因管理制度新的生机。
第二,传统无因管理制度对管理人所遭受不利益的救济范围存在缺陷,管理人仅得就所支出的必要费用(expenditure)而非所遭受的损害(damage),向被管理人求偿,这从对《德国民法典》第683条的文义解释中可以得知,〔23〕《日本民法典》第702条存在类似缺陷,该条也只规定了管理人的费用偿还请求权,该法第701条准用性法条也未准用第650条第(3)项“受任人为处理委任事务,自己无过失而受损害时,可以请求委任人赔偿其损害。”而后期的判例法则逐渐对管理人所遭受的损害和支出的必要费用采取相同的处理态度。这也在欧洲各国民事法律中获得广泛的立法例支撑。〔24〕See Christian von Bar﹠ Eric Cliveeds,Principles,Definitions and Model Rules of European Private Law,Oxford,University press,2010,p.3056.Dieter Medicus,Bürgerliches Recht,21.Auflage.Carl Heymanns Verlag 2007,S.250;[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08页。
第三,在传统无因管理制度中,管理人最重要的权利就是管理费用偿还请求权(the right to claim reimbursement of expenditure)和管理人所负担必要债务的求偿权(the right to claim indemnification of liabilities),这两项权利在欧洲大陆法律体系下都被认可,也都对应就管理人在管理活动中自愿承受的不利益之救济。“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DCFR)对无因管理制度中管理人的请求权作了扩充,草案V.-3:103条规定了管理人对被管理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right to reparation),并将之定位为“必不可少条款”(indispensable)。〔25〕See Christian von Bar﹠ Eric Cliveeds,Principles,Definitions and Model Rules of European Private Law,Oxford,U-niversity press,2010,p.3033.3052.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76条似乎早已规定管理人对被管理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管理事务利于本人,并不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者,管理人为本人指出必要或有益之费用,或负担债务,或受损害时,得请求本人偿还其费用及自支出时起之利息,或清偿其所负担之债务,或赔偿其损害”;“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项规定之情形,管理人管理事务,虽违反本人之意思,仍有前项之请求权。”但“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DCFR)所规定的管理人损害赔偿请求权并非“全有全无式”的,草案V.-3:104条进一步规定了对管理人损害赔偿等请求权的减免情形(reduction or exclusion of intervener’s right),该条第2款基于公平合理原则,对管理人请求权对应的被管理人责任予以减免,〔26〕Draft Common Frame of Reference(DCFR)V.-3:104(2):“These rights are also reduced or excluded in so far as this is fair and reasonable,having regard among other things to whether the intervener acted to protect the principal in a situation of joint danger,whether the liability of the principal would be excessive and whether the intervener could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obtain appropriate redress from another.”在利益冲突规则的设计上更加动态衡平。这也是《民法通则意见》(试行)第132条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76条之“全有全无式”(all or nothing)规定所不及之处。“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V.-3:104条规定在利益衡量时,通常应当考虑多个因素,其中每个因素的强度和数量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展现了动态系统论的思考方式在利益衡量中的适用。〔27〕参见[奥]海尔穆特·库奇奥:《损害赔偿法的重新构建:欧洲经验与欧洲趋势》,朱岩译,载《法学家》2009年第3期。此种做法有助于更加动态地构成法律规范及其法律效果,避免僵硬地运用法律,其基本构想是“特定在一定的法律领域中发挥作用的诸‘要素’,通过‘与要素的数量和强度相对应的协动作用’来说明、正当化法律规范或者法律效果”。〔28〕[日]山本敬三:《民法中的动态系统论——有关法律评价及方法的绪论性考察》,解亘译,载《民商法论丛》第23卷,第177、181页。根据该理论,在利益衡量过程中决定某一利益是否优先保护时存在诸多的影响要素,某一要素缺失并不当然危及对该利益的保护,完全可以通过其他要素的补强来替代。
作为特殊的无因管理之债,《侵权责任法》第23条所规定的见义勇为行为中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义务仅涉及相对于侵权人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补充地位,对救助者是否存在与有过失、受益人补偿是否会导致其负担过重等问题未明确列举为裁判公平权衡的因素。奥地利判例法和民法理论通说也都主张对紧急无因管理中被管理人向管理人承担适当补偿责任(appropriate compensation),但对达到何种程度方为适当则取决于个案中的具体情形,例如被管理人所面临危险、管理人遭受的风险、管理人所受损害的类型和程度、管理人对形成危险的原因力及经济能力、是否存在保险保障等。〔29〕See Christian von Bar﹠ Eric Cliveeds,Principles,Definitions and Model Rules of European Private Law,Oxford,U-niversity press,2010,p.3068.对受益人“适当补偿”义务之动态权衡因素的揭示是未来对《侵权责任法》第23条进行司法解释的方向,通过给法官更多的裁判指引并相应地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避免法官在个案裁判中过多关注法外因素。
四、从受益人补偿义务看社会救助与侵权责任法的衔接
(一)侵权损害多元化救济机制的建立
在多元化的侵权责任方式中,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是最主要和适用最广泛的一种,是对侵权行为所致损害后果的救济。而当民法不足以救济受害人所遭受损害时,就应该考虑社会法的弥补。社会救助是国家和社会为依靠自身能力难以满足其基本生存需求的公民给予的物质帮助和服务,以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为基本内容,并根据实际情况实施专项救助、自然灾害救助、临时救助以及国家确定的其他救助。司法实践中在大规模侵权领域还存在政府先行垫付赔偿金的做法。〔30〕参见《贵阳公交纵火案每名遇难者家属获赔60万 由政府垫付》,来源http://news.szhk.com/2014/03/04/282868674908180.html,2014年3月5日访问。
《侵权责任法》通过以前,民法学界和社会法学界也对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与社会法相关制度的协调配合进行了较多研究。但相关研究更多集中于社会法中的社会保险法与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协调,对社会救助法与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探讨较少。有学者指出,侵权责任法从过错责任到无过错责任的发展推动了责任保险的广泛适用和工伤保险的日臻完善,应当协调社会保险法与侵权责任法的关系。〔31〕参见林嘉:《社会保险对侵权救济的影响及其发展》,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有学者认为,对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与普通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应该采取替代模式和改良的选择模式,但关键是提高工伤保险给付水平,使其与普通人身损害赔偿水平相当。〔32〕参见张新宝:《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与普通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关系》,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有学者认为在现代风险社会,在事故损害赔偿领域,很多国家或地区逐渐形成了以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和社会救助为内容的多元、系统的受害人救济模式,主张我国也应顺应此种重要发展趋势,并依据法制的发展现状,以侵权责任法为基础,建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和社会救助并行发展的多元化受害人救济机制。〔33〕参见王利明:《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受害人救济机制》,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4期。
上述研究都是从立法论的角度出发,关注重点是责任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与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受害人救济机制》一文也讨论了社会救助与侵权损害赔偿的立法论架构,作者努力明确两种制度各自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以期既发挥侵权责任的基础性作用,又充分发挥社会救助的辅助性功能。
《侵权责任法》通过之后,有学者指出要建立以侵权法、责任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为主体的多元化救济体系,但文章更多地仍在讨论社会保险法的相关制度,对社会救助制度涉及较少。〔34〕参见张俊岩:《风险社会与侵权损害救济途径多元化》,载《法学家》2011年第2期。还有学者在著述中力主设立大规模侵权赔偿基金,而不应该过度依赖政府主导型的权利救济模式。〔35〕参见张新宝:《建立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赔偿)基金的制度构想》,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6期。可见,《侵权责任法》通过并施行之后,学者对多元化救济机制的研究更多集中于责任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和大规模侵权赔偿基金之上,对《侵权责任法》中已经体现出的社会救助思维从解释论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比较欠缺。实际上,不仅在大规模侵权或事故侵权领域存在社会救助制度的运作空间,在普通侵权领域也有其广泛运作空间。我们有必要分析梳理学者相关建议在我国《侵权责任法》上的实现程度,并在侵权责任法救济功能的基础上结合社会救助思维,对相关制度作出理论体系构建和法律解释适用。
国外对侵权受害人多元化救济机制的研究比较全面。其不仅在责任保险与侵权损害赔偿之间的衔接问题上论著颇多,而且在我国学者关注较少的社会救助与侵权损害赔偿之间的制度协调问题上也有很多有力论述。如德国学者乌尔里希·马格努斯主编的《社会保障法对侵权法的影响》对社会保障法与私法之侵权法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讨,来自十一个欧洲国家的专家对其本国实施的社会保障制度概况进行了介绍,并指出了社会保障与侵权法赔偿在人身伤害领域的重要差异,内容丰富的比较报告强调了社会保障法与侵权法之间的广泛互动。〔36〕参见[德]乌尔里希·马格努斯主编:《社会保障法对侵权法的影响》,李威娜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
(二)见义勇为行为中社会救助与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在类似于救助溺水者这类无加害人的见义勇为补偿案件中,如果救助者在救助过程中伤亡,能否要求被救助者(受益人)进行赔偿或者补偿?若救助者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救助义务,法院在此类案件中一般都会认定救助者救助溺水者的行为属于无因管理,而在具体法律后果上,则基于公平责任原则,要求被救助者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而非全部赔偿。司法实践中相关请求权规范基础如前所述,主要为《民法通则》第109条和《民法通则意见》(试行)第142条,以及《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5条或《侵权责任法》第23条第2句。“在无加害人的见义勇为补偿案件中,受益人承担的是补偿责任,而非赔偿责任。这是因为,在此类案件中,受益人并非侵权人,从侵权损害的角度看,因见义勇为遭受损害的受害人,与受益人应当是利益共同体,他们共同面对危险。因而,受益人对见义勇为者承担的不应是赔偿责任……对受害人的救助,从长远看应当是社会责任,但在缺乏相应机制的条件下,作为利益共同体的受益人,应适当分担损害,给受害人以补偿”。〔37〕参见“郑花阁诉张鹏等见义勇为补偿案”,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2003)淅法民初字第316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南民一终字第75号民事判决书,载国家法官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5年民事审判案例卷》,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9页。
对救助者所受损害,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3条第2句经由受益人的适当补偿之后仍无法弥补部分如何解决?《侵权责任法》第23条对此保持了沉默,该问题也属于该条的未尽之言。“许多人由于不可避免的偶然事故而无法依靠劳动维持生活,我们不应当任其由私人慈善事业救济,而应当根据自然需要的要求,由国家法律规定供养”。〔38〕[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70页。从比较法上看,“欧盟很多成员国都成立了公共保险机构(public insurance body),以弥补救助者为他人提供救助过程中所遭受的损害。这种对紧急情况下救助者的保险由国家的公共财政负担,……立法者此时也相当于在公权力机关未尽到救助义务时,对其科加相应责任”。〔39〕See Christian von Bar﹠ Eric Cliveeds,Principles,Definitions and Model Rules of European Private Law,Oxford,U-niversity press,2010,p.3063.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行为的行政协助性质决定了行政机关应该使用公共财政进行行政补偿。见义勇为行为的救助者在紧急救助中代行了危难情形下公权力机关的救助义务,见义勇为行为中的受益人不仅仅包括权益获得维护的被救助者,还包括负担救助义务的公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的这些行政补偿责任可以通过在各级政府财政中专设“见义勇为基金”的做法进行专款专用并常规化。〔40〕参见陈林林、姚春芳:《无因管理中的损害赔偿问题探讨——兼及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救助”》,载《浙江学刊》2004年第5期。对地方性法规的相关做法,请参见《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第7条、第12条、第13条和第14条。“见义勇为基金”可以通过公共财政资金和社会捐助资金等多元化资金支持,实现行政补偿和社会救助的合一。
社会救助是在侵权受害人多元化救济机制中居于补充地位的重要制度,是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获得物质帮助权的具体化。社会救助制度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救助义务,应当予以法定化。我国现行《侵权责任法》在应当通过社会救助制度对受害人补充救济之处并未加以规定,如第23、87条等,造成了社会救助制度在《侵权责任法》上“接口”不足,堵塞了公法进入私法的有效渠道。以《侵权责任法》第23、24、87条为代表的侵权损失公平分担机制通过内化民事主体之间的损失分担起到了代行社会救助制度的功能。未来,随着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我国《侵权责任法》修订及其司法解释制定中应该参考该法第53条的规定为社会救助预留必要的“接口”,使公法救助顺畅进入私法领域。
当然,在公法救助进入私法领域之后,还会遇到追偿权的问题,当公法上社会救助制度比较发达完善的情况下,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3条就可以调整为:“因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权益被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被侵权人请求救济相关损害的,见义勇为基金应当给予垫付。见义勇为基金垫付后,其管理机构有权向侵权人追偿。”那时,见义勇为基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救助者对其在见义勇为行为中遭受的非自愿损害不再需要公共财政负适当补偿,〔41〕See Christian von Bar﹠ Eric Cliveeds,Principles,Definitions and Model Rules of European Private Law,Oxford,U-niversity press,2010,p.3063.而是交由全社会分摊,而无因管理制度又可以回归到对管理人在管理活动中自愿承受的不利益之救济,或许这也是无因管理制度伴随社会发展必然需要经历的一起一落。
五、结语:利益动态衡量与见义勇为行为中救助者损害救济
传统无因管理制度主要涉及管理人和被管理人之间的内部利益冲突,一旦构成无因管理,对管理人所遭受的不利益,立法者采取全有全无式的调整策略。在对见义勇为行为中救助者和被救助者冲突利益进行衡量时,全有全无式的概念法学机械适用论的思维方法过于僵化,或多或少式(more or less)的动态系统论方法更合乎民法公平原则,有助于解决利益冲突情形下法律安定性和妥当性上的矛盾,属于法律发展的重要价值导向思考方法。〔42〕Karl Larenz,Grundformen wertorierten Denkens in der Jurisprudenz,Festschrift für Walter Wilburg zum 70.Geburtstag,1975,S.226ff.另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51、352页。作为紧急无因管理行为,见义勇为要求传统无因管理之债中发展出被管理人(被救助者)的适当补偿义务来适当弥补侵权人对救助者损害赔偿之不足,这就涉及无因管理当事人和侵权人之间的外部利益冲突。在紧急无因管理中,不能将侵权人对管理人负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这一外部关系内化为管理人得向被管理人主张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这属于被管理人“不可承受之重”,也不符合紧急无因管理行为的“多重主观归属性”特点。
见义勇为行为给传统无因管理制度提供了发展完善的契机,无因管理制度这只旧瓶有能力装下见义勇为这杯新酒。“如无必要,勿增实体”,民法学理论体系应该追求简单性原则,没有必要一面对见义勇为行为中的复杂利益关系就大费心思、另起炉灶,为其寻找新的体系化位置,毕竟受益人的“适当补偿”义务随着社会救助制度的发达可能又会逐渐消退,而当“适当补偿”义务复归沉寂,民法学又如何面对先前为之创生的那个体系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