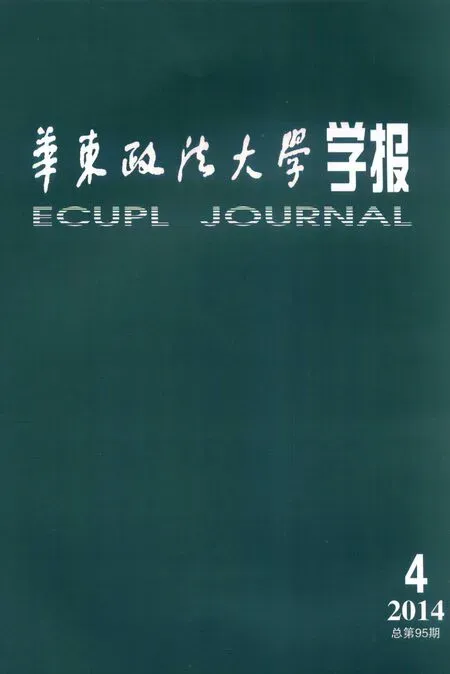我国冲突法中的法律规避制度:流变、适用及趋向
许庆坤
在我国冲突法历史上,法律规避制度于1988年首次为最高人民法院一手创制,并一度在涉外合同司法实践中频繁适用。〔1〕笔者在“北大法宝”和“北大法意”数据库中检索发现,自从1988年法律规避制度问世至今,共有21个适用该制度的法院判决。其中2002年至2007年的判决19个,占总数的90%多。例如“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诉广东省友和集团公司担保合同纠纷案”((2006)穗中法民四初字第309号)、“大新银行有限公司诉上海联博智能图文技术有限公司等融资租赁、担保合同纠纷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沪一中民三(商)初字第135号)等。虽然2010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该制度未置一词,但是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1条却使其再度复活,内容别具一格。面对若“不死之虫”的法律规避制度,有诸多谜题待解:如何理解其要素内涵及其学术薪火传递路径,法院在涉外司法实践中应如何正确运用,未来立法又应如何理性对待。
在冲突法上,法律规避是指当事人借助冲突法规则中可变连结因素,故意避开本应适用之强行法而使利己法律得以适用之行为。〔2〕参见陈卫佐:《比较国际私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立法、规则和原理的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51页。法律规避又称“法律诈欺”、“选法诈欺”、“窃法舞弊”和“回避法律”等。〔3〕参见刘铁铮、陈荣传:《国际私法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524页。对法律规避行为的效力予以全部或部分否认之规定,构成法律规避制度。其与公共秩序保留和“直接适用的法”制度同样具有排除外国法适用的功效。
作为一种法律现象,基于趋利避害之人性的法律规避在内国法领域也普遍存在,各国法律史表明,“破坏法律的方法和技巧是无穷无尽的”。〔4〕参见[德]马丁·沃尔夫:《国际私法(第二版)》,李浩培、汤宗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为维护法律尊严,禁止法律规避的国内法规定早已有之,而将法律规避制度移植到冲突法,各国学者普遍认为源自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的“鲍富莱蒙案”(Bauffremont affair)。少数国家追随法国风习,进而将该制度成文化。〔5〕See K.Siehr,General Problems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Modern Codifications,7 Yearbook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57(2005).法律规避行为合乎法律形式,而不合法律目的,因此规避意图成为惩戒之源。由于国际民商事交往中经验法则提炼的难度极高,界定规避意图若非不可逾越亦是关隘重重,因此冲突法中的法律规避制度即便在其诞生地也是争议纷扰,〔6〕参见[法]亨利·巴迪福、保罗·拉加德:《国际私法总论》,陈洪武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512-515页。不仅面临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主观意图与客观归责的矛盾拷问,而且关涉其与公共秩序保留和“直接适用的法”制度关系的厘定。
法律规避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经留法学者之手蹒跚步入中国,但在立法上长期付诸阙如。民国数位学者筚路蓝缕、拓荒垦殖,诸多成果可圈可点。但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对外政策学派之学说席卷中国,对20世纪80年代重新起步的研究影响颇深,而民国时期的成果几近束之高阁。在立法上,1986年《民法通则》对其未置一词,而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对该法的司法解释却使其横空出世,在中国冲突法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这一基本制度。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而将其用于合同冲突法。2010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下文简称《适用法》)再次将其搁置,而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法的司法解释(一)中再次肯定这一制度,并做出重大革新。
下文将首先分析该制度的内在机理及历史流变,然后探讨法院应如何厘定法律规避意图以及该制度的外在关系,最后结合世界立法潮流论证我国未来立法对该制度的合理取舍。
一、法律规避制度的机理流变
2012年12月28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下文简称《解释(一)》)第11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制造涉外民事关系的连结点,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认定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2013年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称,该制度旨在“为法官在处理涉外民事案件过程中维护我国的社会公共秩序增加一道屏障”。〔7〕张先明:《正确审理涉外民事案件、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负责人答记者问》,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1月7日第6版。遗憾的是,后文未对法律规避制度作进一步的阐释。
由是观之,法律规避制度的构成涵盖六个方面:(1)法律规避的主体为一方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8月在该司法解释第三草稿(下文简称《第三稿》)“说明”部分明确指出:“法律规避一般是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才能构成,双方当事人的共同故意不构成规避。”(2)法律规避的主观要素为故意。(3)法律规避的方式为制造连结点。(4)法律规避的对象为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律中的规定。(5)法律规避的后果为法院不适用外国法。(6)法律规避制度的目的是维护我国的社会公共秩序。
《第三稿》第7条曾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规避我国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的,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两相比对,《解释(一)》的变化有:(1)将“我国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2)在“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之前增加了“人民法院应认定为”;(3)增加了“制造涉外民事关系的连结点”而且将“故意”一词置前。
由于强行法既包括禁止性规范也包括命令性规范,二者均可能成为规避的对象,因此第一项修改将“禁止性规定”改为“强制性规定”合乎法理与实际;但是,在“强制性规定”之前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的”予以限定,不合理地压缩了强行法的范围,因为在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中也存在关乎涉外民事行为的强行法。〔8〕比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03年运用法律规避制度时适用了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参见该院对“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与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保证合同纠纷案”的判决((2003)苏民三终字第023号)。在第二项修改中,只强调“人民法院”而忽略了“仲裁机构”和“行政机关”,与《适用法》第10条规定的冲突法适用机构不相一致,倒不如不予规定。第三项修改将“故意”置于“制造”之前容易导致错觉,其实“故意”应是法律规避行为而非制造连结点的主观要素;“制造涉外民事关系的连结点”是错误表述,因为对于作为冲突法规则构成要素的“连结点”,当事人无从制造,当事人能制造或改变的是连结点所对应“事实”。例如,当事人为规避原应适用的中国法,将中国国籍改为日本国籍,此处作为冲突法规则必要成分之连结点的“国籍”未被改变,但作为事实的“当事人的国籍”已前后不同。在中国国际私法学术史上,“制造连结点”之类舛误首先见于新中国第一部统编教材,〔9〕参见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9页。后为众多学者盲目效仿、绵延至今。〔10〕比如赵相林主编:《国际私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页。该书认为法律规避的行为表现是“有意改变或制造某种连结点”。在笔者手头十二部民国时期国际私法著作中均未见此类表述。〔11〕例如于能模教授的界定:“有人因本国法律,不利于其所企图,乃设法投身于他国法律之下,专以遂此企图为目的,此之谓窃法舞弊。”于能模:《国际私法大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08页。但是,此类舛误早在上世纪就已被学者觉察和矫正,〔12〕参见孟宪伟:《法律规避的两个问题》,载《法学杂志》1999年第5期,第5页。孟教授正确地指出:“当事人所改变的只是冲突规范连结点所指引的具体事实,而不是冲突规范连结点的本身。”依然存在于最新司法解释中乃决策者失之明察,令人扼腕。
最早确立法律规避制度的是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4条:“当事人规避我国强制性或者禁止性法律规范的行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将其用于合同冲突法,规定:“当事人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该合同争议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抛开细节相比对,《解释(一)》中规定的特色在于将法律规避的主体限定在一方当事人。值得深究的是,此种特色的范例和法理依据何在?
通过考察《适用法》的多部建议稿和立法草案,笔者发现我国过去从未有此类规定。〔13〕参见黄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建议稿及说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在笔者收集到的120部国外冲突法立法中文本中,采用一般性法律规避制度的共17部,同样无一如此表述。《解释(一)》中的法律规避制度可谓绝无仅有。究之于法理,法律规避制度主要意在维护强行法权威,〔14〕参见曾陈明汝:《国际私法原理(上集):总论篇》,曾宛如发行,2008年第8版,第303页。无论因双方当事人合谋抑或因一方当事人故意,惟规避行为触犯了法律权威,自应在规制范围。国际私法权威学者李浩培教授在论及法律规避时所举四例中有三例均为双方当事人合意而为。〔15〕参见李浩培:《李浩培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7、68页。民国时期的著作、建国初期的前苏联著作以及晚近汗牛充栋的冲突法精品力作,无一持此观点。《解释(一)》这一规定的起草者可谓“匠心独具”,“傲视”冲突法学术之林。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法律规避制度兼及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公平,这一规定意在于此而非顾及维护法律权威。但此解释不仅有悖于该制度的本质,而且与最高人民法院将其作为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另一屏障的意图相悖。
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负责人答记者问时的明确表态无意间使国际私法史上的一桩“公案”尘埃落定,即法律规避制度实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特殊形态。对于法律规避制度的性质,民国时期的学者曾各执一词。留学法国七年并获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于能模教授沿袭部分法国学者的观点,在1931年始将法律规避制度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相提并论。〔16〕参见于能模:《国际私法大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01-216页。在巴黎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的阮毅成教授于1933年明确指出,适用两种制度的原因“大异”。〔17〕参见阮毅成编著:《国际私法》,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201、202页。但是,同时期的卢俊教授却认为,“盖某行为是否诈欺,必以一国之公安(即公共秩序——笔者注)观念为标准”。〔18〕卢俊:《国际私法之理论与实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该书系重印,原版为1937年中华书局出版。随后李浩培教授明确指出:“当事人的规避法律,如有悖于我国的公序良俗,我国法院应不适用当事人希图适用的法律,而仍适用原应适用的强行法规;反之,如不背我国的公序良俗,则适用当事人所希图适用的法律。”〔19〕李浩培:《国际私法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45年版,第65页。建国初期引进的前苏联著作持法律规避制度“独立论”,〔20〕参见[前苏联]隆茨:《国际私法》,顾世荣译,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30页。并影响到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部国际私法教材。〔21〕参见姚壮、任继圣:《国际私法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37页。其后国际私法权威教材对此详加论证,但此论证彰显了“独立论”者所犯的致命错误,即将法律规避行为而非法律规避制度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两相比较,“进行法律规避是一种私人行为,而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则是一种国家机关的行为”,因而得出“行为的性质不同”的荒谬结论。〔22〕参见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页。此次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负责人的答记者问拨云见日,恢复了民国时期“依附论”的面目,符合《适用法》立法者的意图。〔23〕负责《适用法》起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王胜明副主任正确地认识到法律规避制度并无多大意义以及其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之间的关系,主张“对现实中的规避行为,可管可不管的,一般不管;对个别情节恶劣、影响较大的……可以通过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予以处理。”参见王胜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争议问题》,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2期。其实,在该制度起源地法国,诸多杰出的学者亦正确地主张“依附论”,视其为“公共秩序的一种特殊情况”。〔24〕参见[法]亨利·巴迪福、保罗·拉加德:《国际私法总论》,陈洪武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515页。比利时学者罗兰(Laurent)同样指出,当事人规避本国法行为之所以无效,是因为其违反公共秩序保留制度。〔25〕Batiffol,Traité élémentair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3è éd.1959,p430.转引自曾陈明汝:《国际私法原理(上集):总论篇》,曾宛如发行,2008年第8版,第304页。
二、法律规避制度的司法运用
法律规避制度的内在元素复杂多样,尤其是规避意图的认定难度若非不可逾越亦是关隘重重;外在关系错综复杂,其与公共秩序保留和“直接适用的法”制度的适用次序需谨慎厘定。
无规避意图则无规避行为是法官适用该制度时理应谨记之要诀。在法律规避制度的构成六要素中,法律规避的主体、方式和对象均易客观认定。法律规避的意图最难判定,但其却是构成法律规避的“最主要因素”;〔26〕参见曾陈明汝:《国际私法原理(上集):总论篇》,曾宛如发行,2008年第8版,第302页。个中缘由是当事人巧妙利用了法律漏洞,外在形式合法,惟内在规避意图构成惩戒之源。规避意图便成为该制度的“阿格琉斯之踵”,饱受学者诟病。欧洲的批评者认为,“对意图的探索是对人的内心意识的侵入”,“法律只涉及外部行为,而人的意图属于道德范畴;关于意图是不能得到可靠的结论的,这样就会使法官做出不可接受的专断结论”。〔27〕[法]亨利·巴迪福、保罗·拉加德:《国际私法总论》,陈洪武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512页。
在内国实体法领域,犯意之于犯罪、过错之于侵权亦为通常必要构成要素。为何主观要素的认定在刑法和民法领域波澜不惊,而在冲突法领域却掀起轩然大波呢?这可求解于证据学原理。对于犯意的认定,警察可凭侦讯手段获取口供和证言;对于侵权过错,当事人和法官也可借证言佐证。即便如此,犯意和侵权过错的认定还是面临主观过错认定如何客观化的难题。于是,基于经验法则的推定便成为打开症结的不二法门,立法和司法解释中的大量推定规范降低了主观因素认定的难度。〔28〕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涉及推定的司法解释基本上局限于对犯罪的主观构成要素的推定。参见劳东燕:《认真对待刑事推定》,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2期。但是对于法律规避意图,既无刑事侦讯手段,也无相应推定规范,同时涉外交往的复杂化使证据获取困难重重。尤其是我国的法律规避制度只认可一方当事人规避行为,单方规避意图的证据更难获取。
心怀规避恶意的当事人通常不会主动袒露心迹,则法官往往需在司法中推定作为事实的规避意图。事实推定适用的常见条件有:(1)存在经验法则。“经验法则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通过大量同类事实得出的事物间或然性联系的一般性结论,其或者是一般生活经验,或者是专门的专业知识。”(2)基础事实可信赖度高。(3)无相反证据。(4)遵循公正理念和高尚社会价值取向。〔29〕参见郑世保:《事实推定与证明责任——从“彭宇案”切入》,载《法律科学》2010年第3期。对于涉外审判的法官,其中两大障碍需要特别克服,一是找寻经验法则,二是排除相反证据。即便对于从事内国案件审判的法官而言,经验法则内涵的模糊性、盖然性的差异性、相对性以及内隐性、地域性和实效性等也使其难以认定。〔30〕参见羊震:《经验法则适用规则之探讨》,载《法商研究》2012年第2期。对于涉外审判的法官而言,超越其生活经验的复杂多变的涉外交往通常使其内心更难确认经验法则。同时,从事法律规避的当事人可轻易提出意图正当的诸多证据,而法官和对方当事人往往因未参与其中而对此束手无策。
规避意图极难认定提醒我国法官在适用法律规避制度时应高度谨慎。法国学者对法官谆谆教导:“法官不应该在没有决定性理由的情况下怀疑当事人的意图。”〔31〕[法]亨利·巴迪福、保罗·拉加德:《国际私法总论》,陈洪武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513页。这一警告转化为司法策略即是“宁纵勿枉”。
笔者在“北大法宝”和“北大法意”两大中文数据库中反复查证,收集到的21个适用法律规避制度案例,均为内地当事人向位于香港的金融机构提供外汇担保或向其外汇借款,当事人约定适用香港法,触犯了内地对于外汇担保或借款须经国家批准和登记的强制性规定。对此类案例如何适用法律规避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一份判决中的表述可谓经典:“我国内地对于对外担保有强制性的规定,本案担保契约如果适用香港法律,显然规避了上述强制性规定,故本案当事人关于担保契约适用香港法律的约定不发生法律效力……。”〔32〕“中银香港公司诉宏业公司等担保合同纠纷案”,(2002)民四终字第6号。此番论证涉及法律规避的主体、对象、方式和后果,惟规避意图这一关键要素付诸阙如。如此避重就轻地论证,法院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认定法律规避行为。“法律规避向来以国际私法领域最为滥用的概念之一而名声大噪”,〔33〕K.Nadelmann,The Benelux Uniform Law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18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406(1970).国外学者的论断亦近乎我国以往的司法实践。但是,乱象中亦不乏亮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曾正确理解了该制度,在2004年一份判决中指出:“法律规避的一个重要的构成要件是当事人有规避相关法律的故意……”,并据此否定了下级法院适用法律规避制度的判决。〔34〕参见“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诉铜川鑫光铝业有限公司等担保合同纠纷案”,(200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6号。其实,我国对外汇担保或贷款审批制度属于强行法,本应直接适用,而与法律规避制度无涉。《适用法》第4条“直接适用的法”制度的立法目的即在解决此类法律适用难题。〔35〕参见刘贵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审判实践中的几个问题》,载《人民司法》2011年第11期。
“直接适用的法”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与法律规避制度虽形态各异,但根脉相通,均旨在维护法院地国的根本利益。我国三种制度齐备,如何在司法中厘清其相互关系和适用次序是法官面临的现实课题。对此,我国有学者主张,“直接适用的法”制度在先,法律规避制度居间,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殿后。〔36〕参见肖永平、龙威狄:《论中国国际私法中的强制性规范》,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直接适用的法”是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国内实体法,其适用径直基于对实体法内容和目的之考量,而无需顾及冲突法的指引。〔37〕参见许庆坤:《论国际合同中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度》,载《清华法学》2008年第6期。鉴于司法效率和效果,“直接适用的法”制度相对于后两者优势明显,其最先适用应毋庸置疑。但对于公共秩序保留和法律规避制度的适用顺位,民国时期的学者主张:法律规避制度应在“无他救济方法的时候,方行应用”,其理论依据是,“万一应用不当,甚易引起国际间的误会与争论,甚而影响于两国的感情与国际的福利,便与国际私法的目的不符了”。〔38〕阮毅成:《国际私法论》,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95页。这一谨慎姿态与我国当下规定的意旨不谋而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已明确将法律规避制度视为维护公共秩序的一道屏障。据此,法官在司法中不仅需证实一方当事人的规避意图,而且需论证规避行为已经严重到触犯公序良俗,难度可想而知。因此,法官的明智之选是若能用模糊的公共秩序证成判决,便不宜动用法律规避制度;唯有不用后者不足以惩戒明目张胆以奇巧藐视法律权威者,方需谨慎指明当事人的规避意图。
三、法律规避制度的立法趋向
在该法起草中,绝大部分相关中文论著持法律规避制度“独立论”,甚至有学者主张以立法将其确立为“一项独立的、一般性的、非歧视性的制度”,其理由之一是“在立法上和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倾向于对法律规避行为加以禁止或者限制”。〔39〕参见赵生祥:《禁止法律规避制度在中国国际私法中的地位——对〈民法典草案〉第九编禁止法律规避条款的思考》,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5期。但立法者并未为之心动。此处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世界潮流的真相如何,我国未来立法是否有必要将司法解释中的规定提升为一项独立的一般性制度。
真实的世界立法潮流是法律规避制度正逐步走向消亡。固然就其数量而言,晚近确立该制度的立法呈增加之势,如突尼斯1998年《国际私法典》、阿尔及利亚2005年《民法典》以及部分独联体国家的最新立法。但个别国家的立法毕竟不能代表世界发展趋势,此类立法的发源地国其实已废弃该制度。就笔者研究范围所及,采用一般性法律规避制度的国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大陆法系之法国支系国家,另一类为原社会主义国家。前者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加蓬和阿根廷等八个国家,后者包括前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和乌克兰等八个国家。《美洲国家间关于国际私法一般规则的公约》亦是法国支系国家缔结的国际私法条约。法国支系国家采用该制度应受其起源地法国的巨大影响。但这一传统的冲突法制度晚近在法国已成为历史陈迹。由于采用该制度一方面会否定当事人行为效力,导致跨国交往中的跛足情势(如结婚在一国有效而在另一国被宣告无效),另一方面会对抗外国文书(如结婚证书)的效力,制造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因此法国最高法院2007年的执行令要求放弃对外国法官适用法律的审查,传统的法律规避制度据此失去了作用对象。〔40〕B.Audit,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5e éd.,Economica,2008.pp.205,208,209.欧美知名冲突法学者 Peter Hay教授在给笔者的来信中确认了这一事实。五个独联体国家的法律规避条款均出自俄罗斯1996年《民法典(草案)》第三卷第七篇第1231条,但该条尚未生效就胎死腹中。针对俄罗斯草案中法律规避条款,穆拉诺夫(А.И.Муранов)教授洋洋洒洒地罗列了其十大罪过,诸如背离已有的国际私法优良传统、内部自相矛盾、为陈旧过时的法律手段、忽视了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背离全球国际私法的现代发展趋势等。学者们的口诛笔伐立竿见影,俄罗斯立法者从善如流地将其从草案中彻底删除。〔41〕参见邹龙妹:《俄罗斯国际私法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知名的比较法学家拉贝尔(E.Rabel)就曾预言:法国表述宽泛的法律规避制度正渐趋消亡。〔42〕See E.Rabel,The Conflict of Laws:A Comparative Study,in Foreign Corporations:Torts:Contracts in General,University of Michigan Law School,vol.2,1960,p.402.如今这一预言正逐步变为现实。
法律规避制度的消亡符合冲突法发展的世界潮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全球化推动冲突法步入发展快车道,原来僵硬而单一的连结点逐步让位于灵活而复杂的连结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后者甚至成为一些立法的基本原则。〔43〕参见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问题专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1页。灵活而复杂的冲突法赋予法官和当事人更多的法律选择自由,当事人规避法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随之减少。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使个人摆脱对立法者和法院的简单附从而一跃成为“解决他们自己纠纷的主导者”,〔44〕See F.Vischer,General Cours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232 Recueil Des Cour 127(1993).从本质上否定了法律规避制度的存在前提。最密切联系原则赋予法官根据个案灵活选择法律的自由裁量权,当事人的意志已无从主导法律选择,规避法律也无从实现。
我国《适用法》紧随世界潮流,广泛采用了弹性冲突法规则,第5条将最密切联系原则确立为一般性补充原则;在15个条文中采用意思自治原则,〔45〕《适用法》第 3、16、17、18、24、26、37、38、41、42、44、45、47、49、50条。超过了具体法律适用规则总数的三分之一,并史无前例地将其作为基本原则列入“总则”。在最易发生法律规避的涉外婚姻、家庭和继承领域,我国主要以“经常居所地”作为连结点。“经常居所地”即中国化的“惯常居所地”,它源自学界对传统属人法僵硬连结点的反思和批判,意在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46〕See E.Scoles,P.Hay,P.Borchers,S.Symeonides,Conflict of Laws,5th ed.,St.Paul:Thomson Reuters,2010,pp.299,300.通过对经常居所的灵活解释,我国法官可轻易击溃当事人的法律规避意图。考证于我国既往司法实践,法院无一则成功适用法律规避制度的典型案例,将来涉及外汇管理法之类的案例应正确适用《适用法》第4条的“直接适用的法”制度。
因此,无论立足于世界潮流,抑或基于我国现行立法和既往实践,我国未来立法均无必要将司法解释中的规定提升为独立的一般性法律规避制度。在经济全球化和跨国交往愈益频繁的今天,人们在国际间挑选最好的合同法,根据最佳公司法成立公司,移居到税负最轻的地区生活,或者移民到对遗嘱无限制的国家,此类行为均无可厚非,这是人们在充分利用对其有利的制度。〔47〕See K.Siehr,General Problems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Modern Codifications,7 Yearbook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58(2005).当事人规避法律的前提是存在立法漏洞,此类漏洞本应由立法者自行填补而不应归罪于当事人!即便将来万一在某领域意外出现大量性质恶劣的法律规避行为,我国立法者也不妨届时制定具体领域的特别法律规避制度,恰如我国《民法(草案)》第9编第61条第2款和瑞士1987年《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45条第2款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