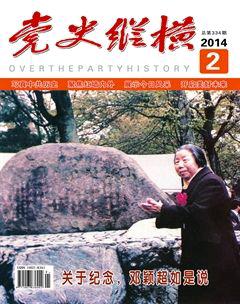抗美援朝第六次战役缘何撤消
夏明星+肖鹏+郑丽霞
1959年8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彭德怀,“会议对彭德怀揭发和批判的问题是极其广泛的,从平江起义的思想动机到庐山上书的政治目的;从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贯彻执行到1958年炮击金门时的组织指挥;从红一、三军团的关系问题到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活动等等,无一不加以追查和批判。”其中,也涉及到抗美援朝战争。有人说,彭德怀擅自制定了抗美援朝第六次战役计划,“违背了毛主席确定的打小歼灭战的方针,脱离了当时我军的实际,‘搞左倾军事冒险,并以此定为彭总‘与中央对立的罪状之一。”时至今天,彭德怀冤案虽已平反,但关于第六次战役仍然众说纷纭。笔者通过搜集大量资料,冀望还原这段历史真相。
斯大林首先提出抗美援朝的第六次战役问题
从1950年10月25日到1951年5月21日,经过抗美援朝连续五次战役的较量,中国高层领导人逐渐认识到:美英军不易对付,朝鲜战事必须从长计议。
1951年5月26日,正当中国人民志愿军结束第五次战役收兵转移之时,毛泽东总结抗美援朝连续五次战役的经验,致电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提出了对美英军打小歼灭战的方针:
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就是说,打美英军和打伪军(注:南朝鲜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每个美英师,都再有三四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一个整师,或两三个整师的计划了。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一军、新六军、五军、十八军和桂系的第七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到大歼灭的过程的。……还须经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的阶段,进到大歼灭战的阶段。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
5月27日,毛泽东将上述电示彭德怀的内容通报了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但斯大林显然对这个电报产生了误解,5月29日,他复电毛泽东指出,这个方针是“冒险的”,很易被美英军识破,“拿蒋介石军队作类比,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一旦美英军向北推进并建立一道道防线,你们突破防线就会付出巨大损失”。出于上述担心,斯大林提出建议:“看来你们将要准备一次重大的战役,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局部机动,而是为了给美英军以沉重打击。”
可以说,是斯大林首先提出抗美援朝的第六次战役问题。不过,“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并未接受斯大林的建议,而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按打小歼灭战方针对部队进行了教育和部署。”5月30日,彭德怀曾欲致信朝鲜人民军总指挥金雄(这封信经毛泽东批示没有发出),强调:
一、从历次战役来看,美英军还保持着相当高的战斗意志。我们现有条件,每次战役要求消灭其一两个师是困难的,即消灭其一两个整团亦属不易。然而,伪军的战斗意志是薄弱的,一次消灭其两三个师是可能的。把美英军的战斗意志削弱到现在伪军的低度还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准备半年至一年)。志愿军在今后三个月内,一般(特殊情况在外)对美英军不拟组织全面的大战役,以兵团为单位不断进行小战役,争取一个军每月平均消灭美军一个整营(击伤除外)。假如志愿军经常以八至九个军作战计,每月即可消灭其八至九个建制营,再加上人民军经常以两个军团计,每月消灭美军两个营,即可每月消灭美英军十至十一个营。如此,有三至六个月,美英军战斗意志必然逐渐降低,那时大规模地消灭美英军的客观条件就将成熟。同时,目前主观方面每月组织一次大战役,我之供应运输和兵员补充也来不及(今后一个战役需四万五千至六万人的补充)。目前迫切需要改善运输条件,加强新兵训练,克服各种困难,准备长期作战是必要的。
二、我之优势是正义和人力,敌之优势是装备技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是争取胜利的基本方针。由于我技术条件不如敌人,因此一次不能大量地消灭敌人,因此必须采取削弱敌人,一股一股逐渐地消灭,然后进行大规模地歼灭之。……在这样的方针下,暂时让出一些地方给敌人,缩短我后方供应线,不仅与我无害,反而有益。
彭德怀起草信稿后,立即电呈毛泽东,听取毛泽东的意见。而这时,金日成正要赴北京与毛泽东讨论战争形势和方针问题,故毛泽东指示此信暂不发。“6月2日,彭德怀将此信内容转发志愿军在第二线的各军、志愿军空军和后勤部门,要求按此布置工作。”
可以说,“今后三个月内,一般(特殊情况在外)对美英军不拟组织全面的大战役”,是彭德怀的最初考虑。不但如此,他还设想“暂时让出一些地方给敌人,缩短我后方供应线”,以诱敌深入,后发制人。
中朝双方“准备八月进行一次有把握的稳打稳扎的反攻”
巧的是,就在1951年5月30日,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致信彭德怀,专门就如何能够争取较短时期内战胜敌人的问题,提出在6月末或7月中旬对敌进行一次大的反攻行动——第六次战役的建议。在这封信中,金日成郑重指出:“朝鲜战争由于美干涉者日增其武装力量,而战争更加困难,增加残酷性和长期性是无容隐讳的事实。”“当然,在朝鲜延长军事行动,这一点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均对我不利。”因此,“我之军事行动,我意不必延长。”他最后建议,“总攻击日期可预定为6月末或7月中旬”;应充分利用雨季,在雨季开始前10日进行攻击;拟将朝鲜人民军3个机械化师编成1个独立机械化军团,配属中朝联合司令部之下使用;将必要的粮食弹药聚积于三八线一带,继续收集粮食至少保障20天的供应;以航空掩护这次反攻行动。
作为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希望中朝联军尽早反攻,早日实现国土统一,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彭德怀本意“今后三个月内,一般(特殊情况在外)对美英军不拟组织全面的大战役”,故对金日成的建议很难赞成,遂将其来信转报毛泽东。endprint
5月31日,美国国务院派乔治·凯南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明,美国愿意通过谈判沿三八线一带实现停火。苏联将这一情况向中国和朝鲜作了通报。6月3日,金日成火速来到北京,与毛泽东讨论战争形势问题,确定边打边谈的方针,“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会谈中,毛泽东对发动大的进攻行动问题与金日成进行了磋商。6月1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告知关于作战问题与金日成会谈的结果:“已和金日成同志谈好目前两个月不进行大的反攻战役,准备八月进行一次有把握的稳打稳扎的反攻。”“六七两个月内如不发生意外变化(即登陆),我们必须完成下列各事:甲、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乙、迅速补充三兵团及十九兵团至每军四万五千人,并有相当训练;丙、十三兵团各军休整完毕;丁、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有两条,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区屯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
就是说,经过毛泽东、金日成的最高级会谈,中朝双方互有妥协:中方放弃了“三个月内,一般(特殊情况在外)对美英军不拟组织全面的大战役”的主张,朝方不再坚持“总攻击日期可预定为6月末或7月中旬”,双方一致同意“准备八月进行一次有把握的稳打稳扎的反攻。”
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马修·李奇微发表声明,表示愿意通过谈判结束朝鲜战争。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复电李奇微:“我们受权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
而在6月29日,即停战谈判即将开始的情况下,毛泽东致电金日成并告彭德怀,指出在准备同敌人谈判的同时,“人民军和志愿军应当积极注意作战,不使敌人乘机获逞。”7月1日18时,在和金日成共同声明愿意进行停战谈判的当天下午,彭德怀根据“不使敌人乘机获逞”的指示,致电毛泽东汇报了为配合停战谈判,着手计划第六次战役的设想:
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方针是完全必须的。我能掌握和平旗帜,对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均有利。坚持以三八线为界,双方均过得去,如美国坚持现在占领区,我即准备八月反击,在反击前还须放他前进数十里,使军事上、政治上于我更有利些。再争取一两个或两三个军事上较大胜利,将影响所谓联合国全部的可能分裂,美军战斗意志的必然降低。
根据电报中“如美国坚持现在占领区,我即准备八月反击”可以看出,彭德怀是把拟定中的第六次战役,直接服务于停战谈判的,即以战逼和。
邓华、解方提出谈判要“战斗胜利相配合才更为有利”
1951年7月2日,就在朝鲜战场双方协商停战谈判的时间、地点等问题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高岗、金日成,要求对谈判有关事宜作出部署,同时进一步提醒志愿军领导:“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毛泽东的这份指示,吹响了积极准备第六次战役以配合停战谈判的号角。
7月8日,志愿军司令部向各部首长下达了战役准备工作指示,在分析第五次战役后敌情特点的基础上,针对第六次战役将面临的阵地攻坚和连续纵深突破作战的新情况,强调要与过去攻坚作战经验相结合,在部队中展开对敌纵深攻坚突破学习的浪潮,求得第六次战役更多地歼灭敌人,7月底或8月初前教育准备完毕,随时待命出动作战。
7月10日,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开始,但由于美方不愿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直到7月24日竟连谈判议程问题也未能达成协议。于是,第六次战役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7月16日,彭德怀致电中方谈判人员李克农、邓华、解方,指出:“如果没有和平攻势(和谈)的政治斗争,只有单纯的军事斗争,要想迅速孤立美国,迅速结束朝鲜战争是不可能的。……但和谈并不一定是顺利的,可能遇着很多困难,甚至曲折过程,可能还需要经过严重的军事斗争。再有两三次较大的军事胜利,才能使敌人知难而退。”同时,他通报了志愿军和人民军积极进行第六次战役战术演习教育和具体准备工作情况。
7月24日,由于美方一直消极谈判,彭德怀就组织战役反击以配合谈判问题致电毛泽东,谈了自己的打算:“我再有几次胜利战役,打至三八线以南,然后再撤回三八线为界进行和谈,按比例逐步撤出在朝外国军队,坚持有理有节,经过复杂斗争,争取和平的可能仍然是存在的。……从全局观点来看,和的好处多,战亦不怕。……我于八月中争取完成战役反击的准备,如敌不进攻,则至九月举行。最好是待敌进攻,我则依靠阵地出击为有利。”
从7月中旬到8月中旬,“由于停战谈判开始,双方作战均较谨慎,多属于小部队的前哨战斗,因此,战线无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设想的诱敌深入、防守反击难以实行,遂建议“如敌不进攻,则至九月举行”反攻。这就初步改变了“我即准备八月反击”的原定计划。
7月26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肯定其意见:“敌人是否真想停战议和,待开城会议再进行若干次就可判明。在停战协定没有签订,战争没有真正停止以前,我军积极准备九月的攻势作战是完全必要的。”这样,原定的“八月反攻”改为了“九月攻势(或九月战役)”。
不过,事情又有了戏剧性的变化。
7月27日,在停战谈判进入军事分界线问题的实质性讨论后,美方首席代表、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更加傲慢,不但丝毫没有让步的表示,而且狂妄地炫耀海空军优势,并无理要求这种优势要在军事分界线的确定上得到“补偿”,要求中朝两军不战而退出1.2万平方公里的地区。7月31日,鉴于这种谈判形势,志愿军谈判代表邓华、解方致电彭德怀等志愿军领导人,满腔怒火地建议:“争取和谈来结束朝鲜作战的方针是正确的,但目前谈判时机不恰当,加之我们在谈判上的某些让步,敌已发生错觉,故谈判时敌之气焰甚高,借口海空优势吃了亏而在陆地来补偿的论点,把分界线及非军事区都要推到我方地区以内,数天来的争论,敌毫无让步,据我们估计,至多只能让到现地停战。如果没有外部的动力(如苏联压力、英法等国的矛盾、特别是我之战斗胜利等),要想敌人撤回三八线以南十公里是极端困难的。谈判需要战斗胜利配合,并须作破裂之军事准备,为此建议:……战役准备,争取八月十五以前完成,准备破裂后的反击以八月内动作为宜……如谈判仍在持续,最好是乘敌进攻时予以有力地打击……或者我举行地区性的主动攻击敌人。总之,谈判需要政治攻势,特别是战斗胜利相配合才更为有利。”邓华和解方还对战役的兵力部署(包括使用已入朝的坦克部队)、战役的组织和作战目标提出了建议。endprint
“八月反击”,似乎就要名符其实了!
彭德怀发布预令动员全军“积极准备作战”
1951年8月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对“九月战役”的兵力部署和粮弹储备问题作了原则指示,实际上否决了邓华、解方的建议。同日,中央军委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致电彭德怀,报告空军参战准备情况。
8月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并告高岗,报告了第六次战役的作战意图和基本设想:
拟以第十九兵团3个军加上第47、第42军,以2个军牵制英国、加拿大、土耳其共4个旅,以3个军附炮兵、坦克,争取消灭涟川、铁原线之美骑兵第1师;
拟以第九兵团2个军牵制金化之美第24、第25、第3师及南朝鲜军第2、第9师,求得歼敌一部;
拟以第二十兵团2个军沿北汉江两岸突破南朝鲜第6师防线,向山阳里、华川迂回攻击;
北汉江以东至海岸由人民军2个军团进行牵制攻击。
以上共计志愿军9个军、人民军2个军团。
另,以第40、第38军及第三兵团3个军共5个军为战役二梯队,以便机动使用;第39、第20军分别担任东、西海岸预备队;空军联合司令部应于8月20日移至平壤,准备参战之空军技术熟练的10个团于9月8日进入平壤机场。
如无意外变故,拟于9月10日下午发起战役攻击。下一战役无论进攻或反击,准备连续激战20天至一个月。如我第一线伤亡严重,不能再继续作战时,将二梯队5个军及第20、第39军共7个军和人民军2个军团,适时投入战斗,再持续一个月攻势。我能坚持两个月的连续攻击,打破我以往6~7天的短时攻击。每月消耗敌4万人左右,美帝似有可能屈服求和,以三八线为界,撤退在朝外国军队。
电报同时指出,“如敌在8月底或9月初向我进攻,则在现阵地以逸待劳,适时举行反击最为有利。”言下之意,一旦敌人主动大规模出击,“九月战役”将推迟。
8月9日,彭德怀致电刘亚楼:
8月1日电共有空军22个团于9月初参战,甚为欣慰。空联司最好8月20日左右移平壤,并盼你于8月底或9月初来平壤主持如何?
8月17日,在8月8日关于战役意图和基本设想的基础上,彭德怀以志愿军司令部和中朝联军司令部名义向部队下达了作战预令,同时报金日成、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这一预令与8月8日的基本设想略有不同,朝鲜人民军多了2个军团参战,歼敌对象也由美骑兵第1师变为美第3师、美第25师,其基本部署是:
战役第一梯队为志愿军8个军,以第十九兵团3个军牵制铁原至临津江西岸之敌,坚决阻击铁原以南之敌向北增援;集中第47、第42两军包围歼灭铁原地区的美第3师。
以第26军和第二十兵团2个军除各一部牵制当面之敌外,集中主力突破,然后视情况,歼灭金化东西地区的美第25师(2个团)和南朝鲜军第2师。
第二梯队志愿军第三兵团3个军,第38、第40军,共5个军,于战役开始后开进到指定地点,视情况投入作战,继续扩大战果。
人民军4个军团在北汉江以东至东海岸,分两番配合志愿军作战。
预令要求各攻击部队务于9月10日前完成连续纵深攻坚战斗的充分准备,各兵团和军于8月25日前研究出具体的作战方案。担任战役第二梯队各部根据距离远近不同,于8月28日前作出开进计划。第9兵团(欠第26军)应随时策应元山方面和南线主力方面作战。特种兵的配属将另以补充命令下达(预计参战炮兵,榴弹炮3个师,战防炮1个师,火箭炮1个师,坦克3个团,连同队属炮兵的火炮在内,共有各种火炮2119门)。
彭德怀在电报最后指出:“以上系预定方案,请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并请金日成总司令提出意见。”同时,他将预案发给在开城谈判的邓华和解方,征求他们的意见。邓华和解方分别对17日的预案提出了具体的补充完善意见。
8月24日,彭德怀在给邓华、解方的电报中,进一步阐明了战役意图,并强调指出:“17日预备命令,是要把全军动员起来,积极准备作战,而非具体部署。”
志愿军政治部下发“第六次战役的政治工作指示”
早在1951年5月1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5号文件,第一次明确“联合国军”的作战不再以实现军事占领全朝鲜为目标。6月上旬,“联合国军”全线转入战略防御,并进行各种军事准备。为应对中朝军队的进攻,“联合国军”加强了阵地工事。到7月下旬,基本完成了“堪萨斯——怀俄明线”的工事构筑。
“堪萨斯线”西起临津江口南岸,沿江而上,经积城、道城岘、华川湖南岸、杨口至东海岸杆城以北马达里一线,全长约230余公里,是“联合国军”的主抵抗线;“怀俄明线”,西起临津江口北岸,向东北延伸,经铁原、金化到华川湖南岸与“堪萨斯线”相接,全长约150公里,是“堪萨斯线”在西部地区的一道屏护线。为此,7月间,“联合国军”调用南朝鲜3个国民警卫师构筑“堪萨斯——怀俄明线”的阵地工事,用圆木、沙袋构筑了各类坚固的掩体,包括坦克、火炮、机枪、步枪等各种火器掩体,并有堑壕相连接,且阵地前均设有大量地雷和铁丝网,在“怀俄明线”还构筑有永久工事。
不言而喻,“联合国军”的纵深防御明显加强,是“八月反击”推迟为“九月战役”的重要因素。由于“九月战役”将是阵地攻坚的纵深作战,所以彭德怀不能不慎之又慎。由于这次参战兵种较多,遂在部队中进行了攻坚突破的教育和准备,结合各种地形进行攻坚突破演习,组织了步兵、炮兵、坦克部队之间的战术协同和通信联络教育,着手攻坚突破的器材及作战所需粮食弹药的准备。7月29日,志愿军司令部转发了第64军进行攻坚突破教育情况,以促使各部队科学组织,正确施教,切实提高效果。次日,又以中朝联军司令部名义,将第三兵团成立战术研究会及其活动的做法通报各部队“依照办理”。根据志愿军司令部指示,志愿军炮兵下达了机动炮兵调整方案,要求进行充分的准备和油弹粮食的囤积,积极配合部队作战役性质的侦察,认真了解掌握预定进攻方向的敌情道路情况。endprint
8月18日,为查明“联合国军”前沿阵地及其纵深情况,中朝联军司令部指示第一线各部队,不放过有利机会,歼灭在前沿探索和进扰的小股之敌,询问情况;以精干的兵力,对敌兵力不多、阵地不坚的突出的前哨阵地实施攻击,力求夺取之。8月中旬,中朝联军还派出了战役侦察。
8月21日,为把全军动员起来,积极准备作战,志愿军政治部专门就“九月战役”下发了“第六次战役的政治工作指示”,提纲挈领地指出:第六次战役是再度给敌人以重大打击,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有伟大意义,并从而彻底揭破美帝在最近和平谈判中的阴谋诡计。要取得胜利,必须估计到敌人是有准备的,这是一场激烈的持续攻坚战。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也为“九月战役”做了必要的准备,主要是:一、决定调第二十三兵团2个军共3.5万人,在修建新的机场的同时,兼在后方反特和反敌空降任务;2个火箭炮团、2个榴弹炮团和1个重榴弹炮团,待命入朝;二、“九月战役”各种主要弹药己运到前方,并有超过;三、志愿军冬季服装拟于9月、10月、11月运入前方;四、9月份所需粮食,决于8月底前运完,准备9月上半月抢运战役发起后的10月份用粮;五、从关内抽调500个车皮专供加强在朝鲜的运输。另决9月份补充前方汽车1700辆,以后按每月消耗拨补;六、准备新兵17万人于9月底前集中东北整训待补。
中朝联军司令部关于“九月战役”的预备命令下达后,志愿军各兵团各军按照预令要求,认真研究制定出作战行动方案和开进计划,并按时上报联军司令部。人民军亦详细研究了上级意图和敌我情况,拟订出具体作战方案,上报联军司令部。
诚如中国军方组织编写的《抗美援朝战争史》所言,“从7月8日志愿军发出第六次战役准备工作指示后,各部队即结合贯彻持久作战方针,开始了第六次战役的准备工作。”
不过,准备工作也有不足之处。8月4日、5日,周恩来携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同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就中国、苏联空军进驻朝鲜的时间和进驻前机场增建问题进行了研究,因机场的修建要到11月份才能完成,因此“我空军出动和作战必须推迟到11月份才能实现”。
空军推迟入朝,不能不影响“九月战役”的发动。
中央军委建议第六战役“可否改为加紧准备而不发动”
无论是“八月反击”还是“九月战役”,第六次战役都是旨在配合停战谈判,争取早日实现停战。但是,何时发起攻击,发起攻击以后能否顺利发展,这些必须从是否对谈判有利来考虑。在接到彭德怀8月8日关于第六次战役的作战意图和基本设想的电报后,毛泽东于8月10日批示:“请周、聂迅即集会研究,提出意见。”10日夜间,周恩来邀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炮兵司令员陈锡联、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等,对彭德怀8日来电进行了研究,与会者研究认为:
根据目前朝鲜雨季情况,九月份铁路、桥梁、公路不一定能完全修好,即使预计的九月份全月粮食能于八月中旬抢过鸭绿江,但不一定都能运过清川江(桥梁全断)。如果粮食不足,弹药有损(潮湿一部是可能的,前方尚未查清),便决定大打,而空军又确定不能参加,在敌人又已确定坚守的条件下,恐很难连续作战二十日至一个月。同时,在政治上,九月如仍在继续谈判,我便发动大打,亦不甚有利,如再不能大胜,则影响更不好。从种种方面看,我以加紧准备,推迟发动大打为有刊。九月谈判如破裂,则十月便须准备大打;如敌不进,则九、十两月可在沿线寻找小战,不断给敌以杀伤,至十一月再大打,空军或有配合的可能。
就是说,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倾向于缓打:“九月战役”推迟为“十月战役”甚至“十一月战役”。
8月11日早晨,周恩来将讨论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但“关于空军参战的机场尚未准备好,中央军委决定空军参战时间推迟到11月份,征求斯大林的意见还未得到答复,因此上述研究意见未及时通报给彭德怀。”所以,彭德怀仍然坚持“九月战役”,志愿军司令部遂于8月17日下达了作战预令。接到彭德怀8月17日下达的作战预令电稿后,周恩来起草了中央军委给彭德怀并告高岗的电报,经毛泽东亲自阅改后,于8月19日发出。
首先,这份电报分析说,美国不敢彻底破裂和谈:
敌人对于朝鲜谈判,只打算实现军事休战而不妨碍他的世界紧张政策,故他反对以三八线为分界线,政治原因大过军事原因。其拖延谈判,一方面企图以此逼我让步,另方面也为拖过旧金山会议(注:解决所谓对日“和约”问题)及便利其国会通过预算和加税。敌人敢于这样拖延,自然是因为了解我们正在诚意谋和。但敌人也怕负起谈判破裂的责任,其原因由于他们了解我们在朝鲜的力量已在加强,如果破裂后大打起来,问题依然不能解决,如因此而将战火扩张至中国大陆,可能又遇到英、法的反对。
接着,这份电报详细分析了发动“九月战役”的不利因素,建议“可否改为加紧准备而不发动”:
但从现在具体情况看来,不仅空军在九月份不能参战并也不能掩护清川江以南的运输,而且其他方面也不易使我们这次战役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首先,朝鲜雨季八月底才能结束,清川江、大同江、新成川、富城几座桥梁尚未修通,清川江以北堆积的粮车最快恐需至八月底才能倒装完毕,因之,连续作战一个月的粮食在九月份得不到完全保证。弹药从现在前方储量计算可供一个月作战消耗,但雨水浸蚀的程度不知检查结果如何,有些仓库距离前线较远,尚不能供应及时。且战役发起后,不论胜利大小,均有使战役继续发展可能,我们粮弹储备只有一月,而后方运输又未修畅,设敌人窥破此点,我将陷入被动。次之,从战术上看,在九月份谈判中,敌人向我进攻的可能是较少的,因此,我军出击必须攻坚,而作战正面不宽,敌人纵深较强,其彼此策应亦便。我第一线又只能使用八个军突入,……(敌)有十六个师旅可供呼应,即使我在战役开始时,歼敌一部,但突入后迂回渗透,扩张战果及推进阵地,则须经过反复激战,时间拖长的可能极大,结果对谈判可能起不利作用。现在我们握有重兵在手,空军、炮兵逐步加强,敌人在谈判中对此不能不有顾虑。设若战而不胜,反易暴露弱点。如谈判在分界线及非军事区问题上,在九月份尚有妥协可能,亦以不发起战役为能掌握主动。据此种种,望你对九月战役计划再行考虑,可否改为加紧准备而不发动,如此,既可预防敌人挑衅和破裂,又可加强前线训练和后勤准备。endprint
8月21日,中央军委又将国内为原定“九月战役”所做的有关部队调动、机场修建、兵员补充、物资供应及运输等各项准备情况电告了彭德怀,表明“加紧准备”有条不紊。
彭德怀最终决定“大战役反击在无空军配合情况下暂不进行”
而早在7月初,“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就担心,“中朝联军会利用谈判时机聚集起强大的进攻力量,一旦谈判破裂,就能够发动强大的攻势。”对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极为担心”。“李奇微并从有关方面获知,志愿军将于8月底发动‘第六次战役。”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军方策划,决定对朝鲜北方实施“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即所谓的“绞杀战”,目的“一、阻止敌人在北朝鲜建立重要的空军基地;二、阻断敌人的供应,使他们不能发动及维持一个大规模的地面攻势;三、以空军压力伤害敌人,以影响停战谈判。”
8月18日,出乎中央军委8月19日电报的意料(“在九月份谈判中,敌人向我进攻的可能是较少的”),“联合国军”以其地面部队发动了夏季攻势;同一天,“联合国军”以其空军(美国空军为主)发动了“绞杀战”。
正当美军开始“绞杀战”时,朝鲜北方爆发了40年来罕见的特大洪水,美国人狂呼“老天也帮了轰炸机指挥部的忙”。8月间至9月中旬,美国第五航空队每天为其每个战斗轰炸机大队规定一段15至30英里长的铁路,由他们前去轰炸。美战斗机大队一般以大队编队方式,以32机到64机的大机群出动,对京义线沙里院以北和整个满浦线进行轰炸;轰炸机指挥部的B–29战略轰炸机,对平壤以北正在修建的机场和几座主要铁路桥梁进行轰炸;海军舰载航空兵对朝鲜东海岸的铁路进行轰炸。由于美军“绞杀战”和洪水的双重破坏,到8月底,朝鲜北方1200余公里长的铁路中,能通车的线路仅有290公里,整个铁路交通处于前后不通中间通的状态。
本来志愿军运输能力弱又没有空军掩护,战场运输相当困难,“绞杀战”一来更如雪上加霜。对此困境,彭德怀当机立断,于8月21日、22日两次致电中央军委,表示鉴于“空军九月不能入朝参战,运输物资又无保障”,“同意将九月战役进攻,改为积极准备”。“九月战役改为积极备战,防敌进攻,准备适当时机反击,如敌暂不进攻,待十月再决”。
9月初,志愿军前线部队出现了食物短缺状况,且冬寒将至,棉衣尚未运到。9月7日,彭德怀在给聂荣臻的电报中有一段话反映了当时前方的困难:“早晚秋风袭人,战士单着,近旬病员大增,洪水冲,敌机炸,桥断路崩,存物已空,粮食感困难,冬衣如何适时运到,实在逼人。”
与此同时,就在8月18日,即“联合国军”发动1951年夏季攻势当天,邓华在给彭德怀并转毛泽东的电报中,仍然主张以军事胜利配合谈判:“在军事上我应有所准备,纵目前不进行战役反击,也当尽可能作战术的反击,收复些地方,推前接触线,更好地了解敌人阵地及其坚固程度。”8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请他考虑邓华的建议:“我认为这个意见值得认真考虑,请你计划一下,九月份能否进行此种战术反击,如何进行法,须用多少兵力,胜利把握如何,敌人的反应将会如何,请就这几点考虑电告。”8月23日,彭德怀复电毛泽东,说:“九月不举行大的战役进攻时,可选择伪军突出部队举行局部进攻。”最终,在8月18日至9月18日的粉碎“联合国军”夏季攻势、10月1日至10月22日的粉碎“联合国军”秋季攻势中,中朝联军相继歼敌7.8万人和7.9万人,证明依托阵地举行战术性的反击作战,更有利于大量歼敌,更有利于战线的稳定,对坚持持久作战更有利。因此,到了10月下旬,彭德怀最终决定,“大战役反击在无空军配合情况下暂不进行”,“十一月甚至今年底(除特别有利情况在外),拟不准备进行全线大反击战役,根据九、十月经验,采取积极防御方针,敌人消耗很大,敌对我亦甚恐惧”。
至此,第六次战役计划遂告撤销。
第六次战役计划虽未实施,但这一战役计划是根据停战谈判的需要而提出的,也是根据停战谈判的需要而放弃的。第六次战役计划的拟定与取消,完全是在毛泽东的过问下,根本不是彭德怀擅自制定的,甚至一开始他是反对第六次战役的——“一般(特殊情况在外)对美英军不拟组织全面的大战役!”同时,第六次战役的准备,在军事上对1951年粉碎“联合国军”夏秋季攻势作战和坚持持久作战方针,具有直接的积极的作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