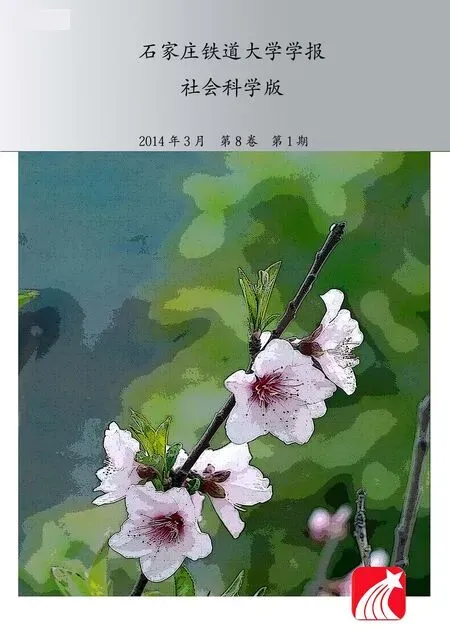打工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
陈 一 军
(陕西理工学院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文坛开始出现打工小说,经过一二十年的积累,到21世纪初,打工小说创作已成繁盛之势,且有了不菲的实绩,自然得到了评论界的热切关注。
打工小说是一种题材的分类,就是叙述打工者经历和感受的小说。打工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生活方式,主要是千千万万农村或乡镇的农民到城市做工以谋求自身与家庭的生存和发展。所以,打工者大多具有乡村文化背景,在卷入城市化进程以后往往要经历种种遭遇和精神结构深处前所未有的冲突①,因此逐渐成为小说家竞相描述的对象,终于形成打工小说创作的潮流。在打工小说创作中,有一种现象颇为引人注目,就是以打工者作为叙述者兼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小说作品的大量涌现。这里随便拈出几个文本就能让人感觉到打工小说第一人称叙事的繁盛,像张伟明的《我们INT》、于怀岸的《台风之夜》、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夏天敏的《接吻长安街》、王十月的《烂尾楼》、李一清的《农民》、贾平凹的《高兴》、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等等。
第一人称叙事是“叙述者和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同为一人”的叙事。[1]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这种由“我”讲述“我”自己故事的第一人称叙事并不稀罕,甚至在某些时段颇为兴盛,比如“五四”时期。陈平原先生即将由叙述者讲述自己故事和感受的第一人称叙事看做是“五四”新文学的特征之一。[2]85-88然而,包括五四文学,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人称叙事主要是知识分子形象担任叙述者兼主人公的,农民形象作为叙述者兼主人公的情况并不多见。可是,新时期以来的打工小说却改写了这一历史,这显然不是偶发事件,应该是特定的时代背景、文化取向和审美情趣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时代脉动
打工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反映了特定的时代风尚。打工小说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它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渐多,新世纪初期呈现繁荣景象。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将中国推进俗世的生活世界,彻底告别了漫长的革命时代。从实质上说,革命时代是一个英雄时代,谋求和看重先觉意识与超凡价值,所以从“五四”到“文革”期间的小说农民叙事主要取向国家—民族的意识形态表达,农民基本作为被叙述者,作为媒介在表现写作主体的理想和价值选择。因此,这个时期农民作为叙述者兼主人公在第一人称小说作品中很难出现,因为英雄意识本质是精英式的,它排斥和遮蔽了农民自己的话语。穆木天在20世纪30年代即认为:“在现在中国写工人农民用第一人称是难以使文章与主人公的身份相适合,因之减少作品的真实味。”[3]231他的理由是工人农民是文盲,难以承担叙述者的角色,而时代要求文学创作要“表现客观的复杂的现实”[4],表现“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工农大众的情绪”[3]233。要实现这一目的,只有借助知识分子的分析和发掘。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小说创作者便一味以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观察、玩味、品评被认为是还未发蒙的那些苦难寒怍的农民,农民本身成为完全没有叙述能力的人,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成为被任意言说的对象,而由农民形象作为叙述者的第一人称叙事在极大程度上被压抑了,排斥了。
但是改革时代的农民不同了。俗世社会不再将目光聚焦在非凡价值和英雄品格上,而是更多投向谋求日常生活的平凡人生。不同阶层、不同类型人们的实际生存境况逐渐得到了重视和关怀,漂洋过海的西方人生哲学等社会文化思潮进一步廓清和助长了这种意识和行为。知识分子包括小说创作者的视点开始真正下移,渐渐潜入到底层民众的心灵世界。1990年代以市场结构为导向的中国社会化转型[5]又给这一趋向以更加切实有力的推动,大众文化的勃兴将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同时,又在他们的观念中渗透和融汇了民间情调和平民意识,这在小说创作者的身上体现为一种民间化叙述立场的获得,就是“根据民间自在的生活方式的向度,即来自中国传统农村的村落文化的方式和来自现代经济社会的世俗文化的方式来观察生活、表达生活、描述生活……”,表现的是“民间自在的生活状态和民间审美趣味”。[6]这个时候,穆木天当年立论的那些理由似乎动摇了。世俗化的时代不再谋求主题宏大的叙事,而是着眼于人生体验的“狭小”格局,真理向当年与穆木天争论的另一方——陈君冶——的一边倾斜,第一人称叙述的关键在于作者对于作品中的自白者的身份认识的程度。[7]这即是说,如果作者对于作品中的自白者的身份的认识没有“缺憾”,就可以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在打工小说中,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李一清的《农民》等小说作品都给这一观点以支撑。而且,穆木天先生若能再世,会惊奇地发现今天的许多农民已经不再是文盲,而成了具有一定知识的人。显然以这样的农民主人公作为叙述者将不会再是“滑稽”的、“困难”的、“不适宜”的事情[8],这是打工小说中大量以农民主人公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小说作品出现的主要原因,像夏天敏的《接吻长安街》、贾平凹的《高兴》、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都属此类情况;而张伟明的《我们INT》、于怀岸的《台风之夜》、王十月的《烂尾楼》等一律是打工作家创作的打工小说,更将农民主人公作为叙述者的第一人称叙事的“虚假”和“越界” 荡涤净尽,并且实现了新文学史上叙述主体的一种颠转,既往文学格局中的被书写者、“沉默的大多数”——农民等,拥有了话语权,并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9]92
总之,农民主人公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小说作品相对集中出现在打工小说里是一个富有意义的文学现象,它反映了农民作为弱者的言说欲望以及被关注的程度,也反映了我国社会的进步和农民自身的觉醒。解放前,中国农民苦难深重,一直粘滞、挣扎在求生的境地;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的不少利益被长期截取用来助推国家重工业的发展,农民自身积弱积贫,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直到90年代后期,国家才意识到农民的卑微、屈辱、不堪重负,开始真正给他们减负,开始切实重视和维护他们的权益。作为社会神经触角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创作者,更是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们在自身地位边缘化的同时,在西方理性的启迪中,自觉地站到了农民的一边,这时,集中了最尖锐矛盾和冲突的农民打工者成为他们追逐、感受的对象,他们热忱地为农民打工者立言。对农民打工者来说,打工之路将他们推到了一个与乡村文化异质的城市文化带,他们在用身心体验这种异质文化的冷漠、高傲,甚至残酷的时候,也打破了自己原来思维的封闭、僵化,开始用新异的目光审视他者,思量人生。所以,打工经历往往会给进城的农民一种自觉意识,这一点非同寻常,表明几千年尘封的农民开始自动参与到社会变革中,这也是打工题材在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初期被众多作家注重的原因所在,而农民形象作为叙述者兼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事可以看作是农民觉悟的最醒目的标志。
二、从口到书到笔
农民形象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一直是“不具备叙述能力”的人。[10]然而,这一定性在打工小说这里变得复杂起来,成了一个疑问。更为准确地说,农民形象是“不具备叙述能力”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这一命题在打工小说这里变得只是部分有用,部分已经失效了。
农民形象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兼主人公的情况在打工小说这里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不具备叙述能力”的第一人称打工叙述者。鬼子《瓦城上空的麦田》、李一清的《农民》可以看作是此类叙述的代表。《瓦城上空的麦田》中的“我”——胡来城——一个捡垃圾的十五六岁的少年,几乎没上过学。《农民》中的“我”——牛天才——一个四五十岁的农民,根本没上过学。面对这样的小说主人公,叙述主体[11]66叙述的时候面临较大的困难,必须尽可能模拟叙述者的话语,以使叙述语言符合叙述者的身份。好在“第一人称小说是最典型的‘讲故事’的作品,它所擅长的是对各种微妙故事的述说……”[11]281而讲故事是人的天性。所以,打工小说的这类第一人称叙事就极力呈现主人公讲故事的原生性和朴拙感,絮絮叨叨地把他的生活遭遇和人生经历和盘托出。因此对于这类叙事而言,最恰当的叙述就是语言极为本色的朴实无华的表达。然而,这样的叙述极难控制,稍不留神就会造成视角越界,给文本带来人为虚构的不真实感。但是一味地谋求叙述语言本真的努力又会使叙述处处受鲠,变得寸步难行。由于时代让作家走进了农民心灵的深处,《农民》、《瓦城上空的麦田》整体上获得了淳朴性,但是叙述视角的频频越界还是给文本留下了些许不真实感。下面不妨看一段《农民》中的文字,这是牛天才在果城打工,一天晚上到郊区菜农那儿买菜时眼见的情景:……那些棚外生长着的蔬菜,一畦一畦,被江风吹拂着,绿汪汪的叶面上,跳跃着光和月的影子。不远处的嘉陵江,弯弯的,细细的,灰灰蒙蒙,涛声隐隐,偶尔就见一点渔火 ,在江心闪烁不定。……[12]这段诗意的描写显然牛天才做不到,只能是背后的叙述主体所为。为了掩饰和弥合文本的这种裂痕,叙述主体有时不得不故意掩饰道:“看看吧,我这个老农民,大老粗,也像个迂夫子般酸文倒醋起来。”这里能够感觉得到叙述主体在叙述时的窘迫与不安。即便这样,由于叙述主体与叙述者之间的巨大落差造成的文体构造的人为痕迹还是显露出来了。鬼子《瓦城上空的麦田》也存在类似情形。
(2)基本具备叙述能力的第一人称打工叙述者。这类叙述的叙述者兼主人公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他们和叙述主体的距离与上一类叙述者相比大为缩小。《接吻长安街》、《高兴》、《吉宽的马车》等作品可谓此类叙述的代表作品。这几部小说的叙述者都是较为年轻的农民工。《接吻长安街》中的“我”(小江)是初中毕业就跑到北京打工的小青年。《高兴》中的“我”(刘高兴)是高中毕业生,《吉宽的马车》中的“我“(申吉宽)是初中毕业生,两人都三十多岁。小江、刘高兴、申吉宽这几个人物的共同特点是都爱看书(报),都有一定的艺术欣赏能力,申吉宽简直是个诗人,刘高兴可称得上是吹箫的能手。《接吻长安街》、《高兴》、《吉宽的马车》这几部小说之所以这样定位它们的叙述者/主人公,是为了使整个叙述切合叙述者的身份和特质,使其显得真实可信。应该说,这几部作品都获得了很大成功。因为它们的叙述者/主人公在现实中已经有不少这样的原型,而小说叙事的真实感其实就在于它向读者提供了众多可被现实社会证实的“蕴含”。[13]190因此,广大读者已经基本能够认同那个有着强烈变态精神需求的小江,那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吉宽和那个有着艺术家风范的自省的刘高兴,因为他们都不过是在城乡对峙、城市对乡村过分压抑的情况下打工者精神的畸变和寄托。这样,小江的看书和“接吻”,吉宽的那首诗和进城携带的那本法布尔的《昆虫记》,刘高兴动辄在街头奏响的箫声,就不是简单的叙事行为,而成为支撑小说文本整体叙事的关键因素,成为小说文本精神深度的象征,而所有这些都凝结为一个可被现实证实的“指涉蕴含”[13]190: 现实生活中的不少农民已经成为要求精神滋润的、要求自由平等和舒展美丽的新型农民。
但是,不管是小江、吉宽还是刘高兴,毕竟都不是叙述主体本身,他们与叙述主体的距离还是存在的,因而给叙述主体的叙述也制造了小小的麻烦,给小说文本带来些许矫揉造作。贾平凹的《高兴》是非常优秀的作品,即使这样,文本的有些情节仍不太契合叙述人身份,比如刘高兴对锁骨菩萨的情有独钟,刘高兴与韦达的交往,以致不少读者给贾平凹反映说感觉刘高兴不像农民。[14]吉宽尽管读过不少名著,进城也不忘随身携带一本法布尔的《昆虫记》,还有诗为他作证,但是《吉宽的马车》的一些叙述话语毕竟过于诗意和缜密,感觉超出了吉宽的能量,只有叙述主体才能做到。而夏天敏的《接吻长安街》的结尾的矫揉造作显而易见。看来第一人称最相宜的叙述只有在叙述者与叙述主体基本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种情况对于农民叙述者而言,只有在打工作家创作的打工小说那里才得以圆满。
(3)完全具备叙述能力的第一人称打工叙述者。打工作家是深圳特区最早造就的文坛风景。在深圳特区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出身乡村或乡镇的青年走进了深圳这片热土,走上了深圳的生产流水线,走进了深圳生活的角角落落。受现代化的压迫和刺激,复被自身的孤凄漂泊驱遣,从这些队伍中逐渐成长起一批书写打工者奋斗历程、曲折遭遇和情感波折的打工作家,其中不少人创作了运用第一人称手法叙述自己和打工族的打工生活的作品,造成第一人称打工叙事在打工作家这里成为一个十分惹眼的现象。像张伟明、于怀岸、王十月这些打工作家都有他们的第一人称打工小说,包括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我们INT》、《台风之夜》、《烂尾楼》等。在打工作家的第一人称打工叙事里,叙述主体与叙述者兼主人公的距离消弭了,《烂尾楼》中曾经用漂亮字迹填写骗人招工表格的“我”在后来拿起笔开始叙述自己的既往经历了。事实上,《我们INT》、《台风之夜》中的“我”都是有一定知识、一定见解,有思考能力和清醒自我意识的青年,这和叙述主体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又决定了叙述话语的自然流畅、清新朴实。打工作家第一人称打工叙事的一笔一画都是生活雕刻出来的,显示着生活的原生态性,极具生活的实感。“真实”可谓打工作家第一人称打工叙事的最高审美价值。这种“真实”其实内含了我国新生代农民自我反省和言说的能力以及直面人生的态度。
在打工作家的第一人称打工叙事中,叙述主体对于自身身份有一种勇敢的裸露和坚持②,就像张伟明的小说《对了,我是打工仔》这部作品的题目所示。正是这种身份的裸露和坚持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小说农民叙事提供了一种宝贵的“农民”的叙述主体资源,“弥合了原来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底层写作中表述者和被表述者之间由于身份、处境的差异而存在的裂缝,以质朴本真的写作状态为曾经弥漫于当代文坛的‘伪真实’提供了绝佳的反证……”[9]94
三、艰难和自省
打工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因为“正是叙事视点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13]128徐岱也说,叙述人称“意味着一种叙事格局的确立,这种格局关系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方式。”[11]274这就是说,叙述人称关系小说文本的艺术形式和审美感受。第一人称叙事能给人强烈的真实感,由作为叙述者的主人公讲述自己曾经发生过的故事,而且所讲述的内容夹杂“某些具体可考的历史事件与明确的时空背景时,”就会显得更加真实可信。[11]275《台风之夜》、《烂尾楼》、《高兴》、《接吻长安街》等都有明确的时空和具体的事件,而且牵扯到真实的地方,比如,《台风之夜》中的广东和汕头,《烂尾楼》中的东莞,《高兴》中的西安,《接吻长安街》中的北京。这就使得这些第一人称的打工小说以叙述者兼主人公的“诚实报告”的形式报告了他们的“心的状态”[15]56-58,不容你有所怀疑。而伴随这种真实感而来的,是没有距离、促膝恳谈的亲切感,是一种让人心热的主体性和浓郁的抒情味[11]276,这使得小说文本极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能够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当叙述人遭受的是无奈、屈辱、痛苦、不幸的事件时,就越能打动人。因此盖利肖如是说:“要是想让小说人物讲一个对自己不利的故事,你就让他做主角——叙述者……”。[16]
这恐怕就是贾平凹将《高兴》最终改写为第一人称叙事的原因。根据贾平凹在《高兴·后记》中所说,面世的《高兴》是更换角度和叙述人之后的重写:“这一次主要是叙述人的彻底改变,许多情节和许多议论文字都删掉了,我尽一切能力去抑制那种似乎读起来痛快的极其夸张变形的虚空高蹈的叙述,使故事更生活化,细节化,变得柔软和温暖。”[17]根据这段表白,《高兴》的初写本很可能是全知叙述,因为全知叙述最便于凌空的说三道四。如果《高兴》依这样的角度写来,肯定会变得硬涩,失却那份温情、那种凄恻动人的力量。贾平凹显然为《高兴》找到了最相宜的叙述视角。《高兴》的成功也在相当程度有赖于此。正是采用了以刘高兴作为第一人称叙述人兼主人公的叙述视角,《高兴》才把刘高兴这样的乡下进城群体的生活境遇异常逼真地、直接性地[18]呈现给大家,让广大读者的心灵深处在刘高兴的娓娓絮叨中掀起阵阵波澜。
打工生活的艰难险阻是中国最近二、三十年城市化进程中的尖锐现实,就像船只行过浅水的怪石嶒崚的河床。然而,这样的事情往往是矛盾的纠合点,在富于褶皱和张力中蕴蓄着旺盛的含蕴,给文学创作能够提供很好的素材和丰富的想象。具体来说,城市打工者粘滞在城乡文明的错杂交织中。城市和乡村本来是两种文化生态,农民由农村或乡镇来到城市,迷乱彷徨在所难免,城市一面排斥、戏弄和惩罚他们,一面又诱惑、利用他们;许许多多打工者就在这种揉搓中饱尝辛酸痛楚,内心晃荡着一腔苦水。中国最近二三十年的打工生活对大多数打工者而言,是文明碰撞的辛路历程,是一段悲情时期。此情此景,获得平民意识的创作主体不甚唏嘘,显然最相宜的叙述视角就是盖利肖所说的第一人称主人公叙事。这就是打工小说为什么相对集中了第一人称主人公叙事的原因之一。《吉宽的马车》、《接吻长安街》、《台风之夜》、《高兴》等等都让人们能够切身感受到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这一叙述角度选取的恰切和精当。
对第一人称叙事来说,“我”作为叙述的主体,维系着作品的全部叙事魅力,因此,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必须是具有鲜明个性色彩和人格内涵的富有魅力的人。[11]277-278前面已经提到,打工者面对城乡两种文明,心灵充满了对撞和皱褶,是含蕴极为丰富的存在者。当他们再以鲜明的个性开口讲述时,他们的话就有了磁力。《农民》中的“我”(牛天才)本是个木讷的人,却讲出了精彩的深刻的故事;其实,“精彩”“深刻”的是他的人生,木讷更能给人们牛天才人格实诚的印象。《瓦城上空的麦田》中的胡来城小小年纪,却历经沧桑,最重要的是他在“破烂”人生中依然保持人性的美好,给冷酷的城市以有力的激灵。《接吻长安街》中的“我”(小江)的变态就是一种个性、一种深度、一种魅力。而且,自省,个性的增长和主体性的增强更为打工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主人公的人格增添了魅力。申丹认为,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通常有两种交替作用的眼光: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19]可见,第一人称打工叙述必然会体现主人公觉醒和反思的过程,这即是刘高兴不时挂在嘴边上的“反刍”能力。打工者由乡下进入城市,意识必然在与城市的对撞中激变。打工经历让牛天才对土地有了新的认识。吉宽也在城市的折腾中走向成熟,获得了自主人格。而刘高兴在经历城市的打工波折后,自省意识已由原来的轻浅明快变得悲凉深沉。现在可以在更高层次上认识第一人称的打工叙事。陈平原在论及五四小说时说,“‘五四’思潮解放了‘自我’,也真正赋予第一人称叙事模式强大的艺术生命力。”[2]97这是“五四”时期第一人称叙事兴盛的原因。同样的道理,最近二、三十年,第一人称打工叙事的繁盛也是农民自我觉醒和心灵解放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小江、吉宽,特别是刘高兴成为新文学史上农民走上自省和自觉的里程碑式的人物。
注释:
①雷达语,见《打造“打工文学”品牌,促进社会和谐进步——首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纪要》,载杨宏海:《打工文学备忘录》,第20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②李敬泽语,见《打工文学:身份验证后登陆社会》,载杨宏海:《打工文学备忘录》,第12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参考文献:
[1][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71.
[2]陈平原.中国小说故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穆木天.再谈写实的小说与第一人称写法[A].吴福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穆木天.读写实的小说与第一人称写作[A].吴福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21.
[5]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10.
[6]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160.
[7]陈君冶.谈第一人称写法与写实小说[A].吴福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31.
[8]穆木天.关于写实的小说与第一人称写法之最后答辩[A].吴福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37.
[9]杨扬.新中国社会与文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0]申洁玲.论现代小说“不具备叙述能力”的第一人称叙述者[J].广东社会科学,2005(5):162-167.
[11]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2]李一清.农民[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100.
[13][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4]贾平凹.关于〈高兴〉[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26.
[15]唐热风.第一人称权威的本质[J].哲学研究,2001(3):54-60.
[16][美]约翰·盖利肖.小说写作技巧二十讲[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81.
[17]贾平凹.高兴·后记(一)我和高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363.
[18][美]利昂·塞米利安.现代小说美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65.
[19]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