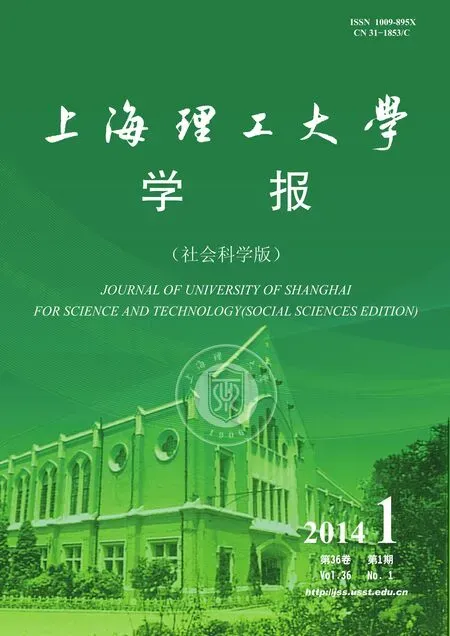蒂姆·温顿《浅滩》中的生态思想
徐显静
(1.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上海200093;2.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上海200083)
《浅滩》是一部旗帜鲜明的生态小说,发表后即获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文学奖“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小说围绕澳大利亚传统产业捕鲸业的兴衰展开,再现了白人在澳洲这块古老又崭新的大陆150多年的定居史。充满了悲剧色彩的库珀家族是这一历史进程的见证者,世世代代都与鲸结下了不解之缘。来自美国的先祖纳撒尼尔·库珀是安吉勒斯捕鲸业的缔造者之一,他用日志记录下了这个过程。但是早年血腥的捕鲸活动给纳撒尼尔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这种创伤甚至波及了后代。与其祖先相反,库珀家族的第五代继承者昆尼·库珀却是鲸鱼的守护天使,她身上寄托着作者的生态理想。通过《浅滩》蒂姆·温顿想要传递的生态观就是:无论是日志中所记录的早在150年前纳撒尼尔·库珀对于残忍的捕鲸活动表现出的质疑和彷徨,还是现实生活中安吉勒斯小镇岌岌可危的捕鲸工业都明白无误地表明:人类无权这样践踏自然,毫无节制地猎杀同样具有生存权的海洋生物。遗憾的是,小说虽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但除了一些介绍性的书评略有提及外,在文学批评界却鲜有人对文本中体现的作者的生态意识做深入分析。本文将利用西方生态文学批评理论,从分析库珀家族四代人与捕鲸业的纠葛入手,通过对基督教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对现代捕鲸工业的批判、对工业社会开发的工具理性批判以及对澳洲土著生态智慧的借鉴四方面解读《浅滩》中体现的温顿的生态文学思想。
一、对基督教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它把人看成是自然界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是一切价值的尺度,自然及其存在物不具有内在价值而只有工具价值[1]51。20世纪最著名的生态文学作家雷切尔·卡森认为,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根源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她指出“犹太—基督教教义把人当做自然之中心的观念统治了我们的思想”,于是“人类将自己视为地球上所有物质的主宰,认为地球上的一切都是专门为人类创造的”[2]171。
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控诉在文本中比比皆是。比如,丹尼尔·库珀哀叹: “因为那些居住者的罪过,野兽和飞禽都一扫而光。”[3]75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使得地球上的无数飞禽走兽灭绝。生态学家的确认为消失的物种是对人类的一种警告,告诫人们在恐怖的情况出现之前,最好停止掠夺自然资源[4]81。又如,遵循自然法则也那么难[3]282。人类破坏自然法则,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于是大自然就用自己的方式惩罚人类,澳大利亚在70年代末经历了连年干旱。所以“由于人的可怜的自尊的缘故,光之父不让雨落下来。自尊可以休矣。但是,自尊等待着,直到其他一切都凋谢了”[3]282,这才是人类的悲哀。此外,人类必须认识到“不采取行动也是一种罪孽”[3]96。面临着诸多环境问题,每个人都“具有天赋的义务去医治自然受到的创伤,并保护自然不再受到蹂躏,不再呈现死亡的迹象”。正如利奥波德指出的:保护生态整体,是每一个人的责任[2]199。
温顿态度坚决地批判了把《圣经》作为人类荼毒生灵的理论依据行为。温顿小说中常常刻意使用圣经训示或直接引用圣经经文,使之在小说文本内产生一种预言式的共鸣,使人物达到一种崇高庄严的境界[5]476。但是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他对以基督教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例如,前文所引丹尼尔的哀叹实则语出《圣经·耶利米书》。又如,他引用了以赛亚的一段话:“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接着作者痛斥:这些无知的家伙相信抹香鲸就是毒蛇,恶魔的代理[3]121。纳撒尼尔·库珀的日志中细致入微地记录了人物内心的彷徨和挣扎,捕鲸经历给纳撒尼尔造成了心灵严重的创伤,使他对上帝产生了质疑,丧失了信念的他,不能给予和接受爱,众叛亲离,最终自杀。怀疑上帝,是因为《圣经·创世纪》里上帝赋予人至高无上的权利:人类是万物之主,人类早就获得了上帝的授权,人类可以对自然万物随意处置[2]172。通过纳撒尼尔这一人物形象说明:在目睹人类为了自身的贪欲而荼毒生灵时,人们也会经历信念消失,精神萎缩,甚至异化。此外文中多次提及《圣经》中约拿与鲸鱼的典故,但《浅滩》提出的问题不是约拿被鲸鱼吞下,而是人类吞噬鲸鱼将会发生什么[6]221,其寓意耐人寻味。
《浅滩》还表达了温顿朴素的生态伦理思想。生态伦理学是由法国哲学家史怀泽和英国环境学家利奥波德创立的,史怀泽从对生命的崇拜出发,进一步提出尊重生命的伦理学。利奥波德则提出了“大地伦理”概念[7]1185。他认为现在的伦理学研究要把道德权利扩展到动物、植物、土地、水域和其他自然界的实体,确认它们在一种自然状态中持续存在的权利。即从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过渡到生态中心主义的伦理[1]37。生态伦理学理念能有效打破人类中心的思维方式,把人类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部分看成大地共同体平等的成员。《浅滩》明确指出“要是我们能证明它们富有智慧,我们就可以保护它们了”是地地道道的“智慧怪论”、“伦理垃圾”,因为“一件东西不需要有智慧才能找到存在的理由”[3]152。正如小说中环保主义者马克斯所言“鲸鱼是地球上的居住者——它们需要保护,就这么回事,因为它们指定要在这儿,不需要论证合理性”[3]152。人类生存并且使其他生物也能够生存在温顿笔下是不言自明的事实,无须任何证明。
二、对血腥捕鲸工业的批判
捕鲸业是19世纪30年代羊毛成为主要产品前,澳大利亚的支柱产业。但是由于人类长期的恣意捕捞,更由于捕鲸手段的日益更新,二战末,海洋的鲸鱼资源就显示出了枯竭的迹象,捕鲸站也陆续关闭,澳洲最后一个以陆地为基础的捕鲸站就位于西澳阿尔巴尼 (Albany),也被迫于70年代关闭[4]79。所以,说“正是这些捕鲸工创造了这个国家”[3]40一点儿也不为过。
先祖纳撒尼尔·库珀早年在捕鲸船上工作,亲历了这项血腥产业的发迹:当时捕鲸设备落后,生活环境恶劣,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渺小的。早期的捕鲸过程伴随着病、死、疯的痛苦,同时还有遗弃、冷漠、人性的丧失。他在日志中记录下了在当时艰苦环境下人类异化的生活:捕鲸工酗酒、斗殴;把被打掉的左耳垂藏在水手柜里;发泄生存压力,玩土著女人甚至奸后将其分尸;厌恶甚至鸡奸同伴;在同伴死后就随意丢弃或者吃了他们的肉……于是从事着血腥产业的人也变得面目狰狞起来。人们做着残忍的工作,精神也处于崩溃边缘。正如阿尔·戈尔所断言:环境危机就是精神危机。捕鲸工的残忍使人退化成野蛮人,禽兽不如。
捕鲸的罪恶甚至波及后代。在缺少父爱家庭里长大的马丁·库珀是个神经质,他无能却又自尊,开枪自杀后给妻子和儿子留下一屁股债务,还使他们丢了土地[3]87。马丁的儿子丹尼尔也受家族的影响丧失了爱与被爱的能力,致使妻子一生孤独,在刚刚品尝到丈夫的爱时却意外身亡。妻子的身亡,使丹尼尔猛然觉醒,追悔莫及,于是,晚年的他一直在孤独地探求罪过与救赎之道。
现代的安吉勒斯 (以阿尔巴尼为原型)正是1978年澳大利亚社会的缩影:经历着气象的 (暗示精神上的)干旱,面临着资源枯竭及外界要求停止捕鲸的内外压力,最后一批捕鲸从业者在做着最后的抗争,拼命想要留住这种行将消失的生活方式[4]79。因为对于当时的小镇人来说,没有了捕鲸业,人们将面临着失业,生活方式将面临重大转变。环保主义者所面临的压力和抵制可想而知。即便如此,温顿并没有放弃努力。为了唤醒人们的同情心和环保意识,他不动声色地把捕鲸工业血淋淋的场面描述给读者看:雌鲸为了保护幼鲸,暴露自己,惨遭杀戮[3]160;小鲸从母体破腹而出;群鲸大批涌向海滩集体自杀……场面悲壮至极、令人为之动容。由此,温顿对捕鲸业的批判是血淋淋的。
昆尼·库珀是批判现代捕鲸工业及作者环保理念的践行者。她清楚地意识到“已经等不及自上而下来改变一切了。鲸们已经奄奄一息,正被灭绝”[3]63。商业捕鲸破坏了自然美和诗意生存,捕鲸业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海洋里最大动物鲸的灭绝,继而导致一场生态灾难。为了参加国际环保组织的护鲸行动,昆尼甚至不惜与着迷于这一传统产业的丈夫克里夫闹翻。克里夫喜欢阅读《白鲸》,“惊叹鲸鱼庞大的身躯,羡慕那些捕获并肢解鲸鱼的人”[3]36,这些显然是主张护鲸的昆尼无法苟同的。但是在与妻子分居期间克里夫仔细阅读了纳撒尼尔记下的日志,这深深教育和感化了他。读懂了库珀家人,也逐渐理解了妻子的护鲸举动,最后他把“鱼枪丢到街上的垃圾桶里”[3]267,加入了保护鲸的行列。除了丈夫的不理解,小镇的人也敌视昆尼。在她第一次参加环保者抗议活动时,那个“曾经开过她们校车的可爱家伙在骂她”[3]38,甚至到后来,昆尼听见了枪声。昆尼虽然在小镇人眼中是异端,但她毕竟勇敢地走出了第一步。面临着“做地球的朋友,你就不得不做人类的敌人”[2]124的痛苦抉择,她选择了向前而不是退缩。面对早已深刻异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一个人的抗争力量虽然有限,但环保运动需要这种不懈努力,更需要《浅滩》这样的生态文学作品来唤醒早已麻木的人类。
三、对社会开发的工具理性批判
小说中的人物德斯·普斯特林是个房地产商,在他身上充分体现着西方现代社会的一些理念,如开发、竞争等。他野心勃勃,想趁佩尔牧师退休后,把教会用作某种经济上的掩饰和骗税的手段,然后去买地、开发;他还打算以小镇150周年庆祝活动为契机,发展旅游、餐饮等所谓让小镇活起来的产业等。他的目的就是赚钱,他的行为试图抹掉小镇与大海的古老的、确定的联系。意味深长的是,他是不能生育的[4]79。温顿批判了这种以牺牲其他物种利益为代价的社会经济开发,而普斯特林的不育则暗示着无论产生多少经济利益,这种发展模式终将是无果的,因而也是不能持续的。
拖拉机、推土机以及卡车等意象出现在温顿的多部作品中,具有深刻含义。它们代表着工具理性,彰显着技术改造世界的霸权。随着工具理性的极大膨胀,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中,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退化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以至于出现了工具理性霸权,从而使得工具理性变成了支配、控制人的力量[8]88。推土机等是现代技术的产物,它们是经济开发的先锋部队,把自然的原生态,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存状态一手毁掉。出现在海滩上的推土机意象更加耐人寻味:当人类开发的触角已经伸到了陆地边缘——海滩,这就意味着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最后生态乌托邦家园也行将被吞噬,社会经济开发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侵蚀和挤占也就发展到了极限。
此外,小说第一章有个细节值得关注:她 (昆尼)不允许在水下使用武器[3]4。随着技术进步,正是使用武器 (大炮)捕鲸,进行商业捕鲸,才造成了鲸的濒临灭绝。工具理性借助科技的力量,人们改造或是更确切地说是破坏自然的速度显著加快了,全世界范围内,工业和科技文明对自然的征服和破坏,在20世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生态文学作品有责任和义务“向工业化和科学技术发出强烈的质疑和激烈的批判”[2]177。《浅滩》向读者揭示了工具理性霸权向人类诗意栖居的乌托邦家园蚕食鲸吞、步步渗透的过程,期间人类逐渐变成面目狰狞的征服者,自然则变成了所谓的资源,因此这一过程同时伴随着人的异化和自然的物化。但是,作者并未放弃希望,因为有昆尼这样寄托着作者生态乌托邦理想的人物在:儿时的昆尼天真烂漫,会同海豚说话,能在海贝里听到上帝的声音;成年的她虽然被安吉勒斯小镇的人们视为怪人、异端,但是由于童年起便与鲸鱼相伴嬉戏的个人经历,昆尼终于成长为一位勇敢的环保卫士。正如《浅滩》中环境保护者弗勒尔所说:“我们的未来在于物种之间的交流,在于与环境共存。”温顿希望人与自然可以进行交流,和谐共生。
值得一提的是,《浅滩》的续篇短篇小说《游泳》继续着这种对社会开发的工具理性批判。当昆尼一行回到外祖父的农场时 (现在归普斯特林所有),看到的是普斯特林开发理念造成的恶果:土地被过度放牧,变得沟壑纵横;农场大门口赫然挂着一个告示牌—— “禁止穿越,射杀袋鼠中,请勿靠近”。昆尼儿时的天堂现在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虽然捕鲸业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社会开发的脚步并未停歇,在“城市海滩”上,有钱人正在为美国游客修建滨海旅馆。克里夫说:“他们在撕碎我青春的源泉。”他们六岁的女儿点点说:“他们把一切弄得乱七八糟。”[9]76旅游开发正以不可逆转之势继续着,生态保护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工具理性也助长了人类的征服欲望。在围绕着捕鲸—护鲸这一主线,作者还别出心裁地穿插了特德·贝尔捕鲨的辅线。特德·贝尔试图要在安吉勒斯捕到世界上最大的鲨鱼,要破1 900磅的纪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最终捕到了一条2 700磅的大白鲨。然而,贝尔的成功并非偶然。表面上,人类又一次征服了海洋里最凶猛的生物鲨鱼,满足了人类无限膨胀的征服欲望。但是,之所以引来巨鲨,是因为安吉勒斯拥有捕鲸产业,是捕鲸活动的血腥引来了大批的鲨鱼前来光顾。设计特德·贝尔捕鲨的次要情节,不仅彰显了温顿对人类征服欲望的批判,而且强化了生态保护主题。特德·贝尔破世界纪录的捕鲨活动正值小镇成立150周年的纪念活动,人们复制早年的捕鲸船“奥农”号,进行旅游促销,欢迎女皇来访,在沸腾的庆祝活动中,读者分明听到了丧钟在鸣,为鲸,为鲨鱼,更为执迷不悟的人类自身。因为在一派歌舞升平的闹剧的背后,是人们深陷危机而不自知的愚蠢。人类的征服欲望永无满足之时,这样的欲望在现代危机四伏的生态环境中显得荒谬。在现代化武器协助下,人类似乎愈加强大,但作为自然界的一种生物其面目却愈发狰狞,人类欲望膨胀导致疯狂地掠夺自然,导致扼杀人的灵魂和美好天性,人类再也没有闲情逸致享受诗意的栖居。
四、对土著生态智慧的借鉴
温顿充分意识到土著文化的价值和重要性,并在多部小说中融入了土著元素。如在《云街》中,有位神秘的土著人物时常出现,给彷徨中的费希指点迷津。又如,在《土乐》中他更是让主人公鲁按照土著人的方式,在“地图外”而不是在“地图上”行走,即摒弃对现代文明的产物——地图的依赖,仅靠一支低音风笛、一根钓鱼线过简朴的荒野生活。历经生存考验及自然的锤炼,鲁受伤的心灵逐渐康复了[10]313-314。
当被问及比起西方文化来他是否与土著文化更接近时,温顿回答:“我应该说比起我的苏格兰祖先来,我离土著文化更近,我已经学会离这块土地更近,但这几乎不能与真正的土著意义上的归属相比。我羡慕土著人与大地及部落神灵的同一性。”[11]107景观在温顿的小说中的重要性不亚于其中的人物,因此温顿也被称为“景观作家”。在他的小说中反复表达了文学与景观间的紧密关系,景观被赋予了他个人的特质。他对空间景观的探讨方式常常使人想起澳洲土著文化,特别是土著人有关人属于地球的理念[11]101。
对土著人来说,不是土地属于你,而是你属于土地。土地不是你的家园,它是你的偶像,你的圣地,你的脐带之地。与土地分离就意味着被置于地狱的边缘,卡在生死之间[12]21。温顿吸收了这种价值观,《浅滩》中昆尼能在海洋中自由地游泳,连他的丈夫克里夫都不禁觉得她“不该生为陆地哺乳动物”[3]4,她六岁的女儿也是在学会说话之前就会游泳了[9]76,因此你不得不产生她们是属于海洋的想法,而不是相反。而昆尼对安吉勒斯故土的眷恋更是刻骨铭心。环保活动失败后,昆尼作为一个失败者、甚至弃儿,带着深深的遗憾被迫离开自己深爱的家乡。在《游泳》中:阔别七年后,昆尼和丈夫回到了安吉勒斯小镇,并且带了女儿点点来朝拜自己的圣地,来延续这种与故土的难以割舍的脐带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昆尼才能继续正常地生活。
澳洲土著文化的基础信仰是泛灵论。泛灵论的文化信仰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相信现象世界是活生生的世界;二是相信非人类世界不仅是活生生的,而且到处是能够与人交流的言说主体。在泛灵论的社会中,道德关怀涵盖的不只是上帝、天使、圣人以及其他人,也涵盖其他存在物,一切存在物都有神性。这与利奥波德提出的“大地伦理”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借鉴土著生态智慧是因为泛灵论社会几乎毫无例外地避免了环境灾难[1]61-62。温顿对白人恣意开发澳洲西海岸的行为深感不安,如《游泳》中所述,他无法容忍看到沙岸上的起重机、钢铁架子、建筑工人和地上可怕的伤口[9]76。温顿把这种对工具理性开发的质疑与自然的敬畏融入字里行间,在温顿看来,海滩的破坏仿佛是在自己的躯体上开挖出大洞,令人感到切肤之痛。而这正契合了土著文化的生态思想:土著人认为总是对土地做着什么将会导致恐怖的后果,而这正是白人来到后一直在做的事情[12]21。
西方生态批评学者认为,从根本上说,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反映的正是西方文化的危机,西方文化要实现自救,就必须放弃殖民心态,虚心向其他边缘化、受压制的文化学习生态智慧,反省自己的进攻性、侵略性行为[1]297。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澳洲兴起了一股土著文化热,白人主流文化对土著文化的态度开始改变,许多有识之士开始认真研究土著文化,解读其古老而深刻的智慧,而作者生活的西澳又恰巧是土著文化研究与保护做得较好的地方,土著文化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土著文化里万物有灵,人类要负责照看好本部落的土地及万物。在土著部落的交际网络里,人类与自然亲密无间,充分了解与其共生的万物,能与之进行交流[13]300。于是《浅滩》中儿时的昆尼可以与海豚说话,《云街》中猪开口说话了。温顿小说中的人物大多不善言辞,但却能与大自然进行无障碍沟通。可见,交流未必要通过人类语言这个单一渠道进行,人类不应因为拥有语言能力就在“伟大的生命之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中凌驾于其他生物之上。因此,工业社会的人类的确能从土著文化那里获得灵感,从而做到对自然界的互联、互惠交往模式做出反应,滋养自己的生命,也滋养万物的生命[13]300。温顿借鉴土著文化中充满生态关怀的价值观念,希望劝说人类放弃把自然及其他存在物当成沉默的他者的做法,自然的主体性是土著人和西方人可共同参与的建设性对话领域[14]57。面对众声喧哗的自然界,人们应该心生敬畏与尊重,从而找到拯救之路。
五、结束语
雷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控诉了DDT等化学农药在大地上甚至天空中的荼毒生灵,进而指出是人类一手毁掉了有声有色的春天,使一切归于死寂。温顿在《浅滩》中则控诉了人类将海中的鲸鱼猎杀殆尽的罪行,暗示出如果不采取措施人类又将一手制造出另一个生态悲剧——寂静的海洋。为了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作者在文本中不惜笔墨再现了工业捕鲸、解剖巨鲸的血腥场面以及群鲸集体自杀的悲壮场面,令人不得不去思考该怎样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重大命题。在《浅滩》中温顿通过对基督教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对现代捕鲸工业的批判、对社会开发的工具理性批判表达了他反对人类以任何理由为借口大肆捕鲸,致使浅滩真正的主人座头鲸、露脊鲸、鲨鱼等大型海洋生物濒临灭绝的环保理念。最后,通过借鉴澳洲土著文化中充满生态关怀的价值理念,温顿表达了自己的生态伦理思想,希望启迪深陷生态危机的人类找到拯救之路。总之,这部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以环保为主题的小说为安吉勒斯小镇完成从捕鲸业向观鲸旅游业的华丽转身吹响了号角。各物种间平等交流,和谐共生,是温顿本人,也是全世界具有生态意识人士共同的生态理想。
[1]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王诺.欧美生态文学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蒂姆·温顿.浅滩 [M].黄源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4]Turner J P.Tim winton’s shallows and the end of whaling in australia [J].Westerly,1993(1):79-85.
[5]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476.
[6]Willbanks R.Shallows[J].World Literature Today,1995,69(1):221.
[7]任重.全球化视阈下的生态伦理学研究述论 [J].生态环境学报,2012,21(6):1184-1188.
[8]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88.
[9]Winton T.Mininum ofTwo[M]. Camberwell:Penguin Books Australia Ltd,1998:76.
[10]Jacobs L.Tim Winton and West Australian Writing [M]∥Nicholas B,Rebecca M.A Companion to Aus lit since 1900.New York:Camden House,2007:307 -320.
[11]Ben-Messahe S.Mind the Country—Winton’s Fiction[M].Crawley:University ofWestern Australia Press,2006.
[12]Butstone D.Spinning stories and visions [J].Sojourners,1992,21(8):21.
[13]Rose D.An indigenous philosophical ecology:situating the human [J].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2005,16(3):294 -305.
[14]Prigogine I.The End of Certainty:Time,Chaos,and the New Laws of Nature[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