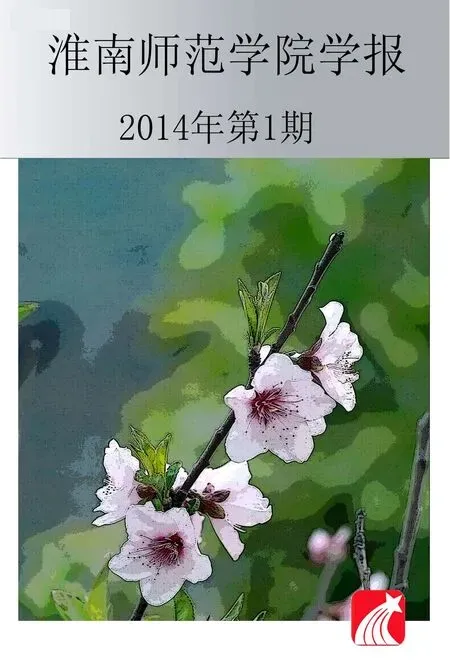管宁“清声远播”与“不为守高”之悖论探析
——兼谈汉末魏初士人的仕与隐
杨霞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安徽合肥 230022)
管宁“清声远播”与“不为守高”之悖论探析
——兼谈汉末魏初士人的仕与隐
杨霞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安徽合肥 230022)
汉末魏初高士管宁以清虚自守、激浊笃行而清声远播,同时,他又受到来自上层统治者的调查,并得到“不为守高”的另一种评价,帝王对其的征用与犹疑是这一悖论产生的深层动因。面对仕与隐、生与义的传统命题,以管宁为代表的汉末魏初士人开辟了一条隐身民间以行义的新路径。
管宁;悖论;仕;隐
“汉末魏晋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①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8页。受儒家经世思想熏染的汉末魏初士人处在这样一个大变革时期,思想上发生重大转变,部分士人远离政治,独守一隅,忘怀得失,然而却无法真正、完全独立于政治之外。管宁就是这样一位高士、隐士,在其时声名远播。朝廷屡次征召,管宁坚守不出,最终引起高层对其思想动向的怀疑与考察,也带来对管宁的另一种评价。管宁的行为举止及其社会评价虽属个例,但其中包含着复杂的时代文化信息,值得深入讨论。
本文即尝试从关于管宁的两种不同评价入手,分析其成因,并对以管宁为代表的汉魏易代之际的士人在仕、隐问题上的认知做一初步考察。
一
管宁生于158年,卒于241年,一生历经东汉桓帝、灵帝、献帝与魏文帝、明帝、齐王芳数位帝王,正值乱世。管宁一度避乱辽东37年,在当地谈祭礼、治威仪、明礼让,为人“渊雅高尚,确然不拔”②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66页。下文注释出处相同时,仅标书名及页码,其他引书亦同。,时人多慕其风。他的名望在汉末魏初这一时段的荐书与诏书中得到了较为清晰的展示。司空陈群称管宁“行为世表,学任人师,清俭足以激浊,贞正足以矫时”,乃“昭明古今,有益大化”之人③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197页。。魏明帝颁诏称管宁“耽怀道德,服膺六艺,清虚足以侔古,廉白可以当世④陈寿:《三国志》,第356页。。”大司农桓范赞管宁“于混浊之中,履洁清之节,笃行足以厉俗,清风足以矫世。”他还作书于管宁,表达了“清声远播,顽鄙慕仰”的心情⑤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258页。。太仆陶丘一、永宁卫尉孟观、侍中孙邕、中书侍郎王基联名推荐管宁,称其“总九德之纯懿,含章素质,冰洁渊清,玄虚澹泊,……清高恬泊,拟迹前轨,德行卓绝,海内无偶。……览其清浊,未有厉俗笃行若宁者也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301页。。”
避乱辽东时,公孙度(时辽东太守,占据一方)
管宁固守不出,其志愈坚,其名愈显,但也招致了魏明帝的不满。这种情绪在明帝的几次诏书中依次递进。
明帝初即位,下诏征管宁为光禄勋时就已透出对管宁“黄初以来,征命屡下,每辄辞疾,拒违不至”的失望之情,诘问管宁:“岂朝廷之政,与生殊趣,将安乐山林,往而不能返乎!”暗示管宁需在朝廷之政与山林之乐中重做选择,并“望必速至,称朕意焉”。语气尚温和。
随后,明帝诏问青州刺史,言管宁“违命不至,盘桓利居,高尚其事”的不仕行为已“失考父兹恭之义”,并质疑其“澡身浴德,将以何为”,要求刺史派遣别驾从事郡丞掾“以礼发遣”。这一诏书在责怪管宁居地之刺史办事不力的同时对管宁不仕已有不满情绪。
朝廷“自黄初至于青龙,征命相仍”,管宁依旧不出。明帝于是诏问青州刺史程喜:“宁为守节高乎,审老疾尩顿邪?”在此之前,管宁屡次辞命,皆以身体不适为由。如辞魏文帝所诏太中大夫一职,言“内省顽病,日薄西山”;辞魏明帝光禄勋一职,则言“年疾日侵,有加无损”。管宁究竟是身体有恙无法入朝做官“以隆斯民”,还是为前朝守节、不愿为新王朝效命?皇帝对管宁不能出仕的理由起了疑心。
青州刺史程喜复命明帝,他转引管宁族人管贡之言:
宁常着皂帽、布襦袴、布裙,随时单复,出入闺庭,能自任杖,不须扶持。四时祠祭,辄自力强,改加衣服,着絮巾,故在辽东所有白布单衣,亲荐馔馈,跪拜成礼。宁少而丧母,不识形象,常特加觞,泫然流涕。又居宅离水七八十步,夏时诣水中澡洒手足,窥于园圃。①上述引文皆出自陈寿《三国志》,第354-358页。
管贡的描述有这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对管宁的着装做了较为仔细的描述:冠黑帽,着布衣,祭祀时穿过去在辽东时所穿的白衣。“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②孔颖达:《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61页。——管宁生活简朴、按规矩着装。二是对管宁的身体状况有描写:“辄自力强”、“能自任杖,不须扶持”——身体尚可,但已是垂垂老矣。三是对管宁的礼节、礼仪有描述:“四时祠祭”,“亲荐馔馈,跪拜成礼”——延续其在辽东“谈祭礼、治威仪、明礼让”的一贯作风。四是对母亲的思念:“常特加觞,泫然流涕”——管宁每逢祭祀流泪,乃是为母亲(非为前朝)。经过管贡的描述,一个清俭出行、厉俗笃行的高士形象就呈现在明帝眼前。而程喜特地转引管贡言论,正是表明这一调查结果的可信度。并且,程喜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管宁屡次辞让,“独自以生长潜逸,耆艾智衰,是以栖迟,每执谦退。此宁志行所欲必全,不为守高”。③陈寿:《三国志》,第358页。
一方面,管宁因其清高的品性得到了上层统治者的褒奖与征用,另一方面他又因同样的原因招致了帝王的疑猜。帝王究竟是器重积极进取、委身仕途的入仕者,还是更亲睐安居乐道、清贫守业的无为者,这导致了在逻辑学上可以同时推导出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即悖论的产生。
二
管宁“清声远播”与“不为守高”是基于同一质素“清高”所引发的两种不同评价。有关这一悖论的成因可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1.管宁坚守不出是悖论的缘起,个体的禀性、经历是重要内在原因。历史上关于他的“割席断交”、“锄园得金”的故事体现了他天生淡泊名利的气质。而避乱辽东时,公孙家族(度、康、恭、渊)父子兄弟间的尔虞我诈,以及后来为曹丕所殄灭,“辽东之死者以万计”④陈寿:《三国志》,第358页。的政治攻伐对管宁的仕隐选择应该也大有影响。
对管宁不仕的认知,还可结合另两位同时期士人华歆、邴原的政治经历来加深理解。三人一起游学,彼此交好,“时人号三人为‘一龙’”。⑤陈寿:《三国志》,第402页。三者皆有才华,但个性有别,在仕隐选择上也各有不同。
华歆(157年—232年),汉时,先“为吏,休沐出府,则归家阖门”,后“举孝廉,除郎中,病,去官”,灵帝崩,何进辅政,歆“为尚书郎”,后太傅马日磾辟歆为掾,再被拜豫章太守;一度为孙策谋划;后曹操征为议郎,“拜议郎,参司空军事,入为尚书,转侍中,代荀彧为尚书令”,后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国,封安乐乡侯。及践阼,改为司徒”;“明帝时,“进封博平侯”,“转拜太尉”。曹丕称他为“国之俊老”,曹睿赞其“深虑果计”。⑥陈寿:《三国志》,第401-405页。
邴原(生卒年不详),“少与管宁俱以操尚称,州府辟命皆不就。”时孔融为北海相,“举原有道。原以黄巾方盛”,遂至辽东,“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①陈寿:《三国志》,第350页。后依次辟为曹操司空掾、五官将长史。太祖征吴,邴原随行,途中去世。邴原的仕途生涯并不长,且出仕期间,“躬履清蹈,进退以道”②陈寿:《三国志》,第366页。(陈寿语),以“合葬,非礼也”拒绝曹操将其子与邴原女合葬的要求,以“父也”回答曹丕“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的两难选择题。时人(崔琰)评价其“清静足以厉俗,贞固足以干事”③陈寿:《三国志》,第351-354页。。连“心不安之”的公孙度也谓邴原乃“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罢也”④朱碧莲,沈海波译注:《世说新语》,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97页。,可谓得其实也。
在辽东期间,邴原清议格物,引起公孙度猜疑,管宁曾这样劝诫邴原:
潜龙以不见成德,言非其时,皆招祸之道也。⑤陈寿:《三国志》,第355页。
从中颇能看出管宁对时局的把握与对士人与政治关系的理解。身处乱世,士人应保全自身,放低姿态,成就德行。可见,管宁既不似华歆游刃于政治,如陈群评价华歆“清而不介”⑥陈寿:《三国志》,第404页。(清廉却不固执)那般,也不似邴原耿直清议,以言招祸,他选择的是远离政治,潜行民间,化民成俗。
2.评议管宁者的视角、立场不同是悖论生成的主要原因。可从民间与官场两个角度进行理解。
一是民间评议者,他们的品鉴基础是以家庭道德为中心的社会舆论。管宁居于辽东时,“(公孙)度安其贤,民化其德”。乡人眼里的管宁是个能礼化风俗之人,其所在村落,“会井汲者,或男女杂错,或争井斗阋。宁患之,乃多买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来者得而怪之,问知宁所为,乃各相责,不复斗讼。”“邻有牛暴宁田者,宁为牵牛着凉处,自为饮食,过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惭,若犯严刑。是以左右无斗讼之声,礼让移于海表。”⑦陈寿:《三国志》,第354-355页。“每所居姻亲、知旧、邻里有困穷者,家储虽不盈担石,必分以赡救之。”其“醇德之所感若此”⑧陈寿:《三国志》,第360-361页。,焉能不清声远播?
二是官场中人,即陈群、桓范乃至后期齐王芳时期的陶丘一、王基等人。陈群,九品中正制的创始人,出身名门,历仕曹操、曹丕、曹叡三朝,重规矩礼仪。曹睿爱女去世,丧礼过度,陈群进谏劝阻,“愿陛下抑割无益有损之事”;后朝廷营治宫室,“百姓因而尽失农务时利”,陈群亦进言,言“丧乱之后,人民至少”、“边境有事,将士劳苦”。⑨陈寿:《三国志》,第636页。《三国志》评价陈群“动仗名义,有清流雅望”⑩陈寿:《三国志》,第653页。。桓范其人,在历史上亦以清廉节俭见称,以有文学与王象等典籍《皇览》,著《世要论》。这些本身都是名士的官吏,在推荐同道中人时皆不遗余力。
作为对管宁作出“不为守高”结论的观察者与评价者,程喜值得关注。关于程喜为人,史书记载不多,他在明帝时期任青州刺史,在齐王芳时期为征北将军。《三国志田豫传》记载这样一件事:
初,豫以太守督青州,青州刺史程喜内怀不服,军事之际,多相违错。喜知帝宝爱明珠,乃密上:“豫虽有战功而禁令宽弛,所得器仗珠金甚多,放散皆不纳官。”由是功不见列。11陈寿:《三国志》,第728页。
陈寿评价田豫“清俭约素”12陈寿:《三国志》,第729页。,与他对立的程喜却对其“多相违错”,且其为人善察言观色,很清楚地知道明帝的好恶,知道从哪个角度可以令田豫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可以推想,他受命调查管宁的不仕原因,心理很是明白明帝的隐忧。他评价管宁“不为守高”可以看做是深谙帝王狐疑心理的表现,也可以看做他对管宁的暗中相助。元末明初戴良有《和陶渊明杂事》一诗,其中提到,“东汉有两士,幼安与程喜。爰得交友心,知音乃余事。”13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二十四),见《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幼安是管宁的字,戴良认为程喜正是管宁的知音,是他尽力维护了管宁的“志行”之全。
3.帝王的用疑。在中国古代人治社会中,帝王的态度直接影响或决定短期的政局,更决定着士人的命运。
曹操平定北方后,“士人靡然归之”,荀彧“为之经营谋虑,一旦小异,便为谋杀”,孔融“每所论建,辄中操意,况肯为用,然终亦不免”①孔凡礼点校:《管幼安贤于荀孔》,《苏轼文集》(卷六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19页。,尚有“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崔)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②陈寿:《三国志》,第370页。关于曹丕对士人的用与察,汪春泓先生曾撰文指出“汉末士人起而挽救汉刘政权的命运,大肆讲政治道德和原则,自然就潜伏着冲突的危机”,因此,“曹丕独表徐干‘有箕山之志’,推崇徐干式以文章‘经国’”,意在“引导士风,当他推行改朝换代的重大举措时,亦令士人无意干预时政。”③汪春泓:《吴质〈答魏太子笺>笺说》,《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第135页。这是对帝王、士人、文学、政治复杂关系的新解读,极具启发意义。
曹魏时期,不惟管宁受到了暗查,其他屡征不就的士人也会得到上层的注目。齐王芳正始年间,与管宁同时期的隐士胡昭被大臣荀顗、黄休、庾嶷联名举荐,史书有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记载:
有诏访于本州评议,侍中韦诞驳曰”礼贤征士,王政之所重也,古着考行于乡。今顗等位皆常伯纳言,嶷为卿佐,足以取信。……昭宿德耆艾,遗逸山林,诚宜嘉异。”乃从诞议也。④陈寿:《三国志》,第363页。
一个“驳”字反映了在当时官场对胡昭是否嘉奖、是否征用还是存有不同的声音。这也间接表明了高层的意见,即对隐士的征辟与否。
综上,无论程喜言管宁“不为守高”究竟是据实以告还是有意维护,都改变不了这一悖论生成的事实。管宁不仕是悖论生成的导火线,时人不同视角、立场造就了悖论的内容,而帝王的用疑之间则是悖论成型的深层动因。
三
汉末魏初时局动荡,“人士流移,考详无地”⑤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58页。,但是绝大部分士人依旧在传统“士志于道”的儒家观念的影响下委身官场,无论是察举还是征辟,都造就了一大批当官的士子。就察举而言,即令曹操本人,也是先得乡里评议,后举孝廉为郎,出任地方官,再进入中央权力核心。荀彧也是先举孝廉,董卓为相辄弃官归乡,后投奔曹操,为其出谋划策,名重一时,有“荀令君”之称。从征辟来看,陈群早年被刘备辟为豫州别驾,司马懿被曹操辟为文学掾,戏志才、郭嘉被荀彧荐举等。这些都是士人进入仕途的各种途径。当时士人大多走的还是这样一条西汉武帝为天下士人开启的通经致用的利禄之途。
同时,汉末魏初士人相对于先前士人的仕隐而言,又具有这一时代的特质:大多都有先学后游、先隐后仕的经历。(这与其时流行的游学之风,党锢、清议造成的激扬名声、互相题拂之风有关)。一代名相诸葛亮,始躬耕南阳,心怀天下,与刘备隆中对策,后辅助刘备、刘禅两代君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汉末思想家仲长统“年二十,游学青、徐、并、冀”,先是避地上党郡,“每列郡命召,辄称疾不就。⑥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43-1644页。后被尚书令荀彧举为郎,一度参与曹操军事谋划。荀彧死,“复还为郎”⑦陈寿:《三国志》,第620页。,卒于曹魏代汉之年。被曹丕誉为“彬彬君子”的徐干,少年专志于学,“轻官忽禄,不耽世荣”⑧陈寿:《三国志》,第599页。,曹操辟之,称病不就,“潜身穷巷,颐志保真”,“并日而食”⑨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360页。。后见曹操平定北方,即应诏出仕,历数年,又以疾辞归。国渊,先避世乱与管宁等渡海至辽,后返回中原被曹操辟为司空掾,辅助曹操推行屯田制,为官敬业,后任太仆,位列九卿。张范,出身名门(祖父为汉司徒,父为太尉),然“恬静乐道,忽于荣利,征命无所就”,后被曹操辟为议郎,“参丞相军事,甚见敬重”⑩陈寿:《三国志》,第337页。。这些士人,无论是仕是隐,都保有一份心忧天下的士子情怀。
还有一部分与管宁做相同选择的终身不仕者。王烈,与管宁同时渡海至辽,屡次被举,然终身不仕,而“东域之人,奉之若君”11陈寿:《三国志》,第356页。。与管宁同时期的隐士胡昭,避地冀州时即“辞袁绍之命”,后曹操任司空时“频加礼辟”,胡昭应命前往,面陈心意,欲躬耕乐道、经籍自娱。隐士焦先,“见汉室衰,遂不语。露首赤足,结草为庐,食草饮水,饥则为人佣作,不冠不履,魏国建立,太守贾穆、董经均往探视,与食不食,与语不语。”12陈寿:《三国志》,第362-364页。他们是真正的疏离政治之人。
选择不仕的士人的生活方式又可分为不问世事与不涉政治两种,前者是对包括政治在内的所有世俗事务的漠然,如彻底隔绝人事的焦先;而后者仅是对政治的回避,如化民成俗的管宁。管宁的清誉正是与“激浊”、“厉俗”、“矫世”、“笃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东汉盛行奢侈之风,汉末尤甚。而管宁身处乱世,却秉持朴拙本性,“年十六丧父,中表愍其孤贫,咸共赠赗,悉辞不受,称财以送终”,后至辽东则“庐于山谷,凿坏为室”①陈寿:《三国志》,第354页。,“环堵筚门,偃息穷巷,饭鬻糊口,并日而食,吟咏《诗》、《书》,不改其乐”②陈寿:《三国志》,第359页。,正是出尘不染的隐士气节与名士风度。此外,管宁有感“衰乱之时,世多妄变氏族者”,叹其“违圣人之制,非礼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论》,“以原本世系”。③陈寿:《三国志》,第360页。可以说,管宁虽不涉政治,却在民间实现了士的“社会良心”的身份和“志于道”的理念。
“社会良心”尚有“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④范晔:《后汉书》,第2226页。的社会名流郭泰,还有以著述传道、成就经学一统的经学大师郑玄等。往者士人有“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附庸、附属思维,而到了汉末魏初,士人厘清现实,已经明显感受到国家与社会的分野,并日益突出士人在社会层面的作为。许倬云先生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变化时,曾提出“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民间社会与社会公众领域是否存在”这一命题,并以殷商至秦汉为时代范围对此期“国家”与“社会”的变动关系进行了考察。他这样描述秦汉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一步一步收夺了社会资源,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但社会力中一股代表知识资源的力量则寄托于国家权力结构,壮大了这一股力量。知识分子群内部的质变及分化,也使这一股社会力发展为复杂的性格。”⑤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的变动》,《文物季刊》1996年第2期,第75页。其中,依托于国家权力机构的力量是选择“仕”的一群士人,而导致社会士人群体呈现复杂性格的力量正是选择“隐”的另一群。
造成管宁“清声远播”与“不为守高”之评价悖论的深层原因是帝王的用疑,而帝王的用疑来自对管宁政治立场的考察,在明帝看来,不仕意味着不合作,不合作意味着对现行政权不满。而管宁以其躬身民间之大有为化解了明帝的疑惑。他以乞骸骨为由规避政治,却在民间身体力行,感化世人,“以隆斯民”。,以至于管宁耄耋之年,朝廷依旧“特具安车蒲轮,束帛加璧聘焉”⑥陈寿:《三国志》,第360页。。
苏轼曾将管宁的这种“隐”与另外两位同时期大名士荀彧、孔融的“仕”相比较。他认为曹操父子乃“穿窬、斗筲”之人,而荀彧、孔融犹为之经营谋虑,后果为诛杀;而管宁“怀宝遁世,就闲海表”、“终身不屈,即不得而杀”。故而,管宁“贤于文若、文举远矣。”⑦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19页。
苏轼的评判标准是几位贤士的生死结局。事实上,士人的仕隐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生死问题。或可进一步言之,士人在仕隐之间来回选择,反复思量,其痛苦就是来自“济世行义之志与乱世生存欲望的冲突”⑧胡秋银:《试论郭泰之不仕不隐》,《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1期,第41页。,亦“生我所欲,义亦我所欲”的古老命题的重现。当两者不可得兼时,是苟全性命于乱世,还是但求闻达于诸侯?或者,还有一种更为通融的做法,即隐于民间社会以求生,却不忘激浊、笃行以行义。管宁即是如此。钱穆先生曾说,三国人物,管宁第一。⑨钱穆:《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讲,北京:三联书店,第105页。原文“管宁在当时,实是一无表现。但论三国人物,管宁必屈首指”。从这一角度来看,非张大其词也。
A study of the paradox abou t Guan Ning's assessm en t——A concurrent discussion on the scholars'choosing their careersbetween Han and W eidynasties
YANG X ia
Guan Ning,who was living between Han and Wei dynasties,had a good reputation for his behavior.He was investigated by the governor at the same time and got the different assessment.The emperors'trust and distrust was the deep reason of the paradox.Facing the choice of being an official or not and the choice of life or moral principle,the scholars between Han and Wei dynasties opened up a new route of hiding themselves and achieving something valuable,and Guan Ning was the exponent.
Guan Ning;paradox;official;hermit
K236.1
A
1009-9530(2014)01-0070-05
2013-11-22
安徽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建安时期书体散文研究”(2011sk525)
杨霞(1978-),女,安徽大学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汉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虚馆以候之”,而管宁“既往见度,乃庐于山谷”。曹操拜司空,一度“辟宁”;魏文帝黄初四年(223年),“诏公卿举独行君子,司徒华歆荐宁”,“诏以宁为太中大夫”;黄初七年(226年),文帝崩,明帝即位,“太尉华歆逊位让宁”,“司空陈群又荐宁”,则“以宁为光禄勋”。而所有这些征召都遭到了管宁的“固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