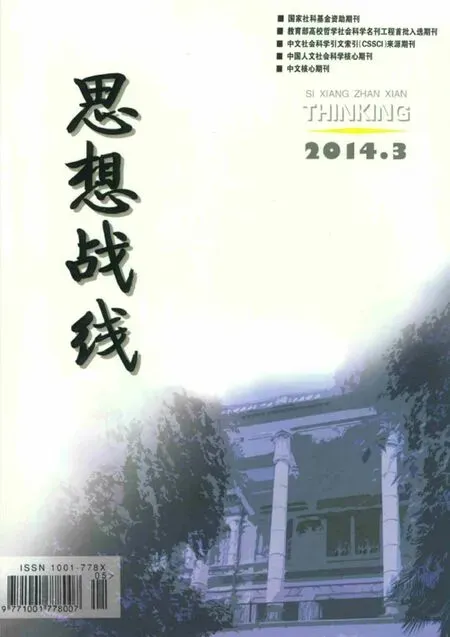亲密的生命政治
——家庭权责主体与精神卫生立法
马志莹
一、引 言
2013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作为我国历史上首部全国性精神卫生立法,该法把家庭作为照料精神障碍患者的主体,赋予家属对患者实行非自愿住院和对治疗知情同意的权利,同时也规定了其看护管理患者并为伤人患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义务。[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http://www.gov.cn/jrzg/2012-10/26/content_2252122.htm,2013年4月14日。相比之下,许多国家的精神卫生立法把知情同意权交给患者个人,把非自愿住院的决定权交给公权力,把照料责任行政化或市场化。因而,中国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属所具有的巨大责任与权利,实为中国精神卫生立法的一大特色。[注]谢 斌等:《精神卫生立法的国际视野和中国现实——来自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的观点》,《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1年第10期。
从1985年开始准备立法到2012年《精神卫生法》最终出台的过程中,家庭在精神医疗实践中的卷入虽然不断持续,却也越来越备受争议。那么,《精神卫生法》作出承认和建构家庭主体性地位的历史性选择,其可能性条件是什么?这种选择如何揭示和建构社会转型时期的公私关系?从《精神卫生法》管中窥豹,我们应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生命政治、亲密政治与大政治的缠结?
讨论上述问题的基础,是笔者对家庭在《精神卫生法》中角色的解读。笔者从2008年开始以人类学视角研究中国的精神卫生体系,走访过多家精神卫生机构,采访过《精神卫生法》的立法者、公益律师、基层精神卫生工作者、患者和家属,也出席过医学界与法律界关于《精神卫生法》的辩论。本文将结合这些访谈和田野观察的资料,[注]对于立法者等公众人物和已被媒体实名报道的精神医疗案件当事人,本文使用其真名;对其他被访者和精神医疗机构,本文采用匿名处理或集体报告。以及媒体和学术出版物中关于立法和精神卫生的评论,分析精神卫生法律改革中关于疾病、个体、家庭、公共的话语想象及其历史性,从而理解亲密的生命政治在当代中国如何可能。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精神卫生立法的过程长达27年,但这一过程很少受到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的重视。直到本文最终稿成形之际,在“中国知网”使用“精神卫生立法”作为关键词查阅,可找到352篇论文,其中仅有两篇社会学论文,而人类学者撰写的论文数量为零。在两篇已经发表的社会学性质的文章中,一篇关注“被精神病”的问题,另一篇关注城市化进程与精神病的关系。[注]储鹏飞,殷 帆:《“徐武事件”的媒介呈现——以<南方都市报>“徐武事件”的社论为例》,《东南传播》2012年第8期;张广森:《社会学视角下的城市化进程中精神疾病现况探析》,《医学与社会》2011年第12期。鉴于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十分关心的家庭责任及家庭关系问题在中国精神卫生立法中占据关键地位,笔者认为有必要剖析中国精神卫生法如何将家庭确立为送治、照料、监管精神障碍患者的权责主体。
二、生命政治、亲密政治与大政治
上文中笔者提到的“大政治”是指狭义的、大写的政治(Politics with a big P),即政府、政党组织和管理国家的活动与政策,包括这种组织管理的合法性、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与此对应的是广义的、小写的政治(politics with a small p),即遍及日常生活各方面的权力关系,包括权力主体、对象、手段多元。例如,福柯曾指出,在现代国家中,生命政治——即凭借医药、科技等手段对生命和生物体实行无孔不入的规训、控制——成为了重要的治理机制。[注]Michel Foucault,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ége de France,1975~1976,David Macey (trans.),New York:Picador,2003,p.239.既有关于生命政治的研究往往集中于生物化的个体和统计学意义上的人口如何作为治理对象出现,[注]例如,关于生命政治在中国的兴起及其中个体与人口的关系,请参见Ruth Rogaski,Hygienic Modernity:Meaning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pp.300~306.却少有研究关注家庭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医学、法律等学科对家庭作为治理单元的建构。这样的忽视未免让人遗憾。
从本文将分析的精神卫生法中可看出,家庭是生命政治同时塑造生物个体和公共安全、管理人口秩序的关键节点。[注]家庭在生命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也可见于计划生育制度,请参见Susan Greenhalgh,Just One Child:Science and Policy in Deng’s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p.27.以及Ann Anagnost,“A surfeit of bodies:population and the rationality of the state in post-Mao China”,In F. Ginsburg&R. Rapp (Eds.),Conceiving the New World Order:The Global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p.22~41.本文关注生命政治对家庭的形塑,并把治理过程对家庭形态、家庭关系的塑造及其效果称为“亲密政治”。[注]“亲密政治”(intimate politics)这一概念散见于各种女性主义论著中,含义略有差异,其中最接近本文所使用意义的是Sara Friedman,Intimate Politics:Marriage,the Market and State Power in Southeastern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3.而且,与一般关于生命政治的研究忽视意识形态的作用不同,笔者认为家庭在个体和社会之间的枢纽作用使得它常被转喻为整体社会文化的缩影,所以家庭在生命政治中的角色往往与大政治息息相关,关乎公共资源的安排,以及关于国家过去、现在、未来为何及应该如何的意识形态。本文正是要从精神卫生立法改革这一案例中,管窥当代中国生命政治、亲密政治和大政治如何相互影响。
格尔兹指出,“法律是地方性知识,而不是与地方性无关的原则,并且法律对社会生活来说是建设性的,而不是反映性的,或者无论如何不只是反映性的”。[注][美]克利福德·格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77页。追随这一阐释学的思路,本研究分析中国《精神卫生法》立法论辩过程,及法律条文中关于公私关系的地方性、历史性话语,探讨法律建构家庭权责主体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精神障碍患者处于“正常”社会的边缘,谁能界定这一边缘群体的组成,以及“边缘人”应被纳入社区还是送进机构、享有权利还是接受规训,关于这些问题的制度性安排,能揭示制度设计者和各方公众对社会发展,尤其是公私关系变迁的想象,并通过呼召理念和情感建构人们对于社会文化的认同。[注]Jan Hoffman French,“Dancing for land:Law-making and cultural performance in Northeastern Brazil”,POLAR:Political and Legal Anthropology Review,no.1,vol.25,2002,pp.19~36.因此本文选择法律这一棱镜来分析大小政治的交缠。
三、家庭、国家与精神医学
《精神卫生法》中“监护人”的出现达38处之多,[注]相关概念如“家庭”提及8次,“近亲属”提及6次。与家属这52次出场相比,各种公权力/公共部门的曝光就少得多,如各级“政府”提及40次,“社区”12次,“公安”4次,“法院/法庭”0次。法律定义“监护人”为“依照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可以担任监护人的人”,[注]《精神卫生法》第八十三条,http://www.gov.cn/jrzg/2012-10/26/content_2252122.htm,2013年4月14日。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其他近亲属;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四条,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06/content_4470.htm,2013年8月14日。即精神科医生及大众常称的“家属”。在《民法通则》中, 只有经法院宣告为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人才需要监护人。与之相较,《精神卫生法》没有规定行为能力宣告程序,反而以“患者或者/及其监护人”的提法,使家属自动成为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为患者承担了大部分的权利和责任。家属承担的责任包括看护管理患者,协助患者康复以及为患者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负担民事责任,等等。家属行使的权利则包括,将疑似精神障碍患者送往医院诊断,对医疗行为实行知情同意,以及——最备受争议的——决定患者非自愿住院。法律虽然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然而对有自伤行为或危险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是其非自愿住院的惟一决定人。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有伤害他人行为或危险的患者,虽然公安机关有权决定收治,但患者或监护人可以质疑决定、要求二次诊断;而被家属决定非自愿住院的自伤患者,法律没有提供任何司法救济的途径。[注]《精神卫生法》第三十到三十五条,http://www.gov.cn/jrzg/2012-10/26/content_2252122.htm,2013年4月14日。因而有精神科医生评价:“你可以打人,但你千万别伤自己。你一伤自己,你把你所有的权利都给了别人……,(这是)世界罕见的做法!”[注]引自唐宏宇教授在2013年全国精神病学伦理和法律问题学术研讨会上的口头报告。在我的田野调查中也有基层精神科医生表达过类似观点。
中国家庭这种“世界罕见”的重大权责并非自古如是,而是随着中国精神病学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逐渐形成和加强的。回顾中国精神医学史,我们发现关于个体、家庭、医学、公共的关系存在着其他话语可能。19世纪末,常年在广州行医的美国医学传教士嘉约翰(John Kerr)目睹当地家庭常以锁链或铁笼禁锢疯癫者、如同对待畜生般虐待疯癫者,评论道:“在一个父亲对其家庭拥有生杀大权的国度,一种轻易摆脱病入膏肓者的办法毫无疑问被采用了。”[注]John G. Kerr,“The ‘Refuge for the Insane,’ Canton”,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no.4,vol.XII,1898,pp.177~178.为了终止这一悲剧,1898年,嘉约翰在广州创办全中国第一家精神病院“惠爱医癫院”,积极倡导将患者视为仁爱的对象。医癫院的治疗宗旨是:“尽管这些病人疯癫,但他们仍然是人而不是禽兽。”[注]Charles C. Selden,“A work for the insane in China:the John G. Kerr Refuge for Insane,Fong Tsuen,Canton”,The Chinese Recorder,vol.XL(May),1909,pp.262~267.关于惠爱医癫院建立过程的介绍,可参见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5~87页。自此之后,作为如缕不绝的传统,中国的精神科医生(无论是传教士还是本土医生)一直把从家庭牢笼中解放疾病个体视为己任。2004年开始实施“全国重性精神疾病医院—社区一体化管理治疗项目”仍有“解锁”任务,力求发现家庭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关锁,并以住院治疗代替之。
惠爱医癫院成立之后,在北京(1906年)、苏州(1929年)、上海(1935年)等城市陆续出现了精神病院。这些精神病院为了在当地站稳脚跟,获得地方政府的“官方认同”,[注]Charles C. Selden,“The need of more hospitals for insane in China”,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1910,pp.325~330.就积极与当地警察合作。警察普遍认为精神病人是危险和暴力的来源,因而把危害他人或公共安全、在公共场合行为怪异的病人大量输送到精神病院中。与此同时,部分家庭固然也开始把患者送到医院以释放其内部压力。但出于对医院治疗的怀疑和对劳动力的需求等,家庭往往违背医生的建议,提前把自己或警察送治的患者接回家。[注]当时民国政府对精神病患者的收治问题并没有专门立法,北京警方允许精神病患者出院的相应法律依据是北平警务局的治安条例,其中包括家属请愿的规定。参见Francis L.K. Hsu,“A brief report on the police cooper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mental cases in Peiping”,in R. Lyman et al. (ed.),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Studies in Neuro-Psychiatry,Beijing:Henri Vetch,1939,pp.199~230.故民国时期至少在广州和北京的精神病院中,警察送诊的比例都超过家庭送诊的比例。[注]Neil Diamant,“China’s‘Great Confinement’? Missionaries, municipal elites, and polic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Mental Hospital”,Republican China,no.1,1993,pp.3~50.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受到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精神药理学、前苏联巴甫洛夫生理学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中国精神病学一方面认为精神疾病有其生理基础,需要药物治疗;另一方面强调精神疾病是旧社会压迫性的环境导致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残余,需要用革命思想教育来纠正。故治疗也强调社会多方面的参与,包括家庭、单位、地方政府或解放军官员等,他们都可以直接介入或把病人转介到医院。[注]John J. Kao,Three Millennia of Chinese Psychiatry,New York: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search in Asian Science and Medicine,1979,p.76.由此可见,在传教士试图打破父权家庭的牢笼之后,无论是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障碍都被视作对某种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或意识形态)的违背,其治疗都依赖社会各方——包括地方政府——的参与。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革命话语的隐退和生物医学的独尊,中国精神医学界越来越强调精神障碍是生物性个体的问题,从治疗实践上越来越依赖家属合作,这也成为《精神卫生法》赋予家庭重大权责的基础。当代精神病学知识认为,严重精神障碍特别是精神分裂症会干扰患者的思维和情感能力,使患者失去自知力——即对自己精神和障碍状况的认识。[注]Zhiying Ma,“Psychiatric subjectivity and cultural resistance:experience and explanations of schizophrenia in contemporary China”,In A. Kipnis (Ed.),Chinese Modernity and the Individual Psych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2,p.203~328.而中国精神科医生一般认为在患者不能自知时,家属能最亲密地了解其病史、关心其利益,因而在病史收集过程中多依赖家属的陈述。甚至为免刺激患者,精神医学教科书还要求病史收集时患者不能在场。[注]赵振环:《精神卫生和精神病防治技术培训教材·精神科临床技能操作手册》,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章第1节。相应地,在《精神卫生法》实施之前,保守估计50%以上的住院患者都是由家属决定将其送进医院实施非自愿治疗的,医生只提供诊断和治疗建议——该程序被称为“医疗保护入院”。[注]潘忠德等:《我国精神障碍者的入院方式调查》,《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3年第5期。另见Yang Shao, Bin Xie, Mary-Jo Good, & Byron Good,“Current legislation on admission of mentally ill patients in Chin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Psychiatry,no.1,vol.33,2010.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关于入院方式的调查没有全国性的数据。笔者在华南一家大型精神病院成人精神科做田野调查时,发现病区内90%以上病人都是家属送院的。不过,由于当时全国不少精神病院都有外出接诊的服务,所以家属多是委托院方派医务人员到家中以“精神抚慰”和“强行制服”的手段把患者带到医院。[注]宋合营:《京两家医院今起将不再外出接诊精神病患者》,《京华时报》,http://health.sohu.com/20070301/n248427333.shtml,2013年12月20日。另外由于“谁送来,谁接走”的惯例,患者出院的决定权也往往在家属手中。[注]黄雪涛:《被精神病因制度性歧视 忽视个人尊严》,《蓟门决策》第4期。以上种种实践,使一个家庭—机构圈在当代中国形成,联手塑造和管理生物性个体:精神医学机构通过家庭把医学知识渗透到日常生活中,而家庭则在此知识指导下监管其成员的心理和行为,把私人生活史乃至成员的人身自由交给专家,以期获得重新正常化的个体。[注]马志莹:《因爱之名,以医之义?从权利角度看精神病院住院女性的体验》,《残障权利研究》2014年第1期。另见Michel Foucault,Psychiatric Power: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1973~1974,G. Burchell (Trans.), J. Lagrange (Ed.),Basingstoke, Hampshire England,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p.125.
面对家庭在精神医疗中的高度卷入,公益法律界担心家庭滥用精神医学剥夺患者的权利、实现自身的利益。从2006年的“邹宜均案”到2012年的“陈丹案”,近年来不断有(曾)住院者在公益律师的协助下,控诉家属为利益或其他控制目的,而将正常的自己送进精神病院,并控诉医院与家属合谋剥夺自己的人身自由——即所谓“被精神病”。[注]何海宁,温海玲:《飞越疯人院之后——邹宜均案奇特收治程序在法庭受审查》,《南方周末》2009年3月19日。何 平:《女工程师自由恋爱被父母送入精神病院? 剥光受检》,《羊城晚报》2012年6月28日。在此背景下,公益律师呼吁效仿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由独立的第三方——法院或者包含非精神医学专业人士的审查委员会——对精神障碍非自愿住院进行审查。[注]缪 琦,田享华:《黄雪涛:一个公益律师的愿景》,《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11月6日。另外,除了家属与医生共同替代患者作出住院决策之外,非自愿住院还依赖于封闭式医疗机构的存在。故公益法律界也呼吁中国精神卫生体系学习欧美国家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去机构化和患者权益运动,关闭大规模封闭式的医疗或托养机构,代之以对患者人身自由限制较少的社区化服务。
从上文介绍可知,在中国精神卫生法律改革的十字路口处,存在着关于个人、家庭、机构关系的多种历史性可能:家庭可能仅仅是协助维持公共秩序的其中一员;即使它成为制度焦点,也可能被视作专业机构的关键合作者,或是需被现代科学替代的“吃人”传统,又或者是与封闭机构同为专制之恶、开放社会之敌。《精神卫生法》在很大程度上确认和延续了精神医学对家庭的依赖和两者的合作,而规避了其他的历史可能性。那么,这种历史性选择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都有哪些?
四、儒家的医学化与市场化?
《精神卫生法》对家庭主体地位的确认和建构,支持者赞扬其继承了儒家文化的家庭本位,反对者则批评其承袭了中国传统的父权和家长制文化。的确,法律中关于家庭决定自伤患者住院与否的规定,呼应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注]李隆基注,邢 昺疏:《孝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的道德要求,说明在儒家文化中身体从来都不只属于自己,更属于生命之所来源的家庭。法律中家庭享有知情同意、决定收治的权利而基本不受监督,此规定来自于立法者对家属的善意推断。例如参与立法调研的精神病学家孙东东教授曾评论道,媒体对“被精神病”的报道都强调人性恶,但“其实亲情是所有的情里面最善的一个情”。[注]孙东东教授在2013年6月22日全国精神病学伦理和法律问题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立法者的善意推断可以说体现了儒家关于孝弟等家庭之爱作为仁之根本——即最基本道德情操——的思想。[注]孔子在《论语》中把“仁”定义为“爱人”,又道:“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精神卫生法》关于家属权利的规定是建基于儒家之亲情和亲权的。
然而从儒家的本体论和伦理学到现代医学实践和法律制度,其中经历了复杂的转译过程,本文只能略述。根据笔者对精神科实践的田野观察,当代精神医学参与塑造了以生物性躯体为边界的个体,其核心在于自我知识、自我一致性和随之而来的自我主权。在此话语里,严重的精神障碍尤其是精神分裂症,损害了个体的自我知识,使个体需他人代为知觉内部世界。[注]宋合营:《京两家医院今起将不再外出接诊精神病患者》,《京华时报》2007年3月1日。且精神障碍诊断目前主要依靠对患者近段时间行为、觉知、情感的评价,评价标准除了行业诊断手册和医生经验以外,还包括患者的生活史——即现在与过去的自我是否同一。而当患者自我已被医学假设为解体时,能够提供生活史并代患者而知的,在中国精神科医生看来只有与患者朝夕相处的家属。笔者在其他文章中曾论述,当今医学知识逐渐渗透到日常亲密关系,使个体精神健康成为家庭目标,[注]缪 琦,田享华:《黄雪涛:一个公益律师的愿景》,《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11月6日。因而密切监测个体精神状况、代个体而知,就成为了家庭生活的功能和任务了(与之相较,中华帝国时期关于疯狂的医学并不强调疯狂者对其内在状态的觉知,[注]关于帝国时期对疯狂的知识,请参见以下系统介绍:Fabien Simonis,Mad Acts, Mad Speech, and Mad People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aw and Medicine,Ph.D.dissert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2010.因而也不突出今天作为替代性认知主体的家庭)。因此我们可以说,精神医学以其个人主义与儒家的家庭本位相互糅合、相互支持,即精神“正常”的个体需要家庭来塑造,而医学界定的精神异常和自我瓦解则使家庭可以介入成为患者的扩大自我。同时精神医学也向儒家家庭关系引入了新的知识论维度,也就是对照医学标准,替代个体进行觉知、决断。
另一方面,家庭在医学实践和法律制度中所承担的照料权责,也与改革开放以来卫生服务和福利的市场化紧密相关。1985年,也就是卫生部下令四川省卫生厅代为起草《精神卫生法》的同一年,中国的医疗改革开始。此后,政府对医院的资金投入逐渐减少,医院逐渐自负盈亏,公费医疗也逐渐淡出。另外,从1958年起民政部就向“三无”和困难精神病人提供免费住院服务;到了1957年,民政部宣布其工作重点要转向对“大多数对社会无用但有家庭支持的病人”提供自费服务。[注]Veronica Pearson,Mental Health Care in China:State Policies,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Family Responsibilities,London:Gaskell,1995,p.75.医疗服务的市场化和福利的私人化使得家庭担负起了照料的重责:对于没有工作、独立收入来源和医疗保险的患者(青少年或长期患者情况往往如此),家庭承担其高额医疗费用和日常开支。而且由于我国以家庭为单位的福利计算方式,家庭中只要有一人有正式工作、收入,往往就很难得到低保等社会救助,以致普遍出现“老养残”的现象,即老年父母用并不丰厚的退休金抚养精神残疾的子女。作为精神科医生的立法者有见及此,纷纷感叹精神病患家属“是我国乃至全世界最忍辱负重的几千万人的群体”。[注]谢 斌等:《精神卫生立法的国际视野和中国现实——来自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的观点》,《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1年第10期,第724页。另外参与立法的刘协和、唐宏宇、孙东东等都曾在笔者访谈或公开会议上表达过类似观点。
《精神卫生法》作为卫生部部门立法,[注]中国精神卫生立法鼻祖、华西大学精神科刘协和教授向笔者忆述,1985年卫生部计划系统建立卫生立法,把精神卫生法起草任务交给四川省卫生厅主持,湖南省卫生厅协助,卫生部医政司管辖。1999年卫生部把立法任务转给疾控司,后者重新任命了新的立法团队,包括唐宏宇、谢斌等精神卫生专家。2009年卫生部把草案交给国务院法制办,后者在修改审议的过程中仍保持与卫生部的协商。从刘教授的回忆可见卫生部主导了立法过程,精神医学专业知识指导着立法思想。无法撬动其他公共资源改变现有的照顾责任分配,[注]刘协和教授在访谈中反复表示,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能力治疗、住院的病人,政府应该为其提供免费服务。然而当初他在起草法律的时候,被上级告知不要谈钱的问题。立法者只好选择向承担治疗、照料和管理重担的家庭赋予参与治疗决定的权利。“在赋予他们(家属)监护责任与看管义务的同时,却剥夺其参与并决定患者治疗的权利,将对现实造成巨大冲击,造成更大的混乱与不和谐。”[注]谢 斌等:《精神卫生立法的国际视野和中国现实——来自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的观点》,《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1年第10期,第724页。当然,在“被精神病”的话语压力下,为了避免医院卷入家庭内部关于非自愿住院的可能纠纷,法律把医院排除出送诊者之列,因而家属不能再委托医院接诊。[注]《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http://www.gov.cn/jrzg/2012-10/26/content_2252122.htm,2013年4月14日。但这项规定丝毫不会削弱、反而可能增强家庭的主体地位,因为家庭在送诊时需发挥更大的“能动性”。故笔者认为,家庭在医学和法律中的主体地位来自于医疗/福利市场化过程中公共照料责任的私人化。换言之,与过去人类学关于市场化导致个体化的论调不同,[注]Yunxiang Yan,“The Chinese path to individualization”,The British Journal to Sociology, no.3,vol.61,2010,pp. 489~512.笔者发现至少在精神卫生方面,市场化过程所塑造的医疗服务消费者和权责主体常常是家庭。而这个政治经济学过程又包含着道德经济学:精神科医生和公众大多认为,家庭愿意承担高昂的医疗成本为个体寻求治疗,这只能说明家庭对个体的深挚关怀,恶意滥用医疗资源的家庭只属例外;而随着医疗服务的普及和家庭支付能力的提高,绝大多数家庭会接受精神健康所定义的生命价值、积极为患者求医,忽视、虐待和禁锢患者的家庭只属少数。
五、回忆的恐惧与展望的迷茫
若说《精神卫生法》中家庭的主体地位仅是自动延续了儒家文化传统,未免陷入文化原生主义(primordialism);而若仅把立法看做政府利用儒家家庭主义规避公共照顾责任,也会有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之與——两者都忽略了法律过程中情感和认同的作用。事实上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法律界定了人的地位和权利,因而能帮助人们建立对自我和社会的认同,呼召着最深层的情感和对地方的归属感。尤其是在不同法律体系交错下的后殖民社会,具体法律争执常被纳入一个总体框架,直接塑造着人们对该社会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想象。[注]Jan Hoffman French,“Dancing for land:Law-making and cultural performance in Northeastern Brazil”,POLAR:Political and Legal Anthropology Review,no.1,vol.25,2002,pp.19~36.从情感、认同和历史想象的角度看精神卫生法,我们会发现27年来的社会变迁,特别是其中精神医疗制度引起的各种纠纷与争议,使立法深藏着专家和公众对计划经济和总体性政治的回忆与回应。另一方面,几乎是从一开始,《精神卫生法》的立法主力——司法精神病学界——就与各发达国家的专家有深入交流,[注]2013年4月刘协和教授在访谈中对笔者表示,1987年开始,世界卫生组织多次派英、美、法、日的专家来中国与司法精神病学界交流。因而法律也包含着他们(当然还有各方公众)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思索与展望。
对总体性社会和威权统治的恐惧,使《精神卫生法》拒绝了单位和地方司法/行政力量等公权力参与治疗决定的可能。前文已述,在《精神卫生法》实施之前,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单位也担任着送治患者的角色。但近年来,单位对其职工精神医疗方面的介入已迅速减少。而在新法之中,单位只能把有自伤或伤人危险的疑似患者送往医院寻求诊断,[注]《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http://www.gov.cn/jrzg/2012-10/26/content_2252122.htm,2013年4月14日。却没有决定住院等其他权利和实质性责任。单位角色的淡化固然与公费医疗体制解体有关,同时也是由于市场经济培养出来的隐私意识,使得越来越多人不满以往总体性社会下单位制对个人生活无孔不入的渗透。[注]孙立平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2005年3月18日,出自http://www.aisixiang.com/data/6143.html,2013年8月21日。Gail Hershatter,“Making the visible invisible: the fate of ‘the private’ in revolutionary China”,In J. W. Scott & D. Keates (Eds.),Going Public:Feminism and the Shifting Boundaries of the Private Sphere,Urbana & Champaig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4,pp.309~331.据刘协和教授回忆,20世纪80年代,杭州一位老师因疑患歇斯底里而被其学校校长送入精神病院治疗。家属得知后,认为老师并没有病,便将学校告上法庭,学校一审败诉。类似案件后来时有发生,例如2010年,深圳护士郭俊梅诉单位在其不知情时请精神科医生为其诊断,并当众宣布诊断结果要求其调职一案。[注]王 莹:《被单位宣布为精神病 深圳一护士打赢官司》,《南方都市报》2011年5月9日。这些案件经媒体发酵,不仅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而且使精神科医生不愿再做单位的“共谋”。
类似地,面对公益法律界反复呼吁对非自愿住院采取第三方审查的机制,立法者深知这种做法来自其他国家的普遍实践——非自愿住院的决定权在美国、澳大利亚由法院掌握,而在同属亚洲的日本、印度归于地方行政长官,甚至在同属中华文化圈的台湾地区也由独立的审查委员会决定。[注]谢 斌等:《精神卫生立法的国际视野和中国现实——来自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的观点》,《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1年第10期。然而立法者担忧,将非自愿住院的决定权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地方行政或司法机关,将可能加剧部分地方政府将精神医学和精神病院作为维稳工具的做法。[注]例如,2011年8月唐宏宇教授在接受笔者访谈时提出此观点。在转型时期,结构分化和社会矛盾的加深大大超过了地方政治资源可以调节的范畴,因而上访成为了一些感觉受侵害的民众抗争的方法。而部分地方政府出于维稳指标等考虑,把上访者拘禁在精神病院中,通过精神病诊断取消上访的正当性而维护政府自身的合法性。刘刚、孙法武、吴春霞[注]《辽宁猪贩两次“被精神病”起诉四部门索赔200万》,《新京报》2013年6月21日;朱柳笛:《(回访)孙法武:怕再进精神病院》,《新京报》2011年11月10日;焦红艳,闫 格:《农妇的胜诉与一部法律的难产》,《法治周末》2012年9月19日。……这些上访者对“被精神病”的控诉,记录着精神医学不能独立于行政权力的尴尬。[注]上访者被强制收治的问题涉及对转型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医学知识的详细分析,深入考察超出了本文的主题。目前国内唯一关于此问题的研究,请见房清侠《上访者“被精神病”现象的法社会学思考》,《河北法学》2011年第1期。鉴于地方行政/司法尚不能受到有效监督,《精神卫生法》立法者选择把这些公权力拦在住院决定的门外。不少基层精神科医生都为法律对公权力的拒绝而击掌,感叹终于不用受不必要的压力。由此可见,《精神卫生法》对家庭的依赖,也来自于立法者与公众对威权社会公权干预专业、侵入私域、侵犯私权的恐惧。
《精神卫生法》既有对中国正在走出的威权社会之恐惧,也有对可能面临的极端自由之迷茫。法律中对住院治疗所采取的自愿原则、严重标准和危险性标准,很大程度上参考了美国的精神卫生立法。而如果公益法律人士如黄雪涛律师所倡导那样,将美国模式推到极致,就应该效仿美国的去机构化运动,把非自愿住院当做需要法庭决定的民事拘留,且大幅减少专科医院封闭病房。然而立法者和不少基层精神科医生都指出,在家庭照料普遍缺失、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去机构化带来的是大量需要帮助的患者辗转于不同的社区机构甚至流落街头,他们因不能得到及时治疗而病情加重;且由于法院对危险性的判断严苛,不少有肇事肇祸风险的患者不能被及时管理而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严重伤害。[注]谢 斌:《患者权益与公共安全:“去机构化”与“再机构化”的迷思》,《上海精神医学》2011年第1期。因而在精神科医生的理解中,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人人权(自主权)的过分强调和放任与医学对公民——患者、照料者、公众——的人道主义责任相冲突。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医生眼中人道主义所要达到的“人”,自然是精神医学所界定的能自立、自理、意识情感不异于常人之人,是生物化的人,而非去机构化运动所倡导的多样化的人。在此基础上,精神科医生向立法论辩引入了生命权和健康权的概念,以学科内关于“人”及“健康”的统一标准界定之,并将其作为比自由权更基本的权利。[注]例如,贾福军:《健康权也是人权》,2010年11月9日,http://www.cpa-pa.org.cn/news/jskcontent_c0605_x37766__.html,2013年8月22日。但进行这一比较者没有提及的是,国际人权公约所规定的健康权包含了个体对健康服务行使知情同意的权利,也更强调国家采取措施向公民提供健康服务的义务。[注]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五条,http://www.un.org/chinese/disabilities/convention/convention.htm,2013年4月12日。相反,在中国的立法语境里,国家义务被淡化,(精神)健康权成为了个体的“客观”需求。当个体无法认识到自身这一需求——尤其是当其可能伤害自己或他人时,家属就有义务为其向医生求助,使其重返健康。因此,用法律形式规定家属的送治权利、照料义务,是国家把精神健康概念渗透到家庭、塑造统一的健康主体、进行生命治理的过程,也是国家把其促进个体健康的义务交给家庭、以家庭—机构圈预防类似资本主义社会人道主义危机发生的措施。
六、讨论:当代中国亲密的生命政治
《精神卫生法》中家庭的主体地位,揭示了转型中国生命政治、亲密政治、大政治的缠结。在精神卫生的家庭—机构圈中,家庭并非自然而然的存在,而是不断被医学、法律等学科和机构塑造着其道德形象和构成形态(如对监护人是谁的规定),规定着其行动和权责边界,指引着其追求的目标(如成员的精神健康)。另一方面,家庭不仅为机构提供着治理所需的知识,且其内部的张力和权力关系及其对外的诉求(如以往家庭在委托医院上门收治时出现的纠纷),也会折射到机构的实践和政策中去。中国精神医疗实践和法律制度中生命政治和亲密政治的众多纠缠,最突出的体现是“家庭的公民权(domestic citizenship)”[注]Das和Addlakha在其关于印度残疾女性的研究中提出“家庭的公民权(domestic citizenship)”概念,即家庭往往决定着残疾人是否享有公民权, 残疾是一个人的责任还是在照料网络中共同承担,谁来为残疾发声等。Veena Das & Renu Addlakha,“Disability and domestic citizenship: Voice,gender,and the making of the subject”,Public Culture,no.3,vol.13,2001,pp.511~531.——在精神医学知识的指导下,家庭监督个体的精神状况,决定个体何时失去行为能力、可能危及自身,从而代替个体行使公民权利(限制自由权以实现健康权)。亲密政治或家庭的公民权在中国生命政治中占有的这一重要地位,是由大政治的态势所形塑的:亲密政治不仅是立法者顺应市场经济中公共照顾责任缺席的安排,更是立法者和公众在社会转型时期怀着对过去威权社会的恐惧和对将来资本主义可能的迷茫所做的历史性选择。
《精神卫生法》中家庭的主体地位体现了今日中国变动的公私关系,特别是裹挟在生命政治、亲密政治和大政治中的家庭在公私划分中所具有的灵活性和模糊性:[注]Susan Gal在研究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性别、家庭话语后指出,公与私的划分不应被简单看成家庭与外部世界的固定空间分隔,而是多变的不规则碎片(fractal)。她提出分析公私关系时应将其视作受意识形态塑造的元语言,同时又是与语境相关,具有灵活性和模糊性的言语实践。Susan Gal,“A semiotics of th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In J. W. Scott & D. Keates (Eds.),Going Public:Feminism and the Shifting Boundaries of the Private Sphere,Urbana & Champaig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p.273.一方面,家庭作为市场经济中被凸显的私域,能在界定个体行为的正常边界后替代越界个体行使私权。这种私权是对威权社会公权力侵入私域之反应,使精神医学从被滥用的公权力中获得独立。另一方面,家庭作为儒家哲学中生命和基本伦理情感的普遍来源,是更高意义上的“公”。[注]在中国儒家哲学中,公私之分不只是空间概念或政治概念,而且是西方语境下罕有的道德—宇宙学概念(“公”象征公理、公道)。[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公与私·公私》,郑 静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1年,第50页。在政府直接责任缺位的情况下,家庭承担照顾患者和保护他人的公共责任,与机构一起实行被医学定义的人道主义关怀,因而也是预防极端个人化、自由化悲剧的“公道”。总而言之,当今中国家庭的亲密关系之所以成为生命政治的关键节点,掌控着“家庭的公民权”,是因为转型时期要求家庭在公私关系中承担灵活的角色。家庭的灵活角色也表明,对当代中国而言,发展和法治并不是某种单一意识形态指导下的线性进程(如资本主义的限制公权力和发展私权),而是人们带着复杂的历史情感同时想象和回应着传统与现代、威权社会的控制与资本主义的自由。
尽管《精神卫生法》对家庭权责主体的构建有其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但通过本文对中国精神医疗史的回顾,以及对立法过程中历史想象和文化转译过程的分析,我们能发现现有制度存在问题,而要改善这些问题也不乏条件。其中一个问题是法律忽略了当代中国家庭关系的复杂性。前文提到,《精神卫生法》中家庭在送诊、收治和知情同意等方面有着无可置疑的权利,一定程度上来自于立法者在儒家亲情与亲权基础上对家庭的善意推断。但即使是传统儒家法律体系,对家庭关系之善也更多的是作为应然去追求而非作为实然来预设,而且对违背家庭伦理的行为(如不孝)有高度的警惕和严厉的惩罚措施。[注]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页。相比之下,《精神卫生法》2011年公开讨论草案中本也有对不良家庭关系的警觉,即规定患者被家属决定非自愿住院后可以申请复诊和鉴定。但在法律最终稿中,该条款以不利于缺乏自知力的患者接受治疗为由被删去。[注]胡 浩,吕 诺:《精神卫生法草案就精神障碍鉴定性质和程序作出调整》,2012年8月28日,http://www.npc.gov.cn/huiyi/cwh/1128/2012-08/28/content_1734466.htm,2013年12月22日。有趣的是,立法者作为精神科医生,在医疗实践中多能认识到当今社会家庭关系的复杂性及其权力关系。例如唐宏宇教授曾调侃道,法律规定家庭是唯一能决定有自伤危险患者非自愿住院的主体,可能导致家属故意阻碍患者获得医疗资源。“这就是为中年男人提供了很好的创造自己‘三大喜’的机会——升官发财死老婆。自己的老婆有抑郁症,想自杀。她去了(医院)以后,由监护人决定啊,他说:‘回去,不住。等她死,等她跳楼。’你(医生)怎么办?毫无办法。”[注]引自唐宏宇教授在2013年全国精神病学伦理和法律问题学术研讨会上的口头报告。又如,刘协和教授曾向笔者表示,他在20世纪80年代起草法律时并没有遇到、也没有想到亲人会把正常人送进精神病院,那是改革开放形成商品社会、出现私有财产之后才有的现象。那么如何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转化为制度上的警示呢?这就需要我们整理区分法律中的实然与应然,并结合社会科学对亲密政治中权力关系进行考察与直面,重新界定家庭成为监护人的条件与权利。
前文已述,家庭在精神医疗中备受争议的权利,是与其在照料患者过程中承担的沉重责任相对应的。要解决家庭高度卷入精神医疗带来的各种问题,就需要引入其他主体,包括重申国家的健康责任和慎重使用公权力的必要性。不仅国际人权公约规定了国家采取措施向公民提供健康服务的义务,而且儒家伦理中也非常强调国家超越家庭之上的照料义务。大同理想中就包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注]郑 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58页。需要注意的是,国家健康责任的履行不宜以塑造统一的生物化个体为目标,更不应只把精神障碍患者作为扰乱公共秩序的危险源,否则只是以更强大的国家父权取代了家庭父权。[注]Virginia Aldige Hiday & Lynn Newhart Smith,“Effects of the dangerousness standard in civil commitment”,Journal of Psychiatry and Law,no.15,1987,p.433.对超越生物性之上的生命多元意义之尊重和培育,应是国家和其他主体参与照料和支持服务的目标。另外,对于公益法律界关于公权力设立非自愿住院审查程序的呼吁,立法者以公权力可能被滥用而拒绝。且在笔者观察到的基层实践中,随着媒体对“被精神病”的批评声渐隆,各公权力机关对介入精神医疗和康复服务越发畏缩,有时甚至使家庭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但很明显,解决滥用公权力的出路并非不用而是慎重使用公权力,协助个体和家庭走出生命健康和伦理的困境。对威权社会的历史性恐惧固然应被重视,但这不应成为笼罩在公权力上空的乌云,而是作为反思的起点,鞭策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如何构造一个新的共同体,以及边缘群体与共同体如何相关。
鸣谢:成文之际,笔者感谢几年来向自己慷慨分享信息、经历和观点的立法者、公益律师、医生、家属及精神医疗使用者/幸存者。本文曾在2013年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大会医学人类学分论坛上报告,分论坛召集人为景军、余成普老师,点评人为庄孔韶老师。尤其是景军老师在会后指导修改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深刻而细致的意见,还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在此笔者向几位老师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