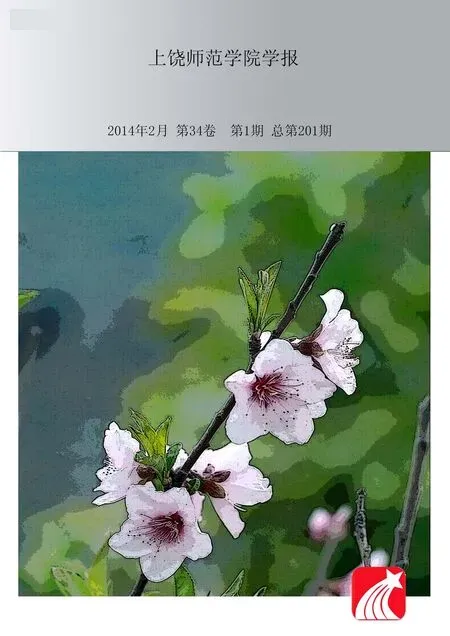论地方志商人传记的思想倾向
张世敏,成亚林
(1.上饶师范学院,江西 上饶334001;2.江西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330013)
商人传记是研究商人的重要文献,余英时在《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中论道:“今天我们对于明清商人的活动情况能够有所认识,主要材料都是士大夫提供的,他们在文集与笔记中保存了大量的商人传记,对商人的生活形态给予生动的描绘(尤以墓志铭、传记、寿序等最为丰富)。其他的材料如官方文献、史书、小说,甚至所谓‘商业书’等都只能处于辅助的地位。”[1](P168)与墓志铭、寿序等文体相比,狭义的商人传记“质实而随所传之人变化”[2](P246),真实生动,对商人研究具有更大的价值。
商人传记按照出自文献的不同,主要可以分为文集商人传记、族谱商人传记与地方志商人传记三种。由于源于不同的文献,不同类别的商人传记在内容、风格以及思想倾向等方面都存在差别。笔者在阅读宋、元、明、清四代地方志时,发现徽州地区与河北府新安县的地方志中,商人传记比较集中,具体分布情况如下,宋代赵不悔所编《新安志》中1篇,弘治《徽州府志》中2篇,嘉靖《徽州府志》中6篇,康熙《徽州府志》中19篇,河北府乾隆《新安县志》5篇。以上所列是传主可以确证为商人身份的传记,另外,各地方志中还收有相当数量的疑似商人传记,为避免论证中出现偏差,本文将它们排除在论述范围之外。
研究地方志中商人传记的思想倾向,并把它们与文集商人传记的思想进行对比,是对明清商人研究所据文献的一次梳理与反思。这个问题以前没有被学者注意到,对它进行研究,目的是在商人研究之中更合理地运用这些文献。
下面对地方志商人传记的思想倾向,以及地方志商人传记与文集商人传记思想倾向的差异、形成原因展开论述。
一、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
三教合一在唐代得以完全后,至明、清二代,儒、释、道三教在我国思想史上大多数时候都呈三足鼎立之势。不过,在地方志商人传记中,儒家思想却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儒、释、道三教鼎立之势并没有得到客观地呈现。以上所述33篇地方志商人传记,有27篇只能看出有儒家思想,占总数的81.8%,剩下6篇,也只能从其中看出佛教思想的蛛丝马迹,儒家思想依然是主要方面。
地方志中商人传记一般被收录在《孝友》、《尚义》、《宦业》、《乡贤》等类别中。这些商人传记按照传主的身份,可以分为儒行义士与官宦乡贤两类。
1.传主的儒行义士化
地方志中的商人传记,很多传主被塑造成了儒行义士,这反映了儒家思想是它们创作的指导思想。这些商人传记被收录在《孝友》、《尚义》、《质行》中,传中所载传主的孝义之行,大多完全符合儒家伦理的要求,传主堪称践行儒家伦理的典范。
父慈子孝,兄友弟悌作为儒家伦理的核心,对此孔子说过:“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仁是儒家思想最基本的要求,孝与悌又是仁之根本,由此可见孝、悌在儒家思想中所占的地位。《孝友传》中的商人传记的传主,顾名思义,也都是践行儒家孝、友伦理道德的典范。乾隆《新安县志》2篇商人传记收录在《孝友传》中,两位传主是明代商人,其孝友足称高义。首先看《杜廷岳传》,传文为:
明杜廷岳,家贫,贸饼为生,每晨先以精白者奉母,四十年不辍。母殁,结茆墓傍,期居三年,会兄弟中有谋阻之者,竟罗织以归,其心哀哀然,终不释也。有司开而以冠带荣之。[3](卷六)
杜廷岳家贫,而能以精白者奉母,四十年如一日,母亲故后,决心结庐守墓,虽然没有如愿以偿,但终日哀哀然。廷岳以卖饼为生,家贫仅能自存,当没有多余之资请人作传,并以经济利益为手段让地方志的编撰者将其传采入地方志中。
与《杜廷岳传》同卷的《管六传》,传主管六的孝行与杜廷岳相类。管六是一名以收购废品为生的商人,没有家室,生平事迹除了孝敬母亲之外,无它可称道者。地方志为他们立传,完全是因为他们的孝敬父母之行与儒家思想暗合,记其孝行可以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有利于名教。
除了前文所引乾隆《新安县志》中的《杜廷岳传》与《管六传》之外,康熙《徽州府志》卷十五《孝友传》中所收录的明代商人的传记如《汪存传》、《吴球传》、《谢广传》、《金应忠传》等,也都是纯孝纯友之人,其行为完全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传记所载之事,与佛、道二教扯不上关系。
徽州地方志《尚义传》、《质行传》中收录的商人传记,思想倾向也以儒家为主,佛、道二教只是补充。这将在下一部分中细述。
2.传主的官宦乡贤化
《宦业》与《乡贤列传》中的商人传记,儒家思想也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如《汪杲传》,弘治《徽州府志》,嘉靖《徽州府志》及康熙《徽州府志》中均有收录,弘治《徽州府志》中《汪杲传》全文为:
汪杲,字廷辉,休宁人,寓居府城,弱冠用父命商于松江,不惬志,即从钱学士溥学,昼夜勤励不息,三年始迁入郡庠。以《诗经》领景泰丙子乡荐,登天顺甲申进士,授南京户部山西司主事。清谨详慎,升员外郎,寻升郎中,擢曲靖军民府知府。时罗雄州土官自相雠杀,杲躬抵其地,谕以朝廷恩威,两感而解。自是民夷帖然。三载入觐,以老致仕,归,闲十五年,闭户观书,足不入官府,卒年七十有六。弟荣领景泰乡荐,卒。[4](卷八)
嘉靖《徽州府志》与康熙《徽州府志》中所载《汪杲传》与弘治《徽州府志》稍略,但大体相差不大,嘉靖《徽州府志》中《汪杲传》全文为:
汪杲,字廷辉,休宁人,寓居府城,弱冠用父命商于松江,不惬志,即从钱学士溥学,昼夜勤励不息。三年始迁入郡庠,登天顺甲申进士,授南京户部山西司主事。清谨详慎,升员外郎,寻升郎中,擢曲靖军民府知府。时罗雄州土官自相雠杀,杲躬抵其地,谕以朝廷恩威,两感而解。自是民夷帖然。三载入觐,以老致仕归。弟荣领景泰乡荐。[5](卷十七)
康熙《徽州府志》中《汪杲传》则为:
汪杲,字廷辉,休宁上溪口人,天顺甲申进士,授南京户部山西司主事,历曲靖军民府知府。时罗雄州土官自相雠杀,杲躬抵其地,谕以朝廷恩威,两感而解。自是民夷帖然。[5](卷十四)
地方志在重新编修时,一般都会保留前朝已有版本中的内容,但人物传记通常会有所简化。弘治、嘉靖、康熙三朝所编修的《徽州府志》中的《汪杲传》能够反映这种保留而略加简化的编纂原则。在弘治《徽州府志》以及嘉靖《徽州府志》的传记中,汪杲还只是一位志在儒而不在商,有过一段经商经历的儒士化的官员。到了康熙《徽州府志》中,汪杲则变成了一位纯粹的儒者,经商经历已被略去。这说明地方志《宦业传》中的商人传记,儒家思想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又如《乡贤列传》中的《杜国基传》,全文如下:
杜国基,邑庠生,赠贵州安顺府知府,孝友天成,色养备至,棠棣峥嵘。家本寒素,学计然术,遂渐致丰裕。性好义,推解不吝,值岁饥,出粟数百石以赈,至今邑人德之。敦本睦族,有婚嫁失时,丧葬不举者,出资相助,遇祭期,必大合族人而训之,以孝弟为重,戒争斗,尊卑大小之序,照叙分明,勿逞凶暴以陷刑法。教子有方,名垂守令,绩列龚黄,为仕宦之最,皆不愧家训焉,乾隆六年崇祀乡贤。[3](卷六)
如果不是因为其中有“学计然术”这句话,表明了传主有着商人身份,杜国基完全是一位行为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贤人。在岁饥之时出粟赈灾,救济族人,教育族人以孝悌为重,后代位列守令。杜国基之所以能入乡贤祠,正是因为他有上述儒家义行。
在佛、道二教,尤其是佛教已被下层人民广泛接受,大多数的商人都有佛教信仰的明、清时期,以上所述的传记中看不到佛教的任何影响,是值得思考的。这说明地方志的编撰者在撰写这类传记时,在内容上是有选择性的,即作者以传主的事迹是否符合儒家思想作为取舍的标准。
二、潜隐的佛教思想
相对于儒家思想,佛教思想在地方志商人传记中不是主流。但在儒、释、道三教思想深入人心的大环境下,即使编撰地方志的指导思想是儒家思想,佛教思想也可以潜隐于其中。
首先来看《汪廷美传》,三个版本的《徽州府志》都收录了《汪廷美传》,只有弘治《徽州府志》卷九的《汪廷美传》中,可以看出传主与佛教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该传中的开头部分曰:
汪廷美,婺源人,孝友纯至。义居数十年,聚族众数百口,旦暮食必同席,有未至者不敢先。廷美节嗜欲,身衣缯布,非因祭不肉食。亲丧尽哀,不应宾客,遇忌则终日斋肃。大中、祥符中,东封,赦减天下赋十之二,廷美亦减其佃者租十之二。乾兴,颁遗诏,衰糹至号慕,营佛斋七日……性不嗜杀,牛罢老不堪用者,终饲养之。[4](卷九)
传主汪廷美聚族而居,食必同席;亲丧尽哀,遇忌则终日斋肃;得鬻香之贾遗金,追而还之;人偷其鹅祭祖,助以鱼酒等义行,都可见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具体可参见传记原文。唯有“乾兴,颁遗诏,衰糹至号慕,营佛斋七日”,“性不嗜杀,牛罢老不堪用者,终饲养之”之类的记载可以反映传主接受了佛教思想的影响。不过,即使是这两处仅有的能够反映出传主与佛教之间存在一定关系的文字,在嘉靖《徽州府志》以及康熙《徽州府志》中的《汪廷美传》中都被删节了。原文篇幅过大,这里不做征引,读者可以参读原文。
嘉靖《徽州府志》和康熙《徽州府志》中的《汪廷美传》,都是以弘治《徽州府志》中的《汪廷美传》作为母本进行简化的。其依据是,康熙《徽州府志》所载汪廷美之事迹比嘉靖《徽州府志》更为详尽。关于汪廷美聚族而居,嘉靖《徽州府志》曰:“义居数十年,聚族众数百口,旦暮食必同席”,康熙《徽州府志》则为:“义居数十年,聚族众数百口,旦暮食必同席,有未至者不敢先。”显然,康熙《徽州府志》的内容反而更接近弘治《徽州府志》。此外,康熙《徽州府志》中所记载的“廷美节嗜欲,身衣缯布,非因祭不肉食”,“尝使兄弟子鬻帛他县,归银数百两,皆赝,廷美不复言”,皆转录自弘治《徽州府志》,嘉靖《徽州府志》中没有记载这些内容。两者在编撰时都不约而同地将弘治《徽州府志》中《汪廷美传》能够反映传主与佛教之间存在关系的部分过滤掉,说明地方志商人传记编撰的指导思想是儒家思想,其中即使有残留的佛教因素,在地方志重修时,也会被剔除出去。
除《汪廷美传》外,与佛教思想相关的还有嘉靖《徽州府志》中的《汪琼传》、《佘文义传》,康熙《徽州府志》中的《汪琼传》、《佘文义传》、《佘文焯传》。这5篇商人传记收在《尚义》类中,没有明言传主信佛,我们只能通过传中所载传主的佛教式义举,将传记与佛教思想联系来。
现以康熙《徽州府志》中的传记为例,康熙《徽州府志》中《汪琼传》载传主生平事迹如下:
汪琼,字时献,祁门昼绣坊人。少豪迈多大虑,手致数万金。邑南阊门溪流激撞,善覆舟。琼捐金四千,伐石为梁,截冲,别为凿道,引北东诸水由丁家湾而西,再折而南,迤五六里至路公溪与阊水会。舟行始安。嘉靖六年邑大水,溃其堤,坏民田百余亩,琼重修治,计田而偿其直。田税五石余,入本户供输,子孙因以贫乏。邑人怀其义,诉于知县孙光祖,为免其税。[6](卷十五)
《佘文义传》载传主生平事迹如下:
佘文义,歙岩镇人。尝构屋数十楹,置田百二十亩,以给贫族,日食甫粟一升,矜寡废疾者,倍之。丰年散其余,荒年益赀补助。又度地二十五亩作义冢,以葬死无归者。构石梁于文凡山侧,以济病涉。子训诲诰,同爨雍睦,有父风。[6](卷十九)
《佘文焯传》载传主生平事迹如下:
佘文焯,歙人。性孝友。少家贫,然父有所欲,无不遂之。中年游于淮扬,家业稍振。见族祖文义所造石梁倾圮,罄其家赀以新之。[6](卷十五)一般而言,佛教所提倡的义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者兴立佛图,僧房堂阁;二者园果浴池,树木清凉;三者常施医药,疗救众病;四者作牢坚船,济渡人民;五者安设桥梁,过渡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饮”[7](P777)。以 上 几 篇 传 记 中,传 中 所 载 “琼 捐 金 四千,伐石为梁,截冲,别为凿道,引北东诸水由丁家湾而西,再折而南,迤五六里至路公溪与阊水会”;佘文义“构石梁于文凡山侧”;佘文焯“见族祖文义所造石梁倾圮,罄其家赀以新之”,与佛经所倡义举相类。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地方志编撰者在撰写商人传记时,会尽可能地屏蔽传主与佛教之间的关系,不过,这并不能将佛教思想从地方志商人传记中完全剔除出去。对传主佛教式义举的记载,使得佛教思想潜隐地出现在了地方志商人传记中。
三、地方志与文集中商人传记思想倾向的异同及原因
根据前文的论证,可知在地方志商人传记中,儒家思想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佛教思想潜隐在其中,处于可有可无的补充地位。文集商人传记的作者虽然同样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但佛教思想在文集商人传记中却占有重要地位。地方志商人传记与文集商人传记在思想倾向上的差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方志中商人传记所记述传主的佛教式义举,范围没有文集商人传记广。第二部分在论述佛教思想时所引述的几篇地方志商人传记,所述传主的佛教式义举,仅限于营佛斋、建造桥梁与兴修水利三个方面。文集中的商人碑传文,“所记载的善行与义举大致可以归纳为赈贫饭饥、除道梁津、兴修水利、棺敛尸殍、施药救人、修建寺庙等几个方面”,佛教“‘七法广施福田’中所列的七项善行与义举,唯有‘有者造做圊厕,施便利处’一项在商人碑传文中完全没有被提起过”[8],两者相比,地方志商人传记所记述的佛教式义举,范围远没有文集商人传记所记述的佛教式义举广。
第二,地方志中商人传记所记述的佛教式义举,程度没有文集中商人传记所记述佛教式义举深。康熙《徽州府志》所载汪琼建造桥梁,兴修水利,属于《六度集经》等佛教经典所提倡的义举。嘉靖《徽州府志》对此事有更为详尽的记载,其文为:“邑南闾门两石对峙,溪激撞,善覆舟。春夏间,商贾不能,米价腾踊,向为民患,知县洪皙欲治之,以费钜寝,琼慨捐金四千,伐巨石为梁,截冲,凿地通道,引北东诸水由丁家湾而西,再折而南,迤五六里至路公溪与阊水会。舟行始安,民食因足。”[4]汪琼建造桥梁,兴修水利,是在知府的主导下完成的,他只不过是出金赞助而已,与文集中商人传记中传主主持或者倡议修建桥梁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此外,《佘文焯传》载佘文焯“见族祖文义所造石梁倾圮,罄其家赀以新之”,其义举有存先人之迹的目的,亦不能以纯粹的佛教式义举视之。因此,第二部分所引几篇传记所载之义举,唯有佘文义“构石梁于文凡山侧”之事,最有可能是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而施行的。
第三,地方志中传主有佛教式义举的商人传记,佛教式义举所占传主生平事迹的比重较小,传中更多的是传主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义举。汪琼助人修治溃堤之田,代人完田税;佘文义给贫族,作义冢;佘文焯性孝友,家贫,父有所欲,无不遂之,都是符合儒教伦理道德规范的义行。文集商人传记有所不同,如果传主信奉佛教,则整篇传记所记义举,几乎都是佛教式义举。如汪道昆所撰《汪处士传》,传主汪通保:
尝梦三羽人就舍,旦日得绘,事与梦符,则以为神,事之谨。其后,几中他人毒,赖覆毒乃免灾。尝出丹阳,车人将不利处士,诒失道,既而遇一老父,乃觉之。处士自谓幸保余年,莫非神助,乃就狮子山建三元庙,费数千金。[9](P129)
传主汪通保信奉的应当是民间宗教,其中佛、道二教思想难以截然分开。在民间宗教佛、道二教思想的影响下,该传所载义行,与典型的儒家义举不太相类,而是与佛经的所倡义举完全吻合,详情可参读这篇传记。佛教义举成为这类文集商人传记记述的主要内容,说明文集商人传记的创作与地方志商人传记相比,摆脱了儒家思想的统治,佛教思想可以自由地纳入其中。
一方面,地方志商人传记与文集商人传记的作者都是文士,在传统社会中,他们会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会反映在他们的商人传记创作之中。另一方面,在商人传记兴起发展的明、清二代,“儒者绌,佛氏滋甚。夫儒服先王之教,日操功令以徇齐民,然而向者十三,倍者十七。西域去中国踔远,言语谣俗不通,东渡以来,靡然顾化。其间长者子出,率以信心、直心、深心而得菩提心”[9](P421),佛教有凌驾于儒家之上的趋势,因此佛教思想出现于商人传记之中,没什么好惊奇的。地方志商人传记与文集商人传记之所以会出现思想倾向的不同,原因在于地方志商人传记的撰写是官方行为,政治色彩浓厚;文集商人传记属于私家著述,可以适当地淡化政治色彩。
在中国古代,地方志通常与正史并举,与封建政权的关系十分密切,章学诚说过:“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10](P574)与正史同为《春秋》流别,地方志具有明显的政治功能,董在《严州图经序》论道:
岂特备异日职方举闰年之制,抑使为政者究风俗利病,师范先贤懿绩,而承学晚生,览之可以辑睦而还旧俗,宦达名流,玩之可以全高风而励名节,渠小补也哉
地方志的作用,除了引导社会风俗之外,更重要的目的在于让官宦与文士们学习先贤的美好政治,培育他们的高士之风,这就自然要求地方志在编撰过程中以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文集商人传记虽然也承担着传记文体必须具有的惩恶扬善的功能,但明、清二代,文集中收录的商人传记,有些作者收取了商人的“润笔费”,属于私家撰述,因此,只要商人有善行义举,无分儒、佛,都会被写进文集商人传记中。
地方志商人传记与文集商人传记对传主善行义举的不同的选择,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的不同,使得它们在明代思想史、社会经济史等领域的研究中,具有不同的价值。地方志中商人传记适合用来研究封建政府是如何引导商人阶层施行义举的,即朝廷希望商人阶层多做哪些善事,通过对商人的引导实现社会各阶层之间较低层次的和谐。文集商人传记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传主的信仰情况,比较适宜用来研究明代商人的精神世界。
[1]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陈绎曾.文说[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482册)[Z].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高景.乾隆新安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本(河北府县志辑34册)[Z].上海:上海书店,2006.
[4]彭泽.弘治徽州府志[M].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21-22册)[Z].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1.
[5]汪尚宁.嘉靖徽州府志[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29册)[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6]赵吉士.康熙徽州府志[M].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第237号)[Z].台湾:成文出版社.
[7]六度集经[M].台北:佛陀基金会出版部,1990.
[8]张三夕,张世敏.明代商人的佛教信仰与义举的关系[J].江汉论坛,2013,(6):118~121.
[9]汪道昆.太函集[M].续修四库全书本[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0]章学诚.文史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王晓岩.分类选注历代名人论方志[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