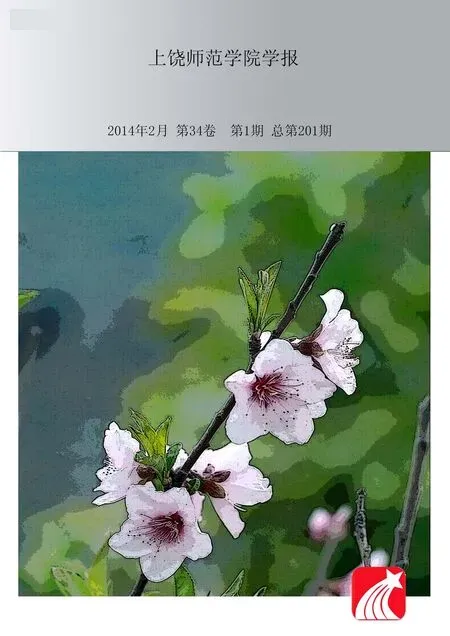南宋汪应辰军事思想探略
夏时华
(上饶师范学院,江西 上饶334001)
汪应辰(1118—1176),字圣锡,信州玉山(今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人,自幼聪慧过人,绍兴五年(1135)十八岁中进士第一,后因反对秦桧议和而遭贬谪达17年之久。在秦桧死后,汪应辰遂受重用,勤政有为,刚正不阿,颇有名望,官至吏部尚书,卒谥文定。
南宋偏安江南,与金南北紧张对峙,战争持续不断。汪应辰作为一个士大夫,以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不但贯通经史,而且对军事兵书、兵法也颇有研究,力图从中汲取用兵之道,为时所用,希望改变当时南宋王朝积弱偷安的局面。他根据南宋当时积弱的政治军事形势,针对当时政治和军事上存在的弊病,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军事主张和思想。对于汪应辰的军事思想,目前学界尚无人涉略,因此笔者对此作如下初步探讨,以期能对历史人物汪应辰的研究有所补充,并抛砖引玉,以求正于方家。
一、思患预防,常若敌人之至,厚为守备
绍兴八年(1138),汪应辰任秘书省正字。当时秦桧当权,力主与金议和,而宋高宗以为与金达成和议就可以万事大吉。汪应辰却清醒地认识到,从当时形势来看,国家还没有到孟轲所说的“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这样太平的时候;当时宋金即使达成和议,而朝廷上下因和议而出现因循无备、苟且偷安现象是令人可畏的。他引经据典,分析指出:战国时秦之谋楚,尝与之土地、借之兵而结为兄弟,又为婚姻,结果秦还是灭掉楚;秦之谋齐,与齐通和,凡四十余年未尝交兵,结果秦还是一样灭掉齐。[1](P1)以史为鉴,汪应辰认为当时金“所谓还我梓宫、归我母兄、复我舆地者。”[1](P1)宋金和好局面也许能够维持一段时期,但必须在政治和军事上保持警惕和戒备。然而当时南宋统治者宋高宗因和议而毫无忧患意识,却是“今乃肆赦中外,厚赏士卒,褒赏帅臣,动色相贺,以为休兵息民自此始矣。”[1](P1)因此,汪应辰不得不发出“纵一朝遂忘积年之耻,独不思异时意外之患乎?”[1](P2)这样的感叹,指出当时朝廷上下缺乏忧患意识,出现因循无备、苟且偷安现象之可畏。
对于当时金与宋和好,南宋朝廷甚至有人以为金敌“有悔过效顺之意”,汪应辰冷静地指出这是不可信的,其中有两点值得可疑:一是“臣闻王伦之行未尝一诣其庭,是必有诡谋密计而畏吾使者之或能觇之也,是岂能洞然无疑于我哉?”[1](P1)二是“又闻敌之迁而北也,竭取财物,尽驱其丁壮而往,下至鸡豚狗彘,靡有遗者,是岂能有爱于我而不取哉?”[1](P1)这些正是说明当时金“夫非诚有悔过效顺之意,而翻然以与我和”,是值得可疑的。
针对朝廷上下缺乏忧患意识,因宋金和议而出现因循无备、苟且偷安这一可怕现象,以及金讲和之可疑,绍兴八年(1138)五月汪应辰在上《轮对论和议异议疏》提出,要求统治者宋高宗不仅要具有忧患意识,“陛下痛心尝胆以图中兴,勿谓和好之可以无虞,而思患预防,常若敌人之至。”而且在军事上“所宜申戒执事,交修庶政,阴饬边吏,厚为守备。”[1](P2)由此可见,汪应辰反对朝廷因宋金和议而因循无备、苟且偷安,呼吁朝野上下要有“思患预防,常若敌人之至”这样强烈的忧患意识,加强军事守备,可谓是切中时弊,唯我独醒,在当时应具有振聋发聩之意义。可惜的是当时汪应辰这一军事主张并未得到统治者重视,却由此得罪权相秦桧而遭贬谪。
二、国于江左,必据上流
南宋迁都于临安,偏安江南,与金对峙,但金经常南下侵扰对南宋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绍兴三十一年(1161),汪应辰在《应诏言弥灾防盗事》中从国家安全战略角度明确指出“大抵国于江左,必保两淮,必据上流。”[1](P6)控制两淮对于南宋国家安全来讲固然重要,但控制长江中上游地区也是至关重要。汪应辰以三国孙吴为例分析指出:“然孙氏之吴,未尝有淮南尺地也,亦仅足以自守。魏文兵至瓜步,则淮已不守矣,而卒不能渡江。至于上流之地,万一敌据之,则鲜有不得志者。盖其顺流而下,通行无累,若高屋建瓴而莫之御也。”[1](P6)后来绍熙四年(1193)辛弃疾在给宋光宗的奏议《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中也同样强调长江荆襄上流的战略重要性:“自古南北之分,北兵南下,由两淮而绝江,不败则死。由上流而下江,其事必成,故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必然之势也。”[2](P831)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当时两淮、建康一带,营伍相望,防御较为巩固,但长江中上游地区防御,尤其是襄阳一带比较松懈。对此,汪应辰分析认为襄阳一带防御存在着令人担忧的五个方面问题:
一是襄阳非险阻之地,防御兵力不足。汪应辰指出,“《兵志》曰:‘以一击十,莫善于阝厄。以十击百,莫善于险。以千击万,莫善于阻。’”而“襄阳之地,平原广野,非有险阻之限,所恃者兵而已。今兵实不足”,[1](P6)此其可虑者一。
二是襄阳守将田师中庸碌无为,刻剥其下,士兵嗟怨,严重影响军队战斗力。汪应辰指出,将帅“与士卒同甘苦,然后可与之同死生。”然而“今田师中刻剥其下,而奴隶使之。平居无事,藉藉嗟怨;一旦有急,彼能死其长乎?”[1](P6)此其可虑者二。
三是襄阳军队捉募行旅以补军籍,战斗力差。汪应辰指出,“捉募行旅以补军籍,至有断截肢体以求免者,人情可见矣。其可驱而使用命乎?”[1](P6)此其可虑者三。
四是襄阳守将田师中忙于敛财,难以勤命于朝廷。汪应辰指出,“唐杜牧论用兵之弊,以为爵命极矣,田宫广矣,金缯溢矣,子孙官矣,焉肯勤于我哉?今(田)师中不几于是乎!”[1](P7)此其可虑者四。
五是襄阳守将不和有隙,不能彼此应援。汪应辰指出,“李道之于(田)师中,故部曲也。师中怒其去己,予以羸卒而留其家赀。夫两不相能而欲望其彼此应援如左右手,其可得乎?”[1](P7)此其可虑者五。
除长江上流襄阳一带防御问题令人担忧之外,汪应辰还指出,其实令人更为担忧的是,长江上流军事防御的战略重要性并未引起统治者宋高宗重视,所谓“独未闻执事者有所措画,岂其知两淮之重,而不知上流之为尤重乎?”[1](P7)所以汪应辰提出,要求宋高宗“陛下诚留意于此,使将足以用其兵,兵足以为将之用,形势相接,声气益振。……惟是备御大计,所当有一定之说者,愿陛下密诏诸将,悉意条具,使议臣参订其可否,有未尽者,往复诘难,然后断自渊衷,裁处其当,表里相应,鹨力 力而行之。”[1](P7)也就是说,希望统治者宋高宗能从国家战略安全的角度出发,高度重视长江上流地区的军事防御,并针对当时长江上流襄阳一带防御存在的问题,积极谋划,采取措施加强军事防备,确保南宋国家社稷安全。可见,汪应辰提出国于江左,必据上流,并加强军事防御的这一主张对于南宋国家安全来说无疑是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
三、海道未可进,以逸而待劳
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金主完颜亮率兵大举南侵,其中一路金兵由海道直趋临安,南宋告急。为防止和迎击金兵海上进攻,汪应辰奉命在浙江沿海措置海防,并提出一些积极防御备战的建议。汪应辰分析认为当时南宋水军在海上还是处于劣势:
一是敌顺风我逆风,迎击敌人十分困难。汪应辰分析指出:“盖今明州之分屯于海上,皆水军也。舟楫之于海,其所因者风尔,顺风而行则瞬息之顷已数百里,不然则寸步不能进也。彼其所以能来者,其得风可知矣。我乃溯风而迎击之,其难易劳逸之势,不侔甚矣。或以为扼其后而袭之,则我之与彼皆顺风也。夫均是顺风,然彼先而我后,彼往而我随,亦未见其必可胜也,况或者众寡强弱之不敌耶。”[3](P17)
二是明州水军在海上战斗力不强。汪应辰也分析指出:“伏见明州水军有选于诸寨土军者,有选于本州禁军者,有取于诸州弓弩手者,其间虽多强壮伉健,而海道则往往非其所习也。驱之登舟,掀簸奇支仄,则悸眩而不能立,呕逆而不能食。濒海之人,类能言之,此正可以用之于陆也。至于见在海舟,以近降指挥则例计之,其羡卒不下千人,舟之大小,自有分量,人数过多,适足为累。而明州弓弩手五百人,名为水军,其实止就本州教阅。”[3](P18)
正因当时南宋水军在海上处于劣势,所以汪应辰认为应该扬长避短,不可盲目从海上迎击敌人,而是应该发挥陆上优势,以逸待劳,陆海结合,掌握时机消灭敌人,所谓“能据其便利,扼其要害,则用力甚省而功倍 之。”[3](P18)他 还 分 析 如 何 扬 长 避 短 的 具 体作战方法:
敌人之来,非大舟不可以浮海,非乘潮不可以入港,非小舟不可登岸。今诚于明之定海,选练步兵,分列港岸,而又多设机械以隔阂敌所从入之路。彼虽仅能入港,而潮退之后,舟为无用矣,岸上之兵强弓劲弩,拳石火炮,乘间俱发,彼辗转于泥涂之中,进则不能前,而退则吾以舟师邀之,可坐而毙也。如有纵之使去,虽复入于海,亦将安所为哉?此万全之计,甚易见也。夫舍坚而攻瑕,以逸而待劳,处高而临下,此皆用兵之道。[3](P18)
他建议朝廷“今若于军中通选一千五百人,取其可用于陆者以为步兵,如此则无益兵之费,而水陆之技各尽其长,备御之方始得其要矣。……不复他议,况舟师在海,乃曰备之于陆,其言若未易信,而理则有可见者。”[3](P18)只有这样,才能打败金兵在海上的进攻。
汪应辰提出“海道未可进,以逸而待劳,陆海结合,掌握时机消灭敌人”。这一主张为后来绍兴三十一年(1161)底击败金军水师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由此体现了汪应辰这一军事主张和思想在当时的战略和战术意义。
四、修治军政,精兵强将
宋金绍兴讲和以来,南宋军饷不足,士兵移作营运负贩、失于教阅训练,军备松弛,军政荒芜腐败现象日趋严重,例如绍兴十三年(1143)宋高宗自己在诏书中就指出:“殿司诸统领将官别无供给职田,日赡不足,差兵营运,浸坏军政。”[4](P4847)绍兴二十四年(1154)有臣僚也指出:“州郡禁卒,远方纵弛,多不训练,春 秋 教 阅,临 时 备 数 ”[5](P4869)。 绍 兴 三 十 一 年(1161),宋高宗又在诏书中讲到:“比闻诸路州厢、禁军、土军,有司擅私役,妨教阅。”[5](P4869)而汪应辰对当时军政荒芜腐败、军队战斗力差的现象则分析更为详细:
自讲和以来,诸将坐拥重兵,初无尺寸之功,而高爵厚禄,极其富贵,安享优佚,养成骄惰,无复激昂奋励之志。兵籍虽多,初不阅习,或拘之以为工匠,或驱之以为商贾,或抑之以为仆厕之役。既虐使之以不当为之事,又侵夺其所当得之食,行路之人皆知其不可用也。已而敌骑奄至,曾不一战,望风遁逃峡辰之间,而两淮之地蹂践几遍。[3](P13)
接着,汪应辰还指出当时军队中冒功领赏,赏罚不当,公肆欺玩,军令不行等问题十分严重:
方且恬不忌惮,咨为诞谩,列上战功,狂惑群听。急危之际,被旨应援,乃或游辞诡计,顾望不进。陛下虽尝取其不用命者治之,终未足以震服中外,且钧是罪也。而罚有轻重,人犹不能无词,况于或罚之、或赏之乎?故其免于罪而蒙赏者不知愧怍,而反谓朝廷之可欺,偃蹇傲睨,日以滋甚。陛下损金帛以赐士卒,适以资其刻剥之计。至于怨雠并兴,无以自解,乃复奏功第赏,超越资级,动以数万。……方无事时,朝廷有所使令,率以诏旨行下,或阴为迁延,或公肆欺玩,或直抗执而不行。[3](P13)
针对上述当时南宋军队普遍存在军政荒芜腐败的严重现象,汪应辰认为南宋军队战斗力不强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兵力不足,而是有以下几点原因所致:
一是军政不修:“不知一旦有急,能惟命是听以徇国家之难乎?四方之人,何所观望?三军之士,何所动沮?虽有貔虎百万,将谁用之?故臣之所忧,不在乎兵之不足,而在乎军政之不修也。”[3](P14)
二是兵多而冗。汪应辰以三国诸葛亮出师攻魏为例分析指出:“诸葛亮出师无功,或劝以益兵者,亮曰:‘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反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减兵省将,明罚思过,校变通之道于将来。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自今以后,有忠虑于国者,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死,功可路乔足而待矣。’由此观之,亮非徒不 肯 益 兵 也,又 欲 减 省 之。”[3](P14)而 当 时 南 宋 军 队“且今中外之兵,其老弱强壮,不可得而分也;其逃匿死亡,不可得而见也。然则虽欲益兵,亦不知其所以益矣。”[3](P14)他进而强调指出:“盖胜败在将不在兵,兵多而冗,不若少而精也。”[3](P14)
要提高当时南宋军队战斗力,汪应辰认为就必须革除弊病,加强修治军政。那么,如何加强修治军政,他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精兵强将,将得其人,操得其柄。汪应辰指出:“昔(唐代)陆贽有言,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将非其人者,兵虽众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将虽材不为用。兵不足恃与无兵同,将不为用与无将同,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赋以殄人也。”[3](P13)他接着以北宋仁宗时谏官范镇、大将狄青为例进一步指出:“至和中,朝廷招募新兵,谏官范镇以为财用不足、民力凋敝而又欲募兵,是何异欲救火而益以薪,流之浊而复挠其源也。兵不在众,在练之与将何如耳!方侬智高寇岭南之后,遣将不知几辈,遣兵不知几万,死亡奔北,不可胜纪。然狄青所以取胜者,番落数百骑耳,此兵不在众,近事之效也。”[3](P13)所以,他认为陆贽、范镇之说切中当时南宋军队之弊病,值得借鉴采用,当务之急是要将得其人,精兵强将,从而提高军队战斗力。
其次,要治军有法,整治军纪,正名分纪律,严密军制。他分析指出:“何谓治军有法?……况于兵者,聚天下骁勇之徒,粟之以不可向迩之器,而教之以战斗杀伐之事,其所恃以制御柔服之者,以有名分纪律也。”[6](P22)他认为唐末祸乱继起,兵革不息的重要原因是名分纪律不明:“一切姑息,上下之分不明,士卒不知有偏裨,偏裨不知有将帅,祸乱继起,兵革不息者,凡二 百余 年。”[6](P22)而北宋初令行禁止,中外肃然,东征西讨,无思不服,主要原因是“我太祖始定军制,使以阶级相承,毫厘之间不容侵越。”[6](P22)汪应辰进而认为当时益修武备,应将儒家理学的礼义思想运用于军事教阅训练中,严正名分纪律,以提高战斗力:
今欲专任将臣,益修武备,则宜以名分纪律为先,而所任以领其事者,乃独不用等级,既非所以尊朝廷,亦非所以率其下矣。或者以为今帅守之职,初不废也,特教阅之际不相统临,其余则自依军制也。臣窃以为天下之事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将教人以父子之义,则必制为坐立拜跪之仪;将教人以兄弟之序,则必制为徐行后长之节。盖有文具而本未必然者,未有荡然无文而以为其本犹在也。今既已不相统临矣,则所谓军制者,其能以独立哉?孔子为政,以正名为先。盖名正则言顺,而事成也有其名,然后可以责其实。[6](P22)
最后,汪应辰希望南宋统治者能够内自省察,行至正之道,申严军纪,加强军队训练,提高战斗力:“以前日之失为在己,奋发英断,力行大公至正之道,而不牵于异说之私,赏善罚恶,无偏无党,示天下以好恶所在,使人皆洒心易虑,以听陛下所为。然后兵籍之多寡,人材之高下,皆可以按见其实。谨其训练之法,号令必行,等级必明,技艺必精,心志必一,周旋进退将无所不可者矣。”[3](P14)
上述可见,汪应辰提出精兵强将,将得其人,严正军队名分纪律,行至正之道,加强军队训练以提高战斗力的这些军事思想主张,可谓是切中要害,鞭辟入里,这实际上也是他儒家理学思想在如何加强修治军政问题上的充分反映,在当时南宋军事建设上具有它的重要战略意义。
五、御戎以自治为上策
绍兴三十一年(1161)底,金兵南侵失败之后,金主新立,遣使通和。南宋朝廷苟且偷安,对于当时金的情况了解不实,传闻不一,因而摇摆不定,正如汪应辰所指出:“盖自今日以来,传报不一,或以为金主宽厚,能得众者;或以为懦弱不立者;或以为急于和亲,欲复还河南地者;或以为彼方厚立赏格,以勤战士,如唐、邓、陈、蔡之类,失而复取,其志盖未已者;或以为河朔群盗扰其南,而契丹之遗种攻其北者。”[3](P10)
针对当时对于金的情况了解不实,朝廷受各种传闻扰惑,第二年(1162)五月汪应辰在轮对《应诏陈言兵食事宜》中明确提出,不要受各种传闻扰惑,为国者不当问敌人之盛衰,而应该积极修治内政,使国力强盛,即所谓自治,才是御敌之根本。他分析指出,东汉光武帝初定天下,臧宫、马武皆以为匈奴衰落,时不可失,而光武帝答以北边匈奴尚强,从而屯田以加强警备。而南宋当时关于金的传闻之事“常多失实,古今通患,实在于此。要之,为国者不当问敌人之盛衰,顾吾自治何如尔。”[3](P10)接着,他又以东晋为例进行分析,再次强调自治的重要性:
东晋之季,符坚以百万之师,战胜之威,长驱入寇,自谓投鞭于江,足断其流。至于淝水之战,敌众奔溃,首尾不支,卒以亡国。然则敌人虽盛,未足为中国患也。晋之谋臣皆欲乘符氏败亡,开拓中原,王师一出,尽得兖、青、雍、豫之地,然而君臣宴安,无复顾虑。以谢安之勋劳犹不见容,而道之、元显之流,出而用事,晋之不振皆自此始。然则敌人虽衰,未必为中国福也。臣故曰:不当问敌人之盛衰,顾吾自治何如尔。[3](P10)
南宋与金长期对峙,金对南宋的威胁最大,而在如何抵御和应对金的威胁问题上,时人议论不定。汪应辰在轮对奏议《论御戎以自治为上策》中则进一步提出御戎以自治为上策的重要思想。他十分赞同唐朝杜牧提出御敌上策莫如自治的主张:
唐杜牧追咎长庆以来朝廷措置无术,复失山东,作《罪言》曰:若欲悉使生民无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东,兵不可去,是兵杀人无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法令制度,品式条章,果自治乎?障戍镇守,干戈牛马,果自治乎?井闾阡陌,仓廪财赋,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敌为虐。环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复有天下阴为之助,则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为浪战。[7](P64)
他认为杜牧所说的自治才是根本:天下之事,变化百出,不可以穷于应付,“自其本求之,则一言而足,杜牧所谓自治是也。”[7](P64)如果 舍其本而求末,则虽千万言终也毫无益处。汪应辰接着分析指出,春秋战国之际,多事之秋,孙武助吴之攻战,张仪助秦之纵横,奔走旁午,当时各国君用之,天下为之骚然,得不偿失。然而“孟轲居其间,独曰:‘盖亦反其本矣。’”[7](P64)孟轲之所谓反本,则是杜牧所主张的自治。汪应辰认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盖自开国以来至于今,未有不自治而能治人者。牧之说,则虽圣人复起,不能 易矣。”[7](P64)汪应辰指出,杜牧所说的上、中、下三策中,只有自治,修治内政,使国力强盛,这才是对付敌人的上策,其余中、下策皆不足取:
自治之外复无他策矣。今以自治为上策,而又有中策、下策,是未始有定论也,是谓其君不能也。若(孟)轲则不然,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夫不能治其国家则已矣,岂复更有中策、下策者哉?[7](P64)
汪应辰最后强调,只有当时南宋统治者能够以自治为本,使国力得以强盛,才能做到作战则胜,防守则固,讲和则久。他说:“臣窃惟今日所以待敌人者:曰战、曰守、曰和,然此三者皆末也,要当以自治为本。吾之国家治矣,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所谓修其本而末自应。”[7](P64)
总之,在宋金南北紧张对峙,战事持续不断,南宋积弱的背景下,汪应辰作为一个士大夫,以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根据当时政治军事形势,针对当时政治和军事上存在的弊病,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军事主张和思想。针对朝廷因宋金和议而因循无备、苟且偷安之可畏现象,汪应辰呼吁朝野上下要有“思患预防,常若敌人之至”的忧患意识,加强军事守备,在当时可谓是振聋发聩;从南宋国家军事战略安全的角度出发,汪应辰主张高度重视长江上流地区的军事防御,积极谋划,采取措施加强防备;针对当时南宋水军在海上处于劣势,汪应辰主张应该扬长避短,不可盲目从海上迎击敌人,而是应该发挥陆上优势,以逸待劳,陆海结合,掌握时机消灭敌人。上述这些军事主张和思想充分反映了汪应辰深邃的军事战略眼光。
同时,针对南宋当时军备松弛,军政荒芜的严重问题,汪应辰主张修治军政,精兵强将,强调治军有法,整治军纪,严密军制以及行至正之道,加强军队训练以提高战斗力;在如何抵御和应对金的军事威胁问题上,汪应辰强调御敌以自治为上策,只有当时朝廷能够自治为本,国力得以强盛,才能做到作战则胜,防守则固,讲和则久。汪应辰加强修治军政、自治为本以御敌的这些军事主张,则是他“内圣而外王”儒家理学思想在军事问题上的充分体现。虽然汪应辰的这些军事思想和主张在当时未能完全得到统治者宋高宗、宋孝宗的重视和采纳,但是依然闪烁着其光芒,对后人有着一定启迪和价值。
[1]汪应辰.文定集(卷一)[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
[2]辛弃疾.辛弃疾全集校注[M].徐汉明校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3]汪应辰.文定集(卷二)[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
[4]脱脱.宋史(卷194)·兵志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脱脱.宋史(卷195)·兵志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汪应辰.文定集(卷三)[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
[7]汪应辰.文定集(卷七)[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