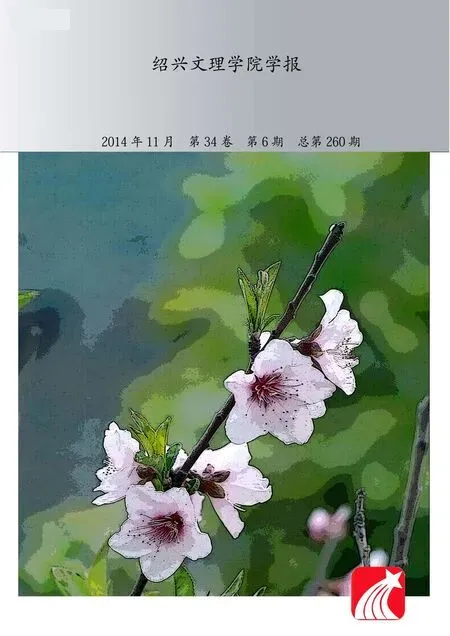论张中晓《无梦楼随笔》的抗争意识
韩 璐 卓光平
(绍兴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绍兴312000)
论张中晓《无梦楼随笔》的抗争意识
韩 璐 卓光平
(绍兴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绍兴312000)
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潜在写作”的代表作之一,绍兴作家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所展现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精神抗争,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有着重要价值。在《无梦楼随笔》中,张中晓始终以浓烈的抗争意识保持着对良知的坚守和对生活的睿智思考,而张中晓的抗争意识正是通过映射在文本中的文人气节与理性精神呈现出来的。
《无梦楼随笔》;张中晓;文人气节;理性精神;抗争意识;越文化
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潜在写作”的代表作之一,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无疑印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气节。众所周知,自1955年5月受胡风冤案牵连以后,张中晓虽然身处劣境,贫病交加,但是他一直坚韧地通过随笔写作来坚持自己的精神追求和思想探寻。而作为一位生于越地长于越地的绍兴文人,张中晓身上流淌着越文化的精神血液,骨子里明显继承了鲁迅等越地先贤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无梦楼随笔》记录了张中晓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面对极左思潮时的心路历程和思想抗争,反映了他不屈的性格,表现了他的睿智与理性。因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无梦楼随笔》不仅有着较高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一、《无梦楼随笔》的抗争意识及其独特意义
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写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前后历时近十载。张中晓去世三十多年后,整理者路莘以对一个未曾见过面的朋友的责任感整理了张中晓在家乡绍兴养病时写下的三本思想笔记——《无梦楼文史杂抄》《拾荒集》《狭路集》,并将其合为一集命名为《无梦楼随笔》。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地下文学”创作,《无梦楼随笔》与《顾准日记》《傅雷家书》《沈从文家书》等一样发出了那个时代被压抑的文人的真实心声。对于这些“潜在写作”,援引李慎之评价《顾准日记》的话来说,它们“是一个时代的实录,一个受难的灵魂的实录”[2]10。这些“潜在写作”在当时恶劣的社会环境下虽然只能以破碎的形态存在,但却是时代的真声。《无梦楼随笔》是张中晓在被剥夺正常的创作权利时记录下的颇为复杂的情感心理的随感和杂记,在50至60年代的“潜在写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无梦楼随笔》是张中晓在人生最困顿之时写作完成的,字里行间凝聚着他对现实生活的思索,对真理与正义的追寻,以及与现实命运的抗争。张中晓在随笔中多次提到“斗争”“努力”“坚持”等字眼,他以一个坚韧的思想斗士来定位自己,让自己树立正确的人生路标,为坚持真理而抗争。正因为他身上坚韧的文人气节,在遭受压迫时才会挺直腰板来反抗强权;也正因为他真理在握,面对社会的不公才会不顾一切地去揭露虚伪。张中晓挺立起知识分子的傲骨,毫不妥协与屈服,不断发扬读书人的良知与勇气,与社会的不合理现象斗争到底,可以说整部《无梦楼随笔》就是他心灵的抗争史。
与《顾准日记》《傅雷家书》《沈从文家书》等几部“潜在写作”作品相比,《无梦楼随笔》中的抗争意识显得尤为浓烈。对张中晓来说,他坎坷的人生经历对其随笔中抗争意识的形成有着决定性作用。张中晓年纪轻轻便涉嫌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而锒铛入狱,连像其他右派分子“下放”改造的机会也没有,又因严重的肺病不能干重活而少有集体劳动和外出活动的机会,因此孤独一人很少与外界接触。相比于用口语来总结一天学习工作的《顾准日记》而言,张中晓的随笔缺少生活气息与人情世故,更多是来自阅读作品后的思考,是将书本道理对应有限生活得出的结论,蕴含很重的说理意味。随笔写道:“君子卓行绝识……独立不惧,坚贞不移……不惟一毫不动,而更是磨练生平学力识力之好机会。”[1]63面对孤独依然在危难中看到机遇,坚持不懈地抗争。“一个正直的人应当以愉快的语言推进各种有价值的努力。追求真理,为正义而斗争。”[1]106在窘境中不断尝试,念念不忘抗争。牵扯胡风案受排挤这一关键因素不允许张中晓融入社会,这点是随笔抗争意识在同时代“潜在写作”中尤为浓烈的一个重要原因。张中晓在《无梦楼文史杂抄·后记》中提到自己作随笔的目的,涉及“大义微言”“后日之观”等词汇,大意是敝帚自珍不忍弃之,较之日记体更具经世致用的动机性,可见在落魄形势下,仍能做到“不以己悲”“著书立言”,此行为本身即是抗争。张中晓在严酷的处境中仍顽强抗争,坚韧思索,故其《无梦楼随笔》令读者为之动容。
就写作风格而言,如果说《傅雷家书》和《沈从文家书》属于“闲话风”,那么《无梦楼随笔》与《顾准日记》则属于“独语体”。“独语体”较之“闲话风”具有明显的排他性,故而《无梦楼随笔》的文字较之家书亲切感人的温情对话则显得有些不近人情。如随笔中所写:“人在这世间的确是慌乱和孤独,都会心存叵测,有便宜可得则和好,一旦吃亏则恶绝,亲戚则冷淡无情,同事则尔虞我诈。”[1]71张中晓未婚,无子嗣,缺少为人夫与为人父的体验;其自身被迫与亲生父亲分离,兄弟也因他下放边疆。未来家庭茫然无形,现有家庭支离破碎,因而孑然一身,单调生活使前文两本家书中常提及的衣食住行等琐屑之事在《无梦楼随笔》中极少见,纵然有也是“早餐阙如”“咯血之后”等悲怆的语句,可见张中晓的随笔缺少家书特有的那种天伦之乐。即便如此,张中晓仍不懈斗争,“知识人的道德责任,坚持人类的良知。只有正直的人们,才不辜负正义的使命。”[1]115《无梦楼随笔》字里行间可谓将抗争意识彰显得淋漓尽致。
张中晓《无梦楼随笔》的抗争意识在同时代“潜在写作”中一枝独秀。正是由于不被允许融入社会而缺少世俗生活的经历,正由于孤独,也源于贫穷困窘,更因为自身不屈不挠的斗争,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的抗争意识才没有被生活磨去锋利的棱角,才没有受裙带关系牵连而拖泥带水,才没有受家庭子女的牵绊而无法决绝,而随笔的抗争意识才得以完整地呈现出来。《无梦楼随笔》的抗争意识相较于同时代的“潜在写作”显得坚定和沉毅,对当时“地下文学”甚至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思想史以及精神史的价值定位都具有重大意义,抗争意识通过张中晓的文人气节与理性精神融会贯通而呈现了出来。
二、《无梦楼随笔》与张中晓文人气节的发扬
作为一名中国知识分子,张中晓有着传统文人“士不可以不弘毅”的气节,他在《无梦楼随笔》中将自身的文人气节渗透到文字中。事实上,张中晓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尤其深受传统士人的人格精神感染。孩提时代的他便接触古典文学,“张中晓五六岁时,他父亲就向他诵读和讲述《古文观止》《左氏春秋》《战国策》的故事,他后来总忘不了‘三言成虎’、‘董狐直笔’的教训。”[3]169传统文化的礼义廉耻在他心中留下烙印,教会他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这为他五六十年代表现出来的抗争意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家乡绍兴养病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古籍,古典文化的字字箴言警醒着他。他在随笔中写道:“人情率始勤而终怠,易发而难收,此言软弱的意志与无意志也;坚忍不懈,能放能收,坚强的意志也。”[1]17“应付危机,宜光明正大。或追求真理,独行其愿;或中不自乱,幽人贞吉”。[1]119他阅读《周易》《左传》《三国志》《魏晋玄学论稿》《荀子》《薛文清公读书谈》《韩非》等等古典著作,并将感想写入随笔,以此来鼓励自己:“易曰,自强不息。易之动力在人之能振作(意志)”[1]44。“无梦楼案曰:大易教人以艰贞,发扬战斗精神也,高扬心灵的道德力量也。”[1]52随笔中虽然也不乏许多批判宋明理学等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学说的言论,但不可否认张中晓的确受到传统文化的很大影响,从而形成了自身的文人气节。
张中晓对于传统的士大夫、君子一类的人是非常敬佩的,他在随笔中写道:“《后汉书·马援传》论,夫利不在身,以谋则智;需不私己,以之断义必厉。”[1]42对于东汉大将军马援不徇私利己的大丈夫气魄赞赏有加。随笔提到:“昌黎之所谓发潜德之幽光者……而更重要为受屈受冤者发言也。斯正气之所申天理之所存也。”[1]52话语中流露出对唐代韩愈为民请愿的正直为人的钦佩。张中晓发扬文人气节,歌颂君子道德气节,如其所说:“《礼·书仪》,君子不食溷余,道德自乐也。无梦楼案:中土二千年封建社会中的士……惟君子方可乐其道,小人仅能便其器也。”[1]58
张中晓除了受到古代士人的影响,也深受鲁迅、胡风等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作为现代中国的“民族魂”,鲁迅影响了现代许多知识分子,其中,胡风就受鲁迅影响极深。胡风主张的“主观战斗精神”和鲁迅在“五四”特别是三十年代杂文创作的“批判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胡风强调受磨难的痛苦、拒绝肤浅的颂歌与鲁迅认为读书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6]292有着极其相似之处,那就是作为一个文人就应像战士一样活着,要有气节,活着就要抗争。张中晓曾这样说道:“《时间》,同鲁迅底杂文一样,它指出了我们底路,我真切地感觉到,新的人民道路非这里走出来不可!”[4]24钱理群评价过鲁迅、胡风、张中晓三者的关系:“胡风所起到的‘鲁迅’与‘张中晓们’之间的桥梁作用是非常明显的。”[7]58鲁迅与胡风的作品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文人气节,这与张中晓受到古典文学中的文人气节影响是一脉相承的,并最终“合力”汇聚在张中晓身上。张中晓在大学和养病期间反复阅读《鲁迅全集》《七月》《希望》等书刊,他认为:“鲁迅的伟大,是因为他是一个战斗者,是道德的存在,是激动人心的力量。”[1]76张中晓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在鲁迅那里找到了共鸣,他在随笔中写道:“(老子)他强调相对现象成为绝对原则,在相反的方式上成为杀人灵魂的软刀。”[1]17“庄子——消灭了人生的庄严感,彻底的虚无主义,市侩主义和厌世主义。”[1]14“(庄子)自我欺骗,糊涂苟活,是他的人生态度。”[1]16随笔还提到“鬼魅”“软弱”等词,字字掷地有声,随笔中的“市侩主义”“马虎了事”“禽兽的哲学”等用词辛辣,完全颠覆了老庄的圣人形象。这很容易使人想到鲁迅《故事新编》中《出关》《起死》对老子和庄子的批判。老庄思想以无意志对抗坚强的意志,缺乏文人的良知与气节,因而最终落败。
显然,张中晓所继承的鲁迅先生“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文人气节以及伴随这种气节的抗争意识,正是源远流长的越文化精神的一种体现。早在上古时期,越人面对数次海侵造成的沧海桑田,就出现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表现了越地先民敢于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的精神。鲁迅也曾在小说《理水》中赞扬过大禹坚韧不拔地带领人们治水的事迹。张中晓在《无梦楼随笔》中引用了唐代韩愈《争臣论》中针对大禹的论述:“自古圣人贤士……不敢独善其身,而必兼以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对于人类的责任,道德的光辉,乃圣人贤士也。”[1]24尽管原文为了论述韩愈的党同伐异,论据仍然肯定了大禹顺天意,同情百姓,艰苦卓绝的品格。越地人杰地灵,越中名士就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句践,针砭时弊的王充,不拘礼教的徐渭,不畏强暴的陶成章、徐锡麟、秋瑾,而同样身为绍兴人的张中晓也是越文化精神的忠实继承者与发扬者。越地先贤嵇康曾以仗义执言、狂放任性来表现对虚伪世俗的抗争,张中晓在《无梦楼随笔》中引用嵇康《释私论》“有宰嚭耽私,卒享其祸之语”[1]42来论述公私之辩,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张中晓虽被定性为“反革命”,却仍以国家的富强民主为己任,与造反派抗争到底,这正是他实践公义胜私欲的表现。从大禹与自然作斗争,到鲁迅与封建势力作斗争,再到张中晓与文革造反派的顽强斗争,越人传统基因中的勇悍坚忍已融入一代代人的血液中,而越文化的特质之一——抗争精神也随着越人的传承而源远流长。
张中晓一直坚持顽强抗争,他在随笔中写道:“只有信心,给人注入信心,使人继续下去,坚持,不屈不挠,赞助之,鼓励之,附合之,才能使之坚强起来。”[1]72“困难的时候,是显示一个人的品格、能力和意志的机会。”[1]106虽然一直深陷逆境之中,但张中晓毅然坚定不移地抗争,俨然是凝固在风雨中的战士形象。正如其所说“即使狂风和灰土把你埋没了,但决不会淡忘,当精神的光明来临,你的生命就会更大的活跃。”[1]115而面对苦难做出的是非抉择尤能检验文人,“越是经历过苦难越应当珍惜自己和宝贵的生命。苦难越多,生命也越宝贵,越有价值。”[1]36人面对世俗的黑暗而清醒地活着就如同受难,这就使得活着比死亡更需要勇气。外界环境越是险恶,自身抗争才越显珍贵,这更表明了若无一股强大的力量支撑,不等张中晓战斗到底,恐怕他羸弱的身体早就垮掉了,这股力量就是一个文人从灵魂深处散发出来的人格精神。
三、《无梦楼随笔》与张中晓理性精神的坚守
《无梦楼随笔》的抗争意识一方面表现为文人气节的发扬,另一方面则是对理性精神的坚守。不论是面对残酷的政治斗争,还是面对窘迫的现实生活,张中晓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以理性精神和理智思维面对人生,进行抗争。他曾在《拾荒集·序》中说道:“临亢者固须理智克制,处卑时尤须理智照耀。”[1]67可见张中晓清楚意识到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都需理智来约束自身,而《无梦楼随笔》的抗争意识也正是以理性批判呈现出来的。
张中晓酷爱阅读西方哲学著作,在与西方哲人进行心灵交流的过程中逐渐培养了他的理性批判精神。张中晓具有阅读英文原著的能力,他不仅“自修到已能读《莎氏乐府本事》”[4]16,还能针对他人译作的好坏做出深刻评论:“最近听说有一本《杜勃罗留波夫研究》……但错误很多,把metaphysical method of thinking译作‘思惟底玄学方法’。看来是毫无哲学知识的。”[4]26张中晓不仅经常阅读柏拉图、黑格尔、康德、狄德罗、车尔尼雪夫斯基、斯宾诺莎等西方哲学家的著作,而且还阅读了《史迁普金》《圣经》《哲学史讲演录》《伦理学》《罗曼·罗兰文抄》等大量西方名著。在群众热烈追捧领袖思想的五六十年代,张中晓却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希腊、德国、法国、西班牙等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并写下大量札记、随笔。他在阅读西方哲学间隙中思想,在思考过程中阅读,在思想的历练中逐渐形成理性精神。
自身文化功底过硬,使得张中晓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被官方文字与评论所误导,这为他在极左的思潮中能够坚持抗争奠定基础。他说:“歌德‘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一语,应当解释为:在各个思想领域和精神工作中,一切应当是哲学和生命,理性和经验的结合……纯粹理性的思辨是灰色的,但实践理性却有着生机的跳动。”[1]90张中晓反复要求自己像哲人那样思考,他在随笔中写道:“要以哲学家的语言来说话,不以嫖客的语言来说话。应当是明彻的智慧,而不是热烈的激昂。壬寅年元旦诚笔书此于无梦楼。”[1]46这句话中的“诚笔书此”是一个伏案书写抗争的倔强背影所留下的,而句中的“哲学家”表明其以此作为标准来要求自己,他围绕着理性来展开抗争。他将理性看作是与恶势力抗争的必备品性,如其所说:“个人血肉的天性(任性),必须经过理性的改变(外在教养、锻炼……)才能成为具有现代水平的东西。”[1]23可以说,也正是理性精神使张中晓没有跟随大流在谬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极左思潮中,张中晓一直保持着独立的思想坚守显得非常难能可贵。他清楚意识到文艺政策的不合理,但他没有叫嚣,而是清醒地认识到“人所面对的实际上是广大的中间层”。[1]78他的这句话有力批驳了当时流行的“一元论”,批驳了被简单化直接化的“阶级成分”鉴定法。不幸的是,他本人深受这一方法论的迫害,常无缘无故被拉去审查,但是他冷静地认识到:“如果一个人想从紊乱不堪的日子中脱颖而出,最重要的是要使精神的导线指引那附丽生命中的一片盲目的混乱。这是终生的工作。精神的导线=理性的力量……”[1]71张中晓内心的真实想法也只有在原本给自己看的《无梦楼随笔》中才让后人知晓,文字虽无声,抗争却掷地有声,感人肺腑。
张中晓辩证地看待情与理,他说:“在每一个人的心灵中,理智和感情永远是矛盾的,而意志在谁战胜谁的斗争中起着决定的作用。”[1]116他将意志作为决定性因素,即使其内心无比痛苦,纵使外部条件极其不利,即便生活极为困顿,他仍保持高度清醒。随笔的句子常以“应当”“必须”“不要”等命令式口吻出现,表明他在不断尝试说服自己。这些话起到安慰作用的同时,也是自我心灵的对话,亦是在激励反省指导自己如何与这不公的世界抗争,同时也将一个理性抗争的灵魂展露在读者面前。明知会有悲剧的结局仍义无反顾斗争到底,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品质正是一代文人良知的印证。张中晓一生身处劣境坎坷之中,但他的理性精神使他超越了痛苦,《无梦楼随笔》就是最好的见证。这股理性精神与他的文人气节已融为一体,支撑着他在追求真理顽强抗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越走越坚强。
总之,《无梦楼随笔》中的抗争意识是异常浓烈的,而正是这种抗争意识使得《无梦楼随笔》具有独特的价值意义。尤其是在文学创作陷入口号式呐喊与学术研究依附权贵的年代,张中晓在《无梦楼随笔》中表达了一个正直文人的真挚情感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探索,显示出其难能可贵的精神与品质。知识分子固有的文人气节与理性精神所凝聚的抗争意识一直支撑着他一路前行,并在不断尝试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更坚守着自己的信念。《无梦楼随笔》所展露的知识分子坚守正义理性的社会担当与深刻反思的价值立场,以及蕴含的抗争意识正是张中晓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1]张中晓.无梦楼随笔[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
[2]顾准.顾准日记[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3]罗银胜.王元化和他的朋友们[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4]张中晓.无梦楼全集[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
[5]梅志.胡风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6]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钱理群.张中晓提出的问题——读《张中晓和胡风的通信》[J].书城Book Town,2008(1).
On Resistance Consciousness in Zhang Zhongxiao’sInformalEssaysofWumenglou
Han Lu Zhuo Guangp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otential writing” in the 1950s and 1960s, the Shaoxing writer Zhang Zhongxiao’sInformalEssaysofWumenglou, which exhibits the intellectuals’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spiritual struggle, is of great value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of literature and ideology. InInformalEssaysofWumenglou, Zhang Zhongxiao consistently holds to the clear conscience and gives life a wise thinking with an intense resistance consciousness which manifests itself in the integrity and rational spirit of the literati in the text.
InformalEssaysofWumenglou; Zhang Zhongxiao; integrity of scholar; rationalism; resistance consciousness; Yue culture
2014-09-15
韩 璐(1991-),女,浙江宁波人,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2010级本科生;卓光平(1982-),男,湖北随州人,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讲师,浙江大学在职博士后。
I206.7
A
1008-293X(2014)06-0063-05
(责任编辑张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