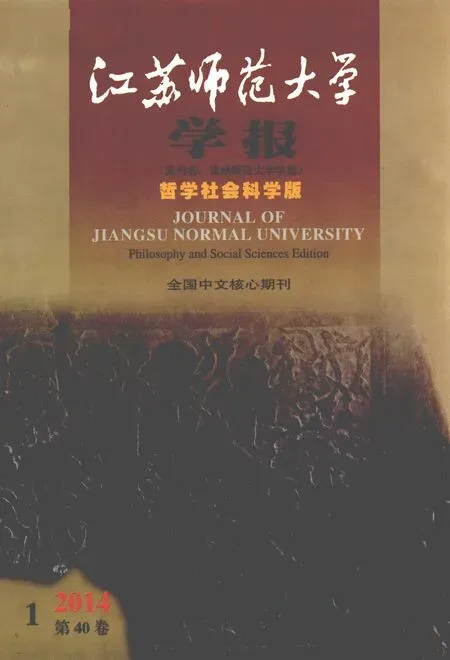当代文学想象与国家形象构建
——以乡土文学创作为视角
郝敬波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当代文学想象与国家形象构建
——以乡土文学创作为视角
郝敬波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当代文学;国家形象;乡土文学;文学想象;乡土中国
国家形象是一个认知和评价的综合体,并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进行建构和传播。中国当代文学是国家形象内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其艺术建构的重要方式。乡土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以此为视角,可以整体观照当代文学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真实面貌,有效探讨前者之于后者建构的诸多可能性。从创作实践来看,当代乡土作家主要以怀恋式、联想式和寓言式三种乡土情结形态来呈现自己的情感经验,并集中以“结构性”和“阐释性”两种想象方式言说人与土地关系的时代变迁,以乡土中国的书写实施对国家形象的艺术建构。由于乡土经验的断裂和乡土世界变化的复杂性,乡土作家的这种想象书写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乌托邦的特点,形成了对乡土中国形象的某种遮蔽和误读。突破历史的局限将为国家形象的艺术建构提供新的可能,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也是深化国家形象理论和实践研究所要面对的课题。
随着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地位的变化,人们对国家形象话语的关注变得日益广泛和深入。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形象研究视野的拓展也随之成为了一种趋势和必然,“国家形象,作为大国崛起中的文化动员,必然要从国际关系和新闻传媒扩展到其他方面,扩漫到文学和艺术上,哲学和理论上”[1]。尽管目前关于国家形象的理论研究尚处于“进行时”,许多问题还存在着诸多争议,但国家形象被认为是一个认知和评价的“综合体”[2],并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进行建构和传播,这应该是没有多少歧义的。本文拟从这一层面上来反思当代文学与国家形象的关系。
毋庸置疑,中国当代文学所进行的想象和书写是这个“综合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其建构和传播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乡土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传统,在中国当代文学乃至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都具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现代白话小说诞生之后,如果在题材范畴内谈论的话,最成功或者成就最大的,应该是乡土文学或后来被称作‘农村题材’的文学。”[3]因此,以乡土文学创作为视角,可以整体观照当代文学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真实面貌,从而有效探讨前者之于后者建构的诸多可能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农村经济、文化的复杂转型,乡土文学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如此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中国乡土小说创作不仅出人意料地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低迷中走了出来,形成一个新的高潮,而且从外形到内质,都发生了不同于以前的颇为显著的变化,生长出许多不容忽视的新质,亦即发生了新的转型”[4]。乡土文学的这种变化和转型是在乡土中国形象的时代变迁中进行的,因而乡土文学对乡土中国的书写方式就成为当代文学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内涵,并具有了某种代表性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乡土文学入手反思和探讨当代文学与国家形象建构之间的艺术关联,对于二者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艺术建构的情感起点
与其他建构方式相比,文学对于国家形象的建构有着更多的特殊性。文学是个体化的艺术创造,其对于国家形象的建构是一种艺术建构,作家的情感经验往往决定着其艺术手法和书写方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国家形象的艺术建构。从乡土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几乎所有的当代乡土作家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乡土情结”,这种情结是长期孕育和积淀的情感经验,是他们进行乡土文学创作的原点和动力,也是对于国家形象进行艺术建构的情感起点。情结总是伴随着某种距离的产生而发育和生成的,对于乡土情结而言,乡土作家往往是离开了“乡土”之后而产生的一种内心深处的情感纠葛。“一般来说,和现代西方乡土小说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绝大多数乡土小说作家,甚至说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乡土作家都是地域性乡土的逃离者,只有当他们在进入城市文化圈后,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乡村文化的真实状态;也只有当他们重返‘精神故乡’时,才能在两种文明的反差和落差中找到其描写的视点。”[5]这一点显然与非乡土作家的创作情形是不一样的。同样具有乡土情感经验的作家,其乡土情结的具体形态也不尽相同,从而构成了风貌不同、纷繁多样的乡土世界。
为了进一步探讨这种情感经验对于形象建构的影响,我们可以将当代作家的乡土情结大致分为以下三种形态:一是怀恋式的乡土情结。这种情结形态具体表现为作家对乡土的一种极为浓郁的情感,沉浸着对乡土故乡挥之不去的记忆和怀想。更为重要的是,在作家的头脑中,怀恋式的乡土情结是现实和具体的,是历历在目的人与物交织在一起的乡村图景。“十七年”中的乡土作家如赵树理、周立波、柳青、马烽、李准等往往都具有这种情结形态,尽管这种情感经验与政治情感不同程度地交织在一起。在新时期,贾平凹应该是怀有这种情结的典型作家,其小说《秦腔》就明显表现了这一点。贾平凹在《秦腔》的《后记》中写道:“当我雄心勃勃在2003年的春天动笔之前,我祭奠了棣花街上近十年二十年的亡人,也为棣花街上未亡的人把一杯酒洒在地上,从此我书房当庭摆放的那一个巨大的汉罐里,日日燃香,香烟袅袅,如一根线端端冲上屋顶。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歌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6]贾平凹的这种沉郁的乡土悲情,显然是从对故乡的人与物的具体记忆和想象中孕育和积淀的。二是联想式的乡土情结。与怀恋式的乡土情结不同,尽管作家对故土乡村同样具有一种沉积的情感,但这种情感的存在形态是有差异的。作家往往把这种情感在广阔的时空中弥散开来,以故土乡村为一种精神图腾展开联想,打开乡土情感的时空纵深,来表现积淀在心中的乡土情结。最为典型的应该是莫言。莫言一直说自己是农民,他与山东高密的乡土情结是难以割舍的。值得关注的是,莫言的乡土情结是以对高密的时空联想方式存在的,他以高密作为情感原点,以发散型的思维探寻着乡土世界的历史和现在、物质和精神的复杂世界,而不同于贾平凹在《秦腔》中对棣花街细密的情感编织,因而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一书的扉页上为小说作了这样的情感注脚:“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7]三是寓言式的乡土情结。这种情结形态往往表现为对乡土情感的抽象化,它不是怀恋式的情感念想,也不是联想式的情感抒发,而是从浓烈的乡土情感中抽离出一种观念,将丰厚的乡土情感简洁化甚至符号化,以一种寓言的方式表达对乡土世界的情感和思考。阎连科可以称得上是寓言式乡土情结的代表作家,《年月日》、《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等小说中奇谲的梦幻形象都使其创作打上了寓言式书写的色彩。
无论以上哪种情结形态,都是来源于作家对乡土世界的记忆和眷恋,来源于作家对乡土世界中人与土地的情感亲近,来源于由此而产生的复杂的乡土情感经验。可以说,中国当代优秀的乡土文学作品都是在这些乡土情结中产生的,比如陈忠实、路遥、王安忆、韩少功、刘震云、迟子建、李佩甫、张炜、孙慧芬、关仁山、赵本夫、刘醒龙、刘恒、乔典运、刘庆邦等作家的一些乡土小说。值得注意的是,如上所述,乡土情结是作家离开故土乡村后所生成的情感积淀;也就是说,正是作家与乡土的现实距离产生了不同形态的乡土情结。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在乡土情结中产生的文学书写,是否能够有效地表现正在变化中的乡土世界?或者说变化最为复杂的乡土中国形象在文学创作中是否得到了真实的艺术呈现呢?有评论家指出:“当前乡村社会正经历着巨大而艰难的转型,其中的政治、经济、特别是伦理文化在接受着现代文化的巨大冲击,较之新文学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当前乡村社会的变化和复杂都是最显著的。但是,我们在当前乡土文学中却鲜见对这种变化的深刻揭示。它们或者是流于作家个人情感的宣泄(包括贾平凹、陈应松等较突出的作家创作中都有显著的表现),或者是对生活停滞的记叙(在许多西部作家的创作中可以普遍地看到这种迹象)。其中或许有地方风情,或许有文化记忆,但却没有对现实的深刻把握和真实再现,没有展现出乡村社会在时代裂变中的真实状貌、复杂心态和内在精神。”[8]因此,当代作家以乡土情结为情感起点所建构的乡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联性是值得反思和审视的,这对于我们探究当代文学与国家形象的关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正如韦勒克和沃伦所说:“倘若研究者只是想当然地把文学单纯当做生活的一面镜子、生活的一种翻版,或把文学当做一种社会文献,这类研究似乎就没有什么价值。只有当我们了解所研究的小说家的艺术手法,并且能够具体地而不是空泛地说明作品中的生活画面与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关系,这样的研究才有意义。”[9]
二、形象建构的现实图像
人、土地无疑是所有乡土文学中最主要的书写对象和叙事主题,伴随着几十年来中国社会改革的巨大变化,人与土地关系的改变是空前的,因而也成为乡土文学的叙事焦点。从创作情况来看,无论是对“农民工进城”的观照,还是对“城市异乡者”的书写;无论是对乡村传统的批判,还是对乡村风土的怀恋,实际上都是围绕中国乡村的这种人与土地关系的变化而展开的。对于人与土地关系的书写和想象,可以说也是乡土文学建构国家形象的主要内容和方式。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人与土地关系的视角来审视和反思当下的乡土文学创作,更有必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现实中的乡土中国,从而客观地把握这一形象建构的现实图像。
那么,应该怎样认识人与土地关系改变的现实图像呢?我们在这里不妨进行一个大致的梳理,以便从整体上观照当代文学创作关于人与土地的叙写。从乡土生活中人与土地关系的疏密程度的视角出发,可以把这种关系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紧密型的关系。紧密型的关系是传统的人与土地关系的延续,具体表现为人与土地是不可分离的依附关系,人依旧把耕种劳作作为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从当前中国乡村的整体情况来看,可以说大致50岁以上的村民是构成紧密型关系的主要人群。这部分群体是中国传统乡土文化的最后留守者,他们秉承了祖祖辈辈对于土地的观念和情感,以“庄稼人”的身份保持了与土地的紧密关系,以传统农民的生存方式不自觉地抵制着乡村的时代变化。二是松散型的关系。具有这个关系特征的主体多集中在30—50岁之间。他们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不是完全依赖式的紧密关系,而是一种“半依赖”的松散关系。他们的生存状况已经受到乡村变化的巨大影响,传统的乡土观念在他们身上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与土地根深蒂固的关系已经逐渐松动,于是他们的脚步悄然从乡村的土地上迈开,走向城镇和城市中去获取更多的生活利益。然而,他们依然是以土地为家,也从事农忙耕作,只是把城镇和城市作为临时的“打工点”,不断地穿梭在城乡之间,相对于紧密型的关系而言,这种联系是一种较为松散的人地关系。三是脱离型的关系。脱离型的关系是指无论从生活方式还是情感观念等方面都已经与传统的人地关系区别开来,这部分群体主要集中在30岁以下的青年人。他们基本上已经从乡村的土地上脱离了出去,几乎没有从事农耕活动的经验,分布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谋生行当。这个群体是当下中国城镇化的主体,他们一部分漂泊在大城市里生存下来,更多的是在小城镇中定居了下来。尽管从土地制度上来说他们在农村尚有一份土地,但他们基本上与土地上的农事无关,间或踏上故土或者尚存一些对土地的情感,或许更多地来源于一种家庭伦理关系的需要。
乡村中人与土地的关系是由以上三种关系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网络,正是这种纷繁交错的人地关系构成了当下乡土世界丰富变化的现实景观,缺失了其中任何一种关系的呈现,当下的乡土世界都是不完整的。而且,这三种关系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由于乡村复杂伦理关系的存在,三种关系在此基础上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融进了中国乡村巨变的时代洪流。因此,对任何一种人与土地关系的孤立书写都是对乡土现实图景丰富性的遮蔽,也极易形成对当下乡土世界的一种乌托邦想象。当下的乡土文学书写实际上也注意了这一点,以不同的表现手法力图完成对“乡土中国”的艺术建构。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如上所述,由于作家乡土情结形态的不同,作家往往不能够深刻地实施对人与土地关系的把握,或者说在全面把握人与土地关系的变化上尚显得力不从心。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乡土情结是作家离开土地之后积淀生成的,因而他们笔下的人与土地的关系往往是记忆中的乡土图像,也就是说,当下不少乡土文学中的乡土世界是“过去式”的,而不是“进行时”的,这与当下的城市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乡土记忆是乡土作家创作的重要源泉,人与土地的关系也是作家关于乡土世界极其重要的记忆空间。从现代文学史来看,鲁迅、彭家煌、许杰、蹇先艾、许钦文、台静农、沙汀、艾芜都是在离开故土的环境之后,通过对乡土的记忆来书写的。从小说题材的来源来看,鲁迅等早期的乡土作家仅仅凭自己的乡土记忆就能创作出优秀的乡土小说,譬如鲁迅的《故乡》、彭家煌的《怂恿》、许钦文的《病妇》、台静农的《地之子》等。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这些作家所处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的总体变化并不是非常显著的,特别是人与土地的关系并没有出现巨大的改变,因此,作为乡土小说的叙事背景是相对稳定的。作家的创作诉求也不是聚焦乡土世界的变迁,不是展示人与土地关系的可能变化,而是深刻地审视和剖析社会制度和传统乡土文化对人的影响。在小说《故乡》中,“我”“回到相隔两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算是简单交代了叙事的背景,并没有铺陈当时乡村的现实图景。鲁迅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对闰土进行了艺术刻画,便深刻地表现了那个时代农民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如果把闰土放在一个动荡变化的乡村世界中,特别是在人与土地变化的乡土背景中,那么这个形象就缺乏必要的建构空间,缺乏必要的阐释背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乡村人与土地的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而引起了整个农村面貌的改变,这当然对乡土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作家再仅仅依赖一种乡土情结和记忆,就很难准确地展现乡土世界的真实变迁,于是才有柳青落户陕西乡村、周立波迁往湖南老家等一批作家融入乡村生活的创作活动。除却政治因素对作家的影响之外,体验乡村生活、把握乡土变化无疑是作家走进乡土世界的内在动力。尽管像《山乡巨变》、《创业史》这样的小说明显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它们对乡村变化以及农民精神状态的鲜活展现无疑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家对农民的历史境遇和心理情感的熟悉,弥补了这种观念‘论证式’的构思和展开方式可能出现的弊端”[10],它们的表现方式和艺术价值也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问题。而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变革无疑是一场更为深刻的革命。如何丰富地展现当代乡土世界的复杂景观,深入地探析这场变革中农民的精神世界,是当下乡土文学创作不可回避的问题。但是,从阅读感受来看,乡土文学中让人感受深刻的依然是“记忆中”的乡土世界,从而也显露出许多作家在乡土历史经验方面的一种断裂。正如有学者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与‘乡土世界’相关的小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作家的历史意识出现了裂痕,不再有着完整的内在逻辑,对于充满了生机和混乱的现实,在价值判断上呈现出茫然和困惑。”[11]在这种情况下,当下变化中的乡村往往作为乡土记忆的一种续曲,而这种续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作家的乌托邦想象构成的。
三、想象方式与形象建构
文学创作当然离不开想象,但想象也必须具有艺术的真实性,由此而产生的象征和寓意也应该建立在对现实真实性的把握之上,“小说也正是以这种方式达成了它的叙事与它由叙事所显示的象征寓意之间的平衡——作品的象征寓意,是由对于人物境遇的极具现实性的真实展现凝结而成的”[12]。譬如,卡夫卡想象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文学的形象建构是对一个世界的艺术创造,它必须依靠创作主体的想象力,而且这种想象力必须建立在对构建对象的真实认知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文学的艺术世界才是自然、深刻和富有逻辑的。正如美国文学批评家布鲁克斯、沃伦在其名著《小说鉴赏》中认为的那样:“小说可以从任何事物发源,只要这些事物能激发人的想象力从而去完成小说的特殊使命,即把事物有机地联系起来并从中生发出某种意义来——不,不仅仅是联系起来就够了,而且要创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各种事物相互依存而其中又富有意义。”[13]乡土文学对当下变迁乡土的书写当然也少不了艺术想象的表现方式,但这种想象不是凭空而来的,不能仅凭作家的才气联想而来,也不应当是为一种预设的观念而进行的乡土情节虚构,而应是建立在作家对当下乡村生活变化的充分了解之上,建立在对人与土地关系改变的把握之上,建立在对乡土中国历史变迁的深刻认知之上。只有这样,乡土文学才能真正对应于乡土世界的时代变革,才能鲜活地展示当下的乡土生活,深刻地表现历史变迁中的乡土世界,真实地触摸当下乡土中的精神世界。然而,许多的乡土作家往往以自己乌托邦的“想象”方式来呈现当下的乡土世界,阐释人与土地的时代变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乡土中国的建构路径。其中,以下两种“想象”的类型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
一是“结构性”的想象。不少作家明显感到当下的乡土世界已是今非昔比,自己的乡土记忆已经覆盖不了乡村的变化。如此一来,作家在一部作品中娴熟地使用完乡土记忆的资源后,此时文本中的乡土世界对于真实的乡村来说并不是完整的,其中关于乡村“现场“的图像缺失就是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为了弥补这种乡土书写“结构性”的不足,作家往往通过想象来拥有这部分并不熟悉的乡土资源,从而来完成一次完整的乡土世界的艺术建构。在这个过程中,作家的心态也是非常失落和矛盾的。正如贾平凹所说:“我的创作一直是写农村的,并且是写当前农村的,从《商州》系列到《浮躁》。农村的变化我比较熟悉,但这几年回去发现,变化太大了,按原来的写法已经没办法描绘。农村出现了特别萧条的景况,劳力走光了,剩下的全部是老弱病残。原来我们那个村子,民风民俗特别醇厚,现在‘气’散了,我记忆中的那个故乡的形状在现实中没有了。农民离开土地,那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将无法继续。解放以来农村的那种基本形态也已经没有了,解放以来所形成的农村题材的写法也不适合了。”[14]贾平凹在《秦腔》中力图叙述清风街近二十年的乡土景观,特别是表现该地正在发生的时代变迁。小说用极其细密的书写方式去编织乡村的精细图像,塑造了夏天义、夏天智、夏君亭、张引生、白雪等鲜明的人物形象来表现多种文化力量的融汇和对抗。在小说描写的整个乡土世界中,最为生动鲜活的依然是传统的乡土画面,很容易看得出作家对于这些生活画面的熟悉和眷恋,小说也因此成为传统乡土文化的一曲挽歌。而小说关于对清风街带来冲击的一些变革元素的描写则显得有些生疏和僵硬,譬如夏君亭力建农贸市场、丁霸槽开的带有色情服务的万宝酒楼的描写就多带有主观臆想的印痕,像挤进去的“楔子”,用以建构变化之中的乡土世界。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莫言的小说《蛙》中,譬如,小说对袁腮开办代孕公司的描写就显得较为单薄,完成代孕公司的指代意义或许正是作家对其想象书写的主要诉求。这种“结构性”的想象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小说叙事的长度,拓展了小说叙事的空间,在表现作品主题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小说的艺术逻辑性,弱化了小说应具有的艺术感染力,影响了作品对于乡村变迁中人与土地关系的书写深度。
二是“阐释性”的想象。长期积淀的乡土情结无疑使作家对乡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关注和创作冲动,但由于不少作家对当下的乡土世界缺乏像以前那样的体验和把握,在创作中往往表现出一些概念化的思维。比如,乡村的人与土地的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传统的农民身份产生了历史的改变,传统的乡土文化受到了时代的冲击,农民离开土地的漂泊和挣扎,打工者难以融入城市的尴尬和苦痛等等,对于许多作家来说,诸如此类的观念并不是从新鲜的乡村土地或活生生的农民身上获得的,而是从社会学的一些结论或大众媒体的观点上截取的,不少作家在表现这些主题话语的时候往往就出现了主题先行的问题,小说所进行的叙事就很容易存在“阐释概念”的先天不足,此时叙事中的想象部分就具有了一种“阐释性”想象的特点。这种“阐释性”的想象在当下的乡土文学创作中是较为普遍的。米兰·昆德拉曾经说过:“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是说出惟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15]因此,“阐释性”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小说本身的艺术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乡土小说应该丰富、鲜活地展现当下的乡土世界,以文学艺术的方式为读者提供乡土世界变化的复杂性和可能性,而不应是以想象的故事去说明一种观念,去阐释一个道理。
由于人与土地关系的改变,乡土小说的叙事边界也随之扩大。进城的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进入到作家的创作视野,作家对农民工的书写多为描述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经历片段,并没有把农民工放在人与土地关系的层面上去观照,而是更多地叙述农民工在城里的挣扎和艰辛,间或增加农民工的某些不合时宜的行为来营造黑色幽默的效果。对于丰富的精神世界而言,笔者觉得这是对农民工书写的一种简单化处理。农民工离开土地走进城市,其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叙事空间。但由于作家对当下农民生活的陌生感,致使他们在创作时要么割舍农民工之于土地的复杂关联,只是凭“农民工”一词试图让这种关系不言自明;要么就采取“阐释性”想象的方式去弥补经验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往往选择叙述农民工的“另类”故事,用以增强创作的自信。小说中的故事一般诉说农民工奔波和辛酸的求生之路,表现他们作为“异乡者”的漂泊的精神感受,反映这部分底层群体的生存状况。这些故事实际上弱化了农民工与土地之间的精神联系,如果从农民的视角来看,这些故事只是一种“传奇”,而不具有农民故事的普通性,难以有血有肉、深入细致地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以及当下人与土地关系的复杂变化,因而小说的叙事想象也难以达到一种艺术的真实。《泥鳅》是尤凤伟新世纪以来创作的一部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小说以农村青年国瑞的生活为叙事线索,描写了一群打工者在城市的悲惨命运。其中,国瑞的遭遇最具传奇性。他经过一番打拼,似乎要混迹到城市的上层,被委以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但这是城市的一个陷阱,只是被人利用以便从银行骗贷。因骗贷负法律责任,最后国瑞被判处死刑。小说故事光怪陆离,让人印象深刻,表现出作家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小说显然在很大程度上阻隔了国瑞等人与乡土之间复杂的内在联系,只是简单地赋予他们以农民工的标签,并用“泥鳅”作为其身份的一种象征。因此,国瑞与城市里非农民身份的底层打工者的遭遇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这样一来,小说关于农民工的叙写就缺乏对这个社会群体独特属性的具体观照。换句话说,这部小说的创作起点是从农民工在城市里的生活场景开始的,并没有从国瑞所走出的那块土地上去寻找人物的精神踪迹,正如尤凤伟在讲述创作这部作品的缘起时所说,“他是在晚报看到了打工妹受到凌辱、打工仔在中介公司受骗的社会新闻,促使他要为这些农民工‘立言’”[16]。因此,在笔者看来,这部小说的叙事便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一些“阐释性”想象的印痕。
四、结语
毋庸置疑,包括乡土文学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对国家形象的建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对上述问题的审视也是源于对国家形象的关切,以及对当代文学的关注和期待。正如亨利·詹姆斯指出的那样:“小说有着一个毫无障碍的场地供它驰骋,如果它倒毙的话,那肯定是由于它自身的过错——换句话说,由于它的浅薄,或者由于它的胆怯。就是为了出于对它的爱,我们几乎喜欢想象它受到了这种命运的威胁,这样就可以设想,一个具有起死回生之术的大师施展其妙术使它复活时的戏剧性的一幕。”[17]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上的叙述或许充满了风险性,特别是一些分类和命名更是一种冒险的行为。但在我看来,或许它们的价值正是便于为我们打开一条回眸和眺望的路径。从当代乡土文学创作的具体情况来观照,乡土情结是乡土作家积淀的情感资源,其存在形态的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土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在这个过程中,以人与土地关系变化为核心的乡土中国变迁的复杂性实际上也冲击着作家的乡土情结,从而又不同程度地调整着作家乡土情结形态的变化。需要指出的是,怀着浓郁的乡土情结,面对着人与土地关系的现实复杂性,乡土作家用一种乌托邦的乡土想象来调节自己与创作客体的紧张关系,这也只是乡土文学所表现的一种创作特点和叙事方式。当然,也有一些作家如关仁山、孙慧芬等一直用一种深切的关注来延续自己的乡土经验,努力表现人与土地改变的乡土世界。譬如关仁山的小说《麦河》,就在人与土地关系的视阈中书写了乡村土地权益流转的现实问题,充分表现了在此基础上农民生活的动荡和精神世界的微妙变化。此外,像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更以一种“非虚构”的书写方式,为乡土中国的形象建构提供了新的可能,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总而言之,乡土中国的改变从不同的层面深刻影响着当下乡土文学的创作,乡土文学还远远没有完成对时代变迁中的乡土中国形象的书写。从这个视角出发,可以说当代文学的想象在国家形象的艺术建构方面,还存在着许多值得关注和反思的问题。如何突破历史的局限,为国家形象的艺术建构提供新的可能,则是中国当代文学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也是深化国家形象理论和实践研究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
[1]张法:《国家形象概论》,《文艺争鸣》,2008年第7期。
[2]如管文虎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见管文虎主编:《国家形象论》,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3]孟繁华:《乡土文学传统的当代变迁——“农村题材”转向“新乡土文学”之后》,《文艺研究》,2009年第10期。
[4]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5]丁帆:《乡土——寻找与逃离》,《文艺评论》,1992年第3期。
[6]贾平凹:《秦腔·后记》,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517页。
[7]莫言:《红高粱家族》,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8]贺仲明:《乡土文学的地域性:反思与深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9][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页。
[10]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11]王光东:《“乡土世界”文学表达的新因素》,《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
[12]王耀辉:《文学文本解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页。
[13][美]布鲁克斯(C.Brooks)、沃伦(R.P.Warren):《小说鉴赏》,主万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69页。
[14]贾平凹、郜元宝:《〈秦腔〉与乡土文学的未来》,《文汇报》,2005年4月22日。
[15][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16]尤凤伟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和上海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泥鳅》作品讨论会”上的发言,见《尤凤伟新作〈泥鳅〉引起关注》,《文汇报》,2002年6月3日。
[17][美]亨利·詹姆斯:《亨利·詹姆斯文论选》,朱雯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mag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Literature
HAO Jing-bo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 221116,China)
contemporary literature;national image;local literature;literature imagination;local Chinese
The national image is a complex of cognition and evaluation that spreads and constructs through various forms and channels.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s an indispensable component part of the national image and is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the artistic construction.Local literature has extremely important status and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From this perspective,it can see the truth of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the whole national image construction and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of how the former constructs the latter effectively.From the writing practice,contemporary native writers express their emotional experience mainly in three native forms——Nostalgic,Associative and Allegorical.They focus on the"structural"and"interpretation"the two imaginary relationships to tell the times changes between man and land.Also,they complement the artistic construction by writing about the Chinese countryside.Because of the complexity of local experience of the fracture and local changes of the world,this imaginative writing with the feature of Utopia forms a folk Chinese image obscured and misread.Breaking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he history offers new possibilities for the national image construction of art which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that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needs to face.
K207.42
A
2095-5170(2014)01-0057-07
[责任编辑:周 棉]
2013-08-19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构建研究”(主持人:徐放鸣,项目编号:12AZW003)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短篇小说艺术范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3BZW122)阶段性成果,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阶段性成果。
郝敬波,男,江苏徐州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