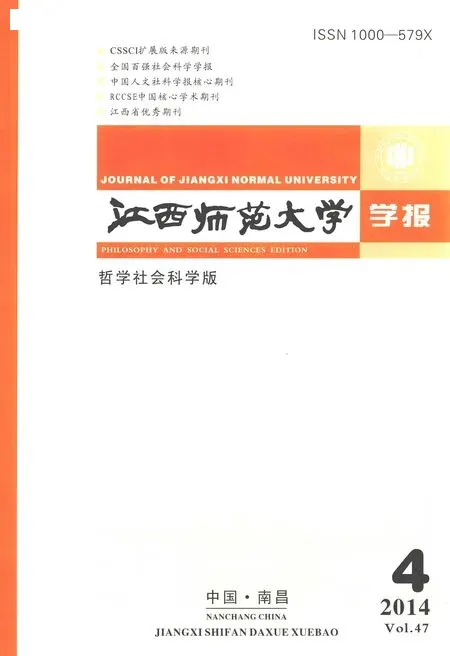唐代古文运动与山东士族的家学门风
李建华
(宁波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唐代古文运动与山东士族的家学门风
李建华
(宁波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中唐时期,随着山东士族的复兴,古文运动蓬勃发展。在骈文盛行的中古时期,山东士族有不废古文的优良传统。古文运动的精神实质与山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相契合,同样具备宗经的传统、反佛的立场以及尚功用、重实际,反对浮华风气的特点。山东士族对古文的勃兴居功甚伟,参与并引领了古文运动。
山东士族;古文运动;家学门风;儒学
自魏晋以降,骈文以其辞采的华艳、形式的整饬风靡文坛。下殆有唐,文坛诸家无不延承风绪,三代两汉的古文则被遗置一隅,浸微将绝。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以复古为己任,远绍三代两汉的古文传统,将古文运动推向高潮。在古文的发展过程中,山东士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唐代古文运动的开展与成功与山东士族的参与密不可分。
所谓山东士族,就是以五姓高门为代表,主要包括荥阳郑氏、范阳卢氏、太原王氏、陇西李氏和赵郡李氏、博陵崔氏和清河崔氏等五姓七家及其婚姻集团。唐代山东士族对古文运动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古文运动的主张和精神实质与山东士族门风相契合,符合山东士族的根本利益。
一、引言
骈文兴起于南朝,由于片面追求美学效果,往往忽视了文章内容,逐渐变得浮艳。北人倡导儒家文艺思想,崇尚质朴刚健的文风,北朝文风总体上是复古主义的。处于北朝的山东士族较少受到南朝文风的影响,南朝文风往往与山东高门家风相牴牾,据《唐国史补》:“崔颢有美名,李邕欲一见,开馆待之。及颢至,献文,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起曰:‘小子无礼!’,乃不接之。”[1](p162)
崔颢少年时文风浮艳,唐人殷璠《河岳英灵集》称:“(崔)颢少年为诗,属意浮艳,多陷轻薄,晚岁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2](p161)李邕出自山东士族赵郡李氏江夏房,是唐代书法大家,但其文学成就远不及书名之盛。崔颢文学创作极有成就,其献于李邕之诗歌《王家少妇》,全文如下:
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自矜年最少,复倚婿为郎。舞爱前溪绿,歌怜子夜长。闲来斗百草,度日不成妆。
此诗写一位贵族美少妇生活的娇逸自得,颇有齐梁遗风,李邕怒斥崔颢说明了齐梁文风与山东士族传统家学门风存在很大区别。对此,胡应麟说道:“‘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是乐府本色语,李邕以为小儿轻薄,岂六朝诸人制作全未过目邪?唐以诗词取士,乃有此辈,可发一笑。”[3](p186)崔颢虽然不为李邕所重,却被杜希望奖拔。杜希望为杜牧曾祖,以边将进用。杜氏家风沦丧,故有杜希望之子杜佑晚年的“以妾为夫人”、“母丧不去官”[4](p818)以及杜佑孙杜牧的诗酒风流。李邕与杜希望对崔颢不同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家族家风的迥异。
儒学与文学常相龃龉,有时候还会处于对立的地位。山东士族本不重文学,陈寅恪先生在论及出自山东高门清河崔氏的崔浩时说:“(崔)浩之通经律,重礼法,不长属文,及不好老庄之书等,皆东汉儒家大族之家世传统也,与曹操父子之喜词赋慕通达为东汉宦官寒族之传统家学者迥异。”[5](p154)与寒门子弟好文辞不同,作为数百年来的文化士族,山东士族特别重视传统经学的教育。
殆及中唐,执政的山东士族开始标榜传统的门风,奖掖礼法之士,甚至公开反对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反对进士的浮夸风气。山东士族的世传经学、礼法门风在关陇贵族的统治下是不合时宜的,但是他们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崇高的社会声望使其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一旦他们掌握政权,又开始恢复其固有门风(经学传统)。
李德裕的家庭比较典型,其祖李栖筠在“仕进无他途”的情况下,在族子李华的执意请求下,以进士及第。李栖筠一方面被迫参加科举考试,另一方面又认为进士科“试辞赋浮文,非取士之实”。[6](卷一四六《李栖筠传》)李德裕任武宗朝宰相时对武宗说:“臣祖(李栖筠)天宝末以仕进无他岐,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6](卷四四《选举志上》)当指此事。
唐代进士所试辞赋与梁萧统所编《昭明文选》有密切关系,欲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必须精读《文选》。科举举子有“《文选》烂,秀才半”[7](p100)之谚语,连大诗人杜甫也要求儿子“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由于《文选》的选文持“详近略远”的标准,大量近代作品被收入。*综观全书,在入选作家中,西汉以前(含西汉)总共只有22家,而仅晋朝就有45家;在入选作品中,屈原、宋玉、司马相如三人加起来才28篇,西晋陆机一人就有130篇,南朝谢灵运、江淹等人作品入选也相当多。南朝骈文占据文坛主体,唐代所试诗赋效仿《文选》,多为南朝文体样式,与山东士族固有门风相去甚远。
陈寅恪先生说:“《文选》为李氏(李德裕)所鄙视,石经为郑覃所建刊,其学术趣向殆有关家世遗传,不可仅以个人之偶然好恶为解释。否则李文饶固有唐一代不属于复古派之文雄,何以亦薄《文选》之书?‘熟精文选理’乃进士词科之人即高宗、武后以后新兴阶级之所致力,实与山东旧族以经术礼法为其家学门风者迥然殊异,不能相容耶?”[8](p74)
唐代山东高门家传儒学,文学只是其进身的工具。他们大多主张在文学创作意旨和文字风格上,应该以六经为归依。古文运动提倡的宗六经、尚质实的古文与山东士族古老门风是一致的。
二、山东士族的家学门风
(一)宗经的传统
自汉武帝崇儒政策推行之后,士人开始重视子弟教育,从而向士族转变。东汉君臣多好儒,由于东汉建都于洛阳,属于秦汉以来的山东文化区域。因此,这一文化区域的士族即山东士族成为累世经学的代表。
东汉世家大族强调“累世经学”,荥阳郑氏的代表人物郑玄是东汉大儒,其对儒学影响之深,罕有其匹。郑玄入关后就学于大儒马融,学成后辞归山东,马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9](卷六五《郑玄传》)郑玄沉沦典籍,遍注群经,儒学著作凡百馀万言,代表了汉儒的最高成就。清河崔氏被称作:“崔为文宗,世禅雕龙。”[9](卷八二《崔骃传》)其代表人物是东汉大儒崔骃,崔骃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自崔骃之后,清河崔氏世有美才,遂为儒家文林。
由于东汉以来,山东地区的文化积淀一直优于关中和江左,其儒学传统亦非其他地区所能媲美。自北朝以来,山东高门社会地位最为隆盛,这与其家传经学传统有关。如北魏名臣高允出自山东高门渤海高氏,他“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10](卷四八《高允传》)与高允同时的李曾出自赵郡李氏,他少治《郑氏礼》、《左氏春秋》,以教授为业。其子李孝伯,少传父业,于崔浩被诛后总揽机要。山东士族家传儒学,其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这也正是北学繁荣的基础,正如《魏书》卷四七《卢玄传》所载:“卢玄绪业著闻,首应旌命,子孙继迹,为世盛门。其文武功烈,殆无足纪,而见重于时,声高冠带,盖德业儒素有过人者。”山东士族“为世盛门”源于他们自东汉以来的家学传统。
隋文帝混一南北后,四方群儒靡不毕集,“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11](卷八一《儒林传序》)足见山东经学之盛。
唐代山东高门以其儒素德业迥异于寒庶,并因此于有唐一代延祚不绝。崔良佐出自博陵崔氏,是唐代大儒,其子元翰少传父业,权德舆《比部郎中崔君元翰集序》云:“(崔良佐)探古先微言,著《尚书》、《演范》、《周易》、《忘象》及《三国春秋》幽观之书,门人诸儒易其名曰贞文孝文。君(崔元翰)绍文宗雕龙之庆,究贞文法义之学,洁廉清方,敦直庄明,博见强志,不取合于俗。”崔良佐父子绍继东汉以来的家族传统,以经学世代相传。
唐代荥阳郑氏能远绍先祖郑玄之风,谨遵儒术。郑覃本故相郑珣瑜之子,长于经学,稽古守正,曾上奏文宗曰:“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12](卷一七三《郑覃传》)唐文宗遂刊刻《九经》于石碑(今藏西安碑林),而当时主持刻经的正是郑覃。
(二)反佛的立场
中古时期,中国佛教臻于极盛,同时也带来了传统文化与佛教所谓的华夷之辩,最终酿成了被释氏称作法难的“三武灭佛”。作为华夏文化的代表,山东士族以儒学世代相传,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受到山东高门的攻讦。
山东高门参与并影响了“三武灭佛”运动。北魏太平真君年间的灭佛与出身于山东高门清河崔氏的崔浩有密切关系,源于寇谦之与崔浩的天师道改革。崔浩母出自范阳卢氏,崔浩与天师道的领导者卢循两人实为中表兄弟,其家世相传之信仰,自属天师道无疑。崔浩于释氏殊无好感,站在尊华攘夷的立场上称佛祖释迦牟尼为“胡神”。[10](卷三五《崔浩传》)
崔浩于太武帝时总揽机要。当道士寇谦之献书于太武帝遭冷遇时,崔浩上疏赞明其事,经过崔浩的解释,太武帝遂信行其术。“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10](卷一一四《释老志》)实际上,寇谦之虽推崇道教,但并无灭佛之意,崔浩决意灭佛时,“(谦之)苦与(崔)浩诤,浩不肯”。[10](卷一一四《释老志》)正是在崔浩的鼓动下,太武帝下诏灭佛,太平真君年间大规模的灭佛运动由此拉开了帷幕,而出自山东高门的崔浩直接促成了此次灭佛运动。
唐武宗会昌时期的崇道毁佛事业也与山东高门的影响有关。会昌二年(842),分别出自山东高门太原王氏与范阳卢氏的检校左仆射太常卿王起和广文博士卢就向武宗提出恢复用大祠之礼祀道教的九宫贵神。[12](卷二四《礼仪制》)唐武宗会昌时期,出身于山东高门的李德裕大权独揽,“会昌灭佛”与李德裕有密切关系,宋人陈善认为:“会昌之政,(李)德裕内之,其深信道家之说,恐非但武宗之意。”[13](卷一○)汤用彤先生说:“武宗信道毁佛,卫公(李德裕)亦不喜释氏,宜其毁法至酷烈也。”[14](p47)也认识到李德裕对会昌灭佛的影响。
唐武宗会昌时期的宰相中:李德裕与李绅出自赵郡李氏;崔珙与崔铉出自博陵崔氏;李让夷出自陇西李氏;郑肃出自荥阳郑氏。会昌灭佛自然与山东高门掌控的权力中枢有密切关系,山东高门的家族门风对武宗的灭佛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三)经世致用的家风
东汉以来,山东士族以儒学世代相传。汉代经学强调经世致用,儒学经典《春秋》、《尚书》亦带上了浓厚的实用功能。六朝时期,玄学兴起,老庄思想盛行。玄学主要影响了江东吴姓士族以及永嘉南渡的侨姓士族,而滞留北朝的山东士族犹能恪守传统礼法。与南朝儒学重视探隐索微,推求义理不同,山东士子赅博坟典,他们将儒学应用到实践中,置于家族和国家的秩序建设,形成了北朝尚功用、重实际的士风。
六朝时期,儒学本身也是作为生活实践之学发展起来的。《魏书》载:“(崔)浩能为杂说,不长属文,而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10](卷三五《崔浩传》)清河崔浩的家学是北朝山东士族家学的典型。与南朝侨姓士族不同的是,他们“不好老庄之书”;与东汉经学相比,他们更“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清河崔氏家学注重实用,这也是北人“尚实”的传统。
清人赵翼也认识到北学的实用性,他认为北朝经学“其所以多务实学者,固由于士习之古,亦上之人有以作兴之”,[15](p313)将北朝经学称为实学。山东士族家学代表了北朝经学的最高成就,因此,北周武帝灭北齐后首先拜访北齐大儒熊安生,隋文帝平一寰宇后,原北齐统治的山东地区,学者尤多。清人皮锡瑞认为北学胜于南,“由于北人俗尚朴纯,未染清言之风、浮华之习”,[16](p127)肯定了北学尚功用、重实际的传统。至于北学胜南的原因,皮锡瑞理解为北人的纯朴。事实上,北学胜于南学,绝非五胡统治者和庶民之功,北方士族尤其是山东士族才是支撑北学繁荣的根本。
山东高门以积极入世为主,其所以能从东汉迄有唐绵延数百年而冠冕不绝,与其经世致用的家学门风密切相关。北朝时期,山东高门子弟为了维系宗族力量,不顾夷夏大防而仕于五胡;唐代山东士族为了自身发展,随时俯仰,积极参与科举考试,与寒门庶族子弟在科场上一较高下。这都是山东士族尚功用、重实际家风的体现。
三、古文运动的精神契合山东士族的门风
(一)古文流变中的宗经传统
古文运动的健将们实际上并不十分重视文学,他们常常将儒学置于文学之上,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古文运动轻诋六朝沿袭下来的骈文,主张恢复三代两汉的古文,往往以儒家六经为宗旨,而这与山东士族“通经律,重礼法,不长属文”的传统家学是一致的。
唐初文坛沿袭六朝遗风,陈子昂最早提倡复古,这对当时文坛起到了摧陷廓清、振聋发聩之效。陈子昂的好友,出自山东士族范阳卢氏的卢藏用最早认识到陈子昂的贡献,他在《唐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说道:“昔孔宣父以天纵之才,自卫返鲁,乃删《诗》、定《礼》、述《易》道而修《春秋》,数千百年,文章桀然可观也。孔子殁二百岁而骚人作,于是婉丽浮侈之法行焉。……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卢藏用没有夸耀陈子昂文学创作的艺术性,注重的是其教化的意义,这是当时古文家对文学的理解,也正是儒家思想的文艺观。
对唐以前历代著名文学家如何总结是摆在古文家面前的一个重要难题,对此,出自山东高门赵郡李氏的李华在《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介绍了萧颖士对前代作家的评价:“君以为六经之后,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壮而不能经。厥后有贾谊,文词最正,近于理体。枚乘、司马相如,亦瑰丽才士,然而不近风雅。”萧颖士和李华所肯定的作家大抵在魏晋之前,但对于《文选》中以文学名世的重要作家,如屈原、宋玉、枚乘、司马相如等“瑰丽才士”则以为“不近风雅”。古文家往往反对魏晋以来的艺术本位思想,追求复古宗经,进而推崇“六经”的载体——散体单行的古文。
从“萧李”开始的古文运动多以六经为宗旨,他们轻视六朝文风,往往将经学置于文学之上。李华为文主张宗经,他在为博陵崔沔所写《赠礼部尚书孝公崔沔集序》中云:“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夫子之文章,偃、商传焉。偃、商殁而孔伋、孟轲作,盖六经之遗也。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李华为文主张宗经,强调文章要表现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发挥教化作用。
古文运动的先驱人物柳冕共有传世文章14篇,其中论文作品占了8篇。柳冕认为有德行的人才可能写出好文章,风俗淳美则文学自盛。他抱持极端的儒家教化思想,对屈宋以下的辞赋诗歌一概否定,要求“尊经术,卑文士”(《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甚至不以文士自居。他在《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中云:“昔游、夏之文章与夫子之道通流,列于四科之末,此艺成而下也。苟言无文,斯不足征。小子志虽复古,力不足也,言虽近道,辞则不文。虽欲拯其将坠,末由也已。”柳冕与柳宗元出自同一家族,他虽喜好论文,但却缺乏应有的文人认同感,更似一个道学家。
作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提倡写古文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文体改革,而是为了宣扬圣道。他认为:“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送陈秀才彤》)韩门弟子李汉出自山东高门陇西李氏,李汉秉承韩愈之志,他说:“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序》)在大多数古文家的眼里,文章只是他们布道的工具。
大多数古文家的复古运动并不是站在文学革新的立场而是站在儒学复兴的立场之上的。古文家在鄙视文学的同时,往往十分重视经学,很多古文家实际上是打着宗经的旗号来反对骈文家的,他们具备深厚的经学基础并留下了相关著作。《新唐书·艺文志》留下了古文家大量的经学著作书目,如:卢藏用著有《春秋后语》十卷、韩愈注《论语》十卷、樊宗师《春秋集传》十五卷、柳宗元《非国语》二卷等。
唐代是文学昌盛而儒学衰落的时代,古文家在倡导儒学的同时,常常将文学置于儒学的对立面而加以谴责。山东高门有重经学而轻文学的传统,古文运动正是儒学的复兴运动,古文家的复古目标符合山东士族的根本利益。我们看到,古文运动实际上是儒学的复兴运动,散体与骈体文之争只是儒学与文学之争的副产品
(二)古文家的反佛立场
与山东士族排佛之家风相类似,古文家往往据儒反佛。韩愈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也是著名的反佛斗士。初盛唐时期,佛教大行于天下,举国上下皆从风而靡,惑于释氏者甚夥。韩愈素不喜佛,他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原道》)韩愈反佛建立在夷夏之辩的基础之上,将佛教视同夷教。当时,佛教各宗派都有自己的祖统,如禅宗即有所谓西天二十八祖和东土六祖之说并深入人心。韩愈在《原道》中也建立了儒家的道统谱系:自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而至孟子,成为佛教各宗派强大的对立面,其影响十分巨大。
中唐以后,山东士族全面复兴,中华本土文化逐渐为士人所重。这一时期,复古思想开始抬头,由于尊华攘夷的传统,士人们将矛头指向佛教。针对遍布朝野的佛风法雨,韩愈写出著名的《论佛骨表》:
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以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12](卷一六○《韩愈传》)
韩愈冒着生命危险向唐宪宗上书谏迎佛骨,强调的就是夷夏大防。韩愈的继承者李翱亦据儒学反佛,李翱认为:“佛法害人,甚于杨墨。论心术虽不异于中土,考较迹实有蠧于生灵。浸溺人情,莫此之甚,为人上者所宜抑焉。”(《再请停率修寺观钱状》)韩愈和李翱等古文家多谨遵儒术,鲜有旁骛,他们往往将文与道结合起来,主张“文以贯道”,反对佛教的悖礼行径,对宋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古文运动的实用主义
由于魏晋以来的南朝强调艺术本位,骈文在这样的土壤上逐渐繁荣。南朝自齐梁以后,散文逐渐衰落。北方文风质朴,在南方盛行骈文之际,北朝散文却出现了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郦道元《水经注》这样的作品。北人“尊儒”和“务实”,在文学方面,其“仿古”和“复古”的主张远比南朝人激烈,虽有南朝文学的引进,对传统的重视始终没有中断,散文的繁荣为南朝所不及。永嘉之乱后,地处河北的山东高门未及南渡,滞留于北朝。由于他们笃信汉儒家法,没有受到南朝骈俪文风的影响,为文尚能恪守古文传统。北魏出自山东高门的名臣崔浩、高允等皆擅长散文。
自魏晋以降,文坛竞骋文华,遂成风俗。骈文以其对称、声律之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文士所喜好,并压制古文而独步文坛。三代两汉古文有极强的实用性,儒家经典的教化作用可以使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是修身、齐家、治国的思想武器。骈文夸辞藻以饰章句,一味强调形式美,忽视了文章的实用性,其缺点正如隋代李谔上书所云:“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损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17](卷六六《李谔传》)
针对当时文坛词藻犹多淫丽的骈俪之风,中唐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开始攻讦骈文的浮靡竞丽、华而不实的风气,主张斫雕为朴的质实之风。韩愈文章力求陈言务去,倡导文从字顺的朴实简洁之风。柳宗元文章也洗净铅华,力求清通晓畅。
六朝骈文过于强调艺术本位,忽视了文学的社会功能。骈文作品普遍表现出浮艳纤巧、空虚贫乏的倾向且存在不宜叙事的缺点,这越来越为文士所诟病。古文运动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这是儒家功利主义思想的体现,实用的古文因之逐渐受到文士的喜好。
四、山东士族对古文运动的影响
古文运动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西魏时期苏绰、卢辩的文体改革。西魏权臣宇文泰欲行周官之制,命苏绰专掌其事,未几而苏绰卒,乃令卢辩成之。卢辩出自山东高门范阳卢氏,他博通经籍,累世儒学。宇文泰的复古事业在苏绰死后由卢辩完成,改革多依古礼,革汉魏旧法。宇文泰令卢辩作诰谕公卿,其文体无异于苏绰所仿的大诰体。大诰体模仿《尚书》,与当时流行的骈文殊不相类。
隋文帝时的李谔出自山东高门赵郡李氏,他对骈文的形成及其缺点作了评论,上书提出“屏去轻浮,遏止华伪”,奏议立即得到隋文帝的采纳,并颁示天下。隋文帝虽欲整顿文风,反对骈俪浮艳的时文,但其继承人隋炀帝以及后来的唐太宗皆好南朝庾信的文章,经过他们的倡导,骈文在初盛唐仍占绝对优势。
古文运动发轫于西魏、隋初的文体改革,这一时期的复古主义者主要是北方士族,苏绰出自武功苏氏,属于关陇士族;与苏绰共同提倡复古的卢辩以及隋代李谔都出身于“山东五姓”。
陈子昂与其好友,出自范阳卢氏的卢藏用同为古文运动的先驱,谢无量指出,武周革命后,“一时文士,如苏、李、沈、宋之闳丽,陈子昂、卢藏用之古文”,[18](p24)也肯定了出身于山东旧族的卢藏用古文的影响。
古文运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唐时期勃兴的。这一时期古文家辈出,古文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可媲美于先秦两汉时期。唐代古文家很多出自山东高门,如:李华出身于赵郡李氏,与萧颖之齐名,人称“萧李”;李翰为李华族人,古文家梁肃师事之;崔祐甫出身于博陵崔氏,提倡复古;崔元翰出身于博陵崔氏,与梁肃同为独孤及弟子,论文主张载道与复古;李观出自陇西李氏,与韩愈为同年,以古文知名于世;韩愈出自昌黎韩氏,虽非高门,亦属于山东士族;刘禹锡出自彭城刘氏,精于古文,是古文运动积极的响应者;李翱出自陇西李氏,是韩愈古文主要继承人,后来成为韩愈侄女婿;李德裕出自赵郡李氏,为文多用散体,无意追求华丽词藻,有汉代晁错之风。
山东士族不仅直接参与了古文创作,而且与古文家关系十分密切。唐代古文家的重要人物如:独孤及、梁肃、权德舆、韩愈和柳宗元,其郡望虽非山东高门,但都与山东高门有密切关系,深受山东士族的影响。
独孤及与赵郡李华同志友善,曾为李华文集作序。他在《赵郡李公中集序》中称李华:“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泉源。”赞扬了李华复古宗经的古文。博陵崔元翰曾向独孤及求教,论文主张载道与复古,他在《与常州独孤使君书》说:“阁下绍三代之文章,播六学之典训。微言高论,正词雅音,温纯深润,溥溥宏丽,道德仁义,粲然昭昭,可得而本。”崔元翰将独孤及文章比作三代之文,显然是指独孤及的古文。同样出自博陵崔氏的崔祐甫本人善古文,曾为独孤及写神道碑文。
梁肃是著名古文家,且对唐代科举与古文运动有深刻影响,他与山东高门关系十分密切。崔群出自清河崔氏,陆贽主贡举时,梁肃荐其有公辅才,擢甲科;王涯出自太原王氏,梁肃荐于陆贽,擢进士第。博陵崔恭工古文,自言与梁肃同为天台大师元浩弟子,谓梁肃所作古文“粹美深远,无人能到”(《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古文家崔元翰自称是梁肃的挚友,曾为梁肃撰写墓志(《右補阙翰林学士梁君墓志》,见《全唐文》卷五二三),元翰还与梁肃同荐韩愈、李观、欧阳詹等登第。出自赵郡李氏的李翰亦善古文,梁肃师事之,李翰曾撰古文名篇《张巡传》,该书虽已失传,韩愈《张中丞传后叙》正是摹仿其体例所为。很多出自山东高门的古文家日后取得成功与梁肃的举荐有关,如李观、李绛、崔群、韩愈等皆出自山东士族,前三者出自“山东五姓”。李绛早年与李观、韩愈、崔群过从甚密,俱以文学为梁肃称奖。
古文家权德舆与山东高门关系同样十分密切,多次为他们文集作序,并将自己的古文观念表现在所作序文中。权德舆曾为李栖筠文集作序,说李栖筠“不苟合于时”,称李栖筠的文章“大凡出于《诗》之无邪,《易》之贞厉,《春秋》之褒贬。且以闳奓钜衍为曼辞,丽句可喜非法言。公之文简实而粹精,朗拔而章明”(《唐御史大夫赠司徒赞皇文献公李栖筠文集序》);他为崔祐甫所作序文《崔祐甫文集序》认为:“作为文章,以修人纪,以达王事。”为崔邠诗作序《崔工二侍郎诗集序》;为崔寅亮文集所作《崔寅亮集序》称文章要“有补于时”;为崔文翰文集所作序中不满于文章“词或侈靡,理或底伏”(《崔文翰文集序》)的衰薄文风。李栖筠、崔祐甫、崔邠、崔寅亮、崔文翰皆出自“山东五姓”。
唐代古文运动的双子星座韩愈和柳宗元皆非出自山东高门,其中韩愈出自山东一般士族,柳宗元出自“关中六姓”之一的河东柳氏,但他们的成长及其领导的古文运动的成功与山东高门密切相关。
韩愈幼年失去双亲,由从兄韩会夫妇抚养成人。韩会妻郑夫人出自山东高门荥阳郑氏,韩愈父母以及韩会去世后,郑夫人担当起母亲的责任,“(韩)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韩)会贬官岭表。(韩)会卒,嫂郑鞠之。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6](卷一七六《韩愈传》)韩愈事嫂如母,“(韩愈)嫂郑丧,为服期以报”。[6](卷一七六《韩愈传》韩愈的成长以及世界观的形成与其嫂郑氏密不可分。
韩愈举进士时,“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馀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寻登进士第”。[12](卷一六○《韩愈传》)郑馀庆十分赏识韩愈古文,韩愈在《上郑尚书相公启》中说道:“愈幸甚,三得为属吏,朝夕不离门下,出入五年。”[19](p149)郑馀庆出自山东高门荥阳郑氏,能沿承家学中的古文传统,《新唐书·郑馀庆传》载:“(馀庆)奏议类用古言,如‘仰给县官’、‘马万蹄’,有司不晓何等语,人訾其不适时。”[6](卷一六五《郑馀庆传》)郑馀庆所用“古语”就是不适时的古文。郑馀庆曾延复古主义者韩愈、孟郊、樊宗师入幕,其中,韩愈与樊宗师为古文家,孟郊作诗力追汉魏,因不守格律而不合于时。
贞元九年(793),韩愈为求仕进而应吏部试,主试官是出身于博陵崔氏的崔元翰。崔元翰好古文,十分赏识韩愈,将韩愈的名字上报中书,尽管惨遭淘汰,韩愈还是写信(《上考功崔虞部书》)表示感谢。[19](p660)
郑絪亦出自荥阳郑氏,与郑馀庆齐名,世谓“南郑相”、“北郑相”。宪宗元和二年(807),韩愈任国子监博士,郑絪爱其诗文,韩愈抄若干篇以进,遭嫉妒者攻击,韩愈作《释言》辩解。
元和七年(812),韩愈在任四门博士期间失意时作《进学解》,这篇文章马上得到当时宰相出自赵郡李氏的李吉甫和李绛等人的赏识,“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6](卷一七六《韩愈传》)
柳宗元的成长也与山东高门有密切关系。柳宗元自幼丧父,由母亲范阳卢氏抚养教育成人。卢氏家学渊源,她七岁即通《毛诗》及刘氏《烈女传》,柳宗元四岁时,居京城西田庐中,家无书,卢氏教以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卢氏的口传身教对柳宗元文艺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柳宗元日后的古文成就与母亲卢氏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中唐以后,山东士族全面复兴,出自“山东五姓”的宰相,不仅人数多,而且位高权重,他们多为皇帝心腹、朝廷股肱之臣,这与其在初盛唐时期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山东士族在中唐复兴后,开始标榜门风,反对时下流行的骈俪文风。古文运动的宗经传统、反佛立场以及尚质实的精神与山东士族的古老门风相契合,得到了山东士族的支持。综上可见,山东士族参与并深刻影响了古文运动。
[1]李 肇.唐国史补[M].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3]胡应麟.诗薮外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8.
[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上海:上海书店,2005.
[5]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A].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
[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陆 游.老学庵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
[8]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9]范 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0]魏 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1]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刘 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3]陈 善.唐武宗、李德裕深信道家之说[A].扪虱新话[M].上海:上海书店据涵芬楼旧版影印,1990.
[14]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5]赵 翼.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6]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7]魏 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8]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19]韩昌黎文集校注[M].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张立荣)
AncientChineseProseMovementintheTangDynastyandthePaternalTeachingandFamilyTraditionofShandongIntelligentsia
LI Jianhua
(School of Humanities,Ningbo University,Ningbo,Zhejiang 315211,China)
In the Mid-Tang Dynasty,the ancient Chinese prose movement flourished with the revival of Shandong intelligentsia,who did not abolish the tradi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rose when the “pianwen” (rhythmical prose characterized by parallelism and ornate style)prevailed in the Middle Ages.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ancient Chinese prose movement agree with the paternal teaching and family tradition of Shandong intelligentsia.They are in the same tradition of “Zong Jing” (all writings must learn from classics),with anti-Buddhist stance,and the same features,such as valuing effects,emphasizing utility,and opposing the ostentatious style.The Shandong intelligentsia participated in and led the ancient Chinese prose movement,making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flourishing of ancient Chinese prose movement.
Shandong Clan;ancient Chinese prose movement;paternal teaching and family tradition;Confucianism
2014-03-09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代山东士族的复兴与文学思潮”(编号:09CZW027)
李建华(1970-),男,文学博士,博士后,宁波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I207.23
A
1000-579(2014)04-008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