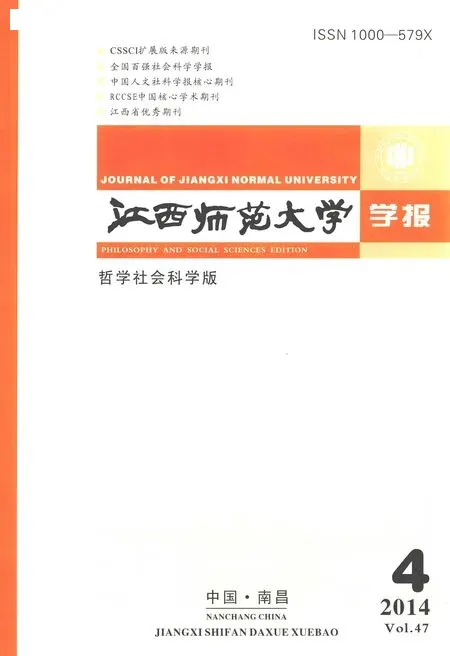游走乡土:2000-2009中国公路电影论略
徐文松
(江西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游走乡土:2000-2009中国公路电影论略
徐文松
(江西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2000—2009年是中国公路电影类型的成长初期,尽管作品不多,但在叙事和影像技巧的本土化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一时期作品偏重关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的乡土流动,初步形成了迥异于美国公路电影的类型特征与影像风格。
公路电影;单向性流动;类型美学;现代化
公路电影通常被认为是典型的美国电影类型,拥有非常风格化的影像体系:辽阔粗犷的西部空间、无限延伸的高速公路、飞驰的汽车以及四处游走的主人公——这些都是极其“美国化”的。不过,正如美国西部片刺激了其他国家的西部片创作一样,美国的公路电影也影响和推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公路电影创作。2000年,号称“中国第一部公路电影”的《走到底》横空出世,拉开了乡土中国现代游走的序幕。不同的国家,不一样的文化地理空间、各有差异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各有特色的交通体系和流动方式都会对公路电影的文化内涵、叙事手法及影像形态产生很大的影响,各国的公路影像由此异态纷呈。而比较与差异化的视角正有利于对自我的认知,本文即尝试从一种比较维度出发,在探讨类型特征与影像差异的同时,对2000——2009年间的中国公路电影做个简略的考察。
一、作品概况与总体境遇
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公路电影创作的探索期与实验期。这一时期的公路电影作品一是数量少,十年间只有五部作品,而且除了施润玖的《走到底》(2000年)之外,其他作品都出现在这十年的后半期,像韩杰的《赖小子》(2006)、张扬的《落叶归根》(2006)、蔡尚君的《红色康拜因》(2007)和袁卫东的《过界》(2008)。因为公路电影原本就不是一个主流的电影类型,即便在美国也是如此。而当中国电影在新千年开始进入商业转型的快车道时,留给一个新入境的外来类型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当犯罪公路片《走到底》(2000)因其生涩的影像叙事和水土不服的类型嫁接而受到媒体、学界以及市场的一致吐槽后,若干年内再无宣称“中国公路电影”的作品出现,实属正常。而且,就大环境而言,参差不齐的现代化进程,和以被动流动及单向流动为主的社会现实也决定了通常是建构在发达的消费社会和汽车社会基础之上的公路电影类型短时间内还不大可能在国内大量涌现。
二是创作者都以学院出身的青年导演为主。施润玖和张扬是第六代导演,底层关怀与现实视角是这代导演的共同气质,而类型尝试和黑色喜剧及现代性迷茫则是这两位导演为中国公路电影所作的独特贡献;韩杰、蔡尚君和袁卫东都是70后。《赖小子》和《红色康拜因》更是韩杰和蔡尚君的导演处女作,影片清晰地烙下了他们自身青春成长的深切记忆与现实反思,本色写实的影像风格冷静而内敛,在被动的流动中描写了两部地域与情怀都各不相同的青春残酷物语;《过界》则是袁卫东执导的第二部电影,音乐剧导演的背景给他的作品带来了鲜明的戏剧特征和实验风格,但这部公认的小众电影却有着一个非常大众的救赎式结局——显然,这五部作品中的每一部,就中国公路电影类型的发展而言,都是一个成就,它们多样化的主题关注和影像风格指向了这一外来类型在本土化过程中的各种可能。
三是斩获多项国际性电影奖项,艺术水准得到肯定。《赖小子》获得第35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最佳金虎奖;《落叶归根》获得第57届柏林电影节独立影评人(全景单元)最佳电影奖;《红色康拜因》获得第48届塞萨洛尼基电影节最佳影片金亚历山大奖;《过界》获得第42届美国休斯敦国际电影节雷米奖导演金奖和摄影金奖。作为中国公路电影类型的尝新之作,这些奖项一方面证实了它们的成就与价值,另一方面,又将艺术与边缘的标签更为明确地贴在了导演和作品的身上。加大了这些作品在中国电影市场的推广难度——后者正在全速驶向全面商业化的进程之中。
四是在国内普遍受到市场和大众的冷遇。学院青年导演、中低成本制作、边缘类型加上国际艺术奖项,这些元素在电影大片叠出的时代和电影审查高度敏感的语境中,基本上都是不受欢迎的代名词。即使是努力向市场靠拢的《落叶归根》,它“奢华”的4500万投资、全明星阵容、柏林电影节大奖、贺岁档期,最终也只斩获2000万的票房,而对此“片方已感到满意”。[1]相比较于蔡尚君300万的投资和欲排六一档而不得的尴尬来说,的确是已经非常好了。套用贾樟柯的话来说,就是“在这个遍黄金的时代,有谁还关注孓然奔波的旅人”?而这种状况显然使得后续的公路电影创作更关注市场需求,更注重喜剧化的“看点”和“笑点”,比如《人在囧途》(2010,2012)。
二、主题特征与类型比较
如果说美国公路电影的发生是缘起于公路、电影和汽车的相遇,那么,这一时期的本土公路电影则大多是因为乡村遇上了城市。《落叶归根》、《红色康拜因》自不待言,基本上就是农民工的故事;看上去时尚华丽的《过界》在剔除了鲜亮的城市外衣后,指向的也就是理想化的乡土回归。而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流动的深切关注,既是中国公路电影类型在本土化进程中的主题特色,同时也是中美公路电影在影像表达上的显著差异之一。
造成这一特色差异的原因在于:欧美现代社会的完全城市化,乡村往往成为度假休闲场所,个人拥有较高流动自由及能力。而这在中国还是遥不可及的未来,中国社会中的流动还集中于城乡极端不平衡的群体性单向流动之中。现代化进程的意义具体对多数中国平民而言,不是指在城市里游走,就是指游走在去城里的路上,而流出城市流向旷野或流向文化反思层面,短时间内还难以实现。而在急剧的现代社会变革中,受到冲击最大的,正是广大的中国农村——这个传统乡土中国的基柱,正在被分裂和剥离出社会越行越快的发展轨道之外,其非正常的破碎和毁灭几乎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种献祭和牺牲。“由于现代性的滞后,新世纪的中国乡村还处于这样一个历史过渡时期。……城市不再仅仅是罪恶的化身,乡村也不再是诗意的家园。现代性以其强大的穿透力刺穿了乡土文明的厚壁,推动乡村和城市的双向流动。”[2]从这个角度出发,在中国电影鲜有从城市角度来批判现代化与现代性的情况下,青年独立导演或作者导演通过对乡土、农村、农民、农民工以及城乡间的单向流动等现实问题来表达自己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及其问题的关注或批判,亦可谓是扣到了中心一环。
文化地理空间的不同带来了中美公路电影的第二大差异,即影像风格和文化指向的不同。在美国公路电影类型中,西部空间、汽车和公路在反复的书写和文化投射过程中已经成为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象征性影像符码;半个多世纪的类型发展亦形成了一整套流利而圆熟的影像手法,来描述各种公路故事。而中国公路电影因关注重心和创作的相对分散,尚未形成标志性的影像符码,尽管中国西部的地理地貌与美国西部略有形似,但共同文化积淀与投射的缺失,使它在景观之外难以提供更多的内容。另外中国社会的乡土变迁也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因此对叙事空间的选取和表达更多的从现实需求出发,像满是煤灰的破败小镇、日渐凋敝的乡村、等待收获的金色麦田、短暂路过的他人的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化地理景象,随着众多的写实性镜头被逐一纪录。受现实主义及真实美学等因素的影响,大量长镜头下的乡土流动中鲜见旷野中的速度与激情,公路和汽车在叙事中彰显的大多是它们的实际功用,极少被刻意标出。人与人,人与乡土、与社会变迁之间的现实关联,才是这些作品影像关注的重点。
在诸多差异之外,中美两国公路电影在叙事模式上也有相似之处。那就是经典叙事模式和现代叙事模式在公路电影创作中交错存在,指向着各自不同的审美与批判。通常意义上,指向成长、救赎与修正的经典叙事模式,其商业意图相对明确,像《走到底》,像《人在囧途》系列;而现代叙事模式则多为开放式的结局,直面现实的反思与关怀,像《赖小子》、《红色康拜因》,以及《落叶归根》;而《过界》在艳丽的先锋影像之后续上一个心灵救赎的经典结局,成了一个奇特的存在。
三、转型中国的《落叶归根》
相比较于同时期的其他公路电影而言,张扬带有寻找与回归意味的《落叶归根》不仅表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之价值冲突和还乡困境,而且无论是在叙事模式、影像手法的把握,还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矛盾的体悟与表达上,都更具普遍性和代表性特征。电影真正将公路叙事的空间架构模式及其开放性特征融合到了本土叙事中。影片以真实事件为缘起,却不为事件本身所束缚,没有做成惯见的悲悯式的底层纪录,而是借用公路叙事形式使之成为一个超越性的、开放的流动景观卷轴,展现了转型中国的一个社会横剖面。
在突出公路的结构性功能的同时,《落叶归根》将这一电影类型与本土文化反思及现实观照的主题很好地结合起来。赵本山所饰演的送友回乡的农民工形象,既有重诺、实诚、忍辱负重的一面,也有狡黠、滑头和苦中作乐的幽默一面,尽管其表演偶有过度之嫌,但总体上这是个立得起来的有血肉感和真实气息的底层人物形象。在谈及人物形象以及叙事框架构想时,导演张扬说道:“这一趟旅行不光是写一个人的经历……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个旅程中出现的人,他们的生活状态、生活经历。甚至有很多不同地域的风光、风俗,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去审视中国一些地方的民众生活与面貌。”[3]
显然,《落叶归根》具有自觉的行游意识或流浪精神,以及对现实社会状态的深切观照。它淡化了在路上的目标性,强调人物的本真状态和公路的开放性特征,这都是契合现代公路电影类型风格的处理方式。而在影片最后,老赵手捧工友火化后的骨灰,站在一片废墟前——工友的家已因三峡水库工程迁移,周围只剩已拆和将拆的废墟与空屋,一块灰败的门板上模糊不清地写着迁移地址,除此之外,便是滔滔江水。这种打破传统封闭式圆满结局的方式,既是现代公路电影常用的开放性手法,也更是现代中国社会中,“落叶归根”所暗指的传统文化赖以存在的乡土根源与精神归依被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冲击变形以至崩塌的深刻现实的表现。“现代性流动叙事从整体上瓦解了传统的乡土想象的基础。”[2]一个流动能力和流动空间受限的主人公,一个最终未能亦无法完成的旅行目标,沿途各色人物各种遭遇,荒谬、反讽、温情和黑色幽默——诸多形式风格鲜明的类型特征都标注出《落叶归根》的公路电影特征。而就中国公路电影类型发展的角度来看,《落叶归根》更大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它在外来电影类型形式中所贯注的中国文化精神与现代主题,或者说,导演为表达现代中国社会状态而自然地借用了公路电影这一相对自由的叙事形式,以边缘人物及事件表现主体社会文化与精神上的裂变。立足于自我的文化立场而化用外来类型,从这一角度来比较《落叶归根》与《走到底》、《赖小子》和《过界》,虽然模式不尽相同,但显然张扬不仅在自我与外来尺度的把握与融合上要更为成熟,而且在对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精神状态的认识上亦更为明晰。其不多做幻想的开放性结局,比《过界》一再叮咛要面对自我回归内心来得更为冷静且现代。
就以《落叶归根》为例比较尚不成熟的中国公路电影与欧美公路电影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落叶归根》中难以从自身文化与生活环境剥离的人物形象,更具现实性及日常化的影像表现方式与手法,以及对现代精神指向的关注与欧洲反思型的公路电影有精神上的相似性。这部电影在5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独立影评人(全景单元)最佳电影的奖项,或许与这种相近的现代文化反思不无关系。
不过,《落叶归根》情节设置稍嫌密集,叙事上留有中国传统叙事作品中推重情节而不够重视人物心理刻画的特点,人物旅程的实在感强而精神性表达不足。换句话说,影片所指向的精神之旅是在接受层面完成的,在叙事层面上体现尚有欠缺。作为个案,《落叶归根》当然也并不能穷尽发展中的中国公路电影类型的所有特征及可能,而中国独特而深厚的文化传统、审美习惯以及不一样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会在中国文化与地理空间中将欧美公路电影类型进行本土化的改造,在框架共通的公路叙事模式中用现代电影语言和影像手法绘写中国的现代公路故事,构建中国公路电影风格。同时,现代化进程中巨大的冲击性力量也将对中国文化与社会带来深刻变革,正如张扬电影中落叶已无根可归的文化感伤一样,这些变革与社会文化互动影响,亦将赋予中国公路影像独特的风格与气质。乡土与城市,传统与现代,张力的两维,渐变成型中的中国公路影像,可值期待。
四、结语:公路电影之辨
在论及这一时期的公路电影时,有不少分析将《芳香之旅》(章家瑞,2006)也纳入公路电影范围进行讨论。好像判断一部作品是不是公路电影只要看它是不是有路、有车、有往返奔波就行了。但实际上,汽车、公路和在路上行走,只是公路电影成立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决定公路电影类型归属的是它的叙事模式和叙事重心。从类型角度来看,公路电影的叙事是松散的、线性的和开放式的截取式叙事——即专就主人公某一时段的公路旅程生活展开区间叙事,其叙事重心是一定时间内人物在空间中的流动状态,而非一定空间内人物在时间中的变化。流动是这一叙事过程中主人公最主要的生活与生存状态。以此为标尺,《芳香之旅》显然不属此列。
《芳香之旅》是个通过一个女性生命中的爱情生活来感慨时代变更命运无常的怀旧故事,尽管被安排成与一辆乡村公交车和一条漫长的行车路线密切相关,但它古典的、封闭的、缺乏多维阐释空间的叙事模式,以及它对时间跨度的强调甚过于对空间行程的强调,决定了它和众多意欲以小写大的人物志一样,是一部大时代变迁下的凡人史传,而非公路电影。影片所凸显的是历史与时代对个体命运的挤压与掠夺,封闭空间内乡村公交的来回运转不具有现代流动的意义,亦非影片叙事重心所在,它仅仅起了一个功能的作用,这显然与现代公路电影中公路影像及流动影像所具有现代性指向的意义相去甚远。
无论是单个的影像元素还是影像元素的组合,都不是可独立判断类型归属的依据,这也是为什么在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中,关于车和路以及行走的影片不少,但公路电影并不多的原因。不过,在第二个十年里,纯商业公路电影的出现与成功,或许能使之大大改观。
[1]李 谷.《落叶归根》票房突破2000万片方已感到满意[R].现代快报,2007-01-31.
[2]黄佳能.新世纪乡土小说叙事的现代性审视[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4).
[3]张 巍,洪 帆,谭 政.拍给更多人看的公路电影——张扬访谈[J].电影艺术,2007,(2).
(责任编辑:张立荣)
RoaminginHometownanOverviewofChina’sRoadMovie(2000-2009)
XU Wensong
(School of Humanities,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Nanchang,Jiangxi 330013,China)
China road movie type was in the early growth in 2000-2009,although the works about China road movie were few,it mad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in the localization of narrative and imaging techniques.The works in this period focused on the attention of the local flow of Chinese society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initially forming type characteristics and image style different from the American road movie.
road movie;unidirectional mobile;genre aesthetics;modernization
2014-05-03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艺术学青年基金项目“转型社会的流动影像:20世纪下半叶美国公路电影研究”(编号:YS1313)
徐文松(1978-),女,江西泰和人,文学博士,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影视美学、文化产业。
J901
A
1000-579(2014)04-009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