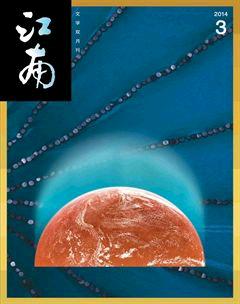储福金与围棋小说
李洁非
围棋者,天道也;小说者,人道也。一主格物,一主辨人,于其所长,皆可谓穷形尽相。研围棋益深必以皈悟天理为要,治小说益精则非得透悉人伦世情。储福金君,小说家里围棋最佳,弈者内小说第一。二十年前识荆,我对他就有此概念,然而很长时间中,于这两点却只有单独和分别的认识——我是他小说的读者,也曾在纹枰上向他请益,可是却没有机会领略他将小说和围棋熔于一炉的风采,写作的储福金与下棋的储福金,各行其是,并无交集。文坛中一班嗜棋的朋友,对他何时动手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围棋,揣此想望久矣,而他迟迟不出手。2007年,他终于破此悬念,出版小说《黑白》。以我所知,这应是史上第一部长篇围棋小说。何遑多言,作品取得了可以预料的成功及反响。记得《黑白》讨论会上,不单文坛棋友济济一堂,当时尚健在人世的陈祖德先生以及围棋专业媒体《围棋天地》的编辑记者,亦惠然光临。虽说在古代,文棋之雅常常如影随形,但方今之世,这样耸动了文棋两苑而令其一时聚首,似乎也只拜储福金《黑白》所赐。
围棋乃地道的国粹。象棋虽然现在普及度远超围棋,实际却是发明于异域、由外输入的舶来物。故唯围棋才体现原汁原味的中国思维,与我们哲学、文学等关系深远、互为润滋。历史上第一流的文人好像不曾咏过象棋,但题吟围棋的则不胜枚举,我见过的就有白居易、杜牧、孟郊、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钱谦益、袁枚等等。可以说,在以诗为正宗的时代,围棋本就是中国文学常见题材对象。唯自小说时代以来,文棋二者的关系疏淡起来,偶有一二作品(如《三国》《红楼》)在局部情节写到围棋,但论着以围棋为对象、为主体,这样的创作严格说来在中国是没有的,相反写象棋倒是出过名篇,例如阿城《棋王》,此作被尊为“寻根派”代表作,论者颇感慨于它如何把中国智慧、生存态度与棋道相融合,但以我看来,这样的主题借象棋而非围棋说之,其实令人怅然有失。然而文学与围棋何以睽隔若此,往虚里说,应是古今文化精神悬殊所致,如果切近务实来讲倒也简单:围棋的道儿太深,研摩费时,非矻孜以求不能至万一。欲以围棋入小说,有此念者,兴许不在少数;但真正能为此念拈动笔头者,如今作家中必属凤毛麟角。储福金便是这凤毛麟角,至少我私下认为,有资格做这事且可以做好的,储福金该称当仁不让。《黑白》的出版,从文学角度讲,将古代文棋之雅的传统在小说时代接续下来,从围棋角度讲,也补了现代以来围棋越来越偏于竞技体育而疏离于文化之不足。读者对它的喜爱也是如此。《黑白》的读者,必兼爱围棋与文学,或者是文学爱好者中雅爱围棋者,或者是围棋爱好者中文化趣味较高者。在这样的读者心目中,围棋葆有一番特别的意义,他们于围棋,既不目为饭碗,也不仅以消遣、娱乐视之,颇作为修身养性之器来看待。从这一点来说,一部精写围棋的小说,是人们所乐见的,而完成这任务,非以优秀作家又深通棋艺者才可致之。环顾当今文坛,此人确可谓舍储君而其谁乎?故而很久以前大家暗中怀翘首之望,等他终于写出《黑白》,我们都感到心愿得以释放。
从世界范围讲,过去最有名的围棋小说,当数川端康成以木谷实为主人公的《名人》,篇幅约六万字,只好算中篇。《黑白》不但在规模上超过它,内容和文化分量亦不输彼。《名人》以一局超长对局,表现日本弈坛两大时代的交替,写得极富美学精神。《黑白》时空却跨了小半个世纪,塑造了一组棋士群像,又将沧桑世事与枰间悟道熔于一炉。两部作品之间,处处显出中日历史、社会和文化格局的不同,其实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很好对象。储福金或许写不出《名人》,但川端恐怕同样写不出《黑白》。这些都留待有识者将来细细讨论,重要的是,自从有了《黑白》,中国当代作家总算可以说不愧对祖上发明的围棋,否则我们拿再多围棋世界冠军,棋文化却终矮人一头。
迄《黑白》之问世,又已七年。这当中,与储兄偶通音讯,却未谋面。偏偏刚入2014年没几天,收到他发来《黑白》之“白之篇”,并告出版在即,令人喜不自禁。回想那时读到《黑白》,已有心中石头落地之感,对他再写一部,何敢望焉。然而此刻又一部二十万字小说稿却已在眼前。获此先睹良机,一气读完,餍足之感无以言表。
情节上,“白之篇”延续《黑白》而来。《黑白》人物故事收尾于抗战“惨胜”,“白之篇”则自建国后写起,线索仍以陶羊子为端绪,就这一点说二者有起承关系。但新作有个很大不同,原来有贯穿性的主角、中心人物,现在没有了,而写成四代棋手的多部曲式,陶羊子而彭行,彭行而柳倩倩,柳倩倩而侯小君,相当于有四位主人公。这种非中心人物的故事结构,过去长篇小说也有,《儒林外史》就是如此,小说理论称之“以人串事”,人物起一种情节穿线功能的作用。“白之篇”四位主人公之间的转换,有类似意义,作为叙事原点分别指向或辐射出五十年代至“文革”、“文革”期间、八十年代以及市场经济当下这四个大的当代史段落。
但这仅为此种安排较浅显一面,实际上还有含而不露的话语值得体会。从《黑白》叙事通体突出着一个主人公,到“白之篇”用四位棋手分别描摹现实、作跳跃式叙述,蕴藏了很多感触和思悟,比如“一”与“多”、不变与变之类对比或反差。曩者,陶羊子以对棋道一以贯之、矢志以求的形象留在读者脑海,到了“白之篇”,这种内涵不觉间从围棋现实和棋手身上隐退,而无迹可求了。彭行虽拜陶羊子为师,并在技艺乃至见地上接受乃师启迪,但他始终无法如老师那样对围棋奉求一种信仰。之后,柳倩倩之于彭行、侯小君之于柳倩倩何尝不如是?所学益止乎技术层面,不能从技术精进到精神,如庄周庖丁之喻,“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以神遇,不以目视”。盖当代背景下,弈之一事“变”的意味益浓,生存即在于“变”,凡善变或能“变”在先者最宜生存,而无可“守”、不能“守”、也不值得“守”。从师承关系讲,侯小君算陶羊子三传弟子,但传到他这儿,围棋从路数风格到内涵,不单毫无陶羊子遗韵,乃至实已背道而驰。侯小君心中浑然不知“棋道”二字为何物,他是十足的在功利、锦标刺激下成长起来的棋手,身边始终跟着一位满脑财会思维的母亲,然而他战绩甚好,小小年纪已打入世界冠军赛决赛,正所谓赢棋是硬道理、一胜遮百丑。
这究竟是个人之失,还是时代和文化之失?小说中的笔触,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有许多精彩情节或细节。尤其是彭行的段落,他那俄底修斯般的围棋流浪史,他与烧饼贩子查淡(“炸弹”谐音,典见小说)有如草寇剪径、丛林求生的棋上体验,他在方城矿区终因棋捧上一只饭碗以及这碗饭的种种吃法……写尽棋底人生波澜。读书人逢乱世易叹天下之大容不下一张书桌,而彭行从海城到方城,也无非是要找一处容下一张棋枰的地方,而为此漂泊上千公里,乃知斯文坠地、无枝可栖。棋士之心就是在这东播西迁的路上被改变,且不能不改变。师傅陶羊子身上有一种化为棋格的人格,彭行对此不是没有意识,却因所处现实无法效摹、纳为己行。
或许我不能指陈如上叙事隐含对围棋文化品格流失的感喟,但四代棋手的变迁史本身,客观上呈现了这种关系。胜负(输赢)与内涵(妙谛),这两种对围棋同样重要然而在现实条件下又颇为矛盾、似难兼得的东西,是小说留给我们的推不开的思索。小说最后收束于一幕大戏,亦即师祖陶羊子与徒孙侯小君的跨代对决,这段情节精彩之至。行棋中,双方秉各自围棋认知,你来我往,表面上是陶、侯两位特定棋手对局,其实却是不同精神体系的围棋的淋漓尽致演示。黑棋(侯小君)处处“寻衅挑事”,时时“求复杂的转换”,白棋则不动如山,“以不变应万变”。 小说写道:“对局中的陶羊子心境一片清明,仿佛回到了早年在烂柯山顶观天地的时光,棋形如山边之云,或凝定,或飞散,多少年来没有意识着这样清明的心境了,他在存世中已经顺随,早已离开了对弈的局面,生死在岁月中变得轻,变得空,变得坦然无碍。”棋局甫终,侯小君诧异道:“太师公他这么快睡着了!”其实陶羊子是棋上“圆寂”,以生命行完最后一局棋、在棋中走完生命最后一步。如此煞尾,自具点睛之意。回看围棋气质愈益物化的现实,应见作者心中实有古调不弹之痛。
孔子以“文”教天下,中国历史的灵魂和价值核心尽在一个“文”字,而这也是储福金用以把握围棋、透视其本质的柄杓。所以他的围棋小说立意很高,充分调动了自己对围棋、对文化双重的精深见地,真正做到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读者阅其书,所获不只是棋人棋事而已,更有从文化、哲理和道行的高度对围棋的把握。然而,他一点不说教,当初读《黑白》后我曾指“这部小说奇就奇在风骨雅正,却丝毫没有教化的痕迹”,到了“白之篇”,还是这样。这一点其实最难,当文学想去发扬一种道理时,极易流于说教,今天称之“概念化”,古时所谓“以理入诗”等,以致思想含量上去了,作品却味同嚼蜡。储福金的好处在于,不光对围棋有深入认知,更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有的是办法让叙事情趣横生。之前《黑白》,袁青原型明显化自吴清源(袁青者,清源之音逆读也),而“白之篇”的旋风王脱胎于何人,略知弈坛掌故的读者亦不难会意。此外,彭行少年及当知青时的情形,多少有些“自传”的成分和影子。海城盖即上海、南城盖即南京,与这两地有关的故事,我觉得也会是虚虚实实。这种写法,是地道中国式小说独有趣味。曹雪芹最谙其道,一部《红楼》,妙在“贾雨村”和“甄士隐”两者间。余如《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叙事亦行于真实与虚构边缘。可惜中国小说这一传统韵致,“现代”渐渐流失,而从《黑白》和“白之篇”,我却得到了重温的机会。
【责任编辑 李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