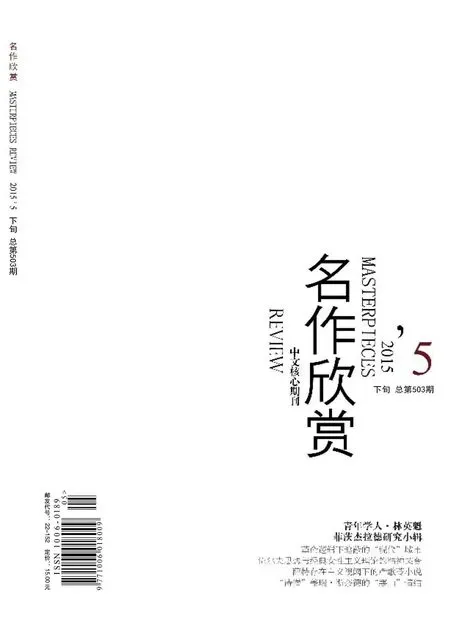《小鲍庄》中的大众面孔
⊙姚丽晶[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81]
《小鲍庄》中的大众面孔
⊙姚丽晶[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81]
通过对《小鲍庄》中伪善、偏执、冷漠的大众进行论述,分析原委,进而呈现出作品中独特的大众面孔。
大众伪善偏执冷漠
西班牙作家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大众的反叛》中曾写道:“大众是人类历史所宠坏的孩子,这个宠坏的孩子之行径仅仅是个继承人,除了继承遗产之外,他一无所能。”王安忆在上世纪80年代的《小鲍庄》中就描写了一些人类历史所宠坏的孩子——偏执推崇仁义的大众群体,他们不能正视自身不断膨胀的欲望,于是在仁义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一张张伪善、偏执、冷漠的面孔。
伪善作为一种虚假之善,是道德主体行之于不善而饰之于善的自欺欺人行为。人之为善,源于人之善心,显于人之善行;人之伪善,源于人之无善心,显于人之虚假善行。无心之善,是善之无实、是虚善;假行之善,是善之失诚,是假善。虚假善联姻,两者合题,生成伪善。伪善又分为个体伪善和群体伪善,《小鲍庄》中的村民们呈现的是赤裸裸的群体伪善。
小说中的小鲍庄是个仁义的村子,祖祖辈辈,不敬富,不畏势,就只是敬重仁义。当鲍五爷最后的亲人小孙子死后,村里无人不同情,无人不信誓旦旦地要伸出援助之手;鲍秉德的妻子疯后,虽然没有儿女,但鲍秉德仍然不离不弃地照顾,表现得可歌可泣;当外乡小翠来讨饭,鲍颜山家的生活虽然贫苦,但也慷慨施粥,村上的人在外乡人眼里都表现得重仁重义,完美诠释了中国古代儒家成仁成德的思想核心。
但是仁义背后我们真正看到的是村民们的“道德心理失序”,从而产生了仁义认知的“缺失”、仁义情感的“异化”、良心的“形式化”、仁义动机的“倒置”。《小鲍庄》的村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私心欲望,但仍然死命地抓着仁义的衣角不肯放手。如果真那么敬重孤寡老人鲍五爷,为什么当洪水来临时,没有人想到老人的安危,满腹的舍生取义、仁者爱人,最后仁义之心的指针还是指向了自己;如果真那么爱自己的老婆到不离不弃,鲍秉德怎么会因为鲍仁文广播了自己的事情而怨恨,他并非死心塌地地想照顾妻子一辈子,这些照顾与其是逼疯妻子的愧疚还不如说怕别人说其不仁不义;如果说鲍颜山家给小翠的第一碗稀饭是出于人心本善,那么之后的吃食则是自己“仁义”外衣下用尽心机进行权衡与私欲的诱饵,甚至怕自己吃亏,拼命地使唤小翠使其获得最大的收益,小翠实际上被当作了一件名副其实的获得利益的物品,最初的那点“仁义”之心被后来的心机和刻薄所代替,“仁义”至此已发生质的异变。村民们本质上表现出的完全是自欺欺人由内而外的群体伪善。
人是理性存在者,应是“善”的存在;人之善在,是善心、善行与善格的统一。小“捞渣”是唯一从群体伪善中脱离出的真“仁义”孩子,皮亚杰认为儿童代表着人类的童年,“捞渣”这个儿童形象是人类童年“人之初,性本善”的象征。“捞渣”的“仁义”是既不想施恩,也不想报恩的,全没有成人世界的心机,纯是本性使然,“捞渣”的“仁义”是真正的仁义之根。
人又是有限理性存在者,难以摆脱自身内外的纷扰,导致善之分裂,滋生“伪善”。《小鲍庄》中伪善无需继承,但是真正的“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文化极其珍贵的遗产,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品牌”,是具有永恒、普遍的意义和价值的。小鲍庄的大众只是没有能力处理社会变迁导致的一些矛盾,也不懂得怎样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们唯有机械地以这种变质的“仁义”作为人生信条僵硬地套取在生活当中,并拿其作掩护,为了自身的私欲利益不断扭曲变化,所以我们看到了小鲍庄的大众,他们天使的面孔、魔鬼的内心。他们的“仁义”是伪善之果。
大众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他们感到自己是平庸的,却振振有词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拒绝服从任何高超于己的权威,并要求强制推行这种权利。鲍秉德家里的女人疯了,只打自己的男人,村里人却从来不思考其原因;女人疯了之后完全失去了话语权,他们只看到了鲍秉德的苦闷、不离不弃,从未想过是谁造成的这悲剧,真正该同情的人究竟是谁?正如勒庞所说,专横和偏执是群体有着明确认识的感情,他们很容易产生这种感情,而且只要有人在他们中间煽动起这种情绪,他们随时都会将其付诸行动。鲍二爷曾经劝鲍秉德:“啥事都有个头,你又没做过缺德事,凭什么这样为难你?”可实际到底是谁为难谁,谁害了谁?当村子里唯一的文化人鲍仁文提议要送这个疯女人入院治疗时,周围的人是这样反应的:
“那是不成的。”大家一起反对。
“那么些疯子都关在一起,不打成一堆,撕碎了才怪!”
“听人说,那就像坐大狱似的。”
“大夫都拿着带钉的棍哩!”
“这不是病!”
鲍秉德自己是不用再说什么了,只是恨恨地盯着鲍仁文。
鲍仁文长叹一声,立起身,走了。傍晚的太阳,落在地沿上,把他的影子拉得细溜溜长,孤孤单单地斜过去了。
这就是大众,他们觉得可以免除了对那些非凡卓越之士的服从,所以蛮横无知地推行自己的权力。最终这种无知使鲍秉德家里女人丧失了最后一次治疗的机会,最后由于难以忍受折磨拒绝被救,选择离开这个“仁义”的村子,从某种意义来讲整个村子的村民都是害死疯子的凶手。然而面对鲍秉德不到三个月后的再娶,鲍仁文除了感觉失落外,大家似乎认为值得谅解,这难道不是对死者的不仁义吗?这难道不是失落了“仁义”之心吗?无人知晓小鲍庄中所谓的“仁义”二字的真正含义。
当大众发现其他一切正常的手段都不足以捍卫他们认为自己拥有的或应该拥有的正当权利时,他们也会诉诸暴力。他们只会偏执、专横、无知地使用自己的权利不允许其受到威胁,当村里的人看到外乡人拾来和二婶的结合,认定是其败坏门风,是桩丑事,动了众怒,于是一伙人对他们拳打脚踢,一顿暴打,即使乡里有寡妇再嫁合法的公断,但是众人依旧难以认可,直至拾来因为捞“捞渣”的尸体成了英雄,村子的人才开始认可他,并敬其三分。由此看来,大众虽然愚昧无知,但他们却处处插手频频干涉,强制推行自己的观点,他们并不为自己在医学、法律上的无知而反思,而是继续偏执地使用自己的权力。
大众表现出来的感情不管是好还是坏,其突出特点就是极为简单而夸张,大众情绪的夸张也受到另一个事实的强化,即不管什么感情,一旦表现出来,就会通过暗示和传染过程非常迅速地传播,它所明确赞扬的目标就会力量大增,它所贬斥的就会一文不值。这种情绪上的简单夸张极其不负责任,反映出的是大众的冷漠。小鲍庄里的“仁义”大众也大抵如此。
如果说小鲍庄是原始仁义精神这种“传统性”的缩影,那么“捞渣”就是其仁义的化身,他总是和和气气地微笑着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对父母、对邻居、对童养媳小翠、对鲍五爷都投以真诚善良的微笑,尽管他是个孩子,却可以做游戏让着别人,把上学的机会让给哥哥,最后在全村人都自顾自地逃命时,他为救老人结束了自己短暂而又大仁大义的一生。“捞渣”死了大家很惋惜,把他当作英雄,并迅速塑造了“捞渣”伟岸的形象,并且全村的大人都去为这个孩子送葬,让大家看起来小鲍庄好像的确是个重情重义的庄子。但有些人却有这样的批评:“我不明白庄中那么多重仁重义的大人,为什么没有一个在洪水袭来时想到鲍五爷,而把大仁大义的机会留给一个稚子;我更不明白,他们还居然面无愧色地为这个死去的孩子送葬。”但我想说的是,他们当然会去送葬,他们当然也没有特殊资质想那么深刻的道理,他们去送葬只是缘于自己对英雄那种单纯夸张的感情,他们把“捞渣”当成了舞台上的英雄,他们所要求的英雄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勇气、道德和美好的品质,所以他们丝毫不会反思自己的过失,而是在塑造自己的英雄的同时,进而提升自己生活环境的道德境界——更“仁义”的庄子。
最后似乎村里的每个人都因为“捞渣”的死而获得了益处,似乎也改变了整个村子的处境,但是他们在获益之时丝毫没有对死者存有感激之情,而是陷入了各种私欲的纠纷,他们对“捞渣”那种假仁假义的尊敬与怀念,与其说单纯、夸张,不如说是一种冷漠。这个仁义的村庄继承下来的“仁义”意识已经被大众的偏执、无知、冷漠变迁成一种原罪意识。
大众在过去仅仅是社会舞台的背景,如今越过舞台的配角摇身一变成了主角,在社会的舞台上,再也看不到严格意义上的主人公,取而代之的是合唱队。在小鲍庄里我们看到古老理想的丧失、才华的泯灭、野蛮风的盛行,再华丽的文明也是久远的历史赋予的外表,实际上它已经成了一座岌岌可危的大厦,失去了任何的支撑,下次风暴一来,立刻倾覆。“捞渣”的死无疑给这个仁义之村带来了莫大的好处,有人说他会改变小鲍庄落后贫穷的命运,从而改变小鲍庄贫瘠落后的思想,但我觉得这些观念已经变成一种情感深入到小鲍庄大众的头脑之中,并且他们深知这是一种权力,会带来一系列自己想要的效果,所以新的意识和它对抗都是徒劳的,因此,我敢断定小鲍庄下一次风暴带来的损害一定是毁灭性的。
[1][西]加塞特.大众的反叛[M].刘训练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2]王宏.伪善论[M].长沙: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3][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辑出版社,2004.
[4]余晓莲.解读《小鲍庄》——在“仁义”与“仁义”之间[J].今日湖北(理论版),2007(2).
作者:姚丽晶,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魏思思E-mail:mzxsws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