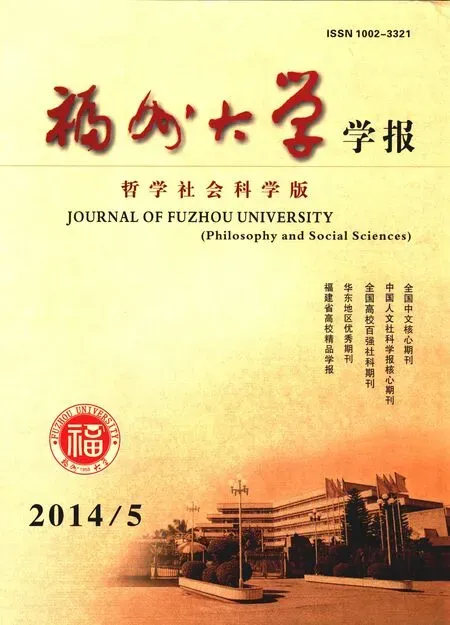“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章“命”意识辨正
——兼谈“五十而知天命”
陈洪杏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哲学部,福建福州 350001)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章“命”意识辨正
——兼谈“五十而知天命”
陈洪杏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哲学部,福建福州 350001)
“命”的话题永远不可能被否弃。人作为一种肉体的存在,只有通过与外界进行必要的物质交换才能使其富有生机的肉体得以持存,对待性或有所对待是人的存在的一重规定,在这个向度上“命”的话题永远不会过时。同对“道”的瞩望一样,对“命”的顾念构成了人生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终极眷注。因此,问题不在于谈“命”与否,人生的境界即有不同,不在于孔孟之“道”被觉悟后,“命”是否为“道”所取消,而在于二者在孔孟的价值判断中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孔子在生死危厄关头勃发的殉道精神,可谓极其典型的道德崇高感,它是孔子持久地涵养着的日常崇高感即“知其不可而为之”精神,在特殊时刻受到某种“命”意识强烈刺激后极其璀璨的一闪。对死生、富贵价值和“仁”德价值的觉醒,对人生终极眷注之重心的转换,对“中庸”作为一种道德信仰的觉悟,这是孔子对殷周以来根深蒂固的“命”意识之功能所以能作出富于时代变革意义之扭转的底蕴所在。
命; 生; 或然性; 道; 崇高感
《论语·宪问》载:“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孔子在这则对话所发露的“命”意识颇为典型,凝集了其对“生”、“命”、“性”、“道”诸话题的体会,并于不经意间激发出了这位儒学始祖的一种甘于殉道的崇高感。此章学人素来着意甚深,近代以来的注家踵武前贤,强探不已,在沿承前人识见之际,亦陆续提出了一些极有价值的观点。本文拟就此对孔子“命”意识再作探玩。
一、近代以来注疏举要
历史上对这章的诠解最可留意者为朱子、张尔岐。朱子注谓:“谢氏曰:‘虽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实寮无如之何。’愚谓言此以晓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圣人于利害之际,则不待决于命而后泰然也。”[1]关于“圣人于利害之际,则不待决于命而后泰然”,《朱子语类》进一步解释道:“圣人不自言命。凡言命者,皆为众人言也。‘道之将行也与?命也。’为公伯寮愬子路言也。‘天生德于予’,亦是门人促之使行,谓可以速矣,故有是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亦是对众人言。”[2]所谓“命”,据《论语或问》,“命者,天理流行、赋于万物之谓也。然其形而上者谓之理,形而下者谓之气。自其理之体而言之,则元亨利贞之德,具于一时而万古不易;自其气之运而言之,则消息盈虚之变,如循环之无端而不可穷也。”朱子指出:“万物受命于天以生,而得其理之体,故仁义礼智之德,根于心而为性;其既生也,则随其气之运,故废兴厚薄之变,惟所遇而莫逃。此章之所谓命,盖指气之所运为言。”[3]与朱子相异,张尔岐《蒿庵闲话》谓:“人道之当然而不可违者,义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争者,命也。贫富、贵贱、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强也,君子与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君子当以义知命矣。凡义所不可,即以为命所不有也。故进而不得于命者,退而犹不失吾义也。小人尝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争,则智邀之,智力无可施,而后谓之命也。君子以义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争命,故其心多怨。众人之于命,亦有安之矣,大约皆知其无可奈何,而后安之者也。圣人之于命安之矣,实不以命为准也,而以义为准,故虽力有可争,势有可图,而退然处之,曰:‘义之所不可也。’义所不可,斯曰命矣。……故圣贤之与众人安命同也,而安之者不同也。”[4]
近代以来注家多不出朱子、张氏之思维引力场。承朱者或侧重于认为孔子唯义是从,于利害之际不待决于“命”而后泰然,此章“命”乃为公伯寮愬子路而言,如郑浩[5]、徐英[6]、姚永朴[7];或着重于强调“道”之兴废乃“气命”使然,不过并不执着于“气命”仅为中人以下而说,亦不再对“气命”之必然性多所坚持,如王邦雄等,其《论语义理疏解》谓:“人生的理想,客观的道义,是否能大行于世,此中有社会因缘与历史条件的限制,不是主体生命的修养显发,所能独立为功的,所以不能刻意强求,也不必极力逃避。公伯寮这个人,破坏了季孙对子路的行仁,子服景伯对孔子说,我的力量还能够置公伯寮于死地,孔子回答说,道的行废,不仅是出自主体生命的自觉担负,同时也落在客观条件的限定中。这个条件系列又哪里是公伯寮一个人所能决定的呢?……命连着天而言,有时指形而上的理命,有时指自然天的气命,斯文不丧是理命,道之将废是气命,‘天命在我’自觉担负起来,气命限定者无可奈何了。”[8]踵继张氏者以为君子以义知“命”,以义安“命”,凡义所不可,即以为“命”所不有,如钱穆《论语新解》谓:“本章当与上章不怨天不尤人合参。人道之不可违者为义,天道之不可争者为命。命不可知,君子惟当以义安命。凡义所不可,即以为命所不有。故不得于命,犹不失吾义。常人于智力所无可奈何处始谓之命,故必尽智力以争。君子则一准于义,虽力有可争,智有可图,而义所不可,即斯谓之命。孔子之于公伯寮,未尝无景伯可恃。孔子之于卫卿,亦未尝无弥子瑕可缘。然循此以往,终将无以为孔子。”[9]
别趋一途者则或指出万事皆非人力所能为,有必然之天命在,孔子安“命”、信“命”而乐“命”,如康有为《论语注》谓:“孔子立命,故《易》道之至,则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得之不得曰有命,道之行与废亦有命。盖自虞舜起匹夫而为圣帝,微子生王子而遭亡,殷太公八十渔钓而成大业,颜子之三十陋巷而遂夭死,皆非人力所能为也,有天命在。助我者命使之,攻我者命致之,故知命则不怨天不尤人矣。孔子之待伯寮,孟子之待臧仓,皆归之天命。”[10]或将“命”把握为某种人无法宰制的时运、外部情势或偶然性,认为孔子借着“天”、“命”酝酿出了一种甘于殉道的宗教感,如黄克剑先生《论语疏解》谓:“诚如孔子所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道如果行得通,这除开人为的努力,那一定是人们无法宰制的时运或‘命’起了作用;同样,道如果废而不行,那也一定是人们无法宰制的时运或‘命’起了作用。当然,‘命’只是在‘外王’这一对待性领域才对‘道’的‘行’、‘废’有所制约,而在‘内圣’这一非对待性心灵境界上是无从施加影响的。”[11]复谓:“称‘命’、称‘天’而以‘道’、‘文’自任,表明孔子是一个宗教感很重的人,但这宗教感并不导向对‘天’、‘命’的盲目崇拜或一味仰赖,它在更大程度上是受德性之‘仁’熏炙的。这一份富于‘仁’之德性内涵的宗教感,支撑着孔子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信仰,养润着其‘知其不可而为之’、‘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殉道精神。”[12]
钱氏、郑氏两系学者所见互异,不过在根柢处皆否认与外物之成毁相关的必然之“命”或偶然之“命”曾为孔子所重。这一看法显然既与康氏不同,亦与王氏、黄先生相左。这章的难解之处在于孔子“命”意识之究竟。
二、“生”之或然性:孔子之前中国人的“命”意识
能自森然万象之“多”领会某种一以贯之之“一”,或能以某种赋有究极意味之“一”统摄纷繁复杂之“多”,这是一个民族的心灵触角开始探向人生的终极话题的标志。当至上神“帝”从商人的心灵深处冉冉升起时,中国人业已对“一”、“多”关系有了朦胧的意识,开始从万物的生生不已里体味那个渊默之“一”了,尽管这一切尚在以蒂为帝的隐喻里酝酿着。
从甲骨卜辞可知,至少在殷商时期,中国人已有了相当确定的“帝”崇拜意识。司生殖繁衍的“帝”起初只是风神、雨神、河神、土地神等众神之一,不过耐人寻味的是,越到后来,“帝”越为信仰中的人们所看重,并逐渐演为至尊之神,相应地“帝”字的写法在甲骨文中亦已大体定型。[13]清人吴大澂认为帝,“像花蒂之形。蒂落而成果,即草木之所由生,枝叶之所由发。生物之始,与天合德,故帝足以配天。”(《字说·帝字说》)结合近人郑继娥对“帝”字甲骨文写法、商周金文写法及战国文字、小篆写法的探究[14],和刘翔对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陶文、乐都柳湾马窑文化马丁类型陶文、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陶文、郑州二里岗商代早期陶文等史前陶文均已出现“▽”或“▽|”这一花蒂之形的考证[15],可以断定,吴氏所论大体可信。黄克剑先生指出,吴氏这一发现乃是“对先民们‘帝’崇拜这一千古之谜的道破。先民们心目中的至上神‘帝’由神化花蒂而来,花蒂却又是植物结果、生籽以繁衍后代的生机所在”。因此,“‘帝’崇拜,说到底是对生命的崇拜;在这种崇拜中,寄托了崇拜者对生命的珍爱和对生命的秘密的眷注。”[16]吴氏、黄先生的看法诚具慧识。花蒂若是“一”,由花蒂结果所生出的种子便是“多”;“帝”若是“一”,由“帝”通过众神等媒介赋予生机的万物便是“多”。在华夏民族的先民这里,“一即多”、“多即一”的探询胎育于连着“生”之根蒂的“帝”崇拜。“多”由“一”生,从被生的“多”向着“一”这一神秘的始源处问讯,人这唯一达到“生”之自觉的生灵便产生了“命”的意识。这是因为,人作为一种肉体的存在,唯有通过与外界进行必要的物质交换才能使其富有生机的肉体得以持存,对待性或有所对待是人的存在的一重规定。这里便有某种人难以主宰、难以预料的外部情势或时运、偶然性在起作用,而且越是在远古,这股力量在人的存在的这一向度就越发令人感到神秘莫测。当人由一己之“生”、由关联着一己之“生”的一族之“生”、一邦之“生”乃至天下之“生”、由关联着人之“生”的万物之“生”叩问那使众生得“生”的“生”之究极处时,“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自何处去”、“谁主宰着我的生,谁又主宰着我的死”的“命”意识便油然而生,其与“生”因之与“生”之或然性密切相关。

三、与“道”错落而行的“生”之或然性:孔孟之“命”意识
孔子之后,中国人的心灵眷注的焦点开始由“命”转向“道”。“一即多”、“多即一”的思致依然存在,不过不再是“一”于“命”,而是“一”于“道”。但“命”意识在孔孟这里并未消失,尽管它已是改换了一种人文背景的“生”之或然性。
孔子指出,与同“命”密切相关的死生、富贵的价值相比,人生还有另外一重更值得追求的价值,此即使人有别于其他一切存在物的“仁”的价值。“仁”的价值涉及心灵的纯洁、精神的净化、境界的提升。它在人的生命中有其内在的根荄,人只要觉悟到了这一点并愿意努力求取这重价值,总可以依照自己努力的程度达到相应的心灵境界。所以孔子亦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又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这两重价值分别对应于人的受到“命”的限制的对待性存在与不受“命”的制约的非对待性存在,相互独立,彼此不可替代。不过,既然死生、富贵的价值有待于“命”的成全,而且,比起“仁”心、人格的修养来,亦非人生的第一位价值,因此,一个真正领悟到人生真谛的人自当首先存心于“仁”的德性的陶冶,不必过分执着于死生、富贵而以夭寿、爵禄为念,当这两重价值发生根本性的冲突而不能两全之际,他能够为了“成仁”而将死生、富贵置之度外。所以孔子又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可以说是从“仁”道的高度对受“命”的因素制约的死生、富贵价值的穿透。[19]与此可相互说明的是,由孔子赋予一种诠释的价值取向,以诠释《易经》的方式渐次形成的《易传》,其主题词已落在“时中”而“养正”,无论是就乾卦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还是就坤卦所说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都表明《易》的理趣在孔子之后已发生了由关联着“吉凶休咎”的“命”转换为“道”的深刻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命”的话题并未就此隐去。孔子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又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这些说法表明,在孔子看来,贫贱富贵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弃”、“取”或“去”、“得”,并非由上天安排或命中注定,只是死生、富贵价值不再被看作是人生的最高价值,甚至唯一价值。
对孔子这种“命”意识作了重要阐发的是孟子。其谓:“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在孟子看来,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可称之“性”,但是,无论是它们的产生或其可能获得的满足,均与人的肉体自然及与满足人的众多肉体需求之外部自然直接相关,这里遂有一重人无法宰制、无法逆料的“命”的因素在起作用,所以君子并不将其归之于“性”。与此相对,父子之间对“仁”的履蹈、君臣之间对“义”的恪守、宾主之间对“礼”的践行,以及圣人对“天道”的先觉,其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与每个人天生的禀赋、后天的教育状况、人生际遇等“命”的因素相关。然而任何人只要努力去践履,总可以做得更好一些,这是由于“仁”、“义”、“礼”、“天道”诸德性境界之根芽皆内在于每个人的“天性”,故而真正的君子将提升它们视为人的份内之事,不将其委之于“命”。此处所作的“性”、“命”分辨说明,尽管被充实了德性内涵的“性”在孟子这里更被看重,与某种难以掌控、无从预料的外部情势关联着的“命”的话题——所谓“生”之或然性——依然延续着,只是在新的人文视野里被赋予了更加复杂、深微的含义。孟子亦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朱子《孟子集注》注谓:“在我者,谓仁义礼智,凡性之所有者。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则不可必得。在外者,谓富贵利达,凡外物皆是。”[20]“求有益于得”是指所求与所得成比例,“求无益于得”是指所求与所得不成比例。这句话表明,在孟子这里“求在我者”之“仁义礼智”这类德行的养成是每个人能自我作主因而无可推诿于外的,“求在外者”之“富贵利达”这类外物的致取需合乎道义,而且即便这样,能否如愿亦与“命”的因素有关,可见,“命”的话题并非不受“道”的辐射,但在涉及外物因而必有待于外部条件成全之对待性向度上是被确认为有其独立价值的,不可为“道”的话题所涵盖。
这里,所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即孔子所说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所谓“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即孔子所说的“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二者合起来其意味正相通于孔子所说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事实上,“命”的话题永远不可能被否弃,同对“道”的瞩望一样,对“命”的顾念构成了人生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终极眷注。因此,问题不在于谈“命”与否,人生的境界即有不同,不在于孔孟之“道”被觉悟后,“命”是否为“道”所取消,而在于二者在孔孟的价值判断中孰轻孰重,孰先孰后。钱氏、郑氏、徐氏、姚氏可以说皆致误于此;王氏等谨从宋儒“理命”、“气命”二分法而不拘泥,反倒融通许多;至于黄先生的见解,最为精到。
四、孔子对“命”意识之功用的转化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孔子素日留给弟子、时人的是一个有着真挚信仰而率性、谨敬的做人范本。面对达巷党人“博学而无所成名”的叹惋,他会诙谐地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同上)时人有以为圣者,他会极认真地分辨道:“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叶公问夫子于子路,子路一时语塞,孔子听说后,描绘了一幅栩栩如生的自画像,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同上)但临危遇厄之际,他却又总会称“天”而呼、称“命”而叹。“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便是其中一叹。朱子认为,孔子称“公伯寮其如命何”,不过“言此以晓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钱穆指出:“孔子临危,每发信天知命之言。盖孔子自信极深,认为己之道,即天所欲行于世之道。自谦又甚笃,认为己之得明于此道,非由己之知力,乃天意使之明。此乃孔子内心诚感其如此,所谓信道笃而自知明,非于危难之际所能伪为。”[21]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不过皆有欠妥切。值得留意的是黄先生的诠解,其将孔子“称‘命’、称‘天’而以‘道’、‘文’自任”关联于一份“富于‘仁’之德性内涵的宗教感”,断言正是这份宗教感滋养着孔子的殉道精神,此说深美有味。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谈到“力学的崇高”时指出,“力学的崇高”归根结底“不存在于自然界的任何物内,而是内在于我们的心里”[22]。不过,正像他在论及“数学的崇高”时强调数量上“绝对的大”的刺激,他在说到“力学的崇高”时亦分外看重力量上“绝对的强”的刺激,认为自然力的暴烈、可怖使人“认识到我们物理上的无力,但却同时发现一种能力,判定我们不屈属于它,并且有一种对自然的优越性”[23]。他宣称,如此被激发出的超乎自身自然而足以俯瞰外部自然的那种力是以理性为依据的人格之力。它意味着,纵使人在肉体上被无情的自然暴力所挫败,人也不应就此降低自己的人格。由人的肉体自然与外部自然的相较量所引生的恐怖在被理性的力量解除后,人遂获得一种自重压下透出的快感——崇高感。康德在列举这类自然力时,提到了高耸而下垂的危石断岩、滚滚而来的乌云中的雷鸣电闪、飞流直下的悬崖高瀑、撼天动地的火山爆发,等等。这些可以说是“力学的崇高”所必要的表象依据。
道德之崇高感的产生有一种情况与此相似,亦离不开酷烈的外部条件的触发,此即那种至大至刚的道德崇高感的瞬间勃发。绝对强大的足以摧毁人的肉体存在的自然威力、绝对威烈的人间势力、冥冥中某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又时时处处无不催逼人的时运,这些都足以让人在对待性领域产生一种强烈的莫可奈何的“命”意识。但是,一个有着高卓的道德境界的人,能够在对待性领域受到重挫之际骤然察觉到纵使自己在此是无能无力的,但他另有一方非对待性的心灵世界,那个独立的王国以“仁”德的修养为主,他于彼完全可以秉持“自律”、“自得”、“自贞”的原则而不受任何外部力量的限制,在死生、富贵价值与“仁”的价值不能两全的状况下,为了笃守对人来说最为珍贵的“仁”的价值他甚至可以视死如归。当这个真诚的修德者瞬间反省到了这一点,一种足以俯瞰外部情势、足以抗衡外部情势的巨大的信仰力量便喷薄而出,据此,人可以藐视在对待性领域里绝对无法抗拒的一切力量,并由此获得一种直塞于天地之间的甘于殉道的崇高感或宗教感。不过,正如缺少了力量上“绝对的强”,“力学的崇高”将无从激发一样,倘若“命”意识不够强烈,异乎寻常的道德的崇高感或宗教感亦难以勃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这是以任何人皆无法宰制的时运之“命”抗拒人间某种倒行逆施的威势之“命”,时运之“命”只在对待性领域对“道”之“行”、“废”有所制约,对非对待性的心灵境界无从施加影响。因此,“公伯寮其如命何”说到底乃是“公伯寮其如道何”。孔子这一叹,是在受到“命”意识的强烈刺激下油然而发的。平时少了这一层可谓“无目的而合目的性”的刺激,遂归之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渊默、从容。正像缺乏必要的表象,审美的崇高亦无从发生。黄克剑先生认为这一叹表明孔子是一个有着深沉的宗教情怀的人,可谓颇有见地。
有意味的是,康德还认为,对于崇高的美学判断,“虽然需要文化修养,却并不因此首先是由文化产生出来的和习俗性地导进社会的,而是它在人类的天性里有它的基础的。那就是对于(实践的)诸观念(即道德的诸观念)的情感是存在天赋里的。”[24]不过,他承认,从战栗于自然威势的“粗陋的人”进到能够在心意中超越自然威力以评赏崇高的“受过文化陶冶的人”,有待于道德观念的演进发展。从康德这段意味深长的谈论中,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启示:(1)审美意义上的崇高感是瞬间爆发的,它的得以可能需以道德崇高感的持续培壅为前提;(2)尽管引发审美崇高感的最根本依据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力量上“绝对的强”却只是在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者那里才可能激发出一种审美崇高感。由此又或可作如下两点引申:(1)气贯长虹的道德崇高感的勃发,是持久地涵养于一衣一食、一语一默、一坐一卧皆求“中乎礼”之素行的日常崇高感,在特殊时刻受到某种“命”意识强烈刺激后极其璀璨的一闪,默运于庸言庸行的道德崇高感之于可充塞于天地之间的道德崇高感的关系,勉可类比于道德崇高感之于审美崇高感的关系。(2)没有“仁”的觉悟,没有“道”的反省,没有“德”的自得,“命”意识只能在人们的心灵营造出一种恐怖的氛围,作为“生”之或然性的命比之作为“一种不可挽回的必然性”的命运多了份亲切的幻象,但它终究属于人不能逆料的情势或时运,结胎于此的“命”意识并不能唤起丝毫的超越生死利害的崇高。对死生、富贵价值和“仁”德价值的觉醒,对人生终极眷注之重心的转换,对“中庸”作为一种道德信仰的觉悟,这是孔子对殷周以来根深蒂固的“命”意识之功能所以能作出富于时代变革意义之扭转的底蕴所在。“命”意识在孔子这里从未被遗弃,这固然是由于人生的有待性或对待性是人的一重规定,也由于它在孔子这里被有意无意地用于酝酿一种道德的崇高感。这是孔子对“命”意识之功用所作的最有价值的转化。
五、“知天命”:道德信仰烛照下的“命”意识
在孔子所有谈“命”的话语里,“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常被学人拿来与“公伯寮其如命何”等语相参。它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两颗同样光彩夺目的宝石的关系,不如说是同一颗宝石在荫蔽处与日光下的关系。
“天命”的觉悟与“中庸”观念有关。长期以来,尤其是大半个世纪以来,学人惯于在上下、前后、左右以至好坏、优劣的居间或调和之位置上理解“中”,这“中”其实是“中间”、“中等”、“中级”的同义语,它与孔子作为修德之至境的“中庸”并不相干。所谓中庸,是指一种确然不移的标准,它指示着一种毫不含糊的“分际”,一种不可稍有苟且的“度”。比如勇敢,稍微过了一点即是鲁莽,稍微不及便是怯懦,那个可用“恰当”、“恰好”、“恰如其分”一类词藻作形容或描摹的“勇敢”,在人的价值追求当中是真实的,它是勇敢的极致状态。它可作为一种最高的标准,用来衡量现实中所有的勇敢行为勇敢到何等的程度,亦可作为一种最高的理想,吸引着现实中的人们努力减少鲁莽的成分或怯懦的成分,在逼近最圆满的勇敢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其德行修养的状况。然而,这种虚灵而真实的中庸,依孔子的理致却是“不可能”的。孔子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又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礼记·中庸》)所谓“不可能”,即是指对任何经验的个体来说,欲达致无一丝一毫之“过”、亦无一丝一毫之“不及”的绝对恰切之“中庸”,皆是不可能的。[25]正如对任何经验的个体来说,无论其技艺何等娴熟、高超,绘出或造出自圆心至圆周的所有半径完全相等的绝对的圆,都是不可能的。这个“不可能”的中庸,对现实中的不断自我砥砺以求精进不已的修德者说来,便构成一种既殊异于上帝、“绝对精神”又有别于偶像化了的人间权威的非实体的信仰。它以其无以伦比的风致,散发出无穷的魅力,诱导人以之为最高的范本持续不辍地向之而趋,人纵使竭尽全力犹无法最后完全接近,同时它又仿佛蕴含着不尽的督责,策勉人以之为最高的衡准刻刻抚躬自问,直至生命的最后一瞬仍战兢不已。作为一种道德信仰的“中庸”观念,使孔子的以“仁”为根本价值取向的学说有了形而上的一度,从此“命”意识在孔子这里有了另一种功用。
“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这句由衷的自励励人之语道出了孔子对“道”的无限仰慕。人有此富于形上色彩的觉悟,即懂得了一生的志业之所归,在人间践行、推广“为仁”之道的神圣使命是“道”或“天”赋予的,人除了谨遵这一使命别无他途。此即所谓“知天命”。人有了这一观念,可以说便有了一种任何人间的威压或诱惑皆无法摇夺的天职观念。只是这里的“天”已不是周人信仰中的与“帝”相通的掌控人间祸福的至上神,而是与“道”相贯的以“仁”为价值内涵的义理之天,亦即“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或“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之“天”。相应地,这里的“命”亦不是殷人、周人信从的可左右人的死生、富贵价值的被神圣化了的或然性,其重心落在涉及人的“仁”德价值的“绝对命令”,它在信从者这里遂转为一种天职观念,其意味在曾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一语有过极恳切的呈示。不过,由“道”或“天”所赋予的推行“为仁”之道的神圣使命既然必须在人间展开,因而必有待于外部条件的成全,“天命”于是便同时涉及人生的无待向度和有待向度,并在承认有待向度的独立性的前提下以“无待”烛临“有待”、导引“有待”;或然性意义上的“命”意识在这里依然若隐若现,只是不再占居主导地位。与此略异,“天命”在承担者那里则将召唤出富于崇高感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强调以“无待”穿透“有待”。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原是隐者对孔子不能割舍那点“类万物之情”而陷入隐者决然避开的世俗纠葛犹不舍不怨的讥讽,然而,换一种角度,这讥讽也未尝不可理解为一种至高的赞誉。知其不可,仍执着为之,非有坚确不拔的道德信仰而能置个人之生死利害于不顾者决不可为。这种情怀,这种精神,这种境界,养润了孔子日常容色言动皆求合于礼仪的一丝不苟,亦孕育了孔子厄于陈蔡而弦歌不辍的从容,其于生死危厄关头沛然而发的那份感人至深的崇高感,不过是平日这份默运中的渊醇的崇高感在特殊时刻的升华。
注释:
[1] 朱 熹:《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8页。
[2] 黎靖德:《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142页。
[3] 朱 熹:《四书或问·论语或问》,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第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40页。
[4] 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 593-594页。
[5] 郑 浩:《论语集注述要》,台北:力行书局,1970年,第 323页。
[6] 徐 英:《论语会笺》,台北:中正书局,1987年,第214-215页。
[7] 姚永朴:《论语解注合编》,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251-252页。
[8] 王邦雄、杨祖汉、曾昭旭:《论语义理疏解》,台北:鹅湖月刊社,1982年,第12-13页。
[9][21] 钱 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384,224页。
[10] 康有为:《论语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22页。
[11][12][25] 黄克剑:《论语疏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4,193,7页。
[13] 陈洪杏:《生命崇拜与“帝崇拜”——一种对商人形成中的宇宙意识的探寻》,《殷都学刊》2010年第1期。
[14] 郑继娥:《甲骨文中的“帝”字》,《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1期。
[15] 刘 翔:《中国传统价值诠释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0页。
[16] 黄克剑:《由“命”而“道”——先秦诸子十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17] 黄克剑:《〈周易〉经、传与儒、道、阴阳家学缘探要》,《黄克剑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18] 伊壁鸠鲁:《致美诺寇的信》,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69页。
[19]黄克剑:《“生”·“命”·“性”·“道”——对先秦人文意识嬗变的一种阐释》,《哲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朱 熹:《四书集注·孟子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50页。
[22][23][24]康 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04,101-102,106页。
[责任编辑:陈未鹏]
2013-09-20
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学以致其道’——近代以来〈论语〉注疏辨正”(2012B153)
陈洪杏, 女, 广东揭阳人, 福建省委党校哲学部副研究员。
B222
A
1002-3321(2014)05-005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