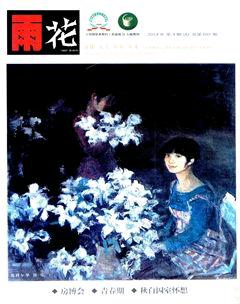苏州好,水调旧家乡
●陈 武
苏州好,水调旧家乡
●陈 武
故乡的情怀,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很深的暗藏,我不知道,俞平伯频繁地来往于苏杭,也是在寻找他的故乡吗?
俞平伯对于家乡苏州,有着特殊的情怀,这里有他童年、少年成长的故园旧宅,还有他读过书的中学——虽然只有几个月,但在他求学生涯中,不能不说是重要的一站。
1920年12月11日,俞平伯从杭州出发,和舅父、夫人一起,开始六天的苏州、无锡、上海三地游。历史上,文人们喜欢把苏杭相提并论,主要是因为相似的江南风光和人文环境。对于俞平伯来说,还有另一层意义,两地都是故乡。苏州自不必说。杭州呢?曾祖父在此担任多年教习,有故宅俞楼,而曾祖父母的安葬地也在西湖边上。早在1918年,俞平伯在北京大学求学时,就有四首《忆江南》,把苏杭一并包罗了:
江南好,长忆在西湖。云际遥青多拥髻,堤头腻绿每皴螺。叶艇蘸晴波。
江南好,长忆在山塘。迟日烘晴花市闹,邻滩打水女砧忙,铃塔动微阳。
江南好,长忆在吴门。门户窥人莺燕懒,日斜深巷卖饧声,吹彻杏花明。
江南好,长忆在吾乡。鱼浪乌篷春拨网,蟹田红稻夜鸣榔,人语闹宵航。
到苏州的第二天下午,俞平伯一行就到全浙会馆,听了一出昆剧。苏州和杭州都是昆曲中心,会馆、戏园、茶社常有演出,那咿呀声中,道出多少江南水乡的清音味儿。这次听曲,给俞平伯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直到五十年后,他还写词怀念:“苏州好,水调旧家乡。只爱清歌谐笛韵,未谙红粉递登场,爨弄兴偏长。”这首词,如果把第一句改成“江南好”,可以和上述的四首合为一辑了。虽写作时间相隔五十多年,情感和诗意上,却是相互牵连的,甚至相互递进的。
苏州好,我是知道的。我多次去过苏州,开始也只想着寒山寺、拙政园、山塘街什么的。后来便沿老街随意走走,发现情趣大为不同。如凤凰街附近有条不起眼的小河边,是一条麻石铺的路,随河蜿蜒。我走在路上,看着脚下的石板,石板上的纹和字,看着流动的河水,看着河边的白墙和灰黑的小瓦,感觉有一种安静、恬淡和优雅的气息,那些老式的窗棂、雕花的门楼,又有一些古老和隐秘。当门窗里透出一缕琴音或清唱时,我的心会跟着琴弦、清音怦然一动,感觉苏州的味儿有了,情也有了。
俞平伯这次在全浙会馆听曲,莫非是计划中的一部分?而我相信,第二天重游平江中学旧址,肯定是有所计划的。俞平伯在投考北大之前,曾在这所新式学校里,突击上了半年课,时间是1915年春到这年的高考。在这之前,俞平伯的读书生活,全部是家教或家塾,对于饱学一肚子旧学问的俞平伯来说,平江半年,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新式的教育,不仅让他开了眼界,顺利考入北大,这半年的平江学习生活,对他也特别关键。所以北大毕业后,经历短暂的留学,回杭州小住半年,游山阴道,八月又去南京游览莫愁湖和秦淮河,去上海访陈独秀,和周作人通信,游杭州皋亭山,还写了好几篇关于诗歌的论文,这些成就不可谓不大。但苏州,毕竟是他出生地,有他的曲园祖宅,有小时候无数次进出的马医科巷,内心里还是要回来看看的——并不是要装点衣锦还乡的荣耀,而是人人都有的少年情结。那么,平江中学,也就不能不去了。
12月18日,俞平伯专门绕道,去干将坊巷让王庙旧址,这就是母校平江中学了。只是此时此地,这里已经颓废得不像样子了。站立旧址前的俞平伯,忆及几年前的聚读时光,感怀是如何的深,心情是如何的不平静,想必外人无以知晓吧。但,这样深切的感受,至少一直萦绕于这次旅行,否则,何以一回到杭州,就写下新诗《如醉梦的踯躅》呢。而诗前一段小序,读来更让人唏嘘:
一九一五年之春,予在苏州平江中学校读书半年,后即北去。校旋亦闭歇,旧时朋侣星散。予亦东西奔走无所成就。一九二○年十二月自杭而苏,特迂道过干将坊巷让王庙校址,屋宇荒寂殆将倾圮。惟儿时聚读光景,忽忽五六年矣,久已淡如烟雾;一旦旧地重来顿堪仿佛。寻迹堂庑间,低回不能遽去;奈守庙童子不解人意,屡相催追以目,遂怅然而去。归途夕阳在树,曲陌新晴,卖糖声,挑担声,驴步得得,驴铃郎当声,耳目所接皆如旧相识。踯躅街头,如醉如梦。旧感丛绕,明知其无当;惟不堪排宕,返杭后姑以诗写之;诗既成,姑序。序之工拙与成诗与否,均不及计矣。
一九二○,十二,二十七,在杭州记。
干将坊巷,是旧时苏州一条普通的小巷。据《姑苏志》称:“因干将墓对峙而名。”又据《吴郡志》载:“吴王使干将铸剑于此,故曰将门。今谓之匠,音之讹。”据上海、苏州等地的民间传说,吴越时,干将是铸剑名手,与欧冶子齐名。干将铸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阴阳同光,而金铁之精还不见销融”。其妻子莫邪说,“神物之化,须人而成”,铸剑不成,是否也要得人而后才成。于是莫邪投身炉中,结果铸成雌雄两把名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这个传说,苏州人记忆最为深刻,某园的试剑石,传说所用宝剑就是干将的剑。干将坊巷在苏州存在很久,和如今的干将路不是一回事。据苏州朋友相告,昔日从人民路到言桥这一截,就是干将坊巷。那时候高高的石牌坊立在巷口。据说,直到1982年才被毁掉。苏州好东西太多了,毁掉一两个古牌坊也许并不心疼,毁掉一条小巷也无所谓,毁掉一代人的记忆和情结,却是任何东西也无法弥补的。
《如醉梦的踯躅》这首诗,收在俞平伯的诗集《冬夜》里。这首诗所传递的信息,小序里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但等把全诗读完,还是心随俞平伯如醉梦般地踯躅了:
匾是竖着;/庙门是开着;/要枯而不愿意枯的树,/还是三株四株这样立着;/尘封了的大殿照旧肮脏着;/什么都是一样!/早跑了五六年底时光,/什么都是一样吗?
俞平伯的无奈一问,没有得到回答。也不需要回答,答案在他眼里清清楚楚了。最后,诗人只能说:“历来人事所暗示的,只是添些无聊赖的感慨。暂时撇去,也暂时温暖起‘儿时’的滋味,依稀酒样的酽,睡样的甜。”看来,童年记忆的力量,真能消除人生很多无奈的。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到了来年的1月12日,俞平伯还时时记得半个多月前的游览所见所闻,又写了一首《哭声》:“一别六年的地方,六年后来了的我,顿从可厌中变现可怕的光景来,从可怕里又翻涌出一种摇动的悲哀。这叫我永不忘记!”
时间很快就到了1921年9月14日,心里一直惦念着家乡的俞平伯,和夫人一起,再次从杭州来到苏州。俞平伯这回没有去访旧,而是和夫人乘船去了寒山寺。不知为什么,对于这次寒山寺的游览,俞平伯心情也并不愉快,回杭后,于三十日创作一首《凄然》:
哪里有寒山!/哪里有拾得!/哪里去追寻诗人们底魂魄!/只凭着七七八八,廓廓落落/将倒未倒的破屋,/粘住失意的游踪,/三两番的低回踯躅。
明艳的凤仙花,/喜欢开到荒凉的野寺;/那带路的姑娘,/又想染红她底指甲,/向花丛去掐了一握。/他俩只随随便便的,/似乎就此可以过去了;/但这如何能,在不可聊赖的情怀?
有剥落披离的粉墙。/欹斜宛转的游廊,/蹭蹬的陂陀路,/有风尘色的游人一双。/萧萧条条的树梢头,/迎那西风碎响。/他们可也有悲摇落的心肠?
镗然起了,/嗡然远了,/渐殷然散了;/枫桥镇上底人,/寒山寺里底僧,/九月秋风下痴着的我们,/都跟了沉凝的声音依依荡颤。/是寒山寺底钟么?/是旧时寒山寺底钟声么?
每每读这首诗,就会想起我的寒山寺之游。我到了寒山寺时,心情也不爽,说不出的理由,也许张继的那首诗太有名了吧,去时,诗中的情调,不由得会涌上心头。那么俞平伯的游览,给他的感觉,正如标题所说,也是凄然的了。诗前依旧有一小序,照录如次,来作证我的推测:“今年九月十四日我同长环到苏州,买舟去游寒山寺,虽时值秋半,而因江南阴雨兼旬,故秋意已颇深矣。且是日雨意未消,游者阒然;瞻眺之余,顿感寥廓!人在废殿颓垣间,得闻清钟,尤动凄怆怀恋之思,低回不能自已。夫寒山一荒寺耳,而摇荡性灵至于如此,岂非情缘境生,而境随情感耶?此诗之成,殆吾之结习使然。”已经说得极为明白了。特别是那连用的三个惊叹号,还有四个问号的安排,把俞平伯当时的心境和寒山寺秋意融合得十分体贴。这次寒山寺之游,他是否专程一见曾祖父重写的诗碑呢?“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诗在,碑在,人已不在。张继的诗不朽,书碑的曾祖父也不朽,但是来客的心情却是悲戚的。不问是否和俞平伯有着同样的情怀,就是和诗碑毫无瓜葛的我,一到寒山寺,心情也同样地落进了《枫桥夜泊》所营造的氛围里。
接下来的1921年11月9日和10日,年轻的俞平伯轻车简从,又来到隶属于苏州的常熟游览两天,在美丽的虞山下、尚湖边,留下他亲密常熟山水的印痕和足迹,也留下他对常熟山水的情思和感念。但是,这一次初冬的浏览,似乎有些特别,和前几次的心情大为不一样,荡舟尚湖,并非惬意和放松,而是带着某种心情吧,否则,怎么会在常熟旅馆中,想起在杭州看到的那首情歌呢?
歌谣只有四句:“高山有好水,平地有好花;家家有好女,无钱没想她。”这是一首纯朴、明净、简洁的歌谣,俞平伯反复咀嚼,夜不能寐,就在旅馆里,把歌谣扩写成一首白话诗。俞平伯在创作自认为重要的作品时,都会写篇小序。这次也不例外,在序中,他自谦地说:新译的“词句虽多至数倍,而温厚蕴藉之处恐不及原作十分之一。”看来他还是被原作深深地感动着。
第二天,俞平伯作了尚湖之游。俞平伯对尚湖并不陌生,他知道黄公望、沈周、唐寅、康有为等历代文人均有题咏,也知道虞山西麓拂水岩下的拂水山庄,这是钱牧斋早年的读书处,也是柳如是生活几十年的地方。俞平伯一边荡舟,一边欣赏浩渺的湖水和背后的青山,引发了诗兴,但他并没有被湖光山色所蒙蔽(或者他心底里寻找的,并不是湖光山色),而是在船上信笔写了一首极具现代意义的爱情诗《不解与错误》。
红月季,开着花,空山里,/会觉得孤寂吧,/大约是的!
我来呢,轻轻地握着,/她已先低头了。
我想慰她底孤寂,/她偏独自去零落,这将使我不可解了。
诗人借开在空山里的红月季之名,感叹“她”的孤寂。即便是“我”来了,轻轻地握着“她”,想慰“她”的孤寂,也没能挽回“她”的零落。真让人伤感。这是作者抒发爱情的无常吗?记得我年轻时读这首诗时,被深深地感动着,也深深地惋惜着,怀疑俞平伯美满的婚姻中,会不会也有遗憾。
尚湖我去过三次,都未及划船。想起九十多年前的湖面上,一叶小舟轻巧漂移,诗文两绝的俞平伯,只二十出头岁,多么的意气风发,他看满眼湖光山色,难道仅仅是为抒发一点个人的私情?那红月季是暗指谁呢?
结束尚湖之游,俞平伯于11日又赶往苏州。在苏州做何游览,见了谁,都无从查考了,但他创作的新诗名篇《愿您》,却是很多人知道的,一来,是这首诗被朱自清选入了《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二来,这首爱情诗里的“您”指向谁,和《不解与错误》里的红月季是否是一个人呢?我们只能猜测了:
愿你不再爱我,/愿你学着自爱罢,/自爱方是爱我了,/自爱更胜于爱我了!/我愿意去躲着你,/碎了我底心,/但却不愿意你心为我碎啊!/好不宽恕的我,/你能宽恕我吗?/我可以请求你底宽恕吗?/你心里如有我,/你心里如有我心里的你;/不应把我怎样待你的心待我,/应把我愿意你怎样待我的心待我。
苏州对于俞平伯来说,是水调旧家乡,难道也有遗落的爱情?俞氏的老师周作人写过一篇《初恋》,对那个曾经暗恋过的杨家三姑娘,有过细微的心理刻画。俞平伯也有过这样的初恋吗?这首诗,通过主人公告白的形式,表现自己对恋人的心意,完全袒露了自己的心声。这样的爱情,是双方都把握不了的,不知什么原因,“我”不得不与女友分手。但,两人的情感,依然藕断丝连,虽嘴上说,愿你不再爱我,其实是多么希望对方还在爱他啊。而且,这样的感情一咏三叹,不断重复,就是“我”希望“你”爱“我”,而不是不爱“我”。联想到前一天,他在尚湖舟中写的《不解与错误》,俞平伯对失去的曾经的爱,多么的刻骨铭心。请看诗中这样的两节:
她或恨我底自私,/我也怨她底负心。/她已误,我已错。/
错是错了,/不解只是不解了!
把俞平伯这两首诗对照着读,如此的直白、坦率的爱情表白,对俞平伯来说是很少见的。这样,我们就联想到,为什么俞平伯匆匆一到常熟,在旅馆中想到在杭州看到的童谣了,“家家有好女”只不过是引子,是他念起自己心中的“好女”,所以才从杭州赶往常熟,才有心情把这四句童谣改写成长长的一首白话诗。
同时在尚湖舟中,他还填写了那首著名的《霜花腴·尚湖泛舟》:
稻塍径窄,耐浅寒,低颦屡整罗裳。风懒波沉,橹稀人淡,深秋共倚斜阳。暮山静妆,对镜奁、还晕丹黄。溯来时、翠柏阴多,故家乔木感凄凉。谁醒泛秋轻梦,近荒城一角,夜色茫茫。邀醉清灯,留英残菊,连宵倦客幽窗。旧游可伤,纵再来、休管沧桑;更西湖、倩影兰桡,哪堪思故乡。
从这首词中,也可知道,俞平伯不是第一次来尚湖了。这次泛舟,给他留下的记忆,更多的是伤感的主调,发出“旧游可伤”、“哪堪思故乡”的感慨。“低颦屡整罗裳”的人啊,还能“深秋共倚斜阳”吗?
从1920年12月16日到1921年11月9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俞平伯三次去苏州,每次都有新诗创作,粗略统计,共有新诗六首,还有古诗词若干。这些新诗,都收在他重要的一本诗集《冬夜》里。特别是1921年11月9日的常熟、苏州之游,他已经于10月辞去浙江一师的教职,准备赴美考察,却抽时间回苏常。他对苏州的情怀,在许多诗章中都有流露,最让人感怀的,是他在《小诗两首》的《客》里所说:“我北归,我又要南归,归来底中间,把故乡掉了!”
故乡的情怀,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很深的暗藏,我不知道,俞平伯频繁地来往于苏杭,也是在寻找他的故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