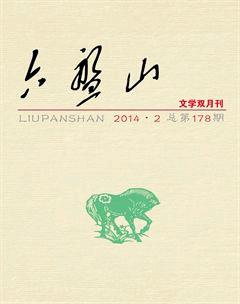她的手
石也
总之,对我来说,那是一个渴望爱与被爱,有机会干很多好事也有机会做很多坏事的特殊年代。可是我什么也没来得及做,就沦为一个街头混混,一个让人望而生畏又无限怜惜的可怜虫。
这一切要从亚桐说起。
那天早上我奉父亲之命去城东的农贸市场买菜,父亲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下岗工人,每日都会把自己整醉,醉了就没完没了的数说家里人的种种不是,仿佛是酒让他开了慧眼,只有不停地喝酒,只有从早到晚地醉着,他才能正确看待世界才能认清家人的嘴脸。父亲在喝酒前必须要整两个小菜,如果有谁违拗了他,让他喝得不顺意,轻则摔碟子砸碗,重则大打出手。母亲当然是父亲铁拳的重灾区,忍无可忍的她带着小妹去城南一家腌菜厂做了洗菜工,吃住都在厂里,工资不高,却能挣来一份短暂的安宁。从此,母亲很少回家,偶尔回来,也是顶着一团浓浓的腌菜味搁下几个钱就走。父亲无处发泄,经常莫名其妙地逮住我就是一顿胖揍,活像一个即将成人的小小男子汉不经过捶打就不可能成人。
街上到处都是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当官的,打工的,流浪的,花花黎黎,形形色色。我喜欢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我渴望能在人群中找到一个可以倾心相谈的朋友,无论男女。
我脑子乱哄哄的,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样一天天过下去有什么意义?还有,这种无聊又无趣的日子到底能不能如常过下去?我不爱想这些问题,一想,脑子就疼,可我还是忍不住想了又想。
我就在这乱哄哄的思绪里上了一辆公交车。那时公交车在这个北方小城刚刚兴起,人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它,还不能充分享用它,只有少数无事可做的闲人才会偶尔坐坐。总之,小城公交的顾客寥寥,为了拢住这为数不多的顾客,公交司乘人员不惜和他们拉关系套近乎,甚至为他们改变运行路线。想走哪儿就走哪儿,爱怎么走就怎么走,坐公交有如打的一样舒服。即使如此,愿意坐公交的人还是稀稀落落。
我毫不费力的在后门靠边的位置找到一个座位,既能方便地看到街景,又可以轻易地总览车内各色人等。坐定以后,我看到车里空座还很多,有几个行迹可疑的家伙却不去坐座位,反而在车里蹿来蹿去,就像坐公交的全部乐趣就是在阔大的车厢里抓着扶手来回蹿动。我在心里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我相信最早熟悉公交的不是普通乘客,而是那些寄生虫一样无处不在的扒手,当游走在公园、商场、银行、车站等一些地方的人们见惯了自己或别人被割破口袋或皮包,辛苦钱被轻易顺走的情景以后,他们的警惕性也空前高涨,扒手们不得不开拓新的地盘。作为一种新生的、人口可能密集并方便下手的公众场所,公交车潜在的“商机”不可能不让这些嗅觉灵敏的家伙心动。
当然,我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车上任何人,我只能睁大眼睛看这些可恶的家伙怎么表演下去。我盯着,一眼不眨地盯着这几个人的一举一动。这几个人好像并不急于下手,还是在车厢里来回走动,就像那些虚位以待的座位统统有刺。我的眼睛因长时间的凝视变得酸涩,脖子也跟着僵硬了。这时候,车上又跳上一个活灵活现的女孩,她左手提着一只份量不轻的书袋,右手抓紧扶手,却也不去坐座位,就像和前面几个家伙是一伙的。
这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女孩,她头发长长地从肩上瀑布样披下来,整张脸也被葱郁的头发遮盖起来,两只眼睛却在时隐时现的发丛里闪着狡黠的光。她上车以后一直保持着同一姿势站在离后门最近的地方,有人上下车,她会主动侧一侧身子。她不时要甩一甩满头长发,腾出眼睛快速又轻缈地掠一掠车内的景象,看起来对所有人都保留着足够的戒备。
她与我四目对接的那一刻,我感到一股电流一样的东西穿过全身,我被一种神秘的东西打中了,即刻产生想要认识她的冲动。但我知道人的真实想法不能轻易地表露,而是要适当地遮掩一下、隐藏一下。可是我没办法做到心如止水,我的目光开始定定地围绕她,暖暖的,很可能也色迷迷的。我其实没有那么坏,我只想把这个可爱的姑娘用目光和那几个可恶的家伙隔开,免受污染。
也许是我的心思过于集中,竟没注意先前那几个家伙怎么凑到长发女孩身边。只见他们故意在她面前碰碰撞撞,狼子之心昭然若揭。正好票员开始报站,说下一站就是农贸市场,下车的往外换一下。我站了起来,抓紧扶手盯着那几个人蠢蠢欲动的手。就在车门打开的那一瞬,一个五大三粗留着光头的家伙故意朝她身上一撞,另一个留着长发眼睛有点斜的家伙假意帮她托快要掉地上的书袋,却不失时机的把手伸进去。一摞大票的一个拐角已被他从书袋里拽出。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贪吃逞能是非分明的蠢货,看到丑恶现象,我会大声表达自己的厌恶,遇到不平事,我会挺身而出,用拳脚表明自己的立场。父母给我了强健的体魄,既经得起打,又能打出威势。我却因这种直鲁鲁毛糙糙的性格,广泛树敌,鲜有人缘,活的十分孤独。
说时迟,那时快。我一把扼住斜眼抓着钱的那只手腕,声色俱厉的吼道,你要干什么?!光头和另外几个人立刻过来在我身上左一拳右一拳打开了,但这不疼不痒的捶打在我简直如同搔痒。公交车上顿时乱成一团,好在长发女孩已经警觉,抱紧书袋先自下车了。我的事情却还没完,我一手扯着斜眼,一手阻挡光头他们的进攻。司机早已不耐烦了,说你们下车打去,别影响其他人了。司机的话没有让我难为情,反倒提醒了我,车里碍手碍脚施展不开,我在几个人的夹击下处于尴尬的被动状态,如果换到大街上,谅这几个小蟊贼也不会是我的对手。我狠狠扯下斜眼,却不料,这一扯竟扯出了一长串,公交车几乎被我扯空了。
下了车,我立刻和那伙人用拳脚交流,路上好多人都停下来看我们打斗。让我想不到的是,光头一边和我打斗,一边大声指责我手脚不干净,斜眼也立刻会意,说再他妈乱偷人家东西,老子废了你。
我挡开一个脸上长满疙瘩的家伙迎面砸来的一拳说,你们真不要脸,要是我,做贼也做个光明磊落的贼,这样贼喊捉贼把人都羞死了。但是他们哪里能容得我分辩,砸向我的拳头一下比一下重,踹向我的大脚一下比一下狠。我看到围观的人中有几个也凶巴巴地扑向我。成了众矢之的的我很快招架不住,但我嘴里还一遍一遍的申明我不是贼,打人的才是贼。
农贸市场外面的马路已经被不断涌来的人流围了个水泄不通,越来越多的人涌向这里,路过的车子也一辆接一辆停下来,交通被严重堵塞。闻讯赶来的交警急急忙忙地疏散越聚越多的人和车辆,顾不上处理我们这些仍还扭在一块的“骚乱分子”。我感到身上的疼痛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我同时看到无数人向我挥拳。虱子多了不叮,疼多了也就不知道疼了。到了这个地步,我根本不再去躲袭向我的拳脚。打吧,打死我也不会承认我是贼。
我不是贼——我大声喊着。根本没人在乎我在喊什么。
交警终于让交通恢复如常,转而开始专心“研究”我们这些仍在混战的鼻青脸肿的家伙。
你们怎么回事?
他是贼!许多个指头同时指向我,许多张嘴同时表述着一个不是事实的事实。
我不是,他们才是。
好汉难敌四拳,更难敌这么多张嘴巴。光头已经开始绘声绘色地向交警讲述我如何偷盗一个八十岁老太太的钱包,他们又是如何见义勇为挺身而出。
他们瞎说,我不是。我有气无力地申辩着。
谁能证明你们说的是事实?交警显然有些不耐烦了,想要快刀斩乱麻解决这一桩无头案。
我们都能证明。许多个人大义凛然地举起了自己沾满血水的手说。
证明……我嘴里喃喃着,能证明我清白的只有公交上为数不多的乘客,特别是那个长发女孩,可是我到哪里去找他们?就算找到了,他们愿不愿意为我证明清白?
光头他们把谎话越说越圆,不断加进一些新细节,声音也越说越大,仿佛声音越大越占理。我也大声吼着,他们都在说谎他们才是贼。
都不要吵了,搁着安生日子不过,吃饱了撑的!交警各打五十大板,说要是你们觉得气还不顺,找个僻静的地方接着练去。临走又再强调了路的重要性,“路是让人走的,不是吵架的地方,更不是打架的地方,都像你们这样胡闹,那不乱套了嘛,都赶紧回家去。”
那一天,他们并没有遵从交警的嘱咐,让我“回家去”,他们像拖一只拉杆箱一样把我从农贸市场拉到西街一处烂尾楼。这段路,坐车只需十多分钟,他们却扯着我的双手走了整整一下午。我的衣裤被磨得支离破碎,我的身上早都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脊背上的皮肉磨掉一层又一层,我仿佛能听到肌肉不断爆裂的声音。呲——呲——呲。但我一声不吭,我咬牙挺着。巨大的疼痛让我昏了,醒了,醒了再昏,昏了再醒。生不如死。但是对我的折磨还远没有结束,他们又轮番在我头上撒尿,嘴里一直不干不净地骂着。
经过这一番长长的难捱的折磨,我成了农贸市场到西街这段路上的一个响当当的硬汉,成了街头小混混想揍却又不敢随便揍的“打不死”。如果我再次对某件事稍有不满,人们会一反常态马上附和我,西街那些小混混也甘当我的拥趸。
就这样,我也成了一个连自己都瞧不起的混混。
为什么会是这样?在无数个白天和黑夜我这样问自己。我因一点心动为保全一个陌生人的财物差点搭上自己的性命,更要紧的是,我的人生轨迹就此改变。这样做值得吗?那个长发女孩在事发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了,我甚至没有得到她一句带有感谢性质的话。父亲说,现在的人都聪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家早远远的躲开了,谁会像你那么傻,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我傻吗?我不觉得。一个人,能快意表达自己的喜好,做自己想做的事,就是最大的“值得”,受一点皮肉伤又怎么了,丢掉本就不光明的前程又怎么了。我高兴这样。
大概过了两个月,其时我已经威名赫赫,和南街的周大脑袋北街的沙丁鱼东街的小瘪三齐名,并称县城“四大门神”。我应朋友之邀去北门调解了一场非打不可的纠纷,完了喝了点酒,朋友们借着酒兴说要去唱歌。在路上,我竟然再次看到了长发女孩,我迷糊的眼睛突然间清亮了,凌乱的脑子也变得清晰起来。她隔着老远就向我伸出了手,笑吟吟的向我大步走来。然后还没等我回过神,她温热的小手就被我紧紧握在掌心,触电般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原来目光与目光的对接可以生电,手与手的碰撞也能生电。我痴痴地捏着她的手竟忘了松开,她也不急着抽回,还一个劲的叫我大恩人。她说那天真是太感谢了,那天她下了车就急着去给东街一病危亲戚送钱,十万火急,都没顾上说声谢谢。她说她后来听说了我的一些事,知道我为那事受了不少委屈,一直想找机会登门致歉,谁想隔天就被发配到外地出了两个月的长差。这不,刚一回来就碰到了大恩人。
赶巧了。
就这样,我认识了这个叫亚桐的长头发姑娘。我发现她是一个能说会道的活套人,小嘴一张,那些枯燥的事也给她说的馨香无比。有那么一刻,我甚至想变成一个方方棱棱的字,被她轻快地从嘴里吐出来,和她一起感受人世的快乐和苦闷。人海茫茫,相识就是缘,我被我和亚桐这种离奇的相识深深陶醉,我梦想着我们的关系能近一步,再近一步。
亚桐其时在县自来水公司做水表工,主要任务是月末到各单位核查、登记用水量,平常也没多少事做。每周还能轮休两天,闲暇时间她会主动帮同事做这做那,在单位人缘很好。她也喜欢这工作,和这份恬静淡然的心境,平常总是笑呵呵的,就像永远没有烦恼。
认识以后,亚桐见天就从县城东街赶到西街看我。这段路远虽不远,却是县城最繁华的地段,人多,车也很多,因此特别拥挤,走一趟下来简直就像唐僧取经一样。亚桐说她决定减肥,每天走一来回就当锻炼了。我说你不肥,再减就成麻杆了。她揪着我的耳朵问我,那你说麻杆好还是胖大猪好?我却没头没脑的回了一句,你怎样我都喜欢。
有一阵我总是为她的安全担忧,劝她尽量待在单位,非要来,就坐车来。她说好啊,富轻松,你这么快就烦我了,我偏要走着来,天天来!
其实我挺烦我这名字的,每回听到别人叫我名字,我仿佛都能闻到一股古怪的药水味,并且固执地认为这味道是由我散发出来的,因此满心愧疚。亚桐这样叫我,我一样不舒服,可我喜欢我的名字从她嘴里轻轻绷出的感觉,那种古怪的药水味好像被她嘴里淡淡的清香过滤了,没有那么浓烈了。但我还是不喜欢这个名字,我自作主张改了个新名字,富小虎。我决定从亚桐这开始纠正过来,可我说了很多次,亚桐每次都能答应,可到再次叫我的时候,她还是富轻松、富轻松的,就像这三个字已在她舌尖生了根似的。
父亲照常酗酒,我照样隔三岔五地和别人干一架,亚桐还是经常造访我位于县城西街破烂的家,日子还是这么不紧不慢地向前滚动着。亚桐有时来还带着酒菜,殷勤的劝父亲多喝点,这让父亲喜笑颜开。亚桐一来家里,就一刻不停地收拾屋子,甚至把我和父亲的衣服也从那些写旮旯里搜出来洗。父亲睁着蒙胧的醉眼说,儿子,亚桐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闺女,你他娘的给老子好好待承着。就这样,亚桐成了常年醉着的父亲唯一作出肯定鉴定的人,开天辟地的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个。母亲、妹妹和我连她一根脚趾都不如。
在没有旁人的时候,在有机可趁的时候,我总是喜欢抓住亚桐的手,就这么静静地握着,我希望世界所有的干扰都不在了,让我一握就是一辈子,一握就是千年万年。亚桐也不挣脱,好像也很享受这种被握住的感觉,有时她还主动把头靠在我饱经捶打的胸膛上。这样的时刻真是再美妙不过,一股又一股的热流从我身上每一个毛孔涌出来。我的热似乎也感染了亚桐,我看到她也大张着嘴巴,像一条缺氧的鱼,她的鼻尖也涌出许多细密的汗珠。必须承认,我不是个坐怀不乱的真君子,我不止一次的想把亚桐扳倒,让我温热的嘴巴走过她的每一寸肌肤。但我是个无所事事的混混,她是个有体面职业的“工作人”,我干什么都可以,但不能破坏她的美好,不能亵渎她的神圣。不能。我最多是握着她的手,让她的心跳连同体温一起慢慢渗进我手心我的骨血我的澎湃青春,让我亲切的感触她甜丝丝的气息,直至地老天荒。亚桐。
我没有对亚桐说破我的心思,亚桐也没有更多表示。我们像两个握手爱好者,坐到一起就用一只手和对方粘连在一起,说笑,逗乐,倾听彼此嗒嗒嗒的心跳。
我不知道我和亚桐这样算不算恋爱,我想恋爱应该有个正式的仪式,牵手显然不算什么仪式。我承认我对亚桐的欲念不是牵手那么简单,人生的风浪太过频繁,谁也不知道究竟哪片云彩会下雨。如果因我的过失,导致亚桐不快乐,甚至打碎她的幸福,我说什么也不能原谅自己。那么,亚桐,就让我这么牵着你的手,走过这段我们各自孤独的时光。百死而无悔。
我曾问过亚桐,要是我们成天什么都不做,就这样彼此握着对方的手行吗?亚桐噘着小嘴想了想才说,你傻啊,别人都恨不得多生几只手多做点事,你可倒好,倒想着把自己的一只手绑起来——那样什么也做不成你吃啥喝啥啊?还有,要是我不小心摔一交,连累着你也栽一个跟头,我可不干。我说亚桐,其实我们是很好的一对呢。她的脸红了一红说你想得美,我是想不了那么远,我们能不能走到一起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我说难道我们连自己的主也作不了?她说傻瓜,世上的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我恨透了这些酸溜溜的话,我以为人世的很多事就坏在这些话上,行就是行,不行就不行,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是讨厌。多么简单明了,没必要把这些意思揉蔫巴了再曲里拐弯地说出来,或者干脆隐藏起来遮盖起来。比如男女间的事,一上来双方就开始打哑谜,结果在很多时候会错了对方的意,造成终身遗憾,得不偿失。
这一天,亚桐破天荒的叫了我一声小虎,在我一愣神的工夫,她忽然抓过我的一只手,轻轻地抚摩起来。我粗糙的大手在她的抚摩下,也变的柔软了,我用指肚探着她的手心,一遍又一遍,就像那里藏着她所有的秘密。火舌不知疲惫的舔着锅底,流水一刻不停的浸润着土地。我要一点一点抠出来,抠出来。
秘密果然被我抠出了一点点,亚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小虎,其实我们那个破单位,也没你想象的那么好,有些人的人品就很有问题,特别是那些老光棍,见到女的就起腻,就胡说八道,还动手动脚。
我却说,哪里都有好人,也有坏人,谁敢对你动手动脚,我非把他的爪子剁下来喂狗。
亚桐嘻嘻一笑说,我知道你厉害。可是你整天这样打打杀杀,我真地好害怕。求你以后别再和人打架了。说着,她竟攥住了我伸进她手心里的那根手指,使劲拧起来,疼得我嗷嗷大叫,她还是不肯撒手,“我要你答应我——别—再—打—架—了!”
我赶紧点头如捣蒜,好好,我答应你。
我万万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握亚桐的手了,这样的温情时刻今生不会再有。亚桐一连几天都不再露面,一开始我以为是她单位里忙,可能走不开。于是我接着等,可亚桐始终没再出现,我越等越是焦急。我已经离不开她温热的小手了,没有她的手的抚慰,我宁可去死。又是几天后,我终于等来了一个消息,自来水公司的那个常年叼着烟,牙齿被烟熏得金灿灿,满嘴烟臭的煤质化验员老胡,已经先于我,用一双黑糊糊的大手,把我的亚桐霸占了。更要命的是,一个浓缩了的化验员老胡已经甜蜜地钻进亚桐的肚子里了,为了遮丑,老胡和亚桐决定用速婚遮盖丑恶。亚桐最后找我的那次,就是她决定和老胡结婚的那天。我的天就这么被亚桐和老胡轻轻掀开了一个边角,流金满地。
我疯了一样冲到街上,我想尽快找到老胡,一拳打碎他那秃亮的脑壳,再一拳打碎他对亚桐的所有无耻念想。
老胡老胡,就算你是关公,我也要在你面前耍耍大刀;就算你是猫我是老鼠,我也要捋捋你的胡须;就算你是黄鼠狼我是鸡,我也要去给你这个狗杂种拜个年。
我像一股风,从西街刮到东街。我的闪电速度我的凶狠表情,一定吓坏了人们,我看到路人纷纷停下脚步为我让道,来来往往的车也放慢速度,给我留开一条可以自由穿行的通道。只用了抽根烟的工夫,我就跑到自来水公司街口。我生了风的一双大脚顾不上作半点停顿,拐了个弯,又大步连天地跑向那个光棍云集色狼多多的自来水公司。
门卫想要拦住我,却差点被我带起的疾风掀个跟头,只能讪讪的目送我闯进厂区。
经过一路的飞奔,我的脑子也给风吹清醒了些,我是先打碎老胡的那颗狗头还是先剁了他那双胡作非为的爪子?还没等我和老胡干上架,这两个念头先自开战了。打头的念头说,先打头,多坏的主意都是从脑袋里产生的,手不过是受了脑子的驱使,打碎了脑壳,老胡就再也想不出什么坏主意了。剁爪的念头不甘示弱,脑子再坏也得通过爪子使坏,剁了,再没法使坏,那才叫一个难受。
我顺手抄起一根生满铁锈的自来水管,见人打人,见物砸物。十多个保安七八个工人从四面向我扑来。我手里的自来水管挥得呼呼有声,他们一时也无法靠近。
打他下盘!居中一个穿着西装领导模样的人大喊一声。十多根胶皮棍七八只扳手钳子一起朝我下身捅来,我抡着水管护住下盘。却不想,一根胶皮棍狠狠砸在了我背上。我向前扑了一交,手里的武器在瞬间成了他们抽打我的凶器。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们终于打累了,胶皮棍扳手钳子成了多余的东西,在他们手里晃荡来,晃荡去。我像一个杂耍演员被他们围在中间,我看到他们有好些人也挂了彩,还有几个人的胳膊腿也好像被我打出了毛病。我浑身酸软,眼冒金光,周身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眼睛也血乎拉拉看不清楚。我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围着我的人立刻紧张了,手里的胶皮棍扳手钳子马上绷得笔直。
那领导模样的人朝我大喊一声,哪来的这么个瘪三,还无法无天了,这里是你闹事的地方吗?啊?!
我说我不闹事,我找老胡!
老胡请了三个月假,去云南旅行结婚了。
我訇一声软在地上。
我最终给送进了县医院,胳膊腿多处骨折,腰膝脚踝多处软组织损伤。父亲自此不再喝酒了,母亲和妹妹也从腌菜厂搬回家住。一家人围在我的病床前,其乐甚是融融,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是多么叫人蛋疼的一段难捱时光。我在病床上一躺就是三个月,我享受到了从前没有享受过的家庭温暖,也享受了从前没有享受过的那种因相思因痛失而来的切肤之痛。我一遍又一遍回忆我和亚桐交往的全过程,回忆使痛苦加重,也让甜蜜蔓延。无论如何,我都真心希望亚桐幸福,我不想损害她一丝一毫。亚桐给过我无限甜蜜,当然,也给我带来无限痛苦,但留在我心里的甜蜜似乎更多一点。我想明白了从前不明白的许多道理,也坚定了从前飘忽的一些信念。在亚桐这事上,我之所以败给老胡,并不是老胡比我更出色,也不是亚桐对我不用心,归根结底,是我的原因。我本来不是什么斯文人,却在亚桐面前装斯文。我没有给亚桐更多的爱,甚至连一点爱的表示也没有。老胡胜就胜在不伪装,不遮掩,直接“上手”上。但我并不能因此削减对老胡的恨,更不能眼睁睁看着老胡在亚桐面前为所欲为。
我终于能下地走路了,在办理完出院手续准备回家的时候,我看到亚桐从出租车里走下来,她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像是决意要和从前的长发时代告别。长发不在了,但长发时期的习惯还在,她仍要走几步甩一下头。天地间尽是温情的辉光,我坍塌了的天也给严丝合缝的缝上了。我挤出一丝笑,朝她伸出一只手说,新婚快乐!
她也笑呵呵地伸出一只手,轻轻捏了一下我的指尖说,你可要记得对自己好啊,天天快乐!
突然她又俯在我耳边说,对不起,我尽给你惹麻烦。
我哈哈一笑说哪能怨你呢,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是我没有照顾好你。唉,说这些没用,这不都是你说的那个命里有没有的事么。
亚桐从身后的提包里摸出一件鲜亮的T恤说,这是我跑了很多地方专门给你买的,你一定要记得把自己打扮得帅帅的哦。你放心,我和老胡都会把你当朋友,也会经常去看你。丢下这些话,亚桐就像一只翩跹的鸟从我身边飞走了。就在那一瞬,我已经决定不再难为老胡,就全当是为亚桐好。
从医院出来,我看到前面聚了一大群人,吵吵嚷嚷的乱成一片。我凑过去,一眼看到我的小兄弟小宝也在里面,他正扯着一个留着毛寸的青年不依不饶。原来小宝给毛寸的电动车刮了一下,小宝没伤到什么,却喊来几个兄弟索要天价“医疗费”。对方自然不肯,僵持不下。这时候出现了令所有人吃惊的一幕,只见一穿着牛仔毛边短裙的女子上前啪啪甩了小宝几个耳光说,你不是要医疗费吗,先让我打出点问题再给,肯定给!小宝懵了,他带来的兄弟也懵了,但是很快他们就反应过来,纷纷扑向那女子。这时候我喊了一声:小宝,让他们走!他们没走,走的却是小宝几个,围观的人也跟着走了。我看到那女子回头深深的看了我一眼,好像是感激,好像是轻视,又好像什么内容也没有,眼神显得有些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