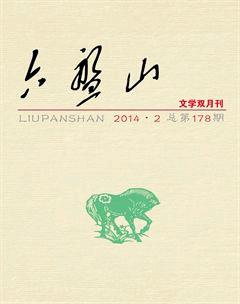远去的母亲
张永生
在生命的历程中,每个人终生难以忘怀的恐怕只有父母的恩情。这根感情的线索自出生起系在心上,直到生命终结的那一时,还要呼唤一声“妈——”确实是这样的,母亲于每个人不只是血肉关系,而是整个生命的涵盖。
母爱深如海。在这个世界上,最牵挂我最疼爱我的人莫过于母亲了。母亲生了几个孩子,却只有我一个男孩,在传统观念的支配下,母亲一生对我的呵护牵挂可想而知。儿时我多病,能够忆起的是我常常伏在母亲单薄的脊背上,由母亲背着从乡下到城里,看完病再从城里回到乡下。我家离城市四里路,母亲背着我路上要歇缓几次,这样母亲仍然是一身汗水。也许我降生在这个人世上就是来折腾母亲的,多病的我常常使母亲提心吊胆,寝食难安。及至我长大成人,我的安危冷暖饥饱病灾,依然使母亲常常牵挂。但坦率地说,母亲对我的呵护没有糊涂到忘记如何教我做人,这使我懂事后从她善良刚直的品行中汲取了做人的品德而不至迷路。
记得十五岁那年,我被生产队派去挖沟,繁重的体力活别说少年的我吃不消,就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若吃不饱肚子,那活干一天也够呛。沟里的稀泥粘在锹上,如没有相当的力气是很难甩上岸去的。我满身糊满泥巴,费尽了力气也没有干完那一天分派的活,用大人们的话说,我是抱着锹在泥沟里摔跤呢。干不完活不能回家,我的堂家三叔干完他的活,过来帮我,才在天黑时挖完了分派的活。三叔人高马大,正值青年,有的是力气,可肚里却无食。别人中午都带干粮,惟独三叔没有,我就把母亲给我带的两个馒头分给三叔一个,三叔便也可以垫垫饥了。回家后我把挖沟的事对母说说了,第二天母亲就在书包里又多装了一个馒头,让我中午和三叔分着吃。那年代家家都缺粮食,有的人家等不到麦子黄就断了粮,三叔家就是这样。因此,三叔忍饥挨饿是常有的事。母亲知道我干的活累,自己嘴里省着,却把吃食给我带足,就这样,在三叔的帮助下,我终于熬下了半个月的苦活。母亲没有盲目溺爱把我从挖沟的工地上弄回家,将我遮护在她的翅膀下安逸无忧,实在是她的聪明。爱有多种形式,让儿女品尝劳作的苦累,经历生活的艰辛,在困难中磨练摔打,长一双坚硬的翅膀,日后遨游人世,这难道不是母亲的深爱吗?
而我,真正理解母亲这种深爱的苦心,已是三十岁以后了。
母亲性格耿直好强,善待他人也乐于助人,周围的邻居如有了难处,只要家里条件允许,母亲都会不计回报伸出手去。母亲时常对我说,谁家都有个难处,人就是在帮帮衬衬中过来的,若能帮时不帮一把,你有了难处咋办?母亲还说,既然帮了就不要想着让人家报答你,帮不帮是你的事,记不记情是人家的事,若总想着让人家日后怎么报答你,这事就寡味了。饿着给一口,强如饱着给一斗。
母亲的善良无疑具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她活着时几乎每晚家里都有来串门子的邻居,三五个人夏天坐在院子里,冬天坐在炕沿上,一只木盒里盛着父亲种下的烟叶,他们抽着呛鼻子的旱烟,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谝着家事农事,坐久了才散去。母亲一生好强,却命运偏偏不济,后来一场一场的病折磨得她骨瘦如柴。但她没有被疾病打倒,病愈后仍然坦然地面对人生,善待他人。那些年我最怕的事就是母亲住院,算来动手术她就做过四次,看着她在病床上倍受疾病的折磨煎熬,有时我忍不住背过身去偷偷地抹掉眼泪。母亲最后一次手术刀口长时间不愈合,每次扶她到治疗室换药我都不敢看她肚子上的那道口子,我躲到一旁去,由姐姐扶着她。护士拿镊子药纱在母亲的刀口里搅动,疼得母亲喊出声来,声声刺进在我的心里。母亲人在病床上,病情一旦好转,心就飞回了家里,为这事那事操心。往往这时候我心里就不由得生气,锐声劝慰她好好治病,别的事不要管。母亲不计较我的态度,叹息一声说她死了就算把心操到头了。我不能再说什么了,母亲也不说了,都沉默着,在沉默中彼此用心灵交流。
母亲病愈后身上有了些力气能够下地走动了,家务活便不再让父亲伸手,由她慢慢去干。母亲说人得动弹着吃,光吃不动弹就成了死人。家里的一份责任田父亲种着,每年到收割时,我都去帮着收割。母亲能干动活时,也拿着镰刀伏在地里挥汗如雨,以后割不动了,还总是惦着在地里干活的我们,顶着毒烈的太阳,提一壶泡好的凉茶蹒跚到地里。我实在是怕母亲经不起折腾,歇息一阵就催她回去。她临走时总要吩咐父亲不要下死力干,让父亲悠着点。母亲和父亲的相濡以沫我是深切地感受到了的,他们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年轻时的事我不得而知,但在晚年,那种丝丝缕缕的相互关爱常常使我感动,也使我明白了什么是情分和责任,让我处处为鉴,时常反省。
有母亲在,我心里就有一个温暖的家,有一处泊靠心灵的港湾。尽管以后我也成了家,有了女儿,不和父母亲一起住,但母亲所在的那个家总是给我坚实的感觉。是的,是一种无可替代的坚实,一种深彻骨髓的坚实,一种能唤起我情感涌动的坚实。有母亲在的日子里,不管我什么时候回家,母亲总关心着我吃了没有。尽管母亲后来精疲力竭,可她对我的那种关心、牵挂、呵护,仍像一束太阳的光芒直射我的心田,使我感受到那温暖的纯净、浩大、无私。
如今,母亲的关爱成了我永久的记忆,有时想起来仍使我泪濡双目。母亲的恩情于我难以尽说,她活着时我从没有细细想过,待她永远地走了,我才倏然发现,在我的面前,出现的是一个令我无法弥补的空旷……
在母亲就要离开人世之际,她已处于昏迷状态,我抓着她的手,她仍用指甲一下下抠着我的手心,把她已经难以表述的牵挂和挚爱毫无保留地传达给我。在那一个夜晚,我攥着母亲的手,躺在她身边,听着她微弱的呼吸,直到天快亮时我一时迷糊过去,而那时母亲就面含微笑悄然地离开我远去了。
母亲活了六十八岁,这样的年纪还算不上高寿。人生过多的磨难和过重的负荷过早地耗尽了她的心血,使她尤如一盏油灯,油干了灯自然要灭。母亲对生死持超然态度,她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时,一再地嘱咐我在她死后不要过于破费,要一切从简。母亲在走到生命的尽头时还在替我分忧着想,怕我把丧事办得隆重花销过大以后日子拮据。对母亲的嘱咐我只能遵照,至于别人如何看我毫不在乎。我以为只是心里有母亲就行了,对母亲的爱和恩情,怎能是一场隆重的丧事就能报答了的?我厌恶那种母亲活着时不管不顾的忤逆之徒,在母亲死后却极力营造出哀荣场面以博得孝子名声的假模假式,那是做给别人看的,这一切与我无关。对母亲的爱除了行为上的表达外,还应该是心灵上的感应,这才是真的。
母亲信佛,等我此后阅读了一些佛经,才明白了母亲咽气后面含微笑的含义。佛把人的意识分为八种,最深层次的意识叫阿赖耶识便通过表情显现,一个人一生的善恶莫不在这一瞬间刻写在脸上,见善相善,见恶相恶。对佛的经典我不敢妄加议论。但就我所知,科学对人的意识的揭示最高层次达到潜意识,也就是第六意识。阿赖耶识——于我们人的世界还是个谜。母亲含着微笑离我远去了,留给我的是魂牵梦萦的怀念,这怀念会直到永远——我生命终结的那一刻。
母亲去世后,我把孤单的父亲接来与我一起生活。在母亲去世十年后,父亲也离我远去了。
安葬了父亲后,我对母亲父亲留下的遗物做了一次彻底的整理,能用的我留下,用不上的都给了姐姐。物尽其用,我没有像别人,老人离世后,那些用过穿过的衣物随之抛之荒野,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在翻捡母亲父亲留下的遗物时,我的一件棉袄也混杂其间。这棉袄是老式的对襟棉袄,母亲一针一线给我缝的,时间大约有十几二十年之久。棉袄我穿过两个冬天,以后就再也没有上过身。棉袄被我闲置是因为后来条件好了,有了毛衣、大衣,也就想不起来穿了。因为生活条件的改善,这棉袄才没有被我穿破抛弃而保存了下来,成了母亲留给我惟一的物件。睹物思情,望着母亲缝下的棉袄,我久久无语。姐姐知道这些年我不穿棉袄,问我棉袄是不是她也拿走。要说,姐姐拿什么我都不会心疼,惟有这件棉袄,我没爽快地给她。棉袄还是新的,只是里子上有些汗油,却仍遮掩不住母亲烙印在上面的手迹深情。我对姐姐说这是母亲给我缝的棉袄,也是留下的一个念想,让她拆洗了缝好拿来,到我老了的时候再穿。我知道以后没人能给我缝出这样的棉袄了,虽然服装会越来越新潮漂亮,但那和母亲的爱无关。我想,假如到了我也要离世的那一天,我就穿着母亲给我缝下的棉袄,即使去了另一个世界,身上也是温暖的。
我珍藏着我的棉袄,也珍藏着母亲对我的深爱,一如母亲那样,坦然地面对我的人生。
如今,我没有了母亲,没有了父亲,但我心中的大地依然存在,温暖依然存在,常常令我举首仰望,忆念追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