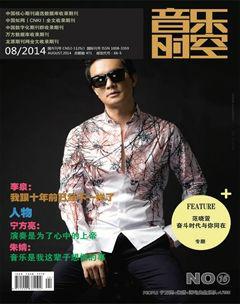论西周时期的民间音乐教育
朱仲毅
摘要:西周时期的官设音乐教育一直是对这一历史时期音乐教育形态研究的重点,然而,西周蓬勃发展的官设音乐教育的教育对象主要为贵族子弟,并非庶民及奴隶所能享有。西周的庶民和奴隶主要接受的是一种以家庭或家族式为主的、长辈对晚辈的民间音乐教育。这是一种在礼乐制度的背景下与官设音乐教育并行发展的、未成系统的音乐教育。同时,官设音乐教育与民间音乐教育有所联系、交融,在官设音乐机构中从事音乐活动的庶民和奴隶便是其体现。
关键词:西周民间 音乐教育 庶民
西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音乐这一艺术形式向国家层面转折的重要时期。礼乐制度的实施,将本服务于鬼神、注重娱乐作用的音乐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强调其与“礼”的结合以及对社会教化的功能性,并与国家的政治政策紧密结合。
随着在礼乐制度下音乐的倍受重视,西周的音乐教育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西周的官设音乐教育机构无论是在教师构成、教师人数还是教学形式上,较之夏商两朝都有着显著的进步,并形成了明文见载的音乐教育系统。于是在西周官方的支持下,西周的官设音乐教育服务于西周的礼乐制度,为西周宗法政权的需求播撒着礼乐教育。
然而,仔细斟酌便可发现,看似如此丰硕的西周官设音乐教育系统,面向的教育对象却十分有限,并非是想象之中的“全民性”音乐教育;与此同时,在西周的民间,伴随着民间音乐活动、民俗文化活动的开展,应当同样有着稀于见载的、未成体系的民间音乐教育在西周的官设音乐教育之下自成一脉地运行。
一、西周的官设音乐教育概述
西周政权在土地国有制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了较为完整且严格的宗法制度。在宗法制背景之下,强调等级观念的礼乐制度的实行便为西周血亲统治提供了强力支持[1]。
服务于礼乐制度的西周官设音乐教育系统主要由“国学”、“乡学”两部分组成,且音乐教官与《周礼》中的乐官在职责之上有所重合,以“官师不分”为其主要特征。
西周音乐机构中的乐官之长“大司乐”,既统掌着西周礼乐机构,同时又是西周音乐教育的执掌者。《周礼·春官宗伯》中记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而大司乐以下各级乐官,宗伯所辖的钟师、磬师、笙师、镈师等,既是周代礼乐的承载者,也当是西周官设音乐教育的教育者。故而,西周的官设音乐教育以音乐机构中的乐官为教育者,以礼乐教育为教育内容;同时其礼乐教育则又是西周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存在于西周作“国学”、“乡学”之分的教育系统中。
西周的国学是西周官设音乐教育的核心,依入学年龄不同又有“小学”与“大学”之分。《礼记·王制》中记载:“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结合后世文献记载及学人所作注可知,小学的学龄当在10-15岁之间,而其设学地点,当在王宫附近。继小学之后学子进入大学。《礼记·王制》中记载:“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可知大学规模较大,天子与诸侯所设大学在名称上有所不同。
国学所指为王都之内的学校,而乡学则是设于王都郊外行政区中的学校,同样以行政区级别划分等级。《礼记·学记》中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然而,乡学并非如想象中级级管理、由地方官府自办的,应当是作为地方性质的教育机构从属于国学的。
二、西周的民间音乐教育
(一)“官乐不下庶人”的辨析
西周的官设音乐教育建制庞大,从中央到地方覆盖广泛。然而对于西周的庶民、奴隶是否有机会参与西周的官设音乐教育,西周的官设音乐教育究竟是不是“全民性”的音乐教育,仍然需要结合文献正确辨析。
上文已知,西周的音乐教育机构分为“国学”与“乡学”。如《周礼·春官宗伯》之记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国学的教育对象为“国之子弟”,正如《周礼》郑玄所注:“国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可见这里的“国之子弟”不外乎王公贵族的子嗣,当与庶民无关。故而,西周的官设音乐教育在国学中的针对对象应当是贵族子弟,与庶民无关。
王都的国学音乐教育中无庶民,而西周乡学中生源情况可从当时国学、乡学的礼乐教育内容以及西周宗法制政策推知一二。《礼记·王制》中记载:“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即乡学之中的佼佼者是可以移于国学进行学习的,可见乡学的考察标准与学习内容应当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学有所一致。国学所学为“乐德”、“乐语”、“乐舞”,而乡学所学除《周礼·地官司徒》所载的“六艺”、“六德”、“六行”外,应当亦有“乐德”、“乐语”、“乐舞”的学习;如“乐舞”等教习内容通常都用于国之祭祀、典礼或地方性礼乐场合,并非庶民所能接触得到,同时也不适合庶民学习。由此可见,乡学之中即使有庶民学于其中,也必然是极少数,享受西周乡学音乐教育的主要还是居于王都之郊以外的中、小贵族的子嗣。
(二)西周民间的音乐教育
西周的官设音乐教育无论在国学还是在乡学中都基本不见庶民,而多为贵胄子弟,以宗法血缘为先,“官之子,则就其父学,习其业”。迄今所留存的古籍资料中所载的皆是西周官设音乐教育的相关资料,对于西周时期的民间音乐活动、音乐教育的记载少之又少,这自然与这些史料作者皆处于贵族阶层有很大的关系。西周时期惟官有书,而民无书,这便导致了西周时期的民间音乐活动及音乐教育状况稀于见载,只能从现存史籍的字里行间中零星拾贝。
从现存史籍来看,西周时期的民间必然是存在着音乐教育活动的。这种音乐教育活动并不明文见于记载,但事实上,只要在西周的民间存在着音乐活动及音乐行为的流传,便定然会涉及音乐的传承,即音乐形式、内容和技能的代代相传,这本身便预示着一种未成系统的音乐教育行为的存在。
关于西周民间音乐活动的状况,可从文献中有所解读。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宣公十五年》中记载:“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汉书·食货志》也载:“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上古时期,音乐除了作为一种以娱乐为目的的艺术活动存在以外,在民间还被广大民众用以抒发释放内心情感,“饥者歌”、“劳者歌”等音乐现象的存在实质上便是民间社会生活以音乐这一艺术形式的直观体现。这些现象也成为了一部分民间音乐产生的最初源头。endprint
此外,西周时期民间音乐活动的存在,从文献中“采风”制度的记载也可推知。《汉书·艺文志》云:“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此处的“采诗”即为“采风”,统治者认为,“采风”制度的存在有利于反映民间舆论,看重其来自民间的政治讽谏功能,有利于王者能“不窥墉户而知天下”。“采风”所采为“民间之诗”,实质便是类似民歌的民间诗乐。现存《诗经》为三百零五篇,但依《史记·孔子世家》所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即使《诗》三千中并非皆属“国风”题材的民间音乐,却同样可见周代民间音乐发展之繁盛。
周的民间同样是有着民间礼俗、祭祀等活动存在的,无论是民俗活动还是祭祀天地神灵、地方社神、家家户户的先祖先妣,甚至是“非其所祭而祭之”的淫祀,都是西周民间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西周社会礼乐制度的影响下,用乐也成为了这些民间文化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如《白虎通·礼乐篇》记载:“郑国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错杂,为郑声以相悦怿。”这里所载的是郑国自古流传的“祓禊”活动,即在每年的三月初三,男女临水洗手洗澡,以洗去不洁,拔除不样,其中所用音乐便为北方民间音乐的代表之一“郑声”。可见,在这些民间文化活动中自然衍生出一套对音乐的使用体系,其中所用音乐大多数源于民间,与官学所授之乐有着较明显的差别。
如此内容丰富的民间音乐活动存在于西周民间,其音乐教育的方式也极大地区别于贵族专享的官设音乐教育。在西周民间,庶民的子女几乎没有接收官学正规教育的机会,同样,西周时期的社会环境以及社会制度也不会允许民间有“非官学”的明文学堂存在。故而家族式的、家庭中的乡风民俗教育便成为了庶民所受教育的全部;而出于对民间文化活动的需要和社会音乐活动的需求,在这些以非正规方式进行的家庭式教育内容之中,必然有着民间音乐之传承,有着音乐教育活动的存在。所以,根据上述内容,应当能得出关于西周民间音乐教育形式的部分信息:西周的民间音乐教育主要在家族、家庭中以长辈教授晚辈的形式留存,且与民间音乐文化活动关系密切;在音乐教育实践上与民间音乐文化活动具有重合性,音乐教育内容以民间音乐文化活动的所用音乐为主;西周的民间音乐教育是一种与官设音乐教育并行存在、却未成系统的非正规音乐教育。
(三)西周官设音乐教育与民间音乐教育的联系及交融
项阳先生曾针对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提出“接通”的理念,“官方与民间的接通”便是其理念的九个组成部分之一。透过这样的理念,我们在意识到西周之音乐教育有着官设音乐教育与民间音乐教育两分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二者之间所具有的必然联系,认识到二者并不是相互割裂、划清界限的。无论是官设音乐教育还是民间音乐教育,都是在国家推行礼乐制度的宏观背景之下运行的,都不可避免地需要适应礼乐制度下所提倡的社会性规范。官设音乐教育从设立初衷而言便是为国家之礼乐制度服务的,其教学内容自然离不开礼乐的范畴;而礼乐制度作为周王室、奴隶主贵族进行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必然会要求西周社会中的庶民、奴隶在言行等方面符合社会规范,因此在以家庭、家族音乐教育为主的西周民间音乐教育之中,必然会有社会主流的礼乐元素的加入。
民间音乐活动也与官学之中的音乐活动有所交流,并不单单体现在“采风”制度将民间音乐带入宫廷上,还体现在一些庶民、奴隶在官设礼乐机构之中从事着音乐相关的工作。根据《周礼》中的记载,在“春官”系统中的音乐官职1600余人之中,管理人员与乐师仅占186人,其余都是庶民或奴隶。这些在官设音乐机构中生存的庶民与奴隶,拥有着服务于国家礼乐制度的音乐技能,但所接受的是有别于官学中的音乐教育。他们承袭着“就其父业”的命运,接受着来自音乐机构内部的、来自他们家庭或是前辈的特殊音乐教育。这样一个存在于“官方”与“民间”交融点上的群体,在其本身来自于民间的同时,又从事着与官方音乐机构相关的工作;在联系了民间音乐活动与官学之中音乐活动的同时,也为贵族音乐教育活动与民间音乐教育活动之间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互通。
根据上述内容,我们可以对西周音乐教育的“官”与“民”关系有正确地理解:西周的民间音乐教育与官设音乐教育,都是存留于西周礼乐制度之下的音乐教育形态,二者在王公贵族与庶民、奴隶两个迥然不同的阶级之中并行发展,在拥有着不同音乐教育形式结构的同时,相互间又尤有一定的交融与联系。
继西周之后的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所谓“礼崩乐坏”冲击的西周官学体制逐渐废弛,其形虽犹在,却“学校庠序废坠无闻”,不复西周“官守学业”之旧景了。在官学衰落、文化下移的同时,私学产生;而私学之中音乐教育的内容,便包容了西周时期呈两分的音乐教育的各方面元素,有西周民间音乐教育的内容,亦有西周官学音乐教育内容。于是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西周所立等级制度的桎梏逐渐减弱,在西周时期于不同阶级之中并行发展的官设音乐教育和民间音乐教育最终有所相融,并体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之中。
三、结语
西周的民间音乐教育有别于官设音乐教育,是一种未成系统的、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长辈对晚辈的传承性音乐教育。而透过“接通”的理念来看,西周的官设音乐教育与民间音乐教育又有着相当的交流和互通,其中为西周音乐机构中服务的庶民和奴隶这一特殊群体,便是西周音乐教育“官”与“民”交融的象征。
有关西周的民间音乐教育往往在研究中容易被忽略,也一直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但随着对西周官设音乐教育研究的愈发深入,便愈会发现民众作为社会构成的根基、作为最为庞大复杂的群体,他们的音乐教育活动对于我们从整体把握历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使得关于西周民间音乐教育的研究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基金项目:
本文为江苏师范大学2013年研究生校级创新项目,项目编号:2013YYB037。
参考文献:
[1]吴小强.略论西周宗法制度特征[J].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04).
[2]项阳.接通的意义——传统·田野·历史[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01).
[3]黄绍箕.中国教育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5.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