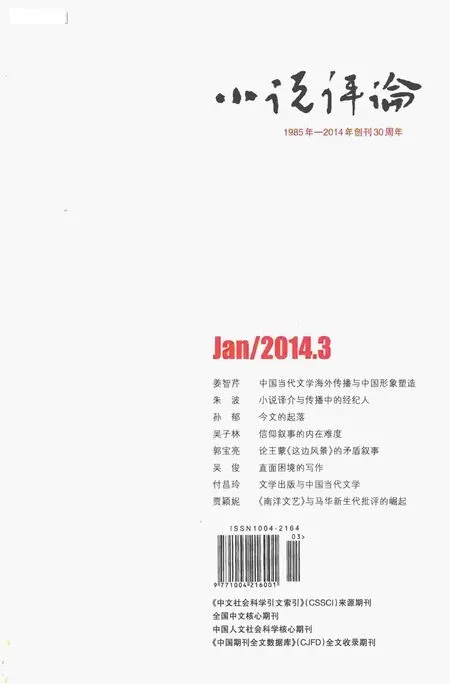双重文化视野下边疆乡土生活的深刻记述——再读王蒙写新疆“在伊犁”系列小说
何莲芳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王蒙向文坛集束式地抛出了写新疆的系列短中篇小说——“在伊犁”,这些小说以浓郁的边疆特色和对极左年代乡村社会人事的独特表达引起了文坛侧目,近三十年过去,我们仍然可以将这批次小说称之为艺术的奇葩。但除《葡萄的精灵》获第一届1983-1984短篇小说百花奖外,其他作品却始终没有象王蒙的其他作品那样得到当时及此后主流社会的高度评价。有意味的是,从这些“在伊犁”作品发表之初评论者提出:王蒙这些写新疆的作品“都深深打上了维吾尔文化及新疆文化的影响……漠视或忽略了新疆生活的影响及那里的文化因素对一个通晓维吾尔语的作家心态的改造,那将是一个难以原谅的闪失”、“他的幽默总是荡漾着浓郁的新疆色彩及维吾尔族民族特性”,直至今天,研究界往往从新疆经历对于王蒙的世界观、文艺观和创作的影响、王蒙的跨文化写作、王蒙创作中对新疆少数民族人物形象的塑造、王蒙小说的新疆民俗美、王蒙与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王蒙创作对新疆的贡献等方面研究王蒙《在伊犁》系列小说,但从双重文化视野下对边城伊犁乡土生活的叙述动源以及由此产生的叙述特色这一角度进行研究的很少。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探讨这一批次小说创作的独有价值。
一、以双重文化视野、以“此时”心态对伊犁乡土社会“彼时”极左年代的亲情友情爱情、日常生活、民情风俗纪实性叙事
王蒙从一个参与共和国建立的少共,一位才华横溢、声名鹊起的年轻作家,到因言获罪的漏网右派,从北京、团市委、乌鲁木齐的新疆文联,再到具有塞北江南之称的边城伊犁毛拉玗孜公社巴彦岱村,经历了从权力中心的青年干部到边地底层农民的全方位的“乡土化”过程。这个过程是从中心到边缘,从中原汉儒文化向收伊斯兰教影响的新疆少数民族文化融入、学习、观察、思考的过程。王蒙从语言、生活、工作开始了主动自觉地自我适应与历练,完成了一个“客居者”和“闯入者”向伊犁人的根本转变,成为“他们”中的“我们”。对此,王蒙说“这块在我孤独的时候给我以温暖,迷茫的时候给我以依靠,苦恼的时候给我以希望,急躁的时候给我以慰安,并且给我新的经验、新的乐趣、新的知识、新的更加朴素与更加健康与观念的土地”。王蒙强调了“伊犁经历”这种独特的异质性的“新”体验给予个人生命涅槃的重要意义,这是王蒙不同于所有流寓作家的最特别之处。
对于伊犁,王蒙说:“从北京到这里非常遥远,时差近三个小时,而越是遥远越是祖国辽阔广大的证明。这里十分平凡,这里永远低调(根本不需刻意保持),这里就是那个需要脚踏的所谓‘实地’。桅灯在这里又称马灯,因为它不是用在桅杆上面而是多用在马厩里,这里除了百姓还是百姓……这里不在意也无来由去过问权利、荣誉、财富与地位,这里文字的东西很少很少。这里人们关心的核心就是生存,就是今天和明天,就是余华小说的主题‘活着’,这里人们围绕着生存而生活而不是围绕着某种理念。这种平凡这种日常这种亘古如一的日子有一种顽强,有一种力量和无法抹杀的存在的坚实性。有一种自在自足自保的力量:夫唯不争,故莫能与之争,为天下谷,以言下之,以身后之。活着的力量正是天下最顽强最不变的力量。而且,这个美丽的绿洲,这里的生活被浩瀚无垠的戈壁滩、沙漠与荒山和人迹稀少的原始森林所包围,后者更有一种大自然本身的威严与宽广,后者更像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后者给你无情的参照:永恒、寂灭、不忍、空无、包容与安息。后者在无言中似乎告诉给你许多许多。这段自述很能表现出王蒙对于边城伊犁乡土,在时空、文化经历参照后的体验:遥远的绿洲、底层世界、生存至上,恒定与守一的生活状态。
属于新疆无数块绿洲的伊犁一样具有绿洲文化的特点。“萨满式文明是维吾尔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绿洲文化的一大特点……只要我们对维吾尔绿洲文化的结构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它既具有塔里木土著化的特点,即地区性特征,又包含北方草原文化、绿洲耕牧文化以及丝路商业文化的多重特点。绿洲文化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歌舞乐三位一体性……绿洲文化第四个显著特点就是绿洲的伊斯兰化……绿洲文化的第五个特点,它属于混合型文化……考察绿洲伊犁的特点,就是典型的绿洲耕牧文化。而王蒙所记述的就是伊犁乡村他兰契人的彼时——极左时代乡村的生活。
“在伊犁”系列小说是在王蒙复出至1981年重返巴彦岱后,时隔近20年,远离第二故乡伊犁之后远在北京创作完成的。在谈到新疆、伊犁时作者说“新疆的生活,伊犁的生活,是我的宝贵财富……我不会放过我的独一无二的创作本钱”,若将“在伊犁”系列小说与王蒙复出前期的创作(《向春辉》、《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相比,可以看出作者创作的裕容状态。这不仅是社会政治化写作、更是作者对于伊犁边地异质化的生活、生命的涅槃之地以深刻的生命体验、文化审视,以汉儒主流文化与边地文化融合的方式,穿行于两种文化间、双重文化视野下,对受伊斯兰教影响的,具有绿洲文化特点的边地乡土文化状态中人的生死、友谊、爱情、美与善的记述,对乡村维吾尔族人的酿酒饮酒、施礼待客、宰牲庆节、庭院布置、生死禁忌、年节习俗(封斋、宴饮、婚礼)、农田劳作——打畊灌水、扬场割麦、盖房上梁,人伦秩序—隔代收养,长幼称谓等等都做了深入其里的纪实性叙述。“在伊犁”系列小说的叙述的边地性、异质文化统摄下的人性,民族文化心理成为叙事的主要对象。它既不溢美,也不讳丑,因而形成了“在伊犁”系列小说文化小说、纪实小说的特质,而这一点,长期以来恰恰没有被关注、被评论,形成了对之的“集体失语”状态。
总起来说,“在伊犁”系列小说对民情风俗、人性、文化纪实叙述内容有:
(一)快乐原则:追求世俗之乐,严峻政治问题的“塔玛霞尔”化
《古兰经》中这样阐述:真主以你们的家为你们的安居之所,以牲畜的皮革,为你们的房屋,你们在启程之日和注定之日,都感觉其轻便。他以绵羊毛、骆驼毛和山羊毛供你们织造家具和暂时的享受(16:80)这突出显示出伊斯兰教的世俗化倾向。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1、新疆少数民族穆斯林群众对粮食珍惜与尊崇。“维吾尔人认为馕——粮食是世界上最高贵的东西。维吾尔人是穆斯林,穆斯林是崇拜《古兰经》、视《古兰经》为神圣的,但是,馕比《古兰经》还神圣。如果馕放在高处……那么为了取下馕来,可以把《古兰经》踩在脚下”阿依穆罕大妈用铁锨填埋洒地的牛奶,对“我”能吃得一粒馕渣都不剩感到满意(《虚掩的土屋小院》);因为妻子艳羡,不知名的邻居,小个子的维吾尔老太太每次打馕时都馈赠我们一个油亮的、喷香的小圆馕,房东茨薇特罕请我参加乃孜尔享用的色、香、味俱佳的抓饭,盛放抓饭的精美绝伦的清官窑出品的盘子,饭后人们庄严的祈祷(《逍遥游》);待客食品多,数量大、礼仪繁复庄重:“王民”去马尔克木匠吃夜宴一共享受了“甜食、肉饼、奶茶、抓饭、酒菜、面片汤”可谓吃得成龙配套,一丝不苟(《淡灰色的眼珠》);维吾尔族乡村农人对待实物的尊崇和珍惜不仅反映了在极左时代底层生活的困窘,还特别反映出绿洲文化中的生存原则和伊斯兰教对饮食文化的影响。在《最后的“陶”》中,传统哈萨克将脱了脂的牛奶排到山涧,认为“如果连雪白的牛奶和雪白的牛奶制成的食品还要卖钱,那就是对于雪白的牛奶的最大污染”。这是对天然食品的尊重,反对食用加工产品的饮食观念,更是伊斯兰教自然和谐理念的具体表现。
2、乐善好施,仪式庄重的待客习俗:“在伊犁”系列小说中对处于单一生活方式、封闭环境中的维吾尔、哈萨克族人待客的习俗有较多表现,这就是倾其所有、热情待客,仪式庄重,好酒美食与朋友共享。默哈默德.阿麦德即使在贫苦的日子里,也倾其所有,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招待吃“大半斤”,他将饭碗递给我时,平摊双手,脸色极为恭敬、在孝敬了父母、照顾了妹妹后,还招待过路的行人,而自己仅吃了几根面条(《啊默哈默德.阿麦德》);曹千里到遥远的牧业队统计数字,路过“独一松”,饥疲交加,向哈萨克帐篷里的老妈妈乞食,老人家因无食可吃招呼曹千里睡一觉,又拿出最后的马奶子酒招待他,没有一丝犹豫;(《杂色》);鹰谷深处的哈萨克青年妇女将刚打的孢子肉送给萍水相逢的伐木者(《鹰谷》),爱弥拉姑娘因哥哥家待客的茶薄而羞愧,以和养母补请我们喝奶皮厚的茶而心安的礼性(《爱弥拉姑娘的爱情》),马尔克木匠为答谢我而准备的隆重的酒、茶、点心和饭……落后封闭的乡村民性醇厚单纯、世故而世俗,“在伊犁”系列小说反映了伊犁乡村鲜明典型的前现代人情社会的特点。
3、对故园和亲人的珍惜、看重。“在伊斯兰教看来,联系血亲的必要性在于亲戚远离自己后,要主动联系。这就是穆圣所说的:‘联系者绝不是报仇者是那种断绝了血亲时,便去联系起来者’”因此,穆敏老爹在经历曲折找到失去多年联系的弟弟后,同村的人对他举行了盛大的上路乃孜尔(《虚掩的土屋小院》);哈萨克老妈妈为儿子死亡举办庄严肃穆、盛大平静的送葬活动和四十天对亡人超度的隆重的乃孜尔。这和古兰经提倡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有关,如古兰经宣告“除因复仇和平乱以外,凡枉杀一人者如杀众人”
《爱弥拉姑娘的爱情》上半部写爱弥拉姑娘与养母的血浓于水的亲情和美好的生活,下半部写爱情的甜蜜与痛苦、友情的醇厚与质朴,理想的爱情与世俗的婚姻的矛盾,作品将爱弥拉姑娘对待亲情、友情 、爱情的理想主义态度同伊犁乡村世俗社会的现实人生、安逸平庸的生活态度,世故凉薄的社会氛围联系在一起,将人物命运同社会文化联系在一起,写出了文化制约下的人的命运和心理。
4、爱情婚姻观念的宽容务实、入世理性。伊斯兰教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对妇女的保护性措施和对婚姻的入世、包容、理性的态度。首先表现为为了生存,在婚姻中淡化贞操观念,追求生活的安稳和实际。如穆敏老爹与阿依特罕的结合,两人相敬如宾的生活(《虚掩的土屋小院》);马尔克木匠与有婚史、且年长的阿丽娅的婚姻与爱情,家境殷实,有数次婚姻的老裁缝阿卜杜拉赫曼与独臂姑娘艾丽曼的结合(淡灰色的眼珠);凯里碧努尔姑娘对于制帽匠的选择(《心的光》;高中生玛依努尔与乡村文书雅阔甫的结合(《啊,默哈默德·阿麦德》)等,都是基于一种世俗、宽容、务实、理性的婚姻观。
5、一切源于真主的创世观、以自我、“此在”为中心的时空观。边疆乡土社会的中的农民由于生产生活的单一单纯封闭自足,加之受伊斯兰教影响,使他们的创世观与时空观都表现出强烈的宗教性和乡土性。《古兰经》这样认为:“真主是万物的创造者,他确是独一的,确是万能的”(13:16)、“他使你们为大地的代治者”(35:39)。当老王的朋友送来收音机,收音机的特殊功能引发了老爹的兴趣。他认为:收音机这种万物真主早就在《可兰经》中写清楚了,“圣人们在修《可兰经》的时候也写下了如何制造万物的书,这些书有的藏入了山洞,有的沉入了海底,人们陆陆续续地发现了这些书,便造出了万物,难道不是这样吗?老王”当“我”说出发达国家法美英俄和著名科学家的事实,老爹很是尴尬和慌乱,显然“我”的世界观与他的基于《古兰经》的世界观是完全冲突的。而阿依特罕的时空观更为有趣“法国,法国比南疆远吧?还是我们中国好,我们中国的科学技术越来越进步了,我们比欧罗巴好!也比苏联赫鲁晓夫好!再有就是斯大林好!当然,毛主席最伟大,最好!”对1969年美国人成功登月事件,穆敏老爹说:“《可兰经》上说的,月亮距地球的距离,骑上一匹快马,走四十年也走不完”,这里的时空观是狭隘愚昧的,创世观也是荒唐可笑的。它与封闭自足的生活和伊斯兰教的影响密切有关,显示了真主崇拜、万物归一的民族文化心理。
6、对待严峻政治生活敷衍、淡然、随性、“塔玛霞尔”式的人生态度
在《鹰谷》中,“我”喜爱的一首奥迈尔·阿亚穆的“柔巴依”是这样的:“无事须寻欢,有生莫断肠,遣怀书与酒,何问寿与殇?”这是作者在人生困境中以名人名言自我解脱、自我救治的快乐原则,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少数民族的人生观。我们注意到,王蒙“在伊犁”系列小说,确乎表现了伊犁乡村极左年代的社会生活并表现了对之“笑”的解构。这种“笑”的解构,既有人们对极左年代的荒唐、荒谬做法的本能反抗,也反映出特定民族文化和社会心理特征:生活的“塔玛霞尔”化。
《买买提处长轶事——维吾尔人的黑色幽默》分明以买买提与赛买提兄弟俩十年遭际,不同的精神状态写出了“维吾尔人的黑色幽默”。显然,这是“以黑色幽默”的命名刻意表现维吾尔人特有精神状态的文化小说。无论是买买提处长对文革期间对新式婚礼与传统婚礼采取的自我戏谑,自我交代;是添油加醋、弄假成真,终于成为“人民所承认的作家”;还是面对繁重的干校劳动改造,苦中作乐,以丑为美的自我调节;抑或是睡觉不关门的“魔鬼”理论下的自我调侃和放逐,以及因个人牛鬼蛇神的身份而给亲人带来的福利的自我欣慰等,我们都可以看出了维吾尔族文化中特有的塔玛霞尔精神:即以游戏、娱乐态度化解、超越苦难、面向生活。“塔玛霞尔却是天趣无迹,塔玛霞尔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怡乐心情和生活态度,一种游戏精神……维吾尔族人有一句相当极端的说法‘人生在世,除了死之外,其他的都是塔玛霞尔’”将荒谬戏谑,将苦难娱乐化,游戏化以实现精神解脱,这既是作者对十年极左专制时代的批判,也显见出维吾尔文化的特质,是王蒙对异于中原汉儒文化的维吾尔族文化的发现与思考,是作为新疆生活十六年“新的经验、新的乐趣、新的知识、新的更加朴素与更加健康与观念”的审美表达。
如对割“资本主义尾巴”禁令,马尔克木匠疏通与“我”的关系,以摇床换小麦、换药品;公社搞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组织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全村统一的“红挎包”行动,大家的认真庄重与敷衍,推荐马尔克木匠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时,大队干部移花接木材料的荒唐滑稽,大队组织民兵批判电影《冰山上的来客》,认真敷衍汇报,巧妙骗取信任观赏电影的聪明机智与狡黠机变,批判邓拓时大队贫协主席卡利把万岁——亚夏松和打倒——约卡松喊颠倒了,没人抓现行,大家认为“大会开过了,邓拓、吴晗、廖沫沙打倒了,“文化大革命”也就大功告成了”对于特大丰收的1966年因为大搞革命运动社员收入大大低于1965年的实际,上级却要违背现实、弄虚作假、要求年终分配不能少于1965的荒唐做法,大队干部的巧妙滑稽应对,穆敏老爹的“相对论”解释等等。这种“塔玛霞尔”既有对生活苦难的乐观态度,也有对极左年代荒诞政治的巧妙解构和戏弄,更有底层偏僻之地百姓追逐潮流的机巧与懵懂,还有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留下的时代印记。王蒙对具有乡土文化特点的民族文化特质有了最集中和最真实的表现。
(二)对艺术与美的热爱与追求——生活的艺术化和艺术生活化。新疆绿洲文化的特点之一是歌舞乐三一体。在新疆少数民族人们的生活中,这样的特点表现得非常突出。《歌神》作者写出了极左时代歌唱家艾克兰穆因唱歌带来的曲折爱情、坎坷人生以及对歌唱矢志不渝的爱,“歌”是与生命、爱情血肉相连、须臾不可分离的灵魂。作品写出了一个拥有“歌”的灵魂的民族的喜怒哀乐,表现出歌神与生命同在的对“歌”的追寻,其中交织着对美的摧残与破坏的极左势力的抨击。
“在伊犁”系列小说中,作品叙述了人们在孩子出生、婚礼、丧葬、喜庆、娱乐的场合都喜欢用歌舞的方式表达情感。如《歌神》中弟弟的孩子“摇床喜”仪式上的歌声,《心的光》中狄丽碧努尔载歌载舞的婚礼,《逍遥游》中,我的邻居哈萨克老太太儿子葬礼上的赞唤,《边城华彩》中民兵队长艾尔肯聚集各方人物的“神仙会”上的歌唱,《临街的窗》夜归的流浪汉那缠绵多情的《黑黑的眼睛》的吟唱……默哈默德·阿麦德在艰苦的岁月里也没忘记读经典,对美好的事物充满向往(《啊,默哈默德·阿麦德》)、马尔克木匠开满玫瑰花的庭院、精致的家居摆设、甚至家庭半月形贴画像法、(《淡灰色的眼珠》)茨薇特罕精致的盛抓饭的器皿,(《逍遥游》)每家喝茶的大肚子瓷壶,我们都可以看出边疆少数民族热爱生活、美化生活,将凡俗的生活艺术化与艺术的生活化的特点。
王蒙确乎是以了解、爱护维吾尔人的作家身份,写出了边地乡土社会维吾尔人的心灵和文化形态。他们一方面质朴善良、单纯醇厚、因循保守、封闭自足,世故现实、浪漫朴野,对极左政治持“塔玛霞尔”态度,另一方面热烈追求世俗生活之乐、之美和艺术之美。王蒙的叙述绝不仅止于对极“左”年代错误思潮进行社会批判,也不仅是对边疆人民人情和人性美的歌颂,而是“即使在那不幸的年代,我们的边陲、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各族人民竟蕴含着那样多的善良,正义感、智慧,才干和勇气,每个人心里竟燃着那样炽烈的火焰,那些普通人竟是那样可爱、可敬、可亲,有时候复可惊、可笑、可叹!”这正如新疆作家谈到王蒙小说时的深层感喟:“王蒙对维吾尔族是从心底里热爱和尊重的,他把笔下的人看作父老乡亲,才会怀着真挚的爱和深切的同情,去写他们种种不幸和性格的扭曲,这同时也是对文革不正常环境的控诉”。
二、叙事身份、叙事视角、叙事语言和叙事文体:
与叙述动源和叙述重点相关的是“在伊犁”系列小说叙事者的文化身份和叙事视角的独特性。即叙事者的“王民”视角与“我”的情节功能。“王民”是作为一个伊犁乡土文化的观察者、发现者、审视者以及作品中的角色参与文本意义生成的。叙事者具有“彼在”、“此在”的双重身份和叙事时空感,是“彼在”、“此在”的“我”看“他们”,又叙述“彼时”在“他们”中的“我”的生活。陈柏中先生指出:“作品中的“我”即‘王民’,既是小说的叙事者,又是小说的贯穿人物,是那一段难忘经历的当事人,作为叙事者的王蒙自然是以一个汉族作家今天的文化视角去回忆、思索、比照逝去了的生活,采取的自然也是汉语思维和表达方式;但作为当事者的‘王民’去描述活跃在特定环境中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时却转换成维吾尔语的方式,逼真地、传神地写出了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背后的民族性格和心态、灵魂的搏动与忧思,理解事物与表情达意的方式”显然,这个“王民”很大程度上就是王蒙自己。叙事者汉文化身份的间离感、与“我”的角色融入感的复合性,形成了文本的“第三度文化空间”。
王蒙曾这样自述:“在这几篇小说的写作里我着意追求的是一种非小说的纪实感,我有意避免的是那种职业的文学技巧,为此我不怕付出代价,故意不用过去我在写作中最为得意乃至不无炫耀的使用过的那些手段”。这表明了“在伊犁”系列小说纪实性的主观追求。这种纪实性也带来了小说鲜明的散文化特征。即将风俗民情、日常生活记叙同人物形象塑造融合在一起,写风俗即写人,人即风俗和文化。这符合王蒙追求的一种文学创作境界:“真实朴素,使读者觉得如此可靠”。“在伊犁”系列小说这种散文化的纪实性的文体特点,我们还可以将王蒙同期或稍后写作的“伊犁”系列散文对照,发现其有明显的互文性。但它又是小说,我们可以在叙述间隙中经常出现的叙事时间的后发性可以看出,作者是追忆,是对“彼时”伊犁生活“此时”、“此在”的呈示,叙事者 “看”与“演”相映成趣。
《好汉子伊斯麻尔》开篇时使用全知叙事,意在抛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素描。接着以“我”与伊斯麻尔的交往开始采取王民眼中伊斯麻尔的限制性叙事。当“我”与伊斯麻尔配合铡草时,小说写道“我请求他不要叫我先生,然后告诉他,铡草是我在北京门头沟的山区农村下放时学的”,突出了“我”的下放身份与地域间隔。我到伊斯麻尔家做客,作品以呈现的方式展览了伊斯麻尔家庭新疆回族的家居文化的性质。“他的房子一溜四间,建筑在高台上,廊檐宽大。他的房屋陈设在汉维之间。方桌、木椅、茶壶、掸瓶以及墙上挂的‘月份牌’画是汉族式的,壁毯、挑花窗帘、覆盖着挑花白布的挂衣架,洗手用的铜盆以及铺满整个炕的羊毛花毡是维吾尔式的……”在文本内部,作者用预叙的方式说“多年后的今天,我甚至设想如果联合国某个成员国的首席代表回答不怀好意的记者的追问的时候给他这么一个字,那该多精彩!怪不得原始人要把这个东西当做图腾来拜膜了。”,叙事时间从过去进行跳跃到现在、当下,既强化了叙事效果也凸显了叙事的间离感。小说内部记叙伊犁农村他兰契人对田间疏懒、散漫的管理方式时进行叙事时间跳跃,“直到今天,据悉这个习惯也没有改变,而且在使役大畜的时候,就连挂于耳朵上垂在胸前的口罩——做样子的笼嘴,也不见了”叙述时间从“彼时”跳跃到“此时”,强化了叙述的间离感,表达了“看”的立场。在伊斯麻尔因过度使用权利,超额借款引起众怒下台时,作品这样叙述:“他好像一个演员,上台演戏时有声有色,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等散了戏、卸了妆,收起了行头,便心平气和,心安理得的穿上最普通的衣服,融化在普通人群里去了”这是叙事者当然也是“我”的评价。再看小说结尾处作者对叙事时间的强调“八一年重回伊犁的这个公社的这个队以后,人们告诉我,伊斯马尔已经死了两年了”这样的今昔、生死对比、时空跨越突出了人物的戏剧性,对“好汉子”形象既形成了强化也形成了解构。作品用间接“直接引语”的方式介绍伊斯麻尔的死因后,这样写道“对我讲这个话的人本人也是回族,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一定符合现实,反正我写下这一句话,只包含着盼望新疆各族同胞生活的更加幸福的友好情谊。而且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回、汉……各族人民对我的好处,他们身上值得我学习的长处,我是永生不忘的。”再一次突出了叙事者异质于叙述对象但又是叙事对象的双重身份。
通观“在伊犁”系列小说,叙事者身份多重性、叙事文体纪实兼虚构的混成性,叙事语言的杂拌性,叙事时间“彼时”与“此时”的切换、融合与间离都带来了王蒙该类小说社会文化的叙述品质。作者是以极左年代为创作背景,结合作者个人的人生经历、体验,以一个异质于新疆边地农村的观察审视者的叙事视角和被叙述对象的双重视角、以对受伊斯兰教影响的少数民族底层农民乡土生活的叙事者和生活参与者的双重身份,写出了具有浓郁新疆边地气息的乡村人物志、民俗风情和迥异于中原汉民族文化西域少数民族文化特质,将文化学习、观察体悟与审视同对极左时代的批判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小说文体、语体、视角的混成性、杂交性和叙述时间的跳跃性,也形成了王蒙小说的先锋性和创造性。
这是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的互动与互适,“对于汉族作家主体而言,跨文化的体验应该是他们去往异域最深刻的体验,他们是处在汉儒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人,而他们的文学作品表现了异于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本土文化的第三空间文化,或者可以说是杂交文化”。
王蒙的“在伊犁”系列小说确乎是以双重视野、双重文化立场创造出的第三个文化空间。16年尤其是在巴彦岱与底层维吾尔族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强烈生命体验,将再造生命的异质性文化、乡土文化以及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父老乡亲的人性、生产生活、民族文化心理以纪实性的小说的方式叙述,这既带来其叙事方式的独异(此时先锋文学还未在中国登场),也带来其小说文体的特异,“在伊犁”系列小说是对极左时代受宗教影响下的乡土生活的卓越叙事,王蒙凭此获得了维吾尔族不同社会阶层的尊重和认可,评论家买买提·普拉提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第二个汉族作家能象王蒙这样热爱和理解维吾尔族,通晓我们的语言,理解我们的文化,能把我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内心世界表现得这样真切、细致深刻”。王蒙的“在伊犁”系列小说可称为跨文化、双语写作的典范、新时期文学的奇葩,历久而弥新。
注释:
①周政保。关于“杂色”的杂谈[J]。当代作家评论1987.2
②周政保《在伊犁》:王蒙的幽默与思情[J]。小说评论1985、4
③⑤夏冠洲。用笔思索的作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④陈柏中。王蒙的跨文化写作[J]。伊犁河,2010.10
⑥夏冠洲。王蒙小说中的民俗美[J]。西域研究,1991.4
⑦刘金涛。王蒙与新疆少数民族文化[D]。华东师范大学2000。
⑧夏冠洲。王蒙对于新疆文学的意义[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⑨王蒙。重返巴彦岱[J]。王蒙《虚掩的土屋小院》【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5
⑩[22]王蒙。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M】p256、p280,花城出版社,2005.6
⑪茆永福。维吾尔民间文学视野里的沙漠绿洲文化——新疆沙漠绿洲文化论之一[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5.4
⑫王蒙。大块文章[J]p50。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⑬⑱马坚译《古兰经》[M]。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
⑭⑮⑲⑳[21][23][26][27][28][29][30][31][32][33][34]王蒙。王蒙新疆小说散文选【M】p356、p168、p288、p289、p298、p252、p518、p238、p239、p238、p242、p246、p266、p267、p238、p211,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3.1
⑯⑰王新生。古兰经与伊斯兰文化【M】pp260、p261,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8
[24][36]楼友勤。维吾尔友人谈王蒙【J】虚掩的土屋小院【M】p324、p321,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5
[25]陈柏中。王蒙与维吾尔语[J]。虚掩的土屋小院【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5
[35]张雪艳。中国当代汉族作家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D】陕西师范大学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