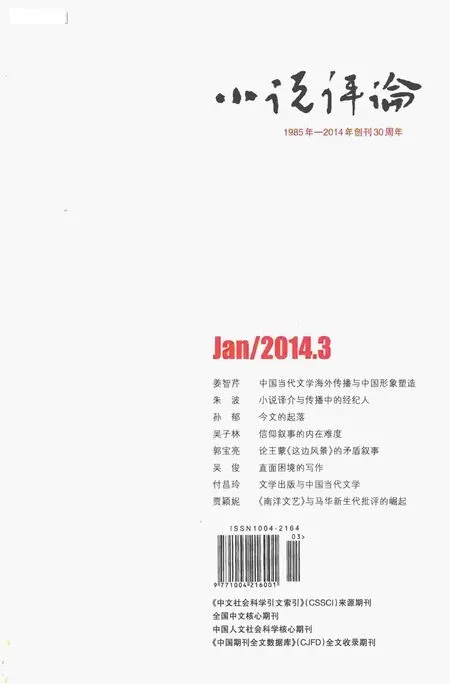化用人间佛教的智慧——评余一鸣的“佛旨中篇三部曲”
贺绍俊
余一鸣在2010年和2011年相继发表了《不二》《入流》《放下》三个中篇小说,这几篇小说所写的生活都是乡村在走向城市化进程中所遭遇到的生活,写的是在乡村走向城市的路途上出现的新人。《不二》是写一群建筑工程队包工头的故事,他们属于来自乡村的“城里人”。《入流》是写长江上的采沙和运沙,农民将此视为通向富裕的捷径。而《放下》则是写在利益驱动下生产的无限扩张将给农村自然生态带来可怕的灾难。余一鸣在这几篇小说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叙述能力,小说的故事性一下子就能抓住读者,而作者丰富独特的生活资源则给这几篇小说带来了新鲜感。当然小说吸引读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余一鸣在这几篇小说中都着力于“恶”,“恶”对于小说来说,就像是一条充满着诱惑力的蛇,尽管人人对蛇怀有一种恐惧感甚至厌恶感,但又禁不住蛇的挑逗。难道余一鸣也是在利用恶的诱惑力吗?从小说的叙述尺度和叙述姿态来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恶”,不过是余一鸣对于现实的一种发现。我以为,余一鸣是一位对现实生活非常敏感的作家,他写的是“新人”,而且这类“新人”与“恶”相伴相生。事实上,与“恶”相伴相生的“新人”也是近些年来一些小说重点表现的对象,不可否认,这些小说不仅抓住了现实之“新”,而且具有一定的批判性。但这类小说很容易滑向揭露小说,甚至蜕化成单纯对“恶”的展览。余一鸣这三篇小说并不是这样,就在于作者面对现实社会的“恶”,有着自己的思考,他决不是要用小说来直接呈现“恶”,因此他将他的这三篇小说命名为“佛旨中篇三部曲”。佛旨,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命题,作者是怎么在他的小说中体现“佛旨”的呢?我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
余一鸣的“佛旨”首先体现在小说的标题上,这三篇小说都是选用了一个佛教用语作为标题的。“不二”来源于佛教中的不二法门,在佛教中,对事物认识的规范,称之为法;修有得道的圣人都是从这里证悟的。佛教有八万四千法门,不二法门是最高境界。入得此门,便进入了佛教的圣境,可以直见圣道,也就是达到了超越生死的涅槃境界。从佛教哲学观来看,“不二”即是“非此非彼又即此即彼”、“众生平等”、“自他平等”、“心佛平等”等,是佛教认知世界万事万物的方法与观念,演绎阐述的是世间万物本质与表象的关系。“入流”如今成了一个日常的俗语,把合乎潮流的行为通称为“入流”,但在佛教中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用语。入流是梵文须陀洹的旧译,佛教小乘分为四果,须陀洹是四果的第一果,所以入流就有初入圣人之流的意思。但佛教又认为,世界一切皆空,所有的法都不存在,自然也就没有流可入,这才是入流的本意。吕纯阳祖师是这样解释“入流”的:“如明镜之显像为之‘入’,其像不留镜中为之‘流’。则菩萨无住之心境,似明镜之不留一切像,故曰‘入流’”。“放下”在佛教中同样是一个充满禅意的用语,佛陀让婆罗门放下,婆罗门放下了手中的一切,但佛陀还在说放下,婆罗门茫然不解,问道,我已经两手空空,还要我放下什么?佛陀说:“你虽然放下了花瓶,但是你内心并没有彻底的放下执著。只有当你放下对自我感观思虑的执著、放下对外在享受的执著,你才能够从生死的轮回之中解脱出来。”
细读小说,余一鸣并没有把这些佛教内涵直接在小说叙述中呈现出来,甚至我想如果读者完全被小说的故事性所吸引的话,都不会去深究小说标题与故事有着什么样的内在关系的。事实上,余一鸣的小说并不是要宣讲佛教的思想和教义。但佛教用语的标题却与小说的故事构成了一种相反相成的效应。佛教是劝善的,而余一鸣的小说则是在呈现生活中的恶的。余一鸣在叙述“恶”的时候,内心里却有一个“善”在呻吟着。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社会拼命发展物质的时候,也养肥了人的欲望,这个社会几乎变成了一个靠“恶”来支撑的欲望世界。余一鸣以非常真实也令人们非常陌生的细节,揭示了恶在当下是如何变得冠冕堂皇的。但他并不满足于将真相揭示给人们看,因为他发现,那些被恶所左右着的,以及在恶行中获取利益的人物,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屈从于“恶”,他们的内心仍然有一个伦理道德的纠结。作者在客观描述现实中的恶时,也在为这些人物担忧,担忧他们的人性被恶完全吞噬。比如《不二》,写了几个进城的乡下人经过一番打拼,终于成功了,成为了包工头,也能在城里享受生活了。但他们并不能成为真正的城里人,因为在他们的内心还有一块乡土的地盘,更因为城市并没有诚心地接纳他们,就像主人公东牛说的:“乡里人把我当城里人,有钱有势。城里人把我当暴发户,吃了你的,拿了你的,转过脸骂你是个土包子。”无论如何,这些进城的乡下人可以说是成功人士,小说一开始展现了这些成功人士在城里的如鱼得水的一面。随着故事的展开,人们就发现,这些成功人士的内心纠结。东牛在这群人里似乎是最懂得收敛的一个人,他小心地循着城市的规则,一步步把自己的事业做大,孙霞的到来,也打开了他封闭起来的爱情,但最终他为了获得资金,不得不让孙霞作为“武器”去对付银行的行长。东牛曾以为他既可以在城里把事业做大,也可以在城里实现他的爱情。但最终他的愿望破灭了——假如读者读到这里再去读一下小说的标题:不二,也许就会明白作者暗寓的深意:难道东牛将自己的爱人去祭奠他的资金的“菩萨”,就是他的“不二法门”吗?《入流》自然写的是在江河上跑运输的船民该如何遵照水上的规矩才能“入流”当上船老大。小说中的那位水上王国的霸主白脸说得很明白:“我开始的时候每次办了事也得难受几天,过了这个坎,把心硬得让它结了茧,你就能在长江里呼风唤雨,人鬼敬畏,这才算真正入流。”所谓办事,就是敢于黑着良心杀人,杀一儆百,这意味着,在这个相当隐蔽的水上王国,你要想“入流”,就要把道德良心、法律法规、善恶标准等所有东西都弃之脑后。佛教所讲的“入流”其实是非常发人深思的,一方面佛教认为圣人的境界分为好几级,入流只是进入了圣人的最初一级,在入流的上面还有更高的级别,但不管怎么说,入流就算进入了圣人的境界。然而你且别急着为你已经入流了而兴奋,因为佛教认为世间万物一切皆空,又哪有什么境界存在,更遑论境界还要分出级别,从而体现出佛法的平等精神。余一鸣所叙述的水上王国并不是一个佛法笼罩的世界,此“入流”非彼“入流”,水上王国的“入流”是以恶为法则的,正如老大拴钱所概括的那样:“人善,鬼比人恶,人恶,鬼见了人躲。这长江里,心中无牵无挂无畏无惧才能做老大。”余一鸣发现,水上王国的“入流”虽然靠的是残酷和丑恶,然而“入流”的同时也许自己就被残酷和丑恶“入流”了。小说《放下》同样还是直面当代社会的“恶”,小说主人公谢无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物,他凭着自己的聪明左右逢源,他的聪明就在于对社会的“恶”了如指掌,知道怎么应付“恶”,知道怎么在“恶”的环境下获取最大的收获。他不仅聪明,而且热心,有一腔侠义正气。他的学生刘和尚如果没有老师的帮助就不可能从一个当地的混混逐渐成为了当地一家公司的大老板。刚刚从牢狱里出来的刘和尚来到老师这儿寻求出路,谢无名要他改邪归正,在农贸市场摆一个摊,还为他筹措了摆摊的第一批货。但谢无名带着刘和尚筹集第一批货的方式却是“恶”。他用草绳沾上羊肉羊血,偷偷放进别人养螃蟹的池塘里,螃蟹顺着腥味的草绳都爬进了谢无名家的厨房。谢无名虽然以这种“恶”的方式获得了摆摊的货物,但他也告诫刘和尚:“人贪腥,蟹也贪腥,贪腥就有被抓的一天。”刘和尚根本不会把老师的告诫放在心里的,不过对于谢无名来说,这才是他心中始终也不能放下的忧虑。这里就说到作者以“放下”为标题的用意了。放下本为佛家之语,也即是舍,说的是人的贪念、欲望若是不能舍弃和放下,便进不到佛家那种聪慧九天的境界。谢无名看到疯狂地发展经济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的后果,他不顾人们的反对,采取各种方式揭露养殖刺蛄的危害,千方百计阻挠县里的刺蛄节。但人们无不劝阻他“放下”,显然此“放下”非佛教中的彼“放下”。殊不知谢无名的内心早已“放下”,他“放下”了世俗的欲望和贪念。
余一鸣的佛旨三部曲都是揭露当代社会的恶相的,但他并没有把小说写成纯粹的揭露小说或黑幕小说,这与他的“佛旨”有关。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古代小说的传统。佛教对古代的世情小说影响很大,这些世情小说大量写到世俗社会的恶行与恶人,但它通过佛教来处理这些恶行与恶人,从而达到“劝惩教化”的作用。因果报应则是这类小说的基本主题。另外像佛教的人生如梦、一切皆空等思想也是世情小说进行惩恶教化的思想武器。这其实反应了佛教与中国社会的特定关系,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逐渐与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思想意识相融合,从而赢得了广大的受众,但它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从纯宗教信仰的高度跌落到世俗化的层面,因此,佛教在中国社会基本不体现为一种宗教信仰,而是一种世俗化的工具,人们进入寺庙是为了追求现实的幸福,祈望菩萨保佑自己的人间愿望能够实现,说到底,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恶行恶人”同样也与欲望有关,所不同的是这种欲望不会得到菩萨的保佑,这也是惩恶教化的核心所在。尽管惩恶教化曾经非常流行,但实际上很少有人会相信小说这样做能够达到惩恶教化的目的的,一个最简单的例证就是,谁也不会因为这类小说具有惩恶教化的作用就鼓励关在监狱里的犯人来读这类小说的。我宁愿相信,所谓惩恶教化,不过是写这类小说的作家为自己的写作找到的一个道德上的免罪理由。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阅读这类小说,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小说中对于“恶”的淋漓尽致的展现,而作者的惩恶教化的企图却显得苍白无力。有意思的是,惩恶教化成为了一种小说公式,至今还在被作家们运用到写作之中,比方充斥图书市场的所谓官场小说,大多走的都是这种路子。最初读到余一鸣的小说,我还担心他也会落入惩恶教化的俗套里,但读完他的“佛旨三部曲”,发现他完全采用了一种新的路子,所谓“佛旨”,并不是以佛教原理和佛教教义来诅咒现实之“恶”,而是要借用佛教的智慧去认识人生的复杂性。余一鸣的这种路子也许才是真正吻合了佛教与世俗的关系。
佛教与世俗的关系在当今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现在有一个“人间佛教”的提法,并认为这是适应时代变化的新型佛教。它针对现实社会中人类越来越严重的毁灭自己的行为,把拯救社会和拯救人类作为自己的目标;它“立足于人生,趣向于佛陀”,提倡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人间佛教强调了人间性、大众性和世俗性。。以往人们把佛教看作是求来世的宗教,解决的是死后升入天堂的问题,而人间佛教则是为了帮助人们摆脱现实的痛苦与烦恼,为了拯救社会和人类自己的生存。余一鸣的“佛旨”就包含着人间佛教对社会问题的诠释。也许在人间佛教看来,东牛的“不二法门”就必然摆脱不了将自己心爱的人去祭奠资金的结局。所谓“不二法门”,就是针对世俗的对立观的,世俗的对立观认为不是生就是死,不是善就是恶,不是入世就是出世。“不二法门”则强调生死不二,世间出世间不二,所以获得涅槃的极乐境界并不要脱离人世间。对于进入城市打拼的乡下人东牛、秋生、当归等人来说,城市就是他们的“不二法门”,他们不得不经历城市之恶的磨练,否则他们也到达不了他们理想的境地。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否在城市之恶的磨练中获得“涅槃”,余一鸣在小说中并没有给予我们一个明晰的答案,或许余一鸣将在另一篇小说中来解答这个更重要的问题。《入流》写到水上王国的“入流”无疑是非常残酷的,拴钱最终似乎是“入流”了,但他的“入流”是以亲手谋害了自己的弟弟为代价的,单纯从这条线索看,结局是很消极悲观的。但我们不要忽略了小说中的另一条线索:白脸的儿子小白脸。白脸是水上王国的霸主,他的残忍和冷酷与他的一副文弱书生的外表形成巨大的反差,但白脸的内心也有柔软的一面,这就是他对儿子的爱,儿子是他的命根子,他希望儿子有出息,所以儿子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贵族学校上学,后来儿子又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然而儿子放假时上游艇来玩,目睹了父亲的所作所为,便与父亲闹翻了。儿子小白脸认为自己所花的每一分钱都带着血腥,他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耻辱,从此他书也不读了,到大山里去做一名志愿者,给山里的孩子当老师,以此为自己的父亲赎罪。耐人寻味的是,小白脸不仅是大山里的老师,而且还是一名水上的绑客,他袭击水上的船只,抢劫船上的钱财,这一点不正是继承了他父亲的衣钵了吗?但他这样做的目的跟父亲完全不一样,他是要为山里的孩子解决一些物质之虞。他称自己的做法是“以罪赎罪”。小白脸未尝不是一种“入流”,他所遵循的恰是水上王国的“恶”的法则,而小白脸的“入流”又在消解他父亲的“入流”,因此可以说他的“入流”是“以恶制恶”的“入流”。儿子的反叛可以说是对白脸最大的打击。在当今社会,像白脸这样的完全痴迷于“恶”、完全依赖“恶”而生存的人来说,根本不会在乎佛教的“地狱”恐嚇,但是他们还有一个精神寄托,就是子孙的绵延。中国传统文化说到底就是家族文化,传宗接代是最大的精神寄托,断子绝孙则是最大的精神恐惧。在这里,仿佛余一鸣最终回到了轮回报应的主题,不过是将其与当代社会结合为一体的方式。在《放下》里,余一鸣将世俗的“放下”与佛教的“放下”并置在一起,完全改变了佛教“放下”的虚幻成分,却激活了“放下”的辩证思维。佛教的“放下”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意义,而世俗的“放下”完全是形而下的指称。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在世俗层面有那么多的东西不能“放下”,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形而上的东西没有“放下”。谢无名这个人物形象充满了辩证法。谢无名应该是一名觉悟者,他觉悟到人类的危机,而这种危机的根源就是人的欲望永远也无法满足。谢无名一方面是一名觉悟者,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名赎罪者,因为他认为现实生态的破坏与他直接相关,他曾放纵了自己的欲望,并参与了破坏生态的恶行,所以他说:“我感到罪孽深重,要尽我一己之力抗争,否则,躺进棺材也闭不上眼。”谢无名其实是告诉人们,一个真正有境界的人,就不会“放下”对世俗的关注。也就是说,只有对形而下的不“放下”,最终才能达到形而上的“放下”境界。
谢无名是《放下》的主人公,也是余一鸣的“佛旨中篇三部曲”中唯一的一个可以称得上是正面形象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是“佛旨”的终结点,这也许是余一鸣以佛旨面对现实之恶的自然而然的结果。“恶”,根源于人的欲望,我们其实没有必要轻易加以否定,因为轻易的否定并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在现实中,恶有时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当然这种动力是很危险的,如果不加以控制,必然会导致恶果。余一鸣在他的“佛旨中篇三部曲”中客观真实地表现了现实社会中的“新人”乃至“好人”与“恶”的纠缠复杂的关系,但他希望人们与“恶”的关系只是一段过程,并尽快走出这段过程。谢无名同样没有摆脱“恶”的纠缠,但他最终“放下”了。余一鸣在三部曲的结尾让谢无名召唤一切还被“恶”所纠缠的人们:放下吧,放下了才有未来。
从“佛旨”来要求的话,我以为余一鸣的小说还有所欠缺,因为“佛旨”在他的构思中还不是那么的明晰,“佛旨”与小说形象贴合得不是那么紧密,如果他能对人间佛教的内涵做更深一步的了解,也许有助于小说的完善。但无论如何,“佛旨”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构思,余一鸣写完了他的“佛旨中篇三部曲”,是否从此就“放下”了呢?我希望他没有“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