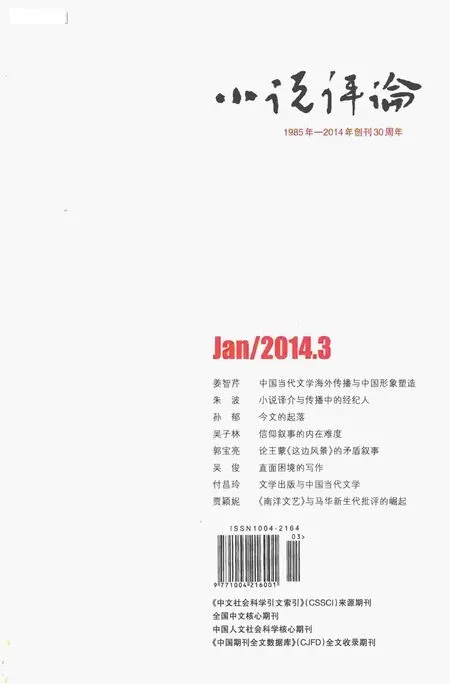对话:文学与现实
何同彬 余一鸣
何同彬:从1984年在《雨花》发表处女作《茅儿墩的后生和妹子们》,到2010年前后经由多篇引起广泛反响的中短篇小说(如《不二》、《入流》、《放下》、《淹没》、《风生水起》、《剪不断,理还乱》等)被文坛瞩目,这近30年的时间里你虽然没有远离小说和文坛,比如编辑过《高淳文学》,出版过两部小说集(《流水无情》、《什么都别说》)、写过电影剧本和长篇小说,但毕竟只是一个喧闹文事的边缘过客,甚至据说曾经沮丧到怀疑自己是否是当作家的料,因此你2010年前后的这种小说创作上的奇异迸发就显得很值得思考和玩味。让我感兴趣的是,这漫长的几十年给予了你何种独特的经验和体悟,迫使或诱导你在小说式微的年代如堂吉诃德一般挥起“社会问题小说”的长矛,直面巨大而邪恶的时代风车?
余一鸣:我常常说自己是文学票友,做编辑的朋友说,你别装萌,现在在编辑眼中哪里还分作家是业余还是专业,只看作者是不是一线的,作品是不是一流。文学界的师长说,你这是示弱,为自己写不出好东西推托。仔细一想,是这个理。只是没人能想得到,做一个专业作家曾是我的梦想。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是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一名学生,学校请当时的《雨花》主编叶至诚先生为我们做了一次讲座,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最后几句话是鼓励我们投稿。我应该是记住了这一句,趴在宿舍的书桌上鼓捣了几个晚上,写了一篇七千多字的小说《茅儿墩的后生和妹子们》,查了地址寄走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写小说,写过了就忘了,我当时年纪小,主要精力是放在调皮捣蛋上,总觉得写小说这样庄严的事应该是文学社那帮酸男女干的事,写一篇是为了证明我也能玩两下而已。没想到《雨花》居然录用了,编辑写信来要求我署名用手写体,好像当时《收获》就是这样弄的,于是就写了几个自己的姓名,挑了一张寄去。好像写的是横的,发出来却是竖排,丑得像爬虾。二十多年后,我终于在《收获》发小说了,这回特意横竖各写了一个姓名,还是丑,这才明白根本的问题是自己这字写得臭。这是后话。横竖是那回发表小说了,稿费没到手,先请班上的男生们出去吃了一顿。
那是个文学年代,发表一篇小说是很风光的事。糟糕的是自此我自己也认为我应该就是做作家的料。毕业分配,我分回县教育局,父母都是教师,想找人把我留在县城,我说,不必了,在哪里教书都一样,你儿子不至于一辈子守着这点地盘。我被分到一个乡下中学,开学一个礼拜了,我还一个人在黄山上转悠,我是穿着一双拖鞋上的山,爬天都峰、莲花顶都趿拉着一双拖鞋,校长找我父母,以为我不想上班了,我去报到,校长很意外,那时大学生稀罕,还是把我收留了。这个乡村中学很偏僻,最让我头痛的是一周有四五天停电,我常常是点着煤油灯看书,我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在三年之内把哲学系和历史系的课程自学完,那是我比较勤奋的年代,尤其喜欢上了西方哲学,捧着一本本大部头专著硬啃,睡觉前不洗脸,洗鼻孔,鼻孔里全是煤油烟。当然也写小说,写了一个长篇《黑鱼湖》,十六万字,三稿,那时都是手写,寄出去了,泥牛入海,这才开始怀疑自己,你究竟是不是做作家的那块料?
让我深受打击的是西方文学思潮对中国文坛的秋风扫落叶,躲在乡村中学的角落里,硬着头皮啃马尔克斯、博尔赫斯,那真叫痛苦,读不懂,反复读,刚读了这个人,又来了那个人,书店里这类书籍滚滚如潮,你刚学到一点皮毛,用到小说里,人家说这玩艺儿不玩了,现在流行另一流派了,城头变幻大王旗。我相信,这次文学西化潮流斩断了无数乡村文学青年对小说的最后一丝情缕,指望靠小说改变命运的农村青年被抽走了梯子,绝望身退。我觉得,我是做不成既拿工资又拿稿费的专业作家了。
我还没绝望,写得少,几乎每篇小说都摆脱不了潮流文学的影响。我对朋友说,流行总有过时的一天,所有的潮流赶完了,小说还会回到传统手法上来,只是那时我们老了。这话说得像一个被丈夫冷落的弃妇,让他去玩吧,玩遍了各种女人,尽兴了,他终归是要回家的。够悲凉的。
若干年后,有一回与毕飞宇喝茶,飞宇说想看看我的小说,那时飞宇已在文坛光芒四射,在他面前我羞于拿小说说话了,反正是朋友,我兴致勃勃地拿了篇所谓的先锋小说给他,他读完了说,赶紧回头,小说已经回归现实了。你只要写出你的生活,写出当下的生活,就比学先锋派好看。这话拯救了我,这二十多年,我从乡村进入县城再进省城,涉及多个商业领域,做过船运经理和包工头等,目睹的人、经历的事仅作酒后谈资确实有点可惜了,写,写出来。
反正不在乎作家梦了,我随心所欲目无纲常地写了几个,还真有人喜欢看。
现在想想,那一次交谈飞宇校正了我的小说方向,功莫大焉!
何同彬:看来毕飞宇对你的影响很大,尤其是你后来坚持采用这种形式严整、质地坚硬的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也和他所说的“小说已经回归现实”的判断有关。但书写现实的方式很多,或者按照加洛蒂的看法,现实主义是“无边的”,没有明确的边界,比如你自己很喜欢的卡佛的“简约主义”;更何况先锋书写一直敌视传统的现实主义书写方式,比如布勒东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把小说“诋毁”为重叠形象的劣等体裁,罗伯-格里耶也认为现实主义是“庸俗的处方”,构成的只是“谎言”。因此我想你最终在小说创作中坚持浓墨重彩、密度极大的写实策略,不仅是毕飞宇几句话的启发,应该也有基于自身经验的独特思考吧?因为这一“陈旧”的选择毕竟还是冒着某种程度的美学风险的。
余一鸣:这个问题可能要从我和诗歌的关系谈起。相比于小说,诗歌总是走在潮流的前面。成家后,我调进县城一所中学任教。县城有一帮文学青年,全是写诗的,领头的是叶辉和海波,成立了诗社,办一本油印刊物《路轨》,当时曾以“日常主义”诗派参加深圳诗歌大展。他们读的都是西方现代文学,海聊时满口洋名字,我无法对话。这使我很自卑,相比较他们,我是科班出身,但读的书却跟不上潮流,为了能不丢面子,强迫自己读了一些现代派经典。那时候,进南京城主要是逛书店。
喜欢简约派,是很早以前,那时国内没有出这几位作家的集子,只能在杂志上搜寻。卡佛的短篇干净,文字之外有光流彩溢,一直爱它们到成了大路货的今天。但是,我认为这种简约它只适合短篇,不适合中长篇。我这几年,主要写中篇,篇幅较长,喜用浓墨重彩。从题材来讲,我写的领域都有独特性,不用力写不透。从人物而言,性格多变,人格多重,鋪张长于简约。最主要的是,生活的磨砺使我习惯用粗犷而风风火火的语言才有表现力。打个比方吧,同样是实木家具,清式雕琢繁重,明式简约写意。二十多年前刚有点钱时,我就买了一套仿明式,虚荣,觉得有面子,房子不大也适合。后来搬家时,发现房子大了,装修复杂了,尽管对旧家具有眷恋,但只有换一套仿清式才搭。换了后发现,繁重也有大美。
做好汉首先得找到适合自己的武器,能用多样武器的人好汉就做得长久一些。写小说亦如此。
都说现实生活比小说情节精彩,这只是外在。我涉历校园之外的商海,起初最受不了的是侮辱,你不得不朝手握权力的官员低头,文人的清高被剥夺殆尽。商人间的算计,是比较智商情商的高下,毕竟有些趣味。尽管一再告诫自己,要遵守规则,让你低头的是权位而不是人,但后来拔腿而去,与这一点还是很有关联。人性之卑污,亲情之淡簿,让人透不过气,也让我畏惧。我有一位老兄,身家数亿,事业正旺,却收山了,告诉我再不收山,夫妻两边的亲戚都没了,老了没人走动了。我写家乡题材的几个中短篇,让我在本地做父母官的朋友也不开心,他们希望我正面歌颂一下政绩,我说应该去找报告文学作家。其实人性与地域关联不大,揭露正是为了挽救,愤怒是因为抱有希望。
我自以为可以冷眼看世界,坐在电脑前其实做不到。相比较纷繁世象,讲究和唯美真的是一种轻慢和调戏。
何同彬:“轻慢和调戏”,很精确,但也似乎让你的写作陷入了与现实生活的某种悖谬关系之中。从你的言谈中,更是从你的书写中,我能看出你对世俗生活以及复杂人性的深度把握,这种基于日常经验和冷静观察得到的小说的“肉感”或“现实感”是很多作家难以企及的。比如让我尤其惊讶的是你对于很多行业、职业(比如建筑、银行、投资、内河航运、教育等等)及其相关人士的那种全景式、立体式的描绘和呈现的能力,以及在西美尔所说的现代社会的语法形式——金钱——面前,各个阶层漫溢的欲望引发的盘根错节、险象环生的人性纠葛,你也都可以驾轻就熟、举重若轻地予以细微地体察和细腻地表达,但这些现实主义书写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按照你所讲的,“揭露正是为了挽救,愤怒是因为抱有希望”,同时你又认为对于纷繁的世相而言,讲究和唯美的文学表达只是一种“轻慢和调戏”,你是如何面对这种悖谬,同时说服自己继续坚持这种“揭露”式的写作呢?毕竟如你自己的经历,文学或文人的清高可能换来的只是屈辱,或者换句话提问,你曾经说“文学能抚慰我的灵魂”,在这一抚慰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来自现实的巨大障碍和困惑呢?
余一鸣:我喜欢过唯美的小说,比如废名和沈从文,我深入过作品,发表过研究文章,也写过模仿他们语言的小说。但是审美观也是与时俱进的。放到今天,我怀疑这些前辈的小说有可能难以发表,读者会极端小众。小说的形式千变万化,读者的胃口酸甜苦辣,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这就是作家“掐麻筋”的能力,乡村的剃头匠有一招功夫,能一下子掐中胳膊肘子关节处的筋络,酸,痛,麻,然后是爽,小徒弟往往不灵。师傅说,功夫在于积累和捉摸。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写作首先要有生活,其次要有切口,切中肯綮。将现实中的美好展现释放,有人喜欢。将现实的丑恶集中暴露,也有人喜欢。作家写作撇开这些为妙,没必要专事迎合。将现实生活的本质呈现,将社会转型的关键弯道捉摸在笔下,针砭时弊,有酸有痛有麻,掐中掐狠是作家功夫所在,并非为”掐”而掐,为揭露而揭露。
文学有疗伤的功能,但在娱乐至死的当下,可以说读者已懒得疼痛了,我写小说,在自己是渲泄和倾诉,虽然也希冀回音。有人动辄称“儒商”,我常常觉得荒谬,商人有商人的文明,儒家有儒家的文化,当下社会这两者都非常稀缺,扯来只是作幌子,商场唯金钱独尊。我所期望的抚慰,是在文学梦中遥望它们,有钱尚不足,有文化有文明人才有尊严。
何同彬:王彬彬教授曾经敏锐地发现“离开农村、进城拼杀的‘农民’”,特别能激发你的“审美兴奋”,比如《淹没》、《不二》、《入流》(后扩展为《江入大荒流》)、《潮起潮落》、《愤怒的小鸟》等大量作品当中,你都以那些成功的农民——包工头、工程队长、船老板、总经理、董事长等各色人等——的生活和成长为文本的核心内容,尤其关注他们围绕着金钱、权力和情欲而产生的畸态生活和扭曲人性,并经常通过一些主人公悲剧性的命运以表现出你明显的批判意图,这一创作倾向是否和你的经历有关?对于乡村、农民、农民工与当代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关系,你觉得如何处理才能避免这么多的社会问题,或者进一步说,你未来的写作是否还围绕着这样的阶层展开?另外,在这一特殊的底层叙事之中,你较为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女性的群像,甚至可以说你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以女性人物形象为叙事重点的,能否解释一下原由?是不是受到毕飞宇的影响?
余一鸣:前一阶段有“底层文学”之说,或称“打工文学”,关注农民进城后的心灵和生存处境。我选择写这个群体的成功人士,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当年的小伙伴现在发迹了,有钱有势却依然痛苦,城市化进程的心理过程是复杂而坎坷的,仇富者有仇富者的愤怒,富人也有富人的焦虑。有的人你给他财富,其实是把他架在火上烤。我觉得这个群体最能体现转型社会的时代特征,现实主义强调的矛盾冲突在他们精神世界鲜明凸现。我以后的小说人物避不开他们。
我不是一个写女人的高手,但是在江苏,有苏童、毕飞宇写的女人招摇于文学长廊,似乎不打造出一个文学意义上的女性形象,你都无法说你是江苏的男作家。写女人难,苏童笔下有《妻妾成群》中解放前的女人,毕飞宇笔下有《青衣》《玉米》中解放后的女人们,我避开她们,写现实经济大潮中的女性,也算是识时务者。
毕飞宇对我的文学影响,不是写好小说中的女人,而是主张我把男人写好。江苏文坛缺这个。而毕飞宇已经改变我的,是我的文学态度,把写小说当一件严肃的事在做。
何同彬:“把写小说当一件严肃的事在做”,我是否可以把这句话分作两个问题和你探讨,一,你认为什么样的写作方式和写作态度是不严肃的,比如可以以当下的文学创作潮流为例;二,严肃的写作态度实际上是和内心的沉静、敏感相对应,也必然带有超越于世俗利益、欲望和人际纠葛的非功利性的一面,但当下每一个成年人都深陷于一种极具功利性的文化氛围之中,另外你本人在是一个安静的作家的同时,也是一个性格豪爽、喜欢结交朋友、喜欢玩儿的一个世俗中的个体,那你是如何在这种现实性的文化悖谬中保持自己写作的那种非功利性的“严肃”的、如何平衡喧闹的现实与“严肃”的内心?
余一鸣: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人标榜自己爱好文学,到现在很多人羞于被划入文学爱好者队伍,应该说这一变化使文学写作者和读者的队伍纯净了。就作家而言,有为读者癖好而写作的作家,有为国内外大奖评委的胃口而写作的作家,奋斗目标在作品中不难看出来。这种追求我认为是有上进心,作家的脑子清醒。我写小说,最初是为成名,后来是怕被小说抛弃,写着写着成了一种精神慰藉,成为生活中不可割离的一部分内容。这几年写作,追求功利的成分少了,这年头,作家的地位不咋的,弄纯文学的作家物质上能过上满意生活的人屈指可数,富裕者也大多是借了影视的光。我现在写小说,不是为了去做成名作家,也从不指望靠稿酬过日子,写得出来就写,写不出来就不写,依从于自我感觉。有人喜欢我的小说,好事。有人批评我的小说,也是好事,但我未必要听从。有个叫栗宪庭的人说,我们的艺术怎么不被一个外部的体系所绑架,而真正回到艺术家个人的内心世界,从而找到一个更好的媒介去表达自己,不断地去突破,艺术获得一种自由和独立的状态,这个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人说得不错,这是一种严肃的态度。
实事求是地说,写作上取得的一点成绩,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我的朋友面越来越窄,心里揣着写小说的事,在外面撒野撒欢都不利落。除了出来与作家们喝茶喝酒,别的圈子活动我基本不参加了,我老婆发现一个规律,我现在只要出去吃饭肯定是我买单,别人请客你能躲,你请客总得到场不可。我老婆很高兴,除了工资卡我还常上交稿费单了,晚上坐家里省钱不说还赚碎银子。做饭的阿姨不开心,这人混得惨了,晚饭顿顿赖在家,麻烦。
诵经需要洗手焚香净心,进入写作状态至少要净心。专注即严肃。
何同彬:孟繁华先生在《人间万象与绝处逢生——评余一鸣的小说创作》一文的结尾,认为你的小说“有更多的中国明清小说的味道和气息,而少了西方18、19世纪小说的韵味和品格”,主要指的是你在现实主义书写时,由于沉溺于自己的经验现实和“迎合”一部分读者的阅读期待,而忽视“应该有一束高远的光芒去照亮他们”,这一批评性的建议你有没有计划在未来的创作中予以回应?
余一鸣:孟繁华先生是我敬仰的评论家,他一直关注我发表的小说,而且常常敏锐地指出我的不足。他提出我作品中的问题,我若辩解争论,他更加激情。我若是觉得他切中要害,无话可说,他就说,你说话,你别弄得好像是谁在以势压人。其实那时我确实满腔腹诽,这人眼光怎么这样毒辣,还让人怎么写小说?
小说有“品”还有“格”,我理解成小说品质和格调,什么是格调,就是孟先生所言“一束高远的光芒”。现实生活的沉重,确实使我的笔下难有轻逸美妙之感。我是语文教师,课本上不乏传统美学意义的经典课文,出于逆反,在小说表达上我不愿中规中矩。有个叫朗西埃的人说,什么是文学?就是突然冲进来,打破当前文学话语秩序的合法性的那种新话语里的力量。一首新诗冲进来,像造反派那样,取缔了现有诗歌秩序的合法性,它身上就带有“文学”了。我引用在此,这也是我持的观点。
我知道,我的小说对现实生活本质的揭露和展示算是一个特点,有人说,读完后有足够的痛感,但喘不过气来,这是我要的效果。揭露是作家的天职,这也只是基本要求,要使作品有“格”,还应该追求那“一束高远的光芒”。我不是上帝,想有光就有了光。但在我以后的作品中,会努力呈现这束光芒,哪怕再多的昏暗也抹煞不掉。我不指望文学拯救人性,但人性中本质的光辉还是温暖的,还是值得呈现的。我们没有信仰,只有依赖人性,也许最基本的也是最永恒的。
何同彬:这几年你的小说作品屡屡在《人民文学》、《收获》、《钟山》、《作家》、《花城》等高端文学刊物上出现,引来好评如潮,作品先后入选多种重要选本,你也先后获得了多种重要奖项(如紫金山文学奖、茅台杯人民文学奖、《人民文学》年度奖、《小说选刊》年度奖、《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奖、金陵文学奖等),这些褒奖和荣誉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认为自己是否已经是一个成功的作家,或者你的“成功作家”的定义是什么?
余一鸣:我说过,我曾经梦想做一个专业作家。后来觉得高不可攀,把梦想往现实拉了一拉,这辈子能在《人民文学》、《收获》这样的大刊发个小说。这些年,王安忆、毕飞宇都进大学做教授了,我的专业作家梦也淡薄了,文坛却给了我很多机会,大刊能发了,还不断获奖了。我这人命运待我不薄,只要付出总有取得。但我没想到,我还能有文运。这就像我前面打的比方,那个怨妇坚守的理由,你终有-天得回到我这里。
我来自一个苏南的乡村,从小接受的熏陶是说话圆润,滴水不漏,我那些出来混的家乡朋友,说话虚虚实实,做事进退自如,从商从政都成一点气候。如果我算是从文,应该更得精髓,但我觉得那样玷污了文学的神圣感。我感谢文学上所有帮助过我的师友,激励之下,我才能取得一点成绩,才会一篇接一篇往下写,才会在写小说这件事上有要求。许多身边的亲友都反对我在写作上花大力气,说你稀罕领奖,我们发给你。当然是玩笑,把我当幼儿园小朋友哄。我能理解,很多政客和商人都把文坛当儿戏玩,波及普世。但文学带给我的快乐无以替代。
衡量一个作家成功与否,当然是看作品。我算不上-个成功的作家,甚至连作家都算不上。这不是谦虚,就像歌坛上歌手与歌唱家之分,我最多算是一个有几支成名曲目的歌手。成功的作家应该如那做得长久的英雄好汉,十八般兵器皆能使得,不断向上,永远让朋友和对手有期待,有惊讶。这样的作家在我眼中只有几位,他们写得不易,活得不易。
作家必须扎根生活。这两年沙场折戟的大牌英雄当年出山匆忙,漏了现实主义这一课,拉架式不小心就露了怯。一位朋友如斯说,我觉得此言有益于我。我将蹲伏于现实,努力前行,力争能在创作中站稳脚跟,不被潮头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