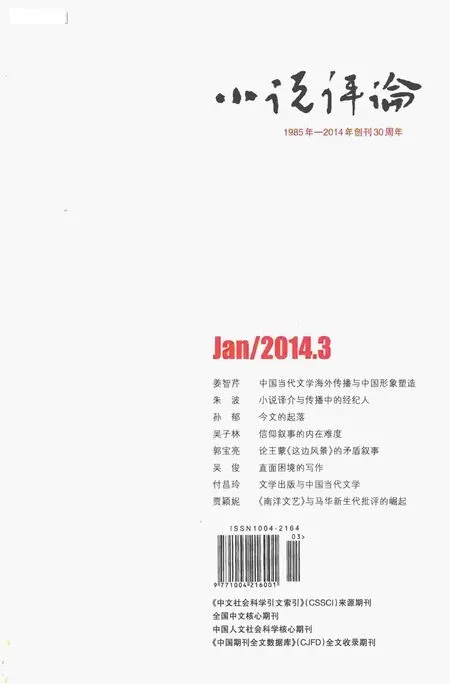1980年代中期中国小说创作理念的转型
吴玉杰 张枫
1980年代中期,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或淡出人们视野或让人们习以为常之时,寻根文学浮出水面。这是新时期文学中声势最为浩大、同时也是充满最多争议与论辩的文学思潮,多元声音的回响掺杂论争话语不对接的矛盾。发展到后来,论争超出文学范畴,进入到文化、民族文化的讨论话语之中。抛却批评界关于寻根文学的各种论争,作为问题主体的寻根小说作家的构成、寻根作品的类别本身就有着各种不同的分类方法。有人认为寻根文学可追溯至汪曾祺的《受戒》等作品,有人认为文化寻根意识“最初起于1982-1983年间王蒙发表的一组在伊犁系列小说”,还有人按照“精神归属的导向”划分寻根。寻根作家以及作品本身的复杂状态与巨大张力导致批评界的“众声喧哗”。
寻根作家也存在前后言论自相矛盾的现象。韩少功于1985年说,贾平凹等“都在寻‘根’,都开始找到了‘根’”。而从1990年代开始,韩少功申明“有些主流是批评家和记者虚构出来的,”是“弄出一个流派来”。韩少功在1980年代对寻根的确证表明,在当时的文学现场中确实有很多作家“寻根”。而他1990年代之后的言论说得也是事实。寻根作家自己并没有自觉的团体,“寻根”的命名亦似“简化”,并不能包含1980年代被称为“寻根”小说作家的所有作家。但他们有相似或相近的文学理念、具有相似或相近的文化追求与形式诉求等等。尽管对根的解释和表现可能略有不同,但在批评家的视野中这样一个创作群体的出现就意味着一个流派——寻根文学的诞生。
我们回到1980年代的文学现场,按照两条思路追根溯源:第一,参与作为寻根文学重要标志性事件即“1984年杭州会议”的部分作家;第二,在创作谈、访谈、信件中谈及与寻根文学相关联的作家。力求客观真实地把握作家们的“寻根”理念,多角度阐发这一理念形成1980年代中期中国小说创作理念的转型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与价值。
一、群起反抗:从政治之维到文化之维
1980年代中期,一部分作家不满政治对文学的越界入侵与捆绑性束缚,强烈要求尊重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以文学话语替代政治话语。恰逢新儒学兴起、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文化,这个曾经和“文化大革命”胶着在一起的文化,刷新了自我,成为那个时代“最热点”、“最时尚”、最具冲击力的符码。此时寻根作家在民族文化断裂的焦灼与文学表意的饥渴中努力寻找一种不同于政治话语的言说方式,寻找一种新的表达的可能性,而文化自然而然地成为批判与反抗、言说与重建的武器。由此可见,文化成为1980年代中国小说创作转型的话语方式,寻根小说作家通过寻根的文化话语实现对文学中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的反拨,与此同时文学中的文化话语解构革命文化,建构他们要寻找的根的文学和根的文化。
倡导寻根是作家对中国文学现状的不满与批判,而寻根也遭到当时政治话语的批判。阿城对小说仅观照社会学不满,“希望通过‘寻根文学’找到另外一种文化来解构革命文化。”韩少功称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在审美和思维上都不过是政治化‘样板戏’文学的变种和延伸,因此必须打破”。“某些批‘文革’的文学,仍在延续‘文革’式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突出政治。还有的作家借阐发古人之文,表达对当时文坛求“思想和主义”的不满。李杭育认为“两千来我们的文学观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仍旧是政治的、伦理的,而绝非哲学的、美学的。”何立伟肯定苏轼、张岱的两篇文章艺术品位最高,“同一味想在作品中求思想和主义的一类作家完全两样的审美态度。”这些表述暗含着作家对当时文学创作环境的不满和变革的内在诉求。寻根,是一种新的小说创作理念,是一种从政治之维到文化之维文学理念的转型,蓄积着巨大的反拨力量和批判力量,当然也是一种巨大的自我建构的力量。但转型不可能顺利地在瞬间完成,它往往会遭遇反拨的反拨、批判的批判或新的批判。寻根思潮在当时遭遇到了强烈的批评,左翼人士说“‘寻根’是回到‘封建主义文化’的危险动作”,右翼人士说“‘寻根’是‘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反动。”一种文学理念受到政治话语层面的批评,体现出当时文学界政治思维模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反向印证了部分作家要求文学创作从政治之维转向文化之维的迫切与必然。
当然,文化之维是批判的武器,作家要寻找的还有文学。文学需要“对人类生活未知世界的探究和发现”,寻找新的写作资源,成为作家们的当务之急,而文化作为开发写作资源的一剂药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这种探究与发现提供了巨大的资源支持。阿城认为文化“是比意识形态更广阔深厚的背景,对于开发写作资源的作用非同小可,是这一代人与狭隘的政治观念脱钩的一个关键契机。”在这里,“文化”好像只是一个支点,“寻求新的可能性”才是关键。
事实上,无论是何立伟主张取法古典文化,还是李陀拿来地域文化,或如李杭育崇尚少数民族文化,作家们或把文化作为一种创作资源,或把文化作为批判的武器。他们时刻也没有离开文学,他们倡导文化却始终围绕文学进行。韩少功认为,乡土文化“更多地显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地下的岩浆,更值得作家们注意”。这显然是与政治典范的对抗,是一种写作策略的转移。郑万隆说“每一个作家都应该开凿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地下的岩浆”、脚下的“文化岩层”,是借助文化的力量,要求复归、找寻被主流意识形态遮蔽的文学本相。李陀道出了寻根的真意,“小说不是文化史”,“你写这一切毕竟是为了写人,是为了创造人物形象”。
作家们进入文化角度不同,但在文化中都寻找到了自己最为认同和亲近的那一部分,殊途同归,寻找的都是新的写作的可能性、文学的超越性。当然,寻根作家用文化话语反拨主流意识形态政治话语,推动小说理念与文学理念的转型,彰显出对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对民族文化的重新审视、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这一理念的具体化实践则表现与揭示了中国精华与糟粕并存的传统文化、多元化的民族文化、多样态的地域文化。寻根,寻找被政治话语遮蔽与漠视的真实与原生的文化,它不是恋旧,而是文学的、文化的、民族的自醒与自省。作家把目光“投向更深的层次”,“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大作家必定感受“他的民族文化的呼唤,”表现出“对这个民族的命运的思考和关切。”由此可以看出,寻根,是寻找一种新的可能性的文学的寻根,当然也是文化的寻根。文化之于寻根,是1980年代中期文学反拨的武器,同时,也是寻根的目的。
二、自觉追求与构建:从群体问题意识到个体审美意识
中国当代文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重思想内容,轻艺术形式;重群体意识,轻个体意识;重问题意识,轻审美意识。这种文学理念严重抑制着文学创作的生命力。1980年代作家们对政治话语予以决绝反抗,开始对艺术创作的内在规律做自觉追求。形式的诉求、感觉与直觉的强化、语言的发现,都在表明,寻根作家是在同过去的具有群体问题意识的文学理念告别,倡导一种新的富含个体审美意识的文学理念。他们的寻根是文学理念的转型。
首先,形式的诉求。提到形式,人们通常会想到新潮文学、先锋小说,事实上,在寻根作家那里,已经开始注重谈论艺术形式问题并追求独特的艺术形式。
新时期初期,文学形式问题仍然较为敏感,直言形式创新还需很大勇气。1980年,“当前文学创新的焦点是形式问题”的言论被不点名地批评,但“形式”却被先锋小说和寻根文学同时发扬光大。“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并不构成一个单一的线性的文学史秩序”,是多元共生的存在。韩少功说寻根对西方文学与思潮如饥似渴狼吞虎咽。李陀认为“先锋小说和寻根小说在中国是互为表里的”。而共有的成分,就与文学形式相关联,“重要的是‘寻’,而不是‘根’。”作家们“呼唤的是艺术创作的独特性”,直指艺术形式。寻根文学正是文学形式创新的一个支流。阿城的《棋王》被李陀推荐给编辑后,被认为是非常好、很难归类的小说,而八十年代对作品的评价最高的就是难以归类。难以归类的小说出现新的创作特征“对文化问题的关注”。由此寻根能成为潮流,除了文化之维,更有形式诉求。
与其他文学潮流中的作家群相类似,被标注寻根文学标签的作家们大多不承认这种所属关系,韩少功拒绝划流派,王安忆说“我创造时根本没想到去‘寻根’”。反对归类验证了作家们对独特性的追求。语言、情调、感觉、形式等词汇开始出现在寻根作家的创作谈和访谈中,他们以个人的审美经验和审美趣味,探索全新的艺术形式,貌似集结在寻根大旗下的一派群体作家们其实更具有彼此独立的个体审美意识,旨在构建形态各异的艺术世界。正是在这一时期,文学开始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审美形态。而从文化的角度追求艺术的独特性,又使得这些作家在艺术形式变革这个层面上获得了内在的一致性。
其次,感觉与直觉的强化。
中国当代文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忽视主观表现,主体性审美经验缺失,艺术感觉僵化,理性的强化导致审美知觉和审美想象的弱化。而寻根小说作家特别注重感觉、直觉,甚至把它们推到“至尊”的地位,含蕴着小说创作理念的转型。
寻根小说作家对感觉与直觉的强化从批判感觉的异化与僵化开始。感觉僵化与异化束缚主体的审美感知,造成艺术表现模式化。当代作家往往想通过文学表现重大社会问题或是揭示一个革命性真理,政治话语的理性干预弱化了主体的生命感觉,导致文学单一化,缺少形式独创性。1980年代中期,寻根作家意识到“感觉力便是作家的创造活力”。寻根作家关于感觉的言说犹如利器,刺痛业已麻木的审美神经,呼唤个体审美意识的觉醒。他们从自我感觉出发,实证性地论述感觉与文学的内在关系,“我常常凭看这种遥远、朦胧甚至有点神秘的感觉来写”,“我竭力保持着这些有生命的感觉。”然而寻根作家没有在自我的感觉中迷失,而是清醒地认识到“个人的感觉体现着某些人类所共有的感觉”。从个体生命体验出发的自我感觉获得普遍性价值。在此基础上,又形成对感觉的形而上思考,具有诗学或曰文学本体的意味。郑万隆认为,“有生命的感觉是整体性的感觉”,“把客体视为有生命的有机整体来进行审美观照,是一种直觉与理解。”李杭育也强调:“发达的直觉恰恰是文学最珍贵的‘神思’”,“经验、直觉、想象力构成的智慧”是“大彻大悟,是至尊的。”寻根小说作家把直觉推为至尊,颇有克罗齐“艺术即直觉”的味道。
寻根小说作家批判感觉的异化,表述自我的生命的感觉,以自我的感觉体现人类共有的感觉,进而把感觉与直觉升华为诗学的高度。这样的逻辑性表明,寻根小说作家不是简单地说明自己的创作体验,他们的言论中深深地镌刻着小说创作的理念。相对于弱化感觉而强化群体问题意识的文学理念来说,感觉与直觉的强化体现出的审美意识是一次文学理念的转型。
最后,语言在传统与民间中的发现。
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而从新中国后到新时期以前,语言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破坏,强化政治功能与表达情感功能要大于语言自身的审美功能。直到新时期作家们才积极探索,突破语言政治工具论的思维框架,上升到对语言本体论的认知。同时,新时期文学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文本的晦涩与读者传统的接受心理不相适应。发现与本民族文化心理相契合的语言成为寻根小说作家在艺术探索上的起点。
寻根小说作家强调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即艺术个性,即风格,即思维,即内容,即文化,即文气,即……”省略号在这里具有特殊的意味,表明“语言”具有无限的涵义,语言就是“第一要义”,但作为“第一要义”的语言却遭到破坏。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何从被破坏的语言瓦砾与碎片中发现语言、重拾语言、修复语言,充分地个性化地表达自我。寻根小说作家从两个方面发现语言。一是走向民间中的发现。王安忆、韩少功等与主流意识形态语言相对抗,采取语言的民间立场。王安忆说,民间语言比意识形态语言更活泼,“一旦被发现,便强烈的吸引了我们”,使我们“纷纷走向民间”。民间语言具有原生气息,也更具生命活力。虽然当代小说作家不乏对民间的重视,但是有的作品表现的却是虚假的民间,所使用的语言也是被过滤掉的民间语言。当民间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发生冲突时,民间话语便让位于政治话语。二是回望传统中的发现。何立伟认为由新文学史大师鲁迅、沈从文等人开启的美文传统似乎是断裂了多年,但他发现,汪曾祺的语言富于音乐的流动美,阿城的语言是绘画的质感的美。这样的品评在历经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后的新时期文学初期,实为新鲜,好像从这一时刻开始语言成为语言,文学成为文学,美成为美。
在寻根小说作家这里,形式被当成一个突出的问题提出,感觉与语言被放到至尊之位,被群体问题意识遮蔽的个体审美意识得到彰显,这些都标示着小说创作理念的转型。
三、对话与超越:从国家民族一隅到现代世界之维
“寻找你自己”。这成为寻根小说作家的“标语”式宣言。然而,最初的现代派探索存在大量复制与仿造问题。这引起寻根小说作家们普遍不满。他们反对“横向移植”,认为小说“从思想,到材料,到语言”,“一切都应该是丰富和新颖的”,也就是说,都应该是自己的。模仿,没有创造力,当然也没有竞争力,不可能走向世界。“寻找你自己”,是走向世界文学格局的基本前提。
既反对横向移植,又要进入世界文学格局,如何对中西文化资源进行创造,使中国文学找到自我是当时作家最为关心的问题。选择之后,他们将本土资源作为与西方“对抗”的武器。这既受到外来文化的启示,更是作家们的自觉追求。在发现横向移植无法走出独特的文学道路之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特别是所谓第三世界国家文学或是亚洲邻国获奖者的经验更为作家所关注。1968年获奖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作品“初看是极日本性的,细品却是极现代的”。1982年凭借《百年孤独》获奖的马尔克斯,“给我们提供一个完全新的视野,把现代主义和他们本土的文化有一个很好的结合”,“是拉丁美洲自己的小说”。川端康成与马尔克斯的作品都是现代主义与本土文化的有机融合。而这两点成为中国小说作家进入世界文学格局的两张王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即是证明。
寻根小说作家对本土文化的寻根,更主要的动因在于他们发现中国本土资源的独一无二性,这和川端康成、马尔克斯找到独一无二的本土文化一样。韩少功认为,本土文化资源“构成了‘寻根’的基本前提。”李陀“一直在考虑中国的文化资源,如何跟中国的小说结合起来”。基于本土资源的独特性与唯一性,作家们选择了寻根。但寻根取向不同,有的主张做“纵的继承”,像何立伟谈“美的情调”;郑万隆在地域文化中寻根,黑龙江是他生命的根、小说的根。乌热尔图表现“地地道道的鄂温克族文学”。韩少功则经常谈到知青资源,认为“寻根”作家比如贾平凹、李杭育等人都是知青,“他们成为‘寻根’意向最为亲缘与最易操作的一群”。知青身份成为一种财富,让作家与本土文化“亲密接触”,让他们在本土文化的土层与岩浆中发现他们从未发现的东西,促使他们进一步以自我的感觉直接体味中国的传统文化、民间文化、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最终,他们都找到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本土文化,找到了“根”。
现代性视域中的寻根,是寻根小说作家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理论自觉。寻根小说作家对“根”有着特殊的情感,也有充满情感的现代性的言说与表达,不是“复古倾向”或保守主义。第一,寻根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现象。韩少功始终强调寻根与现代性关联,如果不是在现代性视域、不是在欧风西雨之中,寻根文学无从产生。第二,寻根是开放的时空观。几乎所有的寻根小说作家对外来文化都采取“拿来主义”,寻根“不是要回复一个旧的时空,而是要打开这个时空。”打开时空,是为了了解外来文化,具有开放性。贾平凹也宣称,对外来文学大量的无拘无束的吸收。第三,寻根的开放是为了充实与再造。郑万隆宣称“我们的文学现实也应该用开放性的眼光进行研究。”李杭育说,“理一理我们的‘根’,也选一选人家的‘枝’”。韩少功认为寻根“只有找到异己的参照系,吸收和消化异己的因素,才能认清和充实自己。”而且,在寻根的过程,也重视再造,贾平凹极为推崇三十年代的作家古典文学水平极高又精通西方。由此可见,寻根小说作家想要达到的寻根,不是复古与保守,而是在现代性视域中保持主体性的前提下充实自己、提升自我的寻根。
世界文学的坐标设置是寻根小说作家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提供的文学参照。寻根小说作家植根本土文化又超越本土文化,从国家民族一隅到现代世界之维,在现代性与世界文学中观照中国的文学与文化。
寻根小说作家在世界文学经验的启发下观照本土文化,进行文学创作,同时又把观照本土文化的创作放在世界文学的视域中考察。乌热尔图之所以对边疆文学给予更多注目,是受苏联和拉美等世界文学经验的启发。世界文学经验表明,深深打上本土文化特点的小说才能真正走向世界。作家站在世界角度看问题,反观本土文化与文学,一种对话的渴望与民族的自信油然而生。阿城就表达出与世界文化对话的渴望,郑义坚信“能跨越民族文化之断裂带,终于走向世界。”世界文学经验对中国作家是富有启发性的,促使中国作家不仅有对话的诉求,而且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对对话本身也充满自信。
世界文学经验不是本土文化的单一维度,还必须有现代性之维,这双重维度是世界文学的经验,当然也成为中国作家设置的世界文学坐标,使“寻找你自己”成为可能。所以,寻根小说作家对民族文化进行更深层次的开掘,寻求“具有现代意识小说的根”。他们学过了乔依斯、马尔克斯等人之后,“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学范式,来对自己脚下的‘文化层’进行考察”,“建立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寻根小说作家一直在本土文化与现代性的双重维度中观照中国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根不仅是寻找文化之根,也是寻找“具有现代意识小说的根”、“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学范式”。这样的寻根理念超越民族国家一隅进入现代世界之维,使中国文学真正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学对话成为可能。
1980年代中期,寻根标示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小说创作理念。从政治之维到文化之维的群体反抗,从群体问题意识到个体审美意识的自觉构建,从国家民族一隅到现代世界之维的对话与超越等等,所有这些表明,寻根,不仅是寻文化之根,文学的根,而且是寻找文学之为文学之根,是寻找属于自己的具有个性化表征的文学范式。同时,寻根也是寻找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立足之根。
寻根是1980年代中国小说创作理念的转型,它为文化成为文化、文学成为文学、美成为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等都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与努力,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寻根的理念,不仅发生在寻根小说内部,更重要的是,对其后的小说发展起到了多方面的影响。个人叙事、新写实小说以及新历史小说等文学潮流,都曾受到寻根理念的启发和影响。“‘寻根’本身就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无限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根是文学史上一次具有无限意义的寻找与发现。
注释:
①季红真:《历史的命题与时代抉择中的艺术嬗变—论“寻根文学”的发生与意义》,《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1期。
②陈思和:《当代文学中的文化寻根意识》,《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
③[26]李庆西:《寻根文学再思考》,《上海文化》2009年第5期。
④⑯⑲[57]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⑤韩少功、罗莎(意大利):《一个棋盘,多种棋子—关于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对话》,《花城》2009年第3期。
⑥⑩[22][23][25][28][42][45][47]王尧:《1985 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以“先锋”与“寻根”等文学话语的缠绕为线索》,《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
⑦[60]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
⑧[39]吴亮、李陀、杨庆祥《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和先锋批评》,《南方文坛》2008年第6期。
⑨韩少功:《杭州会议前后》,《上海文学》2001年第2期。
⑪⑳[56]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9期。
⑫[37][38][41][48]何立伟:《美的语言与情调》,《文艺研究》1986年第3期。
⑬[24][46][51]韩少功:《寻根群体的条件》,《上海文化》2009年第5期。
⑭[62]郑万隆:《文学需要什么》,《文学自由谈》1985年第1期。
⑮王安忆:《谈话录(六):写作历程》,《西部》2008年第1期。
⑰[33][35][49][55]郑万隆:《我的根》,《上海文学》1985 年第 5 期。
⑱[21][50][59]李陀、乌热尔图:《创作通信》,《人民文学》1984年第3期。
[27][43]郑万隆:《寻找你自己—〈青年小说选〉序》,《朔方》1986年第3期。
[29][52][63]韩少功:《文学史中的“寻根”》,《南方文坛》2007年第4期。
[30]王安忆:《从现实人生的体验到叙述策略的转型—一份关于王安忆十年小说创作的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6期。
[31]李杭育:《小说自白》,《上海文学》1985年第5期。
[32][34]何立伟:《作家的感觉》,《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4期。
[36]李杭育:《通信偶得》,《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2期。
[40]王安忆:《小说的技术》,《花城》1997年第4期。
[44][54][58]贾平凹:《四月二十七日寄友人书》,《上海文学》1985年第11期。
[53]李欧梵、李陀、高行健、阿城:《文学:海外与中国》,《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6期。
[61]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文艺报》1985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