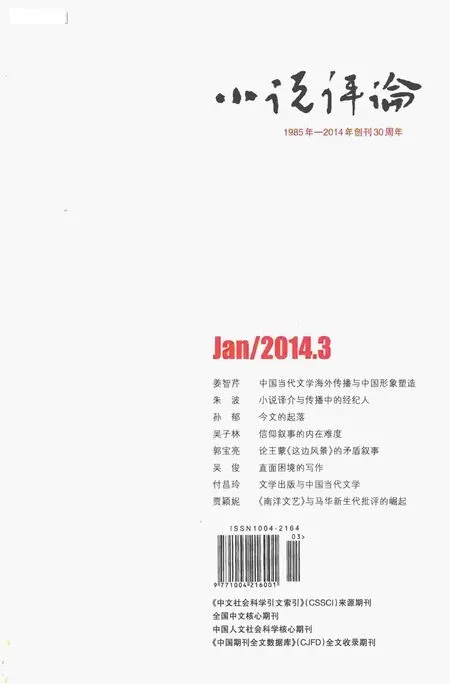“拟像”背后的诱惑与解码——评明明的长篇小说《零度诱惑》
梁海
20世纪初,法国艺术家马塞尔·杜尚挑战受众的常规审美,提出了“零度审美”观。他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垃圾,任何垃圾都是艺术作品。艺术的标准消失了,美的标准消失了。杜尚给蒙娜丽莎添加了两撇山羊须,他没有让她更美,却让她更抓眼球。人们习惯了微笑的蒙娜丽莎,却从未见过长了胡须的蒙娜丽莎。这就是“眼球效应”。它在彻底抹煞美与丑界限的同时,也成为现代媒介对大众生活权力控制的主要手段。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将这种“眼球效应”称之为“媒介奇观”,意指媒体对景观的过度炒作与肆意夸张,视觉冲击力强,传播吸引力大。可以说,这种“奇观文化”正在迅速扩散和渗透到社会和文化的各个领域。在“奇观文化”影响下的现代媒介,已经无时无刻不在以自己领域内的权力系统与文化内涵构筑着人们的生活,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指出的,电视、广告、电影、广播等现代科技产物,以无孔不入的方式挤进人们的内心深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们意识形态领域的消费品乃至只会接受媒介文化的零件机器。明明的《零度诱惑》(《钟山》2013年B卷)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媒介眼球效应”导致人性异化的故事。
小说女主人公尤嘉霓曾经不谙世事,单纯美丽,然而,现代媒介所打造的不容撼动的价值观,彻底改造了她。她在欲望与诱惑的追逐下,一步步走向堕落,以等价交换的方式出卖肉体和灵魂,将自己转化成性诱惑的一个具象符码,最终应验了让·鲍德里亚那句名言:如果我们以诱惑为生,我们将因蛊惑而死。从表层情节来看,《零度诱惑》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有关女性成长与堕落的作品,在中外文学史上可以拉出一张长长的书单,其中不乏经典传世之作。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德莱赛《嘉莉妹妹》、苏童《妻妾成群》……都从不同的视角刻画了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发生的偏差,以致最终走向无可挽回的悲剧命运。在我看来,作家明明选择这样一个故事作为叙述的对象,的确需要勇气和魄力,因为稍有不慎,就会使文本沦为一个老调重弹的故事,毫无新意。然而,明明却巧妙地超越了故事话语的表层,用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问题:媒介对人性的物化和异化。
《零度诱惑》描绘了尤嘉霓从成长到堕落的人生历程。我注意到,与一般的成长小说不同,明明并没有以叙事时间结构文本的整体框架。而是将故事空间作为推动叙述的主要手段。在主叙述层下设置了一个又一个亚叙述层,以叠套结构讲述了不同媒介打造的一个个偶像,以及她们对于尤嘉霓人生道路的影响。首先是陶萃丝。这个被媒体热捧为21世纪女性新偶像的女人,依靠大脑中与生俱来的极其准确的GPS定位系统,锁定了全球奢侈品牌的顶级富豪Robert,凭借野兽般的攻击力,迅猛攥获机会的掠夺力,一举拿下对方,成为所有女性心目中众望所归的英雄。当陶萃丝走进Robert,轻巧地将橙汁泼溅到他的西服上,绽露出的糅杂孩子气和女人味的笑靥;当那双白皙、柔嫩的年轻女人的手轻按餐巾纸擦拭溅溢的橙汁;当她柔软的发丝轻触布满皱纹和老年斑的面颊……她的每一个动作似乎都被定格,放大,张扬出欲望的气息,诱惑着那些渴望物欲享乐的心。尤嘉霓就是其中之一。陶萃丝的“光辉事迹”让尤嘉霓知道了什么是“猎女”,即用自己的美色为诱饵,去捕获那些在荣耀的霓虹灯下熠熠闪光的人,用自己温暖的青春的肉体去换取那些成功人士倾己一生打拼的声名和财富。尤嘉霓开始寻找猎物,最终她选择了陈逸山,她所在报业集团的副总。陈逸山比尤嘉霓大将近20岁,浑身上下散发出成功男士成熟、自信以及由权力所打造的威严,这一切对于尤嘉霓而言,无疑有着巨大的诱惑力。然而,年龄与阅历造成的巨大鸿沟是难以填补的,除了性的需求,尤嘉霓只能以服饰、发型、隆胸、整形来维系陈逸山对她的新鲜感。显然,这些来自表层,而且带着明显交易性质的诱惑是不可能长久的。于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尤嘉霓和陈逸山的性爱宝典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由“我很想你”到“永不停歇的肉体狂跑”,再到“戴着假面舞蹈”、“永不被猎获”、“当激情缺乏新鲜感”,最终凝固成一块“性爱的疤痕”。
被陈逸山抛弃的尤嘉霓并没有气馁。她很快在大众媒介上寻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金玄雅,一位与她长相极其相似的韩国影星。金玄雅为某奢侈品牌所做的广告深深打动了尤嘉霓:炫目的珠宝、华丽的名包、等候在劳斯莱斯中手握方向盘的英俊男士……所有这些都蒸腾出物质的诱惑。既然“猎女”之路如此艰辛,那么不如退而求其次,在物质上尽情欢愉。看着金玄雅的广告,尤嘉霓恨不得钻入其中,获得她喜欢的爱马仕铂金包,卡地亚首饰、法拉利跑车……她与金玄雅一样貌美如花,金玄雅有的她也应该拥有。于是,她开始训练对名牌的鉴赏,HERMES、CHANEL、DIOR、LV、COACH……她一面鄙视着那些对品牌无知的人,一面极尽炫耀,他人越嫉妒,她越有虚荣的快感;她最在意男人的地方是他们拥有的数字:存款多少,豪宅几幢,名车几辆……她所信奉的是台湾中兴公司的那条广告语:“银行倒闭不会令我不安;天堂倒闭不会令我不安;不景气不会令我不安;缺乏物质欲才会令我不安。欲望从来就没有不景气的时候……”,她听着这样的广告词走在城市广场的石阶上,金属鞋跟的回声不知疲倦地响起。姿态妖娆,表情冷漠,眼神骄矜,感知着艳羡或嫉妒的目光。
如果说陶萃丝、金玄雅还仅仅是尤嘉霓可望而不可及的偶像,为尤嘉霓提供了奋斗的标高;那么,林美琪则是现实生活中欲望的化身,她是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指导尤嘉霓走向成功之路的真正“导师”。林美琪似乎是一个典型的泛性论者,相信“力比多”的强大力量,渴望性自由,强调性的开放、敞开、长驱直入、无所边界。然而,与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学说不同,林美琪并非将“力比多”视为包含在“爱”字里的所有本能力量,而是把“力比多”作为换取物质财富的资本源泉。爱情的纯度视乎礼物的昂贵程度,一个人能否立足能否拥有尊重也是要看他过着怎么样的物质生活。每个人的肉里都镶嵌着条形码,存在和价值的标准就是等价交换。在林美琪的引导下,尤嘉霓意识到“一、身体也是资本,性是社交的一种,性本身是给人消费的;二,学会贩卖身体,并将身体贩卖到最高值,实在是门高妙的学问”。从此,这一人生体悟成为了尤嘉霓的行动纲领,她开始穿梭在不同的男性之间,飞速滑进了“公共情妇”的行列。
我想,作者之所以要塑造尤嘉霓这个当代中国的包法利夫人,并不是简单地讲述一个因爱慕虚荣而出卖肉体的堕落女人的故事。在尤嘉霓的身后,作者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被媒体包围、左右的世界。可以说,尤嘉霓的奋斗史就是一场被裹挟在影像喧嚣时代的堕落史。在这个世界中,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地被各种各样不同的媒介所挟持,没有谁能抵挡影视、广告、网络呼啸而来的飓风,信息蕨浪般席卷人们,感官欢叫着,肌肤灼烫着,身体被奇迹、梦幻和狂喜所浸透,每一寸肌肤都嵌满了影像的碎片。影像一笔勾销了道德、信仰还有羞耻感,只留下空洞的欲望狂欢。最终,人被驯化为媒介的奴隶,被媒介所异化。
让·鲍德里亚曾在他的“拟像理论”中指出,拟像,是指没有原本东西、现实坐标的描摹。我们所看得见的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由媒体所营造的、由被操控的符码组成的“超真实”世界。“拟像”不仅包括图像、形象、符号,还包括现实景观、社会事件、生活行为;“拟像”的一连串近义词是:仿制品、仿真幻象、镜像、人造品、作秀、角色扮演、面具、谎言等。“拟像”截取了事物本来的面目,不断地制造伪事件、伪人物、伪情境,而一旦人们情绪的调控器掌握在制造“拟像”的媒体手中,“媒体奇观”变异下的世界将彻底改变人们的感知、思维、行为,导致认知的变异,思维的变异,行为的变异。恰如作者在文本中所写到的,“媒体塑造了偶像,偶像发出了声音,声音到处鼓噪着,干扰着试听,尤嘉霓的时代鼓噪着各种声响,世界背景般的雷鸣声响,屏蔽了内心的真实声音。她听不到自己灵魂的声音,她听到的都是别的声音,网络里的,广告里的,电视里的,她的家人或朋友的,她在嘈杂的声音中行走,这声音如此强大,如轰炸机马力强大地在头顶盘旋,尤嘉霓以为这声音就是自己的声音,她失去了自己的原声”。
显然,作者这部20多万字的长篇并不以情节取胜,它承载了更多对时代的反思和批判。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作者在叙述方式上选择了传统的全知叙述,让读者能够更清晰、全面地透视人物的心理。尽管在现代小说中,这种全知叙述并不被看好,认为悬置于故事之外的高高在上的叙述者,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故事的逼真性、自然性和生动性。然而,作者明明似乎并不在意这些。我感觉,明明是在刻意尝试一种新的文体实验,以最传统的叙述方式,勾连起“非虚构”与虚构之间的通道,从而形成强大的叙述张力。一方面,明明在文本中避开故事中人物的视角,通过故事外的全知叙述者引用了大量真实的新闻报道、媒介素材、广告词、资料数据,让虚构的小说文本出现通常在学术文章中作为佐证的材料注释。如,“2010年,在中国的一次网络调查中,至少有六成的女大学生,希望自己嫁给富二代”。“掌握镜头的人,本身也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大多数新闻是虚假的,因为新闻是经过挑选的,支离破碎的,被放大或缩小,由记者渲染、加工推向公众的,与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吻合”。“抗拒不如主动挑逗!”(台湾中兴百货广告语)另一方面,那位无所不知的叙述者又时不时打断叙述,发表一些即时性的精彩点评。“2008年,中国已全面进入泛娱乐时代。各类娱乐节目,癌变般增长,模仿秀、达人秀、好声音、超女、快男、各式选美、演艺、相亲等节目,热糟糟,闹哄哄占据了中国各地的荧屏。每个人都梦想成为明星,每个人都试图成为明星,途径越来越多元化,海选,网络视频,微博……梦想变成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无限可能的现实,吐着热烈的火舌,肆意吞噬躁动的青春肉体”。显然,这些理论性的、知识性的、资料性的素材零锦碎绣般地插入,貌似割裂了叙述的完整和流畅。然而,非虚构素材的引用,作为虚构故事的一种补充,可以让我们重返现实和个人生活现场,清晰地闪回出现实存在中那些真实的细部。虚构与现实通过严丝合缝的缝制,存在或事实被最大限度地还原,让读者真切感受到现实“黑洞”的巨大诱惑力。可以说,作者在业已模糊的文体界限中营造了一种特殊的叙事策略,试图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重建世界与文学的关系。
为了凸显这一创作主旨,明明在叙述中还非常注重话语空间叙述。有时她会暂时搁置全知叙述,而采用通过人物视角展现故事空间的手法,使得故事在看似“客观”的环境空间展现与人物思想价值密切相关的心理空间,从而进一步放大外部世界对人的深刻影响。我们看到,在文本中尤嘉霓每一次心理历程的起点几乎都是在故事的话语空间中展开的。“当华丽的灯瞬间消失,镜子又是冰凉的,冷嘲热讽的。外面的世界,有五颜六色的镜子,电视里的,橱窗里的,中心广场的大屏幕,到处都是流动的镜子,到处都有参照的镜像,到处都飞舞着她理想的生活图景。然而,尤嘉霓在这些镜面看到的自己,是缩手缩脚,经不住强光照射的,沿着城市壁缝行走的影像”。这段描述让我们透过尤嘉霓的目光,看到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充满着物欲,充满着诱惑,以及这种诱惑在尤嘉霓面对橱窗镜子时所产生的瞬间性的强烈冲击。电视、橱窗、大屏幕无不发散出张狂的欲望气息,让尤嘉霓失去自我,沦为一具“沿着壁缝行走的影像”。事实上,故事中关于欲望的诱惑随处都在一个个空间场景具象性地展现。“长长的餐桌,精致的早点,窗外是开满玫瑰和百合的花园,而她的绅士正含情脉脉地等她喝完最后一口牛奶”;“大幅墙面拼贴马赛克、彩玻、贝壳、地面设计更独具匠心,U形水槽,上面碧水荡漾,地灯一照,蓝幽幽水的世界”;还有“勾缀玫瑰花蕾的黑丝鱼网袜”、“艳冶的绣花鞋”、“孔雀蓝流苏”、“褐色透网面纱”……叙述者对一道道能够勾起欲望的场景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均在强调主人公与外部环境在寓意上的互为照应关系,暗示了尤嘉霓的内心世界犹如现实存在的镜像,虚空,迷茫,膨胀。
无疑,作者明明的创作维度还有着很大的拓展空间。我们看到,《零度诱惑》没有停留在故事的表层游弋,更多的是在揭示深陷于“媒介奇观”时代的人们,在被媒介塑造的一个个“拟像”面前,自我的迷失以及由此导致的价值体系的凌乱和精神层面的崩塌。明明言说了生存的多重困境,她试图为小说构建一种形而上的厚重层面。所以,阅读明明的故事让我们体悟的就不仅仅是故事,还有哲学。我想,在这个时代,作者的愿望,一定是要努力去开启启迪灵魂的写作,尽管在今天,超越个体经验去描述一个时代异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