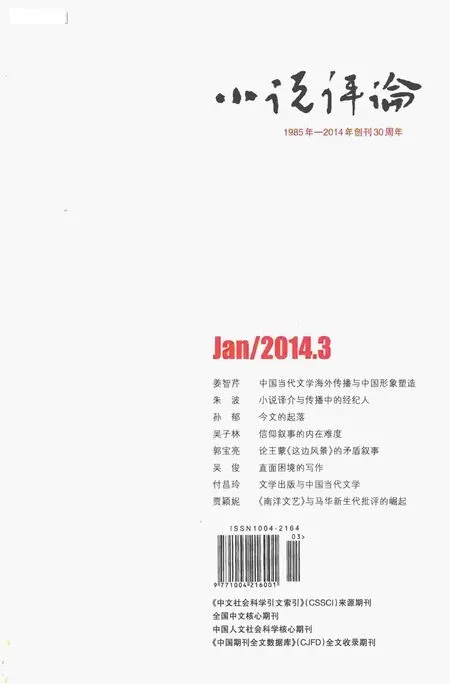论陈毓小小说创作的艺术追求
常智奇
小说,一定是以“小”开“说”,以“小”说“大”。“小”犹晨露映辉,一叶知秋,观微知宏。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发展到今天,在感管刺激,情感至上,消遣娱乐,创作产业化,文化公司化等等思潮和观念的影响下,小说写得越来越满,越来越密,越来越繁,越来越长,越来越实。文坛的许多有识之士都发出呼吁:“中国的小说只剩下说,沒有小了。”这不仅是中国当代小说创作遇到的问题,也是目前人类文学发展中小说创作遭遇到的共性问题。一些优秀的、成熟的、杰出的小说家怀疑“言可尽义”的理论,因为“言不尽义”是客观存在。他们认为言和义之间没有直接的互生关系,并企图以言通“象”,“立象尽义”来逼近小说的精粹本体。卡佛巧用语境的活性空间,将人物的复杂心理镶嵌于场景、活动和对话中,从而把叙事推进到让读者的五官能感受到、体察到的境地。乔伊斯依然走“言可尽义”的路子,他在语言互文的关系中,寻找语义学与逻辑之间的偶然性和巧合性来建立自己小说的结构文本。
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谈一谈走在中国“立象尽义”小说美学之路上的陕西女作家陈毓,谈一谈她的小小说创作的艺朮追求,我认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她近几年来创作勤奋,作品颇丰,己在《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数十家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一百多万字。出版小说集《蓝瓷花瓶》、《谁听见蝴蝶的歌唱》、《遇见红灯向右拐》、《美人迹》、《夜的黑》、《嘿,我要敲你门了》;几十篇作品入选“漓江版”、“花城版”、“长江文艺版”小小说年选及微型小说年选诸多选本。获首届和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三次获《小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两次获《小小说选刊》佳作奖。2006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上榜作家。
不久前颁发的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评委会给予陈毓的评语是:陈毓的小小说文体意识清晰丰沛,并贯穿于她的整个小小说创作过程中。她对现实生活的各类题材,特别是对生命、两性、爱情等有着独特的艺术感觉,有着别人无法重复、很难再现的艺术想象。她用小小说的文体形式来展现人类生命的真实状态,即便是在一些故事元素比较明显的作品里,她的艺术世界里特有的细节描述和氛围营造,她对小说叙述技巧的娴熟运用,以及在生活哲意的智慧传达上,都表现出一个成熟的小小说女性作家日渐灿烂的创作才华。
纵观陈毓的小说,是笔简意丰的范本。她在用语言造象,用象萦造境,在境象互体生成中传达着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对世界的认识。
一
陈毓是一个感性与理性、形象与逻辑、独立与依附、传统与现代共存互依,互汇互融,相互交错,相互磨擦、鼓荡的知识女性,这种剪不断,理这乱的情理相依,象境衍生的语境,使她站在田园牧歌式的审美情趣与现代工业文明的生活观念,古典情结与现代意识相扭结的中介线上,以一个在场者的女性目光和心理,用事象、物事、景象、时象、境象、气象、形象,构建起一个“载道”的互体空间,来以小指大、以微探宏,表现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民族的心灵裂变,情感阵痛,价值失衡,理想迷茫的精神特征。她的小说大多写现代青年的都市生活,写他们的情感世界,具有显明的时代性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既使是对夸父、大禹、赢政、唐玄宗、杨玉环、毛延寿等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等题材的整合与重构,也是站在现代意识、现代观念的基点上,重新阐释和演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感情。她在现实生活的情景事象中表现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与隔阂,情感的冲突与统一,良知的拷问与自省;她在义、象的构成中表现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的冲突情景,在境象的动态生成中揭示真假的分辨与混淆,认识的迷惘与困惑;她在事象的比兴中表达人物情感的时境,使读者陷入她设定的境象之中,体悟到她“以象载道”的良苦用心。她重视表现人物的情感、心态、襟怀、精神、气质。她是在人的生命体验、生活感受、理想追求中,呈现出一种人生姿态、生活情趣、感情方式、生存境遇、期翼想往。她的作品更多的关注人性、人情、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的分析与重构。她长于在柴、米、油、盐的日常琐事中开掘具有时代意义的美学价值,长于在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中,寻觅、提炼出新的思想观念和情感因素,在表现当代人生活的情感方式和理想追求中完成自己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爱情鱼》中的主人公叫“庄子”,是作者对诸子百家中的那位庄子“以象喻理”、“寓理于象”美学观的痴迷和信奉,还是对精神自由的漶漫比兴,总之,庄子失去了他痴爱的爱吃鱼的妻子妙儿,他痛苦万分。多年后他找到了酷似妙儿面貌的梅子。他像给妙儿钓鱼那样给梅子钓鱼。不爱吃鱼的梅子“压根就烦那股味道”。庄子施爱无对象,陷入了深深的孤独与痛苦之中。庄子爱美丽漂亮的妙儿就像庄稼爱太阳一样,妙儿从他身边走开,他却走不出妙儿的爱情阴影。一往情深化为泡影。人生的爱情悲剧在这里发生了。这篇作品告诉人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自己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方式,千万不可以一种“刻舟求剑”的方式以图索骥,寻找自己曾经得到过,但己失去了的爱情。在人生爱情的河流中,不可能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跋涉者的足迹趟过同一河流的水。作品中的“鱼象”,“妙儿和梅子之象”,构成了一个表义的虚拟世界,庄子在这个艺朮的虚拟世界中“载”起了作者要表义的那个“道”。作品优美隽永,构思新颖别致,又切中生活里一些再婚的要害,给人以生活的启迪。
《伊人寂寞》在生活、爱情、生命、科学、金钱的诸多矛盾冲突中,冷静而理性的看待明亮的阳光下,黑影里的博物馆里的那个名叫“惊鸿”的人体生命。作者在芸芸众生的世俗生活中,思考着生命的脆弱与永恒,爱情的甜蜜与无常,精神的坚守与金钱的诱惑,生命的孕育与灾难的厄崩,人类生命科学的进步和人类在生命情感上付出的昂贵代价。作者把对爱情、情感、理智、金线、科学的思考聚焦在一个“人体奥秘”的形象之上,根据博物馆里的“孕妇之象”,导出形成这种“惊鸿”情景和场面的原因和过程,进而描绘“看见明亮的阳光使博物馆呆在黑影里”的凉意感觉。睿智巧思,寓意博深,耐人寻味。
《做一场风花雪月的梦》以现代青年男女吴归与盖青的爱情为背景,写了青春女子盖青在梦中对至情至爱的追摹和献身的境象,又写了现实生活中吴归对她无爱的景象。在英雄美人的古典形象中,提炼现代知识女性对爱的渴望与追求。梦中的盖青与秦王赢政相遇、相恋、相爱,是“热象”,是美与爱,善与勇使之然。她路见不平,拔剑相助。她随他进宫,她看到“他很忙,他活在苦恼中,矛盾中,挣扎中。他要和那么多的人和事斗,要和自己抗争。他时而激昂,时而消沉,时而暴躁如闪电迅雷时而又恬静如若静水。她看见过他兴奋快乐地绽放过孩子似的笑脸,又感受过他无法靠近岸的溺水者的孤独……”梦中的盖青急秦王赢政之所急,忧秦王赢政之所忧,完全是一个把自己的全部的爱献给了自己所爱的那个男人的女子。黄梁一枕南柯梦,身边吴归无处归。她从梦中醒来后,现实生活中她所爱的吴归却太扑朔迷离,忽明忽暗,来无影,去无踪,难以琢磨,是“冷象”。盖青在这梦中之“境象”与现实之“真象”的热冷对比与反差中,心无所归,情无所系,一腔凄凉,满腹闺怨。作品写得明快,大气,简洁。
《看星星的人》从人的情感“心象”出发,表现了一个“立德者”,一个宣传部长和一个“立言者”的有夫之妇夜晚到深山去看星星的浪漫故事。作品中的两个主人公都生活在严酷的现实律令之中,但他们为了心中的那一种纯真感情而狂热地去寻,冲破世俗生活中的道道峡谷,重重山峦,到深山峡谷中去看星星。在这童话般的浪漫寓言故事中,作者直指现实生活中伦理道德的世俗观念,习惯势力对人的束缚,思考人的一种精神独立,情感自由和生存自由。半夜三更一个己婚的青年女子孤身外出,怎样给自己的丈夫解释?一个外地的宣传部长不顾自己的社会形象,行车近三百公里,约一个年青的少妇去深邃的峡谷看星星,成何体统?然而,这两个心中无鬼,感情纯洁,只是互相欣赏和认同的人自己感到有何不可呢。他们勇敢地做了。作品写了人人心中有,人人不敢做的一种感情,一个故事。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禁锢中寻找自由。读来给人以启迪。作品在“黑夜之象”中写“光明之象”;在“现实之境”中写“理想之境”,通过“境在象外”的“载道表情”,把理想融化在生活的闲谈和海聊之中,举重若轻,以虚写实,以实映虚,虚实相生,相得益彰,以此达到了字少意丰的艺术效果。
《温泉》中的小满,是城市化建设中一个“农转非”的洗浴中心的服务员,她犹如自己生活在大山中的那一股清纯的山泉,清洁、透亮、纯净。她面对来来往往,出双入对来洗温泉的男女,发出了“他是她的谁?而她,又是他的谁呢?”的疑问。在这里,地下喷出的温泉之水的“清象”与来自大山深处的小满的“纯象”是互相辉映的。在现代化的爱琴海温泉度假村,我们究竟应该洗掉什么?难道是小满的纯洁、清丽吗?难道是“那个有风俗的年代”吗?这是旧的伦理道德观念面对新时代、新生活,新的人际关系发生变化的一种困惑和疑问。小满在改革开放后爱琴海温泉度假村的“现代洗沐之象”中思恋温泉镇那个民风醇厚,乡俗迷人的年代。那时侯,村里的女孩子出嫁的前天,要去温泉里沐浴,干净鲜亮地迎接自己随之到来的全新的人生。这种矛盾心理是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过程中的社会心理,作者在新旧之境“变”的“生成”过程中表现社会与自然,文明与德道的心理磨擦。
陈毓是一位写现代人生活情感的小说家。她在“立象尽义”、“境在象外”、“言不尽义”的技术手段中寻找着“形象大于语言”的简笔写法。她的笔触携着时代的雷电,纵模驰骋在当下的生活大地上。她写男女在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之情;人性深处相依相恋中那一缕失落、空寂的猜度之情;从古典的历史文丛中走向现代的哲理思考之情。她是以情为媒介,写社会、写人生。她是一个站在桂花簇拥的高地之上,理性地看待芸芸众生,世态百象,人间苦难的“理性”作家。她的笔下,流露着一股典雅、超拔、现代的高天之气。
二
陈毓是一个重情重义,崇尚真、善、美的理想主义的作家。她的作品中灌注的是一种至纯、至清、至洁、至善的情感。她的作品是表现一种感情,一种人性深处那种潜在的意识,一种在“本我”原罪心理基础上的对“超我”原则的顾盼,一种在自然属性的挤压下的超凡脱俗的意绪。她写人性的真,写人性的纯,写人性的美。她在生活的俗常琐事中,捕捉那些最能表现人的情感深处善的东西。她是一个人性本善论者。她在“以事载道”,“缘情写景”,“比兴类推”的本象(文本世界)与外象(客观世界)的互体巧通中,营造出一个让读者有可能再度进行自由创作的空灵世界。
《卜吉寺的钟声》用“宗教钟声”此物唤起“精神救赎”彼物,在“杀人逃亡犯”的此在“心境”与遥望灯火爛珊处不能享受生活之乐的“人性拷问”中,表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一个因婚外情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从监狱里逃出来的逃犯,在卜吉寺院的钟声中剃度出家了,“那一刻,他像是一个即将被冻僵的人遇见了温润的泉水、让他紧缩的、皱巴巴的心灵得以舒展。他如同一块肮肮的冰在那神圣的钟声里慢慢溶化,那被溶解释放的、还有他的满面泪水。他在一种巨大的虚脱中沉沉睡去。”17年他没走出沉重的负罪感,他救死扶伤,打坐念佛,仍然未逃脱“欲知过去因,见其现在果”的法网。宗教的“超我”和犯罪的“本我”形成“快乐原则”和“理想原则”两个情感的“境象”世界,作者表现心灵在这两个“境象”世界由低向高攀爬的心路历程。
《夜的黑》中的老丁,面对自己心爱的女人被一个名叫黑子的青年后生拐跑下山,他一个人孤独地在鹤山公园当着看守山门的护卫,他不怨恨他的妻子——秀。他从自己昔日对妻子不爱或不会爱的行为方式上找失去爱的原因。他认为是他自己对妻子爱的不够才让自己心爱的女人跟着别的爱她的男人跑了。这种对爱的自责、自查、自审、自省的拷问,是人类爱的情感认知的最高境界,是一种爱的自我情感历练的博大胸怀。作品向我们揭示出: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还沉睡在夜的黑暗之中。作者以黑夜之“黑”,引起沉睡在夜的黑暗之中的爱情之“黑”;以黑子拐走他的妻子秀的“事象”,以及黑夜中一对并非夫妻的男女翻车丧命于深山沟的“事象”,在此“事象”引起彼“事象”的“比兴”中,开成一个以言立象,以象尽义的再造空间。
《一生》表现了一个八十三岁的孤寡老妪历经爱情的风雨,对她在八岁时,一个小名叫黑牛,大名叫韩非的男孩子,把一顶用黄豆叶柄编织的灿烂花冠戴在她头上,对她说,他要娶她当老婆的一句童言临终回望。这是生命和爱情在世俗生活中的考量和追寻。作品一开始就以男孩的“童真之情”引起她的“轻率之情”两种爱情态度之“象”开笔,后在历经八十三个苍桑岁月过场的情感之思中,对那顶“金黄色的花冠”的怀恋而收笔,开收在“比兴”之间,“境”阔“义”远。
《惊蛰》以“动物之象”引起“人物之象”,以猫之恋引起人爱之情,作品写年青的妻子对在外打工的丈夫的思念。作者把和暖思念丈夫赭石的那种爱之入骨的情感写得凄清、寂寞、孤零。
陈毓在比兴、类推、类比中赞美和歌颂的纯情,是一种代表了人性本质的感情,代表了社会文明和进步的友情,代表了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亲情,代表了新时代最富活力的爱情。她在以言造象,以象表情的批判中,鞭挺的是那些金钱拜物主义,权钱交易的肮脏之情,卖身求荣的卑污之情,人性异化的种种不健康之情。市场经济的时代,纯洁的感情是什么,在哪里,这是我们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向我们提出的一个尖锐而严峻的命题。有才华、有理想、有抱负、有做为的作家,必然会在这一命题下,表现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过程中的心灵震痛和情感裂变,重构新时代新的伦理道德观念,陈毓在思考,在表达,她的文学价值也在这里。
三
陈毓是一个具有浪漫情怀的作家,是一个在海德格尔诗化哲学的芳草地寻找“灵魂诗意地栖居于大地”的作家。她心中有一个形而上的现代哲思的世界,从这个世界投下的粒粒感情和双双目光,一定是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美学精神与中国本土小说美学精神的融合。她的小说有《聊斋志异》的古雅,有《老人与海》的时尚,有乔伊斯在用语言直通义意世界的构成,有庄子喻理美学在人与自然的摩荡震动中生发的意境,有浪漫主义的审美情趣,也有实证主义的理性拷问。她的作品中荡漾着强烈的主观色彩,有些作品就是在用一种飞扬的想象、幻想虚构出的一个主观自我感知的虚拟世界。她那率直、姿肆、诡谲、神奇、绚丽、多彩的丰富想象,鬼斧神工的异想天开,神与物游,点石成金,鲤鱼化龙的笔法与技艺,让人叹为观止。她在柔情似水的低吟浅唱中,传达出重大的社会主题;她那看似漫不经心的散淡叙述中,蕴含着深沉的人生思考;她在且行且远的慢板散唱中,完成了自己一篇篇以简显丰,以小见大、以少胜多、以俗见雅、以虚映实、空灵虚静、澄澈照天、神彩飞扬、潇洒瑰丽、玲珑剔透的具有欧美先锋主义审美意象的精短佳作。
《魔术师》写得冷静、理性、诡谲、虚幻,有一种西方哲思的荒诞意味,但其中有些细节又极真实,使人感动、沉浸和陷入,充盈着中国传统现实主义的情韵。作者在这真与假,白与黑,夜与昼的交织与变幻之中,表现人格的分裂,人性的异化。在魔术师的虚假生涯中同样潜藏着一颗求真、求纯、求爱、求美的赤子之心。作品在浪漫、幻化、诡谲的氛围描写中,表现了人性之美的张力。从四岁的无邪童真暗夜见真实的陌生女人进了师傅的房子,他追问师傅被师傅搪塞、欺哄开始,到表演开膛破肚,“我用双手,把一颗心捧出,像热恋中的青年向心爱的姑娘表达爱情时那样。虔诚无比。”这是用魔术师表演的“假象”呼唤人生的“真情”之象。
《牧歌》用一个现代知识青年的目光,看待岚城百姓的生存状况和生活方式,岚城的村民为鸡毛蒜皮吵架骂仗,老支书用他那乡村牧歌式的套路、解决问题的办法解决矛盾,令大学生村官李济目瞪口呆。这是现代知识青年面村中国农村精神面貌的一种新鲜感觉。作者极其注意细节景象的对位与契合。“第一夜,躺在窄窄的木板床上,听檐下的雀儿仿佛在对他说话:‘不吃你家的糜子,不吃你家的谷子,就借你家房檐,抱一窝儿子…’”这与半年后“李济一定要娶本地姑娘当老婆,闲身跳出红尘外。”在情感对应上不就有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吗!
《姑娘楼》描写了一个进城打工盖房子的青年民工苟福,与失去土地分得一套房子的莲雾村的姑娘莲巧联姻的爱情故事。作者在爱情描写中,表现我们民族在社会变革中生存的矛盾与困境,表现普通劳动者在推动物质文明建设过程中的精神风貌。作品写得舒展,空灵,既现实,又诗意。“姑娘楼交付验收的那个晚上,苟福对自己奢侈了一回,他把每户的灯都拉亮,他慢慢绕楼房一圈,仰望每一扇亮着灯火的窗子,感受一种深沉的晕眩感。透彻骨头的幸福是晕眩的。苟福总结自己的感觉。莲巧、不管哪扇窗子属于咱们,我都喜欢。”这种沉浸于普通小人物生活窘境的描写,又凌空超拔于世俗生活之上的情感表达方式,使整个作品显示出现代时尚的笔触,蕴藉虚灵的意趣。
陈毓小说中的浪漫主义是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之中的,她的浪漫不是主观感性的思绪飞扬,而是生命感受的超验表达。《石榴花 红石榴》把孩子的童真、童趣和那个践踏人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社会政治生活相对照,作品生动、形象、感人,富有诗意。那时,“政府限定每家只能栽两棵大树或三棵小树”,父亲为了保护那棵大核桃树,把一季一季的石榴树的花蕾及时摘下来,“悄悄扔进猪圈,被猪踩进了泥泞里”。让人感到石榴树是一棵不开花,不结果的小树。智者千虑,也有一失。作者写作品中的“我”发现了一个“被黑夜珍藏的”清涩小石榴在密叶深处隐藏,“我用一片碎镜片把太阳慷慨的光芒反照到一颗青绿的石榴上。”作品以童心的视角,表现扼杀自然天性的社会政治生活。既真实,又浪漫。有童趣,有生活,有哲思,有诗思,有匍伏于生活大地的情感纪实,更有飞扬于精神世界的艺朮想象。
陈毓是一个观察生活细腻,情感体验丰富,既有西方现代主义的眼光,又有中国传统小说情愫的作家。她的笔简神丰,得益于她缘情写景,记事抒情,得意忘形,诗化生活的艺术才华。
四
严格的说:陈毓是一个诗人。她的许多作品是用诗的构思,诗的立意,诗的造境写成的。她的作品有激情万丈的丰富想象,又有人文主义的终极关怀。她在流浪汉的世俗生活中摄取小说的人性、人情、人欲、人论的情感,在花前月下的审美生活中提炼小说的空灵、虚静、洒脱、放达、诗意。她把写实和写意,传统和现代,立象和尽意,简笔和丰神,用诗的情感和意绪凝结而成。她把诗的空灵、跳跃、节奏、意蕴、蒙太奇等手法和技巧运用到小说创作之中。这种特征表现在语言方面是简捷而明快,雅致而蕴藉,灵性而纯真;表现在情节方面是收束而跌宕,别裁而意蕴,率直而整体;表现在人物性格和心路历程的揭示方面是缘情写境,比兴喻理,言外有意。
陈毓小说创作中的空灵、虚静、放达,是诗化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站在垃圾、水泥、血腥、暴力、污秽、色情、野蛮、世俗生活之上遥望人类精神文明灿烂星空的高远之思,是移情化物,超乎象外,凝神聚意,经营意境的放达手段。她的空灵来自思想的活跃,高蹈,情致的虚怀若谷;她的虚静来自情感的淡泊、闲适,意绪的超凡脱俗;她的放达来自心灵的自由、渺远。
总之,陈毓的作品温馨、阳光、细腻、通脱、清新、虚静、灵动,现代、洋气,在中国当代小说表现现代都市生活情感中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