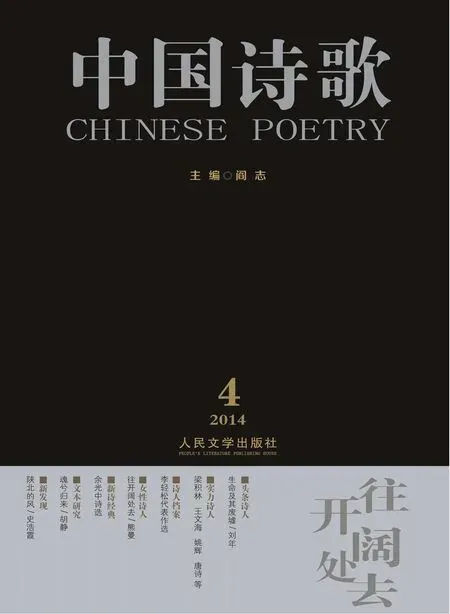盲人替黑暗抚摸了世界
□江雪
盲人替黑暗抚摸了世界
□江雪
盲人替黑暗抚摸了世界
我替自己抚摸了爱情
——李轻松
一
任何了解诗人李轻松的朋友和读者,应不会否认她日益迸发的写作激情和才华。十年来,轻松发表了长篇小说、音乐剧、散文随笔集、诗集等。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十年中又能做多少事?李轻松给我一个惊喜的答案。说严重一点,我感到震惊。在她同时代的女性诗人中,我还没有发现一个能在十年内迸发出如此之大的文化能量和写作激情的人。她是一个特例,也是一个奇迹,她就是诗人李轻松。
二
第一次认识李轻松是通过书信的形式。记得是在1994年,李轻松出版了一本诗集《轻松的倾诉》,没想到她寄赠给我,我很喜欢那本诗集,因此多次向身边的女友推荐轻松的诗,没想到,一个叫潘岩的女孩喜欢上了轻松的诗,结果我忍痛将轻松的诗集赠给了潘岩。我和李轻松失去联系几近十年,前不久竟在平行诗歌论坛里相遇,甚是高兴。更没有想到她说曾在某一年,来到武汉找我,因我多年的深居简出,她最终没有找到,想想也是一件遗憾的事。近期,她给我寄来了她几乎所有的新旧诗作,我深感荣幸和阅读上的快意,终于能较全面地目睹“轻松诗歌之现象”,我为她近几年创作数量之大,创作领域之广,创作激情之高,而深感震惊和喜悦——她,还是不是从前我从书信上认识的那个李轻松呢?作为她的读者和朋友,心里自然会有一个很明朗的答案。这个答案就在这篇文字中,来回穿梭,就像李轻松“风中的蝴蝶”,只不知当你作为此文的读者时,是否愿意去抓住它。
这个冬天,我时常躺在床上,在午夜的音乐声中阅读着李轻松的诗。湖北的冬天,有着不同于北方的寒意,但这个时节,读着李轻松充满激情的诗作,内心不免也会涌起中年的思绪,来自诗歌的温暖。诗歌于李轻松,她是有足够的资历和诗质赢得话语权的。或者说,李轻松是一个被遮蔽了很久的诗人,或许是因为在她的同龄人中,另一些女性诗人如翟永明、王小妮、海男、唐亚平、沈睿、虹影、伊蕾、张烨、马莉、唐丹鸿等整体的张扬与突出,而一向很低调独立的轻松便落寞在她们的光环之下。时过境迁,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轻松的诗,与她们作一个比较,她决不是一个落伍者,她们是可以平行的。尤其近年,我发现她的诗作越发走向大气,进入深度空间。她当下的诗歌作品,在我看来更多的是来自内心的经验和神意。
以前我读到的是李轻松十年前的作品,写得细腻、幽思、轻逸,但是又不乏克制和写作上的警醒,甚至如果你不知道李轻松是位女性,作为读者的你,是很难从作品中猜测出作者的性别的。说到这里,我并不强调性别写作有何区别,但是在事实中却存在女性写作的主体特征,这是大多数女性写作者共有一种心理征象和生理征象。我个人喜欢阅读那种在写作中消失性别旨意的作品,因此我喜欢读李轻松的诗。至今,我尚未能完整地阅读李轻松的小说,但是我知道她的小说十分畅销,在网上可以查阅。作为通过诗歌结识的朋友,我可能更看重作为诗人的李轻松,而不是剧作家或小说家的李轻松。事实上,我也只是她诗歌上的读者,因为这些年的安静独处,导致我很难看到李轻松创作的那么多优秀小说和改编的电视剧,在此也想请李轻松谅解我的不在场。当然,若有可能我很想阅读到她所有的小说,补上这一课。
三
“盲人替黑暗抚摸了世界/我替自己抚摸了爱情”,我很喜欢李轻松的这两句诗。甚至我认为这两句诗可以概括李轻松的整个诗歌创作的心路历程,或者说,我们作为个体的人,在这个世界面前,永远是一个长着眼睛的盲者角色。李轻松抚摸到了一个内心真实的世界,她感受到来自她的世界里的理性之光和激情之火。她把这些光与火,变成了轻松牌现代诗行。
用某一个词,某一段话语来全面解读和统摄李轻松的诗歌,是很困难的一件事。综观李轻松二十多年的诗歌创作历程,可以看出,她的写作一直处于变化中,涌动中,自我颠覆中。她前不久给我寄来她在2000年出版的诗集《垂落之姿》,洋洋五百余页的诗集。一次能出版如此厚重的诗集,在国内女性诗人中是绝无仅有的事,让我着实有些震惊。对于李轻松本人来说,这是她一部个体心灵史,一个征象,一次纪念,是对过去十五年的写作历程进行果敢的诀别。潘洗尘在诗集的序言中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整个九十年代的诗歌评论界对李轻松及其《垂落之姿》或者是李轻松整体创作的漠视是让人无法原谅的,这也许是历史都承受不起的遗憾,我无法想象与那些得到过太多溢美的平庸或垃圾般的诗作相比,李轻松的创作所受到的漠视是幸还是不幸。”反而言之,潘洗尘的这段话在我看来,决不是对轻松的溢美之词,是一种痛,这种痛,甚至还在延续着。在今天,我更愿意把李轻松视为一个诗歌时代的幸存者之一。
理解一个诗人比阅读其作品更重要。作为李轻松的诗歌读者,如果对她的个人生活、日常理想和思想观念等有较为全面的了解,那么对于一种自愿的阅读来说,无疑是有益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作者与读者在抒情愉悦过程中合二为一。李轻松说过这样一段话:“也许没有人比我写得更诚实,更直接,更勇敢!只是我无法不让自己真诚地生活与写作。我用笔来表现我生命底层的困惑、欲望、存在着的种种可能,它是最本质的,最激动人心的。我至今都无法放弃这种状态。”这种写作中出现的困惑状态和“不放弃原则”不仅仅是李轻松拥有,更多的写作者也会拥有,甚至更激烈。社会时态、心灵历程、诗学理念等因素,最终会导致诗人,在某一个时期出现诗义上的失语,这种失语会让诗人陷入痛苦与反省的回流中。
四
女艺术家林天苗在一次访谈中,谈及艺术中的“女性化”问题:“女性作品分好几个层次。有一个层次因为自己是女性,所以她要告诉别人她是女艺术家。比如用自己的生理特征来做艺术,用月经、生殖器告诉别人她的观念。我觉得有些人做得好,我很喜欢,就我本身而讲不太喜欢这么做。还有一种人,她做东西你完全看不出她的性别,她的语言方式跟男人一样。还有一种女性,用她自己的感觉和生活经历去做作品,用她的个人方式来关心和发现”。在诗歌中,同样也存在女性化的问题。
李轻松本人是如何看待“写作性别”的呢?她说性别不应该成为一种标签,更不应该成为一种障碍。她从来没有想过性别与写作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从李轻松的所有作品中,确实可以看出这一点,也就是说她在作品中无意识地消解了“写作性别”的存在。她同时也反对那种有意识的“无性别写作”,她回避那些“性别歧视”和“男性意识”以及“女权主义”的问题,更多的是只让自己的作品来说话,来告诉读者,真正的写作应该是一种“自然流露”,是一种共通。因此,在我的眼里,轻松是一个自觉者,一直从一个女人生命的本质出发,“从不约而同的男性视角形成的话语霸权中”(李轻松语)找到“她们”的权利和自由。
五
从李轻松的访谈录中,我得知她曾在精神病院工作了五年(20岁—25岁)。李轻松的这一段经历,让我十分感兴趣。或许是这个领地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我多次想去这样的地方探访,一直没有机会。我个人总觉得人生中有过这样一段生活或工作经历的人,应该是有福的。我甚至渴望和这样的一群真正的“癫狂者”(福柯语)生活在一起,就是不能如愿。或许有一天一切将会成为可能。李轻松说那五年对她一生来说,很重要,我能理解。李轻松有福了。李轻松在访谈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那时)我就住在病区里,仿佛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那是一座百年墓地,到处都是白骨和飘浮着的幽灵。我又恐惧又迷醉,在那种碰撞与交流中到达过别人无法到达的地方。我们常人的幻想永远都赶不上他们的想象,我们的思维也永远赶不上他们的速度。我每天在精神病患者歇斯底里的喊叫声中开始写作和恋爱,这使我苦闷的青春有了细小的呻吟和回答。我觉得诗歌与精神病有些相通的地方,它使我对弗洛伊德的阅读并不是停留在表面上,而是可能比弗洛伊德更加丰富。”
李轻松的经历让我想起才华横溢的80后诗人苏瓷瓷。她也在精神病院工作和生活过一些年。近期她创作的大量诗歌充满激情和张力,想象力极为丰富大胆,呈现出一种难得的原生态写作,在国内诗界引起震动。我又想起北京诗人食指。一些朋友想让他离开精神病院,重新回到朋友中间来,回到现代生活中来,可是那时诗人不愿意离开他生活了几十年的“流放地”。我想或许是因为食指的身心早已经迷恋上了那种生活状态,他那种多年形成的精神生活时态和淡泊生涯让他更容易与世界达成和解,更容易接受这个虚无世界。
六
李轻松早期诗歌创作量十分惊人,她在《垂落之姿》中进行一个较为清晰的梳理,对早期个人诗歌创作的代际,作了一个划分,分别是1985—1988,1989—1992,1993—1995,1996—2000。她的划分是合理的,只有她本人能清醒地认识到诗歌写作中遭遇的飞升、喜悦、激情、梦想和瓶颈。《垂落之姿》一书,无疑是对个人的一个写作时代的告别,也是对过去十五年的诗歌写作的纪念和诀别。不管这本诗集自身如何,它对研究李轻松的诗歌风格的演变和升华,是极具参考价值的。从该诗集中可以透视出轻松个人早期的诗歌理想,以及她十多年来在诗歌写作上走过的一段不凡的历程,因此说,这是一本很重要的诗集,它的重要更多体现在其完满性、纪念性和真实性上。
在我八年前阅读《轻松的倾诉》,八年后阅读《垂落之姿》时,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李轻松的诗风变化让人吃惊。在《垂落之姿》中既可以看到女性的柔美、温婉、细腻、低迷、幽怨,更多的却是一种冲出栅栏的激昂、游走、裸露、隐忍、香艳,更多的是内心的飞翔、欲望、激情、暴力在诗思中涌动,甚至我能读到一种来自人体中的血性。我试图甄选李轻松几个不同时期的诗歌片断,来表达一下我个人对李轻松诗歌的领悟:
有谁独对暮色歌唱啊?热爱你的人
在歌声之外。用旋律抚摸你的头顶
用水浸透你。暮语沉沉:
回头不回头同是一种过程啊
——《独对暮色歌唱》(1989)
这幽闭而蜷曲的河蚌,我将对谁展开?
双手解开河面的微风
我裸露到什么程度,才能了解
我自己的珍珠,是不是沙石
——《宿命的女人与鹿》(1993)
这浓重的绿色带来了冰凉
这春天!我的身体里裹着一股凉气
触手都是血腥与芳菲
——《血腥与芳菲》(1997)
以月光为栅栏,缩回伸出的手
一种姿势注定我们的失败
红罂粟的惨剧正在上演
而我们已从春天里经过
我们头顶的槐花正被风吹落
——《香气徘徊》(1999)
李轻松在表达个人内心的情感与感受时,是大胆的,没有“隐秘”可言,她更寄语于诗歌,让自己在诗歌的迷宫里,充当一个带着梦想与激情的言说者。所以,她裸露,她表达,她要让你听到一种不一样的呼吸声:急促,回落,带着黏性和血性。因此当你读了传统抒情诗人的诗后,再阅读她的诗作时,你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心灵震撼:这怎么会是一个女诗人写出来的诗歌呢?!
“暮色”,及由其派生的词,在现今的一类诗歌中较为盛行,尤其是在“草根派”诗人的语境中频繁出现,可是李轻松却在十多年前就已经“独对暮色歌唱”了。然而李轻松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草根”诗人,她更多的是一个“追问者”,从她的诗中我甚至能读出她的“弑情”。在她的诗句中,叹号与问号出现的频率是相当高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李轻松在表达诗人内心的真挚情感上,她是不吝啬,不节制的,是豪放的、血性的。如今,确实也有不少诗人提倡诗人应该走向内心,走向节制。事实上,我也发现,从前有不少崇尚节制的诗人,现在退出了诗界,或走向了隐遁,另外有不少诗人出现大面积的失语,被自己规避的诗歌语言方塔逼向死胡同。不难看出,这些年她一直在构建属于她的秘密通道,她的迷宫。我们要想了解裸露心灵的诗人,必须试图打造一把钥匙,去开启他们的诗歌之门。
七
词语情结在每个诗人那里,都会有。一个诗人没有自己独特的词语情结和写作语境,就难构成其鲜明的诗歌风格。正如诗人们一提到“麦地”,自然就会首先想起海子;一提起“暮色”我们首先想到的诗人是杨键;一提起“回答”我们就会想到北岛;一提起“老虎”我们首先就会想起博尔赫斯。这种词语情结,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诗人的诗歌写作标签,也是打开诗人的诗歌之门的一把钥匙,顺着这把钥匙,我们可以探索到诗人内心深处的隐秘之光。
李轻松在访谈中多次谈到诗歌中的词语情结。在李轻松的诗歌中,我们不难发现“桃花”一词,是她早期诗歌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隐喻。李轻松说:“很久以来,我对桃花陷入一种不可名状的迷恋之中。我觉得世上再也没有一种东西可以像桃花一样,把所有的美与凋谢、灿烂与飘零、瞬间与永恒,甚至青春与死亡、快感与羞耻表达得那样淋漓尽致。所以我一再地写到她,一直写到厌倦为止。……我是不知不觉中就陷入到这个诡秘的美感之中的”——
“夜里的夹竹桃被风吹得迷乱”(《追问》),“桃花是开是落我都沉默”(《桃花三月》),“一只桃子在皲裂的伤口上涂抹”(《悠然于外》,“你吸吮我的时候,我千年的叶子已香烂如泥了”(《失血的桃子》),“我的目光里隐含着桃色/这干净的桃色,染上了从古到今的卑微/让我不敢叫自己是桃花/不敢在桃花的汁液里/把我用爱情染红”(《底色》),“樱桃般的微笑转瞬即逝/她身带的咒符无能为力”(《在音乐中倾听》),“我是这样地用尽了自己……它落下,比白还浅/比灰还灰”(《樱桃!樱桃!》),“有一种香气持续不断地送来初秋的风/……/如此强烈地伤感。一支歌飘来/像午夜游荡的灵魂/我已然说不出什么/渐渐沉入的黑暗渐渐地淹没”(《核桃上的血》),“……香气与血构成了桃花的凉气/我们情欲的凉气,蜷伏在一个出处/一场雪正漫过我们的牙齿/找不到与之匹配的笑意//回到我们原始的美德里/回到桃花的红色里,回到/隐痛与剧痛之间。没有什么邪恶/比这杜撰的血腥更有力!”(《杜撰桃花》)
从以上这么多的诗句中,人们没有理由看不到李轻松倾心于桃花的个体情怀。李轻松写桃花,写出了她内心世界的激情、火辣、香艳与卓绝。在众多写桃花的诗歌中,我很喜欢《杜撰桃花》和《红桃》二诗,请允许我在此大篇幅地引述《红桃》:
“……/像整个夏天阴雨连绵/我的身体被腐败的气味渍酸/奶水充盈与蔓延//曾经比水直接,比水极限/比风雨来得清澈/鸟群之上的风声顺水而去//这纯棉的衣衫、纯棉的爱情、纯棉的心/一颗脆弱的红桃,香气若有若无/使我在一次迸裂中愈合/重陷入又一次的破碎//当她被吸吮被压榨被蹂躏/当她赤裸/谁在尖锐的胴体内反光/谁耻辱的心露出腐败?//原来我用自己的生命谢罪/用红颜抵押,以美色行乞/以夜里漂浮着窒息的钟声/来说穿这一只核桃的忠贞//这种损伤,暗含着神秘的砂器/使我莫测的血流更加错乱/满含沙砾的眼睛,疼痛与衰竭//我怎样涂抹那些桃子上的/一种火与绝望的气息,那种命运/与香,我不能描述”。
八
李轻松在九十年代中期能写出大量如此优秀的个性诗作,是十分难得的。她的风格在当时国内诗坛是不多见的,而且李轻松甚至更早地写出了不少大胆表达个人情感的情色诗歌,这在当时是需要非凡的勇气和诗歌精神的,很多女性诗人做不到这一点,但她做到了,只是当时没有引起国内诗坛的重视和关注:“……这样的时刻请拥紧我/直到我的身体动开:吸进我的身心,不够!/吸进一个世界,还不够!/我胸乳微颤的鲜花,鲜花中的笑意/都是这样地感动你/我们浸在莫名的水里,一浮,又一浮//谁触到了我的根蒂,像触碰大海……”(《缚者的微笑》)多年后,中国诗坛才先后出现了像唐丹鸿、尹丽川、巫昂、春树、小蝶、苏瓷瓷等一些优秀的敢于抒写个人情感的女性诗人。
如果说李轻松2000年以前的诗歌创作更多的是关注个体精神当下状态,带有一定的愤青色彩,那么2000—2004年的写作,则明显出现了写作界面、技巧和思想领域的拓宽与飞跃,出现了诗义上的“他者”,逐步沉于大气和理性。正如她近年说过的话:“写诗就是保持心灵的相对纯洁与完整,就是对自己的一次拥抱。诗使我与神秘的事物不期而遇,使我获得那种突如其来的惊喜与意外之美。我将从对自身生命的专注中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向朴素、自然、平静回归”:
生活比我想象的单纯
一场好戏就要开演,而我一直没找到位置
我因而有了一个双重的身份
就是从这个门进去,从另个门出来
我就不再经过原来的自己
——《行走与停顿,2004》
九
李轻松近年在创作大量小说和剧本之余,创作出的大量诗作,无疑受到来自小说和戏剧的影响,这决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写作现象。由诗歌向小说、戏剧、电影转型的现象,国内诗坛上已有多人,比如朱文、韩东、邹静之、邱华栋等。从李轻松近期的诗歌中可以发现,她开始将小说中的一些技巧运用到诗歌作品中,这是值得肯定的。比如元叙事、解构、白描、陈述、场景穿插等,类似这种风格的作品有不少,如她2003年创作的《脱衣秀》、《夜生活》等,2004年创作的《在黑龙江边听“伊玛堪”》、《在山西遭遇暴风雨》、《在江上》等。我个人很喜欢《对“威拉咖啡馆”的叙述》(2004)一诗。《威拉咖啡馆》是意大利的一部戏剧,李轻松深为此剧而震撼,并在《南方周末》上开辟的专栏中写有另一个随笔式的版本《威拉咖啡馆》。我们不妨将此文与上面的一首诗进行一次比较阅读,比较之后,足以窥见李轻松深厚的写作功底。李轻松因为现在卷入小说和剧本的大量创作,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影视和歌剧。这些诗人平常难以亲力亲为的文化视野,对她今后的诗歌创作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也应该成为轻松诗歌写作上的一个独特优势。
十
从李轻松的诗集《垂落之姿》以及2004年以后抒写的诗作来看,李轻松多次通过组诗的形式来表现诗歌题材,且写出了一些较为成功的有影响的组诗力作,比如《游离之姿》、《穿越》、《以我虚构的水》、《伤心太平洋》、《清水洗尘》等。这里我想就她的近作《清水洗尘》来解析一下她的组诗意象与结构。组诗《清水洗尘》由《一顿早餐》、《夜生活》、《来杯茶》三首诗组成。
一顿早餐,对于一个日常主义者来说,是很平常的,可有可无,但也可活生出精彩与情趣。李轻松在“一顿早餐”中顿悟出人们忽略看得见的“早餐”之外的思想与精神之重。“我忽略早餐有二十年了,那时我年轻/贪睡早觉,晨光总是透过一些缝隙/照在我的皮肤上,感觉就像一杯奶”,但是在李轻松看来,“我并不感到空腹。走了那么久/除了词语在慢慢地简化之外/脂肪和日子一块堆积,覆盖了空腹的寂静。/是哪里飘来了炸果子的香味?/我撩开窗帘,感到比牛奶还要香。”李轻松试图通过诗体语言来警醒那些生活在物欲中的人们,应该时刻学会在生活的镜子面前擦拭自己的影像:“从一顿早餐开始/学会应酬、做作,无聊的思想/像酸辣汤那样败坏自己”。诗人的神经与视觉永远是敏感的,容易在时代诉讼和情感诉讼中受伤,并且得到一种诗意的安抚,“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坚硬地刺伤了我”。于是,她想表达她内心对这个不平和的世界赋予的紧张与不安:“吃是一种暴行,在毫无知觉中/一把刀切开了蕃茄/而我还有滋有味地喝着那血/直到我的嘴唇被染红指甲细长/像一个妖冶的女兽”。
从作者写作《清水洗尘》组诗的时间来看,李轻松应该正在北京,此时也正是她的文学创作走向辉煌的时候,声名鹊起的时候。她从一个城市漂泊到另一个城市,那种文化精神上的漫游和现实生活的起落与上升,让她在沉浸于都市繁华中时,产生一种独特的灵魂自我救赎方式,那就是在创作小说和剧本之余,决不丢弃诗歌梦想,让心灵的深处继续葆有年青的丰满、娇艳和诗思。《夜生活》一诗,正体现她的如此心迹和生活历程:“我到底有什么障碍?我的心理/爬满了蚂蚁。那些灯火装得像盲人一样/那些酒杯无耻地交换眼色/还有那些身体,像一些杯中物/被什么摇晃剥光不留一丝痕迹”。诗歌结尾部分是对全诗的一个提升:
这来自城市的神经,这涣散的夜色/经过了多少手的抟制?/变得如此怪异。之于视觉/它有点含混。之于味觉/它有点怪味。我的手只能悬在空中/带着残存的骨头,抓住什么。
整体上说,这三首诗的语调在李轻松的诗作中,是较为舒缓的,尤其是第三首《来杯茶》,其意境安然于物我两忘之间:“在清风明月的夜晚/约上一二知己,闻一闻茶香”,“我见过了太多浓郁的事物/比如咖啡、酒,隐在时间背后的刀/比如油腻与污垢,沉积在我的胃里/还有那些强暴的手指/扼杀了我的平静/我需要透过一些清淡的物质/重新映出自己的面容”。可以这么说,这组诗明显地表明李轻松的诗风开始出现重大转变,走向澄明、宁静、大气。这种转变无疑与李轻松近年来的生活场景和涉世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我再也不能纵情狂奔了/经不起伤害,破坏与损毁/甚至经不起一死”,“我曾经那么尖锐,几乎是刀刀见血/危险纵容我撕开/禁忌成为我的快乐/鸡蛋里生出骨头/而最先中刀的往往是我自己/疼痛因此如此刺骨”。可以说,这首《来杯茶》较为清晰地表现了诗人回首往事时的内心真切感受:“让我收起那些锐器吧,让我学会喝茶/用清水洗脸。学会跟自己说话/炒菜、煲汤,避过一些危险的瞬间/那些平淡的事物,正渐渐地显出它的力量”。
我甚至从李轻松这组不大起眼的组诗中,读出了心灵的感动,读出了时代赋予我们的困境与困惑。她借助于诗歌,道出了一批在沉静中写作的诗人的心声、自省与励志,我真诚地感谢李轻松。
十一
写到这里,已是深夜两点。
这个城市在安详中,透露着她的迷狂和安息。我突然又想起了李轻松的那几句让我彻夜难忘的诗句,就让它作为新年的钟声,在这个城市上空敲响吧:
…………
让我把底蕴放在暗处,无人能见
让我浮出水面的那部分,洗尽铅华
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微笑
说出弥漫这个时代的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