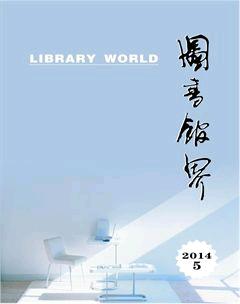嘉庆六年影宋刊本《尔雅郭注》研究
[摘 要]《尔雅》是中国较早的一部字书,流转千年,有众多注疏版本传世,晋郭璞的《尔雅注》是《尔雅》注本中最为精良、流传最广的一个本子。嘉庆六年曾燠从曹文埴处获得佳本予以影刻刊行,本文着重对这个版本的《尔雅郭注》进行初步的探索,主要分以下几个部分进行论述:引言、嘉庆六年影宋本《尔雅郭注》版本情况、避讳问题、校勘初探、结语。
[关键词]尔雅郭注;嘉庆六年;研究;版本;校勘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 引 言
《尔雅》是中国较早的一部字书,主要用于阐释字义,训诂词语。同时,它又是一部百科全书,涉及到古代人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祭祀、器物、天地山川、鸟兽虫鱼等方方面面[1]。从古至今出版了许多不同版本的《尔雅》以及关于《尔雅》的注、疏等书。
《尔雅》的成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流传的版本非常多,并且杂乱,篇目不定,正文偏差,但随着时间的演进,《尔雅》篇目、篇次,正文渐趋稳定与归一,形成了目前三卷十九篇的现状。东汉之后,郭璞为之作注。当然,东汉至西晋的百年之间,已有刘歆、樊光、孙炎等人为《尔雅》作注,这些人所做之注被郭璞认为“犹未详备,并多纷谬,有所疏漏”[2],已散佚。《尔雅郭注》遂成最为通行的注本,成为雅学史上最重要的基础文献[3],后人亦在此基础上再为注疏,成为《尔雅》研究必不可少的部分。
2 嘉庆六年影宋刊本《尔雅郭注》版本演变及版本情况
《尔雅郭注》经由历朝历代不断抄写、印刷、刊刻、影抄之后,版本情况异常复杂,唐宋以前,雕版活字印刷之术尚未流传,因此揣测此时的《尔雅郭注》多以写本传世,诸如唐写本《玉篇》残卷。既为写本,多以孤本或者少量抄本传世,不能像印刷本那样可以批量生产。由于数量不多,流通不广,所以容易散佚。因此,现在多不见有《尔雅郭注》唐宋以前的写本传世。唐宋之时,雕版、活字印刷术兴起,这为图书的批量流传奠定了重要基础。到了宋朝,雕版印书已广为传播,且刻印技术日臻成熟,应用的范围也大为扩大,此期之刻本精良不苟,纯青质朴。元人又加影钞,流传至清,嘉庆六年影宋刊本《尔雅郭注》即以元人影写之本为底本,又加影刊发行。
明清之际,影抄旧本甚为流行,仿宋元影刻之风盛行,清乾嘉之时尤盛[4]。当时许多藏书家诸如顾广圻、张敦仁、汪阆源、赵怀玉、孙星衍等都加入了这一行列,此期影抄了许多宋元刊本图书,大多为精品,嘉庆六年两淮都转盐运使南城曾燠刊刻的影宋刊本《尔雅郭注》为此期之精品。
嘉庆六年影宋刊本《尔雅》之名,在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馆藏的封面仅注名为“尔雅”二字,六孔线装,下标册序,封面钤“贵”字,每册书前页皆盖“木村浩吉寄赠本”,书内有“京都大学图书印”印记,另钤盖藏书印及私章数枚,盖为清朝传日之书。在道光燕山阎氏德林藏本的封面题名为“尔雅图”,四孔线装,此书扉页有大字篆字“尔雅音图”四字,左右有“嘉庆六年影宋绘图本重摹刊”“艺学轩藏版”两列小字隶字。书前载藏书跋语,语后起钤藏书印“德林和印”“二十四琴书屋”。亦有藏书名为“影宋钞绘图尔雅”者,各书品相、封面颜色、装帧有所差异,由此可知此书封面之名可能不统一。
此书为一函三册,线装,纸本,黑口,双黑鱼尾,版心中镌“尔雅”及其卷次。分上、中、下三卷,下卷又分前后两卷,实四卷,每卷卷末均镌刻一列小字“秣陵陶士立临字,当涂彭万程刻”。其中,《释诂》至《释亲》无图,中、下卷诸篇有图,图皆细线工笔,刻画不苟,惟妙惟肖,每图右上角皆有标注,白框黑底,白文名之。注和音夹入正文,注即是郭璞所作之注,注音采用反切、直音的方法,在注音之时往往夹于正文之中,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书前载郭璞所作《尔雅序》一文,半叶八行十三字,字体有颜意,浑厚大气。随后付曾燠文《重刊尔雅音图叙》,此文字较《尔雅序》,字体略小,半叶九行十六字,字体与前者殊异,略微娟秀,颇有柳风,瘦硬挺秀。正文字体愈小,半叶十二行二十字,小注与音双列,半于正文,字数相同,字体清秀舒展,揉颜柳之气。此本为曹文埴所藏元人影宋钞写本,后赠曾燠,孙星衍、张敦仁皆见而誉之,并嘱曾燠以广其传。书中所载之图百余幅,由清代著名工笔画家姚之麟摹绘。该书开本阔大,写刻精绝,由江南名手陶士立临字,彭万程刻字,艺学轩藏版,艺学轩盖为曾燠藏书之地。此书集书、注、音、图于一体,又为当时名家绘图,名手写刻,专家藏书校勘并与刊行,可谓精良之本。
这个版本的《尔雅郭注》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其原因之一在于参与此书刻印的人多为当时名家,他们刊刻了很多精美的本子。诸如陶士立,秣陵人,清嘉庆十一年藤花榭刻本说文解字,即由此人临字,书工精美,柔和颜柳书体之特色,颇具馆阁之风,对此书而言,隽秀的书体无疑为之增色不少,使之不仅是一本小学读物,更像是一本艺术佳品。刻工彭万程与清四大刻工之一的刘文楷共同参与刊刻了清嘉庆丙寅顾广圻覆刻明吴元恭刻本《尔雅注》。这个本子的插图部分仍然采用的是姚之麟的绘本,可见其本之佳。由此也可推论,当时,一图可用于多书,此图亦为传世的尔雅附图中最为精美的插图,后来所印之书多采用此图,线条细致不苟,工笔别致,画面栩栩如生。
再观此书之印刷,墨色浓郁,清晰匀称,经久流传不失其神,精美绝伦。同时,书籍的流转、校勘、刻行皆经于其手,以藏书来论,其流转脉络清晰而有价值。又此书校勘之精良,所选底本为宋元佳本,又经名家校对而后刊刻,所选注音,书前曾燠已做考证。此本《尔雅》集诸家之成,底本、校勘、刊刻、印刷等俱是精美,并不逊于宋元诸本。
3 嘉庆六年影宋刊本《尔雅郭注》的避讳问题
避讳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风俗,大约起自周,成于秦,盛于唐、宋,明、清避讳尤严[4]30。《尔雅郭注》流转千年,版本情况复杂,影本所跨时间较长,致使此书底本情况不甚明了,即所影刻之原书所用的底本不明,传承关系复杂。再者宋朝至清代,文字用字尤为讲究,政治管制更加强烈,在书籍的写作、刊刻、流通领域尤为注重用字的避讳,所以其避讳问题亦是复杂难辨。是忠于原本,一丝不动的影刻下来,还是要为避今讳、或者校勘之故而改动若干字眼?本书底本为元代影写宋本,而本书又刻于清嘉庆年间,三个时间点为宋、元、清,而宋、清两朝对文字的管辖极为严格,很讲究避讳,元朝稍弱,但不应遗漏。宋讳,元讳,清讳三者在本书中杂糅,因此难辨。
宋朝避讳情况复杂,胤、敬、驚、朗、桓、恒、弘、玄、殷、匡、真、禛等字在不同时期的避讳情况有所不同,但皆以缺笔之法行避讳。清朝的避讳字多为皇帝名字,诸如玄、弘、胤、禛、颙、琰等字,从这些避讳字可以看出,宋清避讳字有不少重合,因此在这本嘉庆六年影宋刊本《尔雅郭注》中的避讳字的问题就涉及到了很多方面,从避讳现象来看,几乎分辨不出避的是宋讳还是清讳。而又有一些问题是避讳字中夹杂了宋、清两代的避讳,而在刊本中又不是完全的避讳。比如按照宋朝的避讳情况,敬、驚、殷三字是应该避讳的,而在嘉庆六年影宋刊本《尔雅》中这两个字是避讳的,但是宋讳的其他字诸如恒、桓、匡等字又是采用缺笔的方法来避讳的。又如“禛”字,在这本书中不加避讳,而在影宋监本《尔雅郭注》中是缺笔避讳的。同时,宋、清两朝重叠的避讳字诸如玄、弘、胤等字又是避讳很严格的,所以关键之处在于诸本避讳差异的地方。
从版本来看,此版本为元人影写宋本,清人影刊元人写本无疑,由元至清的流转途径是很清晰的,而元人影写为何本,并不甚明了,敬、驚、殷三字为宋后期的避讳字,遘、禛两字为南宋高宗、孝宗讳[4]32,但是在嘉庆六年影宋刊本《尔雅郭注》中不予避讳,即是原本不予避讳,可以大致推断底本时间应早于南宋高宗时。由前者宋讳,可以得知,影本几乎忠实于原本,几乎是照原样影写而成,而时间推移到了清代,影本犹避宋讳,说明影本几乎忠实原本。因此,从影本及原本避讳字来看,并结合影宋监本《尔雅郭注》的避讳字情况以及版本的书体情况,大致可以得出,此书影写之刊本底本大概出自宋朝前期,当然,利用避讳鉴定古书版本,只能做到大体鉴定古书的版刻时限[5]。
4 嘉庆六年影宋刊本《尔雅郭注》的校勘初探
纵然是写刊精绝,一丝不苟,由于版本流传,雕版刻写等诸多问题,书中偶有错讹疏漏亦是在所难免。本书的主要讹误有以下几个方面:缺笔、讹字、脱文、衍文。
4.1缺笔
造成刻本出现缺笔的原因有很多,在校勘中,大部分缺笔现象宜应保留原貌而不予校出。诸如此书之中,《释言第二》正文中“褊”字缺左半部首上一点画;小注之中“皆”字缺右上一横,这种缺笔现象在此书中出现次数并不多,往往一看便知。影宋监本尔雅郭注以及《尔雅注疏》中都没有类似这样的缺笔。通常的缺笔都是无意而为,多是因失误造成,与版本状况无关。引起重视的应是避讳现象引起的缺笔,避讳与版本的时代紧密相关,匡、恒、玄、弘、胤等字在此书中均以缺笔避讳,在本书中出现较多的缺笔现象往往与避讳相联系,而缺笔大多缺一个笔画,并不会影响一个字的完整性,因此这些缺笔的出现并不会影响阅读使用。
4.2讹字
讹字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外形相似、有相同构件的字出现混淆,以致出现部首等构件的讹误。2)形近义近的字容易出现错讹。3)读音相似而又形近义通的、音近义通字容易出现错讹。
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由于版本情况不同,刻书者在选择底本时的标准也不同,不同版本的用字以及行文有所差异,在校勘未校对出一些字导致错讹。2)在写版之时出现讹误,使之误刻,而后失误。3)误刻之字,即为一个完整的错字。而这些错误多难以分辨哪些是误写哪些是误刻。但显而易见的是,误写之字多于误刻无疑,刻工多依写字而刻,大多不会出现改字等大的疏漏,而以缺笔多见。
诸如《释诂》“讫、徽、妥、怀、安、按、替、戾、底、底、尼、定、曷、遏,止也”中“底”应作“废”字。废,止也,按、戾、替、废皆止住也[2]38,此处无疑,盖为误写所致。前面词条也出现了“底”字,疑误。 “竢、戾、底、止、徯,待也”。“底”应为“厎”,《释文》:“厎,之是反,字宜从一,或作‘底,非也,底,音丁礼反”,厎字为是,所以“底”“厎”“废”三字在这个版本中出现了混淆不清的情况,因其字形相近,读音相近,字义又交叉,所以在校勘时未校对出讹误。
《释亲》“父之考为王父,父之妣为王母”注为“加王者尊之”,注中之“加”误,应为“如”。清嘉庆二十一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为“加”《尔雅义疏》为“如”,有本改“如”作“加”,“加”“如”二字形同易混,又版本不同,难以分辨对错。如,像也,意思为“像……一样”,“加”在此处疑不妥当,应改为“如”字。
《释宫》“垝谓之坫”注为“有堂隅,坫,瑞也”,注中“有”字误,应为“在”。“瑞”字亦误,应为“端”或为“ ”。清嘉庆二十一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为“在堂隅”“端也”。[2]126《论语》:“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6],郑玄云:“坫在堂角”,《说文》:“坫,屏也”,是一种用以放置器物的设备,用土筑成,形似土堆[6]32,置于堂角,因此“有”字错讹,“在”为是。“瑞”字误,“瑞,以玉为信也,从玉耑”[7],从偏旁含义来看,“瑞”字从玉,“ ”字从“土”,“坫”字亦从“土”,“坫”“ ”均有土堆之意,所以“瑞字”应为“端”或“ ”,诸本皆作“ ”,言坫是堂角端也。
《释天》“大火谓之大辰”注为“大火,心也”,注中“心”字误,应为“星”。“心”“星”二字音近,“大火谓之大辰”又“大辰,房、心、尾也”即大辰有三星,房、心、尾三星,“大火”是“大辰”的别名,为星名,即包括“房”“心”“尾”,注中言“大火,心也”从范围上看是不当的,清嘉庆二十一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作“大火,心也”,元大德己亥进德斋刻本《尔雅注》作“大火,星也”。“心”“星”二字在这个位置都有例证,不过“心”改为“星”更为恰当。
《释丘》“天下有名丘五,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注为“说者多以州黎、宛、营为河南……,始自别更有魁梧桀大者五”。注中“始”字误,应为“殆”,邢疏云:“殆,近也,近是更有魁梧桀大者五”,元大德己亥进德斋刻本《尔雅注》、清嘉庆二十一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皆作“殆”。“始”字无“近”意,用于此处不当, “始”“殆”二字形体相近,“始”字讹。
《释草》“荓,马帚”注为“以蓍,可以为扫慧”注中“以”字误,应为“似”。“慧”字亦有本作“蔧”,《释文》曰:“蔧,字又作慧”。清嘉庆二十一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作“似蓍,可以为扫蔧”,释曰:“荓草似蓍者,今俗称蓍荓”。[2]235
4.3脱文
此刊本脱文主要是刊刻之误,同时也涉及到了不同版本版本状之间的差异,脱文的原因往往很复杂。
诸如《释诂》“蛊、謟、贰,疑也”词条下的小注中“《左传》曰:天命不謟,音謟”中,“音”字之前脱一“謟”字,诸本及注疏本皆有此字。“音”字后的“謟”字有本作“縚”“滔”者,注疏本中作“縚”,阮校:《释文》“謟,郭音縚”[2]41。据此,应为縚音。由于语音的演变,直音所用的注音字也发生了变化,所以在这些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字在不同的版本中用于注同一个字音,因而很难说有正误之分,所以对于注音字的校勘应该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活动,其中没有绝对的正确和错误,只有古今时地的区别。
《释地》“大野曰平,广曰原,高平曰陆……”正文中“广”字后脱一字“平”,此词条皆以四字一句,且下句为“高平曰陆”与之相对,清嘉庆二十一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作“广平曰原”,有“平”字,诸本皆有“平”字,此处明显脱落“平”字,无疑。
《释草》“莕,接余,其叶苻”注为“叶生水中,叶圆,在茎端,长短随深浅,江东食之”注中“江东食之”一句脱一字,应为“江东菹食之”,按阮校:“按《齐民要术》卷九引作‘江东菹食之以证菹法,则菹字当有”[2]237,可证此处脱落。
《释草》“蒹,薕”注为“……江东呼为蒹,音兼,薕音廉”,注中“兼”后脱一字“蒹”,以下句可证,句式应相对,即“蒹音兼,薕音廉”,才符合郭注的原则,诸本皆为“蒹音兼,薕音廉”。
4.4衍文
衍文于此本中为数不多,大多存在于语气和连接词之中,诸如“云”“曰”“也”“之”等字,以虚词多见,实词衍的情况极为罕见。因此并不会影响阅读者的使用,不会造成句字之义的曲解。同时在校勘之时,很难确定对错,因此对于这个版本的《尔雅注》衍字的校对应犹为慎重,所本的原则应该是:字顺义通,不必强求语气词、连接词等虚词的完全一致。衍字很少会对句子的结构产生大的冲击,尤其是虚词的衍字,亦是无伤大雅。从数量上看,衍字的数量很少,远不及讹字、脱文、缺笔的数量众多。
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提到注和音夹入正文,注即为《郭注》[8],在校勘时一个明显的结论是,注出现的讹误比正文出现的讹误要多,而注音字和反切字的校勘又存在很大的问题,《尔雅序》中言“别为音图”,即原书有图有音,郭璞《尔雅音义》,宋以后亡佚不存。那么,这部嘉庆六年影宋本《尔雅郭注》所用的音来源于哪呢?而语音是随着历史推进不断发展的,时地不同,音也有所差异,所以不同时期的《尔雅》注音所用的字应该是随着语音成系统的演变的,这在校勘时很难有一个定论。
古书的校勘,必不可少,择善而从,方可获益良多。否则,诚如张之洞所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半功倍。”[9]校勘与研读并行,可以使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校勘宜应广选刊本,诸本之间,相互比对互校,而后可得差异之处,利于校对。
5 结 语
《尔雅》作为小学研究要籍,在我国学术界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位置,雅学也成为儒学、语言学、古汉语等学科研究的重点,嘉庆六年影宋刊本《尔雅郭注》是数千年中所流传的众多《尔雅》版本中的一个版本,可以由一管窥全貌,足见传统典籍的浩瀚深邃。古籍需要保护,同时也需要校勘、流传。古书的流转脉络也是一部文化史,承载着读书人的理想追求。古书的传承与研读,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徐朝华.尔雅今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2.
[2]郭璞著,李传书.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尔雅注疏[M].徐朝华,校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
[3]蒋鹏翔.宋刻十行本《尔雅注》版本源流考[J].图书馆杂志,2011(7):91.
[4]黄毓仪.《尔雅郭注》版本述略[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2):30.
[5]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172.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8:31.
[7]许 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11.
[8]李运益.新印郭璞《尔雅音图》质疑[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8(1),107.
[9]董恩林.《尔雅郭注》版本考[J].文献季刊,2000,1(1):56.
[收稿日期]2014-07-05
[作者简介]张晓程(1990—),男,硕士,上海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