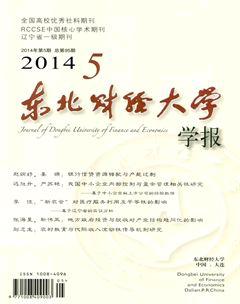农村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性传导机制研究
刘志龙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深入探索中国农村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的内在传导机制。通过双对数代际收入弹性模型得到代际收入弹性为0.689,说明存在代际收入传递固化现象。加入子代教育、教育与父亲职业的交互项及教育与父亲收入的交互项,发现三者对代际收入弹性的贡献率依次递增,由此提出父亲收入与父亲职业通过子代教育产生代际收入传导的两个不平等。引入个体影响因素后,发现其对代际收入弹性系数贡献率很小,排除个体异质性。采用HLM模型将以上两个不平等纳入同一个框架中,发现父亲收入产生子代教育不平等,父亲职业显著影响子代教育回报率,机会不平等阻碍了代际流动。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促进教育机会与就业机会的平等,增加代际收入流动,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
〔关键词〕农村教育;代际收入流动性;教育回报率
中图分类号:F1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4)05-0056-0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放程度逐步加大,一部分人首先实现了财富积累,不同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随之扩大,远离城市的农村显然没能跟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步伐。在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大背景下,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显著。不仅如此,上代的贫困使得子代受教育程度受到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匮乏;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富裕家庭往往利用自身的人脉关系与社会资本影响子代的就业,使得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降低,贫困家庭子代教育回报率下降。以上两点都有可能导致贫困的延续,而农村居民则首当其冲。近年来,受到高校扩招与就业难的影响,“读书无用论”的思想在农村得以盛行。这种思想能否造成“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现象,这使得研究农村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性问题显得十分重要。
一、文献综述
代际收入流动性起源于代际流动理论。早期的代际流动是社会学研究领域之一,它以家庭为观测单位,以父代社会地位(职业地位)为基点,考察子代在同一年龄时的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变动情况。经历了20世纪三代社会流动性的研究自“二战”以来,流动研究先后经历了20世纪 50 年代和60 年代上半期对职业流动表中的流动率进行分析的第一代流动研究、以 1960 年代中期布劳、邓肯将路径分析技术引入地位获得分析为标志的第二代流动研究以及 1970 年代中期以后以对数线性模型的广泛应用、从绝对流动率转向相对流动率分析为标志的第三代流动研究等三个典型的研究阶段。,代际流动的研究方向转向代际收入流动性。而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研究以国外为主,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关系体现在子代的教育获得。教育投资决策主要分为家庭教育投资决策和公共教育投资决策。其中,家庭教育投入表现为家庭提供给子女的教育支出。Becker和Tomes[1-2]最先将人力资本理论运用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微观经济模型中,并给出人力资本在代际传递过程中的理论模型。Solon[3]在Becker和Tomes的模型基础之上加入政府公共支出变量,研究发现代际收入弹性与人力资本回报率成正相关关系,与公共支出成负相关关系。家庭教育投资使得代际收入流动性下降,政府公共支出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Mayer和Lopoo[4]假定贫困家庭面对子代人力资本投资时存在信贷约束,而非贫困家庭则不存在,研究发现人均财政支出高的组代际收入流动性低于人均财政支出低的组17.40%。在无约束条件下,理性的父代对子代进行最有效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子代先天能力的函数,其均衡条件为教育投资等于物质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欧洲大多数研究结果显示,信贷约束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不大,因为欧洲大多数国家属于高收入高福利国家,子代受教育程度不会因为家庭收入多寡而受影响。Lochner[5]认为低收入家庭完全可以在不影响自身消费的前提下通过借贷等形式为子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其次,教育收益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随着教育因素在收入分配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劳动者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个体通过家庭资本投入获取教育积累,最终进入劳动力市场完成收入的代际传递过程。Goldthorpe[6] 按照供给和需求的特征将教育回报分为两部分,即劳动力需求特征与教育收益以及劳动力供给特征与教育收益。Zhong[7]也指出中国、印度、墨西哥及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过度教育现象,过度教育使得教育的市场价值下降。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率成正相关关系。但是,当教育扩张时,人力资本回报率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贫困家庭会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最终导致代际收入固化。
最后,教育与代际收入关系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断代分析法、倍差分析法(DID方法)以及中间变量法。其中,断代分析法需要满足隔代的数据样本,受到数据的限制该方法使用较少。Mayer和Lopoo[8]利用DID方法结合美国收入动态面板数据,研究了政府教育支出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关系,发现政府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提高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实现的。中间变量法在当前研究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关系中使用最为广泛,在双对数代际收入弹性模型中加入教育变量(受教育年限或最高学历)是最直接的方法[9]。由于针对不同的人群,教育中间作用机制与效果可能不尽相同,此时便会出现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非线性作用[10]。郭丛斌和闵维方[11]将家庭收入按高、中、低进行分组,通过在模型中加入子女受教育年限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发现教育有助于低收入组的子女进入高收入组。与郭丛斌和闵维方[14]的研究结果不同,;而Bjrklund等[12]研究瑞士数据却发现教育对高收入家庭的代际传导效果更明显。除此之外,代际收入弹性系数分解法和数据拟合法也经常用于分析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关系。
纵观以上文献,我们发现:第一,各个研究结果均显示出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性产生作用。第二,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相关性存在时间、地区、性别、职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三,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影响的主要来源是教育资本投资和教育回报率。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1.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CHNS)数据。CHNS数据库是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中心与中国预防科学医学院联合进行的大规模社会健康调查。调查内容涉及健康学、营养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等多个学科。CHNS覆盖了辽宁、黑龙江、山东、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和贵州9个省份,迄今为止已经开展了9次调查(1989年、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2006年、2009年和2011年),每次调查访问的城乡社区为200个,每个社区访问20个家庭,共涉及4 000个家庭。CHNS数据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社区调查、家庭户调查、个人调查、健康调查、营养和体质测验、食品市场调查及健康和计划生育调查。CHNS在调查中以家庭为抽样单位,采取了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考虑到该调查数据时间跨度大、区域跨度广、追踪效率高,适合作为本文的应用数据。
2.样本及描述性统计
文中变量主要涉及到农村父子两代的收入变量、子代教育变量和父亲职业变量,其中,父亲为农村户口。在收入变量中,将父亲收入作为父代收入,子女收入为子代收入。在教育变量中,将受教育年限数据进行重新编译,将对应的受教育年限代码换算为受教育年限。在家庭背景变量中选取父亲单位类型为代表,参照Erikson和Goldthorpe[13]的职业等级分类表将父亲单位类型分为四类:第一类包括政府机关、国有事业单位和研究所;第二类包括国有企业、乡镇所属小集体和省市所属的大集体;第三类包括私营企业、个体和三资企业;第四类包括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农业。此外,在性别变量中用0表示女性,1表示男性。具体数据结果如表1所示, 由于篇幅限制,未加入1989—2011年各年的描述性统计,其中,各样样本量分别为310、478、418、366、427、149、127、171、175.样本总量为2 621,性别均值为0.670,说明样本中男性比例高出女性比例34.0%,34%=[0.670-(1-0.670)]×100%。从人口学角度看,该样本存在性别偏差,因此后文可针对不同性别分别回归。子代受教育年限均值为8.727年,该值未达到国家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水平,说明农村子代受教育年限仍然很低,大多数农村子代没有进行素质教育。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必须接受国家、社会以及家庭予以保证的九年义务教育。由于高中、大学及以上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家庭需要其子代进行更多的教育投资。在面对信贷约束时,贫困家庭会选择放弃对其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富裕家庭则不然。
对父亲收入与子代受教育年限做散点图发现:当子代受教育年限小于9时,整个图形呈现
为一个倒立的等腰梯形,子代受教育年限以父亲收入4 105元为分界点均匀分布;当子代受教育年限大于9时,子代受教育年限随着父亲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由此说明,国家强制性的义务教育有效促进了教育公平,此时,父亲收入对子代受教育年限影响较小。而在非义务教育的范畴,父亲收入水平提高时,子代受教育年限增加。父亲收入水平直接影响了子代受教育年限,最终形成了由于收入差距导致的教育不平等。
三、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分析
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主要来源于教育获得和教育回报率的不平等。选用双对数代际收入弹性模型,通过控制子代受教育年限和家庭背景计算二者对代际收入弹性的贡献率。进一步采用多层线性模型(HLM),并将子代受教育年限和家庭背景同时纳入模型中以探究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1.完全竞争市场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
由Solon相关研究[3]可知,子代收入与父亲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与实际的代际收入弹性存在偏差 由Solon(1992)可知b=rlnyi,tlnyi,t-1=b*(Slnyi,t-1Slnyi,t),其中,b是真实的代际收入弹性,b是双对数模型的估计值,而真实地代际收入弹性系数是双对数模型中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值乘以父子两代收入的标准差之比。。通过对各年份子代收入与父亲收入的描述统计得到各自对应的标准差。当标准差比值大于1时,实际的代际收入弹性大于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当标准差的比值小于1时,实际的代际收入弹性小于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当标准差的比值为1时,二者相等。由表2可知,1989—2011年各年的标准差比值围绕1波动,只有2006年的代际收入弹性小于估计值,其他年份均大于回归系数的估计值。
使用双对数代际收入弹性模型,分别对各年份的子代收入与父亲收入进行回归,得到二者完全竞争市场下的回归系数,将其与子代收入、父亲收入的标准差比值相乘得到实际的代际收入弹性,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各年代际收入弹性在0.261—0.639之间波动,各年代际收入弹性变化较大,均值为0.446。使用所有样本的混合数据进行回归,得到代际收入弹性为0.689,即代际收入流动性为0.311。这与Solon[14]使用单独年份的数据可能低估代际收入弹性结论一致。与发达国家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相比,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
2.控制教育、家庭背景下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
经济学中的所有完全竞争市场假说都是理想化的,实际应用时往往不成立。受教育是农村子女改变自身命运的途径之一,对子代本身的收入产生巨大影响。由前文分析结果可知,农村较为富裕家庭的子代受教育年限往往较高,家庭通过对子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使得子代人力资本逐渐积累,并在劳动力市场得以回报。
加入子代受教育年限的双对数模型如下:
加入子代受教育年限后,发现教育对代际收入弹性的贡献率呈现倒“U”型。教育对代际收入弹性的贡献率最小值为1.860%(如表4所示,下同);最大值为23.389%。平均贡献率为8.220%,小于使用全年数据的11.111%。可见,教育变量的加入提高了代际收入流动性。
由于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可能较多地影响贫困家庭对其子代人力资本投资并降低代际收入弹性。而父亲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家庭教育投资不均等会扩大子女收入差距,最终会提高代际收入弹性。由此可能无法得到代际收入弹性变化的真正原因。加入子代受教育年限与父亲收入的交互项可以解决以上问题,此时,双对数模型如下:
Yi,t=c+βYi,s+γYi,sedu+ξ(3)
加入子代受教育年限与父亲收入的交互项之后,得到交互项对代际收入弹性的贡献率。二者的交互项对代际收入弹性的贡献率均值为19.529%,该值小于使用全年数据得到的23.709%。最大值出现在2004年为45.673%,约占代际收入弹性的一半。
这一结论说明,农村父亲收入可能通过对子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一途径使子代收入产生显著差异,父亲收入与子代受教育年限的交互项对代际收入弹性的贡献率统计上显著,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一作用逐渐增强。表4中各自贡献率差值能够反映出交互项的作用比单纯教育对代际弹性的贡献率更加明显,交互项对代际弹性的贡献率大致为后者的2倍。也就是说,近二十年以来,农村由于收入分配不均等导致收入差距逐渐增大,富裕家庭子女与贫困家庭子女由于受教育年限不同而导致了日后收入的不均等,并实现了财富的代际传递,降低了代际收入流动性。
以上分析可以说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家庭对其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成为促进代际收入弹性高居不下的重要因素。另外,父亲职业作为家庭背景的重要指标,可以影响子代教育在劳动力市场的回报率的差异将再次导致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动。
本文加入子代教育与父亲职业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再次得到新的交互项对代际收入弹性的贡献率。由表4第三列可见,以父亲职业为代表的家庭背景对代际收入弹性的贡献率在4.963%—24.864%之间,贡献率均值为11.306%,该值小于由全体样本得出的14.264%。
表4中三组不同的贡献率可以展示出三种代际流动关系。第一列是单纯的教育对代际收入弹性的贡献率;第二列是父代对子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使得子代教育获得产生分层,进而使得子代收入产生差异;第三列是父亲职业影响子代教育在劳动力市场的回报率,从而促进子代收入差距。很显然,第二列的效果强于第三列,第三列的效果强于第一列。
3.代际收入流动性与个体差异
除了父亲收入和父亲职业导致子代收入不平等外,从考察代内收入不平等“明瑟方程”的思想可知,受教育年限、工龄及性别等个体特征也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因此,除了以父亲收入和父亲职业为代表的家庭背景外,本文加入年龄等个体特征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来全面分析教育对代际收入弹性的影响,样本为1989—2011年的混合数据,混合数据主要是将不同截面的数据进行混合,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大样本量,增加估计的精度。建立模型Ⅰ—模型Ⅳ。
通过对公式(4)、(5)、(6)逐个回归得到表5中的模型Ⅰ、Ⅱ、Ⅲ,加入个体特征的影响后,模型解释力度逐渐提高,拟合优度从模型Ⅰ的0.336上升到模型Ⅲ的0.372。模型Ⅰ中加入教育因素的估计方程结果,此时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为0.536。在模型Ⅱ中加入子代工龄的变量后,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为0.522,代际弹性系数变化不大。从子代受教育年限的系数可以看出,学历与个体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加入子代工龄后,子代教育回报率明显增加,说明子代教育回报率依靠自身在劳动力市场的工龄。由于子代工龄二次项系数为负,一次项系数为正,子代工龄与代际收入弹性系数呈现倒“U”型特征,通过计算得到子代工龄在32—33岁之间达到收入的最大值。在模型Ⅲ和模型Ⅳ中加入性别变量后,性别变量前的系数不显著,因此不能判断不同性别的代际收入弹性的高低。由表5中的三个模型可知,加入个体特征变量后,其代际收入弹性系数机会不发生变化,说明与父亲收入及父亲职业等家庭背景因素相比,个体特征因素不影响代际收入的相关性。
由于模型Ⅲ中的性别变量系数不显著,因此考虑对不同性别的农村子代样本进行回归,分别测量他们的代际收入弹性及教育回报率。回归结果如表6中的模型Ⅳ—模型Ⅶ。其中,模型Ⅳ和模型Ⅵ为男性样本对应的结果,模型Ⅴ和模型Ⅶ为女性样本对应的结果。结果显示:第一,儿子和女儿各自对应的代际收入弹性结果变化不大,分别加入特征变量后弹性系数稍有降低。第二,模型Ⅳ和模型Ⅴ中儿子代际收入弹性系数比女儿高出41.743%,说明在农村父亲收入与儿子收入的相关程度比父亲收入与女儿收入的相关程度高出41.743%。由子代受教育年限的系数可知,女儿教育回报率高于儿子,说明农村家庭对女儿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更高。第三,工龄平方项均为负值,说明工龄与收入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男性达到收入最大值的年份早于女性4年左右。第四,加入工龄及其平方项可以提高子代教育回报率。其中,儿子教育回报率由6.930%(exp^0.067-1)提高到13.088%(exp^0.123-1),提高幅度为6.158%;女儿教育回报率由8.112%提高到14.912%,提高幅度为6.800%。说明男性教育回报率略低于女性,而男性通过工龄增加教育回报率的作用强于女性。
综合以上分析,排除个体因素差异,可以得到两条可能的代际传导路径:一是由于父亲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导致贫困家庭子代受教育年限获取与富裕家庭子代受教育年限获取不平等;二是尽管贫困家庭子代与富裕家庭子代有相同水平的受教育年限,二者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的回报也不平等。沿着这两条路径,本文进行代际收入流动的内在机制探索。
四、代际收入流动的传导机制探索
前文对所有回归方程从线性代际收入流动性角度进行测算,得到父亲收入通过影响子代受教育年限对代际收入弹性产生影响。由于平面回归模型体现变量间的直接作用,各个变量的间接交互作用却无法得到,因此无法得到代际收入流动的传导路径和内在机制。为此,本文引进多层线性模型(HLM),并加入父亲收入、父亲职业、子代受教育年限以及子代收入,来探究收入如何在两代之间传导。
父亲收入对子代收入的代际传导作用不仅表现在直接物质赠予或其他物质条件上,更体现在教育和就业机会等的差别。首先,与贫困家庭的子代相比较,富裕家庭的子代教育不受信贷机制的限制。即使贫困家庭的子代与富裕家庭的子代拥有同样的教育,由于父亲单位性质与收入差别,子代教育回报率也不尽相同。因此,教育回报率同样受到家庭环境差异的影响,即存在教育回报率的代际效应。为了研究以上问题,加入父亲收入和父亲职业变量建立多层线性模型。
第一层模型为子代模型:
基于公式(7)和公式(8),采用HLM7.01软件对已建好的sav SPSS数据文件。格式的双层数据集进行建模。给出每层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由于篇幅的原因,两层线性模型的描述性分析未列入文中。,第一层子代样本数为2 621个,第二层父代(家庭)样本数为1 343个。子代受教育程度超过了义务教育阶段;父代样本中有21%就职于政府部门或国企,21%就职于其他企业部门,58%为农民。
利用多层线性模型的描述统计数据,表7给出五个模型,模型Ⅷ为单层模型,即只含有子代信息的模型;模型Ⅸ加入父亲收入变量,观察父亲收入的作用;模型Ⅹ、模型Ⅺ和模型Ⅻ分别将父亲职业作为虚拟变量加入到第二层,观察父亲职业对子代教育在劳动力市场回报率的影响。
模型Ⅷ为单层回归分析,其结果与单纯的OLS结果相等,子代收入与受教育年限成正比且儿子收入高于女儿收入。模型Ⅸ中,将父亲收入加入到性别变量的系数中,很显然估计结果更加显著。此外,加入父亲收入后,性别变量的系数由正转负,且变化很大。说明在农村高收入的父亲会增加女儿的人力资本投资,使女儿收入增幅更加明显,这种变化程度显然超过对儿子投资的回报率。
在模型Ⅹ、模型Ⅺ及模型Ⅻ中,分别在子代受教育年限变量的系数中加入父亲职业。其中,模型Ⅹ的父亲职业为政府职员或国有企业员工;模型Ⅺ的父亲职业为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及私有企业员工;模型Ⅻ的父亲职业是农民。对同等学历的子代,父亲为政府职员或国有企业职员的子代,其教育回报率低于其他子代教育回报率约12.613%(-0.014/0.111)。父亲就职于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及私有企业的子代,其教育回报率高于其他子代教育回报率约62.222%(0.056/0.090)。父亲为农民或小企业的子代,其教育回报率低于其他子代教育回报率约24.324%(-0.027/0.111)。由此可见,农民子女教育回报率最低;政府员工或国有企业员工子女教育回报率其次;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及私有企业工作人员子女教育回报率最高。可以看出:即使农村户口的子代具有相同的年龄和学历,他们的收入差距也非常大,流动性很低,农村子女教育低回报率会挫伤农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这与近几年农村出现的“读书无用论”现象相契合;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推进,就职于外资、合资企业或私营企业(包括企业法人)父代的收入不断提高,通过子女较高的教育回报率将财富传导到子代中去;持有农村户口的政府职员及国有企业员工子女教育回报率介于二者之间,其原因是持有农村户口的政府职员或国有企业职工一般职位较低、收入较少,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国有企业高管或公务员。
通过多层线性模型发现:就个人因素来看,同样持有农村户口,不同职业的居民子女教育回报率差别巨大,以农业为主的农民、女性居民在收入竞争中处于劣势;就家庭背景因素来看,父代工作性质对子代教育回报率影响显著。多层线性模型同时将父代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家庭背景作用于子代收入,结果再次证明:不同收入阶层的父代对子代的教育投资不平等,使得子代受教育年限产生不平等;不同职业类型的父代对子代的就业产生影响,使得子代教育回报率产生不平等。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CHNS数据,采用代际收入弹性的双对数模型测算农村教育对代际收入弹性的贡献率,并应用多层线性模型探索教育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内在传导机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在完全竞争市场下,不同年份代际收入弹性值差异较大,但总体代际收入流动性仍然较低。这说明近二十年中国农村经济结构变化巨大,代际收入流动性在整体上呈现交替变化状态。各年份代际弹性系数均小于使用全部样本得到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值0.689。基于发达国家的实证经验发现,中国农村代际收入流动性不稳定,流动状态较为固化。第二,父代通过对子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使得子代受教育程度产生差异,这种代际传导方式为代际传导的第一阶段。研究发现,单纯的教育因素对代际收入弹性的贡献率较小,而农村子代教育与父亲收入的交互项对代际收入弹性的贡献率为前者的两倍左右。父代收入差距促进子代人力资本投资不平等,通过不同受教育程度产生的回报率实现代际收入的传导。第三,以父亲职业为代表的家庭背景促进劳动力市场的不公平,通过教育回报率的差异,最终实现代际收入传导的第二阶段。通过对比发现,子代教育与父亲职业的交互项产生的弹性贡献率大于完全竞争市场下的弹性贡献率。这说明家庭背景对子代进入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同等教育程度的子代由于家庭背景不同而收入不相同。第四,研究子代个体特征差异后发现,子代工龄与收入呈现倒“U”型。工龄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效果非常有限。在农村,父亲与儿子的代际相关程度大于父亲与女儿,二者相差41.743%。女儿教育回报率高于儿子,在农村倡导男女教育平等有助于提升整体的教育回报率。第五,由多层线性模型从非线性回归的角度,将以上两个阶段的代际传导关系整合在一起。父亲收入通过教育投资增加子代收入,尤其对女儿收入影响显著。父亲职业影响子代在劳动力市场的教育回报率,农民子女教育回报率最低。两个阶段的不平等同时在多层线性模型中得到体现。
由以上结论得到以下政策启示:第一,促进子代受教育平等。与市场规律中的利益最大化不同,教育不存在效率问题而只有公平问题。在机会均等的前提下,增加对农村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共教育支出,减小由于父亲收入差距而产生的子代受教育差距。由义务教育阶段的经验可知,增加公共教育支出提高子代教育的公平性,更有效地促进贫困家庭子代人力资本积累,保证教育成为其往上流动的有效途径。第二,进一步深化劳动力市场的开放程度,消除户籍差异影响,实现就业公平。教育回报率只有在各个部门实现边际值相等时,教育资源才能达到最有效的配置。很显然,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可以促进就业公平,实现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并最终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第三,在实现两个公平的基础上,消除农村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歧视。推进代际收入流动的关键是促进机会平等,增加农村女性的教育投资有效提高总体的教育回报率。同时,促进机会平等有利于推动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增加代际收入流动性,实现收入分配的进一步平等。
参考文献:
[1]Becker,G. S., Tomes, N. An Equilibrium 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9,87(6):1153-1189.
[2]Becker,G.S., Tomes ,N. Human Capital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amilies[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86, 4(3): 1-39.
[3]Solon, G. A Model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Variation over Time and Place[Z].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38-47.
[4]Mayer, S. E., Lopoo ,L . M.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8, 92(1): 139-158.
[5]Lochner, L . Education, Work, and Crime: A Human Capital Approach[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04, 45(3): 811-843.
[6]Goldthorpe, J. H. Understanding-and Misunderstanding-Social Mobility in Britain: The Entry of the Economists, the Confusion of Politicians and the Limits of Educational Policy[J].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013, 42(3): 431-450.
[7]Zhong, H. Does Education Expansion Increas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 Economica, 2013, 80(10): 760-773.
[8]Mayer,S. E., Lopoo, L . M. Has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conomic Status Changed?[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05, 40(1): 169-185.
[9]Valero-Gil, J. N., Tijerina-Guajardo, J. A. Effects of Education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Labor Income in Mexico[J].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2002: 381-392.
[10]Machin, S. Education Systems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Z].CESifo PEPG Conference, Munich, 2004.
[9]Blanden, J., Machin, S. Educational Inequality and the Expansion of United Kingdom Higher Education[J].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3, 60(5): 597-598.
[12]Van de Werfhorst, H. G.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Class Mobility[J].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2002, 41(3): 407-438.
[10]周波, 苏佳. 财政教育支出与代际收入流动性[J].世界经济,2012,(21):41-61.
[11]郭丛斌, 闵维方. 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的关系研究[J]. 教育研究, 2007, (5): 3-14.
[12]Bjrklund, A., Roine, J., Waldenstrm, D. Intergenerational Top Income Mobility in Sweden: Capitalist Dynasties in the Land of Equal Opportunity?[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2, 96(5): 474-484.
[13]Erikson, R., Goldthorpe, J. H. Intergenerational Inequality: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2,16(3): 31-44.
[14]Solon, G.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82(3): 393-408.
[15]Mincer, J., Polachek, S. Family Investments in Human Capital: Earnings of Women Marriage, Family, Human Capital, and Fertility[Z]. NBER, 1974.76-110.
(责任编辑:韩淑丽)
参考文献:
[1]Becker,G. S., Tomes, N. An Equilibrium 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9,87(6):1153-1189.
[2]Becker,G.S., Tomes ,N. Human Capital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amilies[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86, 4(3): 1-39.
[3]Solon, G. A Model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Variation over Time and Place[Z].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38-47.
[4]Mayer, S. E., Lopoo ,L . M.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8, 92(1): 139-158.
[5]Lochner, L . Education, Work, and Crime: A Human Capital Approach[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04, 45(3): 811-843.
[6]Goldthorpe, J. H. Understanding-and Misunderstanding-Social Mobility in Britain: The Entry of the Economists, the Confusion of Politicians and the Limits of Educational Policy[J].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013, 42(3): 431-450.
[7]Zhong, H. Does Education Expansion Increas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 Economica, 2013, 80(10): 760-773.
[8]Mayer,S. E., Lopoo, L . M. Has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conomic Status Changed?[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05, 40(1): 169-185.
[9]Valero-Gil, J. N., Tijerina-Guajardo, J. A. Effects of Education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Labor Income in Mexico[J].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2002: 381-392.
[10]Machin, S. Education Systems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Z].CESifo PEPG Conference, Munich, 2004.
[9]Blanden, J., Machin, S. Educational Inequality and the Expansion of United Kingdom Higher Education[J].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3, 60(5): 597-598.
[12]Van de Werfhorst, H. G.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Class Mobility[J].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2002, 41(3): 407-438.
[10]周波, 苏佳. 财政教育支出与代际收入流动性[J].世界经济,2012,(21):41-61.
[11]郭丛斌, 闵维方. 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的关系研究[J]. 教育研究, 2007, (5): 3-14.
[12]Bjrklund, A., Roine, J., Waldenstrm, D. Intergenerational Top Income Mobility in Sweden: Capitalist Dynasties in the Land of Equal Opportunity?[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2, 96(5): 474-484.
[13]Erikson, R., Goldthorpe, J. H. Intergenerational Inequality: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2,16(3): 31-44.
[14]Solon, G.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82(3): 393-408.
[15]Mincer, J., Polachek, S. Family Investments in Human Capital: Earnings of Women Marriage, Family, Human Capital, and Fertility[Z]. NBER, 1974.76-110.
(责任编辑:韩淑丽)
参考文献:
[1]Becker,G. S., Tomes, N. An Equilibrium 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9,87(6):1153-1189.
[2]Becker,G.S., Tomes ,N. Human Capital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amilies[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86, 4(3): 1-39.
[3]Solon, G. A Model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Variation over Time and Place[Z].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38-47.
[4]Mayer, S. E., Lopoo ,L . M.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8, 92(1): 139-158.
[5]Lochner, L . Education, Work, and Crime: A Human Capital Approach[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04, 45(3): 811-843.
[6]Goldthorpe, J. H. Understanding-and Misunderstanding-Social Mobility in Britain: The Entry of the Economists, the Confusion of Politicians and the Limits of Educational Policy[J].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013, 42(3): 431-450.
[7]Zhong, H. Does Education Expansion Increas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 Economica, 2013, 80(10): 760-773.
[8]Mayer,S. E., Lopoo, L . M. Has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conomic Status Changed?[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05, 40(1): 169-185.
[9]Valero-Gil, J. N., Tijerina-Guajardo, J. A. Effects of Education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Labor Income in Mexico[J].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2002: 381-392.
[10]Machin, S. Education Systems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Z].CESifo PEPG Conference, Munich, 2004.
[9]Blanden, J., Machin, S. Educational Inequality and the Expansion of United Kingdom Higher Education[J].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3, 60(5): 597-598.
[12]Van de Werfhorst, H. G.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Class Mobility[J].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2002, 41(3): 407-438.
[10]周波, 苏佳. 财政教育支出与代际收入流动性[J].世界经济,2012,(21):41-61.
[11]郭丛斌, 闵维方. 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的关系研究[J]. 教育研究, 2007, (5): 3-14.
[12]Bjrklund, A., Roine, J., Waldenstrm, D. Intergenerational Top Income Mobility in Sweden: Capitalist Dynasties in the Land of Equal Opportunity?[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2, 96(5): 474-484.
[13]Erikson, R., Goldthorpe, J. H. Intergenerational Inequality: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2,16(3): 31-44.
[14]Solon, G.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82(3): 393-408.
[15]Mincer, J., Polachek, S. Family Investments in Human Capital: Earnings of Women Marriage, Family, Human Capital, and Fertility[Z]. NBER, 1974.76-110.
(责任编辑:韩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