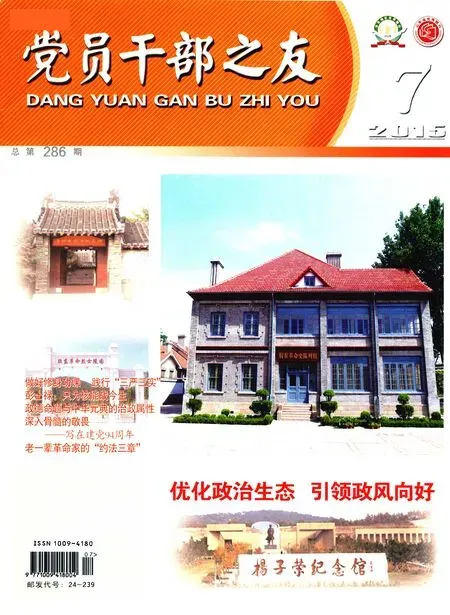彭士禄:只为核能战今生
□ 吴 杰
彭士禄:只为核能战今生
□ 吴 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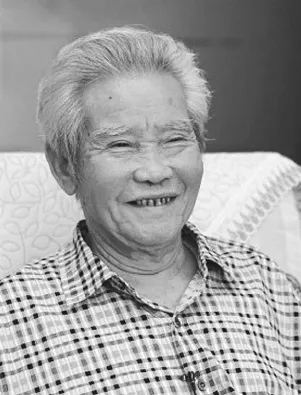
“我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造核潜艇,建核电站。”这是彭士禄院士常常说起的两句话。对于90岁高龄仍致力于推动中国核事业发展的彭老来说,没有什么比核潜艇、核电站更能承载他一生的梦想与追求。
作为我国著名核动力专家,彭士禄是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总设计师,也是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他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身份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革命家彭湃之子……“一生都不离开核事业”的彭士禄,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史,书写了一段传奇。
颠沛童年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童年无疑是美好的。但彭士禄是个例外。他的父亲彭湃,作为党的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曾创建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和东江革命根据地,并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等职。然而,在当时白色恐怖的背景下,这意味着极大的危险。彭士禄3岁时,母亲蔡素屏牺牲。一年以后,父亲彭湃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33岁。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年幼的彭士禄被辗转送到20多户百姓家里寄养。最后,他被送到广东潮安县彩塘区一位红军队长家中,这里也是地下党的秘密交通站。
1933年,潮安县委书记叛变,8岁的彭士禄作为“小政治犯”被捕入狱。他先后被押入潮安县监狱、汕头石炮台监狱、广州感化院,一直囚禁至1935年。释放后,彭士禄回到潮安,继续寄居群众家中,并开始绣花、打柴、放鹅贴补家用。
翌年夏天,彭士禄再度被捕,依然是潮安监狱。这一次,祖母周凤通过彭士禄父亲的战友陈卓凡将其营救出狱。此后,彭士禄跟随祖母颠沛于香港和澳门,在圣约瑟英文书院读小学。
或许是受父亲的影响,彭士禄12岁便独自出门寻找革命队伍,1939年在惠州加入了东江抗日纵队。1940年,周恩来派副官龙飞虎和贺怡辗转找到了彭士禄,经桂林到达重庆。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彭士禄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一见彭士禄便十分激动:“终于把你找到了,你爸爸是我的好朋友!”15岁时,彭士禄辗转抵达延安。
无数的磨难,带给了彭士禄坚韧不拔的品质,也磨炼了他不惧困难艰险的性格;百家衣百家饭,教会了彭士禄以感恩的心报效党和国家,为他后来投身中国核动力事业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与核结缘
在延安中学,彭士禄开始了真正的学习生涯。他担任班长,后来的国家能源部部长黄毅诚、工程院院士戚元靖等都是他的同班同学,那些老同学后来都爱叫他“老班长”。
1951年,彭士禄被选派留学苏联,在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刻苦攻读。1956年,彭士禄以全优的学习成绩获得化工机械优秀工程师称号。
彭士禄还在苏联学习时,1954年的1月,美国东海岸发生了一件大事:康涅狄格电船公司制造的一个庞然大物,转眼潜入太平洋。远远眺望,似一个巨大而灵巧的黑色水怪。不久,水怪幽灵般地游过墨西哥湾、荡过南美洲、横穿大西洋,途经欧亚非三大洲后又回到了美国东海岸,而这一切所消耗的全部动力来自一块高尔夫球般大小的铀燃料。如果换了油作燃料,需要整整90节车皮!消息一经公布,举世震惊。
1956年, 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到苏联访问,正准备回国的彭士禄被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陈赓问他:“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于是,彭士禄成了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专业的进修生。当时,苏联教授给彭士禄这些中国留学生每上一节课,中方要付80卢布的报酬。这对经济基础薄弱的新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正是在这一节课价值80卢布的课堂里,彭士禄与核动力这项神秘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巨鲸潜海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彭士禄学成回国,被安排在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工作。彭士禄所在的二机部(核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主攻核动力。1959年,苏联以技术复杂、中国不具备条件为由,拒绝为研制核潜艇提供援助。为此,毛泽东主席提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必胜决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彭士禄和他的同事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然而,当时国家经济困难,人才奇缺,核潜艇资料更是一片空白。到了1962年,中央又决定集中力量搞原子弹、导弹,核潜艇项目无奈下马。200多人的科研队伍,最后只保留一个50多人的核动力研究室,其中大多数人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所学专业基本与核无关。负责研究室全面工作的彭士禄和其他几位留过苏的同事当起老师,讲授反应堆物理等专业课程。两年后,这几十个外行全部成了核动力尖兵。
条件艰苦卓绝,但全室士气高昂。彭士禄亲自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研发,亲自建立了核动力装置静态和动态主参数简易快速计算法,解决了核燃料元件结构型式和控制棒组合型式等重大技术问题。
“困难时期,我们都是吃着窝窝头搞核潜艇,有时甚至连窝窝头都吃不饱。粮食不够,挖野菜、白菜根来吃。研究室每月每人的办公费才5块钱,里头还包括出差费、笔墨纸张费。那时没有电脑,就拉计算尺、敲算盘。那么多的数据,就是这样没日没夜算出来的。”彭士禄回忆说。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给核潜艇项目带来了转机。不久,搁置多时的核潜艇项目重新启动。一声令下,彭士禄告别妻子儿女只身入川,主持建造中国第一座1∶1潜艇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他敢于面对各种争论,依靠科学数据和实验结果果断决策。试验中别人不敢做决策时,彭士禄只要有七成把握便敢拍板,另外三分困难和风险再努力想办法克服和修正。他说:“不可能事事都等到有十分把握再干,没困难,不冒险,还有什么创新呢?”为此,彭士禄得了个外号:“彭拍板”、“彭大胆”。
1971年,核潜艇首航。依靠自己的力量,只用了6年时间,中国一举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这一奇迹的背后,充分体现了以彭士禄为首的科研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彭士禄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
核电先锋
将核能服务于社会、实现和平运用核能的理想, 是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核动力专家的毕生心愿。核潜艇研制成功后,彭士禄从军工转入民用领域,投入到研究和创建核电站的工作中。
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批准上海核工程研究院从事核电站方案的设计。上海开始提出一套熔盐堆方案。时任719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的彭士禄对此反复推敲,考虑到其难维修的缺点,大胆否定了这一方案,建议采用压水堆方案。他亲率50多位科技人员来到上海,和上海核工程研究院合作,精心计算30万千瓦压水堆的主参数,同时进行设备的选型,为我国自己设计建造的首个核电站——秦山核电站打下了基础。
秦山核电站之后,我国启动了大亚湾核电站建设项目。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大项目,大亚湾项目价值20亿美元。1983年初,彭士禄被任命为该项目总指挥。为缩短探索的过程,大亚湾项目与法国和英国合作,走上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之路。
彭士禄深深知道,搞大型工程,既要懂设计,又要懂经济,还要懂辩证法。如果不懂设计,就不能“自力更生、以我为主”建设核电站;不懂经济,延误一天,损失多少,心里没底;不懂辩证法,绝对管不好工程。于是,在蛇口招商局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彭士禄埋头在写字台前,把外商提供的核电站的100多个主要参数亲自核算了一遍,并自学经济学课程,对核电站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得出推迟一天将损失100万美元的结论。彭士禄综合多方面因素,提出了进度、质量、投资三大控制,为投资和进度控制问题建立数据模型。这套管理思路在大亚湾核电站建设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1986年,彭士禄调任核工业部副部长,负责秦山二期筹建工作。此前计划引进外国核电站,但由于西方某些国家的阻挠,谈判无法进行。彭士禄觉得光靠外国不是办法,就写信给国务院提出要“以我为主,中外合作”建设核电站。为解决资金问题,在大部分人还习惯计划经济模式的时候,彭士禄首次将招投标制度引入到核电工程。可想而知,当时遇到了很大阻力,一些同志仍按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主张设备要定点生产。最后彭士禄拍板,坚持设备、订货实行招投标制。招投标制解决了靠拉关系争项目的不良现象,充分发挥了参建单位的特长。实践证明,当时这一做法虽然超前,却顺应了经济规律。
彭士禄说,“我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造核潜艇,建核电站”。如今,虽到了耄耋之年,彭老依旧十分关心国家的核事业,在高级顾问的角色上继续发挥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