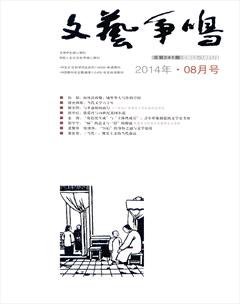争议与繁荣:关于当今中国形象学的研究
赵颖
形象学作为一国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是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中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的比较文学研究类型。按照巴柔的界定,这里的“异国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而形象学真正得到长足发展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而重新焕发活力。例如萨义德在他的《东方主义》中,解剖了西方人眼中作为“他者”的“东方”形象,指出其虚构性和背后隐藏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意识。再如,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族群研究、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关系研究、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研究等对于形象学研究的深入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诸如“东方主义”“异国情调~西方主义”“中心与边缘”“族群认同”等语词不断地出现在形象学研究的范畴中,这让形象学在研究范围上面目一新的同时,也显得难以辨认。
比较文学形象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是近些年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有关形象学的话题就已经通过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比较文学著作进入了中国,但这一时期的形象学研究几乎是同一般影响研究混同的。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乐黛云所编著的《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介绍了形象学在国内外的最新发展。孟华作为形象学的较早研究者,从1994年就开始对形象学的研究进行译介,直到2001年,她将法国形象学研究成果编译成《比较文学形象学》一书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的出版,不仅为形象学在国内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更把形象学在中国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然而,不可避免的是,一方面,形象学研究在中国的如火如荼、颇具声势,另一方面,作为在学科发生地就已经颇有争议的学科,在中国一样有着各个派别的看法。
例如,形象学在中国,对其定性的共性在于都承认是法国学派的老话题。但即便是学科归属也有着很大的争议。杨乃乔把形象学归为影响学派,“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他者形象,即‘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所以,它的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国别文学范围之内,而是在事实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甚至跨学科的研究。”而在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的《比较文学》一书,又将形象学视为平行学派,“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的民族(异国)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造他种文化形象。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的形象学又归属为变异学,“比较文学形象学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形象研究,它是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社会集体想象物本身是不真实的。”这样的争议,实际上也是一件好事,它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形象学研究在中国的研究之热,反映出中国学者对于形象学自身的思考和定位。正如比较文学的他国化,形象学在当前中国也有着中国化的发展趋势。
一、形象学的文化转向
异国形象与文化认同密不可分,异国形象创造是一个借助他者发现自我、认识自我的过程,是对自我文化身份加以确认的过程。就学科价值而言,形象学研究的形象实际上就是“异国形象”或“异族形象”,即是一个他者的形象。它是通过与自身的整体文化与他者的文化比较、交流、诠释所形成的“他者形象”。这背后深藏了本土对异族或异国文化的整体看法、态度、观点和立场,而他者的“形象”也映射出某种对本土文化的态度、看法以及观点和立场。正如有学者断言,“由于研究者的不同学科取向,对文化适应的不同界定,导致不同概念之间的混用和误用现象。不同学科之间的文化适应理论也只是关注文化适应的某一方面,缺乏学科之间的照应与互动。㈣因此,形象学研究的价值,主要不是体现在审美体验层面,而是体现在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与交流的实践层面。
另一方面,就学科本身而言,对于形象学的研究,只要我们接受一个总的前提,即“异国形象”这一现象是存在的,那么对它的解释就只能是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而不是诗学的,即人们只能从形成形象这一过程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而非审美因素中去寻找。这是因为,作家生活于一定的社会环境,思想必然受到所属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当他们在作品中对另一种文化进行审视时,必然会带着“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印记。
例如,法国杜拉斯的小说《情人》,讲述了一个白人少女和一个中国男人的爱情故事,故事中塑造的中国人形象就反映了当时法国人对中国的“集体想象物”。两个人的爱情之所以遭到反对,是因为白人女孩的情人是中国男人,二者的感情定格为一个谦卑的求爱者和一个心怀优越感的女孩。不可否认的是作者看到了中国人的淳朴与善良,但由于法国作家依然无法摆脱本民族所赐予她的灵魂和偏见,中国情人一出场就是一个“胆怯者”,这种被极度轻蔑的中国人形象客观反映了法国人的优越感,更从根本上反映出那个时期法国人所认为的白人优越的精神文化特质。而离我们较近的一部影片《2012》则从另一个维度,反映出今时今日的“中国形象”,例如:影片中,杰克逊等美俄两个家庭在喜马拉雅山被中国藏民冒险救助。再如中国成为“拯救人类”的基地,而中国的大集体精神被宣传为唯一能完成现代“方舟”建造工程的现代精神。这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在21世纪的国际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明显,中国作用的提升会渗透到国际活动的各个领域,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文化领域,从而导致国际社会重新认识和肯定中国形象。
纵观近年来以文化作为研究视角的博士论文频频出现,例如,暨南大学李雁南的《近代日本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四川大学杜平《英国文学的异国情调和东方形象研究》,四川大学姜源的《异国形象研究:清朝中晚期中美形象的彼此建构》。同时,有关的形象学著作更是着眼于文化视野中的异国形象,例如2002年卫景宜的《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2004年张哲俊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2005年姜智芹的《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2006年孟华主编的《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尤其是周宁等人编著的《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更是以系列丛书的形式探讨七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演变过程,观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文化他者”的想象,如何在西方文化中逐渐演变,并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中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政治形态。endprint
而中国近些年之所以出现形象学的文化转向更多的是来源于对中西关系的焦虑和期望,源于中国在全球化语境下对自身形象的重视,而中国形象的建构,最终还是来源于西方的叙述和塑造。正如周宁在对中国形象在西方的考察中指出的,“我们在知识社会学与观念史的意义上研究该形象的历史,至少有三个层次上的问题值得注意:一、西方的中国形象是如何生成的。在理论上,它必须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有关‘文化他者的话语,是如何结构、生产与分配的;在历史中,它必须确立一个中国形象的起点,让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过程,在制度与意义上都可以追溯到那个原点;二、中国形象的话语传统是如何延续的。它考察西方关于中国形象叙事的思维方式、意象传统、话语体制的内在一致性与延续性,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历史中所表现出的某种稳定的、共同的特征,趋向于类型或原型并形成一种文化程式的过程;三、中国形象是如何在西方文化体系中运作的。它不仅在西方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诠释中国形象的意义,而且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在西方文化中规训化、体制化,构成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成分,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及其文化霸权。”
当然,在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关于形象学作为文学研究的性质。“文学性”不等于文学研究,“非文学性”不等于不是文学研究。形象学归根结底还是对他国形象的文学化表达。正如让·马克·莫哈指出:“异国形象属于对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想象,它在各方面都超出了文学本来意义上的范畴,而成为人类学或史学的研究对象。正因为文学作品是在这个广阔的背景上形成的,形象学研究就必须按照跨学科的方法进行”。如此一来,形象学研究就必然面临研究重心的转移,即从文学形象转移到文化形象。
二、形象学“东方主义”的模式化解读
东方主义,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出发,把东西方文化看成截然对立的两面,而萨义德秉承了福柯关于话语权力理论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主张,认为东方主义是一种知识系统和权力体系。正如罗素、梁漱溟等人将文化、哲学分为西方的、印度的、中国的。中国作为东方,必然面临用西方的传统观念和制度对自身文化加以解释和阐发,在西方的价值维度和标准之下,东方文化包括中国形象的真实无可避免地会发生误读和扭曲。
同时,根据形象学的理论,异国形象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它所传达的他者国家的话语,或是体现着对异国的社会集体想象,或是针对着这种想象,总之要受到它的制约。西方形象学研究的经验事实分为西方文明国度之间的相互形象塑造和西方文明为东方国家单向塑造的形象。其中,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真正的意义不是认识或再现中国的现实,而是构筑一种西方文化必要的。因为现代的中国形象,不论是立场和视野还是想象的主体都是西方的。
文化交融和共生中存在着文化本体和文化变异体两种文化形态。可以说,中国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但这均不是“事实的”文化的本体性价值,只能是“描述的”文化的价值。对西方作家而言,中国与其说是一个真实的国家,不如说是他们想象描述的一个神话,是激发他们写作和表达思想的灵感和素材。可见,西方作品中的中国并非地理空间存在意义上的中国,而是被东方化了的中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摆在中国学界的第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该如何面对一个真实的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是不断变化的。最初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被高度美化的物质和精神昌明的综合体。例如《马可·波罗游记》里就有许多对中国物质文明夸张的渲染。但是,伴随晚清政府的苟延残喘,中国在西方的形象被贬斥为封闭、愚昧和落后的。例如,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续编》等作品中,对中国文明进行肆无忌惮地讽刺与攻击。在他眼里,所谓中国的光辉灿烂、强大昌盛颂扬中国的言论,丝毫不值一提;而中国人的自傲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事实上中国人连美洲的生番野人都比不上;中国的宗教则是最野蛮的,中国人在一些怪物的偶像面前弯腰致敬,而那些偶像是人类所能制造的最下流、最可鄙、最难看、最使人看了恶心反胃的东西……
其次,当今中国学界开始对“自我东方化”的重视。例如:周宁指出“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问题,指向另外两组相关的课题:一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影响或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自我东方化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的西方形象和‘西方主义的问题;二是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彼此东方化的问题。”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文学科、社会学科中充斥着的殖民话语,对近代以来中国本土的学术有着深刻的影响。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许多行为和措施都是对西方的一种回应。在急于国际化角色的扮演过程中,中国无可避免地被笼罩在了后殖民主义世界的大气候之下。时至今日,国人仍有将西方当做正面的东西来看待,认为西方的模式和经验就是好的,从而丧失了从根本上去挑战和拒绝西方权势话语、殖民话语的勇气。
最后,正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利提出的“镜中之我”所说的那样,自我是社会的产物,以镜子的反映来说明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随着当代形象学从对他者文化的阐释转向对自我文化的确认,借助他者形象这面镜子认识自我是形象塑造者的一个重要动机。在形象学中,每种形象都是另一种文化的一面镜子,通过他人对自己的意见和态度,可以反观自身,形成自我的观念。而无论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都把中国形象看作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权力运作的结果,是东方主义的产物,而更进一步而言,中国当代形象学更多的是要考虑西方的中国形象对中国社会的能动意义。因为,中国乃至东方就是在西方所塑造的形象的提示和促动下巨变的。
三、文化传播学视野下对“形象”真实性的考量
正如亨廷顿的推断,新的世纪,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主要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目前随着文化因素在国际事务和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上升,通过对外文化传播来塑造和传播“形象”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形象学研究者的青睐,也越来越受到现代国家的重视。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直接塑造国家形象,并且对与国家形象密切相关的诸多方面产生影响和作用。endprint
文化传播不仅为“形象”塑造提供了持续不断的精神动力,更有助于淡化和进一步消除西方人对中国“沉默性威胁”的形象认知。应当说,相对于西方国家相互之间的形象认知而言,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是浅层的、零碎的。西方社会大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更易为政府和社会主流媒体所影响和左右。之所以如此,原因复杂多样,有一定的外部因素。但就中国自身而言,“内敛型”的文化和民族性格以及没有给予对外文化传播应有的重视,应是一个重要原因。“内敛型”的文化和民族性格以及文化传播上的薄弱,在特殊环境背景下,在不知不觉中为一部分西方人构建中国“沉默性威胁”的形象提供了机会。正如迪塞林克所指出,“一个国家在他国所具有的形象,直接决定其文学在他国的传播程度。”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之所以能够得到西方人的喝彩,是因为这些电影呼应了西方人心目中对中国人的“形象”的想象。在现代作家中,林语堂、钱钟书等人的著作在海外呼声很高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反观形象学中的异国形象有两种功能,即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凡按本社会模式、完全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出的异国形象就是意识形态的:而用离心的、符合一个作者(或一个群体)对相异性独特看法的话语塑造出的异国形象则是乌托邦的。”按照这种解释,“意识形态”是对异国形象的贬斥,“乌托邦”是对异国形象的美化。而对形象的塑造只有这两种形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形象”是不存在与现实相符的可能,也意味着“形象”是不真实的。就连法国学者巴柔也提出过,形象学并不研究形象的真伪程度,就表述而言“形象”无真实可言。
另一方面,形象学形象的形成有自己的文化背景,谈及形象更是规避不了文化的因素,所以学者们对其意义作出这样的论述“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塑造(或赞同、宣扬)该形象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并表明了自身所处的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空间。”可见,形象学研究在这里主张在研究作品所描绘的异国的时候,研究的是其与所属国家对该异国的社会集体想象之间的关系,而排除了形象真伪的问题。
但是,当形象学开始对所谓的“误读”进行研究时,首先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形象本身到底是什么样的?正如孟华指出的,“既然‘形象是对异国的误读,要想真正分析清楚‘为什么,首先就得搞清‘怎么样。而研究接受者,就不能不研究他对原文的误读。只有搞清了原型是怎么样的,才能了解接受者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原型,然后才是回答为什么的阶段。”
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什么是真实的?真实的形象是什么?正如我们回答中国的国民性是什么,中国的形象是什么样的面目,很难做出一致的回答。但是又有一些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我们一看就知道是虚假和夸大的。因此我们在利用“真实性”对形象进行界定时,这个形象只能是相对真实的形象。因为文学形象的“真实性”是其核心价值所在,这种“真实性”主要指的是渗透在作品中的主体情感的真实性,即主体的主观真实性,而主观真实的母体毕竟是客观真实性。
对研究者而言,在社会总体想象的层次上讨论西方的中国形象,分析不同领域的研究者怎么样在不同类型的文本中表述中国;而各类文本又是怎么样互相参照、对应、协作和传播;最终形成一整套言说中国形象的话语,这样的“话语”又是怎么样支配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建构,使文本的表述受制于这一整体或原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