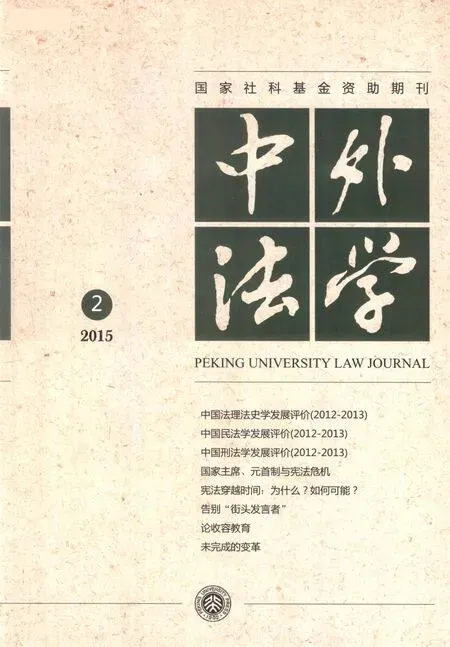宪法穿越时间:为什么?如何可能?来自美国的经验
田 雷
宪法穿越时间:为什么?如何可能?来自美国的经验
田雷*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摘要像人类学家一样去观察美国宪法史,其宪法实践呈现为一种跨越代际而存在的自治政治,这种自治在规范上要求当代人以及子孙后代信守制宪者写入宪法文本的“先定承诺”。但为什么制宪者有权订立垂范千古的宪法?为什么遵守先定承诺反而是民主正当的?美国宪法的路径是建构出一种在时间维度内绵延的“我们人民”这一政治主体以及一种跨越代际而生生不息的共同体模式。美国宪政是一种“叙事宪政”。宪法故事的讲述构成了宪政实践的文化基础,培育了每一代美国人对原初宪法的认同、热爱和信仰。美国宪法之“活”,原因在于美国人有能力去讲述美国宪法之内、之外、之间、之上、之前和之后的故事,由此形成美国这个宪法共同体共同分享的源头叙事。
关 键 词先定承诺人民制宪者宪法文化历史叙事
制宪者已逝,但宪法长存。
——弗里德里希·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It Pro-Slavery or Anti-Slavery?”, Glasgow, Scotland, March 26, 1860.
如果您渴望知道我们宪法的精神,以及在从宪法得以确立至当下时刻,是什么政策主导着这个伟大的时代,就请您在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议会法案和日志中,而不是在“老犹太人”的讲道或“革命协会”的晚宴祝酒词中去寻求它们吧。
——埃德蒙·伯克*(英)伯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页41,题记引文参考伯克原文对商务版中译做了微调。
引言
1789年9月6日,法国大革命的现场,美国驻法大使托马斯·杰斐逊提笔写下一封长信,收信人是时在大西洋彼岸的费城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两年前,杰斐逊因身在法国而错过费城会议,而在这封长信中,他所批判的正是这种为“我们人民”以及“子孙后代”立法的行为。*杰斐逊信的中译文,可参见(美)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选集》,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页478-484。杰斐逊认为,自治政府的原则要求每一代人都应有自己的宪法,任何跨越代际的统治都是一种祖先专制,此命题后来成为著名的“每19年革命重来”的“不断革命论”。有学者称杰斐逊的这封信为第二次“独立宣言”。1776年的《独立宣言》宣告了北美13个殖民地脱离英帝国的宗主统治,这封信则是“时间性的独立宣言”,宣告了每一代人都可以独立于任何祖宗成法而自治,每一代人的政治都是一个新的开始。*Jed Rubenfeld, Freedom and Time: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Self-Governmen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8.
两百年后,美国宪政的发展否定了杰斐逊的命题。首先,1787年的原初宪法非但没有随着革命一代人的逝去而被埋葬,反而在保持文本基本结构稳定的前提下“活”到今天。历史并未站在杰斐逊这一边,反而是道格拉斯这位黑人逃奴概括出了宪法与时间之间的关系:“制宪者已逝,但宪法长存”。其次,如何解释这一部有着两百年历史的宪法文本,美国当下最具统治力的学说就是原旨主义的解释论。*关于原旨主义的实证研究,可参见Jamal Greene, Nathaniel Persily & Stephen Ansolabehere, “Profiling Originalism”, 111 Columbia Law Review, pp. 356-418, (2011)。原旨主义者主张,宪法解释应当回归制宪者的意图或宪法文本的原初含义,这又是与杰斐逊的学说背道而驰的。不仅如此,杰斐逊本人也不是杰斐逊道路的身体力行者。1787年《宪法》诞生19年之际,正是杰斐逊出任总统期间,他却并未严肃思考过重开制宪会议以制定一部新宪法,或是对原初宪法进行正当性的续期。
若只是以成败论英雄,宪法学有理由遗忘杰斐逊的命题。但本文以杰斐逊为引言,所要表达的就是,杰斐逊虽然建构了一个现实政治永远无法实践的自治模式,但这个荒诞不经的答案却是基于一个理论家应予认真对待的问题。在学术研究中,提出正确的问题通常都要比给定正确的答案更重要。如下文所示,宪法学者曾用不同的二元概念去概括杰斐逊命题所关切的政治生活的内在紧张,比如麦克尔曼所说的“法治政府”和“自治政府”,列文森的“基本法理念”和“人民主权理念”,鲁本菲尔德所区分的“活在当下的政治”和“时间延展的自治”。*参见Frank Michelman, “Law’s Republic”, 97 Yale Law Journal, pp.1493-1538, (1988); Robert McCloskey & Sanford Levinson, The American Supreme Cour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Rubenfeld,supra note 4。学者在建构理论体系时未必自觉地怀有杰斐逊情节,但他们的理论展开却有一个杰斐逊的语境,正因此,杰斐逊作为引言有助于我们开启一种讨论宪政的新视野,这就是宪政的时间性问题。
认真对待杰斐逊的命题,原因尚不止于此。首先,杰斐逊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身处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脉络内。此脉络关注的是政治的当下性,即主权者意志在某个时刻的绽放,也因此忽略了政治的连续性,亦即成文宪法作为高级法的理念和实践。在晚近的宪法讨论中,如果说原旨主义是一种反杰斐逊命题的论述,那么与其并驾齐驱的活宪法说则保留了杰斐逊理论的火种。其次,历史虽然并未走上杰斐逊的道路,但这并不等于否定它的意义。两百年后,美国的原初宪法已经呈现出种种病理,由此在近年来催生了一波从根本上检讨美国宪政体制的学术声音,有学者甚至主张要重开制宪会议,只有另起炉灶制宪,才能实现革故鼎新,因此就有了“杰斐逊的复仇”这一说。*代表性的论述可参见Sanford Levinson, Our Undemocratic Constitution: Where the Constitution Goes Wrong (And How We the People Can Correct I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Cass Sunstein, A Constitution of Many Minds: Why the Founding Document Doesn’t Mean What It Meant Befo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还有一处应予指出的历史细节:比较宪法学者统计了历史上所有的成文宪法典,其平均寿命恰恰是19年!*Zachary Elkins, Tom Ginsburg & James Melton, The Endurance of National Constit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难道这真是杰斐逊的诅咒?杰斐逊笑到了最后?
本文主要分三部分来展开论述。第一部分沿着杰斐逊的思路,在时间性的维度内去追问什么是宪政,但答案却是反杰斐逊之道而行之的。宪政是一种跨越代际的自治政治,表现为当代人对写入宪法规范的“先定承诺”的信守。第二部分是对信守先定承诺进行正当性的论证。为什么一时的制宪者可以制定出垂范千古的宪法,为什么21世纪的美国人还要受制于18世纪的已经死去的白人男性有产者制定的宪法,就此而言,杰斐逊的幽灵是挥之不去的。在此问题上,自由主义宪政作为一种学说,其内部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和紧张。本文的论述将借用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的理论资源,建构出一种在时间维度内绵延的“我们”这个主体。在这种生生不息的共同体模式内,每一代人的肉身终将腐朽,代际的更替不可避免,但每一代人却在文化身体的意义上构成了一个单数的“我们”,而宪政的正当性也就建立在这一共同体的模式之上。第三部分将转入美国宪政的文化研究。先定承诺的正当性取决于共同体的文化建构,但没有一种普遍分享的历史叙事,政治文化的共同体就无法形成。“每一部宪法背后都有一部史诗”,*Robert Cover, “Nomos and Narrative”, 97 Harvard Law Review, p.4, (1983).美国宪政实际上是一种“叙事宪政”。宪政故事构成了美国宪政实践的文化基础,培育了每一代人对宪法的认同、热爱和信仰,而信守作为先定承诺的宪法规范也因此成为美国人的公民宗教。就此而言,宪政之“活”,恰恰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去讲述一部宪法之内、之外、之间、之上、之前和之后的故事,有没有一种关于历史源头的共同叙述。
一、 先定承诺的宪政
(一)杰斐逊及其语境
杰斐逊在写给麦迪逊的信中开宗明义,“一代人是否有权约束另一代人”,这是在大西洋政治世界内未得到认真对待、但却事关“所有政府之根本原则”的问题。杰斐逊的论述起始于一个在他看来不证自明的命题:“地球的用益权属于活着的人,死去的人对之既无权力,也无权利”。由此出发,杰斐逊构建了一种代际政治模型:“让我们假定一代人全部出生在同一天,在同一天达到成年年龄,并且在同一天死亡,让接下来的一代人全体在此时刻进入成年”。在这种“代代公民如同游行方阵式同生同死”*正文的概括,参见(美)史蒂芬·霍姆斯:“先定约束与民主的悖论”,载(美)埃尔斯特、(挪)斯莱格斯塔德主编:《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潘勤、谢鹏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页247。的政治模型中,既然“地球总是属于活着的那一代人”,没有共同体可以去制定一部“永恒宪法”,而在代际交接之时刻,前一代人的宪法应当随着他们的肉体消失而自动失效,因此,杰斐逊的结论是,“在每19年终结时,每一部宪法和法律都将自然过期”,“如果宪法得到更长时间的执行,宪法就成为暴力的法律,而不是权利的法律——因此可以说,每一代人事实上都有其废止权,惟其如此才得以自由,如同宪法或法律明文限定在19年”。*杰斐逊,见前注〔3〕,页479、480、482。
杰斐逊的上述命题代表着政法论述内由来已久的一个传统。与杰斐逊同期的潘恩就发表过异曲同工的论述:民主是当下人的自治,“是反对过去的战争”。潘恩反对伯克所主张的1688年英国议会可以制定永恒法律的观点,主张“在任何情形内,每个时代和每一代人都应当如它先前的那些时代和那些代人一样,有自主行动的自由”。*霍姆斯,见前注〔10〕,页228-230。将杰斐逊和潘恩放在一起的讨论,参见Gordon Wood, “The Radicalism of Thomas Jefferson and Thomas Paine Considered”, in Gordon Wood, The Idea of America: Reflections on the Birth of the United States, Penguin Books, 2012, pp. 213-228。诺阿·韦伯斯特也曾写道:“制定永久宪法的企图就是设定了有权去控制未来世代的意见;我们对他们没有权力,正如我们对亚洲的一个民族没有权力,但却预设了我们有权为之立法。”*转引自Gordon 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8, p. 379。在这里,韦伯斯特用空间的位移去比拟时间的流转,既然在“空间位移”的场景内,美国人无权为同时代的亚洲某民族进行立法,那么在“时间流转”场景内,1787年的美国人也无权为21世纪的美国人立法,否则就是“时间性的帝国主义”。*Alison LaCroix, “Temporal Imperialism”, 158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pp. 1329-1374, (2010).
杰斐逊晚年仍未改初衷,一直保持着革命派的本色。他在1824年的一封信内再次回到这个话题,“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首先,杰斐逊如历史上的所有革命家那样“粪土当年万户侯”、“造物主创造世界是为了活人,而不是为了死人”、“死人连物都不是,构成他们肉体的物质微粒现在已成为其他无数种动植物或矿物的主体”。既然肉体已经腐朽,那么原本附随于肉身的权力就不可能永存,而必须在代际流转之际将权力的接力棒交到新一代人的手中。杰斐逊的结论是,“除了不可让渡的人的权利以外,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杰斐逊,见前注〔3〕,页705-706。
(二)“活在当下”的政治及其批判
杰斐逊之所以认为每一代人都应有自己的宪法,代际交替要求宪法政治从头再来,就在于他将共同体的政治生活进行了以“代”为单元的区隔。每一代人在时间进程中都构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单元,自治政府只能在此尺度内生长。不仅如此,各代人彼此之间还是相互独立的,在共同体内,第n-1、n和n+1代人就如同中国人、美国人和德国人一样,相互间不存在政治继承关系。杰斐逊命题实质上否定了政治生活在时间进程中的连续性,每一代人都有自治的主权,正如每一民族都有自治的主权。再进一步,每一代人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是在时间历程中的一个独立片段或“绽出”。不断革命论主张造反有理,每代人都要“遗忘”此前的政治传承,非如此不足以活出自我的新一代,所基于的就是这种“不念过去,不畏将来”的共同体模式。鲁本菲尔德教授将这种无限扩大政治生活之代际间隙的学说概括为“活在当下”的政治。
根据鲁本菲尔德的论述,活在当下的政治看似符合民主自治的抽象原理,政治的每一时刻都是崭新的,如同一次记忆格式化后的重启,而此状态下的个人也是最“自由”的,因为没有记忆带给他的负担,所以最能实现偏好的最大化。但是,活在当下的政治是完全碎片化的,是没有时间性的,其每一刻都是一次旧的结束,同时又是一次新的开始。而在这种政治中生活的人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彼此分裂和独立的“当下”、“时刻”或“瞬间”。*Rubenfeld,supra note 4,pp. 17-44.
在“活在当下”的政治中,自由就是没有时间性的自由,所谓自由人不过是只知道此刻欲望的动物或经济学上为当下偏好所俘虏的理性人,而不是共同体内的政治人,其自治也只是动物的欲望满足,而不是人类政治社会的民主自治。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不可能永远活在当下这个时刻。我之所以成为一个“我”,就要求行为的连续性,不能简单地以今日之我去否定昨日之我。意思自治并不意味着当下偏好或欲望的统治,而是要求要信守承诺。在时间的流转中,昨日之我、今日之我和明日之我是“同一个我”,既然无法完全活在当下,那么就要信守承诺,而不能仅服从当下的欲望或偏好。
在此意义上,活在当下本身就是对政治可能性的否定,因为活在当下意味着政治生活已经失去了元规则。根据杰斐逊的学说,每经过19年就要重新制定一部全新的政治宪法,就是要求每一代人必须从政治国家退回自然状态,重新商定新的社会契约,进行最根本的共识形成。周而复始的推倒重来不是宪政,而是“折腾”。因此,正如私法学说不允许以当下的意思表示去推翻此前的承诺以及基于此的合理期待,民主自治所要求的也不是当下时刻的意志统治,而是对先定承诺的信守。正是先定承诺划定了当下之我们的政治决策的领域。宪法理论常说,宪政就是要将某些议题安放在政治决议的范围以外,但这种限制与其说是少数对多数的制约,不如说是一种在历史维度内生成的有限政治,与其说是一种“反多数难题”,不如说是一种“反当下的难题”。*鲁本菲尔德对反多数难题在时间维度内的再阐释,可参见Rubenfeld,supra note 4,pp. 10-12。
(三)作为先定承诺的宪法
宪法规范是在时间维度内生成的先定承诺,宪法就是对先定承诺的书写,因此不可能是杰斐逊所预设的一代人尺度内的文件,而宪政就是对“先定承诺”的信守,呈现为一种跨越代际的自治工程。作为本文的核心概念,先定承诺(pre-commitment)的重点并不在于“承诺”,*关于宪法承诺的一般性讨论,即为什么写在羊皮纸上的宪法可以去约束掌握着枪杆子和钱袋子的政治力量,为什么多数派在宪法承诺不利于当下时仍选择服从,参见Daryl Levinson, “Parchment and Politics: The Positive Puzzle of Constitutional Commitment”, 124 Harvard Law Review, pp. 657-746, (2011)。而在于“先定”:“先定”意味着宪法是共同体在当下之前所形成的规范,意在构筑起未来世代之自治政治的基本框架。*关于先定承诺在社科以及政法理论中的讨论,参见Jon Elster, Ulysses Unbound: Studies in Rationality, Pre-commitment, and Constrain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88-174;Jon Elster, “Don’t Burn Your Bridge Before You Come to It: Some Ambiguities and Complexities of Pre-commitment”, 81 Texas Law Review, pp. 1752-1788, (2003)。巴尔金的新著《活原旨主义》致力于调和“原旨主义”和“活宪法”这两种原本水火不容的学说,根据他的论述:宪法的核心功能在于“设定政府的基本结构,让政治成为可能,并且创造一个未来宪法建设的框架”。*“框架式原旨主义”的论述,参见Jack Balkin, Living Origin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1-23。
先定承诺的最佳示例就是“尤利西斯自缚”的故事:为防止女妖塞壬迷人歌声的诱惑,尤利西斯提前在清醒时刻要求同伴将自己绑缚在船的桅杆上,同时用蜜蜡封住自己的耳朵。*埃尔斯特曾在社科论域内发掘出此故事,参见Elster,supra note 19;另可参见冯克利:《尤利西斯的自缚》,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美国19世纪的政治家约翰·波特.斯托克顿曾指出:“宪法是锁链,人们在清醒时刻用以绑缚自己,从而防止在他们疯狂的日子里死于自杀之手”;经济保守主义的吹鼓手哈耶克也有过异曲同工的表述:“宪法是清醒时的彼得对醉酒时的彼得的限制”。*转引自Elster,supra note 19,p. 89。而宪法学家桑斯坦曾写道:“宪法写入先定承诺,策略就是要去克服集体的短视或意志脆弱”。*Cass Sunstein, “Constitutionalism and Secession”, 58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p. 641, (1991).
因此,宪法以及任何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都是在为未来立法。如果用“代”作为时间度量的基本单位,那么宪法就表现为前代人对后代人的约束,它必定不是一时一刻的政治,而需要在一种历时延续、跨越代际的政治生活中才能得以展开。美国1787年《宪法》的序言就提供了一种跨越代际的叙事:“我们合众国人民,为……使我们自己和后代(ourselves and our posterity)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就此而言,美国宪法的制定及其两个世纪的历史发展表明,宪法是一种建国时刻的祖宗约法,一部志在“为万世开太平”的基本法。约翰·马歇尔就曾在美国银行案中对宪法“管长远”而非“管一时”有过经典阐述:美国宪法“被设计去经受漫长岁月的考验,因而必须适应人类事务的各种危机”。正是因此宪法在起草时有时必须是“宜粗不宜细”的:“宪法的性质要求,宪法条款仅能勾勒宏伟纲要、指明重要目标,并从目标本身的性质中,推断出组成那些目标的次要成分。”*McCulloch v. Maryland, 17 U.S. 316 (1819).
二、 宪政的共同体基础
尤利西斯的故事并没有提出先定承诺的正当性问题,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个人的“自缚”,是尤利西斯在其尚且清醒时的理性决定,意在约束未来有可能自我毁灭的尤利西斯。但宪法作为先定承诺有本质的区别,如果说“宪法是清醒的彼得,而人民则是醉汉彼得”,*霍姆斯,见前注〔10〕,页262。而在代际交接的政治发展内,此彼得已非彼彼得。根据《美国宪法》的序言,“我们人民”是为“我们自己”以及“子孙后世”制定了本宪法。由此可见,一旦宪法的效力跨越代际而延续,那么杰斐逊的幽灵就在宪政之上盘旋。
为什么一时的制宪者可以制定出千古永续的宪法?为什么在今天奉行原旨主义不会造成“死人之手的统治”?为什么一个由早已死去的白人男性有产者所制定的宪法,还可以统治生活在21世纪的美国人?*关于死人之手的统治,可参见Adam Samaha, “Dead Hand Argument and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108 Columbia Law Review, pp. 607-680, (2008)。杰斐逊确实道出了宪政之先定承诺的正当性困境:一时的制宪者如何有权制定千古的宪法,当制宪者——很多情形内都是背负着原罪的制宪者——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其肉身早已化为矿物质后,为什么由他们制定的法律并未“身与名俱灭”,其效力反而如不废江河一样万古长流。为什么先定承诺是民主正当的,这是本部分所要解决的问题。
(一)现有理论的失败
为什么信守先定承诺,为什么遵守祖宗成法不会造成“死人之手的统治”,美国宪法学界有三种最具代表性的论述。
第一种论述来自于死硬的保守派。在他们看来,宪政的本意就是要遵守祖宗成法,死人之手在道德上是可欲的。美国保守派宪法理论的旗手斯卡利亚大法官曾指出:宪法的“全部目的就是要拒腐防变(prevent change)——要以未来子孙后世不可能轻易夺走的方式去确保某些权利。一个订立权利法案的社会并不相信,‘体面标准的进化’总是‘标志着进步’,社会总是在‘成熟’,而不是‘衰朽’”。斯卡利亚在回应德沃金时举过一个例子:美国1787年《宪法》中写入了禁止“残酷刑罚”的规范,这就构成了一种先定承诺,之所以要将此规范写入宪法,就是为了防止“子孙后代们更残酷的道德感”。*严格说,斯卡利亚并非极端的原旨主义者,他认为“原旨主义”只是“更小的恶”,参见Antonin Scalia, “Originalism: The Lesser Evil”, 57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Law Review, pp. 849-866, (1989),正文所引出自Antonin Scalia, 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0,145。
既然社会有可能“衰朽”,宪法的用意就是要“拒腐防变”。伟大的制宪者们将他们的先定约束写入宪法,意在强化子孙后代拒腐防变的能力。而这种先定约束之所以成立,所基于的就是斯卡利亚建构的衰败叙事:建国时刻的先人更有德性,第二代人及其以后就有可能腐化堕落,因此制宪者为后世约法,是要防止后来人忘记这经由奋斗和牺牲所取得的胜利,背叛宪法去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此场景内,伟大的制宪者和堕落的当代人形成了二元对立,死亡之手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有德先贤的统治。
第二种论述是实用主义的论述。根据这一理路,之所以当代美国人还要服从两百年前的宪法,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当代人基于便利的考量而做出的选择。换言之,之所以这部两百年的宪法在当下仍有其权威,原因就在于有它要比没有它更好、更方便和更便利。
“尽管美国宪法有其缺陷,但总体说来,宪法是件好事,因为它解决了那些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予以解决的问题”,“有时候,更重要的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正确地解决问题”。在斯特劳斯教授看来,一部由两百年前的男性白人有产者所制定的宪法,今天已经无所谓道德意义上的权威,“宪法条款的约束力根源于它解决争议的功能能力,而根本不是制宪的主体应当被服从或者得到‘忠诚’”。*David Strauss, “Common Law, Common Ground, and Jefferson’s Principle”, 112 Yale Law Journal, pp.1725,1734, (2003).而美国宪法的定纷止争功能,主要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争议各方都承认的“共同基础”,如果没有这个由宪法提供的“说服平台”,*“说服平台”,参见Balkin,supra note 20, pp. 129-137。有些激烈的政治争议就失去了妥协的基础,无法得到和平的解决,结局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或者共同体本身的分崩离析。
第三种论述以政治哲学的资源去认真对待先定承诺的正当性问题。此论述起始于杰斐逊在《独立宣言》内所说的美国立国原则:政府的正当性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因此一部宪法是否有让我们遵守的权威,就在于它是否得到了我们的同意,这是人民主权学说的一种表达。*参见Akhil Amar,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outside Article V”, 94 Columbia Law Review, pp. 457-508, (1994)。
同意学说比较成功地解释了公民为何要守法的问题,但宪法作为一种根本法却对此学说提出了严肃的挑战。因为宪法是“管长远”的根本法,其所写入的是先定的承诺,因此,最简单的同意学说无法解释为什么当下的人要服从宪法文本内的先定承诺,因为活着的当代人并没有对其表示过自己的同意。生活在今天的美国人并未参与费城宪法的起草、选举和批准过程。更何况,1787年的制宪主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时代局限的“我们人民”,至少黑人、女性、未成年人和无产者都被排除在这次“民主盛举”以外。*在进步主义的历史叙述中,费城制宪本身即是有产者对革命果实的篡夺,参见(美)查尔斯·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何希齐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而且,美国宪法是文本上最难修正的宪法,两百年来仅有27条修正案,不是每一代人都有机会参与修宪的民主盛举。布莱斯特教授早在1980年就指出:“美国宪法的权威来自于其批准者的同意,这是最深植根于美国传统的政治理论。但即便是宪法批准者曾自由地表示对宪法的同意,这也并未能形成一个充分的基础,要求对这一建国文件的继续忠诚,因为那一代人的同意不可能约束后来人。我们并没有批准这部宪法,宪法的批准者已经死去,已经离开。”*Paul Brest, “The Misconceived Quest for the Original Understanding”, 60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p.225, (1980).
既然简单的同意学说无法挽救一部古老宪法的命运,同意论就发展出形形色色的修正版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隐含同意”论。根据这种修正版本,同意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推定或隐含的。保守派学者巴内特曾将隐含同意学说的逻辑概括为“不爱它,就离开它”(love it or leave it)。“同意的真正根源是‘我们人民’对政府形成的原初同意,自此后,只要人民并没有成功地对政府造反,就可以认为他们已经隐含地对政府表示同意。”*Randy Barnett, Restoring the Lost Constitution: The Presum Ption of Liber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0.换言之,只要一位公民没有通过自杀、移民或造反而选择“离开它”,那就是“爱它”,也由此可推定出“同意”。但这种对同意的推定实属牵强,难以证成先定承诺的民主正当。
(二)回到共同体:从自由主义到社群主义、共和主义
在人民主权学说的脉络内,同意理论展示了一个有希望的思路,但问题仍在于制宪者和“我们”在这一思路内所形成的二元对立。对宪法表示同意的是建国时刻的制宪者,但制宪者不是“我们”,而是已经故去的他者,能构成同一个我们的就是活在当下的人。在本文看来,与其在同意的认定上做手术刀般的技术修正,不如回到一个事关政治共同体的根本问题:美国宪法开篇以“我们人民”进行效力的自我宣示,那么宪法理论就必须回答,作为美国宪法的书写者,“我们人民”在时间性的维度内究竟是复数的主体,即每一代都形成了彼此间相互独立、而仅在空洞的时间维度内有过切面交接的共同体,还是一个在时间流转过程中所形成的绵延的共同体(temporally extended community)。而如果我们人民是一个单数,那么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了一个我们,让不同世代生活的人可以认同一个“我们人民”?
回答以上问题,就需要一个关于“我们”的叙事,讲述一个有关“我们”的故事。但这个关于我们的宪法故事,却不可能在自由主义学说中找到其伦理的资源。社群主义哲学家麦金太尔就曾批判自由主义的个人是没有叙事能力的:在回答“我应当做什么”的问题时,首先应当去回答一个更前的问题,“我自己构成了哪一个故事的片段”。*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7, p. 216.因此,如果要重新讲述一种有关个体、共同体和时间的故事,就必须从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政治学说中寻找新的资源。
1.自由主义学说的缺失
杰斐逊的幽灵在承载着先定承诺的宪法之上盘旋。杰斐逊设想的是每一代人都能重新开始的政治,在他的共同体模式中,每一代人都似寄居于偶然时空内的过客,他们没有能力“继往开来”。而这种在时间绵延过程中仅占据一格的共同体模型,就是一种没有时间感的共同体。
自由主义所理解的共同体就是这种没有时间感的共同体。以罗尔斯的论述为例,在《正义论》的开篇,罗尔斯就对社会有一个定义,社会是“自给自足的个人联合体”,“为了相互利益的合伙”。具体地说,个人认识到生活在一起有可能让彼此生活的更好,所以大家选择生活在一起,正义原则就旨在分配由社会共处和合作所产生的权利、义务以及收益和成本。*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4, 6.
由此可见,根据自由主义的学说,社会不过就是一个“合伙”,个人是先于社会共同体而存在的,社会本身即根源于人的选择或授权,而选择或授权都是基于利益的一个理性判断。罗尔斯的关键工具“无知之幕”正可以表明,在原初情境内立约的个体都是没有故事的,没有“叙事能力”的。事实上,正是这种没有故事的个体才有最大程度上的选择自由,而正是个体的选择决定了个体以及共同体的身份。根据桑德尔对罗尔斯的批判,自由主义所设定的个体是一种离群索居的自我(unencumbered selves),是先行个体化(antecedently individuated)的和彻底脱嵌(radically disembodied)的主体。在无知之幕下的原初状态内,个体是没有面目的,“没有了眼睛也没有了嘴唇”,他无法讲述自己的故事,因此不可能结成一种在时间维度内代际绵延的共同体。*Michael San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社群理论的批判
自由主义认为,“对于离群索居的自我来说,最重要的,对我们的个人性而言最本质的,并不是我们选择的目标,而是我们选择目标的能力”。*Michael 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 America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2.但问题在于,虽然活在当下的个体可以实现选择能力的最大化,但对于生活在社会内的个体来说,选择的能力与“讲故事”的能力是成反比的。麦金太尔也正是基于此提出了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自由主义的个体是没有故事的,由此他提出了“叙事性自我”的概念。自由个人主义认为每一个人都是“赤裸裸地”来到这世界,我的故事来自于我的选择,而不是“一个人的继承”,但麦金太尔认为“我的生活故事总是嵌入在共同体的故事中,从共同体那里,我得到了我的身份。我生来就有一个过去;个体主义的模式希望去隔断我自己和那个过去,这是在扭曲我当下的关系”。*MacIntyre,supra note 34,p. 221.
对于叙事性的自我来说,我应当做什么并不完全取决于我的选择,而是要回到“我发现自己构成哪个或哪些故事的一部分”。每个人一降世就镶嵌在一种或多种叙事之中,人这一世并非只活在由出生到死亡的自然生命,他有未出生前的过去,也有死亡后的未来。同样,在另一位社群主义者沃尔泽看来,“自由主义的实践看起来是没有历史的”,自由主义想象的都是“完全孤独的个体”、“理性的自我中心者”、“由不可让渡的权利所保护并且孤立开来的人”。*Michael Walzer, “The Communitarian Critique of Liberalism”, 18 Political Theory, p. 7, (1990).在组成社会后,个体“想象他享有着权利,社会就是相互陌生的自我们的共存,因为自由主义的权利……更多的是关于退出(exit)而不是声音(voice)的权利”。*Ibid., at 8.沃尔泽对自由主义个体观也有深刻的批判:
自由社会的成员没有共同的政治或宗教传统;他们仅能讲述关于他们自己的故事,这就是从无到有的创世故事,故事起始于自然状态或原初情境。每一个人都相信他自己是绝对自由的,无所拘束的,自治自决的,而仅仅是为了风险的最小化,才进入社会,接受义务。*Ibid., at 7-8.
……
我们自由人可以自由去选择,而且我们有权去选择……我们难以记忆起我们昨天做了些什么;我们也无法确定预测我们明天将会做些什么。我们不可能提供一种有关我们自己的适当叙述。我们不可能坐在一起,讲述整全性的故事,而且我们发现自己的故事,只不过是没有情节的碎片化叙述,如同无调音乐和抽象艺术。*Ibid., at 9.
3.共和主义的批判
“我们都是共和主义者了”,有学者这么形容上世纪80年代美国宪法理论“共和主义复兴”的盛举。*共和主义在美国宪法学内的复兴,可参见《耶鲁法学杂志》(Yale Law Journal)在1988年第97卷的第8期,为“共和主义宪法理论”的专辑。共和主义复兴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其核心是以共和主义的理论资源去批判美国政治的多元主义模式。本文没有必要梳理共和主义复兴的理论全景,仅选择讨论其中最具影响力但在中文学界未能得到应有关注的弗兰克·麦克尔曼的论述。
麦克尔曼宪法理论的内核始终指向美国宪政实践中一种根本性的二元对立,他在不同时段对此二元对立有不同的表达。在《宪法书写》中,麦克尔曼提出了所谓的“权威—书写综合症”。*Frank Michelman, “Constitutional Authorship”, in Larry Alexander, ed., Constitutionalism: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67.根据他的论述,成文宪法的书写是一种历史事实,而宪法以及宪法文本所写入的政治原则却具有当下的规范权威,这其中的紧张就是“我们应当如此,因为他们指示如此(We ought to, because they said so)”,因此生成了“权威—书写综合症”,也即宪法如何通过“书写”的历史事实而取得了当下的规范权威。在更早期的《法律的共和国》中,麦克尔曼使用了另一对范畴来表达这种根本的对立:“自治政府”与“法治政府”。*Michelman, supra note 6,pp.1500-1503.自治和法治同是美国宪政的基础,但两者在实践中却有着深层的紧张,因为“自治”的主体是“我们”,是当下之治,而“法治”的主语是法律,法律必定是生成于某个先于当下的时刻,是过往之治。就此而言,美国宪政如何可以既自治又法治,在时间性的维度内显然构成了一个问题。在麦克尔曼看来,这是美国宪法实践所提出的一个困难、艰深并且永恒的问题。*Michelman, Brennen and Democr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4-5.
在1988年《耶鲁法学期刊》的“共和主义”专号中,麦克尔曼受邀写作“头条”文章“法律的共和国”,文章起始于“自治”和“法治”的讨论。首先,自治和法治都是“宪政主义的共识”,“政治自由的要求”,应为所有人尊重;但“我们人民”和法律又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秩序,前者要求“人民自己去决定那些统治其社会生活的规范”,后者要求“人民享有免于恣意权力的保护”,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紧张。*Michelman, supra note 6, p. 1501.根据麦克尔曼的观点,解决这一紧张的关键在于能否形成一种政治,让法治的主语“法律”同时也是自治的主体“我们”。而自治与法治的统一需要社会规范性共识的存在,但现代社会的多元性却已摧毁了这种共识的基础。“如果有哪种社会条件定义着现代美国政治,这就是多元性,就此而言,现代美国如何形成‘法律生成的政治’(juris generative politics)?”*Ibid., at 1506.只有在这种“法律生成的政治”中,所形成的法律才能是“我们”的法律,而我服从法律也就是服从我自己的意志,是一种“自缚”,而不是外来异己力量的宰制。“调和宪政的两个前提,看起来要求我们设想到一种法律生成的政治的可能性,它有能力赋予其立法产品以一种作为‘我们的’法律的‘效力感’。”*Ibid., at 1502.
“法律生成的政治”是一种“我们”的政治。但问题在于到哪里去寻找“我们”。在麦克尔曼看来,日内瓦的公民可以通过直接民主来实现积极自由,但对美国人民而言,全国政治不可能提供一种真正的自治舞台。他在1986年发表于《哈佛法律评论》的经典论文“自治政府的踪迹”内指出,美利坚民族“看起来注定要承诺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主权分离”,“国会不是我们。总统不是我们。空军不是我们。‘我们’并不‘存在于’这些有机体内。它们的决定并不是我们的自治”。但麦克尔曼在这里所否定的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人民可以出现在美国政治中,却并未因此否定自治的可能性以及人民主权的修辞。而所谓“自治政府的踪迹”也就是要重新去发现“我们”,建构起一种有着“制度化纪律”的“法律生成的政治”。*Frank Michelman, “Traces of Self-Government”, 100 Harvard Law Review, p.75, (1986).
麦克尔曼的答案就是共和主义的审议政治,原本理性自利的私人在进入政治后就成为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公民,他们所参与的政治审议就定义了一种法律生成的政治。换言之,共和主义的审议政治可以最大限度地去调和自治和法治的张力,可以在多元性的现代社会生成“我们的法律”,服从法律就是在实践一种公共自由。可以说,以麦克尔曼为代表的共和主义宪法理论,最大的启发就是对“我们”这个概念的再讲述。
(三)人民的两个身体
美国宪法是“我们人民”所写就的,因此,如果人民自建国迄今形成了一个生生不息的单数主体,那么信守宪法内的先定承诺,就实现了根本法与人民主权的综合,因为先定承诺对我而言,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力量,而是我个人以及我们这一代人所嵌入的我们人民的意志。但难题仍在于,在一个以多元合理性为前提的现代世界内,在一个文化革命后以杂多主义为标签的当代美国,在一个以重新发现亚文化为政治正确的学术场域内,如何才能想象一个在时间进程内寓杂多于单一的美国人民。换言之,我们人民何以构成一个单数的共同体,为什么每一代的新人换旧人并不会增生出一个全新的共同体,*巴内特教授认为,我们人民不过是一种“虚构”,参见Randy Barnett, “Constitutional Legitimacy”, 103 Columbia Law Review, pp. 111-148., (2003);斯特劳斯教授基于实用主义的立场否定存在着一种“世代相继的美国人民”:“今天的许多美国人并不会怀有对前代美国人的忠诚,他们与前代人之间没有关系或联系”,做一个美国人并不需要信仰“美国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统一性”或者“准种族的美国身份”。参见Strauss,supra note 28, pp.1723-1725。反而是在生成一种生生不息、世代绵延的共同体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提出“人民的两个身体”的命题。*此处的讨论受到“国王的两个身体”的启发,参见Ernst Kantorowicz, The King’s Two Bodies: A Study in Mediaeval Political Theolog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国王已死,国王万岁”,同理,我们人民也有两个身体,一个是每一代人必将衰朽的肉身,另一个是每一代人都参与创造和维护的文化身体。如要进一步阐释此命题,就要回到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这就是人有时间感,有记忆能力,因此是一种政治动物。牲口是没有时间感的,也因此牲口的世界没有进步,所有的只是周而复始但原地踏步式的循环往复。而人之不同就在于“他无法学会忘记,其总是留恋于过去;不管他跑得多远,跑得多快,那锁链总跟着他”。*(德)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页1-2。人不仅无法忘记过去,人也无法逃避未来,“在所有有生命的物体中,只有人类自觉地预期着死亡;在死亡必至的预期下选择如何行动——思索着如何死去——这随之而来的需要就将我们人类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经营死亡的需要是人类特有的命运。”*Drew Gilpin Faust, 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s: Death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Knopf, 2008, p. xiv.由是观之,纵然现代人越来越生活在一个扁平的时空内,活在当下已然成为现代人的潮流,但人仍然无法摆脱过去和未来的重负。
也是在此意义上,英国政治理论家伯克有过一段经典的“人非苍蝇”的论述。一个夏天内的苍蝇,生命是短促的;但仅就生命长度而言,人和苍蝇不过是程度之别。根据伯克的论述,人之所以会沦为苍蝇般生活,就在于一代人将自己作为共同体的主人,不承认祖先所规定的先定承诺,由此造成法制的朝令夕改和共同体的变动不居。每一代人的政治都自成一体,这在杰斐逊看来是民主自治的真谛,而在伯克眼中就是如苍蝇般的生活。在此意义上,动物之区别于人就在于它只有当下,隔绝于过去和未来,动物在代际链条内只不过是周而复始地重复着,没有继承,也谈不上传承。“苍蝇的每一代都重新开始其故事,没有背负对过去的重负和对未来的义务……正是这种与过去和未来的断裂,使得苍蝇的生命在人看来是如此异类。”*Anthony Kronman, “Precedent and Tradition”, 99 Yale Law Journal, p.1050., (1990).
人不同于苍蝇,就在于人不仅生存在一个自然世界内,还生活在一个文化世界内。根据耶鲁法学院前院长科隆曼的阐释,文化世界是一个区别于自然世界的人造世界:自然世界是一个纯粹的物世界,而文化世界是一个意义的世界,一个符号的系统。文化世界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是“可积累的”,人可以进行那些在一代人的时限内无法完成的工程,由此人就具有了对抗自然命运之暴政的能力。第二是“可毁灭的”,这是指文化世界的人造物并非一劳永逸的永恒,“如果不能加以适当保育,它们终将会失去,仅仅将它们书写下来从来不足以将之维持,因为有很多法律和诗歌的书籍,我们虽然拥有,但却无从知道如何去阅读……保护一个法律的体系要求这样的教育项目,它可以向每一代新人介绍法律,让新人们学会解释法律的方法。”*Ibid., at 1053.文化世界的脆弱性,就要求每一代人都自觉地作为共同体在当下的“租用者”,在先人和后人之间承担起“信托”责任。而且,也正是在这种无实体的文化世界内,一个共同体才成为了生生不息的共同体,而不是陷入每一代人反对每一代人的战争。反之,如果只是在断裂的自然世界内求生存,失去了文化世界的传承和连续,那么人就只有短促而可鄙的此在生命而已。
回到伯克,人如果像一个夏天内的苍蝇那样生活,“首当其冲”的后果就是人类将不再学习“法理科学”(science of jurisprudence)。法理科学是“人类智识的骄傲”,它虽然有种种“缺陷、冗杂和错误”,却是“世代积累而成的理性”。*伯克,见前注〔2〕,页127。而一旦人不再学习法理科学,“用不了几代人,共和国本身就会瓦解,分崩离析为个体性的尘埃,最后随着天上的风而消逝”。*伯克,见前注〔2〕,页128。正是以这段有关“法理科学”的阐释为过渡,伯克才得出他最著名的结论:如果国家是一种契约的话,那么此契约是发生在活着的人、死去的人和将会出世的人之间的。在此意义上,一个共同体是不是有宪政,并不在于它是不是有一部成文宪法,也不在于成文宪法是否已经司法化,而在于这个共同体是否生成了作为我们的法律的先定承诺,可以有效地约束当代人以及任何一代人首先不去违反先定承诺,以防后世人在危机时刻陷入疯狂状态,作心血来潮的回应。*宪法并非一部自杀契约,可参见(美)理查德·波斯纳:《并非自杀契约:国家紧急状态时期的宪法》,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罗杰·斯坎伦顿曾借用伯克的概念去批判自由主义的国家:“自由主义的国家没有家园,无法生成一种跨越代际的忠诚,因此不可能在已逝去的和未降生的多代人之间形成一种契约”。而哈贝马斯在论述二战后德国的宪政爱国主义时也曾有过同样的阐发:“通过一张家族、地域、政治和智识传统编织起来的网,也就是通过一种塑造我们今日之身份的历史语境,我们的生活形态就与我们的父辈以及祖辈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我们无人可以逃脱历史的语境,因为我们的身份认同,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德国人,都已经与之不可分割地织缠在了一起。”*Jan-Werner Müller, 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7.
由此可见,宪政需要建立在一种社群主义的共同体基础上。我们可以从社群主义的叙事性自我推演到宪法理论的有叙事能力的共同体。在社群主义的论述中,个人的故事首先是镶嵌在共同体自身的历史叙事内的。保罗·卡恩在论述个体和共同体生成的同一性时曾写道:“就在共同体的身份得以创造和维持的那个过程中,我们也创造和维持了我们的个人身份。因此,在历史意义上具象的沟通,位于社群主义理论的核心,同时创造了个体和共同体。脱离了创造和维持共同体的沟通,个体身份不会存在。”*Paul Kahn, “Community in Contemporary Constitutional Theory”, 99 Yale Law Journal, p.5., (1989).而人民的文化身体也正是生活在这种有叙事能力的共同体内,由此才在宪法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成其为一个单数的我们人民。
既然我们人民不再是一个线性时间观内的“瞬间”的“偶在”,并不寄寓在从过去、现在到未来的时间流以内,而是存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彼此交融的“可能世界”内,形成了一个单数的共同体,那么由此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在代际关系上既非西式的“交接”,也非中式的“反哺”,而是一种生生不息、世代绵延的共同体。在此意义上,人民对宪法的历史书写,每一代人对所继承而来的先定承诺的信守,非但不是自由派所标签的“死人之手的统治”,反而成为了一种高级法意义上的自治,由此调和了宪政和民主、法治和自治、根本法和人民主权、历史书写和当下权威等种种困扰美国宪法学者的二元对立。
三、 宪法叙事的生成及其技艺
“这一革命的共同体具有一种跨越时间式的存在:所有的个人——现在的和未来的——都是作为人民主权的成员而参与其中。基于这一原因,建国者的行为可以继续约束未来的世代:所有人都是一个单数我们的组成部分。”*Paul Kahn, “Political Time: Sovereignty and the Transtemporal Community”, 28 Cardozo Law Review, p. 271., (2006).美国宪法之所以可以生生不息地“活”起来,是因为美国人民在历史发展中通过共同的奋斗、牺牲和记忆而结成为同一个共同体——不仅是由地理空间所定义的,还是由时间所塑造的。只有我们认同一部我们继承而来的宪法,使之成为“我们的”宪法,宪政才找到了它的伦理基础或文化资本。巴尔金曾写道:“南非宪法可能被广泛地称颂为当代宪法制定的典范之作,但它并不是我们的宪法”,“当我们认同并且热爱一部宪法,宪法就成为我们的法律,而无论我们是否以一种正式或者法定的形式对宪法表示了同意。”*Balkin, supra note 20, p.60.
巴尔金的表述实际上道出了人民主权理论的关键缺失,现有的论述将人民的意志归结为“正式或法定形式的同意”。但巴尔金在此却区分了同意与认同及热爱,当且仅当我们认同并热爱一部宪法时,这部宪法才成为我们的宪法。巴尔金的区分指向着一种更普遍的二元对立,一方面是基于理性审议的同意,另一方面是基于意志表达的认同。在此二元对立下,宪法正当性的论述大都是“政治科学”的变种:建构出种种可操作的标准,去认定是否存在正式、法定或隐含的同意;但基于意志表达的认同、热爱和信仰,并不是可以用科学手段加以复现、测量和统计的,而需要政治神学的学说才能去感知。*关于美国宪政与政治神学,参见Paul Kahn, Political Theology: Four New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如巴尔金所言,虽然南非宪法被公认为现代宪法的典范,美国宪法却留存着时代刻下的尴尬错误,但美国人民不会认为南非宪法是我们的宪法。即便“世界是平的”,美国人也不会认为他们和南非人构成了同一个我们。为何我们可以成为同一个我们,回答这一问题,关键在于要理解政治信念就其本质而言是以下所讲的“使相信”。“使”相信,是在告诉我们,信念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生成在一种有关共同体的历史叙事之中的,在此意义上,现代国家不仅是“想象的共同体”,还是一种“被想象”或“叙述”的共同体,正是在这种叙事中,我们才可以跨越不同的代际而共同起来。
(一)叙事宪政
“每一部宪法背后都有一部史诗”,巴尔金近期也在论证他的“叙事宪政”的概念。所谓叙事宪政,就是去讲述有关宪法的故事:宪法成为我们的法律,与我们将自己想象为在历史流变中同一个我们人民,是两面一体的。一方面,宪法成为我们的法律,有助于培育我们人民的政治认同;另一方面,唯有每一代人都有此历时而不变的政治认同,宪法才能成为我们的法律,这在逻辑上似乎是一种循环论证,但叙事宪政在实践中就是如此水乳相容。因此,美国宪政的文化基础在于一种作为公民宗教的宪法信仰,*Sanford Levinson, Constitutional Fa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但信仰则生成在一种历史叙事之中。“将美国宪法视为‘我们的宪法’本身就是一则宪法故事——一种构成性的叙事,经由这一叙事,人民将他们自己想象为一个分享着记忆、目标、愿景、价值、义务和理想的共同体。”*Balkin, supra note 20, p.61.因此成功的宪政都是一种有故事的宪政,因为只有在故事的讲述中,我们才能养成对现有宪法的“热爱”。热爱是一种信仰,“热爱是一种不同于同意的态度”,正是有了对宪法的热爱,“生活在宪法下的人民——美国人民——才将这部宪法理解为他们的宪法”。*Ibid., at 60, 61.
关于如何制造政治和宪法信仰,埃德蒙·摩根在《发明人民》中曾有精彩论述:
政府必须制造信念(make believe):使人相信国王是神圣的,王权不会为非作歹,或者,使人相信人民的声音才是圣音;使人相信人民可以直接发出声音,或使人相信人民必须由代表发言;使人相信统治者是人民的仆人;使人相信所有人生而平等,或者使人相信他们并不平等。*Edmund Morgan, Inventing the People: The Rise of Popular Sovereignty in England and America, Norton & Company, 1989, p.13.
摩根的表述有意识地告诉读者,信仰的实体内容经常是并不重要的,政治的关键在于总有一些东西可以成为信仰。回到摩根的语境,他的问题是现代政治在消灭了国王作为“国家的神秘肉体”后,如何重新确立主权。如保罗·卡恩所言:“民族是一个信念的共同体……革命杀死了国王,但也宣布了一种新主权的存在:我们人民。”*Kahn, supra note 62, p.266.在此意义上,摩根的“发明人民”论,所讨论的就是人民主权是如何完成对君权神授学说的革命的。根据摩根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人民在现代政治中本身就是一种“信念”:“政府的成功要求虚构的认受,要求自愿地中止怀疑,要求我们相信国王是穿着衣服的,即使我们看到赤裸的他……英国和美国的人民政府是建立在虚构之上的,苏联政府同样如此。”就此而言,我们人民是一种“虚构”,并不就像巴内特所批判地意味着人民主权学说的失败。准确地说,现代政治中的人民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虚构,是需要“发明”出来的,“人民的同意必须由意见(opinions)来维持”,*Morgan, supra note 68, p.13.因此人民的同意以及人民主权本身就是意见的产物,而非取决于私法学说中要约承诺的认定标准。
(二)宪政叙事的模式
美国宪政是一种有故事的宪政,本文在此归纳美国宪政文化中现有的五种叙事模式,分别为:①创世纪的迷思;②连续性的建构;③永恒性的想象;④同一性的认同;⑤进步性的叙述。*本节的讨论或可归为卡恩所说的法律的“文化”研究,参见Paul Kahn, The Cultural Study of Law: Reconstructing Legal Scholarship,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1.创世纪的迷思
美国是一个宪法共同体,正是宪法将美国建构为一个历时而存在的共同体。而且,美国制宪者起草了人类政治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典,*但这并不意味着成文宪法典涵盖了美国宪法的全部,美国也有“不成文宪法”,参见Akhil Amar, America’s Unwritten Constitution: The Precedents and Principles We Live By, Basic Books, 2012。这就区别于英国政治传统中那“亘古以将”的“古代宪法”——美国宪政有其可确定的诞生日。阿玛教授的《美国宪法传》,正文第一句话就讲:“It started with a bang”;第一章解释美国宪法序言,章名为“In the Beginning”,最好不过地表达出费城制宪乃是美国政治之“创世纪”的意涵——革命领袖们以我们人民的名义为自己以及子孙后代立法,此政治作为实在是开天辟地式的史诗,标志着政治时间的开启。*Akhil Amar, America’s Constitution: A Biography, Random House, 2006, pp. 5,5-53.
现代宪法的制定都是人民主权的绽放。制宪本身是一场革命,而革命则是政治时间的分水岭,以革命为分界,可以将时间分为“制宪前”和“制宪后”的两个阶段。更重要的是,制宪之后,制宪前的历史就被吸纳入一种新的叙事。在此意义上,建国前的历史是没有政治意义的,它所呈现出的都是一种追溯既往式的再建构,“殖民地时期的美国经验并不被理解为一种英国人的生活,而是一种为了美国独立的训练”,“过去就重新编入了革命的叙事之中”。*Kahn, supra note 62, p.274.过去成为为了新开始的预备,新开始才是真正的开天辟地。
早在1776年,独立战争刚打响第一枪,约翰·亚当斯就在抒发着革命者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壮丽情怀:“我亲爱的朋友,你和我生活在即便最伟大的古代立法者都会羡慕的时代!”*转引自(美)拉里·克雷默:《人民自己:人民宪政主义与司法审查》,田雷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页75-76。而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四篇内,麦迪逊已经在主张美国道路的普遍意义:“这是美国的幸福,我们相信,这也是全人类的幸福,革命者在追寻一种新的、更崇高的事业。他们完成了一场在人类社会编年史中无可比拟的革命:他们在地球上建立了史无前例的政府组织。他们设计了一个伟大的联邦,他们的后世有义务改进它,使之永存。”*(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页70。要知道,当时费城宪法草案前途未卜,美利坚民族的命运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现实世界无比暗淡,但丝毫未见联邦党人因此心灰意冷,麦迪逊的修辞显然是要他的读者纽约州民众“使相信”。
创世纪的迷思之所以生成,不只是亲历历史者的“虚构”,更重要的是后来人在原初叙事基础上形成的信仰和再表述。美国制宪是开天辟地的史诗,历来就是美国保守派宪法论述的一个永恒主题。根据极端的原旨主义叙述,宪法的历史就终结在制宪时刻,自此后不再有我们人民,只有对祖宗成法亦步亦趋的“报废的人”。1986年,里根总统出席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和斯卡利亚大法官的任职典礼并发表演讲,这对于美国保守主义宪法运动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而里根在结束他的演讲时讲到:
韦伯斯特告诉我们:“奇迹不会再次发生,坚守住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以及在宪法基础上立起来的共和国——6000年的历史只发生过一次的事情,从不会再次发生。坚守住你们的宪法,因为如果美国宪法失败了,那么全世界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转引自Jamal Greene, “Selling Originalism”, 97 Georgetown Law Journal., p.713, (2009).
里根的话带有美国保守主义的典型修辞风格,就事实而言荒诞不经,但却洋溢着无知者无畏的天真烂漫,在这里如美国的自由派那样去批判此种叙事与史实不符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种叙事从来不是要在理性的场域内去说服自由派的知识精英,而只不过是要对美国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们进行“洗脑赢心”的政治动员。事实业已证明,美国保守派通过这种叙事,基本成功地夺回了对法律的控制权。这种将建国制宪神迹化的历史叙事,在美国保守主义内是层出不穷的。近期茶党运动的主要组织者迪克·阿曼就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声称,宪法是“一种如宗教经典的神圣文件,它由基督教信徒所起草,有可能得到神意的启示,起草者希望它能得到严格文本主义的解读。宪法包括了解决当代美国人所面临的全部公民问题的方案”。*转引自Sanford Levinson, “How I Lost My Constitutional Faith”, 71 Maryland Law Review., p.959, (2012).这是一种宣扬制宪者全知全能的叙事,而如果制宪者真的是“半人半神”,得到神意启示的宪法就是上帝为子民订立的圣约,信守上帝之法哪里还会有死人之手的问题呢?
创世纪的迷思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关键在于神话美国的革命、建国和制宪,让国父们成为真正的fathers,宪政因此就成为因父之名的统治,这虽然是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所不允许的,但确实是美国政治的一种现实。建国史学家戈登·伍德就曾指出:“没有哪个主要民族会像我们美国人那样尊重过去的历史人物,尤其是那些生活在两个世纪前的人物。”美国国父在离世前就已走上神坛,“等到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在1826年7月4日同日离世,而当天正是《独立宣言》五十年诞辰,神圣的光环就开始笼罩着建国一代人”。*Gordon Wood, Revolutionary Characters: What Made the Founders Different, Penguin Press, 2006, pp. 3-4.
而对于美国民众的历史意识的塑造而言,主要的不是象牙塔内的学术论述,而是大众通俗读物。1966年出版后重印至今的《费城奇迹》,影响了数代美国人的心灵,标题中的“奇迹”来自于该书题记所引的华盛顿的一句话:“在我看来,来自这许多不同的州的代表们,带着他们的方式、环境和偏见,可以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全国政府的政体,真不啻为一次奇迹。”*Catherine Drinker Bowen, Miracle at Philadelphia: The Story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Little Brown & Co, 1986.而奇迹既不是政治科学所能解释的,也不是社会契约所能设计的,面对奇迹,人只有信仰、服从,为之牺牲。《费城奇迹》只是代表,美国公共历史读物对于建国一代人的讲述可以说是不厌其烦,每年都会出版多本有关美国革命、建国和制宪的“普法”新著——建国奇迹的讲述还在继续,它不会终结,直至美国消亡。
2.连续性的建构
戈登·伍德指出,现今的美国人“会想要知道杰斐逊将如何思考少数族群平权行动,或者华盛顿将如何判断伊拉克战争”。*Wood, supra note 79, p.3.美国内战史权威麦克弗森也曾讲过一个故事,他曾在林肯诞辰175周年之际的一次演讲后接受电视采访,受访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林肯活到今天,他将对堕胎和预算赤字持何种立场?”麦克弗森就此指出,美国政治文化中有着一种“以林肯为参照系(get right with Lincoln)”的政治心态,这也是本文所说的连续性的叙事。*James McPherson, Abraham Lincoln and 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ix.连续性的叙事就是要勾连起制宪者的法律和当下的政治问题,以制宪者意图为准绳去解决当下的问题。
首先应承认,美国宪政的连续性并不只是由历史叙事建构出的信念,而首先是一个基本的法律事实:美国原初宪法,200年来仅有27次文本修正,至今仍是美利坚民族的根本法。我们视费城会议为“奇迹”,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事后的意义赋予,遮蔽了历史发展的开放性和偶然性:正是美国宪政的连续性事实让费城会议不是一场“失败的遗产”,而成为美国宪政胜利征途的原点。在此意义上,连续性的叙事是美国宪政的一个组织框架,正是有了这个叙事,美国宪政发展才有了一种目的论式的整体图景。拉克劳斯教授近期写道:“不同于许多现代宪政民主国家,美国仍处在其第一共和。这意味着由美国宪法所创造的、名为‘美利坚合众国’的这个实体,可以说是存在于从1789年到如今的一种连续性关系中。”而美国宪法的核心预设之一就是“2010年的共和国在根本意义上是与1789年的共和国相连续的”。*LaCroix, supra note 14, p.1330.
但更重要的是,两百年的故事始终只是一个“神话”或“迷思”。无论如何,与时俱进是必需的,不可想象一部18世纪的宪法可以原封不动地适用于今天的美国,只有一部宪法并不意味着这部宪法没有修正、转型和断裂。因此,连续性的叙事不能否认必要的宪政变革,挑战在于如何在叙事中吸纳变革的元素。换言之,是在连续性的叙事中定位变革,还是在变革的叙事中捕捉连续,结构的不同就意味着基调的区别。这样看来,美国宪政的连续性既是一种基本的法律事实,也无法离开叙事的建构,而如何在连续性的主旋律内吸纳变动的片段,同时又不至于颠覆叙事的基调,这就是法律人的工作。
美国宪政经典内俯仰皆是连续性的叙事。林肯葛底斯堡演讲旨在阐述一种“自由的新生”,但自由之所以新生,是发生在一种连续性的叙事内的。众所周知,葛底斯堡演说的第一句话就重现了一个我们与建国者同在的历史场景:“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所有人生而平等的原则。”由于创世纪的迷思和连续性的建构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保守派同样是连续性叙事的行家里手。原旨主义的兴起,之所以在2008年的持枪权案件判决后“我们现在都是原旨主义者了”,不只是因为其在学术市场上的成功营销,*Greene,supra note 77.归根到底,还是此学说所隐藏的连续性叙事更贴合美国沉默的大多数的政治心理结构。因为美国人相信,当下的我们与历史上的制宪者是生活在一个连续的共同体内,共享着一套语意编码的系统,*Lawrence Lessig, “Fidelity in Translation”, 71 Texas Law Review, pp. 1165-1268., (1993).正是因此,原旨主义在学理上早已是千疮百孔,而保守派对连续性修辞的操控也是路人皆知,但只要它迎合了美国人的政治心理,就可以实现对他们“洗脑赢心”的政治动员。
3.永恒性的想象
自由主义政治理论认为宪法是一种社会契约,美国制宪为之提供了最好的案例:数十位集政治智慧、经验、美德于一身的革命者齐聚费城,经过集体的深思熟虑设计出了一部“可自动运转”的宪法,*参见Michael Kammen, A Machine that Would Go of Itself: The Constitution in American Culture, Knopf, 1986。这对应着社会契约论的结构:从想象的自然状态出发,人们基于理性的能力经由协商谈判而形成了对社会规则的共识。*Kahn, supra note 62, p. 262.
但作为美国宪政的基础理论,社会契约论至少有三个局限。首先,社会契约论是非历史的。其次也与第一点相关,社会契约论无法解释美国宪政发展的过程和结构,“美国宪政作为一种实践……挑战了由社会契约传统所代表的自由思想的整体风格”。*Ibid., at 263.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社会契约的隐喻内含着不断革命的危险,而这与宪政的保守性是背道而驰的。卡恩曾写道:“无论本人的政治气质如何,社会契约的理论家都是革命的哲学家。他们在理论中植入了革命的可能,这表现为社会契约的再制定。”因此,如果宪法是一种假然的社会契约,那么宪政实践在理论上就有被不断革命切割成碎片化政治的危险,因为根据社会契约理论,一旦政治权力的运行违反了理性人在自然状态内所设定的条件,不仅是“越权无效”,也有可能导致政治权力的重组。*Ibid., at 262.因此,美国宪政如要想象一种“永恒性”,就必须超越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而青年林肯在一篇题名为《我们的政治永世长存》的演讲中就提供了一种超越社会契约论的永恒性叙事。*参见(美)亚伯拉罕·林肯:《林肯选集》,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页3-12。
面对着斯普林菲尔德青年学会的听众,当时尚且未到29岁的林肯在开篇就提出一个宪政问题,我们的政治制度并不是我们这代人所创建的,而是我们继承而来的,“它们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财产,我们的祖先曾是坚强、勇敢和爱国的,现在已与世长辞,深受哀悼”。而青年林肯告诉在座也许更年轻的听众:“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美好的国土和政治大厦传诸千秋万代”。林肯所提出的是一个根本的宪政问题,也就是如何守护我们所继承的祖宗成法。*同上注,页3-4。
但我们所继承的先定承诺如要长存,就必须考虑到“新形势所提出的新问题”:如果说新形势就是代际交接,那么新问题就是如何去继承革命。在林肯看来,我们政治制度的设计者已经离世,他们是亲历独立战争的一代人,“战争结束时,几乎每一个成年男子都亲身参加过斗争的场面。其结果是,在每个家庭中,那些场面都从丈夫、父亲、儿子或兄弟的身上反映了一部活生生的历史”。这是一种活的历史,刻画在残缺的肢体和伤口疤痕上,塑造着人民的情感。人性在和平年代的嫉妒和贪婪,在战争状态下就会受到制约,有时甚至会转化为公民参与的积极因素。但对于后革命时代的青年人来说,独立战争不过是书本上的知识,“它必将会被人们淡忘。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愈发模糊”,他们对于独立战争不再有先辈那样的感同身受,流血牺牲从“所见”变成“所闻”,最终成为“所传闻”。林肯动情地讲到,独立战争的经验“曾经是一座强大的堡垒”,但是“入侵的敌人永远做不到的,无声的时光的大炮却做到了”。因此,林肯这里所讲的就是如何在革命之后继承革命的问题:如何让革命者所留下的政治制度永存永续,这是宪政设计时必须自觉考虑的问题。*林肯,见前注〔90〕,页11-12。
在此时,共和国内部出现了一个“不好的兆头”:“全国普遍地越来越不把法律放在眼里,越来越倾向于以粗暴的感情替代法庭的严肃裁决,以颐指气使野蛮的暴民代替司法官”。在林肯看来,公民不守法或者共和国内的普遍不守法就会摧毁“人民对政府的深厚感情”。对此问题,林肯提出的应对之道如他所言那样是“简单的”:这就是每一个美国人都要守法,尊重法律,即便是那些所谓的“坏法律”,在通过常规的政治过程予以废止前,也必须得到严格遵守。*林肯,见前注〔90〕,页6-8。换言之,林肯是不承认所谓的公民不服从的,共和国的每一位公民都无权以所谓的良知或信仰自由去抵抗法律。
更重要的是,林肯在论述公民为什么要守法时所依据的是一种旗帜鲜明的历史叙事,而不是功利主义的趋利避害或自由主义的同意论。换言之,守法在林肯看来应是每个公民的政治信仰,是在革命之后对前人忠诚和对后人负责的一种“心理状态”,每一个美国人都要记住“违犯法律就是践踏他的前辈的鲜血,就是撕碎他自己的和他子女的自由宪章。让每一个美国母亲对在她膝上牙牙学语的婴儿灌输对法律的尊重;让法律在小学、中学和大学讲授;让它写进识字课本、缀字课本和历本;让它在布道坛布讲,在立法机关宣布,在法院执行。”*林肯,见前注〔90〕,页8。
4.同一性的认同
我们是如此不同,但又生活在同一部宪法之下。霍姆斯大法官尝言:“宪法是为具有根本不同观念的人们而制定的”,*J. Holmes, dissenting in Lochner v. New York, 198 U.S. 45 (1905).就此而言,如何在“众声喧哗”乃至“诸神分裂”的条件下,让先定承诺的宪法规范成为共同的游戏规则,在一部宪法必定会出现各自表述的情况下,不至于造成文化分裂乃至内战,就需要本文所说的“同一性认同”的叙事。换言之,宪法作为先定承诺,本质上是经由历史的政治斗争所形成的共识,而宪政就是按宪法的既定方针办,因此宪法就是“一”,而宪政就是要“定于一”,也是在此意义上,宪政就要解决“由谁说了算”的问题。
查尔斯·休斯在担任纽约州长时就曾说过:“我们生活在一部宪法下,但宪法是什么却是由法官说了算的。”当然,在现代社会科学的检验之下,所谓“大法官说了算”的命题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希望”。*Gerald Rosenberg, The Hollow Hope: Can Courts Bring about Social Chan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但从宪政文化的意义上去关照,这种司法审查的神话恰构成了一种同一性的叙述。在此问题上,杰克逊大法官有过一番更坦诚的现身说法:“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永不犯错才成为终局审;而是因为我们是终局审,我们才不会犯错。”无论是“说了算”,还是“终局审”,所说的都是一种同一性的叙事,就是由谁来定纷止争的问题。近年,一批左翼背景的宪法学者高举人民宪政的理论旗帜,要去造司法审查的反,他们所招致的批评之一就是人民宪政会形成一种宪法解释的多元主义政治,因此破坏着宪法的安定性。*例如参见Larry Alexander & Frederick Schauer, “On Extrajudicial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110 Harvard Law Review, pp. 1359-1387, (1997).
罗伯特·卡沃的论文“法与叙事”可以说是阐释法律的多元性和安定性的经典。卡沃创造了一对相生相克的概念:“生法”(jurisgenesis)和“灭法”(jurispathic)。生法是指法律的生成,在一个多元社会内,每个社会群体都有本群体的叙事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法律的理解,因此生法的结果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格局。“正是这种形成关于共同仪式和法律的不同紧密程度的共同体的行为本身,才是通过法律分裂的法律生成”。因此,生法的过程及其形成的多元法律,是对社会多元性的一种正当回应。*Cover, supra note 9.
但一个社会不能只有生法,生法之后,还要灭法,而灭法的过程就是要确定谁才是法律中的法律,谁才是国家暴力机关所维持的法律,就是要“去伪存真”。这里的灭法更像是一个法社会学意义上的描述,它不那么清新、温情,不讲多元竞争、适者生存、言论自由市场或看不见的手,而是强调国家暴力及其在“罢黜百家”后的一元化。但现实的政治是,只有百花齐放式的叙事和生法并不能自动形成一个良好的法制,“法律规范在整个共同体内激增,这一生法的原则,从来不可能脱离暴力而单独存在。解释总是发生在强力的阴影下……法院,至少是国家的法院,就是这种‘灭法’的”;“值得指出的是,在神话和历史中,法院的起源和存在依据很少被认为是对法律的需求。正相反,法院被认为是基于要去压制法律的需要,在两种或多种法律之间进行选择的需要,为诸法律进行层级排序的需要。正是法律的杂多性,生法原则的多产,所造成的问题使得法院和国家成为了解决手段”。*Ibid., at 40.在此基础上,卡沃给出了一个非常具有革命性的判断:“法官是暴力人士。因为他们所掌握的暴力,法官通常不是创造法律,而是杀死法律。他们是灭法的办公室。面对着繁荣生长的争鸣百家的法律诸传统,法官主张某一传统是法律,同时毁灭或要去毁灭其余的传统。”*Ibid., at 53.
虽然卡沃在此文发表后不久即去世,但他这篇文章却成为美国引证率最高的论文之一,关于“生法”和“灭法”启发了一代又一代宪法学人的心智。卡沃关于生法的论述,蕴含着革命和变革的种子,尤其是他承认每一个解释共同体都在生成法律,反映出他作为民权运动积极分子所怀有的造反有理的精神。而卡沃关于灭法的论述也表明他不是一个只讲亚文化、多元合理和学术正确的学者,他非常清醒地指出:“任何一种法系统都必须是统一的,这是指其要有一定程度的意义共同性,才能使得连续的规范活动成为可能。”*Ibid., at 14.确实如此,美国作为一个宪法共同体,不能只有生法,因为随着各路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及其造成相互割据的多元法律格局,共同体会发生裂变;但是也不能只有灭法,因为如果法律完全是由一个代表国家暴力的主体的宣言,那么这种法律也对我而言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法治和自治之间也就出现了最大程度的撕裂。
生法和灭法是一对相生相克但又相辅相成的范畴。从生法到灭法,是一个共同体内多元主体之间相互接触、竞争和斗争的过程,没有这一个竞争和斗争过程,也就不会生成一个“我们”,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在宪法文化中,多元主体间的斗争实际上会重塑一个共同的过去,“过去,过去的意义,以及关于过去的记忆,都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可以利用和共享的资源。我们彼此之间可能会不同于过去意味着什么;我们可能会在过去中记忆着不同的东西……但吊诡的是,我们有关于过去的不同意见,却是那些让过去成为我们共同资源的东西。”*Jack Balkin, Constitutional Redemption: Political Faith in an Unjust Worl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5.卡多佐大法官在1935年经济大萧条过后也曾写下一句经典的同一性叙事:“联邦宪法所基于的理论是,各州人民必须浮沉与共,并在长远看来,繁荣和拯救在于联合而非分裂。”*转引自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168。
5.进步性的叙述
进步性叙事的主旋律是“明天会更好”。“更好”未必是尽善尽美,更多时候可能是要兑现现状所未能实现的承诺,也就是马丁·路德.金所说的那张因“资金不足”而被退回的空头支票。进步性的叙事需要延展到明天、未来或现在之后,其实质是主张当下一代人以及每一代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将美国建设成为一个更自由、更平等和更公正的社会。
美国宪法的序言本身也提供了一个面朝未来的目的论叙事:“我们合众国人民,为了形成一个更完善的联邦,建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御,促进普遍福利,并将自由的恩赐播及我们与子孙后代,特制定和创立这部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自此后,“A More Perfect Union”的表述就成为美国通俗文化讲述费城制宪的关键词。据说在制宪会议代表签署宪法草案之时,富兰克林指着独立厅内华盛顿座椅后的一幅画说,即便是艺术家也说不出画中的太阳是在升起还是在落下,但现在他告诉更年轻的代表们,“我终于有幸得知,这是朝阳,而非落日”,接着流下了热泪。*(美)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法院与宪法》,田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31。
进步的叙述所讲的就是我有一个梦想,只是这个梦不是个人梦,而首先是一个民族梦。约翰·马歇尔在1819年的美国银行案判词内,就在司法讲坛上阐释出了一个伟大的美国梦:“在广袤的共和国内,从科罗克斯海峡到墨西哥湾,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政府将征缴并且支出岁入,调遣同时给养军队。民族危机的关头可能要求北款南调,西税东流……难道我们的宪法解释应当让这些运作变得困难、危险和昂贵?”基于这段叙事,马歇尔吹响的是一种“司法民族主义”的号角,他的传记作者称他为“民族的定义者”。*关于马歇尔法院与司法民族主义路线,可参见G. Edward White, The Marshall Court and Cultural Change, 1815-183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关于民族的定义者,参见Jean Edward Smith, John Marshall: Definer of a Nation, Henry Holt and Co., 1996。但就事论事的话,“广袤的共和国”只不过是马歇尔用法律语言所书写的一个美国梦。在他写下这段话的1819年,美国并不“广袤”,其疆域远不是一个“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自由帝国”。就在数年前的1812年战争中,英国军队还一举攻占并放火焚烧了美国首都,美国可否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尚且存疑。而马歇尔是一位复转进法院的革命军人,因此他的判词不仅在讲述着美国的自由帝国梦,还时刻关怀着国家安全、民族建构和宪政彼此间的相互构成:“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我们正在解释的乃是一部宪法”,美国宪法“被设计去经受漫长岁月的考验,因此必须适应人类事务的各种危机”,而美国银行因为可以在“民族危机的关头”推动“北款南调”和“西税东流”,因此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适当与必要”的手段,因此是合宪的。
(责任编辑:章永乐)
中外法学Peking University Law Journal
Vol.27, No.2(2015)pp.391-416
(三)附论:走向美国宪政的文化研究
前文主要讨论了三个虽然可独立开来但更需要进行体系论述的问题,可概括为美国宪政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办。首先,美国宪法在时间性的维度内表现为一种先定承诺,而宪政就要求去信守先定承诺,此概念的内核决定了宪法政治在基本面上的保守性。其次,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先定承诺的政治会提出美国古老宪法的正当性问题,*关于宪法与正当性理论的评述,可参见Richard Fallon, “Legitimacy and the Constitution”, 118 Harvard Law Review, pp. 1787-1853, (2005)。这就是为什么已逝的制宪者制定出了垂范千古的宪法,在此意义上,宪法政治有它的伦理基础,必须生长在一种生生不息、代代绵延的共同体基础之上。再次,代际共同体的模式以及由此形成的宪法信仰,在美国从来都不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而是一种经由公民教育培养出来的政治态度,一种在历史叙事中生成的政治信念。
而本文对美国宪法的历史叙事做抛砖引玉式的探讨,旨在试验中国宪法学在面对和进入美国宪政实践和理论时的新视野与方法。长久以来,我们自觉地“像法律人那样去思考”,“等待戈多”式地“生活在别处”,不断重述着美国宪法历史和现实的“童话”与“神话”。而本文所试验的“文化研究”,则意图去探索我们能否“像人类学家那样去思考”并且以此为立足点去观察美国宪政的历史与实践,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面对美国宪政时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并且在此基础上找到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为什么法律人要饰演起人类学家的角色,原因还是在于宪法叙事与宪政建设之间的相互作用。宪法叙事的政治功能在于“制造信念”,在于“使相信”:在这个祖先污名化、道德扁平化、时间当下化和神圣世俗化的时代,历史叙事生成着关于国家和宪法的“神话”,由此参与到民族建构或国家建设的政治过程中去。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去体验美国宪法专业研究者所承受的身份张力:一方面,他们皓首穷经在学术专著内论证“国王原来没有穿衣服”。以列文森为例,他近年来在新著内直言批评美国宪政的“不民主”,甚至在文章标题内自我剖析“我是如何失去宪法信仰的”。但另一方面,这些学术专著的受众极其有限,大多数都归宿于大学图书馆那些无人问津的书架上,反而文化政治领域内却讲述着一个又一个有关宪法的神话、迷思和童话。列文森曾在费城制宪两百年之际出版名著《宪法信仰》,没有谁比他更理解宪法信仰在宪政实践中的基础作用。*Levinson,supra note 7,65,78。
这样看来,像法律人一样思考,在象牙塔内的青灯黄卷中潜心阅读那无人问津的书,我们只是在体验着美国宪政的“一个方面”。就好像巴内特以私法学说的标准去宣布我们人民只是一种“虚构”,我们也会在课堂上津津乐道着“宪法顶个球”的段子。但是,只要还停留在“一个方面”而未能自觉,我们对美国宪政的研究就陷入了卡恩所说的“当代法律学术的悖论”:“研究法律,我们却变成了法律的一部分,”*Kahn,supra note 71,p.2.而对中国学者来说,这里面甚至还嵌入了第二层的悖论,即我们研究美国法,却成为了美国法的一部分,忘记也可能是从来没有自觉意识到美国宪法在规范意义上是同我们“不相关”的。像人类学家那样去思考,就是要从听其言进入到观其行,从外部去观察美国宪法的“言”与“行”之间是如何既分裂又抱合的,事实上只有理解到美国宪法实践还有着“另一方面”,意识到美国宪政的历史与实践首先是一种特殊性的文化现象,我们才可能真正展开具有中国学者自身主体性的美国宪政的文化研究。
Abstract:For every constitution, there is an epic. This is especially the case for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history and practice. For the constitu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the most intriguing feature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epic is the impressive longevity of its Constitution, which was enacted in 1787 and had minor textual revisions throughout its journey of more than two centuries. This article, employing the methodology of cultural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meta-stability myth of the dominant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narrative and construct a new narrative, which is distinguished by a trans-generation synthesis combing the stability with the living aspect. In this new synthesis, the original Constitution is revered for it is enacted by the framers who are also the revolutionaries that won the War for Independence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 that united the United States. So long as there is the single American Republic, the pre-commitments written in the Constitutional text are and will be the reasoned will of every generation of this constitutional community. Since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constructed as a single temporally-extended constitutional community, constitutionalism, as a dialogue, struggle, and finally synthesis between generations, is democratically legitimate. In this sense, we must take seriously the narrative craft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history, which is overlooked in our current research and can be discovered by the observers outside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practice, employing the methodology of cultural study.
Key Words:Pre-commitment; the People;the Framers;Constitutional Culture;Historical Narra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