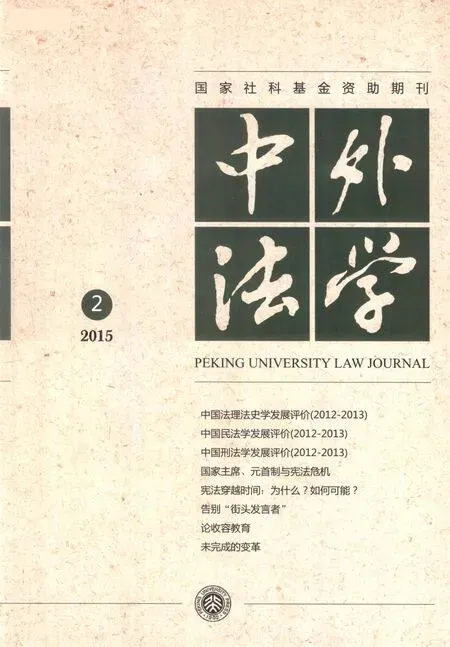执中行权的宪法比例原则兼与美国多元审查基准比较
杨登杰
执中行权的宪法比例原则兼与美国多元审查基准比较
杨登杰*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学院独立研究员。本文为作者负责的德国研究联合会项目“依违于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法治国家——以中国为焦点”(项目编号:YA 357/2-1)的研究成果。This work of Dr. Teng-Chieh Yang is supported under the project “ Rule of Law in the Tension between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 China in Focus” (Reference No.: YA 357/2-1) from the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DFG, German Research Foundation).
摘要就宪法基本权利的审查基准而言,一般最受关注的是源于德国的比例原则与美国的多元审查基准。与认为比例原则失于单一空洞,而多元审查基准较为精细详实的观点相反,本文认为比例原则绝非单一空洞。比例原则要求具体衡量、追求动态平衡,正体现了中国传统“执中行权”与“理一分殊”的精神,反映了“一”与“多”的辩证统一;若论精细详实,它实胜于多元审查基准。本文也认为,比例原则下的类型化、层级化不可与多元审查基准下的类型化、层级化等而视之,否则将扭曲比例原则的真谛。此外,比例原则能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既有诉诸普遍原则的大气与高明,又有关注具体脉络的精细与平实,既能切合中国国情,又能帮助我们以开放的态度走向世界舞台。
关 键 词比例原则多元审查基准基本权利法益衡量类型化
前言:从基本权利的审查基准谈起
现代宪法多有个人或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要求国家予以尊重与保障。然而,基本权利规定大多抽象而宽泛,在纷繁多样的现实生活中,往往会与各种各样的、同样被政治与法律共同体重视的其他原则、价值、利益、或者法益(包括其他基本权利或其他人的相同基本权利)相冲突。如果人们自始就将某一基本权利的内涵与范围界定得极为狭窄,一方面有望大幅减少它与其他法益发生冲突的机会,另一方面也能使对它的拥有变得极端重要而不可或缺,从而造就出它的绝对性,使在任何情况下与它相冲突的任何法益在它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而不得不最终退让。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与宪法学通说就是以这种方式确立了《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款人的尊严的绝对性与不可限制性。然而,绝大多数基本权利若以这种极度限缩内涵与范围的方式解释,将不免丧失希望较大范围地保障基本权利的宪法规范意旨,甚至背离宽泛的宪法规范文义。换言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宽泛的基本权利内涵与范围是必要的。但如此一来,基本权利与其他法益之间的频繁冲突便在所难免。为了合理解决这些冲突,不可能如上述情况一般主张基本权利的绝对性与不可限制性。也就是说,即使宪法没有明文规定可以限制基本权利,也必须承认在一定条件下限制基本权利的正当性与合宪性。
然而,限制基本权利究竟应该符合哪些条件,才不致违背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意旨?此一问题似乎难以单从宪法文本本身找到满意的答案。有时,宪法根本没有明文规定可以限制基本权利。*例如《美国宪法》 第1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立法剥夺宗教自由与言论自由等权利。有时,宪法只规定依法律得以限制基本权利。*例如《德国魏玛宪法》第111条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但以今天的认识而言,我们不可能因此认为,立法者制定法律可以任意限制基本权利,行政机关与法院解释、适用与执行法律可以不考虑基本权利。有时,宪法只用一个高度抽象而宽泛的总结性规定,将某一或某些目的——如他人权利的保障或公共利益的促进——列为限制基本权利的正当理由。*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1条。然而,如果根据这样宽泛的目的对基本权利所作出的任何限制都能被认定为合宪,宪法规定基本权利也就失去了意义。有时,宪法稍加具体地规定限制个别基本权利的正当目的、情况或方式,*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0条关于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规定。这虽然稍微缓解、但并未根本解决上述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会把这些目的、情况或方式视为限制基本权利的必要条件,但无法接受它们就构成限制基本权利的充分条件。有时,宪法加上了必要性作为附加条件,规定只有在对追求某一或某些正当目的有必要的条件下,才能限制基本权利。*例如《中华民国宪法》第23条。然而,难道只要对正当目的之实现有必要,就可以完全不考虑基本权利因此付出的代价吗?有时,宪法规定基本权利的本质核心无论如何得保持完整无缺。*参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9条第2款。姑且不论本质核心如何界定,我们还是不得不问,难道国家对本质核心以外的基本权利领域就可以随意处置吗?有时,宪法虽然对限制基本权利的条件作出较完整的总结,甚至列出在判断限制基本权利是否违宪时应该考虑的因素,*例如加拿大《1982年宪法法案》第1条、《南非共和国宪法》第36条、《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52条。但这样的规定或者由于不够明确,或者由于预设宪法学上的某些理论、学说或背景知识,因此在未获进一步解释前,尚不具可操作性。鉴于以上这些情况,为了合理解决基本权利与其他法益之间的冲突,对双方作出合理平衡,兼顾可以限制基本权利与应该保障基本权利的双重要求,最终还有赖宪法学界与实务界,针对限制基本权利的合宪性条件,发展出较完整而具可操作性的判断基准,也就是基本权利的审查基准。
或许有人会以中国宪法没有规定法律法规违宪的司法审查制度为由,怀疑在中国讨论基本权利审查基准的必要性。然而,就算撇开比较宪法上的意义不谈,只就中国现行宪法而论,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主体的法律法规违宪审查机制仍然必须面对基本权利审查基准的问题。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条第4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宪法;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因此,当法律与法规具有解释空间而包含多种适用可能性时,行政机关或法院就应该进行合宪性解释,选择符合基本权利要求的解释与适用方案。就算法院无权对法律与法规本身进行违宪审查,它仍然可以、也应该回答行政机关或它自己或下级法院对法律、法规——包括民事法律、法规——的解释与适用本身是否违宪而应予纠正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法律解释与适用层面,行政机关与法院仍然必须面对基本权利审查基准的问题。
基本权利的审查基准可大别为两类。一类是形式的审查基准,例如宪法对立法程序的要求。另一类是实质的审查基准,针对的是法律、行政行为与司法裁判的实体内容。在讨论借鉴外国制度与经验以发展我国自己的基本权利实质审查基准时,以德国为代表的比例原则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多元、层级式审查基准是大家最常关注的焦点。在对这两者进行比较并讨论其借鉴价值上,一些学者作出了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尽管本文对这些研究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但本文是建立在对它们的反思之上的,它们的前导性贡献自应予以肯定。在对德式比例原则与美式多元审查基准进行比较时,有一种观点认为,比例原则失于单一空洞,多元、层级式审查基准则有精细详实之长。*例如黄昭元:“立法裁量与司法审查——以审查标准为中心”,《宪政时代》第26卷第2期,台湾2000年10月;黄昭元:“宪法权利限制的司法审查标准:美国类型化多元标准模式的比较分析”,《台大法学论丛》第33卷第3期,台湾2004年5月;林来梵主编:《宪法审查的原理与技术》,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页318-329。而当原则上支持比例原则者主张比例原则也有或也能有宽严不同的审查层级时,似乎就是对这种批评观点的一种回应。*参见许宗力:“违宪审查程序之事实调查”,载氏著:《 法与国家权力(二)》,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版,页61-74;许宗力:“比例原则之操作试论”,载本注前引书,页124、126-127、129-131;台湾《司法院释字第584号解释》,许宗力大法官协同意见书。此外,还有学者鉴于两种模式各自有支持者,彼此难以有效沟通,因此尝试融合两种模式,提出“阶层式比例原则”的构想。*参见汤德宗:“违宪审查基准体系建构初探——‘阶层式比例原则’构想”,载廖福特主编:《宪法解释之理论与实务》(第6辑),台湾中央研究院2009年版,页1-78。
本文欲通过反驳上述对比例原则的批评观点,论证比例原则绝非单一空洞。比例原则要求具体衡量,追求动态平衡,体现了中国传统“执中行权”与“理一分殊”的精神,反映了“一”与“多”的辩证统一;要论精细详实,它实胜于多元审查基准。笔者也将分析,比例原则下的类型化、层级化不可与多元审查基准下的类型化、层级化等而视之,否则将扭曲比例原则的真谛。最后还将指出,比例原则能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既有诉诸普遍原则的大气与高明,又有关注具体情况的精细与平实,既能切合中国国情,又能帮助我们以开放的态度走向世界舞台。
一、 比例原则的基本内涵
比例原则源于19世纪德国,本来只是行政法上的原则。当法律规定留给行政机关裁量空间时,为防止裁量权滥用,于是以比例原则限制它。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宪法学通说,宪法基本权利的法律效果只在于要求国家限制基本权利时在形式上有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作依据。如此一来,基本权利实际上无异于依法行政原则下的法律保留原则,对立法者没有实质内容上的约束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反省纳粹专制与战争罪行所得出的结论之一就是,宪法基本权利必须对包括立法权在内的所有国家权力都有法律约束力。此一结论也被明文写进《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3款。然而,既然国家并非完全不可限制基本权利,如何对限制基本权利的国家权力再予以限制的问题因此产生。此一宪法问题在结构上与行政法限制裁量权的问题有相似之处。联邦宪法法院与宪法学者于是将原来用于解决后一问题的比例原则也用来解决前一问题,并对它作出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不但用它来审查法律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否违宪,也用它来审查行政机关与法院对本身合宪的法律的解释与适用是否违宪。也就是说,比例原则不但针对抽象的立法行为,也针对具体的行政行为与司法裁判。
今天,以比例原则作为基本权利审查基准的,除了德国,不但包括众多欧洲国家与组织,如欧洲法院、欧洲人权法院等,也包括有普通法传统的国家,如以色列、加拿大、南非等。*Alec Stone Sweet & Jud Mathews, “Proportionality Balancing and Global Constitutionalism”, 47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73, 112-160 (2008).甚至在以自己的宪政传统为荣、重视判例的美国,也有学者与最高法院法官主张采用或借鉴比例原则。*Bartnicki v. Vopper, 532 U.S. 514, 535-541 (2001) (Breyer, J., concurring); 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 554 U.S. 570, 681-724 (2008) (Breyer, J., dissenting); Paul Gewirtz, “Privacy and Speech”, 2001 Supreme Court Review 139, 195-198 (2001); Jud Mathews & Alec Stone Sweet, “All Things in Proportion? American Rights Review and the Problem of Balancing”, 60 Emory Law Journal 797-875 (2011).如果比例原则真有上述缺点,很难想像它能被这么多国家与组织所采纳,甚至还跨出欧陆法系的地界。以下笔者将以比例原则在德国的原型为准,说明其基本内涵。
简言之,比例原则要求国家对基本权利的限制与由此得以实现的目的之间必须有合理的、平衡的、成比例的(verhältnismäßig, proportional)关系,不得过当、过度限制基本权利,也就是“禁止过度”(Übermaßverbot)的原则。在结构上,它分为三个子原则或阶段以及一个预备阶段。但须注意的是,比例原则的启动前提是国家限制、干预了基本权利。因此,在进入预备阶段前,得先询问国家行为是否限制、干预了基本权利。为此,就得先确认相关基本权利的内涵与范围;并追问所涉国家行为对基本权利直接或间接的、有意或无意的影响是否可归责于国家、是否阻碍或实质妨碍基本权利的行使,亦即是否在严重性上达到了应受宪法正当性检验的性质或程度,而足以称之为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或干预,还是只是微不足道的干扰而不足以启动违宪审查机制。
一旦确认国家行为限制、干预了基本权利,便进入比例原则的预备阶段,追问国家行为的目的与目的本身的正当性。国家行为的目的必须尽量精确而具体地界定,如果是法律,可通过探究法律文本、立法背景、过程与材料等方式确定,而非指出一个极度抽象而宽泛的目的,如维护公共利益之类,就算了事,否则,以下三阶段的审查将因此流于粗糙而发生偏差。例如在第三阶段狭义比例原则的法益衡量中,将无法准确判定国家行为目的之价值,容易高估它的重要性,使权衡的天平自始就向它倾斜而丧失公正性。与第三阶段还将在法益衡量的脉络中考察国家行为目的之重要性不同,预备阶段要做的,是在暂不进入此一脉络、暂不衡量目的重要性的条件下追问目的本身的正当性。对立法者而言,本身正当的目的是指宪法所限定的或未自始为宪法所禁止的目的。以中国宪法为例,国家干预通信自由、通信秘密的目的若非宪法第40条所限定的国家安全或追查刑事犯罪,便是不正当的。对行政与司法部门而言,本身正当的目的范围较窄,指的是宪法或合宪的法律所限定的、或未自始为宪法或合宪的法律所禁止的目的。目的本身的正当性虽然只是一个基本门槛,用来淘汰明显的违宪行为,但它的重要性不可等闲视之,尤其对法治发展水平不高的我国来说。
一旦确认了国家行为的目的与目的本身的正当性,即可依次进入比例原则的第一与第二阶段,考察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第一阶段涉及“适合原则”(Geeignetheit, suitability),追问作为手段的国家行为是否适合于实现其目的。适合原则不要求手段能完全或基本上实现目的,只要求手段有助于目的之实现。它的基本思路是,如果干预基本权利根本无助于其他法益的实现,如果国家行为不但毫无积极的建设作用,还有负面的破坏效果,这样的行为就根本不值得、不应该采行。反过来说,如果国家放弃干预基本权利,不但能让基本权利毫发无损,与国家干预的情况相比,也不会对其他法益造成较不利的后果,那么放弃干预就是正确的。换言之,适合原则与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理论的思路是一致的,即改善一方处境而又不使另一方的处境恶化。*Robert Alexy, “Constitutional Rights, Balancing, and Rationality”, 16 Ratio Juris 131, 135 (2003).
如果所涉国家行为合乎适合原则的要求,就进一步接受第二阶段“必要原则”(Erforderlichkeit, necessity)的检验。必要原则要求国家在所有对目的实现相同有效的手段中,选择最温和的、对基本权利限制最少的、甚至不限制基本权利的手段。换言之,如果可以找到其他能同样有效地促进目的之实现、却能较少地限制、甚至不限制基本权利的手段,原本的手段便是不必要而违宪的。必要原则并非单纯要求最温和的手段,而是在对目的实现相同有效的条件下要求最温和的手段。因此,即使能找到其他对基本权利干预较少的手段,如果它不能像原本的手段一样相同有效地促进目的之实现,仍然可以认定原本的手段是必要的。必要原则也体现了“帕累托最优”的观念,要求在不妨碍目的有效实现的条件下减少干预,促进基本权利的实现。
然而,如果减少对某人或某些人的基本权利干预虽能同样有效地实现国家所追求的目的或法益,却会对其他人的相同基本权利或其他法益不利,则干预的减少便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对一方有利的固然无损于另一方,却不利于第三方。如此一来,采取较温和的手段不过是将负担转移而已。涉及利益与负担分配的社会与经济措施常出现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必要原则即无用武之地。或者说,手段是否必要的问题其实取决于负担由哪个人或哪种法益承受较合理的问题。而这正是法益衡量的问题,也就是第三阶段狭义的比例原则所要处理的问题。*Ibid., at 135-136; Dieter Grimm, “Proportionality in Canadian and German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 57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 383, 390 (2007).
如果所涉国家行为被认定为必要,或者无必要原则用武之地,就进一步接受第三阶段“狭义的比例原则”(Verhältnismäßigkeit im engeren Sinne, proportionality in the narrow sense)、或称“适度原则”(Angemessenheit, appropriateness)、“衡量原则”(Abwägung, balancing)的检验。狭义的比例原则要求,对基本权利的限制与由此得以实现的目的之间必须有合理的、适度的、成比例的、相称的、平衡的关系。比例原则的前两个阶段都是以国家行为的目的作为判断手段正当性的前提或标准,目的本身是不被质疑的。这个阶段则要跳脱出狭义的目的手段关系,把目的也列为检验与衡量的对象,追问为了特定目的而要求某人或某些人承受特定负担是否合理,追问是否值得为了实现某一或某些法益而付出限制基本权利的代价。具体地说,就是要求,国家所干预的基本权利愈重要,对基本权利的干预愈强、造成的损失愈大,由此得以实现的其他法益就应该愈重要,对这些法益的实现的促进作用就应该愈大,或者反言之,在国家不干预的情况下,这些法益受危害的严重性与可能性就应该愈大。换言之,狭义的比例原则要求相冲突法益之间的相称关系,要求轻重相当、损益平衡,不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利弊失衡。为此,就必须进行法益衡量,或称法益权衡。
无论这种法益衡量是否会涉及一般性地比较基本权利与相冲突的其他法益的价值,*持肯定观点者如Robert Alexy, “The Weight Formula”, in Jerzy Stelmach & Bartosz Broek & Wojciech Zauski eds.,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w: Frontiers of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5-16, 23-24.它肯定不能局限于这样的抽象衡量,而是最终必须着眼于个案特殊情况,立足于个案具体脉络,进行具体的衡量。法益衡量必须在所涉国家行为——可能是特定的法律、行政行为或司法裁判——以及相关事实、背景的具体脉络中,一方面评估受限制的基本权利的重要性与基本权利受限制的严重性,另一方面评估国家所追求的其他法益的重要性以及——若国家不采取行动——这些法益受危害的严重性与可能性,考虑双方在本案具体情境中的分量与价值,权衡双方是否轻重相当而达成平衡。如果是,则对基本权利的限制便是不过度的、成比例的、合理而合宪的。如果基本权利分量较重以致衡量的天平向它倾斜,则对它的限制便是过度的、不成比例的、不合理而违宪的。如果其他法益分量较重以致衡量的天平向其倾斜,固然不会有因限制过度、限制不成比例而违宪的问题。但是,如果国家对其他这些法益负有积极保护的宪法上作为义务,却会产生是否因作为义务履行不足而违宪的问题。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宪法基本权利不但要求国家不得过度干预个人自由,也要求国家对自由的积极保护不能不足;亦即既“禁止过度”,也“禁止不足”(Untermaßverbot)。“限制自由与保护自由都不可以……不成比例。”*BVerfGE 81, 242 (261).因此,当法益衡量的天平两方都是会因国家行为——包括民事立法或法院对民事法律的解释与适用——而受到影响的基本权利时,例如当一方是言论或媒体自由,另一方是受宪法人格权保护的个人隐私或名誉时,便会出现是否未适度平衡双方基本权利地位、是否未适度平衡对自由的限制与对自由的保护、是否因“过”或因“不及”而违宪的问题。
比例原则下的检验既涉及价值判断,也涉及事实判断。事实判断尤其出现在检验手段是否适合、是否必要的前两个阶段,但也会出现在评价是否适度的最后阶段。事实判断一般涉及对现实的评估与对未来的预测,包括对各种手段的效果的预测,因此常带有不确定性。立法尤其如此。问题涉及面愈广、所涉因素愈多、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愈复杂,往往就愈难以作出准确而有把握的评估、预测与判断,有时专家也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面对事实问题时,如果进行的是对具体行政行为或法院裁判的违宪审查,如果涉及的是与此有关的具体事实,则虽非完全、但基本上尊重与依赖原审普通法院或其他专业法院的原来证据调查结果与判断。*Brun-Otto Bryde, Tatsachenfeststellungen und soziale Wirklichkeit in der Rechtsprechung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in: Peter Badura / Horst Dreier (Hrsg.), Festschrift 50 Jahre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Tübingen 2001, S. 533 (546 ff.).但如果进行的是对法律的违宪审查,如果涉及的是较具一般性的立法事实,则往往无从依赖其他法院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联邦宪法法院认为,一方面不能因为事实评估、预测与判断带有不确定性而可能错误,就不允许立法;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因此认为在这里根本不存在合宪性检验的问题,承认立法者享有完全的自由判断权。它认为,应该随着各种相关因素的变化,特别是随着规范领域的特性、形成相对确定判断的可能性与所涉法益重要性的不同,承认立法者享有不同范围或程度的裁量空间,允许、要求宪法法院相应地进行不同密度的审查,亦即从审查是否有明显错误的“明显性审查”、到检验是否能站得住脚而获得合理支持的“可支持性审查”、再到严格要求判断可靠性的“强烈的内容审查”。*BVerfGE 50, 290 (332 ff.); 76, 1 (51 f.); 88, 203 (262 f.); 110, 141 (157 f.); 121, 317 (350).
二、 多元审查基准的基本内涵
美国宪法权利案件的多元审查基准是以“严格审查”(strict scrutiny)、“中度审查”(intermediate scrutiny)与“合理审查”(rational basis review)这三个不同层级、不同强度的审查基准为核心。其中最早成型的是最宽松的合理审查。它是最基本的、默认的审查基准,适用于所有未被归入其他审查基准的案件,例如社会与经济立法。它源于1930年代新政时期。当时,美国最高法院改变20世纪初以来严格审查、积极干预社会与经济立法以保护财产与经济自由的态度,对这类立法改采极为宽松的合理审查基准。合理审查从推定政府行为*在美国,政府的概念包括行政、立法与司法,也就是所有国家权力。合宪出发,除非政府行为恣意而违背基本的合理性要求,才推翻此一推定。基本的合理性要求包括以追求正当的或合法的政府利益(legitimate governmental interest)为目的以及手段与目的间的合理关联(rational relation)。合理关联是相当宽松的要求,类似于德国比例原则下的适合原则。*Mathews supra note 12, at 802.合理审查原则上尊重、依从政治部门的决定,极少导致违宪的判定,以致被称为“理论上最低度的审查而实际上几乎无审查”。*“minimal scrutiny in theory and virtually none in fact”, see Gerald Gunther, “The Supreme Court, 1971 Term - Foreword: In Search of Evolving Doctrine on a Changing Court: A Model for a New Equal Protection”, 86 Harvard Law Review 1, 8 (1972).
就在1930年代合理审查基准成型以后,美国最高法院也逐步对涉及某些权利类型——首先在言论自由领域,然后在平等权领域——的案件提高审查基准,承认某些权利类型享有优越地位,应受特别保护,不应一律适用合理审查基准与合宪推定原则。在这方面具有早期里程碑意义的是大法官斯通(Harlan F. Stone)在1938年“卡罗琳产品案”判决中所下的“第四脚注”。*United States v. Carolene Products Co., 304 U.S. 144, 152-153, note 4 (1938).虽然此一脚注已经提出审查基准分化的基本思路,但是,严格审查基准的内涵要到1960年代才成型。严格审查基准要求政府行为必须以追求“重大迫切的政府利益”(compelling governmental interest)为目的,手段必须必要(necessary)而合体剪裁(narrowly tailored)、必须是限制最少的手段(the least restrictive means)。在1950与1960年代,最高法院内部在基本权利审查问题上存在两种对立立场;一方主张运用利益衡量,具有高度依从政治部门决定与限缩权利保护的倾向;另一方则坚持对权利的高度保护,甚至倾向于权利的绝对性与不可限制性。严格审查基准的出现本来是对这两种立场的一种折衷调和。它除了表现出对某些被置于优越地位的自由与权利的高度尊重外,原本也带有具体法益衡量的色彩。这尤其反映在对重大迫切的政府利益的认定上。政府利益是否重大迫切,不时取决于个案具体脉络中权利与政府利益的分量的比较衡量。*Mathews supra note 12, at 812, 828-832.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严格审查基准从最早适用的言论自由案件进入平等权案件,随着法院将审查焦点转移到手段是否合体剪裁、是否“过度涵盖”(overinclusive)而打击面过广或“涵盖不足”(underinclusive)而犹有漏网之鱼的问题上,严格审查日趋严格甚至僵化;*Ibid., at 812-813, 832-833.从推定政府行为违宪出发,多半以宣告违宪告终;从原本过程与方法上的严格,走向结果上的严厉,以致被称为“理论上严格而实际上致命”。*“strict in theory and fatal in fact”, see supra note 21.今天,严格审查基准主要适用于两大领域。一为涉及种族、肤色等“可疑分类”(suspect classification)的平等权案件。另一为涉及所谓“基础性权利”(fundamental rights)的自由权与平等权案件。基础性权利是指那些被认为最根本而应受特别保护的、或为宪法所明文列举、或为法院所承认的权利。此一领域包括对高价值言论——如涉及公众关注问题的言论——的内容管制以及涉及婚姻自由、家庭关系、迁徙旅行权与选举权的案件等。
严格与合理审查代表严格与宽松两个极端。在这个二分法的架构中,审查基准的选择几乎就决定了审查的结果是违宪还是合宪。1970年代诞生的中度审查基准就是为了缓解二分法的过分简化与僵化,避免非黑即白的思维与争论,给予考虑个案具体情况的法益衡量更多空间,提供一种操作上较灵活、较有弹性而在结果上较不确定的审查基准。中度审查基准要求政府行为必须以追求“重要的政府利益”(important / substantial governmental interest)为目的,手段与目的间必须有实质关联(substantial relation)。它适用于涉及性别、非婚生子女等“准可疑分类”(quasi-suspect classification)的平等权案件、对商业性言论的干预与非针对言论内容的言论管制等。
有的学者还将上述一般承认的三层审查基准进一步细化为六或七层。*R. Randall Kelso, “Filling Gaps in the Supreme Court’s Approach to Constitutional Review of Legislation: Standards, Ends, and Burden Reconsidered”, 33 Texas Law Review 493-599 (1992); R. Randall Kelso, “Standards of Review under 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and Related Constitutional Doctrines Protecting Individual Rights: The “Base Plus Six” Model and Modern Supreme Court Practice”, 4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225-259 (2002); 汤德宗,见前注〔10〕, 页30-37。此外,在长期的审判实务中,美国最高法院还分别针对各种不同的权利或案件类型,发展出各种不同的、与上述三层基准有着或多或少联系的审查基准或规则,例如在言论自由领域的“明显而立即的危险”与“真实恶意”等规则。总而言之,美国的多元审查基准是建立在分门别类与类型化的基础上,将各种不同的权利或案件类型与各种不同强度或结构的审查基准相挂钩。追根究底,这种挂钩是通过一般性地评价特定权利与其他法益的价值或重要性,也就是通过规则取向的或抽象的法益衡量而实现的。举例来说,之所以认为应对涉及公众关注问题的言论的内容管制进行严格审查,是因为已经通过抽象衡量,一般性地承认此类言论的价值高于许多其他类型的言论,也高于其他可能与它相冲突的价值或利益。
三、 单一空洞vs 精细详实?
对比例原则的一种常见批评是,比例原则过于抽象,与各种权利类型的实质内涵分离,无法为基本权利审查提供内容上的实质基准,容易沦为内容空洞的公式;*参见黄昭元,见前注〔8〕,2004年文,页69;林来梵主编,见前注〔8〕,页318。黄锦堂:“自由权保障之实质论证之检讨——以德国基本权冲突判决为初步探讨”,载李建良、简资修主编:《宪法解释之理论与实务》(第2辑),台湾中央研究院2000年版,页221-223。该文虽然也以比例原则为内容空洞的公式,但从上下文来看,用意不在对比例原则提出负面批评,只在指出比例原则应落实为个案中细腻的实质论证。它就像一把标有统一刻度的尺子,*参见林来梵主编,见前注〔8〕,页327。以单一标准套用于所有不同的案件类型,忽略基本权利类型、基本权利限制手段与生活事实的多样性、差异性与复杂性。相对地,多元审查基准与各种权利类型的实质内涵相结合,能够为基本权利审查提供内容上的实质基准;它针对各种不同的案件类型分别发展出不同强度或结构的审查基准,较能反映基本权利类型、基本权利限制手段与生活事实的多样性、差异性与复杂性。*参见黄昭元,见前注〔8〕,2000年文,页164-167;黄昭元,见前注〔8〕,2004年文,页68以下;林来梵主编,见前注〔8〕,页318-320、324-325。
其实,比例原则之所以显得抽象,是因为它本身就无意为特定基本权利与其他法益的各种形形色色冲突提供特定的、单一的、固定的实质解决方案。它其实是一套论证框架或程序,要求人们通过这套框架或程序,详尽考量具体个案中所有相关因素与法益的分量,充分检验与个案具体脉络相扣的所有相关理由与论据的说服力,以为基本权利与其他法益的每个具体冲突,分别寻找兼顾各方合理要求的解决方案,求取各方的动态合理平衡。它最关心的,不是与各种案件类型相挂钩的各项实质基准或规则的分化与精细,不是去建构一套由这些实质基准或规则构成的体系,而是个案事实分析、具体法益衡量与说理论证的精微曲尽。它所要求的深入个案具体脉络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论证与衡量,其实比类型化、规则化或实质基准的多元化来得更精细、更详实,也更灵活,更能因应个案脉络与生活情境的多样性、多变性、差异性与复杂性。一味寻求分门别类、寻求各种案件类型与各项审查基准的对应关系,反而容易简化或忽略个案的具体脉络与因素,掩盖所涉法益面临的真实问题与冲突,而有僵化思考、削足适履的危险。
空洞绝非比例原则的固有缺陷。人们之所以会觉得比例原则空洞,或者是因为运用它的人自己论证贫乏、言之无物,*我国台湾地区早年的“大法官解释”就有这个问题。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廖元豪在“高深莫测,抑或乱中有序?——论现任大法官在基本权利案件中的‘审查基准’”一文(《中研院法学期刊》第2期,2008年3月,页211以下)虽然主张层级式的多重审查基准,但在第263页也表明他并非批评德国的比例原则很空洞,而是批评我国台湾地区大法官操作下的比例原则很空洞。或者是因为人们死盯着它本身看,以为这样就能得出丰富的实质内容。其实,这两者都错失或误解了比例原则的精神。比例原则本不预设立场、不固执一端,而是要求人们走进具体个案,进行实质、具体而详实的分析、说理与权衡,在兼听广察、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随时适变,执两用中。之所以会认为比例原则空洞,也与欧陆法系、英美法系二分的固有成见息息相关。一般多认为,属于欧陆法系的德国比属于英美法系的美国更重视概念分析、释义学体系建构与抽象思维。此一看法一般而言或许没错,但绝不能套用在对比例原则的评价上。比例原则恰恰反对拘泥于概念、规则与体系建构,它的高度抽象反而为个案的说理论证与具体衡量留下广阔空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正是利用它来打破十九世纪末以来宪法学上的实证主义与形式主义倾向,贯彻它经常强调的《基本法》不是要建立一个价值中立的秩序的立场,要求在判断基本权利问题上关注具体事实脉络中的价值、利益及其衡量。相反地,美国的多元审查基准虽然是在个案审判中逐渐形成,但一旦形成,在个案运用中却比比例原则具有更明显的类型化、规则化与形式化特征。在美国,反对多元审查基准的法官与学者正是以这套基准的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倾向为立论根据,主张运用更灵活、更重视个案具体脉络及其所涉价值或利益的“衡量”(Balancing)方法,甚至主张采用与此一美国本土的方法有部分相似之处的比例原则。*see supra note 12.
从比例原则的第三个子原则,即狭义的比例原则,最能看出比例原则不是一把标有统一刻度的尺子。多元、多层审查基准——尤其是严格与合理审查基准——立足于抽象法益衡量,通过类型或规则的形成,预先抽象地为各种权利类型与其他法益设定重要性位阶,概括地赋予某些权利类型优先地位。主张比例原则者或者反对抽象地设定这种位阶,认为从抽象的角度看,所有基本权利原则上都具有同等的效力与重要性,不能说精神性与政治性权利就比经济性与社会性权利来得重要;或者虽不反对设定抽象位阶,但反对根据它来划定审查的宽严层级,认为它只是审查时应该考虑的一项重要参数。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主张比例原则者都认为,只有在个案的具体脉络中,才能对基本权利与相冲突的其他法益谁较重要、谁应优先的问题作出完整而最终的回答。换言之,比例原则要求具体的法益衡量,主张一项基本权利在个案中的重要性、价值与优先性最终应视个案具体情况、视具体社会条件、视具体相冲突的其他法益的分量而定,不可一概而论。
具体法益衡量的操作可以通过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两次“雷巴赫”(Lebach)裁判来具体说明。先看1973年的第一次“雷巴赫”判决。*BVerfGE 35, 202.1969年,位于雷巴赫的一个军队弹药库被劫,数名士兵被杀。1970年,这桩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与媒体热议的案件的两名主犯被判处无期徒刑,另一名从犯被判处六年徒刑。1972年,德国第二电视台(ZDF)制作完成了一部与此有关的纪录式电视剧并准备播出。此剧以犯罪行为人的肖像与姓名介绍开场,然后通过演员的扮演,描绘犯罪的前因、过程、后果以及三名行为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他们的同性恋关系,并在剧中不断提及他们的姓名。即将于1973年假释出狱的本案从犯认为,此剧播出将侵害他的民事权利——人格权、姓名权与肖像权,于是向法院申请假处分,要求禁播。在民事法院驳回他的申请后,他继续以民事裁判侵害他的宪法基本权利——《基本法》第2条第1款与第1条第1款所保障的一般人格权——为理由,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愿。联邦宪法法院认为,民事法院对法律的解释与适用必须合乎宪法基本权利的精神;就本案而言,亦即在对规范肖像权的《艺术著作权法》第23条进行解释时,必须在此一条文所开启的法益衡量空间内,一方面注意《基本法》第5条第1款所保障的广播电视自由以及此一自由所服务的公众知情需要与舆论自由形成,另一方面也考虑同为宪法所保障的个人一般人格权。在两方陷入冲突时,没有任何一方具有一般性的优先地位,而是必须考虑个案具体情况,对两方进行衡量,才能决定在具体个案中哪一方优先。
联邦宪法法院基于以下理由认为,上述电视剧的播出会对诉愿人的人格领域造成严重的干预与不利影响。首先,这类节目类型具有广泛影响,且可能造成人们对犯罪行为人认识的片面与偏颇。其次,虽然诉愿人只被法院认定为从犯,但在此剧的诠释下,人们容易形成他的罪责足以与主犯相提并论的印象。再者,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剧中对同性恋关系的强调会强化人们对诉愿人的贬抑与拒斥。此外,此剧通过运用犯罪行为人的肖像、姓名与其他描绘方式,使诉愿人的身份具有高度的可辨识性。加上此剧的播出在时间上与犯罪的追诉、审判、也因此与在这段期间对犯罪的时事报道已有一段距离,所以它会在时事报道之外,对诉愿人的人格造成另一次新的伤害。更重要的是,诉愿人即将假释出狱,此剧播出会严重危害他的再社会化。至于就广电自由的重要性而言,联邦宪法法院虽然高度肯定公众对犯罪、对重罪行为人的身份与个人生活的知情需要,也高度肯定媒体的时事报道在满足此类知情需要上的作用,但认为本案所涉电视剧在时间上已不属于这类时事报道,认为通过此前在犯罪追诉、审判期间的时事报道,公众的知情需要与媒体的报道需要已经基本上获得满足。此外,电视台所追求的提供公众信息的目的也可以通过不使公众辨识出犯罪行为人个人身份的呈现方式实现。也就是说,就本案而言,保护诉愿人的人格不受危害的重要性要大于广电自由的重要性与公众的知情需要。联邦宪法法院由此认为民事法院未对相冲突的基本权利进行合理衡量,未给予诉愿人的人格权、尤其是再社会化的正当要求应得的重视,因此侵犯了他的基本权利,于是判决撤销民事法院所作的不利于他的判决。
再看1999年的第二次“雷巴赫”裁定。*BVerfG, 1 BvR 348/98 vom 25. 11. 1999.1996年,德国卫星一台(SAT1)又制作了一部描绘雷巴赫士兵谋杀案前后经过的电视剧。在剧中,三名犯罪行为人均以化名出现,他们的肖像也没有出现。此剧再度引发了他们与电视台之间关于他们的人格权是否会因播出而受侵害的民事诉讼,争议最后又到了联邦宪法法院面前。这次,联邦宪法法院选择站在电视台这一边。法院认为,根据第一次雷巴赫判决,宪法的一般人格权固然不允许媒体无休无止地对犯罪行为人“个人及其私领域”进行报道,但这并不意味着,犯罪行为人有权要求社会在一定时间之后完全不再讨论其犯行;决定媒体是否可以报道的关键在于报道对涉案人人格发展的伤害有多大。法院认为,导致在上次雷巴赫判决中人格保护的重要性胜过媒体的报道需要与公众的知情需要的那些因素在这次并不存在。这次并不涉及一种使公众易于辨识出犯罪行为人个人身份的节目,且时过境迁已久,公众对犯罪行为的激愤已经冷却,因此节目的播出不至于对行为人的人格造成上次雷巴赫判决所担心的严重危害。总之,就这次而言,电视剧的播出对犯罪行为人人格的危害没有比禁止播出对广电自由的干预来得严重,法益衡量的天平因此向广电自由倾斜。
用这种具体衡量的方法来处理基本权利与其他法益之间的冲突,能够详尽考虑各种相关事实与价值因素,兼顾与平衡相冲突法益的合理要求。它一方面能精分细辨,随时而变,使事物“千条万绪各有所宜”;*宋儒朱熹语,见《朱子语类·孟子一》卷51。另一方面,它也能一以贯之,使基本权利与其他法益各得其分,在每个案件都获得与其重要性相称的对待。与此相比,在多元审查模式中,严格审查基准与其他类似规则预置某些被一般性地认为非常重要的权利类型于优先地位,合理审查基准则预置另一些被一般性地认为较不重要的权利类型于劣后地位。然而,前者所涉权利可能在某些具体情况或社会条件下不是那么重要,运用严格审查便容易过度保护这些权利,低估或轻忽相冲突的其他法益的价值,甚至走向权利的绝对性与不可限制性。后者所涉权利则可能在某些具体情况或社会条件下变得重要,运用合理审查便容易对这些权利保护不足,高估与它们相冲突的法益的价值,甚至使权利保障形同虚设。
举例来说,美国最高法院在裁决国家对言论的限制或制裁是否违宪时,如果言论涉及公务行为、公众人物或公众关注的问题,便会采取诸如“真实恶意”等规则进行严格审查,结果几乎总是言论自由占上风。言论自由受到极高度保护的代价是与它相冲突的其他法益——特别是个人名誉、隐私、尊严或人格权——有时得不到应有的恰当保护。以佛罗里达星报案(Florida Star v. B.J.F.)为例,*Florida Star v. B.J.F., 491 U.S. 524 (1989).佛罗里达星报通过放置于警察局媒体公关室的警方报告,获悉并公布了一桩性侵犯案件的被害人姓名,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因此被初审与上诉法院判决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最高法院却援用史密斯诉每日邮报案(Smith v. Daily Mail Pub. Co.)*Smith v. Daily Mail Pub. Co., 443 U.S. 97 (1979).所确立的“每日邮报原则”:如果媒体将合法取得的、具有公共意义的真实信息公开发表,除非最高阶利益的需要,否则对媒体的处罚便是违宪的。最高法院据此对法律进行具有严格审查性质的检验,判决对媒体的制裁违反宪法所保障的言论与新闻自由。这样的判决实有过度保护言论与新闻自由,轻忽隐私权与人格利益之嫌。出现这样的判决结果固然有实体价值判断的原因,但也与审查、论证的方法息息相关,亦即与论证所依赖的是将价值判断一般化、抽象化、形式化的类型与规则、而非个案具体法益衡量有关。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美国最高法院布雷耶法官在巴特尼基诉沃珀案(Bartnicki v. Vopper)*Bartnicki v. Vopper, 532 U.S. 514 (2001).的协同意见书。此案也涉及对媒体的制裁,起因是媒体播放了他人非法截获录音的、但事涉公众关注问题的手机交谈,最高法院最后也作出了对媒体的制裁为违宪的判决。布雷耶法官虽然加入了支持媒体的多数阵营,却也通过协同意见书表达自己不同的论证方式。他既拒绝严格审查,反对只要诉诸公众关注就几乎能拒斥一切隐私诉求的做法,也不像反对意见书一样运用中度审查。他根本不采用层级式审查,而是主张具体法益衡量能较好地处理公共言论自由、媒体自由与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他认为应该问的是,本案中对公共言论及媒体的限制是否与由此给个人隐私及私人交谈带来的好处成比例。他认为,媒体之所以在本案胜诉,是因为在本案的具体情况下,手机交谈者的正当隐私利益极低,而拒斥隐私诉求的正当公共利益极高,也就是说,对媒体自由的限制是不成比例的。这样的论证方式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一个类似的、但结论不同的“电话交谈”判决的论证方式若合符节。*BGH, Urteil vom 19. 12. 1978, Az. VI ZR 137/77.此一判决涉及有人窃听当时在野的基民盟主席与其秘书长的一段电话交谈,一家新闻杂志在取得此段交谈内容后予以公布。面对一方面是要求保护私领域的人格权,另一方面是与其相冲突的出版自由与公众的知情需要,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运用具体法益衡量,主张被披露的信息的私人性质愈强,对个人人格法益的不利影响愈大,信息披露的公共价值就必须愈高。法院在检视本案的电话交谈内容后认为,就本案而言,个人的人格利益胜过公众的知情利益,因此判决媒体败诉。
多元审查模式通过抽象法益衡量,预先划定宽严不同的审查层级。比例原则不预设这种层级,*上文提及的、在比例原则下对立法事实的不同审查密度与多元审查模式下的不同审查层级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对此下文还将有所说明。在具体法益衡量中却自然会对审查的宽严作出适度调节。它不是一把尺子,而是一盏天平,一端放的东西愈重,另一端就得放愈多的砝码,视案件具体情况自然会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提出不同强度的要求。这种不同强度是斜坡式的、滑动式的、连续而不断裂的。相反地,多元审查模式立足于分门别类,犹如多个文件夹所构成的文件整理系统,焦点在于某个文件究应归入哪个文件夹,审查的不同强度偏向层级式、阶梯式,是断裂而跳跃的。比例原则着眼于不同的“度”,多元审查基准强调不同的“类”。相比之下,前者比后者更精细,也更有弹性。
人们可能认为,在美国的多元审查模式中,严格与合理审查虽一则趋于严厉,一则趋于宽松,但有中度审查基准居于其中,还是为具体法益衡量留下了空间。然而,中度审查的存在并无法解决严格与合理审查一则太过、一则不及的宽严失度问题。再者,中度审查基准是多元、多层审查模式下的一项基准。它无可避免地得面对哪些权利或案件类型归属于它的分类问题,得面对它与严格及合理审查基准的划界问题。也就是说,中度审查基准的具体法益衡量仍处于类型化的框架与限制中,不像比例原则以具体法益衡量为本,能够一以贯之地在所有案件落实事事物物各得其宜、各得其分的精神。
除非我们重塑多元审查模式,例如把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与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对平等权案件审查基准的独特看法应用到整个多元审查模式,它与比例原则才有趋同的可能。马歇尔法官批评当时通用的严格与合理双重审查基准过于僵化,提出“滑动尺度”(sliding scale)之说,主张审查的宽严程度应随具体所涉法益的重要性而弹性调整。*San Antonio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v. Rodriguez, 411 U.S. 1, 98-103 (1973) (Marshall, J., dissenting).史蒂文斯法官甚至主张:“只有一个平等保护条款。……它不指引法院在某些案件适用一个审查基准而在其他案件适用不同的审查基准。”*Craig v. Boren, 429 U.S. 190, 211-12 (1976) (Stevens, J., concurring).他认为,一个广义的合理审查基准就可以应付所有平等权案件;因为什么样的区别对待是合理的,应具体视其目的以及受到不利对待者的损害而定;如此一来,面对不同的案件自然会有宽严不同的审查,不需要有特别的严格或中度审查基准。*City of Cleburne v. Cleburne Living Center, Inc., 473 U.S. 432, 451-454 (1985) (Stevens, J., concurring).这样的思路倒是与比例原则的具体衡量精神一致。
有人可能主张,在理论上,着眼于“度”的比例原则固然比着眼于“类”的多元审查基准更为精细详实,但在具体操作上,着眼于“类”却较为有章可循,更加稳定而客观。其实,在具体操作上,多元审查基准并不像乍看之下那样条分清晰。或因出现新型案件,或因社会条件改变、案件特殊情况等因素以致原有归类或基准显得不尽合适,或因可归属的类型或可适用的基准不只一个,或因其他归类困难的因素,某一案件究应归入哪一层级、类型或适用哪一基准的困难与争议总是不断发生。上述美国最高法院巴特尼基诉沃珀案*Bartnicki v. Vopper, 532 U.S. 514 (2001).就出现了这样的争议,即究应根据所涉言论涉及公众关注问题而运用严格审查,还是应根据所涉管制措施未针对言论内容本身而行使中度审查。在这类困难与争议中,背后决定审查基准选择的,恰恰常是一种——尽管是隐晦不彰的——具体法益衡量。也就是说,选择严格审查者经常是先有了在本案具体情况下基本权利比国家要保护的其他法益来得重要的粗略判断,才据此选择严格审查基准。然而,为了维系类型化、规则化的表象,运用多元审查模式者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隐讳事实上无可避免的实质而具体的法益衡量与价值权衡,代之以他们认为较客观理性的如何正确归类的形式问题。但如此一来,案件的真实问题与冲突就被掩盖了,决定审查结果的真正因素与理由便隐晦不彰,于是也就不利于他人或公众的检验与监督,审查者的主观恣意反而得以滋生。就算大家对选择哪一审查基准意见一致,操作同一项基准的宽严程度也可能因人而异。这时,与其阿Q般地说没有审查基准的争议,不如坦然面对背后具体法益衡量的问题与争点。与这种情况互为表里的,是虽然两人选择了不同的审查基准,实际上操作的宽严程度却可能没有明显不同。换言之,既可能名同实异,也可能名异实同。这时,与其在名上争论,讨论审查基准的选择,不如回归实质,真诚坦率而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与法益衡量。
面对这样的问题,有人可能想以继续推进、发展多元审查基准的方式寻求解套,亦即将现有层级、类型或基准再予以细化、具体化,使审查基准更加多元、精细与明确。然而,如此一套复杂的审查基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可能治丝益棼,欲治反乱。随着层级与类型的增加,它们之间的划分就更加困难,一个案件有两个以上可归属的类型或可适用的基准的情况也会增加,“欲轻则有轻条,欲重则有重款”。*此语原为清代康熙朝御使李云芳在奏议中对条例纷繁的后果的描述,见《康熙实录》卷33。有美国学者因此直指美国的多元审查基准现状为混乱。*Gewirtz, supra note 12, at 197.至于将类型或基准具体化以形成更明确的规则,将反使类型或基准丧失弹性,更难以应对新的案件类型或新的社会条件。此一窘境正与清末律学家薛允升所指出的条例繁密的流弊如出一辙:“盖例太密则转疏,而疑义亦比比皆是矣。”*薛允升:《读例存疑·序文》。相反地,比例原则在统一的适合、必要与适度要求中就包含了随时而变、千条万绪各有所宜的道理,不但更具一贯性,也更能应对生活情境的多样性与多变性。
此外,多元、层级式审查基准抽象概括地为各种权利类型预设重要性位阶,据此决定审查的宽严层级甚至审查的合宪或违宪结果。这种抽象的、在严格与合理审查倾向于赢者全赢、输者全输的审查模式容易固化、激化意识形态对立,使审查高度政治化。相反地,比例原则不抽象概括地决定审查强度,不以推定违宪或合宪等方式预设审查立场,而是要求紧扣个案具体脉络与问题进行分析、说理与衡量,要求兼听广察、实事求是、因时而变。这种“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第九》)的不执着态度与“切问而近思”(《论语·子张第十九》)、贴近当下的进路有助于审查摆脱主观成见,摆脱固化的意识形态争议,避免谈玄说妙的大而无功之举,避免泛问远思的激化意见对立之病,有助于审查者之间以至于公众之间就事论事的讨论与共识的形成,从而有助于提升审查的理性与客观性。
四、 “执中行权”与“理一分殊”是比例原则的核心精神
中国传统的“执中行权”思想可以用来阐发当代比例原则及其具体法益衡量的核心精神。根据孟子的看法(《孟子·尽心上》),墨子“磨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而不为,两者均有所偏,或过或不及,子莫“執中”虽近于道,但他“执中无权”,胶着于固定之中而不知变,不知持权衡、称轻重以取中,结果仍流于“舉一而廢百”的“執一”,与无偏无党的正道相背离。宋儒朱熹据此而言:“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尽心章句上》。并以“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为“中”,*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以“权轻重、使合义”为“权”;*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子罕第九》,引程子言。又将“中”、“权”与“义”联系起来:“以义权之,而后得中。”*《朱子语类·论语十九》卷37 。至于“义”,则有“宜”(《中庸》)、“天理之所宜”、“道理之所宜为”、*《朱子语类·论语九》卷27。“分别事理,各有所宜”*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之义。也就是说,执中必须度之以义,行之以权。这正是孔子所说的“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第十八》)以及“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第四》)的观念,亦即不执泥于非得如此或必不如此,一切只看是否合于义理之当然、是否适得事理之宜。换言之,“中无定体,随时而在”。*同上注。“中”不是固定的,而是动态的,不同的时空条件有各自不同的“中”,应该因时取宜,随时取中,适时而变。这就是《中庸》所说的“时中”。执中行权不是和稀泥式的折衷调和,不是要人做不讲是非、只求取悦讨好众人的“乡愿”(《孟子·尽心下》)、烂好人,也不是要人只求趋利避害而不惜委屈道义,而是要人因时、因地、因事辨明义理,作出无过与不及的合理、正当决定,要人根据现实具体情况,力求做到不偏不倚、恰如其分。运用到基本权利审查来说,执中行权就是要求审查者准情酌理,求情理之平,也就是立足于“公共底道理”、“天下正大的道理”*皆朱熹语,见《朱子语类·学七》卷13。与正大之情,依此情理之正权衡轻重,以求无过与不及而不偏不倚地解决基本权利与其他法益的冲突,以求事事物物各得其宜、各得其分。这正是比例原则下的适度原则与具体法益衡量的核心精神。
然而,什么才是情理之正,怎么样才无过与不及,是无法从比例原则本身找到具体答案的。比例原则只是一套基本分析框架与论证程序,要求人们通过此一框架与程序,紧扣个案具体脉络,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评价、说理与论证。为此,就必须勇于发挥实践理性,运用道德论证,利用非法学学科知识,如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知识,并重视开放的公共论说。如下文还将论述的,比例原则下的说理论证固然可以凝练成某些法律释义学类型或规则,但不可能被它们所取代。毕竟“情伪无穷,而律条有限,原有不能纤悉必到、全然概括之势”,*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52,刑部,断罪引律令,历年事例,乾隆6年谕。再如何丰富而细密的概念、类型与规则也有时而穷。何况依法与依宪治国不应只是规则之治。规则之治只是法治之用。类型与规则之后、之上的天下正大之理与正大之情才是法治之体。只讲法治之用,而不讲法治之体,一味追求形式规则的丰富与细密,而不知立足情理之正、道德理性与实践理性进行实质说理,法律将与人疏离,法治将空有其壳而无其魂,沦为丧失“以道治天下”精神的“以法把持天下”。*宋儒程颢语,见《近思录·治国平天下之道》卷8,第16条 。既然宪法是一切立法、行政与司法行为的最高法律准绳,对宪法基本权利的解释与适用便尤其应该阐发情理之正,突显法治之体。比例原则正为此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有学者因此指出,立足于比例原则的基本权利审查所表现出来的不是法制主义或法条主义的(legalist)精神,而是理性主义的(rationalist)精神。*Mattias Kumm, “Institutionalising Socratic Contestation: The Rationalist Human Rights Paradigm, Legitimate Authority and the Point of Judicial Review”, Vol. 1 European Journal of Legal Stadies No. 2, 1, 5 (2007).
综上所述,基本权利审查若以抽象衡量为本,以类型化、规则化为依归,*笔者并非完全反对类型化与规则化,而是反对以此为依归。对此下文还将有所说明。将不免有宽严失度之患、过与不及之病。只有像比例原则一样,以具体衡量为本,以追求动态合理平衡为依归,才能适时合度、不偏不倚。将比例原则对所有案件一体适用视为它的缺点,是不了解它的执中行权精神。比例原则不是一种与“多”相对立排斥的“一”,而是一种反映“一”与“多”的辩证统一的思维框架。它虽然只是适合、必要与适度这一套原则,但怎么样才适合、必要与适度的判断会因个案具体脉络的不同而不同。换言之,它既有“一以贯之”、“浑然一理”之体,又“泛应曲当,用各不同”,也就是具有“一本”而“万殊”、*以上数语见《论语·里仁第四》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理一而分殊”*程颐:“答杨时论西铭书”,见《近思录·为学大要》卷2,第89条。的道理。比例原则的特点也可以用中国传统五经之首的《易经》的三个意义——不易、变易与简易——来说明。它将适合、必要与适度要求一以贯之于所有自由权案件,也能适用于至少部分平等权案件,*BVerfGE 88, 87 (96 f.); 95, 267 (316 f.); 99, 367 (388 ff.); 107, 27 (45 f.); Bodo Pieroth / Bernhard Schlink, Grundrechte - Staatsrecht II, 29 Aufl., Heidelberg 2013, Rn. 470 ff.; Marion Albers, Gleichheit und Verhältnismäßigkeit, JuS 2008, 945 ff.此为“不易”。它的具体法益衡量要求精分细辨、随时而变、因时取宜,此为“变易”。它的入门基本知识简单清楚、易教易学,此为“简易”。有学者基于此一“简易”的特点而认为,比例原则适合法治发展初期的需要,多元审查基准则较为精致成熟。*参见黄昭元,见前注〔8〕,2000年文,页165;Frederick Schauer, “The Exceptional First Amendment”, in Michael Ignatieff ed.,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Human Rights, 2005, p. 32.这种观点忽略了比例原则虽然入门容易,但要得其“变易”的精髓却需一番功夫。它有平易明白之处,也有精微高深之处。要论精微,它实胜于多元审查基准。
五、 比例原则与类型化的关系
虽然比例原则不以类型化为依归,但它并非与类型化完全不发生联系。它与类型化的联系可按内涵与性质的不同区分为以下三种。首先,如上所述,在根据比例原则检验国家行为之前,必须先问国家行为是否限制、干预了基本权利,为此就得先确认相关基本权利的内涵与范围。对各项基本权利的内涵与范围的讨论与界定便是类型化的一种表现。以言论自由而言,必须探讨是否应该自始就把某些言论排除在言论自由所保护的言论之外,从而根本无需进一步讨论对它们的限制是否正当、是否符合比例原则。以德国为例,呼吁他人参与某一抵制行动的言论如果以经济制裁的手段作后盾,从而易使言论的受众迫于经济压力而不得不配合抵制,便超出了以言论相互说服、交锋、攻防的领域,因此自始就不属于言论自由所保护的言论。*BVerfGE 25, 256 (264 f.).由于基本权利释义学在德国的高度发展,又由于基本权利的内涵与范围在美国不像在德国一样是与限制基本权利的正当性区分开来的单独问题,因此,就基本权利的内涵与范围而言,德国的类型化程度高于美国。*Mathews supra note 12, at 844-845; 黄昭元,见前注〔8〕,2004年文,页70。但是,这种类型化毕竟不是比例原则本身的类型化。
其次,如上所述,在根据比例原则检验国家行为时,如果涉及立法者的事实评估与预测,依照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看法,应该进行从“明显性审查”、到“可支持性审查”、再到“强烈的内容审查”的不同密度的审查。有学者认为这是比例原则的类型化或层级化。*参见黄昭元,见前注〔8〕,2004年文,页72;林来梵主编,见前注〔8〕,页322-323;对我国台湾地区发展的述评参见黄昭元:“大法官解释审查标准之发展(1996-2011):比例原则的继受与在地化”,《台大法学论丛》第42卷第2期(台湾2013年6月)。笔者却认为,这种不同的审查密度不可与美国的合理、中度与严格三层审查基准相提并论。理由有以下三点。第一点,美国的不同审查层级既立足于抽象的实体法益衡量,对不同类型案件提出宽严不同的实体规范要求,也通过这些要求以及合宪或违宪推定、由人民或由政府负担举证责任等程序性安排,影响立法事实的审查宽严程度,甚至在合理与严格审查的情况极大程度地决定审查的结果是合宪还是违宪。换言之,它是一种使实体规范、事实认定与审查结果三者发生连动关系的设计。*参见廖元豪,见前注〔30〕,页256、260也提及美国的审查基准是举证责任与证明标准的综合体。比例原则的不同审查密度却只适用于立法事实。*参见许宗力:“比例原则与法规违宪审查”,载氏著:《法与国家权力(二)》,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版,页89-90。实体规范要求的强度则主要通过上文提及的两种方式调整。其一,在采取较温和的手段只会将负担转移给第三方的情况,不进行必要原则的审查。其二,狭义比例原则所要求的具体法益衡量有如天平,具有自然调节审查强度的功能。这种实体规范要求的强度调整与立法事实的审查密度虽非毫无联系,但并无紧密的连动关系。如此一来,举例来说,即使在某一案件中,事实判定采用中度的可支持性审查,在考量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否适度的具体法益衡量中,仍然可能随着基本权利限制严重性的不同,对所追求的法益提出从低到高不同强度的实体规范要求。与多元审查基准的连动式设计相比,比例原则区分实体规范与事实认定的脱钩式设计较为细致,在审查结果上也较为开放。如果戴着多元审查基准的眼镜来看比例原则,就容易忽略这种脱钩式设计,将实体规范上与事实认定上的审查强度混为一谈,以至于误认比例原则实质上已被不同的审查密度所覆盖或取代,*参见黄昭元,见前注〔8〕,2004年文,页72;林来梵主编,见前注〔8〕,页322-323;黄昭元,见前注〔65〕, 2013年文,页242。甚至有根据审查结果的违宪比例、而非根据审查过程的具体实质论证来认定审查宽严程度的结果论倾向。
第二点,在比例原则之下,立法事实的审查密度选择取决于多项参数,包括规范领域的特性、形成相对确定判断的可能性与所涉法益的重要性,也就是既涉及立法者是否比违宪审查机关更能胜任决策任务的组织、程序、功能观点,也涉及实体权利与价值的考量。因此,审查密度的选择最终有赖于个案的具体分析与具体衡量,*参见许宗力:“违宪审查程序之事实调查”,载氏著:《 法与国家权力(二)》,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版,页67-74 的叙述实已蕴含此意,只是未明白揭示而已。难以事先抽象而终局地确定不同审查密度所分别对应的案件类型。这不同于分门别类式的、与各种权利或案件类型有较明确对应关系的多元审查基准。*参见黄昭元,见前注〔8〕,2000年文,页165也指出审查密度理论可以是一种个案决定的衡量,而非类型化的标准。
第三点,笔者认为,从“明显性审查”到“可支持性审查”再到“强烈的内容审查”的不同审查密度不是层级式的、阶梯式的、可清楚界分开来的不同范畴,而是斜坡式的、滑动式的、无法截然分割的连续体。*Klaus Schlaich / Stefan 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Stellung, Verfahren, Entscheidungen, 9 Aufl., München 2012, Rn. 536.甚至可以说,对立法者的事实评估与预测的审查其实只有一个标准,即事实评估与预测是否站得住脚、是否可获合理支持。不同的审查密度只是此一广义的可支持性审查在不同脉络下的分化与具体化。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自己也暗示,三种审查密度是否可截然区分开来是一个问题。*BVerfGE 88, 203 (262).也就是说,比例原则下对立法事实的审查密度虽然也表现出一些不同的“类”的特征,但整体而言更像是不同的“度”,与以类型化为导向的多元审查基准在基本倾向上有所不同。
最后,比例原则与类型化的联系还发生在实体规范要求的层面。一般最常举的例子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首先在1958年的“药店判决”(Apothekenurteil)针对职业自由所发展出来的阶层理论。*BVerfGE 7, 377.此一释义学理论将对职业自由的限制依强度区分为对“职业选择”的较强限制与对“职业行使”的较弱限制;对职业选择的限制又区分为较宽松的职业准入的主观要件与较严格的职业准入的客观要件。前者涉及对个人知识、能力或特质的要求;后者则是个人所无法左右的客观条件,如限额措施。相应于这三种不同强度的限制手段,联邦宪法法院对手段所追求的目的提出了不同强度的要求:对职业行使的限制只需基于一般的公共利益,规定职业准入的主观要件则需基于重要的公共利益,规定职业准入的客观要件还需进一步有极重要的公共利益作后盾。这三阶不同强度的要求其实就是狭义的比例原则的具体化。此外,法院还根据这三阶不同强度的限制手段,将必要原则具体化,要求只有在低阶的限制手段无法有效实现目的之条件下,才能采取较高阶的限制手段;也就是说,如果限制职业行使自由就能达到目的,就不应限制职业选择自由;如果职业准入的主观要件就能达到目的,就不应动用职业准入的客观要件。联邦宪法法院自己也说,阶层理论是“严格适用比例原则的结果”。*BVerfGE 13, 97 (104).
这类由学说或判例发展出来的释义学理论或准则固然带有类型化的特征,但绝不意味着比例原则就此朝美式层级化与类型化发展。以职业自由的阶层理论而言,它固然(应)是、但也只(应)是利于比例原则操作的重要论证依据,不(应)是替代比例原则的规范上最终判准。比例原则所要求的适合、必要与适度才(应)是最终判准。这不只是因为某一限制措施究应归入哪一阶层有时会有疑义,更是因为低阶的限制手段有时会比高阶的限制手段更严厉。举例来说,在某些职业可能出现准入的主观要件相当宽松、有关职业行使的规范却相当严厉的情况。*Pieroth / Schlink, Grundrechte (Fn. 61), Rn. 922 ff.在这类情况下,如果还依据阶层理论坚持对职业行使的限制是强度最低的,对它只适用最低的规范要求,就难免陷入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窠臼,与比例原则的执中行权精神背道而驰。这种墨守成规而不知变通的态度拘泥于形式与狭隘的法律安定性,忽略了实质说理论证与价值判断的一贯性与合理性,正像孔子眼中识量浅狭、固守尾生之信的鄙陋之人:“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论语·子路第十三》)这时应该做的是暂时抛开阶层理论,回归它的源头与归宿,即比例原则的根本原理,实事求是地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判定限制手段是否适合、必要与适度,就像孟子所说的“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在这里,作为最终判准的“义”就是比例原则的适合、必要与适度要求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分别事理、各得其宜、各得其分的精神。此外,就阶层理论对限制职业自由的目的所提出的要求而言,什么是重要的公共利益,什么又是极重要的公共利益,也不应完全依赖一般化了的公共利益类型抽象地判断,而是应同时摆在个案具体脉络中审视,借助具体法益衡量,才能最终确定某一公共利益是否具有足以正当化某一限制措施的合比例的重要性。
以上对职业自由的阶层理论的理解同样适用于其他以比例原则为基础发展出来的类型或准则。例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当意见表达本质上涉及公共领域的问题时,应作有利于言论自由的推定。*BVerfGE 7, 198 (208, 212); 61, 1 (7, 11); 90, 241 (249, 254); 93, 266 (294 f., 303 f.).这里所说的推定并非一般性地给予言论自由优先地位,并非排除具体法益衡量,反而恰恰是衡量的起点,要求如果要禁止或制裁这类意见表达,需有比禁止或制裁其他与公共领域问题无涉的言论更充分的理由、更重要的相对法益。这是因为在这里的法益衡量,站在言论自由这一边的,不只有意见表达者的个人利益,还有民主的实现与维系自由而开放的公共讨论这样的公共利益。*Dieter Grimm, Die Meinungsfreiheit in der Rechtsprechung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NJW 27 (1995), 1697 (1703 f.).
我们一方面必须认识到,以比例原则为基础发展出来的释义学类型或准则确实有利于比例原则的入手与操作,有利于基本权利审查效率的提升,有利于法律的安定性。但另一方面也必须了解到,比例原则虽然可以容纳一定程度的类型化,但并非以类型化为依归。分门别类只是一种辅助工具或中介环节,让人更容易进入具体分析、说理、论证与衡量的殿堂。追求动态合理平衡才是比例原则的最终依归,执中行权才是它的核心精神,具体脉络中的适合、必要与适度才是它的最高判准。相对地,多元审查基准立足于抽象衡量,追求类型化,虽然也容纳了一些具体衡量的元素,但不像比例原则一样在多元的类型或规则之上还有一个起统摄、指引与修正作用的、具体衡量式的最高判准;遇到现有类型或规则不恰当时,不是像比例原则一样随时诉诸最高判准进行具体衡量与微调,而是尝试修正既有的或形成新的类型或规则。也就是说,多元审查基准以类型化为主,以具体衡量为辅;比例原则以具体衡量为主,以类型化为辅。两种类型化在旨趣与地位上有所不同。相应地,比例原则下的类型化在操作上较不固定、较有弹性。如上所述,除非我们重塑多元审查基准,像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马歇尔与史蒂文斯一样,淡化层级化与类型化,它与比例原则才可能趋同。
用中国传统的“体用”、“本末”、“道器”范畴来说,比例原则下的分门别类是“用”,是“末”,是“器”,比例原则的适合、必要与适度要求以及它所蕴含的以具体衡量为本、以动态合理平衡为依归的执中行权精神才是“体”,是“本”,是“道”。忽视器用之末固然不对,但也不能走向另一极端,只知钻研、执着于器用之末,而是要同时明道、识体,于必要时回归大本。要本末兼尽,“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才是王道。只有如此,才不会误解比例原则下的类型化,丢失比例原则的精神,使比例原则走向多元审查基准,成为“德国招牌、美国菜单”。*黄昭元,见前注〔65〕,2013年文,页239。这是黄昭元对我国台湾地区大法官解释发展趋势的解读。此一解读既针对立法事实的审查密度,也涵盖实体规范要求的层级化与类型化。此一解读是否恰当已属另一问题,非本文所能深究。。之所以认为比例原则一旦具体化为某些类型或准则之后就会成为“空荡荡的躯壳”,*黄昭元,见前注〔8〕,2000年文,页165。也是因为不了解此一体用本末关系、不了解这些类型或准则并非替代比例原则的最终判准所致。
六、 对必要原则与目的审查的认识误区
对于主张比例原则较为精细详实的以上论述,有人可能回应,这些论述就算合理,也主要着眼于狭义的比例原则,无法反驳对必要原则的以下批评,即美国的多元审查基准只有在严格审查时才要求限制最少的手段,比例原则下的必要原则却对所有案件一律适用,过于单一、严苛。*参见黄昭元,见前注〔8〕,2004年文,页83-87;林来梵主编,见前注〔8〕,页320。然而,必要原则事实上并未适用于一切案件。如上所述,在采取较温和的手段只会将负担转移给第三方、即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情况,不进行必要原则的审查。涉及利益与负担分配的社会与经济措施常属于这种情况。其次,上述立法事实的审查密度也会在运用必要原则时发挥调节审查强度的功能。笔者认为,在有审查密度调节下,不能只根据一律适用过于严苛的直觉或人云亦云地排除必要原则对某些案件的适用。要这么做,须有坚实的理由,如诉诸上述的负担转移。因为如果干预的减少不会削弱目的实现的有效性,为何不减少干预?有利无害之事为何不做?
再者,批评者往往是戴着美国严格审查基准的眼镜来看必要原则。由上可知,比例原则下的必要原则并非单纯追求权利损害的极小化,而是在对国家所追求的目的之实现依然同样有效、在为其他法益带来的利益不因此减少的前提下,才要求权利损害的最小化。相对地,严格审查基准下的最少限制手段不强调手段的相同有效性,较为严格。两者不可相提并论。*参见汤德宗,见前注〔10〕,页19。不仅如此,严格审查基准还要求“合体剪裁”,既不可“过度涵盖”而打击面过广,也不可“涵盖不足”而犹有漏网之鱼。比例原则则不然。一个在严格审查基准下被判定为“过度涵盖”的手段如果能比其他较温和的替代手段更有效地促进目的之实现,在比例原则下仍然会被认为是必要的。一个在严格审查基准下被判定为“涵盖不足”的手段在比例原则下仍然可以符合适合原则的要求。因为适合原则不要求手段能完全实现目的,只要求手段有助于实现目的,也就是只排除有害无利的手段。但是,这并不是最后的结论。因为被认定为适合与必要的“过度涵盖”或“涵盖不足”还得面对狭义的比例原则的法益衡量,所得大于所失才合宪,所失大于所得则违宪。换言之,比例原则认为,只要手段必要且所得大于所失,“涵盖不足”有何不可?只要手段更有效且所得大于所失,“过度涵盖”有何不可?这样的区分与严格审查基准相比,与其说是较为宽松,不如说是较为细致。
此外,由于德式比例原则的预备阶段对目的正当性的审查较为宽松,因此有不少学者、甚至包括原则上支持比例原则的学者认为,比例原则把焦点放在审查限制权利的手段,除了在职业自由领域运用上述阶层理论对限制权利的目的进行较深入的审查外,并不重视目的审查;相反地,多元审查基准同时审查目的与手段,对权利的限制愈大,对目的之要求就愈高,从合理审查的正当利益、到中度审查的重要利益、再到严格审查的重大迫切的利益。*参见黄昭元,见前注〔8〕,2004年文,页77-78;林来梵主编,见前注〔8〕,页323;许宗力,见前注〔67〕,页91-92。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观点没有注意到比例原则第三阶段的狭义比例原则其实也是一种目的审查,并且是一种更为细腻的目的审查。狭义比例原则正是要跳脱出适合原则与必要原则所关注的狭义目的手段关系,把目的本身也列为检验与衡量的对象。与多元审查基准的目的审查具有较强的抽象衡量色彩与类型化倾向相比,狭义比例原则的目的审查是通过更精细的具体法益衡量来进行的。也就是说,只有考量个案具体脉络与具体相冲突的基本权利,才能确定某一目的是否具有足以正当化某一权利限制的分量与重要性。如上所述,当在职业自由领域运用阶层理论进行目的审查时,也不应错失这种具体衡量的精神。既然目的审查是在具体法益衡量的框架下进行,就应该从实事求是的个案分析出发,以适合原则与必要原则下的分析与论证作为狭义比例原则下衡量的基础,逐步抽丝剥茧,才能既面面俱到,又纲挈目张。至于比例原则的预备阶段所从事的目的正当性审查,则是一种基本门槛式的审查,用来在审查一开始就排除那些无需经深入的轻重权衡便可判定为违宪的目的。但如果认为比例原则的目的审查仅止于此,那就大错特错了。
(责任编辑:章永乐)
中外法学Peking University Law Journal
Vol.27, No.2(2015)pp.367-390
七、 结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如上所述,“执中行权”的比例原则体现了“理一分殊”的精神。“理一分殊”也可说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比例原则的普遍性表现在它以适合、必要与适度三个子原则一以贯之,贯通于涉及不同案件类型与不同时空条件的基本权利审查中,也表现在它是当前被最多国家与组织所采用的、且跨出其欧陆发源地的基本权利审查基准。*见上文第一节比例原则的基本内涵的第二段论述,并参见 Sweet supra note 11.
与这种内容上、时间上与空间上的普遍性同时存在的是内容上、时间上与空间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源于比例原则自身的要求,亦即分析、说理与衡量应紧扣个案具体脉络而进行。分开来说,分别事理而使事物各得其宜造就了内容上的特殊性。随着被限制的基本权利、其重要性、或权利限制的严重性的不同,随着国家要保护的法益或其重要性的不同,审查的结果便可能不同。时间上的特殊性源于随时而变、因时取宜的“时中”之道。随着时代的不同,社会会变迁,基本权利与相冲突的其他法益的重要性以及它们所面临的风险或机遇也会随之不同,比例原则下的适合、必要与适度判断便可能发生改变。“时中”之道也要求因地制宜,考虑空间上的特殊性。在不同的空间中,行为条件与社会条件可能有所区别,于是会有不同的应然之理,比例原则下的适合、必要与适度判断也就可能随之变动。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采用比例原则作为基本权利的审查基准,就能在解决基本权利与其他法益的冲突时,充分考虑中国自己的国情。由于社会条件的不同,看似相同、却分别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发生的案件其实是处于不同的具体脉络中。在考虑具体脉络的比例原则要求下,即使大家对抽象层次的普遍之理看法一致,最终的适合、必要与适度判断还是可能有所不同。这种对特殊性的考虑也能延伸到中国自己内部。由于中国各地的差异,在比例原则执中行权的要求下,针对不同地域所作的适合、必要与适度判断便可能有所区别。不仅如此,由于中国正处于一个剧烈而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后所作的适合、必要与适度判断也可能不同于今日所下的判断。
当然,我们不应该忘记,在比例原则下特殊性与普遍性、灵活性与原则性、多样多变与一以贯之是相互结合、相辅相成的。一切变化莫不立基于适合、必要与适度的统一原则以及执中行权的核心精神。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建构一个与众多其他同样采用比例原则的国家相互沟通、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的平台。我们应该依循“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曾国藩全集·日记二》,岳麓书社1988年版,页851。的传统精神,建立一种开放的主体性;既不陷溺于狭隘与封闭的特殊性,自求安适,你我无涉,拒绝学习;也不妄自菲薄,以为中国要落实依宪与依法治国,只能与现实切割,与传统告别。以比例原则而言,它的运用正要求我们关注具体事实,它的核心精神正可以通过我们传统的执中行权精神来阐述。执中行权以求情理之平的精神绝不仅仅是一种中国自己的特殊性。它完全可以是一种中国人自己认为具有普遍性、而愿与其他民族共享的道理与精神。它完全可以用来作为比例原则的普遍之理,充实比例原则的内涵,丰富全世界范围内与比例原则以及基本权利有关的讨论与实践。
Abstract:Regarding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s review, there is a view in China that the proportionality test, first developed in Germany, is deficient because of its monism and lack of content; and, on the contrary, that the U.S. multiple, tiered standards are finer and more elaborate. Against this view,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proportionality is by no means monistic and empty. In fact, it is more thorough and elaborate than the multiple standards of review. The proportionality test requires a concrete balancing in pursuit of dynamic equilibrium. It just embodie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deas of“zhizhong xingquan” (执中行权; holding to the Mean with weighing circumstances) and “liyi fenshu” (理一分殊; one principle, many manifestations). It reflects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one and the many. It is also analysed that categorization under the proportionality test should not be equated with categorization employed by the multiple standards of review. Furthermore, the proportionality combines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in such a way that it both represents itself as a universal principle and yet is intrinsically connected to the particular context. Accordingly, it can be well suited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s well as help China keep an open mind to the world.
Key Words:Proportionality;Multiple Standards of Review;Constitutional Rights;Balancing of Interests;Categor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