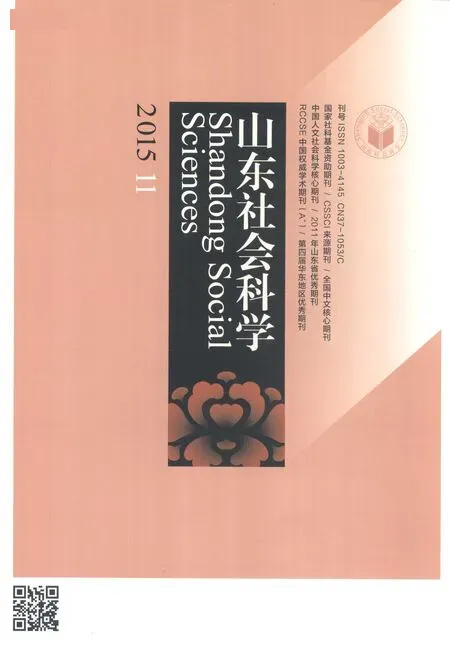从李大钊“第三文明”说看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重撰
穆允军
(山东大学图书馆,山东 济南250100)
从李大钊“第三文明”说看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重撰
穆允军
(山东大学图书馆,山东 济南250100)
从文化比较视域考察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必须突破以往实证性叙事方式和政治学术的壁垒,对二者关系进行重撰,才有可能真正把握融合的内涵。李大钊提出的“第三文明”说,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合的起点。厘清“第三文明”说的文化背景和思想进路,有助于揭示马克思主义同儒学相融合的实质,重新审视东西方文化融会的当代形态,进而看清儒学是融合的主体,两者关系的重撰是融合由自发到自觉的契机。
李大钊;“第三文明”;马克思主义;儒学;融合
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实践成果和典型理论形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期受意识形态影响,“中、西、马”一度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被人为地割裂为两个相互独立、隔阂的系统。目前,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推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自觉,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逐渐成为当代最重要的文化课题。从文化比较的视域看,对二者融合的探讨必须突破以往实证性叙事方式和政治学术的壁垒,重新梳理二者的关系,才能真正认识融合的内涵,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对二者关系的重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提出的“第三文明”说,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合的历史和逻辑起点。厘清“第三文明”说的文化背景和思想进路,有助于我们把握二者融合的特点,认清中国文化启蒙的主体性与特殊性,在文化基因和文化原型层面上建立起意义世界的坐标,以增强文化融合的自信与自觉。
一、李大钊“第三文明”说是在文化的世界主义和十月革命胜利影响下作出的新文化选择
从文化比较视域探讨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其他外来文化为中国所接受,一个可能的办法就是回到起点,从起点重撰东西文化冲突、碰撞中新文化探寻之路。这种重撰类似于利奥塔在《重撰现代性》中包含的两层含义:回归起点和深加工①参见[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重撰现代性》,载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上册,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回归李大钊“第三文明”说,可以清晰看出在新文化选择上世界主义思潮的坐标意义、俄国十月革命的示范作用。
晚清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文化层面上的突出表现就是中西文化之争。由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传入中国,其中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充当了最初论争的理论基础。社会进化论打破了守旧派“夷夏之别”的文化中心论,但一味用文化的时代性作为判别文化优劣的依据,隐含的是在肯定文化时代性的单一维度而遮蔽了民族性维度,尤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这集中体现在新文化运动“打到孔家店”和对西方“德、赛”两先生的推崇。在新文化派那里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优劣似乎在进化论的支撑下显而易见,胡适就主张全盘西化。但吊诡的是,当国人自认为找到了文化的病根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对中国利益的粗暴践踏,使人们耳闻目睹了西方现代文明先天的内在弊端和强权丑态,这启示国人必须重新审视孕育出现代文明的西方文化。
中西文化都积弊重重,那么创造新文化的路在哪里呢?李大钊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构想出具有超越中西文明弊端、带有理想色彩的“第三文明”。1916年,他发表《“第三”》一文认为:“第三者,理想之境,复活之境,日新之境,向上之境,中庸之境,独立之境也。第一文明偏于灵,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盖‘第三’之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盖‘第三’之说,乃刚柔适宜之说,中庸之说,独立之说也。”他用儒学的中庸之道来阐释“第三”的内涵,使新文化的期许富有哲学意味。在此文中,李大钊还不能肯定这种超越中西文化弊端、灵肉一致的新文明能否变为现实,他说,“顾‘第三’者,有其理想而无其实境”。但又预见这是人类进步之阶,是新文化努力的方向,“老子有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故‘第三’之境,实宇宙生生之数,人间进步之级,吾人当雄飞跃进以向‘第三’”①李大钊:《“第三”》,《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0页。。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布尔什维克所尊奉的马克思主义显示出“改变世界”的巨大力量。李大钊敏锐地从新生的俄罗斯文明中看到了“第三文明”变为现实的可能性。1918年7月,他发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和《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明确把俄罗斯文明称为“第三文明”。李大钊指出:“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有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退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②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页。将东西文明的根本不同,归于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的确从精神气质上抓住了两者的特质。在李大钊看来,东西文化之间不再是社会进化论框架下明显的优劣关系,而是被视为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于理想的“第三文明”而言,又都居于一偏。对新文化的选择,他已不再局限于中国文化自身,而是立足于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所谓救世界之危机即是指救世界文化之危机。李大钊从文明史和地理环境等多角度进行文化分析,认为英法文明臻于熟烂,德国已呈盛极而衰之势,俄罗斯文明最迟,发展空间与潜力最大,且俄国居欧亚之交,兼欧亚文明特质,所以“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③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32页。他认为俄国革命不仅预示着俄罗斯自身的发展,还预示着世界历史的走向,所谓“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④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32页。。可见,此时李大钊对新文化的探索,不仅仅局限于中国新文化的路向,而是在更宏大的世界文化视野上,去把握世界文化的整体性发展潮流。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揭橥了“第三文明”的现实可能性,恰恰为李大钊的思想升华提供了契机,使其对中国新文化的选择,不再囿于中体西用的窠臼来确定世界文化的走向,成为中国新文化选择的基本前提和思想坐标。
立足于世界文化潮流探寻新文化之路,在当时也并非李大钊独有的见解,美国学者普赖斯和张灏都曾指出转变一代“世界主义”的思想倾向。以现代新儒家梁漱溟为例,他正是将世界主义与儒学传统相结合,而建立起现代新儒家的。梁漱溟说:“从已往到未来,人类全体的文化是一个整东西,现在一家民族的文化,便是这全文化中占一个位置的。所以我的说法在一句很简单的答案中已经把一家文化在文化中的地位、关系、前途、希望统通表定了。”⑤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3页。他将世界文化划分为西、中、印三个阶段,此处的西、中、印代指三个阶段文化的典型形态,并非仅指一种民族文化的复兴,表示整个世界文化共同趋向某种文化精神。对文化世界主义潮流不同的认识和把握是导致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化流派不同走向的一个学理原因,正是因为对这种世界主义潮流认知不同,对推动历史、文化发展动力的不同理解,而对世界文化的走向有着不同的展望,进而对新文化开出不同的选择道路。文化世界主义应该说是马克思所谓“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背景下文化的一种特有属性,是文化时代性和民族性之外的世界文化整体性属性,表现在世界文化作为整体所具有的时代特征对其中所处文化的某种不可抗拒的影响。世界主义成为继社会进化论之后文化选择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根据。
1918年底,李大钊又陆续发表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再次重申俄罗斯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意义,明确指出俄国革命胜利的理论指南是马克思主义。他认为未来的世界文化潮流是灵肉一致的“第三文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继而认定“第三文明”的现实版就是俄罗斯文明,俄罗斯革命所尊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到达“第三文明”彼岸的理论指南。可见,“第三文明”说起初是李大钊超越中西文明弊端的一种文明理想,是一种主观的期许;俄罗斯文明从人类文明史和地理环境上看都可以兼容中西文明之优势,这又是一种客观的考察。十月革命的胜利促成了李大钊思想上主客观认知的结合,从而认定俄罗斯文明即是所追求的灵肉一致的“第三文明”。
在对世界文化发展方向有了自信的把握后,李大钊认为中西文化要反省自身的不足,自觉容纳自身没有而对方富有的精神,以便趋于“第三文明”,明确指出“所谓本身之觉醒者,即在东洋文明,宜竭力打破其静的世界观,以容纳西洋之动的世界观;在西洋文明,宜斟酌抑止其物质的生活,以容纳东洋之精神的生活而已”①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1-312页。。“第三文明”说的理论意义在于正确把握了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旗帜鲜明地揭橥出马克思主义是顺应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理论指南,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所以说,“第三文明”说是在文化的世界主义和十月革命胜利影响下作出的新文化选择方向。
世界文化的时代特征对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起着重要作用,李大钊对此有着高度的文化自觉。他在就义前所写的《狱中自述》中指出:“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②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8页。他在自述中认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在于顺应了当时资本主义兴盛的潮流,中国民族解放事业不选择日本的西化模式,也正是因为世界文化潮流已改变,所以要采用新的政策。可见,世界文化的走向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选择新文化方向的重要学理依据。
二、“第三文明”所尊奉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文化的现实选择
“第三文明”所尊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西学思潮的一部分,在上世纪20年代迅速传播、发展、交汇,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来文化资源。这不仅得益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示范作用和中国革命的实践需要,也是在诸多的文化争论中中国文化的现实选择。它集中体现在与实验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三次文化论争中。在这三次文化争锋中,李大钊以“第三文明”所尊奉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南,有力地驳斥了不切合中国国情实际的文化改良主张,阐明了只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选择,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亲和性,坚定了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决心。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与自由主义者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曾为推崇科学与民主并肩作战,但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终因主义的不同而分道扬镳。李大钊通过论争,明确了要不要主义,要什么主义,如何运用主义,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植根到中国的文化土壤奠定了初步基础。他申明主义存在的合法性,认为“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③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页。。李大钊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信仰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坚信它是世界文化的一大变动,是中国文化所需要的主义。李大钊在主义的应用上,主张主义与实境的结合,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④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51页。。他进而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结合的理论依据。李大钊在主义与实境的结合上,注意到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实境的结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双重运用。他提出:“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社会问题。”⑤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54页。李大钊“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落实到实际的运动,从而为中国革命指引了的正确方向;他率先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经济与文化关系,拿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分析问题,为中国文化把脉问诊。与李大钊相比,自由主义者胡适有着明显不同的致思进路。1919年底,胡适发表文章,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十六字方针,欲将新文化引向单纯的理论研究方向,这自有其价值,但胡适想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想要再造的文明怎么可能单凭头脑内而不落到实际的研究就能奏效呢?
1920年,梁启超游历欧洲归来,目睹西方文明弊端,发表了有名的《欧游心影录》,催使国人科学万能梦醒。同年9月,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并宣扬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得到梁启超与张东荪等人的认同。1921年3月,李大钊连续发表一系列文章,对这种伪社会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指出,基尔特社会主义只能使统治阶级得利,“在现存制度下谋求实业的兴盛,实质上就是要使我国的统治阶级与各国的资本阶级结合起来,这样只能加强统治阶级的力量,而决不会带来其他任何好结果,这是显而易见的”①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328页。。针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中国产业不发达,不适合发展社会主义的狡辩,李大钊从多方面对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李大钊打破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将发展实业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划等号的僵化思维,从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潮流中把握中国经济组织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行性。
20世纪初,刘师复、李石曾、吴稚晖等受日法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大力宣扬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早期有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但它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成为抵制马克思主义、妨碍党组织健康发展的障碍。李大钊1921年初发表了《自由与秩序》,对无政府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和虚无荒谬进行了批判,指出:“试想一个人自有生以来,即离开社会的环境,完全自度一种孤立而岑寂的生活,那个人断没有一点的自由可以选择,只有孤立是他唯一的生活途径。这种的个人,还有什么个人的意义!”②李大钊:《自由与秩序》,《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326页。李大钊认为自由与秩序、个人与社会是不可分离的,“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③李大钊:《自由与秩序》,《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327页。。通过与自由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的论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增强了对非马克思主义的辨别能力,驳斥了它们不符合中国文化实际的种种主张,更加坚定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文化旗帜的信心。从文化选择的角度看,李大钊“第三文明”说举起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在与各种主义和思潮的多次论争中显示了在中国文化中的强大的解释力和亲和力,成为中国文化多次筛选后的现实选择。
三、“第三文明”启示下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重撰
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重撰,就要以李大钊“第三文明”说为起点,从中西文化比较视域,用全新的眼光重新梳理二者之间文化交流、融会关系,对二者的融合从时代高度加以解读。
(一)“第三文明”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合的起点。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一直被定位为以冲突为主,如有的学者认为:“在20世纪的约80年时间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待儒学的态度是前60年排斥、批判,后20年逐渐改变了态度,与儒学对话,借鉴儒家思想的内容丰富自身,并与儒学实现多元文化下的双向互动。”④徐庆文:《排斥、对话与互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儒学观的变迁》,《文史哲》2010年第6期。应该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学术争论领域上的判断,这种观点是不错的,在学界也很有代表性。但这种观点又是颇为外在、局限的,停留在二者关系的实证性叙事。如果换一种视野,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都作为一种哲学与文化来看,二者的融合肇始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传播,标志性起点即是李大钊所提出的融汇东西文化的“第三文明”说。李大钊在“第三文明”说中擎起马克思主义大旗,率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旗帜和革命行动指南,是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文化和社会领域中的起点。以此为起点,经历百年艰苦卓绝的奋斗,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结出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典型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果,这是二者融合在个体上的完美呈现。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西学东渐取得的最伟大成果,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体,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二者在实践层面的融合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作为中华民族的人伦日用之道,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也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儒学的面貌,其中既有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约表现出的相互认同与汲取,也有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互补充与发明。二者的进一步融合必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良好的历史和文化基础。所以说,“第三文明”即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合的起点。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是东西文化融合的当代形态。从文化时代背景上看,自遭遇西方“他者”文化以来,中国文化一直处于自我反思和文化启蒙之中,融合西方文化,努力进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是主要的文化走向。李大钊的“第三文明”说是在东西文化调和主张中确立的,后将俄罗斯文明作为“第三文明”来追求,标志着中国文化由“以西为师”转为“以俄为师”,正是其文化观合乎历史和逻辑的发展,是东西文化融合大框架之内的深化。
李大钊对待东西文化的态度,不同于当时的全盘西化论,也不同于文化保守派。在他的文化观中,东西文化各有千秋,相辅相成,是世界进步的二大机轴;二者又都各有其弊,东方文化衰退于静止,西方文化疲命于物质。“第三文明”最初是融合东西文化优势,补救两者弊端的一种理想形态,带有哲学意蕴。李大钊所具有的文化世界主义的超迈视野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力量,使他很快找到了“第三文明”的现实版。“第三”之意旨主要取于儒学的中庸之道,也说明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在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正如有学者所说的,“李大钊在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是要把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实现东西方优秀文化创造性综合的一个中介,作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①李存山:《破除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夷夏之辨”》,载崔龙水、马振铎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由“第三文明”开启,经过百年的中国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取得理论和实践的累累硕果,二者融合的一面而不是冲突的一面已然成为当代重要的文化课题。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机理的探寻,是时代赋予我们重撰二者关系的宏大视野和理论高度,也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应有的文化自觉和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的融合就是东西文化融合的当代形态。
(三)由中国文化启蒙的特殊性所决定,二者融合的主体是儒学。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提出,“对于东西文明之调和,吾人实负有至重之责任,当虚怀若谷以迎受彼动的文明,使之变形易质于静的文明之中,而别创一生面”②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2页。。可见,他主张调和须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现代新儒家向来以对儒学主体地位的守持为要旨,梁漱溟强调:“新芽之发还是要从老根上发,否则无从发起。”③梁漱溟:《精神陶练要旨》,《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05页。甚至自由主义者胡适在新文化要达到的目标上,也说过:“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④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胡适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82-583页。可见,在对待东西文化融合的文化主体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现代新儒家和自由主义者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分歧,都赞成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来吸取西方文化,尽管选择的道路不同。对中国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化,更是儒学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契机,这是由文化启蒙的特殊性决定的。相对于西方文化启蒙来说,中国文化启蒙是一种后发、外源性文化启蒙,现实基础薄弱,缺乏成熟的市民社会,救亡与启蒙双重任务同在,救亡曾一度是时代的主题,面临着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超越。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文化启蒙的双重坐标:启蒙与启蒙的反思,也决定了中国文化必须突破“非中即西”的两极思维模式,挺立起文化的主体性。如李大钊所说,“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通过儒学自身高度的融摄力,在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过程中实现文化传统的更新,对世界文化做出新贡献。
(四)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重撰是二者融合由自发到自觉的契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者儒学观和现当代新儒家马克思主义观的考量,然而二者关系的内涵又远不止后二个方面。当代港台新儒家刘述先有儒家三分法:(1)精神的儒家,指孔孟、程朱、陆王的大传统。(2)政治化的儒家,指由汉代董仲舒、班固以来发展成为朝廷意理的传统,以纲常为主。(3)民间的儒家,指在草根层面依然发生作用的信仰与习惯,重视家庭、教育的价值,维持勤劳、节俭的生活方式。⑤参见刘述先:《儒家思想开拓的尝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这种分法与学界熟知的文化三层分类(观念的、制度的、物质的)大致匹配。如果借用这种三分法来回顾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可以看出,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儒学的批判主要是在政治化儒家和精神的儒家层面;就民间而言,儒学依然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主要精神支撑,并未缺位。政治化的儒家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意识形态中,仍然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现代新儒家对马克思主义多持隔阂态度,但并不能完全代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互动关系。儒学的核心在精神层面的儒家传统,这个层面的儒学并未自觉地去会通马克思主义;从对立到融合话语体系的转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在精神层面长期处于自发状态。儒学应该继续秉持对中国文化的生命观态度,以本体论的姿态去自觉会通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提升为一种文化自觉,因为二者在精神层面的自觉融合,尤其是儒学在精神层面的自觉转化,才能将融合的成果扩充至文化的逐个层面。这是中国文化复兴的重要条件,是儒学创造性转化必经路程,而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重撰正是这种由自发到自觉的一个契机。
(责任编辑:周文升)
B27
A
1003-4145[2015]11-0021-05
2015-09-01
穆允军(1972—),女,哲学博士,山东大学图书馆馆员。
本文系许嘉璐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儒学”(项目编号:11AHZ00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