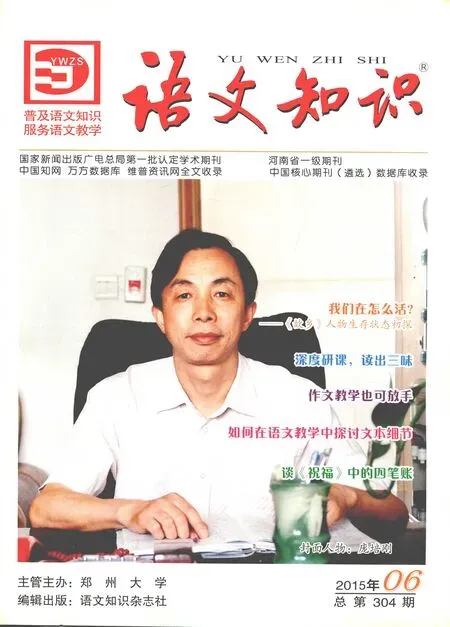对《祝福》之“我”形象的逆向认知
☉山东省德州市第一中学 毕研鹏
对《祝福》之“我”形象的逆向认知
☉山东省德州市第一中学 毕研鹏
《祝福》中的“我”是怎样的一个形象?中学语文教坛并没有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大家所持的观点基本相同:“我”有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憎恶鲁四老爷,同情祥林嫂,性格温文尔雅,对黑暗现实无奈无助,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这些评价告诉我们,对“我”这个人物的感情定位总体是认可的,褒颂的。但在众多大同小异的杂议中,有的碍于“我”与作者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有的试与鲁迅其他小说中的“我”进行比较,并没有客观公正地多方面地去深入剖析《祝福》之“我”的形象特点,即使评价也往往是结论多,依据少;概括多,具体少;称赞多,批评少。没有将“我”放至具体的语言环境和那个时代社会实情中去综合考虑,于是片面的、狭窄的、陈旧的定论一直就这样主宰着“我”,主宰着高中语文教坛,这对作品的认知无疑是不全面的,甚至是有害的。笔者通过认真研读原文,觉得在《祝福》中“我”的身上,除了同行们已经定论的那些特征之外,还觉得这个“我”十分明显地存在着诸多不容忽视的弱点,兹逆向认知如下。
一、心思沉重,疑神疑鬼
“我”回到故乡以后,心情始终如天上密布的“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一直处于压抑郁闷的状态之中,从来也没有开朗过,快乐过,从来也没有见到“我”的脸上有过哪怕是丝毫笑容,并不比《故乡》中的“我”回到故乡时的心情好多少。“我”在生养自己的老家鲁镇活动的这几天,即使是看望朋友、与族人见面、适逢“祝福”大典,也没有给“我”带来丁点快慰和欢乐,为什么会是这种心情呢?也许是工作不顺吧,也许是朋友“云散”吧,也许是对前途迷惘吧,都未可知,也不必去追究。但是我们通过阅读可知的是“我”具有多疑的特点,这与“我”带着沉重的心思回故乡吻合一致。文中写道,与四叔见面,他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这虽然否定了四叔大骂对象并非指“我”,而是骂康有为,但是在“我”的心里当时肯定是产生不快的,因为“我”知道,“我”与新党的政见是一致的,“我”是赞成新党革新做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骂他们就是在骂“我”,具有指桑骂槐的性质,所以“我”表面上排斥了四叔对自己的骂语,实际上“我”多疑的特点这时已经像早春的幼芽一样开始萌发了,只是未明说,没爆发而已。真正让这种“疑神疑鬼”的心态明朗化、最大化的是在后面。文中写道:“我从他俨然的脸色上,又忽而疑他正以为我不早不迟,偏要在这时候来打搅他,也是一个谬种。”根据情节可知,这里的“谬种”绝对是骂祥林嫂的,因为她是在鲁家正欲举行“祝福”大典的时候“不早不迟”地死去,这种不吉利也就“不早不迟”地冲淡了四叔家的祝福喜气。对于四叔在家里的这种私下“骂”语,应属一种十分正常而合乎情理的表现。在四叔的眼里,“我”是他的侄儿,是一个有一定地位的知识分子,又是从城里来的,给他带来的是看望,是亲近,是团聚,是联络,也给了他足够的面子,至少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不祥不吉的东西,与祥林嫂的死讯是有本质区别的,他怎么会视“我”为“谬种”呢?这明显是“我”在自寻烦恼,敏感多疑。特别是后来短工与四叔的谈话,内容是祥林嫂之死,“我”也觉得“似乎这话于我有关系”,再次证实了“我”多疑多心的特点。为什么“我”会产生这种心理呢?也许是四叔对“我”没有足够的尊重吧,也许是四叔家的饭菜没有城里的“鱼翅”好吃吧,也许是四叔因为太忙没有更多的时间陪“我”聊天吧,都未可知。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这些心理和情感都受“我”心思沉重的感情基调支配,因为人一旦心情不好,各种不快心理就会像暖风中的草芽一样涌发出来。“我”的多疑也就决定了“我”要早早地离开这里,短暂的故乡之行就在这样的不快中结束了。
二、空有同情,有心无力
“我”是文中同情祥林嫂的唯一的人,这一点十分清楚,毋庸置疑,难能可贵。这种情感的间接表现是在“我”对主人公三个苦难生活片断的回忆中,直接体现则是在“我”第二次见到祥林嫂以及听说她惨死之后的心理活动中。那乞丐般的外貌描写,惨不忍睹;那死后如“尘芥”似的结局,催人泪下。至此“我”对祥林嫂的同情已跃然纸上。但这种同情并不值得全盘肯定和赞美,它仅仅属于具有进步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同情,属于心情压抑下内敛式的同情,属于只有自己才知道的私下同情,祥林嫂没有感受到,四叔四婶也不清楚,鲁镇的民众更不了解,所以这种同情就显得十分有限,非常软弱,它没有亮色,没有力量,没有呐喊,没有传递出来,只能是空有同情,而这种同情是很容易做到的。“我”在同情时想过改变祥林嫂的命运了吗?想过给她以切实的精神的或物质的帮助了吗?想过请四叔四婶关照她了吗?都没有。这样看来,“我”的同情只对自己起作用,只是一厢情愿,而对主人公祥林嫂的命运则毫无改变作用。真正有价值的同情是将心动化为行动,“我”的心动过程确实很细腻,很充分,也有一定的感染力,可是行动呢?祥林嫂已成乞丐,见她走过来,“我”虽然“豫备她来讨钱”,可最后给钱了吗?肯定没有,因为“我”已被她的几句问话“悚然”了,背上如“遭了芒刺一般”,不得已只有“匆匆的逃回了四叔的家中”躲起来,物质上的帮助不存在了。听说祥林嫂死后,“我”背地里吊唁了吗?前去看望了吗?私下里哭泣了吗?也没有。这种有心无力、仅仅心动而无行动的同情,实际上只能说是感情上的一种支援,心理上的一种呼应,思想上的一种走向,太苍白了,无论是客观还是主观上,都不能引起人们对“我”产生足够的尊重甚至褒赞。这也是“我”的无奈无助、胆小软弱造成的。
三、心猿意马,追求享受
文中的“我”虽然是一个积极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具有勇于改革的思想意识,虽然有比较浓厚的反封建民主精神,但在物质生活上有着不可否认的追求享受的倾向。根据文中记载,“我”是腊月二十四日夜里回到故乡鲁镇的,住在远房四叔家,又在四叔家二十七日晨举行“祝福”大典当天回城的,其间连头带尾总共四天三晚。在四叔家生活情况怎样,文中并无丝毫笔墨,我们并不知道,也无须知道。但“我”在这里的思维方向是时刻想着回城的,可谓心猿意马,寝食难安,从未把四叔的家当作自己故乡的家,也不觉得这是生我养我、魂牵梦绕的故乡,更没有表现出对故乡有多少留恋和依赖,亲热感、久别感、熟识感均荡然无存,“我”随时准备回城,随时想着城里好吃的“福兴楼的清燉鱼翅”。因此“我明天决计要走了”的心思像刚刚点燃的火苗,不断在“我”的心中烧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根据课文叙述,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与四叔说话“总不投机”,这不仅是两辈人之间具有代沟而产生隔阂,更主要的是政见不同,没有共同语言和志趣。二是祥林嫂的不幸在“我”的心中激起了更大的冲击波,行走在故乡的土地上,自然要睹物思人,触景生情,这里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都在随时提醒着某些东西,都在影响着“我”的情绪,身在故乡,却时时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悬浮感,是一个失去精神家园的漂泊者。三是暗含着吃住都不习惯,于是自然想到城里舒适的生活和可口的“不可不吃”的“鱼翅”之类的美味,以及城里安逸稳定的悠闲生活,特别是“鱼翅”的吸引力远远超过故乡的一切。“鱼翅”在《拿来主义》中是比喻为文化遗产的精华部分,在本文则是美味佳肴的代表,吃鱼翅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毋庸置疑,其原因明显是一种贪图享受、追求安逸的思想情绪。人在环境不适应的情况下是会改变初衷的,“我”原计划准备回乡住多长时间,我们并不知道,但“我”因为诸多原因“明天决计要走”则是最终定论,而且四次强调,反复呈现,足见“我”离乡回城决心之坚,欲望之切。
四、迷信犹疑,间接凶手
“我”虽有反封建倾向,但不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反封建斗士,更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对于魂灵地狱的有无、来生今世的演绎,心中并无一个明确的定位,始终处于犹疑不定、将信将疑的状态之中。这种不定的思想意识,也就决定了对祥林嫂问话的回答内容。祥林嫂共向“我”询问了三个问题:一是“有没有魂灵”,二是有没有“地狱”,三是死后一家人能不能“见面”。这三问之间显然是连带关系,形成环链:如果有魂灵就有地狱,如果有地狱死后一家人就能见面。祥林嫂为什么不问别人而单单问“我”呢?因为她知道“我”是一个“识字的”人,一个“出门人”,一个“见识得多”的人,只有“我”的话她才相信。“我”与祥林嫂本来是相识的,现在的突然遇到和她的突然问话,让毫无思想准备的“我”无所适从,匆忙间便只好这样答道:对魂灵,“也许有罢”;对地狱,“也该有罢”;对家人能否见面,则“说不清”。“我”这三答的主要意思倾向分别告诉她:有魂灵,有地狱,一家人死后能够见面。“我”为什么要这样回答呢?因为“我”对祥林嫂的那三个问语,“向来毫不介意”,本来就不甚明了,又处在紧张之中,在这特定时间特定场合下,严峻地考问了特定的“我”,彰显出了“我”灵魂深处的软弱与浅薄。这就表明,在“我”的潜意识里,是有着一定的封建迷信思想的。把这种以肯定为主又含有“说不清”意味的答案传递给祥林嫂,初衷虽然是“为她起见”,实则给她带来了死亡的后果,甚至加速了她人世的终结。我们知道,这是“我”与祥林嫂唯一的一次对话,祥林嫂是在精神痛苦至极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壮着胆子来问“我”的。她虽然穷困之至,濒临死亡边缘,但此时她的大脑是特别清醒的,对于“我”的回答,她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她是确信的,因为这是一个“识字的”人、一个“出门人”、一个“见识得多”的人面对面亲口说给她的,祥林嫂怎么能不相信呢?“我”关于魂灵和地狱的说法,与小说后面柳妈“捐门槛”建议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这就让祥林嫂对今生甚至“来世”彻底绝望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是造成祥林嫂悲剧命运的间接凶手之一。
五、推卸责任,逃避现实
“我”对祥林嫂的不幸遭遇及其悲惨命运深表同情,于是也就设置了“为她起见”的那些答语,可事后又觉得“怕于她有些危险”,隐隐约约感到“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深怕她会发生什么意外,于是“心里很是觉得不安逸”,这种为他人生死存亡考虑的初衷,无疑是一种同情,是值得肯定的。但在言行上却没有这种诚恳求是的认责态度,敢说不敢承认,敢做不敢担当。“我”始终在寻找各种借口为自己开脱罪责,否定对祥林嫂说的话有问题,否定祥林嫂的死与自己有关。这一切主要体现在多次运用的“说不清”三个字上,认为“说不清”推翻了答话的全局,言下之意是“我”并没有肯定说有魂灵和地狱。于是“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即使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我也毫无关系”,因而感到“逍遥自在”,“渐渐宽松”起来,“渐渐的舒畅起来”。这样翻来覆去,自圆其说,好像有理有据似的,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有责甚至有罪辩护。我们知道,“我”头一天对祥林嫂说了关于魂灵与地狱的话,第二天她就不声不响地悲惨死去,这种客观上和时间上的巧合,不正好有力地说明“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祥林嫂的死与“我”说的话有关吗?俗语云“心里有事心里惊,心里无事凉冰冰”,说了关于魂灵和地狱的话之后,“我”当时的表现是说话“吞吞吐吐”,模棱两可,这不是一种“胆怯”和“惊惶”吗?这不是明显的心虚吗?听到祥林嫂的死讯之后,“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也“变了色”,感到“有些负疚”,这不是主动承认祥林嫂的死与自己有关吗?这种心理状态及思维变化,充分显示了知识分子精神道德上的不足,这种不足正是传统思想在“我”灵魂里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暴露了“我”圆滑世故、软弱退缩、敷衍耍滑的特点。到了后半夜将近五更的时候,四叔家开始“祝福”大典,此时“我”的心理状态已经是“懒散而且舒适”了,“我”白天的“疑虑”和祥林嫂的惨死都被时间和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天亮以后,“我”就要离开鲁镇,离开故乡,离开这是非之地。这就揭示了“我”在黑暗残酷的现实面前逃离现实、回避矛盾的软弱心理。
以上从五个方面对文中的“我”进行了逆向认知,主要揭示了“我”在小说中存在的若干缺点,是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来展示的。这样评价,对小说主题、人物特征乃至作者思想的深层认知都具有积极的解读意义。当然,这些文字只是笔者的一家之言,对“我”的这些认识,定位不一定准确,恳望同行大家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