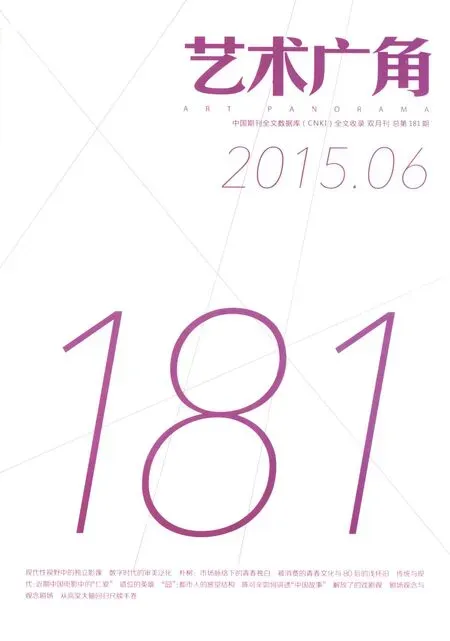芥川龙之介的“中国盒子”
赵月斌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盒子”
赵月斌
赵月斌:评论家、作家,任职于山东省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著有文学评论集《迎向诗意的逆光》《暧昧的证词》等,并小说、诗集多部。
《奉教人之死》:“中国盒子”
“中国盒子”是西方人发明的一个词,指那种大盒子里套小盒子的“套盒”,有时人们也用来比喻故事中套故事的叙述方式。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奉教人之死》就有点“中国盒子”的味道。
首先来看最外面的盒子:罗连若是一个身份不明的孤儿,大难不死,被教堂收养。“问其籍贯,则谓家在天国,父名天主。”“颜如冠玉,其声呖呖类小女子,性复温柔,故深得怜爱。”初看就是这样,罗连若给人的印象是一“道心坚定”的美少年。
打开第二层盒子,事儿就来了:谣传天主教徒罗连若与不远坊间一伞铺之女“有暧昧事”。不过还好,虽然连好友西美昂也“悬悬于怀”,但是罗连若尚能声辩“绝无此事”,神甫也没有听信谣言。当西美昂质问时,罗连若的回答是:“尔以余为欺上帝之人欤?”可见他是直以上帝为鉴的。在这个盒子里,罗连若名虽蒙尘,却属小劫。
打开第三层盒子,事儿闹大了:又传伞铺女身怀六甲,且自谓腹中胎儿乃罗连若所为。至此罗连若“无辞自解”,终因“破色戒”被逐出教堂,成了一个流落街头的叫花子。虽然这时他常被儿童嘲谑,还常常挨打,却仍不忘日课,晨昏祈祷,每以夜深人静时,便到教堂前“默求主耶稣之加护也”。在这个盒子里,罗连若的命运急转直下,好友西美昂亦失望至极,以“老拳”痛击之,按照通常思路,罗连若是罪有应得了。
打开第四层盒子,意外又来了:伞女之子困于大火之中,罗连若冲入火窟舍身相救。众人交口互议,认为这是出于“亲子之情”,伞女则跪伏于地,一心祈祷,不动声色。讲到这儿,似已印证传言不虚,罗连若所受苦厄也算罪有应得了。如果故事在这儿结束,完整倒也完整,却平淡无奇,好在芥川的盒子还没完全打开。
打开第五层盒子,果然还有秘密:孩子救出来了,罗连若却已通体焦煅,奄奄一息了。这时伞女终于愧疚难当,说出了真相:那孩子原是她与邻人异教徒私通所生,罗连若一直在代人受过。至此,罗连若的形象骤然扭转,一洗淫徒恶名,顿为“殉教之士”。故事讲到这儿,有点儿欧·亨利的味道,如果在此收尾,也算峰回路转了,然而杰出小说家总会有出人意料的盒子,并且轻易不会打开。
总算到第六层盒子了,芥川果然把精彩留到了最后:谁能想得到,因破色戒而获罪的罗连若,竟与伞女同性,乃一美目盈盈之少女!“于焦破胸衣中,垂垂露其少女之双乳,莹然如玉。而焦煅之容,益不能掩其娇姿。”这才是盒子的内核,芥川确是会营造气氛的魔术师,经过层层铺垫,终于爆出一个偏离常规的结果。
好小说总是偏离常规,总是从无限的不可能中找出无限之可能。初读此篇时,我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本文亦是为女性立言。罗连若身为女儿之身,却代人担致某女怀孕之罪,此一不易也;其获罪而不辩白,又是二不易也;至某女之私生子遭大火,又入火救人,更是三不易也。此种胸怀,怎不令人吁叹!
这篇小说可与霍桑的《红字》相对照。不过这里的罗连若比《红字》中的海丝特更加难能可贵,虽然都是忍辱负重,海丝特背上的红字事出有因,她保护的也是自己所爱之人;罗连若之辱却纯粹是无中生有的,虽然遭到的陷害也极易揭穿,她却始终缄口不言,情愿自己受难,以保护和宽恕加害自己的人。
当然,还可仅就小说中两女人作比较。伞女对罗连若是由爱而恨,罗连若则自始至终都宽以待人。伞女对得不到的是加害,罗连若既未以眼还眼,反而报之以大义。
呜呼,同是女人,高下自分!
《秋山图》:画境——画镜为牢?
我不知有没有一种“鉴赏发生学”,《秋山图》这篇小说似乎就在表现这种评判观念。如果把“鉴赏”看作抵达真理、诉求本质的行为,这种“鉴赏发生学”实则又是一种“价值发生学”。那幅《秋山图》实为一面镜子,随着时间、地点及观赏者的变化,它的内容也在变化,它所“携带”和“反映”的“价值”从来不是对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能够两次看到同一幅画吗?
听闻之——神往之。
烟客翁(王时敏)崇拜元代绘画神手黄一峰(大痴)——黄留在世间的画,翁差不多全见过,然而被元宰先生(董其昌)赞为极品的《秋山图》,翁却没见过——非但没见过,连听也几乎没有听说过。这让翁“觉得挺不好意思”。翁是黄的信徒,当然急于补上这一课,出于一种求全、迷信心理,在没见到画之前,他已提前作出了价值判断,之所以急着亲自去看,不过是出于对“名画”的景仰而已。
寻访之——疑虑之。
烟客翁拿了元宰先生的介绍信,到润州寻访《秋山图》,却见张氏的家院一片荒凉,厅堂里也是“荒落的气味”,乘兴而来的烟客翁不禁大为怀疑:“这种人家能收藏大痴的名画吗?”在他看来,名画必定藏于名门,因此,也就没指望在这里看到什么《秋山图》。
亲见之——倾倒之。
没想到,一幅名画,就属于这寒素之家,没有藏于秘室,没有锁于匣中,而是随随便便挂在厅堂正墙上——一抬头就看到了,对本已情绪低落的烟客翁来说,可以说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子就被眼前的画境击倒了:“美得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愈看愈觉神奇”。这时候,翁是画的俘虏,他已完全被迷住了。
求不得——断念想。
烟客翁与《秋山图》的一面之缘不过“一会儿”,却再也“忘不了”,“无论如何想得到这幅稀世的黄一峰的画”,然而几次派人交涉,画主人也不肯出让,一年后再想看时,竟被拒之门外。翁只能“想象”那幅名画,也死了收购之心,从此“断念”了。愈是得不到的东西愈显珍贵,何况连再看一眼的机缘都没有。这时候,《秋山图》已占据了烟客翁心目中最神圣的高地,再也无可替代了。
重见之——大失望。
五十年后,王石谷拿了烟客翁的介绍信,再度寻访《秋山图》。原来画已落入“相识的”贵戚王氏之手,王石谷根本不费烦劳,就可“拜观”《秋山图》了。在他看来,名画有主,烟客先生大可安心了,自己也觉得十分“快慰”。然而当《秋山图》“真品”出现在眼前时,他却觉得“和烟客翁在张氏家见到的那幅,确不是同一黄一峰的手笔。比之那幅,这恐怕是比较下品的黄一峰了”。不单王石谷,就连见过《秋山图》的烟客翁也大失所望,觉得这幅《秋山图》真迹远非五十年前所见,“一切如在梦中,也许张氏家的主人是一位狐仙吧”。王石谷与听说的《秋山图》作比较,烟客翁与记忆中的《秋山图》作比较,由是《秋山图》从“神品”堕入“下品”。
画境——画镜为牢。
听其名、羡其实、见其美、憾其失、慰其出、诧其不过尔尔——为什么鉴赏这样一波三折,反复无常?为什么同一幅画在同一人眼里也会截然不同?也许心态、心境是主要的。就烟客翁、王石谷来说,初见《秋山图》之前,都有一个间接认识,《秋山图》之美经他人之口的着力渲染,已被他们心领神受,心里的《秋山图》已悄悄化为一道坚硬的屏障,必然会遮蔽他们的目光。那么,又为什么烟客翁与王石谷第一次见到《秋山图》感觉又相差甚远?或许应该与环境和情势有关。翁见《秋山图》的地点是墙上爬满藤蔓、院里长着长草、鸡鸭成群的张氏厅堂正墙,除了画主人之外,只有翁独自一人观画。而王见《秋山图》的地点是在庭院里玉栏边盛放着牡丹的王氏厅堂侧墙,与他一起观画的,还有画界名人及府上食客。翁见到《秋山图》实出意外,王见《秋山图》则在程序之中。试想一下:一个是在静寂萧素的寒门陋室忽然发现了美,一个是在富贵喧嚣的豪族华府专作欣赏品评,怎么会有相同的感受?所以,即使曾与《秋山图》有过一面之缘的烟客翁,也生出了“如在梦中”的感叹。芥川想必有意作以对比,赏画的心理背景和环境背景变了,对画的看法也随之大变。
此外,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烟客翁在张氏家见到《秋山图》,画主人的态度:
《秋山图》是美的,但这个美,是否只有我觉得美呢?……我总是这样怀疑。(对画)
今天听了您的称赏,我才安心了。(对赏画者)
烟客翁的态度:
完全被迷住了,愈看愈觉神奇——元宰先生的称赏非虚言。(对画)
对主人的话没怎么放在心上,同时也认为他不懂得鉴赏,硬充内行。(对画主人)
再就是众人在王氏家中见到《秋山图》时,芥川在这里更为细致地刻画了画主人的态度变化——
王石谷盛赞画归王氏府上所有,他“满脸得意”;
王石谷不经意流露了不服气的表情,他“带着担心的神气”打问;
王石谷忙称“神品”,他的脸色才“缓和”起来;
烟客翁看画时脸上笼了一道阴云,他“更加不安”,又“怯生生”地问;
翁未作正面回答,他脸上的愁雾却更深了;
待廉州先生进来对《秋山图》表示怀疑时,他“愈加尴尬”;
直到这位廉州先生一一指出画的佳处大大赞赏时,这位画主人才“脸色渐渐开朗”。
看来,这两次鉴赏行为都掺杂了许多外在因素。在张氏家,烟客翁是用元宰先生的眼睛看画,看到的是尽善尽美的黄一峰。在王氏家,王石谷又是在用烟客翁的眼睛看画,看到的则是“比较下品”的黄一峰。虽然他们得出的结论不同,目的却是一致的:他们钟情的只是元宰先生称赏的《秋山图》。鉴赏者在心目中把艺术之美推向了一个不可企及的神秘高度,收藏者却急于得到一个实实在在的结论,对一件艺术品来说,权威的评价无疑倍受瞩目。重要的是,这个结论是谁给的,是怎么给的。在张氏家,烟客翁是替元宰先生说话,在那个谦恭的画主人面前,他表现出的是宣读圣旨般的神气。在王氏家,众人只是贵戚请来的看客,他们只能替画主人说话,所以,烟客翁、王石谷、廉州先生无一例外都只能尽拣好的说。结论就这样产生了——《秋山图》只能是一幅好得不能再好的画,谁说它不好,只能说明他的鉴赏水平有限。
这篇小说当然可以看作对艺术观念的阐释,如果把“鉴赏”当成一般认知过程,我们能否直达本质?我们被蒙蔽了没有?我们的头颅上是不是带着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自己的嘴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背景就有什么样的鉴赏?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是有那么一幅无所不在的《秋山图》,对它,你只能说美,对它的影子,你也要说美。也许真理就是这样产生的:元宰先生说过的话,被烟客先生接受下来,烟客先生再把他的话传布天下——于是,我们听到的看到的莫不是元宰先生,于是,我们说出的莫不是元宰先生,于是,我们都成了元宰先生的替身,我们已无法使用自己的心灵。
《阿富的贞操》:贞洁的底线
“《阿富的贞操》中,阿富为了救助一条猫儿的生命,竟然准备坦然献出自己的贞操。”这是译者楼适夷说过的话。初读此篇时,我也曾批评道:“女性之颂辞,为了一只猫,阿富宁肯付出贞操,试问天下人谁如此珍视一个异类的生命?女性的胸怀……”可是后来再次细读,又觉得这样的评价太表面化了,也许,阿富并不单纯为了救一只猫,促使她献出贞操的,也许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阿富为主人寻找走失的猫,与乞儿老新在一空屋相遇。老新被她“年轻处女的肉体”所诱惑,欲行不轨,却给阿富逃脱了。于是老新掏出枪,对准了神棚上的猫,以此要挟阿富:要么把猫打死,要么“把你的身体让我使一使”。故事就在这个当口绷紧了,阿富只能做出选择。下面不妨来考察两个人的对峙过程。
阿富——“转过脸去,一下子在心里涌起了憎恨、愤怒、伤心,以及种种复杂的感情。”
老新——“深深注意着她情绪的变化,大步走到她身后,打开茶间的门”……“目光落在微微出汗的阿富大襟上凸出的胸部。”
阿富——“好像已经感觉到,扭过身子望望老新,脸上已恢复开头时一样灵活的表情”。
老新——“反而狼狈了,奇妙地眨眨眼睛,马上又把枪口对准猫儿”,继续威胁阿富。
阿富——“没奈何地嘟哝了一句,却突然站了起来,像下了决心,跨出几步走进茶间去。”
老新——“见她这么爽气,有点惊奇。”……“站在茶间外,侧耳听着茶间里的动静。”
阿富——“解去身上的小仓带,身子躺在席子上”……“仰身向上躺着,用袖子掩着脸。”
故事发展到这个地步出现了意外——阿富准备献出贞操了,然而更意外的是老新的反应:“连忙像逃走似的退到厨房里,脸上显出无法形容的既像嫌恶又像害羞的奇妙表情”。
关键时刻,老新没有拿走阿富的贞操,甚至还要不解地问阿富:对一个女人来说,失身是大事,为什么为救一只猫,就随随便便答应了?阿富不答,只是“轻轻一笑,抚抚怀中的猫”,老新继续问:你那么爱猫儿吗?“‘可是大花,大花多可爱呀……’阿富暧昧地回答。”(注意这个“暧昧”!)于是老新又问她是不是因为怕猫死了对不起主人,阿富则答“我不知道怎样说才好……那时候,觉得不那样,总是不安心嘛!”
阿富终究没说清为什么肯为一只猫献上贞操,恐怕她自己确实也说不清的。不过芥川倒是又在后面加了一段尾声:二十三年后,已有三个孩子的阿富与老新在街上重逢,昔日的乞丐老新已成了不胜荣耀的贵族。“阿富不觉吃了一惊,放缓脚步。原来她有过感觉……老新可不是一个平常乞儿。是由于他的容貌么,是由于说话的声气么,还是当时他手里那支手枪?总之,那时她已经有点感觉了。”“那时为救一条猫的命,她是打算顺从老新了。到底是什么动机,自己也说不上来。”阿富为什么会顺从老新?既说为救猫的命,又说不上什么动机,如此只能理解阿富的行为是下意识的,是被迫之后的顺从,或者说是迎合与渴求。在那一刻她突然对老新有了“感觉”,所以就置所谓“贞操”于不顾了。
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不符合动物保护主义者的要求,也不符合贞洁主义者的要求,但我相信,它符合人性最基本的要求。我不会因此鄙视阿富,我仍相信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相信“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报恩记》:以恶报恶
《报恩记》写的是一个关于“报恩”的连环故事。
阿妈港甚内是日本第一大盗,二十年前,他因醉酒打死了一个中国人,被船长弥三右卫门搭救。
二十多年后,阿妈港甚内到弥三右卫门家行窃时,认出了当年的恩人,知道他的船沉没了,要破产了。于是阿妈港甚内答应弥三右卫门:“打救他的急难,报答他的大恩,在三天之内筹到六千贯银子”。
弥三的儿子保罗弥三郎是个败家子,因嗜赌成性被赶出家门。他碰巧听到了大盗阿妈港甚内的的话,于是决定替全家“报恩”——最后他冒充阿妈港甚内,自陷死地,被捉住砍了头。
表面看来,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传奇故事。中国也有句俗话叫“知恩不报非君子”,它告诉人们:既已蒙恩,便当图报,这才是仁义之举。在《报恩记》中,执着的报恩者追求的正是这种定理,上演了一连串的绝妙好戏。
芥川小说的翻译者楼适夷认为,《报恩记》“写一个浪子为报答义贼和剧盗救助一家的恩情,而甘愿以身代死,也是极为动人的”。义贼报恩,浪子代死,乍一看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一事,译者这么说,大概许多读者也会这么看。可是这般高论我实在不敢苟同,在整个故事中,看不到高尚,看不到正义,所谓“动人”又从何而来?读《报恩记》,我实在看不出那三个男人有什么值得褒扬的,我从他们身上看到是恶,是自私,我看到的是一个以恶报恶的黑洞。
先说弥三右卫门“搭救”阿妈港甚内。我想象不出弥三对一个杀人凶手出手相救有什么理由,也许唯一的理由是因为阿妈港甚内是他的日本同胞,而被杀者只是一个中国人。在我看来,这个故事一开始就是在恶的黑洞里孕育的,表面上,弥三搭救阿妈港甚内毫无私心,但是必须注意到:二十多年后他们回忆往事时,都在下意识地认同对方的“日本人”身份,弥三说“我搭救过一个没长胡子的日本人”,甚内说“有位日本人的船长,救了我的性命”。也就是说,弥三对甚内的搭救并非毫无缘由,虽说甚内是杀人凶手,只因他是日本人,弥三就把他救了。对自己的同胞出手相救,这样做有什么错?把弥三的做法拿到当前讨论,肯定还会有人视之为“民族大义”,从而忽略了受害者应该得到的公平。在弥三救甚内时,不会想到他是杀人犯,只会想到他是日本人,所以,不管他做了什么,只管救人了事。弥三对阿妈港甚内的“恩”无非是包庇犯罪而已。我想,日后甚内成为有名的强盗,弥三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他用“善”成就了恶时,“善”即是恶。
再说阿妈港甚内“打救”弥三右卫门。原因很简单:因为弥三曾是阿妈港甚内的救命恩人。所谓一报还一报,强盗阿妈港甚内终于找到报恩的机会。恩人缺钱了,他要为恩人筹钱,至于怎么“筹”,他是强盗,当然要用强盗的手段。阿妈港甚内对弥三的“恩”不过是损无辜补私愿而已。甚内报恩值得称许吗?竟或谥为“义贼”?对此等说法我只能一笑,作为读者,怎么能站在弥三的角度去欣赏一个盗贼?此人即使有“义”,也只是对恩人偶发的“义”,不过是以不义之财行不义之事,当他用“义”成就了恶时,“义”便是恶。
最耐人寻味的是保罗弥三郎“报答”阿妈港甚内。保罗为什么会把身家性命慷慨地转借给一个强盗?也许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阿妈港甚内是保罗“做梦也向往”的人,他“企慕”这个杀人越货的大盗,“干了许多将会世代相传的恶事”——“光是看看他也是一种幸福”,为了“得到更大的幸福”,他决定“报恩”。怎么报恩呢?最初保罗想拜在甚内门下,做他的徒弟。保罗陈述的理由是:“我会偷窃,我也会放火,我干一切坏事,不比人差……”然而,甚内也许以为这是对自己的污辱,反骂他“混账”,“我甚内不要你的报答”,“好好孝敬你老子吧!”报恩的企图一再受阻,成了保罗的一块心病,后来,“报恩”转变成了“雪恨”——他铁了心要把报恩进行到底。两年后,保罗得了吐血的病——“活不到三年了”,他倒想了一条“妙计”:拼掉得病的身子,“代替甚内抛弃这颗脑袋”。他的逻辑是:甚内的一切罪恶可随保罗消灭了,而甚内的荣誉都变成了他保罗的,“天下再没比这更痛快的报答了”。在这个故事中,保罗的报恩付出的代价最大,为个人算计的也最多。
所以,在这三个人身上,我没看到什么恩什么情,相反,我看到的只是一种以恶报恶的恶性循环。他们不过是借着“行善”“报恩”的名义,演绎一个“私”字而已。知道弥三遭困时,想到自己“有报恩的机会了”,甚内异常高兴——这种高兴“除了我自己以外,别人是不会了解的”;想出砍头妙计时,保罗高兴得笑了“三次”——“既帮助了甚内,又消灭了甚内的大名,我给我家报了恩,又给自己雪了恨”。他们的报恩都是从自己出发的,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可以“干一切坏事”。这样的报恩不是太可怕吗?不过,比较来看,弥三的“大义”实为“大私”“大恶”,甚内的报答实为“中私”“中恶”,保罗的报恩只能算“小私”“小恶”了。读了《报恩记》,有理由更加警惕某些“微言大义”,更有理由警惕一些专擅“投桃报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