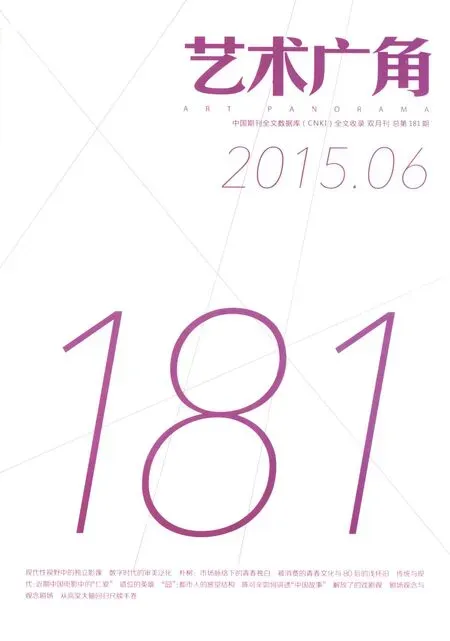解放了的戏剧观
——以邹静之《我爱桃花》《操场》为例
解玺璋
解放了的戏剧观
——以邹静之《我爱桃花》《操场》为例
解玺璋
解玺璋:《北京日报》高级编辑,文艺批评家。曾出版《喧嚣与寂寞》《中国妇女向后转》《雅俗》《梁启超传》《一个人的阅读史》《五味书》《说影》等十余种专著。从事艺术评论、近现代史研究。
邹静之作为电视剧编剧,已经广为人知。近些年来,他又在舞台剧上开疆拓土,至今已创作了四部话剧、三部歌剧。就题材而言,这些剧作是丰富而多样的。如果一定要找出其中的共同点和闪光点,我以为非戏剧观莫属。
邹静之在戏剧创作中始终如一坚持一种戏剧观,我想也许可以称之为“解放了的戏剧观”。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中国戏剧(话剧)已经进入第二个百年,然而,能够进入历史的戏剧作品其实很有限,近年来大家更觉得,求一个好剧本或好的剧作家尤其难。在我看来,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戏剧观限制或束缚了戏剧家的创造力。
戏剧观没有好坏优劣之分,任何一种戏剧观指导下的创作都有可能产生好的作品。但是,如果我们把某一种戏剧观不适当地绝对化,认为它是超越时空、牢笼一切创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后果恐怕就是灾难性的。百余年来的中国戏剧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按照黄佐临先生概括性的说法,两千五百年的戏剧史只有两种戏剧观:造成生活幻觉的戏剧观和破除生活幻觉的戏剧观,也可以说是写实的戏剧观和写意的戏剧观。如果增加一种,那就是写实写意混合的戏剧观。他认为,纯写实的戏剧观历史并不长,而且,“产生这戏剧观的自然主义戏剧可以说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寿终正寝,但我们中国话剧创作好像还受这个戏剧观的残余约束,认为这是话剧唯一的表现方法。”
这个判断应该说大致不错。其实,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有一位名叫维拉·凯尔茜的西方人观察到中西戏剧的这种逆向运动。在纽约出版的《戏剧艺术月刊》上,她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新剧场》的文章,向大家报告了她的发现:“中国剧场在由象征的变而为写实的,西方剧场在由写实的变而为象征的。”[1]这里面包含着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前提,即中国戏剧曾经是“象征”的,而西方戏剧曾经是“写实”的,至少是在自然主义戏剧兴起之后成为“写实”的。证之西方戏剧发展史,1887年3月30日(这是个重要的日子),在巴黎上演了一台小戏,即根据左拉小说改编的《雅克·达摩》。虽然当天的观众不超过四百人,但它却成为西方戏剧史上划时代的一个事件——自然主义戏剧由此产生,并且很快发展为批判的现实主义,他们在“要改变生活,必须先认识生活”的口号鼓舞下,将生活原貌搬上舞台,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告人的卑鄙、愚蠢、伪善、肮脏,一律采取揭露、讨伐的态度,由此表达一种社会理想。易卜生、萧伯纳、契诃夫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而在具体的表现手段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当众孤独”又与他们提出的“第四堵墙”一脉相承。
话剧就是在这种戏剧观的全盛时期进入中国的。很显然,它的创作理念完全契合了现代中国所面临的启蒙与救亡两大任务的要求。要想改变生活,先要认识生活,而戏剧正是最佳的认识生活(开民智、新民德)的工具,即所谓“移人之心,换人之脑,速万倍也”,其作用甚至优于小说,因为,读小说尚须识字,观剧则文盲亦可。事实上,中国话剧自诞生以来,几乎从未摆脱过这种宿命。胡适当年就曾说过:“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应当承认,这种对于戏剧的认识已经包含着工具论的倾向。而随着中国社会的风云激荡,戏剧活动越来越多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发生在1923年的苏俄文艺论战,很快也在中国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其结果是促成了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变,戏剧亦被纳入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如果说以前的写实、写意之争,还只是方法、手段或戏剧观念与美学观念之争,那么此后,写实写意就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写实遂以“现实主义”之名,被赋予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光环,而提倡和强调写意,就成了唯美主义或艺术至上主义,成了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思潮。
显而易见的是,近百年来,给中国戏剧带来巨大灾难的,不仅仅是“自然主义戏剧观的残余”,更有被视为唯一法则的现实主义戏剧观。既然现实主义被看作一种与历史逻辑相联系的客观的创作方法,那么,从历史逻辑到超验的艺术标准,也就再没有任何障碍。在这里,真实被赋予一种崇高感,不真实变成了戏剧艺术的原罪。但这个“真实”已经不是左拉的大胆暴露,也不是胡适的“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而是所谓“本质真实”。卢卡契坚信,现实本身是有深度的,现实是现象与本质的统一。因此,深刻的文艺作品必须直透现象中的本质,揭示社会结构关系、发展原因及方法,否则就会流于浅薄。于是,单纯的写实就有了“自然主义”之名,而现实主义的“现实”却是以某种主义的名义对现实的改写。为什么许多冠以“现实主义”之名的戏剧作品却给人以虚假和粉饰现实的感觉呢?秘密就在这里。这也就是黄佐临在重提写意戏剧观时把矛头指向自然主义戏剧观而小心地避开现实主义的原因。为此,他甚至要强调,梅兰芳、斯坦尼、布莱希特所代表的“三个绝然不同的戏剧观”都是现实主义的。
我在这里喋喋不休地述说这些陈年旧事,其实是想说,邹静之的戏剧创作恰恰是从怀疑这种“唯一法则”的唯一性开始的。黄佐临发出“解放戏剧观”的呼吁是在1962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的呼吁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相应的反响,直到文革结束,思想解放运动兴起,为中国戏剧寻找新的出路的有识之士,才将这篇被人们遗忘了将近二十年的文章发掘出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关于“戏剧观”的大讨论。现在看来,这场讨论的确深刻影响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戏剧创作,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戏剧单一、僵化的面貌,其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便是高行健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思考。由于他的开拓性的探索和实验,中国戏剧领域那种长期“被写实主义和舞台演出的幻觉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已萌生出变动的征兆”。可惜好景不长,这种植根于中国戏剧传统的写意戏剧观似乎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与切实的理解,到了邹静之进入戏剧创作的2002年,他仍在感叹“被无边的现实主义罩住了”。
邹静之的可贵在于他没有因此就放弃,而是一直在寻找能从这个罩子里钻出去的缝隙。他知道,“把戏演得像生活或把戏演得更像戏,是不同的观念,都有过杰出的作品,都出过大师”;他更知道,“多少年来现实主义是显学,没什么不好”;但是,“还有更多样的风格可以用啊!”他钻出这个罩子,觉得自己终于获得了自由,是借助了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一段老话:显而易见,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而他所得到的自由,就是不再按照“唯一法则”讲故事,他要在“讲故事的方法”上创新,却又不是为新而新,他的“新”,是适合所讲的故事。
他的第一次尝试是创作《我爱桃花》。这是一个十分陈腐而又极其无聊的故事。唐代,渔阳少年冯燕与牙将张婴之妻通奸。某夜,张婴醉归,张妻忙将冯燕藏在柜子(米缸)里。不想,张婴醉卧时压住了冯燕放在座椅上的巾帻。冯燕欲逃时,示意张妻将压在张婴身下的巾帻拿过来。张妻错以为冯燕是要张婴腰间的刀,遂悄然将那刀抽出,递给冯燕。冯燕原想拿起巾帻逃跑的,不想这女人竟拿了一把刀给自己。“我要巾帻你却给了我一把刀”,冯燕想,这样的女人心也忒毒了,遂一刀把女人砍了。
这样的故事还怎么往下演?更何况,这样的故事已经在人类历史舞台上演出几千年了。对大多数观众来说,这样一个故事是毫无悬念的。从历史上看,也很少有人会对故事的这样一个结局提出疑问。但是,戏演到这会儿,唐朝牙将张婴之妻,被她的相好一刀杀死之后,忽然又坐了起来,叫住了正要下场的冯燕的饰演者徐昂。她说:“你没有理由杀我。”剧作者这样处理,我是一惊一喜。惊的是,戏还可以这样演,出人意料,剑走偏锋,显示了戏剧舞台重构时空的新的可能性;喜的是,这样一来,也就等于给这个近于僵死的古老题材注入了清泉活水,洗刷了它的一身俗气。
戏的有趣之处就在这里。张妻这一起,似乎把故事打断了,实际上,展开了更加广阔的戏剧空间。在这里,剧作家把两位演员现实中的情人关系扯到戏剧结构中来,由此引出了对故事结局不同的设想和表达。接下来我们看到,故事的发展还有以下几种可能:一,冯燕没有杀张婴之妻,而是把张婴杀了;二,冯燕接过张妻递过来的刀,既没有杀张妻,也没有杀张婴,而是把自己杀了;三,冯燕接过张妻递过来的刀,既没有杀张妻,也没有杀张婴,更没有自杀,而是把刀重新插回刀鞘,平静地与张妻告别了。但也因此告别了他们的爱情。第二天,冯燕来找张妻要回他的话本,张妻说,插回鞘里的刀,比拔出来的刀更有杀伤力。
这几段叙事似乎给人一种重复之感,但绝不是简单的重复,每次重复都深化了对人性的认识,由此可以想见剧作家的用心,其实是对人性多种可能性的不断质询。而且,从戏剧的舞台呈现来说,这种停顿,犹如布莱希特的“间离”,通过演员与角色之间的跳进跳出,在演员、角色、观众三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关系,其效果不仅大大拓展了该剧的表现空间,也把观众从被动的欣赏者,变成了主动的观察者、思考者。这种表现方式和手段对于坚持在舞台上还原生活、制造幻觉的人们来说,也许是不大容易理解的,他们不能允许演员在舞台上“出戏”,因为按照斯坦尼体系的要求,演员是要死在角色身上的,演员与角色之间要“连一根针也放不下”,真正的零距离融合。但是,在中国传统戏剧表演中,《我爱桃花》中的表现方式和手段却是司空见惯的,就像评弹艺人的表演一样,忽而进入角色,忽而跳出角色,随时以艺人身份发表一些评语、感想,忽进忽出,若即若离,颇有助于剧情的进展、人物内心的刻划、作者主观意图的表达,等等。布莱希特总结了这种技巧,他称为“引文”,即让演员引证角色的话,来制造一种特殊的效果,比如张妻坐起之后与冯燕的对话,大约就是他想要得到的效果。
这种探索和实验很久以来常常被人指责为形式主义,其实,这与忙着在舞台上炫耀时尚装置的做法完全不同,在这里,形式与内容是不可分的,是融为一体的,形式即为内容。即以《我爱桃花》为例,表现方式的变化服从于该剧对时间与空间的重新处理,忽而是剧中的特定情境,唐朝牙将张婴之妻的卧房,忽而是现实生活中排演戏剧的舞台。这种做法显然吸收了戏曲的时空观念以及曲艺说唱的叙述手段,而一部戏如何实现与观众的沟通、交流,则主要取决于时间与空间的表达方式与叙述方式。
再以《操场》为例。邹静之说,《操场》是他的“自我批判”。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操场》里所有的人都是我,《操场》里所有的事我都干过。唯一不一样的是,我有痛苦,这痛苦代表着一种光亮。知识分子最伟大的精神就是自我批判,而中国知识分子不爱自省,都以为自己是真理的代言人,你看《百家讲坛》上那些唾沫横飞的学者明星!我们这个时代太缺乏痛苦了。”
与这种自省式的写作相适应,他在《操场》中没有直接讲故事,而是把故事包含在一个人的沉思中,包含在他的自言自语中。这个人就是迟教授,该剧就是从迟教授的大段独白开始的。这不仅考验演员的表演能力,也在考验观众的耐心和接受能力。在长达数十分钟的自我表白中,除了拖鞋和地板摩擦、偶尔会发出鸟叫的声音让迟教授感到焦虑不安外,剧作还穿插了三个想象中的片段,有三个人物先后出场,分别和他有一番交流和对话。第一个出场的是他的昨天,或曰童年,面对自己的昨天,他还是肯定今天,他说:“我活下来了,我一生最大的成功,就是当下!现在!我还活着!或者说你还活着。”但是他很清楚,他为成长付出了什么代价,童年的单纯和理想,都丢失了,他的童年甚至不认他了,这让他焦虑和苦恼。第二个出场的人物是迟教授的妻子,他们现在的关系有一点微妙,做妻子的,对丈夫不甚满意,她说:“活出个新鲜来,让我看看!”如何新鲜?她没有明说,但她在公交车上骂那个臭男人,“没本事挣钱,有本事想歪主意”,其中的含义迟教授心领神会,所以他说:“你骂得对。”他感受到其间的压力。妻子要求于他的,正是他做不到,或不想做的。这时,第三个人物出场了,她是迟教授的学生。由于她和迟教授的关系被其他老师想象为暧昧关系,她的论文便没有被通过。她责怪她的老师,甚至希望像晴雯要求贾宝玉那样,要求老师和她一起“让那些流言得逞”,她说:“我们就做一次吧……抗议性地做一次。”但迟教授以“我有准则”表示了拒绝。女研究生则愤慨地指责老师:“你快变成一个思想的意淫者了!”“你的孤独一钱不值。”
迟教授是个全新的舞台形象。这个形象在以前知识分子倒霉的时代或兴高采烈的时代都不可能有,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只有这个时代,才会有知识分子的迷失或迷茫,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左右为难,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或是怎样做,更不清楚自己的坚持是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邹静之敏锐地抓住了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症候,塑造了迟教授这样一个人物。对于生活,他有一种厌倦感,他感到了孤独,感到了痛苦,但他还想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他在努力地思索,但他的思索又是无力的,几乎不能抵达真理的彼岸。因为,对待真理和知识的相对主义态度的泛滥,已经使得这个彼岸变成了一片虚无。在这里,按照常规的表现方式,剧作家可能会陷入某种困境。因为,一个人的内心活动只能通过一定的戏剧动作才能得到表现,即使是话剧,也不能从头至尾只有一个人的“独白”(除非是独角戏)。他需要对手,哪怕这个对手是他想象中的另一个自我。而这个对手必须出现在舞台上,这又是“还原现实生活”所不允许的,因为现实生活中没有这个人物,他只存在于剧作家的想象中。
但是,邹静之却让迟教授的童年出现在舞台上。应当说,这在戏曲中并非难事,但要让话剧舞台接受,剧作者对于戏剧观念就不能不有所改变。很重要的一点是承认戏剧的假定性,也就是说,舞台或剧场是“由艺术家所虚构并由观众的想象力加以完成的一个非现实的世界,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去展示原则上无限的空间和时间,过去、现在与将来,人世、天堂与地狱,现实、幻想与思考都可以呈现在观众面前,这就是戏剧的魅力。戏剧家没有理由捆住自己的手脚,只限于在舞台上吃力不讨好地去模拟一个弄得苍白、贫乏的现实环境。”邹静之在《操场》中为此做了许多尝试,他不仅让迟教授与自己的童年对话,而且通过光的作用,在不转场换台的情况下,将操场变成了自家的居室,迟教授也从操场转移到自家的柜子里,他的妻子随之出现,二人开始对话。这中间迟教授提到了三天前妻子在公交车与乘客的争吵,舞台的另一侧马上出现一排模拟公交车乘客的人,随后便上演了这样一幕:急刹车,迟妻后边那个男人借势用下身顶了迟妻的屁股,迟妻回手就给了那个男人一个耳光。
女研究生和参加答辩的各位评委老师,也是召之即来,这在常规的戏剧观中也许被认为荒唐,但在解放了的戏剧观中却是可以接受的。这时,剧作家又让角色回到了舞台的现实情境中,一切都是自然而然。迟教授在结束了冗长的内心独白之后,又成了现实的一部分。在这里,剧作家写出了迟教授这个人在现实中的无奈和无力感。他一直在思索,可是,他的思索和现实没有关系。崔傻子让他看一下黑板后边的那个死人,他借口和他无关,让他打110报警。他说:“我不上网,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不听收音机,我不想知道的事越来越多……我恨不得瞎了,我自己的事都管不了……你还让我去看不相干的死人!”尽管他用“我的痛苦在这些之上”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是,他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冷漠和自恋,还是活生生地揭示了当下知识分子对其社会责任和人道主义立场的放弃和逃避。崔傻子凭着一个善良人的直觉,立刻就看穿了迟教授这个人,他说:“那你睡吧,一个根本睡不着而假装着要睡觉的人,……假装痛苦像个学者看见死人就闭眼睛的人,你睡吧!”这里所表现的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对于知识分子的普遍失望。知识分子应该自我反省,但这不应该成为拒绝现实关怀的理由,即使你拥有“更高质量的痛苦”也不行。邹静之写出这一笔,既深刻又不容易。这种直面现实、剖析自身的勇气和胆识是令人钦佩的。同时,他在戏剧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探索精神,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在打破“舞台还原现实生活”的迷信这条路上,他不是一个先行者,也不是一个终结者,他只是行走在这条路,并留下了自己坚实的脚印。
邹静之的创作实践昭示我们,戏剧观的解放仍是当下戏剧创作不能不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尽管这个问题老而旧,却始终未能得到很好解决,时时制约着当下戏剧的发展。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探讨和实践,也许会提供一个很好的契机和切入点,帮助当下戏剧创作走出困境,甚至影响中国戏剧的未来。
注释:
[1]张余编:《余上沅研究专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