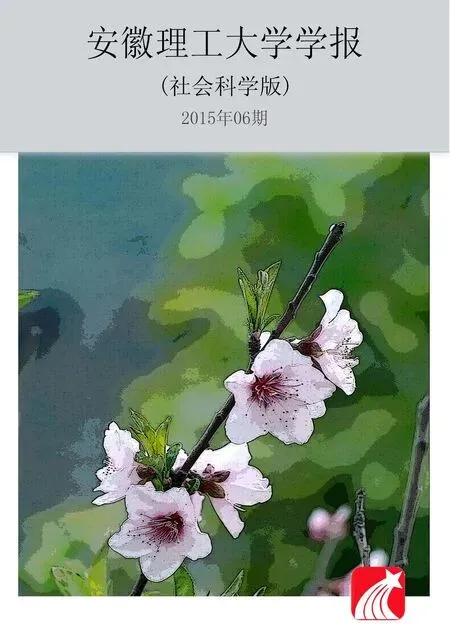“哑铃现象”与“非线性”人口增长解读
廖海亚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成都 610074)
“哑铃现象”与“非线性”人口增长解读
廖海亚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成都 610074)
微观上,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与家庭收入水平有关,这种关系使得现实生育结构宏观上呈现出“哑铃现象”,计划生育政策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宏观上,人口自然增长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关,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处于高位徘徊,在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与经济增长成反比,在高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则体现为达到一定低位时出现分化。微观人口经济学理论对上述现象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哑铃现象”具有负面影响,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人口增长的作用因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递减。适度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努力缩小贫富差距,大力培植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人口发展步入良性循环的必由之路。
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哑铃现象;微观人口经济学;孩子质量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这种关系微观上体现为家庭生育孩子数量与家庭收入水平的关系,宏观上体现为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目前相关研究偏重于探讨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探讨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影响的不多,部分学者甚至认为经济增长对人口增长没有影响,如胡鞍钢和邹平认为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负,但是其预设前提却认为此影响是单向的[1]。同时,对家庭生育孩子数量与家庭收入水平的关系的相关研究也有限。
随着研究的深入,家庭生育孩子数量以及人口增长率受家庭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得到了学界认同,但是相关研究对这种影响呈现出何种相关关系却存在争议。
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增长对人口增长有负相关影响,如杨菊华认为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水平与经济发达程度相关,根据生育意愿来衡量,发达国家实际生育水平偏低,发展中国家实际生育水平偏高[2];梁强、王文杰、徐祎琪认为经济发展越快,则人口增长越慢[3];周长洪通过实证量化分析得出:经济社会发展会促使人口生育率下降[4];王良健、梁旷、彭郁根据2 357个县的“六普”数据分析得出:经济越发达、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离婚率越高,县域总和生育率则越低[5]。这些研究通过经济增长对生育率的负相关影响揭示了经济增长对人口增长的负相关影响。部分学者则持相异观点,如张依娜、刘建波、王桂新认为生育率与家庭收入并不总是呈反向关系,而是呈扁平U型曲线[6];侯佳伟、黄四林、辛自强认为生育意愿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下降,但下降到一定程度后会保持稳定[7];彭浩然、孟醒的研究结论指出:城市经济发展会刺激人口出生率的提升,农村则相反[8]。
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以及人口增长率与家庭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之间究竟何种关系,关涉到对人口增长规律的认识,厘清这种关系并对之做出科学的解读,有利于科学的认识现实人口发展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为相关决策提供理论基础。
微观人口经济学从理论上对家庭的生育数量选择进行了解读,揭示了家庭孩子数量和其收入水平的关系,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揭示了宏观上人口自然增长率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哈佛的莱宾斯坦(Harvey Leibenstein)创立了微观人口经济学。莱宾斯坦根据微观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提出了以“成本——效用”作为分析基础的“边际孩子选择理论”,指出除了维持温饱的贫困家庭和极少数富裕家庭,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需求随家庭收入的提升而下降;20世纪6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贝克尔(Garys Becker)把“消费者选择理论”引入家庭,提出了“孩子替代理论模型”与“净成本”的概念,指出面临孩子数量和质量的选择时,父母的偏向总是指向孩子质量;南加州大学的伊斯特林(R.Easterlin)对莱宾斯坦和贝克尔的分析方式提出了质疑,认为应对社会因素给与重视,基于“市场决策理论”,他提出了“孩子供需理论”,认为现代化诸多因素导致了家庭对孩子的需求降低。上述理论构成了微观人口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根据微观人口经济学理论,家庭收入水平与家庭生育孩子数量有密切关系,经济增长对人口增长的影响的表现形式也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现实也证实了这种关系。
一、中国人口生育现实中的“哑铃现象”及其解读
所谓“哑铃现象”,是指中国现实生育中出现的诸多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农村尤甚)生育率偏高,广大中等收入家庭(城市尤甚)生育率偏低,由此富裕家庭、贫困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的生育状况在宏观上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现象,形如哑铃。
由于缺乏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生育率统计的基础数据,“哑铃现象”更多的是基于观察而得的判断。但是,从已有的相关数据上,我们仍然可以窥探出“哑铃现象”的影子。
根据“六普”人口数据:中国人口出生率城市为26.41‰,镇为31.48‰,乡村为39.04‰;按受教育程度分,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未上过学的为2.54个,小学为2.09个,初中为1.27个,高中为0.72个,大专为0.56个,本科为0.41个,研究生为0.37个;按职业分,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为1.06个,专业技术人员为0.83个,办事及相关人员为0.78个,商业、服务人员为1.08个,大农业人员为1.80个,生产、运输等人员为1.12个,其他人员1.24个。
由于收入水平总体上城市大于镇,镇大于乡村,而且对于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的关系,教育经济学的一般看法认为教育水平对经济收入有促进作用[9],我国劳动力收入与其受教育程度相关性逐步变强[10]。 基于此,从“六普”数据可以看出:总体上,人口出生率随收入水平提高而递减,但是进一步细分,则显现出差异;平均活产子女数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及相关人员最低,大农业人员最高,剩余的人员居中。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大农业人员整体上收入水平最低,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及相关人员收入水平比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低,比商业中的部分人员低,却高于大部分生产、运输人员和其他人员,整体上处于中间水平。这表明:处于最低收入水平人员平均活产子女数最高,处于中间收入水平人员平均活产子女数最低,其余收入人员的平均活产子女数居中,考虑到高收入人员几乎位于其余收入人员中,逻辑上高收入人员拉高这部分人员平均活产子女数的可能较大。
下面,我们根据相关省市数据进一步分析。

表1 主要省市总和生育率与居民收入情况(单位:‰,元)
说明:总和生育率为“六普”数据,居民收入为2010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基于比较的需要,本表选取了中国经济最发达、居中和最不发达的几个省市的数据。
根据表1:除北京、上海外,其他地方城市、镇和乡村的总和生育率呈迅速递增趋势,(“六普”数据中的全国数据与此基本一致,限于篇幅,此处只做代表性的选择)按其他省市的规律,北京、上海的乡村总和生育率应远远高于城市总和生育率,但是北京、上海城市、镇和乡村的总和生育率却差异不太明显。可能的解释是其镇和乡村收入水平已经接近其他省市城市收入水平,不符合贫困家庭多生的逻辑,而其城市富裕家庭较多(中国富裕家庭最集中的城市),又整体上拉升了其城市生育水平。
另外,根据对上海闵行区的调查:年收入5--10万较高收入者,意愿生育二孩的比例46.5%,而年收入10万以上的高收入者,意愿生育二孩比例86.7%[11]。
上述现象基本符合“哑铃现象”的逻辑。当然,“哑铃现象”是一种宏观现象,并不表示个体的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就必然要多生孩子。
微观人口经济学对家庭生育选择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述,揭示了家庭经济状况和孩子数量的关系,从理论上解释了“哑铃现象”的根源。根据微观人口经济学理论,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选择与家庭经济状况具有密切的关系,在选择的时候其主要的考虑因素是孩子的“净成本”。
根据孩子“净成本”概念,其计算方式为:[抚养孩子的直接成本(经济支出)+间接成本(时间成本,通过影子价格换算成经济支出)]-[孩子带来的预期直接收入(成为劳动力后为家庭带来的收入)+间接收入(孩子承担的养老任务折算成的收益)]。从经济上考虑,“净成本”为正会限制家庭多生孩子,“净成本”为负会激励家庭多生孩子。
根据经济状况,家庭大致可以分成3类:低收入类、中等收入类和高收入类。前面已经提及整体上家庭收入和家长受教育水平成正比,而根据微观人口经济学理论,家庭生活富裕后家长首先关注的是孩子质量。一般而言,“收入水平高的家庭,其子女获得的教育数量多,同时获得的教育质量较好。”[12]所以,整体上,家庭收入水平与家长文化水平、孩子的抚养质量皆成正比。
从总体上看,家长文化水平越高,越看重孩子抚养质量(特别是教育质量)。低收入类家庭家长文化程度相对较低,中等收入类和高收入类家庭家长文化一般较高。低收入类家庭面临的最大现实问题是经济问题,在生活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家长对孩子的抚养质量重视有限,家庭投入孩子抚养的费用也必然有限。经济条件和思想观念决定了低收入类家庭很难为孩子提供高质量的抚养条件。很多孩子甚至处于“放养”状态,抚养成本较低。由于抚养条件有限,孩子接受教育的条件也有限,使得孩子较早进入社会,成为劳动力。这样,孩子依靠劳动为家庭提供收入的时间相对较长。同时,“未富先老”是中国社会的现实,养老保障体制目前还无法做到应保尽保,农村家庭的养老问题是中国目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内的重要问题,“养儿靠儿”仍然是一种现实选择。孩子“净成本”自然为负,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会激励家庭多生孩子。当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不能并重的时候,自然倾向于用数量替换质量。
中等收入类家庭与高收入类家庭家长大多具有较高文化,比较看重孩子的抚养质量,事实上孩子的抚养质量也较高,孩子的受教育年限长,父母付出的直接成本和时间成本都较高,孩子步入社会较晚,通过劳动为家庭带来的收入有限。故,孩子的抚养成本较高。由于这两类家庭家长大多具有正式工作,收入条件不错,并不期望从孩子身上获取多少经济利益,且家长一般都有社会保障,养老问题基本不会依靠孩子,不存在“养儿防老”,自然,孩子“净成本”为正。但是中等收入类家庭与高收入类家庭并不完全相同。对于高收入类家庭来说,尽管孩子“净成本”为正,但是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优越,即便给与优厚的抚养条件,增加孩子的数量并不会给家庭带来经济负担,从理论上讲,孩子数量和抚养质量并不冲突,是否生育孩子只与家庭对孩子的喜好有关。与高收入类家庭比,中等收入类家庭毕竟经济条件有限,难以同时给与多个孩子较高的抚养质量。在不降低孩子抚养质量的情况下,增加孩子数量会导致家庭生活质量下滑。而大多数中等收入类家庭家长既不愿意降低孩子抚养质量,也不愿意降低家庭生活质量,唯一的选择就是降低孩子的数量。所以,当孩子的数量和质量发生冲突的时候,中等收入类家庭一般选择用质量替换数量。
根据中国现实,抚养孩子不成为家庭经济负担的高收入家庭和对孩子进行“放养”的低收入家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而孩子数量对家庭生活质量产生重要影响的中等收入家庭所占比例相对较大。于是,现实生育中就出现了整体生育结构“两头高中间低”,且中间部分占比偏重的现象,即“哑铃现象”。从“哑铃现象”来看,家庭收入状况并非和家庭孩子数量成反比。
另外,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种强制性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对“哑铃现象”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根据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九类特殊家庭*九类家庭为:农村头胎为女的家庭,归国华侨、港澳同胞与涉外家庭,农村男子入赘家庭,渔民矿工等特殊职业家庭,伤残军人家庭,头胎残疾家庭,再婚家庭,少数民族家庭,单独或双独家庭。可以生育二胎,其余家庭生育二胎则会受到惩罚。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惩罚是缴纳社会抚养费与行政处分,对非国家工作人员的惩罚是缴纳社会抚养费与纪律处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41、42条对此做了明确规定。。
现实中,对“超生”的行政处分一般是开除,而且严格执行。这使得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一旦“超生”就将失去工作,基本上杜绝了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超生”;纪律处分则相对宽松,基本不存在开除的情况,对企业人员“超生”的约束事实上主要是靠征收社会抚养费。大多数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基本上是靠工资生活,这部分人员主流属于中等收入家庭;企业人员中对社会抚养费不在乎的只能是高收入家庭,广大企业中低收入家庭人员虽然不会如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一样面临开除,但是相对较高的社会抚养费也限制了他们生育二胎的动力。
从管理角度看,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人员有工作单位,利于控制,对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相对容易,也较为规范。没有固定工作单位的人员则存在一定的管理盲区,不好控制,对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相对困难,这部分人员中,农村人员占了绝大部分。同时,农村的社会抚养费相对较低,很多家庭能够承受。另外,农村逃避罚款(包括缴纳社会抚养费和超生罚款),暂时不考虑孩子上户问题,想方设法生下孩子,使“超生”成为既成事实的家庭不在少数,使得农村事实上的“超生”现象比城市严重得多。在农村“超生”人群中,地处偏远的穷困家庭尤其难以管理,而这样的家庭大多有希望通过多生孩子改变家庭命运的想法,事实上造成了越穷越生的现象。就是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主要限制的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和企业中低收入人员,对无固定单位的人员限制有限,对偏远地区农村贫困家庭的限制更是有限。
受限制的人群的低生育率构成了“哑铃手柄”,而受限制有限的人群中的高收入人群和农村低收入人群的高生育率构成了“哑铃两端”。选择“超生”自然考虑更多的是经济承受力(逃避经济处罚也会面临其他压力),这仍然符合微观人口经济学的“成本——效用理论”。但是“超生”将面临罚款仍然带给了潜在“超生”者较大的经济压力,所以,虽然理论上经济因素会自发的促成生育中的“哑铃现象”,但是在中国现阶段,计划生育政策对“哑铃现象”的产生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不容忽视。
二、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关系及其解读
宏观上,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究竟是线性负相关关系还是非线性关系呢?我们用世界不同类型地区或国家的相关数据对此进行分析(见图1)。
根据图1:整体上,经济发展程度越高,人口增长率越低。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处于逐步下降态势,但是较发达地区增长率明显低于欠发达地区,且近10几年人口增长率处于低水平阶段的平稳状态,而欠发达地区则处于逐步下降的趋势,不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处于高水平的起伏状态。
下面,我们用世界主要人口大国的数据做进一步分析。根据综合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状况,我们把相关国家大致分成三类*A类主要为发达国家,基于苏联曾为发达国家且俄罗斯人口增长基本稳定的因素,把俄罗斯放入了A类;B类主要为发展中国家,但不同国家的发展程度有较大差别;C类主要为不发达国家,基于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综合发展现实,仍将其纳入进来。。

表2 世界主要国家平均人口增长率的变化(A)(单位:百分比)
数据来源: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UN,DESA.
根据表2:整体上,人口增长率低的国家呈现出先小幅增长然后小幅波动的状况;人口增长率较高的国家则呈现出人口增长率逐步下降然后小幅波动的情形。在波动方面,不同国家波动趋势不同。澳大利亚维持着较高人口增长率和移民因素有关。

表3 世界主要国家平均人口增长率的变化(B)(单位:百分比)
数据来源: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UN,DESA.
根据表3:整体上,相关国家大致在1985年以前(不同国家时间段有一定差别,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不同步有关,中国为1975年前,和计划生育政策相关),人口增长率处于高水平波动。大部分国家1970年代和1980年代都经历了人口增长高峰(中国为1975年前,与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然后增长率总体开始下降。但是,不同国家下降幅度有别,增长率差别较大,埃及、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等仍然维持较高水平增长态势(和其历史与宗教等原因有关),中国则处于中低增长状况,这与各国发展不同步有关。

表4 世界主要国家平均人口增长率的变化(C)(单位:百分比)
数据来源: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UN,DESA.
根据表4:相关国家人口增长率呈现出先快速增长然后高位波动的趋势。孟加拉国1970-1975年的人口低增长率与其国家刚独立有关,1995年后人口增长率迅速下降与其人口政策有关。
综合图1和表2-4,可以大致得出:宏观人口增长规律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不同的阶段呈现出来的增长率趋势有别;在经济处于极低水平发展阶段的时候,经济增长往往会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升高,当经济发展越过极低水平阶段进入低水平阶段,人口自然增长率会处于高位徘徊;当经济摆脱低水平发展阶段以后,经济增长一般会带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但是,当经济发展达到高水平阶段以后,经济发展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关系则呈现出复杂化,部分国家维持大致均衡,部分国家适当起伏,部分国家缓慢下降。所以,人口自然增长率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线性的负相关关系只是经济发展处于某个阶段的现象,而非两者之间的一般规律。
由于各国发展阶段的差异和发展不平衡规律,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分别处在极低水平、低水平、中等水平和高水平的不同发展阶段,因而所呈现出的人口增长率趋势因其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除美国外,其他发达国家经济都受到重创,相继进入经济恢复时期,各国步入发达阶段的步伐有一定差别,但是,步入发达阶段后,人口增长率都比较低,表2的人口增长率和这个趋势一致。发展中国家的起点低于发达国家,其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水平和较高水平阶段的步伐自然慢了一步,所以,表3中的大多数国家直到1985年后人口下降的趋势才比较明显。而最不发达国家到目前为止大致经历了极低阶段和低水平阶段,尚未达到中等水平阶段,所以,其人口增长率先快速上升而后高位徘徊。
从微观人口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的国家,其人口大多数应为低收入人口,低收入人口家庭的孩子“净成本”为负,家长更关注孩子数量,大量低收入人口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重视必然会导致该国整体人口增长率处于高位;处于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该国人口中的低收入人口比例将少于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的国家相应的人口比例,该国低收入人口的一部分必然已经上升到了中等收入人口行列,中等收入人口家庭的孩子“净成本”为正,家长更关注孩子的质量,相当部分的中等收入人口家庭对孩子数量的减少自然导致该国整体人口增长率降低,由于仍有大量低收入家庭的人口,该国的人口增长率仍将维持在一定水平;处于高水平发展阶段的国家,相对于低水平和中等水平阶段的国家而言,该国人口中低收入人口比例相对最小,而中等收入人口占比相对最高,所以,该国人口增长会随低收入人口进一步下降和中等收入人口进一步上升而继续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但是,高收入国家之间因其贫富差异结构不同,低收入和高收入人口占比有一定差异,这导致了不同国家人口增长率在低水平阶段的不同变化。图1和表2-4反映的趋势与此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总体人口增长状况与这个国家的不同阶层的人口占比状况有比较明显的关系。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微观上,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和家庭收入水平之间存在一定关系,从经济上看,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都不会刻意限制生育孩子的数量,而中等收入家庭却必须在孩子数量和孩子质量之间做排他性选择,这种选择与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相迎合,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作用更加彰显,中国生育现实中 “哑铃现象”的生育结构因之呈现。
宏观上,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之间并不呈负相关的线性关系,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与经济增长成反比,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和高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则呈现出不同趋势,前者是高位徘徊,后者是在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一定标准的时候出现分化。
“哑铃现象”可以归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增长特定阶段的自然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首先是不同收入阶层的人口增长极度不平衡,严重的影响了整体人口素质的提升,同时带来了系列的社会问题。对于“超生”家庭而言,富裕家庭虽然有给与子女良好教育的条件,但是现实中容易出重视物质条件的给予而忽视精神领域的教化,“富二代现象”屡见不鲜,对青少年的教育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贫困家庭则大多无力给予子女良好教育条件或者忽视子女的教育质量,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欠缺带来的竞争压力一定程度上使得部分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孩子容易对社会产生逆反情绪,影藏着不稳定因素。中等收入家庭大多把希望寄托在孩子的教育上,孩子受教育质量整体较高,但是这部分人员的生育率却偏低。其次,事实上主要限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公平性备受社会质疑,而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出现的寻租现象也使该政策颇受诟病。
从宏观上看,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具有不同关系,通过经济发展来影响人口增长具有合理性,但是前提是需要确定经济发展的阶段和这个阶段人口增长规律是否和人口发展规划一致。由此,我国的人口政策是否需要调整以及如何调整,方向就已经明确。
在经济发展的低水平阶段,经济因素对人口增长的限制作用有限,计划生育政策在此阶段对于限制人口增长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当经济发展越过低水平阶段后,经济因素对人口增长的负面影响逐步增强,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增长的限制作用逐步降低,而其负面作用却逐步呈显,事实上成了限制人口素质提升和生育权不公平问题的渊薮。我国已经迈过了经济发展低水平阶段,但是没有达到经济发展的高水平阶段,在这样的阶段,经济增长会带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即使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因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下降将是趋势(当然,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后一段时期内会有一定反弹)。所以,降低出生率和提高人口素质最好的方式是培植较为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
由此,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适度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努力缩小贫富差距,大力培植中等收入群体,才是我国人口发展步入良性循环的必由之路。
[1] 胡鞍钢,邹平.中国发展报告: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距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2] 杨菊华.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发达国家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述评及对中国的启示[J].学海,2008(1):27-37.
[3] 梁强,王文杰,徐祎琪.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0(3):32-35.
[4] 周长洪.经济社会发展与生育率变动关系的量化分析[J].人口研究,2015(2):40-47.
[5] 王良健,梁旷,彭郁.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县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人口学刊,2015,37(3):16-25.
[6] 张依娜,刘建波,王桂新.生育率的经济学分析[J].西北人口,2007(3):69-74.
[7] 侯佳伟,黄四林,辛自强.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1980—2011[J].中国社会科学,2014(4):78-80.
[8] 彭浩然,孟醒.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与经济发展[J].统计研究,2014(9):40-45.
[9] 柯佑祥.教育经济学[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29-30.
[10] 王云多.劳动力教育程度对个人收入分配变动趋势的影响[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7(4):93-96.
[11] 陈钟翰,吴瑞君.城市较高收入群体生育意愿偏高的现象及其理论解释:基于上海的调查[J].西北人口,2009(6):54-57,61.
[12] 王少瑾.收入水平与教育获得:—一个述评[J].江淮论坛,2008(5):85-89.
[责任编辑:吴晓红]
Analysis of the “dumbbell phenomenon”and “non linear”growth rate of population
LIAO Hai-y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of Sichuan, Chengdu 610074, China)
On a micro-level, the number of children born in a family is related to the income of the family. This relation results in the “dumbbell phenomenon” in the fertility and birth structure on a macro-level in reality, in which the policy of family planning plays a decisive role. On a macro-level, the natural growth rate of population is related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pha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conomically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natural growth rate of population is hovering high; in economically medium-developed countries, it i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while in economically well developed countries, it may demonstrate irregularities once it reaches a certain low position. “Dumbbell phenomenon” may exert a negative influence, and the role played by the policy of family planning may become increasingly tiny as the phase of the economic growth shifts. Reasonable adjustment to the policy of family planning, shortening the gap between 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 and fostering the group with medium income through painstaking efforts are a necessary step we must take to put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in our country to a sound circle.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economic growth; dumbbell phenomenon; micro population economics; the quality of children
2015-09-16
廖海亚(1973-),男,四川达州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博士,主要研究人口经济学。
C924.1
A
1672-1101(2015)06-0070-08
-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区域经济发展中高校规模效益与路径分析
- 2005-2015“关于年科技期刊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