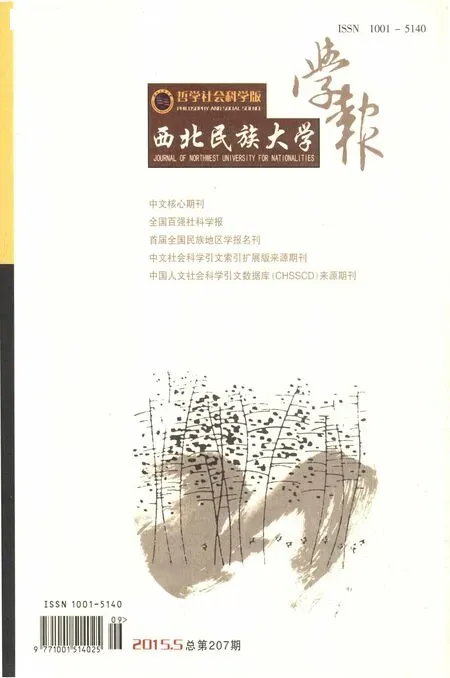回族游学出现的原因与作用探析
马晓军
(河南大学 民族研究所,河南 开封475001)
游学是世界各地较为常见的一种学习方式,从古至今,中国游学现象也长盛不衰。“游学”在《辞海》中有两层释义:“远赴异地,从师求学;以所学游说诸侯,求取官职的人。”[1]《现代汉语词典》中“游学”被注解为:“离开本乡到外地或外国求学。”[2]本文“游学”指离开本乡去求学或者进行学术交流,即“求学之游”或者“授学之游”,宗教游学就是宗教文化的学习和交流活动。
一、游学的出现
游学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春秋时期,游学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经过2000余年而历久弥新。游学具有普遍性,在宗教领域也屡见不鲜,以“求法”、“求经”形式出现的游学成为宗教发展的助推剂,使各种外来宗教以其精华深植中国社会,推动中国文化吐故纳新、升级换代。
(一)游学的悠久历史
游学作为获取知识的一个途径很早就出现在世界各地。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游学活动的一个重要阶段,当时游学之士受到各诸侯国的优待,“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粮,财币足之,使出周游于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3]游学有“授学之游”,“楚惠王五十年,墨子至郑,献书惠王……尝游弟子公尚过于越,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墨子于鲁……后又游楚。尝南游使于卫……老而至齐[4]。游学又有“求学之游”。“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5]游学还有“仕宦之游”,以其学识求得官职,苏秦最初宦游秦国失利的遭遇可以证明宦游的重要,至家“妻不下紝,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然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6]苏秦随后通过头悬梁锥刺股的方式发愤苦读,学问大增,再次通过游学入仕为高官显贵,以至同时挂六国相印显赫一时,终于实现了游学的目标。此后从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以至宋元明清,游学作为一种求知方式对中国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二)宗教游学
宗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性宗教在传播过程中经常出现宗教信徒以“求法”、“求经”的方式追求信仰真谛的现象。《圣经》记载有东方五学士不远万里前去祝贺耶稣基督诞生的故事,他们不仅仅表达祝贺之意,更重要的是想学习、了解当地的宗教文化。
佛教自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后,随着传播范围扩大和信徒人数增加,已有的佛经不但数量少不敷使用,而且由于译经水平低下导致谬误百出。为了求取、传授真经,一批批中国僧人和印度僧人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去印度学经或者来到中国传授佛教经典。前去印度学经的中国僧人魏晋时期有朱士行、法显等人,隋唐时期有玄奘、义净等人。法显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经西北丝绸之路到达印度,遍历印度半岛各国、游学各类佛教经典达10年之久,公元412年从海路携带佛教经典经印度洋、南海返回中国。义净在公元671年从广州经海路前往印度,先后在印度半岛和东南亚地区游历30余国学习佛教经典,历经24年后于公元695回到洛阳。与此同时,大量印度僧人也以游学传经的方式来到中国,与中国高僧切磋佛教理论,在各地宣扬佛教。东汉时有摄摩腾和竺法兰等人,魏晋南北朝时期有鸠摩罗什、竺法度、达摩等人,隋唐时期有达摩笈多、地婆诃罗等数十人。由于隋唐时期佛教盛行,游学成为宗教界一种普遍现象,出现大量游学僧人,即游学行脚[7]。通过中印游学、求法、传法僧人的共同努力,佛教逐渐扎根中土、开花结果。
二、回族游学出现的原因
游学类型多种多样,朝觐游学是回族游学的主要方式之一[8]。回族游学的出现既有伊斯兰教提倡尊重知识、追求学问的原因,也与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形成的游学传统有关,还须归因于探索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推动力所致。
(一)伊斯兰教对追求知识行为的大力倡导
公元7世纪中期,阿拉伯帝国建立,阿拉伯人创造了灿烂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阿拉伯穆斯林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这在一定程度上缘于伊斯兰教极力提倡对知识的追求、学者的尊敬。
《古兰经》多次强调给予知识和学者最高礼遇:“你说:‘有知识的与无知识的相等吗?惟有理智的人能觉悟。’”“真主将你们中的信道者升级,并将你们中有学问的人们提升若干级。”《圣训》赋予学者以较高地位,甚至与烈士相等。“踏上求学道路的人,真主已经使他踏上直达乐园的坦途。”(穆斯林传自艾布·胡莱赖);“学者的墨汁在末日将与烈士的鲜血相等”(艾布·代尔达义传述)。“两种人是值得羡慕的。一种人,安拉赐予他财富,而他则把自己的财富全用于正途;另一种人,安拉赐其学识,他以自己的学识进行判断,并把知识传授于他人”[9]。在《古兰经》和《圣训》的大力倡导下,穆斯林自觉地“在学习中寻求知识,在观察中获取知识,在旅行中寻求知识”[10],而游学就是伊斯兰教这种求知精神的实现方式之一。
(二)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游学传统
在高度重视追求知识的伊斯兰世界中,穆斯林把外出游学作为获取知识的一条重要途径,逐渐形成了游学传统。许多学者通过游学积累了知识,增加了学问,成为声名卓著的大师。
伊斯兰教逊尼派哈乃斐教法学派创始人艾布·哈尼法童年时就在清真寺学习《古兰经》和伊斯兰教知识,年龄稍长跟随父亲到各地经商。经商期间他坚持在各地清真寺学习知识,长期游学积累的知识使得艾布·哈尼法20岁时就能够在库法大清真寺设坛讲学,并逐渐在教法学领域独树一帜。但他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仍旧游学四方,寻师访道,先后55次远赴圣地麦加访师求教,27次前往学者云集的巴士拉等地游学求知。艾布·哈尼法在教法学界泰斗地位的最终奠定,与他积极游学、寻求新知有着直接关系[11]。圣训学泰斗布哈里也有同样的游学经历,他幼年时就能够背诵7万条圣训,15岁时前往麦加、麦地那等地寻访名师学习、研究圣训。此后,布哈里又去伊朗、伊拉克等众多国家游学,与各地圣训学者探讨、研究疑难问题。布哈里在16年间先后访问、求教了1 080位有名的学者,搜集了数十万条圣训,以此为基础编成了著名的《布哈里圣训实录》[12]。布哈里取得的这些成就与游学中不断增长的学识有直接联系。
不仅著名学者以游学的方式获取知识,普通学子也普遍以游学作为学习知识的途径。“阿拉伯学生真是‘求学者’,他们当中有多数人,离乡背井,负笈远游,备尝跋涉的辛苦,踏遍伊斯兰世界,足证他们是名实相符的”[13]。中世纪阿拉伯地区依托清真寺建立了很多类似于现代大学的著名教育中心,这里汇聚了众多的莘莘学子,他们从世界各地前来求学真知。直到今天,一些著名的伊斯兰高等教育机构依然利用古老的游学传统吸引着世界各地穆斯林求学,埃及的爱资哈尔大学[14]和马来西亚的国际伊斯兰大学[15]等就是典型代表。
(三)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现实需要
元末明初,中国境内由不同民族穆斯林组成的“回回人”以伊斯兰教为纽带逐渐形成回族。回族形成后基于对内对外交往的需要,逐渐以汉语汉文作为日常语言文字。语言文字的改变导致回族无法解读用阿拉伯、波斯文字撰写的宗教经典,对宗教教义不易理解。而当时明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海禁制度严厉,对外交往日渐萎缩,结果导致回族与国外穆斯林的宗教文化交流濒于断绝,回族知识分子逐日减少,精通伊斯兰教教义的阿訇日益缺乏。当时伊斯兰教传承已经陷入了“经学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16]的地步,回族面临着文化失传的危机,“倘有教门之家,尚存三分回回气象,如无教门子弟,纯变为汉教矣。”[17]回族急需统筹利用有限的宗教教学资源,而游学就成为提高宗教教学资源利用率和获取外部资源的一种可选途径。
1.游学出现的客观需求。为了摆脱回族文化传承和信仰危机困境,必须培养可以解读阿拉伯和波斯文经典、能够主持宗教活动的伊斯兰教职业人员,还需翻译一批回族能够阅读的汉文伊斯兰教经典,这是挖掘现有宗教资源的可行捷径,这样,经堂教育和“汉文译著”活动应时而生。而当时开展这两项活动的主体─经堂师生和回族学者不得不通过游学的方式来完成经堂教育和“汉文译著”活动,因为伊斯兰教职业人员和伊斯兰教经典严重不足,提高师资和经典利用率的唯一途径就是人员和经书交流。结果,不同地区宗教资源的交流自然推动了游学的发展。
回族散杂居分布也是游学出现的动力。回族以“大杂居、小聚居”的形式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他们在各地一般集中居住在一个区域,形成一个小型居住区─“坊”,在“坊”中修建清真寺。这样各地回族犹如汪洋大海中的一个个孤岛,很容易被淹没。为了延续回族文化,各坊回族除了加强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之外,更需要强化彼此之间的文化联系[18]。回族在本地接受的教育、获得的知识相对有限,如果希望更上一层楼,必须去其他寺坊游学。一些人甚至认为:“非游学不能大成”[19],不游学就不能成大器。另外,品行高深、学识渊博的阿訇、学者散布在全国各地,他们之间切磋学问、交流经验通常就以游学的方式来实现。许多回族后生想提高自己的学识,也只能以游学的方式投靠各地前辈求学。由此可知,回族“大分散、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客观上催生了游学。
2.游学的制度驱动力。伊斯兰教设置各类教职人员分工管理各项宗教事务,其中负责全面领导和掌理宗教事务的就是掌教,这种制度就是掌教制度[20]。回族伊斯兰教先后经历了卡迪掌教制、伊玛目掌教制、阿訇掌教制。在阿訇掌教制中,阿訇实行聘任制,聘期一般3-5年不等,聘任期满如果不被续聘,阿訇必须去其他寺坊应聘,这样就形成了阿訇“游坊制”[21]。在这种类似现代社会招聘人才时实行的双向选择机制下,平庸阿訇只能受聘于一些位置偏僻、待遇差的清真寺,甚至无处“开学”,处于失业状态。而优秀阿訇经常被实力雄厚、待遇优裕的清真寺抢聘。这在客观上激励阿訇必须从小加强学习,提高学识水平,将来才能避免被淘汰出局。而提高学识除了自学之外就是师从著名阿訇、学者,如此自然助长了游学─去异地拜师求学,甚至去国外拜师求学的风气。由此可见,阿訇的“游坊制”带动了游学的发展。
三、回族游学的作用
回族游学的发展,使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学派鱼贯而出、争奇斗艳;回族学者汉文译著佳作风起泉涌、名家辈出;伊斯兰教教派门宦如雨后春笋,扎根中土,对回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陈出新、开拓创新的作用。
(一)游学使经堂教育学派接踵而出、异彩纷呈
回族学子的游学使经堂教育异彩纷呈、人才济济,先后形成了陕西学派、山东学派、云南学派。这三大学派的创始人及代表人物能够兼采诸家之说,独创一家之言,这与他们长期游学积累的丰厚学识密切相关。
胡登洲首开经堂教育之先河,独创陕西学派。胡登洲幼习儒学,年龄稍长跟从本教高太师潜修波斯文、阿拉伯文、伊斯兰教经典。数十年寒窗苦读犹不满足,他在年过半百客寓都门期间又求教于国学名士,“崇延名师,谙习诗书。”[22]在此之前,胡登洲已经在“津渡”附近得遇“赫资勒圣人”的指点,后来又追随从麦加来的“进贡缠头叟”[23]。从胡登洲一生求学经历来看,游学是胡登洲学习、积累知识的主要方式,从这些老师学到了儒家和伊斯兰教两种文化。儒家文化主要来自于“国学名士某”,其他老师传授的是伊斯兰教知识[24]。胡登洲游学过程中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并重的学习态度,使他最终成为伊斯兰教经学大师。
山东学派创始人常志美7岁时学习儒家文化,11岁进入清真寺学经,数年后游学至南京著名经师马真吾门下,得其真传。后来常志美又前往河南郑州貂谷拜胡登洲再传弟子张少山为师游学数载,学业大增。在此期间幸遇异域经师缠头极料理与之切磋教理,深得其精髓[25]。常志美的弟子舍蕴善幼习儒学,稍长跟随军营杨师学习伊斯兰教经典,“不逾月读尊经数本,尽得其妙,能宣圣谕以劝大众,遂谓师曰:‘尊经之习止此乎?’曰:‘经学如海,通理方能究其他经也,非游学不能大成’。”[26]在老师的激励下,年近20岁时,他又投师于常志美门下深造多年。舍蕴善后来多次外出游学,在流寓陕西渭南时投身于胡登洲四传弟子马永安门下学习经典,经过长期游学求教,终成山东学派一代名师。
云南学派创始人马德新出身于经学世家,未及成年已经熟稔伊斯兰教经典。“壮游秦川,博览典籍”,青年时前往经堂教育中心陕西,求学于胡登洲四传弟子周良骏阿訇,钻研伊斯兰教[27]。马德新从陕西游学回到云南后,在教授伊斯兰教经典过程中深深感到“真传之未得,名师之罕遇”,于是在1841年近半百时以朝觐的方式出国游学。在八年游学期间,马德新“游历天方,旁搜博采,与天方宰臣、百官、学士、大夫,究天文杂家之学及天方各国礼乐制度、风土人情”[28]。他考察伊斯兰世界制度和文化,拜访众多的王公、学者,讲经论道,开展学术交流活动。马德新以出国游学的方式提高了学识,奠定了在宗教界的地位。
(二)游学使汉文译著佳作源源不竭、名家济济一堂
明朝中后期,伊斯兰教面临中国化的急迫问题,为了让汉族了解伊斯兰教,使伊斯兰教适应中国社会。回族学者四处游学,学习各种文化,结果出现了王岱舆、马注、刘智等学通“四教”(伊、儒、佛、道)的学者,他们通过汉文译著作品诠释伊斯兰教,为伊斯兰教中国化做出了贡献。
王岱舆的先祖是西域穆斯林,幼承家学,从小学习阿拉伯、波斯语言文字,年龄稍长外出师承胡登洲四传弟子马君实钻研伊斯兰教经典。他发奋读书,“始阅性理、史鉴之书,旁及百家诸子”[29],当时人赞誉“四教博通”。清朝顺治初年,王岱舆携家北上游学北京,在回族开设的学馆里讲经。讲经期间,他经常向儒、佛、道名士求教,并与之谈经论道,他的著作《希真正答》就是与各教人士辩论的真实记录。王岱舆的著作除了《希真正答》之外还有《正教真诠》《清真大学》。《正教真诠》是讲述伊斯兰教义的破天荒之作[30],《清真大学》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第一部名副其实的宗教哲学著作”[31]。
马注是元朝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第五子马速忽的十四世孙[32]。他幼年丧父,立志发愤苦读,成年后在家乡云南各地游学。公元1668年马注离开云南经贵州、湖北、河北等地游学北京,与京师阿訇、回族学者探讨伊斯兰教教义。公元1684年马注离开北京,取道山东,到达江苏、浙江。随后抵达安庆,后来又经河南开封至陕西西安,公元1687年离开西安到达四川阆中,次年经阆中返回云南。返家途中,马注在各地游学结交了大批学者,每每以《清真指南》书稿向人请教。“(余)愚昧不才……海内名师,或睹其书,或见其人,或闻其教,采天下之遗珠,一准于经书。”[33]当时伊斯兰教著名阿訇、学者,如山东李延龄,南京马之骥、刘三杰、袁妆琦,扬州古之珊,湖南皇甫经,陕西冯通宇、舍起云等人都是他在各地游学过程中结识的。马注是“中国回教中绝无仅有之人才”[34],著作《清真指南》影响很大,时人评价:“后尔而生者,非子不能成”[35]。
刘智出身于金陵伊斯兰教世家,从小就全面学习伊、儒、佛、道等各种文化,“于年十五而有志于学,八年膏晷,而儒者之经史子集及杂家之书阅遍。又六年读天方经。又三年阅释藏竟。又一年阅道藏竟,道藏无物也。继而阅西洋书一百三十七种,会通诸家而折衷于天方之学。”[36]为了开拓学术视野,刘智游学访师,足迹遍及山东、北京、河南、陕西、湖北、浙江、广东等地,增长了学识。“忆自初学以至于今四十余年……乃裹粮负笈,历齐鲁,走都门,就正朝绅先达;由襄楚入西秦,访求宿学遗经;过吴门,游武林,越会稽,抵粤东,考文问字,阅胡氏天禄阁藏书,得未曾有。”[37]刘智勤学好问,著述颇丰,刊刻作品约50卷,尤以《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最为著名,其中《天方典礼》被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存目中。刘智是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研究集大成者,“继马注之后将汉文译著活动推向高峰。”[38]
(三)游学使伊斯兰教教派门宦如雨后春笋、扎根中土
伊斯兰教职业人员通过朝觐游学或者向来华的国外传教人员求教,带回或者接受了各种新思想、新观点,他们把这些思想、观点与回族社会相结合,改革宗教习俗,创立了许多教派、门宦,使伊斯兰教真正扎根中国社会。西道堂创始人马启西幼年接受伊斯兰教启蒙教育,11岁进入私塾学习儒家文化,21岁考中秀才后不久放弃仕途之路重新钻研伊斯兰教教义,“更加精心地钻研了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等”[39],且博览诸子百家之书。为了增长学识,马启西两次计划朝觐游学,第一次因故未能启程。1905年第二次出发,“经兰州取道河西,披星戴月,经历霜寒,过嘉峪关、伊犁河、铁门峡、阿姆河,到达了撒马尔罕地区的白帽城。”[40]因中亚战乱受阻,暂居白帽城游学讲经,频频求教当地阿訇、学者,1908年带着三年的游学硕果返回。马启西还数次前往甘肃省张家川游学,与哲赫忍耶第八代沙沟教主马元章交往密切,与之宣教论道,颇为投契[41]。马启西秉承刘智“以儒诠经”学说,利用游学成果,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创建了伊斯兰教教派─西道堂。
马明心是哲赫忍耶门宦的创建者,他尚未出生父亲去世,幼年时母亲和祖父相继离世,跟随贫穷的叔父生活。马明心6岁开始在临夏清真寺学习经文,“学习认真,聪慧过人,成绩优良。”[42]公元1728年,马明心与叔父去麦加朝觐游学,历尽千辛万苦,次年抵达也门,随即进入也门本·载尼道堂学习乃格什板迪耶教团教理。由于勤学好问,深得老师器重。马明心认真研读各种经典,严格继承教团闭门静修的传统。“我遵令在小屋里坐静九个月。后来沙赫让我出去,把我送进一所尊贵的学堂,教给我许多必要的知识。学业成就后,沙赫又指示我坐静三个月。”[43]经过10余年游学的知识积累,公元1744年,马明心带着《古兰经》和一些伊斯兰教经典回国。随即开始在青海、甘肃等地传教,逐渐创建了一个组织严密、传播地域广、影响范围大的伊斯兰教门宦。
嘎德林耶门宦的分支大拱北门宦创始人祁静一自幼父母双亡,从小进入清真寺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同时兼学儒家文化。祁静一年少时就能讲经论道,受到众多阿訇赏识。公元1672年,穆罕默德第二十五世圣裔华哲阿法格·曼什胡勒·赫达耶通拉希从新疆抵达青海湟中,祁静一闻讯前往游学求教,可惜因故未得其传。公元1674年,穆罕默德第二十九世圣裔华哲·阿布杜董拉希到临夏传教,祁静一再次前去诚恳求教,终于被收为门徒,祁静一遵师命长期坚持独自静修,悉心研修嘎德林耶隐修学理[44]。后来他还又多次前去华哲·阿布杜董拉希在中国各地的传教点游学求教。此后祁静一长期在甘、陕、川三地游学传教,宣传噶德林耶教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拱北门宦。
总之,以游学获取知识具有悠久的历史,不仅古代中国有游学之士,阿拉伯穆斯林也有游学求知的传统。回族形成后,在破解伊斯兰教中国化困局时,继承了中外游学传统,以此促进了经堂教育、汉文译著和伊斯兰教教派门宦的分化,使伊斯兰教真正扎根中国,成为中国伊斯兰教。
[1]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2773.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526.
[3][清]戴望.诸子集成(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4.125.
[4][清]孙治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1954.432-436.
[5]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2241.
[6]何建章.战国策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75.
[7]黄夏年.隋唐时代的僧人与游学行脚[J].五台山研究,2004,(03):7-10.
[8]罗彦慧.回回人的“天房”意向─明清时期回回社会朝觐游学初探[J].宁夏社会科学,2013,(1):67-70.
[9][12]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一部)[M].康有玺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37,序言24.
[10]王东平.中国穆斯林的学习观[J].中国宗教,2004,(07):32-34.
[11]哈宝玉.艾布·哈尼法与伊斯兰教法学理论[J].中国穆斯林,2002,(04):6-8.
[13][阿]讬太哈.回教教育史[M].马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41.63.
[14]迟毅.爱资哈尔大学的变迁[J].阿拉伯世界,1982,(03):2-6.
[15]曲红.一所公司大学─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J].世界宗教文化,2002,(3):34-35.
[16]冯增烈.<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碑叙[J].中国穆斯林,1981,(02):24-27.
[17][32][33][35][清]马注.清真指南[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435,23,168,417.
[18]王献军.海南回族与国内外穆斯林的交往[J].海南大学学报,2007,(03):241-246.
[19][22][23][25][26][清]赵灿.经学系传谱[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84,1,26-27,56-59,84.
[20][41]勉维霖.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概论[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173,403.
[21]冯增烈.明清时期陕西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A].宁夏社会科学研究所.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
[24]罗彦慧.回而兼儒贯通一家─中国经堂教育开创者胡登洲之求学经历研究[J].中国穆斯林,2010,(01):36-39.
[27]杨兆钧.云南回族史(修订本)[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189.
[28]马德新.朝觐途记[A].马安礼译.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二卷)[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240.
[29][明]王岱舆.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34.
[30]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319.
[31][38]李兴华等.中国伊斯兰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558,575.
[34]金吉堂.中国回族史研究[M].台北:台湾珪庭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105.
[36][37][清]刘智.天方至圣实录·著书述[M].北京: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编印,1984.4,4.
[39][40]子亨.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史略[A].西道堂史料辑[C].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87.2,7.
[42][44]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273,230-231.
[43]热什哈尔[M].关里爷,杨万宝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