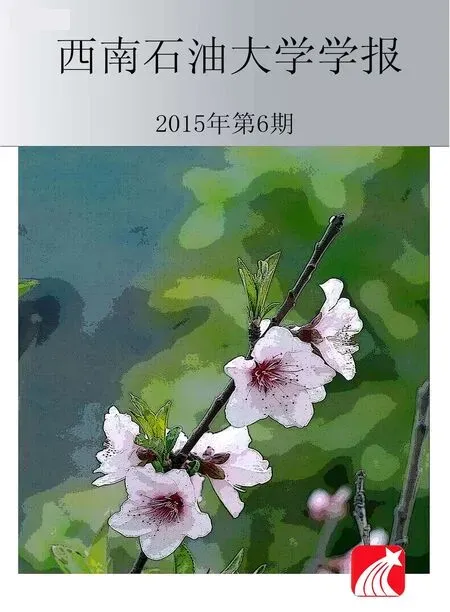危险驾驶罪的教唆犯研究*
贾银生,何显兵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四川 绵阳 621010
引 言
危险驾驶罪,无论是醉酒驾驶型还是追逐竞驶型,其责任形式都应当为故意。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责任形式在理论上虽然有争议①如冯军教授认为是过失,谢望原教授等认为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还有少数学者认为是严格责任。,但主流观点认为是故意[1-2]。然而,交通肇事罪的责任形式通说认为是过失。于是,教唆他人危险驾驶却产生交通肇事结果的情形,如何处理便成为一大难题。于此,就危险驾驶罪教唆犯这一问题,笔者寻探检讨,以求教于方家。
1 教唆他人危险驾驶产生交通肇事罪结果的处理难题
教唆他人危险驾驶,却产生交通肇事结果的情形,至《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以来,学界虽有提及,但少有探讨。具体而言存在如下难题:
难题之一,成立共同犯罪与立法的冲突。教唆他人危险驾驶,他人行为造成的结果具有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对教唆者,成立危险驾驶罪的教唆犯,按危险驾驶罪处理。如果教唆他人危险驾驶,被教唆者造成了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在这一场合下,至少教唆者的介入引起了被教唆者所实施的行为符合教唆故意内容的结果。但交通肇事罪又是公认的过失犯罪,根据我国刑法第25条和第29条第1款,两者不能构成共同犯罪。这就造成以下不合理局面:教唆他人危险驾驶,被教唆者构成危险驾驶罪时,两者可以成立共同犯罪;被教唆者在危险驾驶罪的基础上进一步产生了符合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结果、构成交通肇事罪时就不能成立共同犯罪。
难题之二,轻罪处罚、相对重罪不处罚的悖论。在被教唆者构成危险驾驶罪时,教唆者与被教唆者成立共同犯罪,对教唆犯,以危险驾驶罪进行处罚;在被教唆者危险驾驶进一步构成交通肇事罪时,因两者不能成立共同犯罪,根据刑法第29条第1款,对教唆者也就不能处罚。这样会导致教唆他人危险驾驶,被教唆者构成处罚相对较重的交通肇事罪的情形不受处罚;教唆他人危险驾驶,被教唆者也正好构成处罚相对轻微的危险驾驶罪时反而受到处罚的悖论。
难题之三,教唆犯是否应当处罚的两难困境。根据教唆犯从属于正犯故意的立场,教唆者的可罚性和处罚根据来源于正犯的实行行为和故意。对教唆犯的处罚根据可以肯定的是,教唆犯惹起了正犯产生了符合构成要件结果的故意,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只要教唆犯没有违法的阻却事由,其必然可罚。教唆他人危险驾驶却产生交通肇事罪的结果,从教唆犯的处罚根据上来讲,教唆者惹起了被教唆者危险驾驶的故意,被教唆者也实施了危险驾驶行为,不但造成了符合危险驾驶罪构成要件的抽象危险,还造成了致人伤亡的交通肇事结果,只要教唆者不具有违法阻却事由,其应当可罚。然而,一旦处罚教唆者,又明显违背刑法第25条和第29条之规定,如果不处罚又明显放纵犯罪。简言之,教唆他人危险驾驶却产生交通肇事罪的结果的情形,会面临处罚教唆者则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不处罚又无疑放纵犯罪的两难困境。
2 教唆他人危险驾驶产生交通肇事罪结果的处理方案
2.1 根据行为共同说,否定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肯定对过失犯的教唆
运用行为共同说在否定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上,肯定对过失犯的教唆,以解决教唆他人危险驾驶却产生交通肇事罪结果的难题,在理论界虽然没有人明确提出过,但根据如张明楷教授等部分学者在共同犯罪的本质上赞同行为共同说,否定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的见解[3],不失为解决此难题的一种方案。但该种方案是否合理还有待验证。
2.1.1 运用行为共同说解决上述难题的相对合理性
行为共同说认为,共同犯罪即指数人共同实施了违法行为而不是共同实施了特定的犯罪;共同犯罪意思是不必要的,共同过失的违法行为也应当成立共同犯罪(数人数罪)。行为共同说与犯罪共同说相对,主要是解决共同正犯犯罪本质中“共同性”问题的。近年来,行为共同说在解决共犯问题上也开始成为有力学说。如松宫孝明教授认为,“承认过失共犯可罚性的学说似乎并非这样简单就可以驳倒”[4]。从共犯的处罚根据在于共犯介入正犯的行为,引起了正犯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以共犯固有的违法与责任而受到处罚来看,那么共犯的本质也可以理解为“数人数罪”。易言之,行为共同说为共犯的处罚根据采取因果共犯论(混合惹起说)的立场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从共犯的要素从属性来看,共犯也就没有必要从属于正犯的故意。因此,行为共同说肯定对过失犯的教唆。
如李斯特所言:“教唆犯是指故意教唆他人实施教唆者自己意图实施犯罪之行为。”[5]371成立教唆犯,基本前提是教唆犯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另外,教唆犯是否要求与正犯的故意从属,值得探讨。这在德日刑法学上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其中肯定说是通说。当然,否定说的见解也很有力[5]315[6]。在国内,张明楷教授率先引进否定说[7],后得到钱叶六教授等学者的支持[8]。在否定共犯对正犯故意从属的问题上,认为肯定说不能合理解释诸如共犯错误、身份犯等问题;认为我国刑法第29条第1款、第27条,都没有肯定教唆犯、帮助犯成立的条件是其对正犯故意的从属。
从行为共同说肯定对过失犯的教唆来说,教唆他人危险驾驶却产生交通肇事罪结果的情形,成立共同犯罪。对教唆犯,因其引起被教唆者产生了实施符合危险驾驶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意思,并通过被教唆者的违法行为间接地侵犯了法益。通过其责任形式所对应的惹起被教唆者的法益侵犯结果,符合了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应以危险驾驶罪论处。此时,虽然被教唆者产生了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结果,但也不影响其教唆犯的成立和处罚。
2.1.2 该种方案的缺陷
行为共同说承认对过失犯的教唆,必须要求在教唆犯可罚性的基础上否定教唆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张明楷教授虽然主张否定说,但自己也可能很矛盾。
张教授在论证该问题上主要借鉴日本刑法学者在解决共犯错误问题和身份犯等问题上由肯定说到否定说的转变。但从日本刑法第60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犯罪的都是正犯”,第61条“教唆他人实施犯罪的判处正犯的刑罚”的规定中,不难看出,日本刑法学者主张否定说至少有立法上的依据,不会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和责任主义原理。
另一方面,张教授认为我国刑法第29条第1款、第27条都没有肯定教唆犯、帮助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根据其见解,无非认为我国刑法条文中“共同犯罪”的含义不一样。刑法第25条第1款的“共同犯罪”是一般的责任形式为故意的共同犯罪,第25条第2款明显承认了特殊的共同过失犯罪事实,只是不按故意的共同犯罪处罚而已;刑法第27条和第29条第1款的“共同犯罪”包含了共同过失犯罪和共犯故意、正犯过失等的共同犯罪。
在笔者看来,不能将我国刑法第25条第1款对刑法第26条至第29条“共同犯罪”用语的统领作用视而不见。从刑法体系上说,同样的用语在不同的条文中确实会有不同的含义。如刑法第14条的“明知”和第138条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中的“明知”;刑法第14条的“故意”和第304条故意延误投递邮件罪中的“故意”等。但这是作为刑法总则和分则的用语。虽然刑法总则对分则起指导性作用,但分则本身也具有区别于总则的特殊性。在总则范围内,尤其是在前后关联的法律条文中,相同的用语应当有相同的含义。如刑法第13条至第17条,关于“犯罪”的含义;刑法第14条的“故意”与第16条、第17条的“故意”;刑法第15条的“过失”与第16条、第17条之1的“过失”等①如果张教授否定共犯对正犯故意从属,其在《危险驾驶罪的基本问题——与冯军教授商榷》一文中也就不应该说“将危险驾驶罪认定为过失犯罪,就否定了本罪存在教唆犯与帮助犯”。由此可见张教授在解释法条时的矛盾心理。。
笔者以为,在共犯的本质上,目前还只能采取部分犯罪共同说。我国刑法在对共犯从属性的规定上,教唆犯必须从属于正犯的故意。退一步说,即使承认对过失犯的教唆,也会面临处罚过宽的问题。如西田典之教授认为,“如果认定过失共犯,其处罚范围只能是极其宽泛,在充满危险的现代社会,这又属于过度的刑事控制”[9]。因此,虽然行为共同说肯定对过失犯的教唆,教唆他人危险驾驶却产生交通肇事罪结果的情形成立共同犯罪,对教唆犯也有处罚根据,但这样的处理方式无论从我国的立法技术上还是从实质解释上来说,都难以成立,因而不可取。
2.2 根据法益保护前置化原理和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的处理方案
法益保护前置化原理主要是在风险社会下“风险刑法”理论上提出的②其主要体现是刑事立法中抽象危险犯的扩张。。在国内,该原理也得到部分学者的支持[10-11]。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是张明楷教授在借鉴德日刑法“客观处罚条件”概念和传统刑法“主观的超过要素”对应概念的缺失上创立的。对教唆他人危险驾驶却产生交通肇事罪结果而言,虽然目前理论界也没有明确提出以此方法解决,但也可以进行探讨。
2.2.1 该种方案的相对合理性
如今的车流社会,行为人驾车行驶在客观上已然具有了高度的风险,只是在社会整体利益的衡量下,基于信赖原则,允许了这种风险的存在。但行为人危险驾驶,造成了危害公共安全的抽象危险,刑法不能容忍。从更好地保护社会公共安全的角度出发,对危险驾驶行为所造成的抽象危险,刑法应当提前介入。因此,从增设危险驾驶罪的角度来说,根据法益保护前置化原理,有理由认为危险驾驶行为构成的交通肇事罪属于故意犯罪。
根据张明楷教授的观点,客观的超过要素仍然是犯罪构成要件的要素,是超出与行为人故意相对应的客观结果要素,并且至少要求行为人对这样的要素具有预见可能性。运用客观的超过要素,主要限制有三:“一是客观的超过要素主要存在于故意犯罪中,在过失犯罪中意义不大。二是行为内容所表现的客观危害结果的超过要素,只应当存在于双重法益侵犯结果中。三是只能对法定刑较轻的故意犯罪的实害结果承认客观的超过要素①如这样的情况:行为人明显故意的实施危害行为,刑法又要求发生法益侵犯结果才该当于犯罪的构成要件,而这样的结果往往相当严重,且法定刑又较低。如果承认该罪必须出于故意,又会造成此罪与彼罪区分的难题和罪与刑不相适应的困境。。”[12]227–237
根据法益保护前置化原理,因危险驾驶而产生的交通肇事罪为故意犯罪。如果行为人致人伤亡,法定刑确也较低。这样的伤亡结果,将其认定为客观的超过要素确也合理。具体原因有三:其一,行为人虽然没有希望或放任,但也有认识或认识的可能性。其二,这样的伤亡结果确实也造成了致人伤亡的实害结果和公共安全的法益侵害的双重危害结果。其三,危险驾驶致人伤亡的法益侵犯确实相当严重,且法定刑又较低,如果承认该罪必须出于故意,确实会造成此罪与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等区分的难题和罪与刑不相适应的困境。
结合法益保护前置化原理和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教唆他人危险驾驶却产生交通肇事罪结果的处理如下:其一,如果教唆他人危险驾驶并且希望或放任交通肇事罪结果的发生,则教唆者和被教唆者成立交通肇事罪的共同犯罪。其二,如果教唆者对被教唆者所造成的客观超过要素没有预见可能性,或有预见可能性但并非追求或放任,根据部分犯罪共同说,两者在危险驾驶罪上成立共同犯罪。在这一基础上,对教唆者以危险驾驶罪处理;对被教唆者,还需要对其客观的超过要素负责,以交通肇事罪处理。
2.2.2 该种方案的适用性存疑
“风险社会”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提出。贝克所称的风险主要是后工业时代的技术风险,而非交通风险。同时,贝克自己也认为,“风险”只是一种构想,一种社会定义,就像神一样,只有相信它才知道它的存在和真实有效[13]。“风险刑法”概念受风险社会理论的影响而提出,但其过于扩大“风险”的含义,容易认为刑法立法上新近增加的危险犯都是风险刑法的体现。如陈兴良教授所言,“风险概念被泛化的结果导致风险刑法的理论丧失现实基础,也使风险刑法理论与风险社会理论难以对接”[14]。
虽然国外如日本刑法2001年增设第163条之4的准备非法制作支付用磁卡的电脑记录罪,将刑法第161条之2的非法制作电磁记录罪、提供非法制作的电磁记录罪的预备行为单独处罚[15]552–575;国内如《刑法修正案(八)》修改刑法第141条,将其基本犯罪规定为抽象危险犯,修改刑法第338条,将其由实害犯规定为具体危险犯等,确有通过法益保护前置化以应对风险社会下的一些抽象或者具体危险状态。但这些情况也属于极少数,世界各国刑法还是以实害犯为绝对主体。
同时,风险社会下,法益保护前置化原理在整个大陆法系刑法学者中都争议不断。法益保护的内容如何判定;将法益保护前置到预备行为还是实行行为,以及实行行为的什么阶段;法益保护前置化后刑法的谦抑性价值如何体现,刑罚的正义性和人道性如何衡量等,问题重重。这样一来,容易主观归罪和违背责任主义原理,导致刑罚处罚过重。另外,“客观的超过要素”虽然可以比较合理地解决如丢失枪支不报罪、滥用职权罪等看似既可以是故意又可以是过失犯罪的理论难题,但也存在诸多问题而不被学界广泛认可。
举其一点疑问来说,如果客观的超过要素也属于构成要件的要素,那么就应当有相应的主观要素相对应。张教授认为行为人对行为所造成的结果虽不希望或放任,但至少有认识或认识可能性。这种见解确有一定道理,但其没有明确回答这样的认识或认识可能性是否属于过失。一方面,如果不属于过失就不应当将客观的超过要素认为属于构成要件的要素,刑法处罚行为造成这样的结果无非是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而如李斯特的名言,“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屏障”[16]3,张教授也只是回避了刑事政策和犯罪构成要件定型性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如果行为人对客观超过要素的认识或认识可能性属于过失,那么如刑法第129条的责任形式也就成了故意加过失了。张教授也主张对同一犯罪的责任形式应当整体判断,并且认为,“行为与结果都是认识的内容,如果只考虑一点,显然不能得出适当结论”[12]219。由此可见,“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适用的困难。也如张教授自己所言,在三阶层或两阶层体系下,这一概念是否有存在的余地,还需进一步探讨[12]218。
鉴于“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适用的困难,将危险驾驶造成的致人伤亡的交通肇事结果认定为客观的超过要素,难以说明这样的结果是否属于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要素,更难以说清楚行为人对致人伤亡结果的认识或认识可能性属于什么性质。因此,运用该种方案来处理教唆他人危险驾驶却产生交通肇事罪结果的情形,确实不合适。
2.3 修正刑法以结果为本位界定犯罪责任形式,而以行为为本位来界定的处理方案
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开始探讨修正我国刑法以结果为本位来界定犯罪责任形式,改之以行为为本位来界定犯罪责任。如劳东燕教授提出:“随着风险的扩散化与日常化,结果本位主义的刑法在危害预防与法益保护方面日益显得力不从心,立法者越来越多地采用行为本位主义模式来设置罪刑规范。如果刑法还以结果为本位,便难以解决如丢失枪支不报罪、滥用职权罪等责任形式有争议的难题了。”[17]如果一改以传统结果本位为中心界定犯罪的责任形式,那么自增设危险驾驶罪以来,交通肇事罪也可以轻巧地认定为故意犯罪了,教唆他人危险驾驶却产生交通肇事罪结果的难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2.3.1 以行为本位界定犯罪责任形式的相对合理性
在对犯罪故意认识因素的扩张和意志因素的缩限或否定上,以结果为本位来限定犯罪故意与过失已开始被修正,主张以行为为本位来限定犯罪故意与过失逐渐成为有力学说。如有学者认为,意志因素是针对行为而言而非针对结果而言①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德国的施米德霍伊泽教授,我国的冯军教授、黎宏教授、劳东燕教授,我国台湾地区的黄荣坚教授等。[18]。在此基础上,以对犯罪行为事实的认识,而非对犯罪结果的意欲,界分犯罪故意、过失。由此看来,对犯罪故意、过失的界定以行为为本位来进行判断确实有一定道理。
从以行为为本位界定犯罪的责任形式的角度来说,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都属于风险社会下的产物,对两罪责任形式的划分和责任内容射程的界定也应当以危险驾驶行为或交通肇事行为来进行。而危险驾驶罪就其行为本身来说,行为人已然认识到其行为的危险性或可能造成危险的盖然性,行为人没有阻止和回避其违法行为计划的进一步发展,应当认为是故意。在此基础上,行为所造成的致人伤亡的交通肇事结果也自然归属于行为人没有回避行为计划发展的必然后果,而且这样的法益侵犯后果是刑罚加重处罚的条件之一。
因此,行为人危险驾驶尤其是醉酒驾驶,已然认识到其行为对《道路安全法》等法规范的违反和可能导致的法益侵犯后果,并且其未阻止危险驾驶计划的进一步发展,在责任形式上就属于故意。教唆他人醉酒驾驶却产生交通肇事罪结果的情形,由于危险驾驶所导致的交通肇事罪都属于故意犯罪,两者必然成立共同犯罪,对教唆犯直接按其所教唆的范围定罪处罚。
2.3.2 该种方案适用的障碍
大陆刑法理论通说认为犯罪的核心是行为,但法益侵犯结果才是国家刑罚权发动的根据。为了国家刑罚权发动的正当性,在刑法立法上整体体现着结果本位主义思想[17]。近年以来,虽然国际国内刑事立法上法定犯、危险犯增多,但整个刑法体系以结果犯或实害犯为主体没有动摇,结果本位主义仍然是刑法的标杆。同时,以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结果为中心界分犯罪故意、过失,界定犯罪故意与过失的射程,符合客观主义刑法理念,可以有效保障国民对其行为的预测可能性和行动自由。反之,若以行为本位主义界定犯罪故意与过失,则容易造成刑法的肆意性和国民行动自由的萎缩。
劳东燕教授还认为:“一旦坚持以结果作为认识内容核心的故意理论,如何认定如丢失枪支不报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与滥用职权罪等犯罪的罪过形式,便成为不容回避的难题。”[17]笔者对该观点提出如下质疑。第一,毋庸讳言,以上犯罪的责任形式确实有争议,但以劳教授所主张的,将间接故意等价于直接故意,取消过于自信的过失类型,引入英美刑法轻率的罪过形式[17],难道就能很好判断吗?根据其观点,行为人对其丢失枪支的行为可能属于轻率,不及时报告的行为属于故意。如果以行为本位进行判断,民警丢失枪支不及时报告的行为也有两种责任形式。第二,仅因为刑法分则犯罪责任形式有争议的几个罪名而以行为为本位界定犯罪的故意与过失,还容易造成行为本身的有意性和犯罪责任形式以及犯罪故意认识内容的混淆。第三,丢失枪支不报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等犯罪的责任形式有争议的罪名只是少数,并非刑法分则所有犯罪都是如此。如果仅以此而认为刑法体系应当以行为为本位界定犯罪的责任形式,则大陆法系传统的犯罪论体系必须推倒重来,刑法分则规定的大量结果犯也要重新解释,而这势必造成立法规定犯罪和司法认定犯罪的大洗牌、大混乱。
因此,虽然修改传统刑法以结果为本位界定犯罪的责任形式可以较好地解决教唆他人醉酒驾驶却产生交通肇事罪结果的难题,但这样一来,不仅会产生其他诸多难题,而且整个刑法体系也得重新洗牌,并且严重损害刑法的安定性,导致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受损,行动自由萎缩。
3 应将交通肇事罪作为危险驾驶罪的结果加重犯来处理
教唆他人危险驾驶却产生交通肇事罪结果的难题,还有一种解决方案:将交通肇事罪作为危险驾驶罪的结果加重犯进行处理。这样的方案,张明楷教授有过较为简略的论述[1]。笔者赞同该种方案,在此进行详细论证。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通说认为,结果加重犯对基本结果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对加重结果至少要求过失。在增设危险驾驶罪之前,交通肇事罪本来就包括两个法益侵害后果:一个是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了危害公共安全的抽象危险;另一个是在造成了危害公共安全抽象危险的基础上,进一步造成致人伤亡的加重结果。
增设危险驾驶罪之前,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法益侵犯程度还没有达到值得刑法调整的范围,故而由行政法进行调整。社会生活的变化,违规驾驶的法益侵犯后果越来越严重,如醉酒驾驶行为和追逐竞驶行为。于是《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对醉酒驾驶和追逐竞驶行为进行规制。而且,《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还提出将“在公路上从事客运业务,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的”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纳入危险驾驶罪的调整范围。
因此,根据醉酒驾驶行为和追逐竞驶行为法益侵犯的严重性,有必要将其纳入刑法的评价范围,《刑法修正案(八)》只是将其从交通肇事罪中分化出来单独成罪而已。从危险驾驶行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所造成的抽象危险和行为进一步发展造成的致人伤亡的交通肇事结果来说,交通肇事罪确也属于危险驾驶罪罪质上的结果加重关系。这样的结果加重关系,一方面从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重于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来看合符逻辑;另一方面如张明楷教授所言,“基本犯是抽象危险犯,加重犯是实害犯为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所公认”[1]。如德国刑法第306条第2款的放火罪、第326条第5项的危害环境处理垃圾罪,我国刑法第141条、第144条等。同时,对于基本结果为故意,加重结果为过失的情形,在立法上也有相应的印证,如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抢劫致人死亡等。
因交通肇事罪与危险驾驶罪具有罪质上的结果加重关系,在危险驾驶罪上有罪质的重合部分,教唆他人危险驾驶却产生交通肇事罪结果的情形,根据部分犯罪共同说,教唆者和被教唆者在危险驾驶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教唆者构成危险驾驶罪,被教唆者构成交通肇事罪。所以,教唆他人危险驾驶,结果他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情形,教唆者成立危险驾驶罪的教唆犯。
该种论证合乎理论逻辑,具有合理性。但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一,虽然交通肇事罪在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这一抽象危险上的责任形式为故意,但对同一犯罪的责任形式应当整体评价,交通肇事罪的责任形式在整体上为过失,而部分犯罪共同说要求正犯的责任形式为故意。二,即使承认交通肇事罪是危险驾驶罪的结果加重犯,但我国刑法对加重结果的规定都在同一法条中。笔者回答如下:
毋庸讳言,部分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一样,主要是解决共同正犯“共同性”问题的,其要求共同犯罪部分的“共同”,核心是共犯人之间具有罪质上重合的犯罪。在共犯的从属性问题上,要求共犯和正犯在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上都具有部分重合的要素。在教唆犯从属于正犯故意的问题上,教唆犯出于犯罪故意教唆他人,正犯在责任形式上也要具有故意,两者才有可能成立共同犯罪。
但是,至《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以来,交通肇事罪应当存在两种类型:一种是危险驾驶罪以外的纯过失的交通肇事罪,如超载驾驶、疲劳驾驶所致的交通肇事罪;一种是由危险驾驶罪所致的交通肇事罪。对第二种,作为基本犯的危险驾驶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只不过加重结果为过失罢了。既然部分犯罪共同说的本质在于部分犯罪的共同,教唆他人危险驾驶产生交通肇事罪结果的情形,在危险驾驶罪的范围内当然可以成立共同犯罪,对教唆犯也自然可以以危险驾驶罪论处了。
对比国外,日本刑法理论通说也是将危险驾驶致死伤罪作为危险驾驶罪的结果加重犯处理[15]58[19]。日本刑法第208条之2第1款的危险驾驶致死伤罪和我国的交通肇事罪颇有相似之处;日本的《道路交通法》第65条第1款规定了醉酒驾驶等危险驾驶罪,和我国的危险驾驶罪也颇具相似之处。尤其是该法对醉酒驾驶罪的“难以正常驾驶”必须有认识的故意。对危险驾驶致死伤罪,日本的通说认为其在符合醉酒驾驶罪的层面上属于故意,在对死伤结果的发生上属于过失。于是,危险驾驶致死伤罪是醉酒驾驶罪的一种特殊的结果加重犯。而且,日本刑法通说也将伤害致死罪作为伤害罪的结果加重犯处理;将伤害罪作为暴行罪的结果加重犯处理等[20]47。我国的交通肇事罪和危险驾驶罪的关系处理完全可以借鉴日本通说的处理方式。
另外,虽然我国关于结果加重犯的规定绝大部分都在同一法条中,但也有例外。这样的例外如刑法第114条属于基本犯,刑法第115条第1款则属于第114条的结果加重犯;刑法第116条的破坏交通工具罪、第117条的破坏交通设施罪和第118条的破坏电力设备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等属于基本犯,而刑法第119条属于第116条至第118条相应犯罪的结果加重犯。
因此,教唆他人危险驾驶,被教唆者产生了交通肇事罪的结果的情形,根据部分犯罪共同说,教唆者和被教唆者可以在危险驾驶罪的层面成立共同犯罪,对教唆犯按危险驾驶罪处理;对被教唆者,因其危险驾驶进一步构成了交通肇事罪,单独按交通肇事罪处理。
4 结语
不能认为危险行为的刑罚只是拘役并处罚金,就对其宽容。如考夫曼所言,“宽容并非毫无界限,它不是不计任何代价的容忍。有效的法律必须予以遵循,违背法律,特别是犯罪,是不能容忍的,而非人性者不能有所主张,乃属当然之理。”[21]也不能认为教唆犯引起了正犯的犯罪意思和符合构成要件的犯罪事实,通过正犯的行为间接地侵害了法益,只要没有违法阻却事由,其主观恶性就极大,就可以越过教唆犯的处罚根据而加重处罚。如罗克辛教授认为:“刑罚的严厉性不得超越罪责的范围。”[16]77对教唆他人危险驾驶的行为,尤其是教唆他人醉酒驾驶,被教唆者产生了符合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的结果,对教唆犯应当在罪刑法定的范围内进行严格认定和刑罚规制,以此保障社会的公共安全秩序,保障国民的人身、财产安全。
[1]张明楷.危险驾驶罪的基本问题与冯军教授商榷[J].政法论坛,2012(6).130–141.
[2]陈兴良.过失犯的危险犯:以中德法为比较[J].政治与法律,2014(05).2–15.
[3]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358–359.
[4]松宫孝明.刑法总论讲义[M].钱叶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04.
[5]弗兰茨·冯·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M].徐久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6]山口厚.刑法总论[M].付立庆,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15.
[7]张明楷.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之否定[J].政法论坛,2010(5):11–19.
[8]钱叶六.共犯论的基础及其展开[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209.
[9]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M].王昭武,刘明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346.
[10]姚贝,王拓.法益前置化问题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1):27–33.
[11]王永茜.论现代刑法扩张的新手段法益保护的提前化和刑事处罚的早期化[J].法学杂志,2013(6):123–131.
[12]张明楷.犯罪构成体系与犯罪构成要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3]乌尔里希·贝克,威廉姆斯.关于风险社会的对话[M]//薛晓源,周战超.全球化与风险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2.
[14]陈兴良.风险刑法理论的法教义学批判[J].中外法学,2014(01):103–127.
[15]山口厚.刑法各论[M].王昭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6]克劳斯·罗克辛.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M].蔡桂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7]劳东燕.犯罪故意理论的反思与重构[J].政法论坛,2009(1):82–92.
[18]陈磊.类型学的犯罪故意概念之提倡[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4(5):190–200.
[19]赖正直,朱章程.日本刑法中的危险驾驶致死伤罪评述[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5):119–127.
[20]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M].王昭武,刘明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47.
[21]阿图尔·考夫曼.法律哲学[M].刘幸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