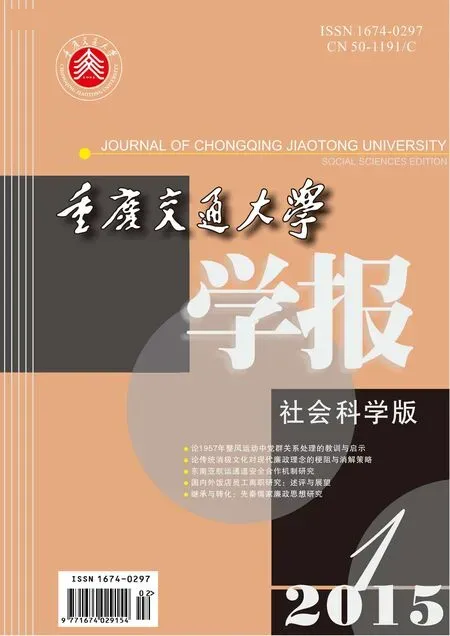论传统消极文化对现代廉政理念的梗阻与消解策略
侯保龙, 王方友
(安徽科技学院 思政部,安徽 蚌埠 233100)
论传统消极文化对现代廉政理念的梗阻与消解策略
侯保龙, 王方友
(安徽科技学院 思政部,安徽 蚌埠 233100)
现代廉政理念是廉政文化建设的前提,该理念由九大意识构成,提出的依据是性恶论是现代廉政理念形成的观念预设,专制恐惧感是催生现代廉政理念的强烈动因,社会民意构成现代廉政理念的终极基础。应从五个层面来消解中国传统消极文化对现代廉政理念的影响。
现代廉政理念; 传统消极文化; 文化反腐
反思和消除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是廉政文化建设的基础工作。如果不认真反思传统消极文化,“我们即使有民主制度的硬件,民主也不会健壮,腐败就会肆虐”[1]。所谓传统消极文化,是一个社会文化传统中那些对社会文明进步起副作用的社会心理、习俗和行为方式的总和,人们或称其为社会“潜规则”。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度,如何打破和消解传统消极文化对现代廉政理念的梗阻,将是我国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斗争绕不开的课题。
一、现代廉政理念的构成及其依据
现代廉政理念是现代廉政文化的内核,它规定了一个国家廉政文化建设的方向,从根本上制约着廉政文化建设的进程和质量,甚至决定着廉政文化建设的成败。
现代廉政理念是指西方文艺复兴以来逐渐形成的一套人类正确参与和处理公共生活的理性思维或观念。其核心问题是理性认识和处理个人与国家或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纵观西方政治文明建设的历程和近现代中国对救国救民之路的探索,我们认为现代廉政理念由以下三点九大意识构成:第一,对于人类理性的社会公共生活而言,人类严格区分和界定“公”与“私”的界限,在公共生活领域高举“公”字大旗,即社会个体应具有公共意识、公益意识、公德意识;第二,从社会公共生活的主体角度看,每一个人都应是公共事务的主人,都应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民主意识;第三,与此相适应,为了有效维护社会个体的正当权利,人们还必须以法治的精神时刻警惕公务人员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这就必须要求每一个公民特别是公职人员树立强烈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限权意识。
上述三点构成现代廉政理念,其根据何在?
首先,性恶论是现代廉政理念形成的观念预设。综观西方人性理论的发展史,性恶说是其主流的思想传统。从古希腊起,西方哲人一直有着人性恶的假设传统。柏拉图在其早年信奉人性善,但在其晚年改持人性恶的观点。在其著作《法律篇》中,他认为人性恶,并主张法律的统治。在文艺复兴运动中,性恶论成为西方社会契约论的认识论基础。正是基于这种性恶的人性设定,以制度、法制约束人性的弱点成了法治主义者的永恒焦点,他律型的腐败治理模式在西方占据着主导地位。在中国,虽然性善论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但改革开放后腐败形势的严峻动摇了中国人的人性观倾向,市场经济的深化正在强化着国人关于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的判断,依法治国和制度反腐的高扬正印证着我国国民人性观的转变。
其次,专制恐惧感是催生现代廉政理念的强烈动因。人类天生就有酷爱自由的本性,专制是对这一本性的压制和藐视。不论任何形式的专制,其共同的特征是垄断公共权力,排斥专权者或家族之外的社会群体参加国家政权共同行使或监督公共权力,并且利用公共权力压榨社会民众,谋取个人或家族利益。所以专制与腐败是一对孪生兄弟,专制是腐败的根源,绝对的专制导致绝对的腐败;腐败天然依赖和扩大专制,腐败分子最害怕民主。故民众对专制甚为恐惧,最痛斥专制和腐败,最热爱民主和清廉。社会民众要维护其正当权利,必然要以法治和宪政限制公共权力的行使。国家公共权力的形成和运行若不具有相当大的公共性,就会丧失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最后,社会民意构成现代廉政理念的终极基础。一个廉洁的政府必然建立在坚实的社会民意基础上,并且能够有效地回应社会民意。在西方,社会契约思想力图使政府建立在社会民意并对社会民意负责的基础之上。以社会契约的方式约束政府行为,目的是打造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一个无私为民谋取福祉的政府。社会契约思想认为政府只是暂时掌握社会公共权力,社会公共权力最终属于全体公民。之所以让少数政府人员掌握公共权力,只是全体社会成员无法共同行使公共权力;政府如果不能很好地运用公共权力为社会民众服务,社会民众有权随时收回公共权力,所以政府必须接受社会民众的制约和监督。这就是西方社会契约论的廉政逻辑。中国古代虽无西方“社会契约”的概念和系统论说,但中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尧舜禅让时期就有千方百计挑选既有智慧又有德行的人充任最高统治者的传统。从此以降,不论如何选拔最高统治者,对他们的最基本要求总是“重民”“仁政”和“德治”。统治者虽秉承“天意”而治,而“天意”与“民意”是直接相通的,统治者若违背天意即民意,就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民贼”,此时,人民群众就有推翻“无道暴君”、重建新政府的革命权利。无产阶级国家成立以来在无形中继承了这一思想,我国宪法明确宣布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一切国家机关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民主、法治不过是民意的体现,是促使政府回应民意的制度安排。
二、传统消极文化对现代廉政理念生成的梗阻
第一,基于人性善的人性预设从根本上阻碍着中国法制理性的培育。儒家对人性中善的一面盲目乐观,而对人性中恶的一面保持理性无知。既然人性是善的,官员的人性亦是善的,相信他永远是“圣人”、是“君子”,相信他会实行“贤人政治”,他会推己及人,像爱护他的子女一样关爱社会民众,当然就无需对官员进行权力制约和监督。即使官员受到各种影响而变质腐化,也不是本性使然,而是官员修身养性欠缺的结果,通过教育可以得到纠正,根本不需要权力限制和依法治国。孙关宏教授在反思我国社会产生腐败的原因时认为,对人性认识的偏颇是我们社会腐败现象严重的深层次原因,“特别是对官员,把他们看做圣人,否认他们有谋取私利的可能,……这样做,客观上保护了官员的私利性,让其不受制约地、隐蔽地发展”[2]。基于人性善的基本预设必然形成德治——人治传统和集权专制传统,制约着现代科学民主治理理念的生成以及社会监督和限权意识的张扬。事实上,人性中善恶的成分都有。马克思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问题永远只能是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3]人类实行法治的目的不是根本不相信人性中存在善的一面,而是对人性中恶的一面加以提防。
第二,官本位传统造成官员官贵民贱的从政心理,造成部分官员私欲膨胀。中国社会有浓厚的官本位传统。在传统社会,官员居于特殊的社会地位,拥有特殊的权利,形成了官贵民贱的官本位传统。“官本位作为一种价值观和思想意识,就是把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当成一种核心的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4]75在传统官员看来,万般皆下品,唯有当官高。因为社会其他阶层都是围绕着官员权力旋转的,官员手中握有各种各样的权力资本,拥有任意处置民众生命财产的大权。于是部分官员产生当官发财心理(所谓 “千里做官为求财” )、自我权威崇拜与浓烈的排外心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衍生出无官不贪的社会心理,导致新的官员崇拜现象,亦使领导干部把权力特殊化处理,盲目排斥圈子外(派别外)的新人加入公务员队伍特别是领导班子,阻碍着现代公务员职业理性和服务理性的生成。
第三,臣民心态不利于公民的主体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权利意识、民主意识、限权意识以及进取意识的产生。在官本位社会,官员凌驾于社会之上,社会民众对官员只能仰视、崇拜,甚至“羡慕”。社会民众无法取得与官员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无法实现真正的人格平等和独立。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一方面社会民众形成了对官员强烈的依附思想,民不与官斗以及消极无为、与世无争的社会心理;另一方面官场和政治的昏暗与民众反抗的无望导致广大民众企盼清官出现,救苦救难。“翻开二十四史,人们就会明白,有名有姓并且货真价实的清官,不过几十位。”[5]138“民众迷信清官,那是一种软弱无奈的表现。清官思想本质是一种企盼救世主的封建主义思想。”[5]150-151因此,在传统消极文化的浸淫下,民众丧失了自我,无法享有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利,只有“官主”意识,少有民主意识,只有臣服意识,更无限权意识。民众得过且过,妄谈创新进取意识。
第四,浓郁的家族情结强有力地冲击着现代廉政所要求的公共意识、公益意识、公德意识的形成。“廉”字从“广”从“兼”,说明廉者必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君子,必是超越狭隘的个人和家族利益、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的贤人。在此意义上,一个人能够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就是廉洁。费孝通曾把中国传统社会称为乡土社会,它是一个以个人家庭为中心逐次向亲戚、朋友、社会陌生人扩散的“差序格局”。一个人或一个官员很可能会情愿地或迫于家族朋友的压力成为腐败的俘虏。因为他和他的家族都认为,他手中的权力首先是属于整个家族的,然后才是属于国家社会的。那么,他在行动上必然把家族私人利益而不是社会公共利益放在第一位。梁漱溟说中国人缺乏公共观念,有发达的“私德”而欠缺必要的“公德”[6]162。所以梁启超才认为,“中国想建设一个新国家,必须先要有新民;新民是不同于旧时的中国人,必须要具备几个条件,最必须的条件,就是公德。”“是故公德者,诸国之源也,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7]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就看到了家族忠诚意识(私德)对民主政治的伤害。他指出,家族成员之间的固有关系尤其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促使他们偏爱和偏袒自家人,即裙带风。这种“不道德的家族主义”与腐败关系密切。
第五,人情礼制传统对现代廉政的制度理性、公开公正和尚廉崇洁心态形成巨大掣肘。中国传统上是一个讲人情礼制的社会,亦称“关系社会”。有学者认为,“‘关系’是理解中国人社会、政治和组织行为的关键概念,用来描述中国人之间的特殊联系。”[8]其特殊性主要体现为“在现实生活中利用个人所拥有的人际资源以谋求政治或经济利益上的好处,使人际关系‘资本化’、工具化的倾向”[4]15。这种功利性的“中国式关系”对我国廉政理念建立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人情、面子和关系网构成了中国人的社会行为特征。中国人办事情首先想到的不是按法规制度走程序办事,而是走捷径找人情关系。不是说中国人办事不想按法规制度走程序,而是说公事公办反而效率很低,或者官员故意拖延,人们没办法才走人情关系。这就是我国为什么法制理性微弱而人情传统不衰的基本原因。梁漱溟认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有“四大短处”,其中第一个就是缺乏法治精神,“亦即事事不按法律来办,执法的精神不够,而且很容易殉情”[6]160。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形成对官员的依赖心理,总会千方百计地与官员攀龙附凤,而官员也心安理得地抱着“当官不打送礼人”的阴暗心理。这样,整个社会难以形成法治理性和尚廉崇洁的氛围。事实上,“不当求利型的人情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不仅没有被抑制,而且呈进一步蔓延之势”[9]。
三、中国传统消极文化对现代廉政理念影响的消解策略
树立现代廉政理念离不开对中西优秀文化的兼收并蓄,也离不开对传统消极文化的理性认知和现代性转化。如果我们的策略得当,就会加速中国传统消极文化从渐变到蜕变的历史过程,更早地确立现代廉政理念。
第一,在思想认识层面,全党全社会都要充分认识清除传统消极文化的长期性,把清除传统消极文化作为党和国家长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全党全社会都要有这样的思想自觉。资本主义国家在立国之前都进行过激烈的资产阶级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文化批判,在此基础上确立了资产阶级新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国没有经过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相当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基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特殊的国际国内形势,我国还未来得及对包括封建主义在内的传统消极文化进行清算,就匆忙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封建主义文化阴魂不散,成为消极腐败的主要祸首之一。“就其对我们思想的影响在现实中所起的消极作用及其历史渊源来看,清除封建思想影响无疑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热衷于搞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的人最忌讳反封建主义,一提起这件事就仿佛挖了它的祖坟一般,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封建主义那一套。”[10]封建文化最主要的内容是专制传统,我们特别要警惕。我们需要辩证地理解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切实贯彻民主集中制。脱离民主的权力集中就是专制。我国历史上的民主传统稀少,而专制集权传统悠久,消除其文化影响,必须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
第二,在价值观层面,应坚持集体主义人性思想,抵制狭隘利己主义。有什么样的人性思想,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以往学界往往从性善或性恶的角度区分人性,都有其片面性。我们不妨换一个视角来划分人性,就是从一个人行为性质的“公”或“私”的角度来具体分析人性。一个人内心中的“公心”与“私心”呈反比例关系,人性发展的方向取决于一人所奉行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或“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所占比例的大小。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人性观。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了人性观的性质,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人性观只能是人性恶,或人是自私的生物,或叫狭隘的利己主义。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坚持和发扬集体主义人性思想;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狭隘利己主义人性思想也在大肆滋生,并与集体主义人性思想争夺思想阵地。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极端利己主义,弘扬集体主义,逐渐压缩狭隘利己主义的生存空间。
第三,在制度建设层面,应持续反对官员特权传统,消减官本位和臣民文化。腐败现象的出现和蔓延原因固然很多,其中制度特别是公务员管理制度现代化的缺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邓小平早就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11]在西方国家,公务员仅仅被看作一种服务公众的普通职业,并不具有凌驾于社会其他职业之上的特权。中国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应为此而努力。首先,要改革党管干部的具体操作机制,在公务员招聘、晋升、退出以及薪酬管理方面奉行公开、平等、竞争和功绩的原则,在公务员薪资和福利管理方面规范化和透明化,逐渐消除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特权色彩,从而消除公众的官员神秘感和官员崇拜的社会心理。其次,探索公务员职业道德法制化的途径。公务员职业道德是一种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道德,是公务员在工作场合或履行公职过程中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它与公务员的“个人道德”(私德)对应。这两种道德不能相互替代和混淆,否则就会出现以权谋私、情法不分或人情高于法律法规的违法违纪问题。为此,必须实现公务员职业道德的法制化,这是西方廉政文化建设的共同取向。我国应该探索进行“公务员职业道德法”的立法工作,各种公务员岗位都应制订相应的公务员工作岗位操作规程,对正常和违规操作进行区分和界定,并实行公开承诺制。
第四,在机构建设层面,应建立透明政府和限权政府,消除暗箱政治和专权传统。腐败官员为了为所欲为、滥用公共权力,往往热衷于暗箱操作。我国自古就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传统,官员盲目自大,自认为能力超强,可以“为”民做主,完全排斥了民众的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现代廉政理念大力提倡公开的政府原则,因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世界各国无不力图打造透明政府。只要政府的一切规章制度和行为规则透明化了,政府就不敢不廉政,而社会民众也没有必要拉关系办事,日久就会逐渐消除人情礼制传统的消极影响,培育现代廉政文化的制度理性、公开公正和尚廉崇洁心态。打造透明政府,主要做到“三透明”:“一是政府组织透明,即政府机关的设置体系公开,各个政府机关的职能分工明确,政府机关的办事规则与要求以及政府公务人员的职权范围透明;二是政府管理透明,即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活动过程及其具体结果公之于众;再次,政府决策透明,即政府决策的方式、步骤、顺序应向社会公众公开以及政府决策结果公开”[12]。
第五,在行为规范层面,应建立各级各类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礼物赠送、收受底线的量化标准,消解人情送礼风俗和面子文化心理对公务员队伍的侵蚀。中国是个人情大国,人情关系不仅广泛存在于私人生活领域,还广泛渗透于我国公共生活领域,造成人情关系对公共权力行使的不当干预。如何让人情关系回归私人领域,让制度理性控制公共生活领域,对我国的廉政理念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弄清人情和礼物的关系。在腐败文化那里,礼物往往成为不当人情关系的表征和实物形式,是迎合部分腐败官员私欲的利器;公共生活也不是一味排斥任何礼物,有时礼物仅仅具有礼节性的意义,例如在一些外交场合。但实际上两者的关系更为复杂。如果不建立各级各类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礼物赠送、收受底线的量化标准,公务人员就把握不住赠送和收受礼物的限度。例如英国《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规定:“禁止公共机构的任何人员在与公共机构有关的任何交往过程中收受或者要求收受、同意接收任何形式的礼物、贷款、费用、酬劳或利益。”[13]195美国规定,公务员接受300美元以上的礼品就须做出说明,并将礼品上交[13]204。我国也不妨建立类似的标准。
[1] (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
[2] 孙关宏.中国政治学:科学与人文的探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92-393.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40.
[4] 赵建国.中国式关系批判[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5] 宋庆森.卿本佳人 奈何做贼——腐败现象的文化批判[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
[6] 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7] 梁启超.新民说[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65.
[8] (英)迈克·彭,等.中国人的心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194.
[9] 冯必扬.人情社会与契约社会——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J].社会科学,2011(9):74.
[10] 徐世杰.清除封建思想影响的长期性[J].理论探讨,1989(5):105.
[11] 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93.
[12] 王勇.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原则探究——从行政法学的视野[J].行政法学研究,2012(2):80.
[13] 麻承照.廉政文化概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张 璠)
On Traditional Negative Culture Obstructing to Modern Integrity Ideas and Resolution Strategies
HOU Baolong, WANG Fangyou
(Politics Department, 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Bengbu, Anhui 233100, China)
The modern integrity ideas are the premises of the integrity culture, and they are made of nine consciousnesses. Their theory bases are as follows: the theory of evil human nature is their idea presupposition, authoritarian fear is the strong motivation, and the social public opinions constitute their ultimate foundation.
modern integrity ideas; traditional negative culture; cultural anti-corruption
2014-08-19
安徽省社科联课题“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廉政文化建设的负面影响与消解研究”(A2014037);安徽科技学院校级课题“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廉政文化建设的负面影响与消解研究”(SRC2014362)
侯保龙(1973-),男,安徽临泉县人,安徽科技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和廉政文化;王方友(972-),男,安徽庐江县人,安徽科技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G122
A
1674-0297(2015)01-0005-04